中国情人的三度出场
邵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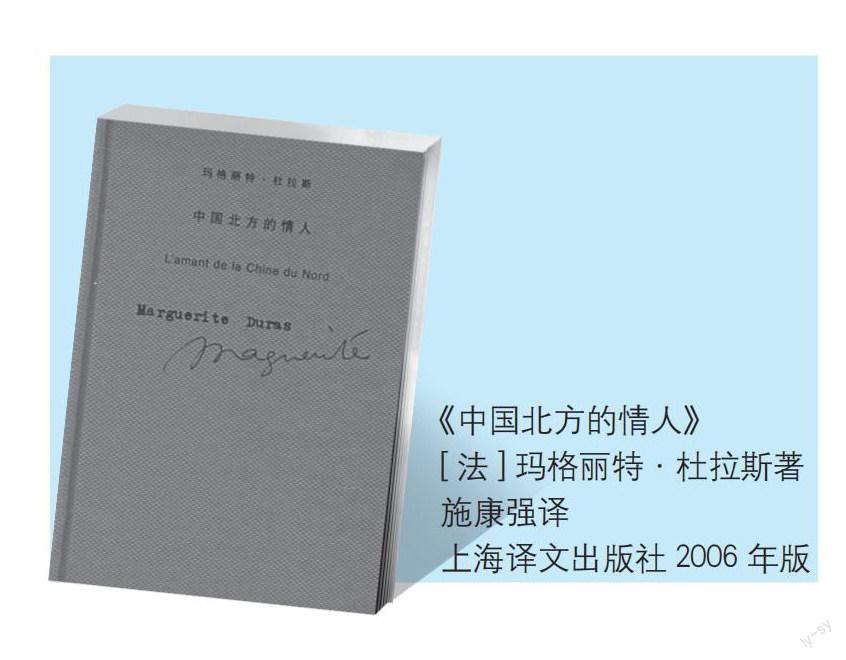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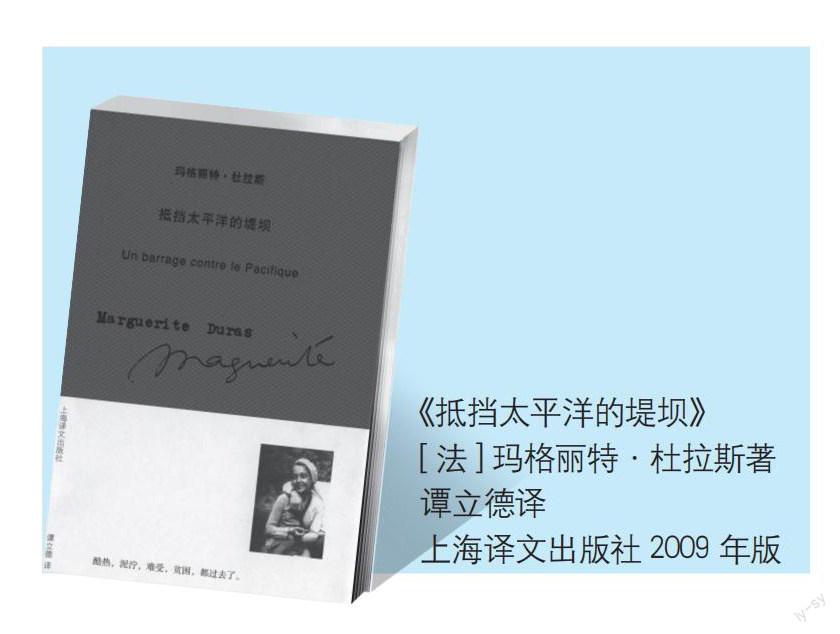

一
这是法属交趾支那的一家穷白人,由于没有向地籍管理局官员行贿,穷寡妇十年的辛苦积蓄化为乌有,租借了一块完全不能种植的盐碱地。她动员当地人修筑了一条堤坝,但须臾间就被太平洋(暹罗湾)的海潮冲垮,还欠了银行一屁股的贷款利息。
穷寡妇有一双儿女,儿子约瑟夫二十,女儿苏珊十七,长得都还不错。穷寡妇便在女儿身上打主意,想用她来钓个金龟婿,改变一家子的穷困命运。
在云壤的一家餐厅里,他们邂逅了一个年轻人,看起来有二十五岁,身穿米灰色柞丝绸西服,手上戴着一枚极美的钻戒,还拥有一辆黑色利穆新汽车,莫里斯·莱昂-博来牌的,配有一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司机。餐厅老板巴尔老爹介绍说:“那车是从北方来的做橡胶生意的那个家伙的,比这里的可有钱。”穷寡妇默默地、瞠目结舌地凝视着那枚钻戒,然后鼓励女儿主动一点。苏珊朝年轻人嫣然一笑,他便走过来邀请她跳舞。全家人都定睛看着他的钻戒,其价值相当于全部租借地的总和。
这是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以下简称《堤坝》)里中国情人的首度出场(她那时还没敢明确说情人是中国人)。他叫若先生,肩窄臂短,身材中等偏下,整洁讲究,文质彬彬,说话的声音温柔优雅,一双小手保养得很好,有点瘦削,相当漂亮。不过在这家穷白人眼里,他蠢笨如牛,长相丑陋,活像个猴儿,只是有钱而已。他看上了苏珊,从此展开了追求,那辆黑色豪车每天都停在她家的吊脚楼前。
现在,母亲心急如焚,期待着若先生的求婚。她盘算着,苏珊一旦完婚,若先生就会给她重新修筑堤坝的钱(她预计这堤坝比其他的要大两倍,并用水泥柱子加固),还有修缮完吊脚楼,换屋顶,另买一辆小汽车,以及让约瑟夫修整牙的钱。这桩婚事必须成功,母亲这么说。这甚至是他们走出平原的唯一机会。如果这件事不成功,那么,这就同堤坝一样,是又一次的失败。
不过,母亲看上若先生的财富,想以之来改变自家的困境,却又看不起若先生的种族,所以只希望他能向女儿求婚,却绝不允许女儿同他睡觉。约瑟夫更是瞧他不起,对他粗鲁无礼,厌恶至极,让他心生恐惧。苏珊也没有动过心,甚至都没拥抱过他,只是奉母命勾搭他,以骗取他的钱财。最后一次见面,他想吻她,她仿佛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连忙挣脱,叫了起来:“我不能。跟您在一起,我永远也不能。”
本来,白人女孩相对拥有性自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睡觉。苏珊后来把自己给了出去,一个白人混混阿哥斯迪,她母亲知道了也没说啥。但是对于有色人种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最重要的是您要娶她。要么就娶她,要么就完,没有别的选择。并不是我们不让她和她想要的人睡觉,而是您,如果您要和她睡觉,您就必须娶她。这就是我们骂您是畜生的方式。而且,即便我们接受了所有的东西,留声机、香槟酒,这对您也无济于事。”约瑟夫如此“点拨”若先生。
然而,若先生受制于父亲的严命,他的父亲对他有别的安排,得娶门当户对的富家女子,所以他知道他不能娶苏珊。在若先生所处的社会阶层,认为女孩在婚前要洁身自好,保持处女之身,但是他也很清楚,在其他阶层,情况并非如此,有钱阶层的男人,可以玩弄贫困阶层的女人。于是他想利用自己的财富,与穷白人家的苏珊睡觉。
这样,就展开了一场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在这本书里,天平毫无疑问地倾向于前者。
若先生送了苏珊许多礼物,连衣裙、化妆品、留声机,换取她洗澡时打开浴室門,以便他看到她全裸的样子。而后他又得陇望蜀,对苏珊说,如果她同意和他一起到城里旅行,一起待三天,一起看电影,他保证不碰她,他就会送给她一枚钻戒。他果真把钻戒带来了,一共三枚,任凭苏珊挑选一枚。苏珊选了一枚最贵的,大概价值二万法郎,抵得上她家的吊脚楼。虽然约瑟夫不同意若先生的计划,但若先生还是把钻戒给了苏珊,希望以大方换取他们的回心转意。
苏珊把钻戒给了母亲。她母亲藏好了钻戒,然后开始痛揍苏珊,用全身力气揍她。她骂苏珊是烂货,怀疑她跟他睡了。这不是因为睡觉,而是不该跟他睡;跟白人睡没关系,跟他睡就是耻辱。苏珊辩称没有睡过,但她母亲还是揍她,因为她要留下钻戒,不可能再归还原主,这让她心里不好受,简直像是受了羞辱,必须通过揍苏珊来洗刷。
为了造那条徒劳无益的堤坝,母亲欠了银行一万五千法郎。现在她有了这枚钻戒,便指望卖了钻戒来还债,即使女儿没跟若先生睡过觉,她也不可能再把钻戒还他了。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她是有权留下一枚戒指的,拒绝接受也许会大错特错。送给你戒指却不接受,这简直不可思议。况且对于若先生来说,一枚戒指实在不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谁可能有相反的意见呢?
他们留下了若先生的钻戒,却让苏珊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他是不可能娶苏珊的。要是他敢要回戒指,那可就有点滑稽了。但他竟想要回自己的钻戒,苏珊坦诚而自然地笑了,笑他头脑简单,天真无知,以为他们可能把这枚戒指还给他。虽然他很富有,但跟他们相比,他只是个小蠢蛋。这枚钻戒现在属于他们了,就如同他们已经吃了、消化了一样,就像这戒指已经同他们的血肉之躯融为一体,难以再拿回来了。况且,若先生太虚弱,分量太轻了,约瑟夫只要一拳,就会把他击得粉碎。
“要是我要拿回来呢?”
“您不能。现在,您该走了。”
“你们太缺德了。”
“我们就是这样。您该走了。”
苏珊跟她哥哥说起此事。“他跟我说我们很缺德。”
约瑟夫又一次笑了起来。“哦,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
是的,他们确实是这样的。近五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谁可能有相反的意见呢?
二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司机穿着白色制服。是啊,这就是我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车厢大得就像一个小房间似的。在那部利穆新轿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看着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米灰色柞丝绸西服。所以,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过的那样在云壤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渡船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之下。”
这是杜拉斯《情人》(1984)里中国情人的再度出场(这次她明确说情人是中国人,却不再赋予他以任何名字)。他也来自北方,也穿着米灰色柞丝绸西服,也有一辆黑色利穆新汽车,也是莫里斯·莱昂-博来牌的,也有穿着白色制服的司机。“我书”指的就是《堤坝》,“我过去写过的”指的就是上述《堤坝》开头的那个情节。杜拉斯在此纠正了三十四年前的叙述,把邂逅中国情人的地点从云壤的餐厅挪到沙沥的渡船,时间也挪到了放弃租借地后的两三年。她想要由此重新展开一个故事,那个关于有钱的中国情人的故事。
中国情人来自中国的北方,不再是做橡胶生意的了,而是房地产金融家的独子,母亲已经过世。父亲不许他同这个白人女孩结婚,况且她家在当地名声也不好,他难以违抗父命而娶她。这与若先生的处境是一样的。这次的中国情人风度翩翩,也是刚从巴黎回来,吸英国纸烟,喝威士忌酒,手上不再戴有那枚大钻戒,豪车及司机则一如往昔。他家也住在沙沥,在河岸上有一幢大宅,平台镶有蓝色琉璃砖。据说它至今还在那里。他对她一往情深,他不惜花费金钱,也给了她一枚钻戒。但他心里有所惧怕,说话怯生生的,声音和手都会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
这次她的年龄小了一岁半,是一个十五岁半的小萝莉,但已有了耽于逸乐的面孔,知道如何激发男人的欲念。他则比她大十二岁,算起来应该是二十七岁,比若先生大了两岁。她与苏珊完全不同,在渡船上,她就已经想要他了,当然也想要他的钱。她喜欢他的文雅,他的温柔甘美,他的孱弱胆小;也深知他的胆怯,知道得由自己主动,事情得由她来决定,他已落入她的掌中。“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当然还要到堤岸的小屋里去做爱。她隐隐约约地想以此来炫耀自己,让中学里蔑视她的同学刮目相看。她这种近乎受包养的生活方式,让人想起了洛蒂的《菊子夫人》(1887),只不过角色分配已经完全相反。她父母当初之所以来到殖民地,就是因为受了洛蒂作品的蛊惑,这对他们不啻是个莫大的讽刺。
母亲仍是小学教师,但这次升为了校长。她还是一个穷寡妇,还是购置了租借地,在柬埔寨的波雷诺(位于云壤附近,距唝吥八十公里),是没法种植的盐碱地,最后只能完全放弃,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但这次母亲没动钻戒的脑筋,没想着用它去换钱还债,而是以女儿的订婚指环,替她向校方争取出入自由。母亲在等着他向女儿求婚,又知道他是完全没希望的,只期待女儿能借此搞到钱。母亲怀疑她已跟他睡过,以后就要嫁不出去了,发起疯来仍会痛揍她。“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还是《堤坝》里的那种调调,但这次却是无奈的谎言。母亲要是知道了真情,一定会把她给杀掉的。
这次又添出了一个哥哥,但两个哥哥都粗鲁无礼,欺负这个柔弱的中国人。在高档的中国饭店,在城里最讲究的地方,他请她的家人吃饭。他们埋头大吃大喝,吃相简直前所未见,但是从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根本看也不去看他,就像他是看不见的,吃完了站起来就走,没有人说一声谢谢,就因为他不是白人。
归根结底,这还是那场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但比起三十四年前的《堤坝》来,天平已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因为男女主角已经揭竿而起。
现在的她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写,是因为母亲和两个哥哥都已不在人世,所以她现在写母亲是这么容易,写得这么长,可以一直寫下去,母亲已经变成文从字顺的流畅文字了。“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由此反推,《堤坝》里写若先生给了苏珊留声机和钻戒,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甚至连接吻都做不到,那纯粹是骗骗还活着的母亲和兄弟的吧。“关于我家里这些人,我已经写得不少,我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母亲和兄弟还活在人世……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
不过,在中国情人的二度出场里,她对自己感情的性质仍难以完全把握—也许种族因素还是残留了一点点。与中国情人相处一年半后,轮船载着她全家回法国。轮船起航了,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她不能够爱他,她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她也没有当着她的母亲、她的小哥哥的面,表示她心里的痛苦,什么表示也没有。后来,独自一人时,她真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上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她,她为此感到痛苦,觉得自己有罪,自己对不起他。但她又说,自从她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她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她知道。
也许,一直要等到数十年后,昔日的中国情人来到巴黎,往她的公寓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仍像过去一样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她才能够确定自己感情的性质,然后重写这个中国情人的故事?要知道,她根据《堤坝》改编的话剧《伊甸园影院》,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奥赛剧院首演,仍沿袭了《堤坝》里的主要情节。决定性的转变,也许在那个电话之后才发生?还是因为有了扬?
此外,我想就连她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次她重写的,不仅仅是中国情人的故事,也是拉拉和洛丽塔的故事,那些二三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故事。她的年龄,正介乎拉拉与洛丽塔之间。“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也用自己的女性身份证明,女孩的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她遇到的是什么人才是关键。又过了二十年,马尔克斯在《苦妓回忆录》中,用他非凡的想象力再次论证了这一点。
三
这是湄公河上的渡船。渡船上有搭载本地人的大客车,长长的黑色的莫里斯·莱昂-博来牌汽车,有中国北方的情人们在船上眺望风景。渡船离岸后,女孩走下大客车。她观看黑色汽车里那个衣着讲究的中国人。他从黑色汽车上走下来,他不是上本书里的那个男子,他是另一个中国人,二十七岁,来自中国东北。他跟上本书里的那一个有所不同,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他更漂亮,更健康。他比上本书里的男子更“上镜”。面对女孩,他也不那么腼腆。一个高大的中国人,他有中国北方男人的那种白皮肤。风度优雅。穿着米灰色柞丝绸西服和红棕色英国皮鞋,那是西贡年轻银行家喜欢的打扮。这次他不再是做橡胶生意的,或房地产金融家的独子,而是百年银行家世家的长子,全部庞大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这是杜拉斯《中国北方的情人》(1991)里中国情人的三度出场。“上本书”指的自然是《情人》。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场景还是那个场景,汽车还是那辆汽车,女孩还是那个女孩,情人还是那个情人,仍然来自中国北方,手上仍戴着那枚大钻戒,但不再像《堤坝》里那么丑陋,也不再如《情人》里那般孱弱,而是变成了一个高富帅,风度更优雅,气场更强大,还有一种华丽的中国式的温柔,身躯瘦长、灵活、奇妙、完美,金黄色的皮肤丝绸般柔软,身体周围飘着欧洲古龙水的香味,以及淡淡的鸦片和柞丝绸的气味,丝绸上和皮肤上的龙涎香的气味。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的好东西,似乎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而她,依旧是上本书里的那个女孩,年龄则更小一些,十五岁都未满—在撰于翌年的《扬·安德烈亚·斯泰奈》(1992)里,更说“那时我十四岁,甚至还不到”。从十七岁,到十五岁半,到十四岁未满,女孩的年龄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洛丽塔了。
女孩从头就吃定了他,说他全身都漂亮,从未见过他这么美。他半真半假地要她承认,她是为了他的钱而来,但她不能撒谎:“不是的。这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在渡船上,没想到钱。完全没有。一点没有,就跟钱这东西不存在一样。”她拿起他的手,看着,吻上去:“对于我,是你那双手……我那时这么以为。我好像看到你动手脱掉我的连衣裙,把我剥光了站在你面前,由你观看。”可见,欲念从头就已存在。当然,金钱仍是重要目标。“她独自与钱待在一起,面对这一笔她从外人那里成功得到的钱,她被自己感动了。她与母亲合谋做了这件事,她们取到了—钱。”这次她终于说出了“我爱你”,平生第一次说出了这句话,为她与他的关系定下了基调,而在《堤坝》中只有若先生说过。“是放学的时间。女孩走到他跟前。一言不发,当着众多行人和学生,他们久久相拥相吻,忘了一切。”这次女孩已爱得如此坦荡大方,令她的同学和路人都刮目相看了。
这次,母亲对中国情人彬彬有礼,完全接受他的安排和做法:“您应该知道,先生,您爱的即便是条狗,那也是神圣的。人有这个权利—它和生存的权利一样神圣—有权不对任何人解释这种爱。”但对女儿的感情,她还是有所保留,她盘问女儿:“那么……你去见他不仅仅是为了钱。”“不是……不仅仅是。”她惊讶,突然感到痛苦:“莫不是你对他有了情……”“也许吧,是的。”但这次女大不由娘,母亲已控制不住了,更不要说是痛揍了。那枚几乎是《堤坝》中心道具的钻戒,在这本书中依然出现了,但就像在《情人》里那样,它已不再具有重要性,卖钻石也已经变成了别人家的故事。
大哥这次叫皮埃尔(作者大哥的名字),一如既往地粗鲁无礼,却再也占不了上风,反被中国人视若无物。中国人与女孩共舞,大哥怪笑讥讽,嘲笑他俩不般配。中国人放开女孩,走到大哥面前,细细打量他的脸。大哥害怕了:“说到打架,我随时奉陪。”中国人开怀大笑:“我练过功夫。我总是事先告知。”母亲也害怕了:“先生,您别在意,他喝醉了……”大哥越来越害怕:“难道我没有权利笑吗?”中国人笑着说:“没有。”大哥远离中国人坐下。母亲心有余悸,声音发颤:“您真的练过中国功夫,先生?”中国人笑了:“没有,从来没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哥:“真奇怪,见了您儿子就想揍他一顿。”母亲说他喝醉了,“这孩子欠揍”,请中国人原谅他。大哥看到危险过去了,于是高声说:“臭中国人。”对比下《堤坝》里的约瑟夫、《情人》里的大哥,这次他真的惨不忍睹。
在高档的中国饭店,在堤岸最讲究的地方,中国人请她全家吃饭。这家人点菜的唯一标准,就是“本店特别推荐”,也就是那些最昂贵的菜,烤鸭、烤虾、鱼翅羹……他们狼吞虎咽,吃相夸张,吃法相同,谁也顾不上说话。侍者用小碟子递上账单,中国人掏出一沓钞票,把其中八张放进碟子。这笔数目使众人目瞪口呆,母亲和大哥面面相觑。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与《情人》里的同样场面比较,人物关系简直是天壤之别。
情人的父亲年迈、高贵、有钱,是个极为强势的中国富翁。他出钱,他买通,他的情报网遍布殖民地,他什么都知道,包括与她家有关的一切。他宁可看到儿子去死,也不允许他娶这个白人女孩,就连做他的情妇也不行;他了解女孩母亲的困境,还知道她家有个败家子;他知道她大哥哪天几点在几号码头上船,也知道她家哪天会坐邮轮回法国;他知道女孩的确切年龄,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但他能把事情摆平,保护儿子不受指控,所以这次情人并不担心:“假如警察找到我们……我可是未成年人……”“我可能会关押两三天……我不太清楚。我父亲会出钱的,没那么严重。”中国富翁出手大方,礼数周到,愿意給她母亲许多钱,让她摆脱欠银行的债务;他把她家的什么钱都付了,包括她家回法国的旅费、大哥在鸦片烟馆的欠账,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她家滚出殖民地,别再来烦他的儿子。
歸根结底,这仍是种族与财富的竞争,穷白人与富有色人种的博弈,穷殖民者与富被殖民者的角斗;但比起七年前的《情人》来,天平已完全倾向于后者;比起四十一年前的《堤坝》来,更可以说已恍如隔世了。
杜拉斯第三度写中国情人,是因为刚获知了他的死讯。“有人告诉我他已死去多年。那是在一九九○年五月,也就是说一年以前。我从未想到他已经死去。人家还告诉我,他葬在沙沥,那所蓝色房子依然存在,归他家族和子女居住。又说在沙沥,他因善良和质朴备受爱戴,他在晚年变得非常虔诚……我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他的身体、肌肤、阳具、双手都会死亡。整整一年,我又回到昔年乘坐渡船过湄公河的时光。”这一次给她带来了更大的震动,比写《情人》时的那次刺激更大,因为那时至少中国情人还在,但现在随着中国情人的死去,一段往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自己的人生似乎也随之而去。“我放弃了手头正在做的工作。我写下中国北方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在《情人》里,这个故事还没有写进去,那时候时间不够。写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写作带来的狂喜。我有一年工夫沉浸在这部小说里,全身心陷入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之中……我又成为写小说的作家。”第三次写完中国情人后又过了五年,她留下了扬,跟着中国情人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从《堤坝》到《情人》再到《中国北方的情人》,杜拉斯的后半辈子,漫长的四十余年间,中国情人在她的小说里三度出场。“玛格丽特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讲述这个和情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她用尽了各种办法。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叙述出来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她那时还没敢让情人成为中国人……必须等到老了,无所顾忌了,等到足够的一把年纪,玛格丽特才敢写情人不是一个种族的,甚至在最后那本书的题目里还写了他的来处:‘中国北方的情人。’”“有个当地的情人是件非常有损体面的事情……一直到生命垂暮,玛格丽特才让别人—同时也让自己—相信她曾经爱过中国人。”(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
有意思且有象征意味的是,在《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破天荒头一遭,中国情人对女孩讲起了中国,讲起了中国历史和近现代史,尽管讲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但看得出杜拉斯经过了恶补。“你的那些个中国故事,我可是百听不厌……”女孩说出的,也许正是杜拉斯彼时的心声。女孩告诉中国情人,中学里没人跟她说话,因为他们怕中国人。“为什么怕中国人?”“中国人没有被殖民化,他们在这里像他们在美国一样,到处流动。人家抓不住他们,没法叫他们归顺。人家不甘心啊。”中国人一笑。她跟他一起笑,望着他,这个明显的事实令她佩服不已:“真是这样的。这也不要紧。不要紧。”—这当然不要紧,不仅不要紧,而且还很正常。在这本书里,借助可能晚年才获知的“明显的事实”,杜拉斯率先让海外华侨“去殖民化”了。另一个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是,中国功夫在这本书里也登场了,而这,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力量的象征。
在传记层面上,中国情人的哪一度出场会更“真实”呢?或换言之更符合杜拉斯的人生轨迹呢?首度出场,他是被极度丑化了;三度出场,他是被高度美化了(她的传记作者说它大大损害了前一部,她自己则坚持说它比前一部更真实);二度出场,看上去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也许可能性最大?但谁知道呢。也许三度出场,都有一些真实,也有许多虚构,合在一起,才是全貌?
而在观念层面上,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一年,中国人在杜拉斯乃至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概也像杜拉斯小说里三度出场的中国情人一样,在缓慢然而有力地发生着变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