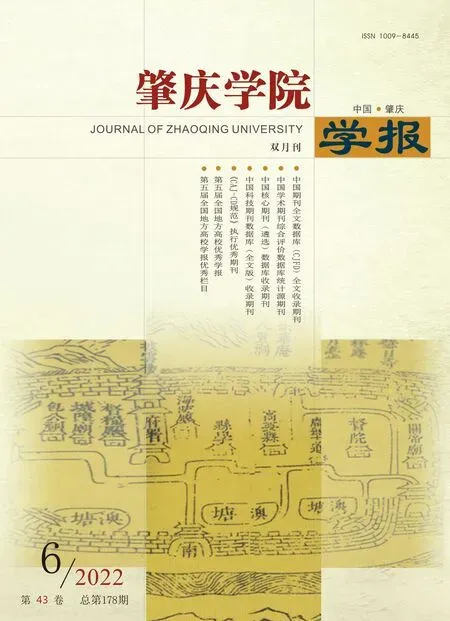“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
——“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陈红旗
(海南大学 人文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作为中国左翼文艺界的核心组织,“左联”不仅开展了很多政治和文艺活动,还吸收、扶持和培养了440位盟员[1],吸纳和创办了诸多刊物,前者如《大众文艺》《萌芽》《拓荒者》《文艺研究》,后者有《艺术月刊》《巴尔底山》《五一特刊》《文化斗争》《沙仑》《世界文化》《文艺新闻》《文学生活》《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世界文化》《秘书处消息》《文学》《文学月报》《文化月报》《新诗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无名文艺》《文艺》《春光》《新语林》《东流》《文学新地》等刊物。另有一些左翼文艺刊物虽然不是由“左联”直接创办,但与“左联”或“左联”盟员有着直接关系,如《译文》《文学新地》《文艺讲座》《杂文》《海燕》《夜莺》《文学丛报》《作家》《文学界》《光明》《现实文学》《中流》《小说家》《文艺科学》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刊物将不断地催动着左翼文学运动、文艺论战的发生,并将源源不断的左翼文学作品努力推出。
一、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必然性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在国民党利用经济、政治、法律、机构和舆论围追堵截、极力打压的情状下,作为新兴媒介的“左联”刊物能够存活和运作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成功。那么,被官方意识形态贬斥和国民党文艺审查机构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出版物”,何以会获得读者尤其是青年的认同乃至青睐呢?除了源于左翼文艺界几乎吸纳了当时创作水平最高的进步作家之外,还在于“左联”刊物登载了大量反映劳苦大众痛苦心声和反抗精神的具有先锋性的左翼文学作品,更在于推出了几场影响深远的文艺论争,这些论争几乎吸引了文坛的所有注意力。以是观之,没有“左联”刊物就没有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和兴盛。
“左联”成立后的一大功绩是努力推行大众文艺运动,至于“为什么推?”“推什么?”“怎么推?”这些问题需要一一加以讨论。“左联”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是必然的,它应和了“左联”的行动总纲领:“(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2]这里的“新兴阶级”意指无产阶级,反对压迫必须号召劳苦大众起来抗争,号召的媒介是“左联”刊物,实现的路径是辨明学理、规定任务、明确目标、分清主次和具体实施:“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具体而言,“实行作品和批评的大众化,以及现在这些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且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3]“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革命大众作品的形式及方法的研究,和欧化文艺作品的大众化问题的研究”[4]。
此后,“左联”依据相应的纲领、原则、决议和制度,在《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月刊》《巴尔底山》《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文艺月报》和《文学》(月刊)上刊载了诸多关涉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追求文学话语权力,培养“化大众”的工农作家,借鉴民间文艺形式,明确大众文艺内容和形式,进而传播大众文艺(其实是左翼文学)作品。
二、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内容与形式
借助诸多刊物的推动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比如在《大众文艺》被吸纳为“左联”机关刊物之后,“左联”随即着手对该刊进行改造,推出了两期“新兴文学专号”,并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的诸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少年大众”和“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四个栏目,来推动文艺大众化诸问题的讨论。
冯润璋认为,文艺是解放人类痛苦的武器之一,而追求自身乃至人类的解放是大众文艺的责任[5]995。按照这种思路,推行文艺大众化和大众文艺运动的必要性不言自明。沈端先认为“普罗文学的大众化”这个题目本身就有语病,因为普罗文学或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他引用列宁的观点强调说,“艺术,非使大众理解不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他觉得“普罗文学”的具体问题只有两个:“1.制作大众性的作品。2.组织的地将上述作品提供给广大的群众。”[6]郭沫若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强调大众文艺应追求“无产文艺的通俗化”,且教导大众“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就是“大众文艺的使命”[7]632。陶晶孙认为,大众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文艺大众化的本意不是以“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还要暴露大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8]。冯乃超认为,文学大众化问题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文学深入群众”的问题:首先要让大众理解或曰看得懂,其次是怎样“使我们的作品送到群众里面去”[9];同时,应该增加大众文艺的组织性,因为“大众文艺过去是文艺的垃圾桶,现在应该克服这样的无组织性”[10]。郑伯奇强调: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核心是使大众“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大众所欢迎的文学“无条件的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文学”;大众文学作家应该“由大众中间出身”“至少这是原则”;中国当时所要求的大众文学是“真正的启蒙文学”[11]636-638。王独清断言大众文艺的任务是“结合新兴阶级底感情,意志,思想,更予以发扬,光大,使得以加增它本身实际斗争的力量”,且主要还是在“大众化文艺的制作”[12]。洪灵菲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内容就是创作普罗文学,他主张充分利用大众所理解和喜欢的旧形式,来书写社会进步意识和无产大众的斗争生活[13],进而创造“合于大众所要出的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的新的艺术形式”[14]。郁达夫主张“文艺是必须要带着普遍的大众性的”,让大众“看得懂”和“能了解”才是正确态度,但这并不等于“文艺的卑劣化”,即不能迎合社会“变态浅薄的心理”,或把文艺作为“做官发财的阶梯”[15]。此外,“左联”于1932年在《北斗》上开设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征文”[16]栏目,参与讨论的陈望道、魏金枝、杜衡、陶晶孙、顾凤城、潘梓年、叶以群、张天翼、叶沉、郑振铎、沈起予一致认为文学大众化是不成问题的。而通过《大众文艺》上的这场讨论,“左联”内部明确了推进文艺大众化和大众文艺运动的根由,接下来就是如何建构大众文艺的内容、形式、审美趣味,乃至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路径等问题了。
“左联”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沈端先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视为“普洛列塔利亚艺术运动”,认为它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配合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应该突破“布尔乔亚艺术形式范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艺术形式并更深广地发展到真正的工农大众中间去,如果左翼作家没有意识到大众文艺已经改变了以往的艺术本质,依然局囿在资产阶级艺术形式范围内来研究和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那么后者在现实层面上是无从解决的[17]。他认定“普洛艺术运动”的终极目的是完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使其教化目标不应局限在文学范围,而应扩展到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的扩大”,所以其“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艺术力量来提高无产阶级文化和政治水准,“用大众化了的Agi-pro的艺术,将大众的感情和意志思想结合起来,而使他们正确地走上革命的道程”[18]。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大众文艺问题”的实质是要发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19]2,“普洛大众文艺”的写作目的是“鼓动”和“组织”阶级斗争,为了“理解阶级制度之下的人生”,为了反对“青天白日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推行“苏维埃的革命文艺运动”,而其实现路径是“俗话文学革命运动”“街头文学运动”“工农通信运动”“自我批评的运动”,尤其是“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20]25-42。华汉认为,“普罗文艺”本质上属于千百万工农大众,其“应该大众化”毫无问题,作为“一般人所说的离艺术性很远的无产阶级的宣传鼓动文学”,它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之新的必要,由新的艺术条件所产生出来的新艺术形态”,是一种“能够鼓动和宣传千百万工农一致起来向他们的敌人肉搏血战”的文艺武器,因此其产生的路径只能是“生活浸润在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中”,或者说,“只有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的集团生活中,才能产生出有集团性的大众化的作品”[21]。郭沫若认为大众文艺的服务对象是“无产大众”,所以实现文艺大众化的秘诀就是走向“通俗”[7]632。他号召无产文艺要实现大众化,并告诫左翼文艺界要“扛举”无产文艺“教导大众的使命”就必须与大众接近,而能与大众接近的艺术形式有绘画、戏剧、影戏、音乐、锣鼓、皮簧等[22]。郑伯奇认为,可以借助表演短剧、巡回图书馆、创作民谣、编排戏剧等方式,助力大众文艺的“建设”[11]637-638。钱杏邨则表示大众文艺的读者对象是“劳动大众”,因此大众文艺的实现路径只能是“把我们的文艺发展到工农大众中去”[23]。
当然,如此并不意味着迎合、媚悦大众,否则就等于消解了大众文艺倡导者的主体性和专业性,加之限于大众受教育水平过低和缺乏政治支持等因素的制约,追求“大规模”[24]640大众化并不现实,而鲁迅的提醒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也等于指出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寻求国家资源、政治势力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乃至直接推动。
“左联”明确了大众文艺应该写什么,即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创作内容,以及由谁来写的问题。冯润璋认为,大众文艺要反映大众的意志、情感和要求[5]995。瞿秋白认为,大众文艺要写工人民众和一切题材,“要从无产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20]31。冯雪峰认为,文艺大众化和大众文艺不是反帝斗争中的“临时工作”,也不专限于反帝的任务,但因为日寇侵略中国,要促进大众文艺运动和进行反帝的群众动员,这确实是“革命的斗争的大众文艺的试验的最好机会”,所以应该号召一切革命文艺家和革命文艺青年,用大众文艺的手段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统治阶级的卖国和对于民众的压迫与欺骗[25]24。周扬认为,大众文艺应该描写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26]424。阳翰笙认为,大众文艺不仅要有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的内容,还应确立无产阶级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乃至恋爱观[27]435。关于创作主体的问题,瞿秋白侧重由大众自身来写文艺作品,茅盾则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用大众语言创作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至于作者不一定非得从无产大众中产生[28]。周扬赞同瞿秋白的意见,认为文学大众化“最要紧的,是要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他以苏联、德国成功培养工人作家的事例为依据,力主“左联”“迫切”推进“工农通信运动”,让工农通信员成为“普罗文学的生力军”,以便“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作品”能早日登上“文学的殿堂”[26]425。郑伯奇也认为文艺大众化的任务是在工农大众中培养“真正的普洛作家”[29]429,这就等于强调无产阶级作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众文艺作家。
“左联”探讨了文艺大众化的形式问题,明确了大众文艺须借鉴各种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则,也形成了创建新的大众文艺形式的基本理念。冯雪峰强调,大众文艺的首要原则须是“大众看得懂,听得懂,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能够接受”,所以要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如唱本、歌谣、连环图画、故事小说、话剧、小调、宣传画、画报、漫画、传单等[25]24-26。瞿秋白主张,多吸纳旧式大众文艺形式,要运用浅近的叙述方法,要运用说书、滩簧、小唱、文明戏等形式,但又不能盲目模仿,更要创造新的大众文艺形式[19]5-6;因为识字的人太少,所以大众文艺要写旧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要写“和口头文学离得很近的作品”,要远离“感情主义”“个人主义”“团圆主义”“脸谱主义”的模式,至于语用问题,他认为用周朝话、明朝话、“五四式的白话”(“骡子话”)、章回体的白话写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能成为普洛文艺”,只有用读出来听得懂的“现代话”——“更浅的普通俗语”来写,才能成就“普洛大众文艺”“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20]16-35。周扬认为,文学大众化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文字”就成了先决问题,“之乎者也”的文言和“五四式”的白话都不是劳苦大众能看懂的,所以要创造大众能够理解的“新的文字”,要采用Sketches、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诵剧、小调、唱本、说书、报告文学等大众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26]423-424。阳翰笙认为,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主要指向语言和体裁问题,前者应采用“普通话”“活着的人说的活话”——“大众日常所说的绝对白话”,后者应运用大众言语创造出报告文学、朗诵诗歌、壁报小说、墙头小说和群众合唱的剧本等“新的形式”[27]435-437。关于创作方法,田汉认为瞿秋白提出的“普洛现实主义”有着机械唯物论的“毛病”,已经被国际普罗文化组织所扬弃,他号召“为获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斗争”[30]。魏金枝主张把文学形式简洁化,须剥下假道学的假面具和教训式的布告体,用电影、图书、戏剧、音乐等来“补助文学的功用”[31]。杜衡认为,大众文艺于形式上应使用口语而不作骈文、律诗,但与其压低水平线去迎合大众,还不如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32]。叶以群认为,文学大众化最先应解决的是形式问题,如要实现文学句法与说话句法的一致性,要采用歌谣、时调、章回小说、连环图画等大众熟悉和喜欢的体裁;同时,形式和内容不可或分,所以文学大众化不单单在于形式问题,还必须实现“内容底大众化”[33]。这里,叶以群对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理解,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形式之争画上了句号。
此后,1934年中国文坛爆发了大众语论争,“左联”主编的《文学》月刊积极参与这次论争,并刊载了《大众语论》(陈望道)、《大众语与大众文化》(高觉敷)、《大众语问题》(许杰)、《大众语万岁》(吴稚晖)、《文学万岁》(傅东华)、《大众语文学解》(傅东华)、《大众语运动的多面性》(江)、《大众语文学的“遗产”》(新)、《大众语文学有历史吗?》(傅东华)、《对于<大众语文学解〉的一点疑问》(傅东华)等文章。但这些文章主要回应和反驳了文言复古派认为欧化的白话文深奥难解的观点,强调白话文还不够“白”,进而主张推进大众语建设。至于大众文艺是否应该采用大众语,在“左联”看来已经无须讨论,其焦点业已转为怎么建设大众语的问题。
三、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意义
通过“左联”刊物作为介体的有效运作,“左联”明确了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的意义。鲁迅认为,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要先有为大众着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如此才能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24]639,即消除封建思想观念之于大众的坏影响。郑伯奇认为文艺大众化有助于建构“中国大众自己的文学”,有助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也有助于在工农大众中培养无产阶级作家,而“新的大众文学”可以表现工农大众“新的革命的感情”[29]430-431。瞿秋白认为,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卖国行径,宣传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因为这样才可以组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革命战争”[34],这就等于明示了大众文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意义。
“左联”组织和参与的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实现了一次对“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白话文欧化运动的反思和梳理,这其中固然有着非理性批判的成分,但确实指出了“五四式白话”过于晦涩和“五四”新文学疏离大众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益严酷、紧张的情状下,新文学被赋予了承担启蒙民众、传播革命精神的历史重任,所以倡导文艺大众化和大众文艺运动的主张也就应运而生。“文艺大众化的论争参与了新的话语主体和新的文学实践的建构过程,论争的参与者从各自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动因出发,试图把文学话语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理念中,从而形成了意见交锋。”[35]这种交锋明确了文艺大众化的目的、任务、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实现了新文学思想主题和话语的嬗变,这为抗战文学的合流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制定做好了前期准备。
透过文艺大众化讨论可知,左翼报刊之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的意义不言而喻。报纸、杂志并非仅仅作为工业社会中的一种传播工具而存在,借助它们的现代性元素,左翼作者们可以把形而下的东西转化为形而上的东西呈现出来,可以把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探索转化为心灵的探寻,可以将民主、自由、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等价值理念及其现实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播撒开来,可以令激愤等理性或非理性的革命情绪和反抗现实秩序的政治诉求通过审美之维的塑形之后及时传播出去,并表征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否定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性。
在某种意义上,报纸、杂志作为印刷技术颠覆性革新后的产物,它们借助现代化工程的力量和相对“完满”的技术合理性,在把反抗社会现实转化为革命意识形态时,很轻松地就突破了统治阶级政治独裁和专制制度的拘囿,并轻松地将左翼的价值观投射出去乃至转为接受者的政治需求,这是两个层次的过程:1.让读者知悉无产大众物质极度缺失、生存极为艰难的现实情状;2.无产者要获得生存和基本的物质满足,必须释放个体被压抑的生命能量,并将其升华为本阶级乃至所有被压迫者的需求。正是在阅读过程中,当年的读者发现还有一个庞大的与自己命运类似的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劳苦大众一直存在着。这同样是“左联”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种意义所在。
同理,正是报纸、杂志不断推出这种“发现”,才令反抗潜能和革命需求以几何级的规模快速增长,才令更多的人产生了变革社会既成制度的诉求,并努力将这种诉求转为现实行为。如此,正义、斗争、自由、革命、解放的观念就会在一个它们过去根本不可能如此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基础上,获得它们的普世性、合理性和组织性,甚至可以说,没有报刊和杂志的兴盛就没有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而左翼文艺界左翼精神的颓圮同样与报刊、杂志旨趣的嬗变直接相关。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