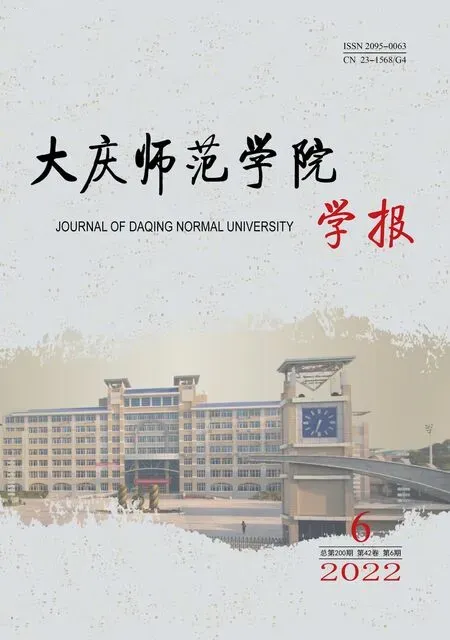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海防实践与思想简析
——兼论近代中国海防变革之迟滞
李光和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耆英(1790—1858),字介春,正蓝旗人,清宗室贵族,道光朝重臣。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对外交涉活动及其思想对晚清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海防实践及思想开启了中国海防战略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序幕。鸦片战争前期,耆英在奉天积极部署海防,提出“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战略防御措施;鸦片战争之后,耆英在江南整军经武,提出“水陆并重”“改革水师定制”“师夷长技”“整顿吏治、融官民于一体”等海防变革举措与思想。但拘囿于时局及其对西方的认识不足,鸦片战争时期耆英的海防变革举措及其思想,方开其端、即告夭折。学术界关于耆英的研究,多侧重于鸦片战争后的对外交涉活动、思想及其影响等方面,于其海防实践与海防思想,则鲜有专文论及。本文依据目前所见的相关档案史料,拟就上述问题做一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盛京将军任上的备战:“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海防战守措施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清廷千里海疆同时告警。道光帝谕令沿海各地督抚、将军加强戒备,积极设防。时任盛京将军的耆英在奉天督率官兵进行积极的军事防御,加紧海防部署,提出了“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措施。
(一)增调兵力,充实海防。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奉天为清朝之根本重地,然驻军数量不多,海防兵力相当单薄。奉天西部的锦州、山海关为京津出入之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驻守兵力不足1千人。耆英奏请从黑龙江、吉林分调官兵5000名进驻锦州、山海关,并多次亲赴锦州、山海关巡察督视,激励将士,积极备战。奉天南部的旅顺口、金州、覆州、盖州各岛屿为海上入陆必经之道,但防守空虚,如旅顺仅有兵力几百人,耆英在该处增派“水师官兵800名,水手100名,战船10余只”,(1)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54页。以严防守。1840年8月,有数只英军船舰游弋于金州、覆州、盖州各岛屿洋面,耆英“先期于省城官兵内,挑选精兵1000名兼程前往,拣派各协领赴各要隘口岸分头堵防”。(2)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55页。在覆州,“增拨官兵300名,协领等官6名,分布安设,并择高埠岭6处,分置官兵,协同民社300名,协力堵防”,又“增调省城马队600名,省城官兵300名驻扎盖州”。(3)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54页。金州战略地位最为重要,为奉天门户旅顺所属第一隘口,耆英在此布重兵设防,“付发官兵400名,民役154名,乡勇1533名,统计兵役乡勇2087名……调熊岳兵200名,酌分工营,于金州城南距红土崖海口八里之丁国寨地方驻扎,以处援引”。(4)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98页。如此,耆英于奉天南路的布防,以旅顺为重心,以金州为前沿哨所,层层设兵堵防,形成相互援引之势。
(二)添铸枪炮,加固口岸。耆英认为“以守为战”海防战略实施的成功,除了增兵设防外,最为重要的是海防设施的坚固与枪炮武器的充裕。由于国家承平日久,奉天与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存在着营务懈弛,炮台废弃,枪械匮乏的情形。耆英深以此为忧,战端已起,以废旧之武器装备,荒芜之炮台防御工事,又如何言守言战?加紧备战,当务之急乃加固口岸防御工事与添铸器械两大要事。(5)参见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99页。就战略位置而言,南部旅顺口当为要冲,其存失关系到奉天全省乃至整个东北的安危。耆英调集大量民夫兵士加紧修葺该口废弃炮台,“除旧有大炮三处外,于临岸新建炮台一座”,(6)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99页。并整固加厚口岸阵地,“深挖壕堑,增埴高垒,以避矢石”,又指出“土堡为御敌要法,扎饬旗民地方官,除沿海口已挖壕外,壕土堆置之处乃须加倍添厚”。(7)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56页。旅顺口之外的金州、覆州、盖州及西部的锦州、山海关等隘口的防御工事均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重新修葺与整固,其防御能力得到了加强。针对各口岸的枪械废缺,耆英下令将奉天省城库存的枪炮器械分运各处,同时开设制造局,铸造新的火炮、抬枪与鸟枪等,以资补卫。据统计,南部的旅顺、金州、覆州、盖州等共计新添“火炮44尊,抬枪130竿,鸟枪980竿”。(8)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97页。西部的锦州、山海关、宁远也增添“5千斤重炮2尊,4千斤炮11尊,3千斤炮3尊”,(9)参见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98页。并抬枪鸟枪若干。如此,各口岸驻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充实与改善。
除上述措施之外,耆英还督促各地方官雇募乡勇、民勇,组织团练,“每100名设头目1人,副头目2人,约束教演”,(10)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65页。严加训练,并号召沿海岛屿居民,自动组织起来,“自卫身家,自固藩篱”,(11)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66页。利用民间的力量协助保卫海疆。
客观地讲,在“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耆英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军事部署使奉天的海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各口岸的防御力量与战斗力也大为加强。当然这只是相对于鸦片战争之前奉天的防守空虚与营务废弛而言,若因此而夸大其防御的功能与作用,则又是一种虚言妄语,这种单纯的海陆口岸防御是不可能有效应对如英国这样的近代海上强敌的。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闽、粤与江南地域,奉天地界洋面,曾有零星的英军船舰过往游弋,是为探测线路和索购食物,并没有与当地清军发生战事。如不幸而战,毫无悬念,其结局应与闽、粤、江南战场一样悲壮。
耆英的“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战守措施,是鸦片战争时期沿海督抚们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海防战略。鸦片战争初期,两广总督林则徐提出“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的御敌方略;两江总督裕谦也曾指出:“出洋击逐,实非万全之策,惟有坚持定见,以御为剿,以守为攻,严防要隘,……或诱彼登岸,更可大加剿洗。”(12)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97页。山东巡抚托浑布在山东的海防部署亦大体相似。这种共性之存在,从思想根源来追溯,一是耆英等清朝的封疆大吏们本能地继承了宋、明以来“重陆轻海,以陆守为主”的海防传统,这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与文化观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来自于他们对当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有限认识,认为清军海上力量不如英军,而英军近陆作战能力则远逊于清军,取长避短,乃是务实明智之策。耆英于是提出,“以严防守,惟思便于水者,必不利于陆,该夷匪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断不容其肆意滋扰”。(13)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54页。林则徐认为:“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利于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14)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17页。诸多清代沿海督抚坚信英军只能海战不能陆战,如果能设法诱敌登岸,则可容易制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15)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79页。正是建立在这种对中英军队海陆战能力肤浅认识的基础上,众督抚自认为寻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以耆英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自视为当然且充满信心的战守举措,应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处于封建末代王朝的整体惰性与虚骄自大氛围熏染中的晚清大臣(纵使开明、果决如林则徐)不可能超越历史的传统,更何况从闭关自守中刚刚探出头来,他们对自身历史的反省与对西方的认识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深化的过程。若罔顾历史场景仅以今人的标准对这一防守措施一味地苛求或指责,就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二、两江总督任上的求变:“水陆并重、师夷长技”的海防变革举措
鸦片战争,英军的船坚利炮使清廷的东南海防设施与海防力量遭受沉重的摧毁和致命的打击,海防几乎全面崩溃。1842年10月,道光帝谕令沿海将军督抚筹议海防善后事宜:“现在英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此办法,并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别讲究?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搅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16)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57页。各地将军督抚纷起响应,就善后防务建言建策,形成战后清政府的一股短暂的筹议整饬海防热潮。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在江南积极部署海防善后,重建被摧毁的防务设施,加强整顿败落的海防力量;提出水陆并重的御守原则以改变传统的“以守为战”模式;倡导师法西方先进的造船铸炮技术,改革水师定制;同时认为修明政治,整顿吏治,以结民心,乃是海防巩固、国防安全的重要措施。
(一)修复、修筑江海防务设施,提出水陆并重的御守原则
江苏省的防务工程设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吴淞口为由海入江必经之处,是上海的门户,也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一直是江苏的海防重点。其西岸土塘共设火炮134位,东岸土塘及炮台设有火炮20位。但经吴淞一战,“庐舍炮台,尽成瓦砾,海塘椿石,亦多裂断,原设铁炮,有敲断两耳、钉塞火门者,有推堕海中者,种种蹂躏情形,竟至目不忍视”。(17)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5—466页。耆英督率军民重建吴淞炮台,添置火炮,同时“于吴淞口东西两岸,设立吴淞、川沙水师参将二员,守口巡洋。又于江北通州地方,设立狼山镇总兵一员,与江南之福山营游击,对峙于江海之交”。(18)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07页。除吴淞之外,在长江隘口江阴的鹅鼻嘴、丹徒的圌山及象山、焦山、燕子矶等处建设炮台,添置战船。由此,战后江苏省的防务设施有所改善,防务力量得以巩固与加强。
除了修复、修筑江海防务设施之外,耆英还提出改变传统的“以守为战”的御守之策,提出水陆并重的御守思想。1843年2月,漕运总督李湘芬上奏道光,认为对付夷人,“拒水不如拒之于陆……,而我之陆路可加倍胜之”。(19)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64页。这是一种清军长于陆而短于水的传统观点,但鸦片战争的事实已证明,清军无论是水战还是陆战,均无法与英军抗衡。耆英根据对当时中英两国军事实力的综合分析,提出“舍水守陆,则水师废,水师废,则不必夷人之或有反复,即沿海土盗已足为患,至设守必当水陆并重,不可偏废”。(20)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94页。因此,在他看来,若株守口岸,或凭城自固,只能处处被动挨打。耆英分析了海防、江防与城防三者的利弊优劣,“从来议海防者,以出海会哨,毋使入港为上策,循塘拒守,勿使登岸为中策,出水列阵,勿使近城为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即为无策”。(21)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09页。他强调上策、中策与下策即海防、江防与城防三者相结合,其中当以海防最为重要。考虑到当时清军水师的落后,“海防未备”尚不能与对手争锋海洋的现实,“不得不先议江防”,而“防江之法,当以训练舟师,巡哨于江海之交”。(22)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43页。这里耆英所指的防江之法,不是单纯在江岸隘口设置炮台,布置军队,被动等待敌人的进攻,而是更注重训练舟师,日夜巡哨,主动拒敌于江海相交之区。从长远来看,海防之道必须突破原来的固守海岸的传统防守之藩篱,尽快训练出新的强大水师,出海会哨,与敌搏击于大洋之中。耆英提出的这种水陆并重的海防思想,是对传统的“以守为战”御守之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突破。
(二)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铸炮技术,改革水师定制
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清军陈旧落后的武器与英军的“船坚利炮”相差太过悬殊。亲历江浙战场的钦差大臣耆英,对此感受尤深,“彼之长技,在于大炮、火箭二项,其接仗时黑夷潜伏舱中,身有所护目有所见,装药下子,又甚便捷,白夷置身桅巅,用测远镜窥定,高下远近,号令施放,故能无发不中。火箭即随炮飞来,燃烧甚烈,我之炮力,本不如彼炮之致远,……我炮施放,一出之后,彼炮则接踵而来,官兵无容身之地,不及装药再放,是彼炮可以连环接续,而我一炮止有一出,发而不中,等诸无炮”。(23)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71页。“夷之不能制者”,不但在其“炮火猛烈,机法灵巧,连环轰击,竟日不休”,而且在于其“舟如城坚,铜墙铁壁,舵手纯熟,驾驶如飞”。(24)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35页。英军“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内地师船不能相敌……,两载以来,迄无成效,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25)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35页。耆英指出清军的战败,“并非战之不利,亦非防之不严”,(26)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71页。而是中英双方军队武器相差太过悬殊。基于这种对中英之间实力的评判,战后的耆英特别留心英军的“船坚利炮”。早在南京谈判时,耆英等曾登上英旗舰“皋华丽”号,向朴鼎查、马儒翰及其舰上的官兵仔细探询旗舰的构造、材料及火炮、枪械等武器情况,并让随从详细纪录。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耆英对此向道光皇帝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南京条约》签订不久,耆英即上奏道光帝:“抚夷本属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熟筹善后,原期经久”,“收拾民心,训练兵卒,造船铸炮,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而切要机宜,则在慎选守令将备,使之养教训练,庶民志固,兵气振,三年有勇,七年即戎。……不战屈夷,久安长治,全在于斯……,惟有卧薪尝胆,力挽颓靡”。(27)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324页。他认为“抚夷”仅仅是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经此鸦片一役,朝廷上下须深刻反省,“卧薪尝胆”“徐图自强”,而抵御外侮、巩固海防的当务之急,首先必须立足于练兵铸炮,“筹议江海防守,自应首先购求战船枪炮”。(28)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10页。他上书建议朝廷专门设立苏宝局,制造新式枪炮、战船,仿造西式火轮船,学习西方军事知识,并将福建贡生丁拱辰的《演炮图说》“刊刻颁行各营,令明白文义之人,与各弁兵先行口讲指画,日夕讲解,俾知放炮之法,然后照式试演,以利军用”。(29)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431页。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耆英派员将江、粤二省收买洋枪共二十二杆并相关配件等物呈进朝廷,(30)参见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06页。以期引起清廷对这种新式先进武器的重视。耆英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主张师法西方先进的造船铸炮技术,改进和研制船舰炮械,以近代先进的武器来武装军队,这是其海防思想的进步。
鉴于清廷水师的腐败、落后,耆英进一步提出“整顿水师,改革定制”。他曾提请增设外海水师,配备新造水师战船,平素严加训练,定期出海会哨,以抵御海上强敌。同时,奏请朝廷改变传统的水师营章程,“水师营以讲求操驾舟楫,辨识风云沙线,熟悉大炮鸟枪为首务,不重骑射……专取水务枪炮,即骑射稍有生疏,亦准录用,并将赴部之员,由部先行阅看鸟枪,如果精熟有准,再准引见,以挽颓风而肃戎行”。(31)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33页。道光帝对此表示赞同,批示:“若不变通,难收实效。”(32)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24页。谕令兵部“妥议简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办,以肃军政”,(33)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24页。兵部遵旨奏报“变通水师章程折”,强调“外海水师,迥非陆路可比,……是以定例于出洋弁兵,责成该管官留心试看,各验水务缓急,技艺高下,分别等第,本不得专较骑射,即将备千把等官,遇有升迁,亦一体考验各项技艺,以定黜陟”。(34)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47页。对于兵部所议“变通水师章程”,道光帝即予允准,以上谕的形式钦定,“以后水师考拔提升即以是否精熟枪炮为去取”。(35)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547页。耆英提出变通传统水师选拔章程,强调注重水师官兵的基本战斗素质、新式技能的培养与训练,适应了近代战争变化的需要,可谓传统海军向近代海军转变的先声。
(三)内结民心,以御外侮
海防的巩固与民心离向关系密切。耆英指出海防失利、鸦片战争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情涣散,内不自安。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军进攻广东的番禺、浙江的余姚、江苏的镇江等地时,当地的部分下层民众或冷漠观火,或趁机揭竿起事,更有甚者给英军提供食物,收集情报,指引道路等等。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呢?耆英认为根源在于清政府自身的内政失修和吏治腐败。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曾上奏道光帝,揭露江苏地方吏治腐败之四端:“如催科之术,则以帮费为名,捐款为词,假手书役,……此民情之所涣者一也”;“如遇有词讼,悉置高阁,棍徒因而无忌,讼师因而播弄,书役因而舞弊,案中生案,枝外生枝,设遇人命案件,未经相验,先索陋规,住离数里者,指为临佑,毫无见闻者,佥为干证,虽路毙必累多家,遇缉凶则人皆正犯,不将附近村庄资产荡尽不已,此民情之所涣者二也”;“迨至盗贼穷发,无不仰勒讳报,若不遵依,可欺者加以刑赫,难欺者指为捏报,辗转提讯,令其废时失事,盗贼并无一获,事主已受累无穷,……更可恶者,捕役豢窃得赃,令其择殷售卖,指赃为证,或牵入案中,或得钱私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此民情之所涣者三也”;“营员兵丁……籍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钱,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牧放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件,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相讼,……此民情之所涣者四也”。(36)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第468—469页。地方官吏极端腐败,造成了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此实不能御寇之由”。(37)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第468—469页。在鸦片战争的善后事宜中,耆英认为修明政治,整顿吏治,以结民心是海防巩固的重要措施,这些认识在当时无疑是远见卓识。整顿吏治,“首重慎选守令”,先“从约束书役,清厘词讼,严拿盗贼,作为下手功夫”,而后“渐推至于省刑罚,薄税敛”,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以收人心”。如此,“俾良民为我所用,莠民亦化为良民,虽有强敌当前,而众志成城,彼亦无能矣”。英人以“区区有限之游魂,安敢轻视我无尽之兵民”?(38)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66页。
梳理鸦片战争后期两江总督任上耆英的海防善后举措与思想,其要旨有三点:一是提出水陆并重的御守原则,甚至强调海防重于陆防;二是倡导师敌长技,制造枪船炮舰,注重训练舟师,御敌于大洋之中;三是从整顿吏治与安抚民生的角度来思考海防建设。以“水陆并重”取代“以守为战”,摆脱单纯被动的陆上防御,这是海防战略布局的改变,可谓中国近代海权意识的萌芽;把造船制炮,训练远洋舟师与师敌长技相联结,这是武器装备与军队的近代化的肇始;将清廷吏治腐败而造成国内矛盾的激化与巩固海防、抵御外侮相联系,指出海防巩固与抵御外侮成功的政治前提是整饬腐败吏治,废除苛捐杂税,安抚民生,以趋至于官民相融一体,这是鸦片战后耆英海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期耆英海防战略举措及其观念的改变,是对清军在战争中战事失利的反思及重新评估中英双方实力而产生的。这一改变与反思,却并非孤例。历经鸦片战争前段,后被道光帝革职查办的林则徐亦经历过这一痛苦的思变过程。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惨败,促使林则徐反省传统的“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之不足,指出一味强调陆守,以守为战,“譬如两人对弈,人行两步,而我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39)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40)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82页。由此,林则徐萌发了建立外洋水军的思想:“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41)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92页。1841年4月,林则徐上奏朝廷提出变更“重陆轻海”的传统海防方略,转而学习西方的造船铸炮技术,创建船炮水军以及“以民制夷”。(42)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组编:《林则徐集 奏稿》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85页。其内容与鸦片战争后期耆英之海防变革思想惊人的相似。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是强硬的主战派,耆英却是软柔的主和派代表,政见行事,泾渭分明,然而在对鸦片战争中清军遭遇失败后的反思中,均能突破传统海陆防守之藩篱,倡导师夷长技,提出建立强大的远洋作战水师之构想,可谓殊途同归。耆英、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关于海防战略之举措与构想,尽管并未付诸实施,却为中国近代海防与近代海军的建构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原料。
三、两广总督任上的懈怠:海防变革迟滞之溯疑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国防形势面临“千古未有变局”之开端,然而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底,道光帝倡导的喧嚣一时的海防善后筹议热潮,并未真正推动清政府开启振衰起弊、整军经武的变革之路。耆英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授两江总督,颁钦差大臣关防;1844—1848年(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职高权重、膺封疆之任的耆英本应有充分机会兑实其前期所提出的具有近代萌芽性质的海防变革之举措与思想,而阅其在鸦片战争后十年的宦海历程,于此几无踪迹可循。溯其迁延迟滞之缘,一是耆英的懈怠与“机变”,二是耆英对西洋认识的片面与不足。
(一)耆英的懈怠与“机变”
1844年3月(道光二十四年),道光帝调两江总督耆英为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负责与法、美等国谈判,先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45—1848年(道光二十五至二十八年),广州城民夷冲突频繁,身任粤督的耆英回旋于民夷之间,东突西蹴,左右迎逢。(43)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七),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3925—3927页。从表象看耆英似乎分身乏术,无暇兑实其前期海防变革举措与思想,而若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道光帝对海防变革态度变化来考量,耆英之惰,则另有一重意蕴: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南京条约》割地赔款的屈辱,曾激起道光帝“卧薪尝胆、整军经武”的雄心,在战后曾掀起“借取西洋武器”、筹议海防的短暂浪潮。而随着英军逐步退出海疆、粤东“抚局”议成,道光帝即刻谕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约庞大的军费开支;并谕示各地海防的善后重整、练兵制器当因地而宜,量力而行,宜戒因势兴奢靡浪费之风。(44)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377页整军经武需要浩繁的军费开支,因而道光帝在战事稍平之后,对于添枪铸炮表现出相当的谨慎。1842年11月祁唝因仿造火轮船,“内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上书提议从澳门雇觅“夷匠”,道光帝即刻下旨阻止——“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45)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470—2471页。1843年7月,耆英曾进呈新式击发枪,请求仿造,道光帝覆批曰:“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叹也。”(46)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3册,第832—833页。1844年2月,耆英又进呈朝廷“洋枪二十二杆”,并奏请开局“逐渐仿造”时,道光帝仅朱批对各地进呈洋枪“酌留之”,而于耆英等所请仿造之事,则无一字作覆。(47)参见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3册,第907页显然,此时的道光帝对于“整革海防”“师西洋器”的态度已发生改变。而“多智术”、敏于时断、思虑精密的耆英,(48)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亦颇能体会上意:“各省置备一切,所请军需,业已不少,不特新制者皆化为乌有,即本有之军装船只炮台,亦多毁失,从新做起,经费实属不赀。臣虽不敢因惜费而误大计,惟制造若不精良,诚如训谕,临时安能得力?而欲期精良,又非尅期可以奏功,器械即已精良,而兵多未练,有械仍同无械。”(49)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3册,第471页。这份奏折讲出了耆英对于练兵制器,需时耗费,非短期所能奏功的忧虑,也折射出耆英原来海防变革之意的游移。1844年6月,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夕,当美使顾盛欲将“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造船图纸、电话机、望远镜”等礼物送交给耆英并请他代为转呈大清皇帝时,耆英却拒绝了。(50)参见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21—126页。有意思的是,半年前的耆英还在派人极力搜罗、购买洋枪以进呈朝廷,此次居然拒绝转呈美使顾盛送给道光帝的礼物,前后之反差,精明的耆英若不是准确地揣测“上意”的变化,是绝不敢冒险擅作主张的。1844年10月,当法使拉萼尼向耆英建议清政府“派官赴伊国,学习修船铸炮水战兵法”,(51)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5页。耆英回应:“船炮水战,用之各有其宜,便于西洋者,不必便于中国,且中国于洋船洋炮亦均能仿造,更无庸远赴弗兰西学习。”(52)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1册,第79页。这种对待西方“船坚利炮”的认知与态度与其先前所主张的“师夷长技”截然相别。思想懈怠随之的是行动上的迁延与保守:耆英莅任两广总督,治粤七年,于粤东海防建设除恢复旧观之外,仅于1846年倡建九龙城寨,(53)参见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页。而新建九龙城寨,从建筑结构、防御设施和防御功能等来看,与鸦片战争以前清朝传统的海防军事防御工事几无任何改造与更新。(54)参见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1页。其他如“水陆并重”“师夷长技”“改革水师”“整顿吏治”之振衰革新之举措则几无涉及。(55)参见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010—3011页。另一方面,《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道光帝对退敌抚夷有功的耆英褒奖有加,赐予其“有胆有识”“有守有为”两块牌匾。(5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0页。同时,对在粤东继续善后“抚局”的耆英在谕旨中反复叮嘱其要与外夷议订“万年和好之约”,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5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七),第3925—3927页。道光帝的意图,主持对外交涉的耆英十分清楚,“力持和局”“避免重启衅端”,不仅关乎朝局之稳、国之安危,也关系到其本人的荣辱得失。1847年12月5日,“黄竹岐案件”发生,耆英屈服于英方的压力,斩首4位村民,判斩、绞监候各1人,充军流放3人,杖一百徒三年6人。(58)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441页。为维持中外相安,不惜残民媚外,此所作为,与其在两江总督任上所倡导的整顿吏治、联民抗夷自相矛盾。一时朝野舆情喧嚣,而耆英的诉由是“兵端不可开,夷情不能不顺”。(59)参见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371页。事实上,“黄竹岐案件”的处理,没有影响耆英的仕途青云,道光帝称耆英忍辱负重,乃“忠贤智良之臣”。(60)参见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2页。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耆英离职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拜文渊阁大学士,权势荣耀臻于至极。
以上观之,两广总督任上的耆英对海防变革的疏离懈怠,表面看来是其浸身于粤东抚局,分身乏术,背后逻辑则是鸦片战争前后道光帝态度由重海事而倾于抚局的转向。耆英的“机变”迎合了道光帝的好恶,也换得了道光朝晚期海疆的短时苟安。耆英也因此踏上了其仕途的巅峰,而那场本该启动的海防变革却黯然湮没。历史的经验是任何一场政治或军事变革,离不开具有坚定改革意志又握有政治权力的能臣名吏主导,更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倾力支持。然而,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处于政治权力中枢的耆英随上意而“机变”;乾纲独断的道光帝恶闻变革,因循苟且。鸦片战争时期海防变革之夭折,也就成为理所当然。
(二)耆英对西洋认识上的片面与不足
海防变革思想的产生源于耆英对鸦片战争情势的判断及其对西方有一定的认识;而海防变革举措实施之夭折则又缘于其对西方认识的不足,这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由于身兼对外交涉的使命,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接触西人次数较多、时间较长的清廷封疆大员。其比较留意西人西事,在两广总督任上,也曾组织专人搜集西人信息。耆英对其时“西人之性”、西方的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西医和西方的宗教均有相当的认识。耆英认为“西洋各国以通商为性命”,(61)参见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1册,第456页。因此,“妥议税饷章程”,裁减海关陋规,以商制之;(62)参见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第1册,第13页。他认识到“船坚利炮”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此提倡学习西方的枪炮船械制造技术,整军经武,以图自强,把学习西方先进的技艺同国家的自强相联系;督粤期间,美国新教传教士兼医生伯驾医好了折磨耆英二十多年的皮肤顽疾,耆英赠给伯驾“妙手回春”“寿世济人”匾额,并对西医产生兴趣,带领所属官员多次到西医局看病,甚至于对西方传教士在广州所开办的医院和慈善机构持默许和肯定态度;对于西方的宗教,耆英认为天主教从其性质来看,应该说是劝人弃恶从善的,与异端邪教迥不相同,(63)参见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黄庆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73—375页。因而在基督教弛禁问题上持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耆英对西方的军事、经济乃至医学、宗教都有一定的了解,而其认识的功利性、实用性也是很明显的。
然而中西交冲之初,拘囿于时代,耆英对西洋的认识又是相当不足与片面的。如其对西医的赞誉与对西方宗教的宽容,负责主持外交的耆英,则是将二者作为融通交涉中外双方感情的工具,而至于西医之科学原理,宗教背后之近代人文底蕴,耆英则茫然不知;又于商贸而言,耆英则认为:“夷性嗜利尚气,而其嗜利之心更胜于尚气,是以不远数万里,历涉重洋,来粤贸易。凡属有利可图之处,即小有不平,亦隐忍不敢较量。粤中习俗,无论在官兵役,小民及肩挑步担、驾船受雇之人,即因其不敢较而侮弄之,又艳其得利厚而勒索之。大小文武官员,于内外之防,过于严峻,一切微文细故,无不持之过急,视之过卑,夷情不能上达,城狐社鼠,即假借为威。于是浮费日增,夷利日薄,随启走私之弊。弁兵胥役,又从而得规卖放,我之利权日渐下移,夷之得值更不如前。利薄则气生,以至逞其骄傲,酿成变乱。”(6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编》,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333页。耆英既揭露了当时清政府吏治的腐败,也认识到从事商业贸易、追求商业利益是外人谋生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目标,同时指出因追求商业利润的受阻,英国不惜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种见识,部分地触及到了西方商贸真实的具象,是对传统商贸认识的某些突破,但程度有限。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背后对外扩张侵略的本质,因此,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亦只是通过开放通商口岸,实施妥协的优惠税则来满足西方的要求,以求“一劳永逸”的“和平”。而于振衰起弊,图强自为,则松缓迟滞。即如耆英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英之间武器装备的巨大差异,亦试图探究其背后缘由:“内地制造枪炮之法,本系传自西洋,而恒不及西洋,每欲得其器,而审其所以”,“铁制精良,熔炼纯熟,其灵巧便捷非内地所能制造,细访西洋各国制造之法,不惜工本,勤加选择,稍不如式,即另行铸造,务求利用而后已,此内地之火器之所以恒不及西洋也”。(65)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3册,第832—833页。然而耆英根本无法认识到其伏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科学体系,更无法了解到其背后强大的工业及其综合国力的支撑。震羡于西洋之“船坚炮利”,一方面主“抚”,另一方面强调“海防之变革”与“师夷之长技”。“言和”“抚夷”原来被认为是权宜之计,其后竟变成了经久之谋;整军经武,谋图自强原被认为是经久之谋,其后竟变成了权宜之计,甚至转眼成了历史的过眼云烟。正是因为耆英等人对西洋认识的浅陋不足,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唤起清廷上层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强劲、长久的改弦更张、励精图治的内在动能,近代海防变革也失去了知耻后勇、迎头赶上的大好时机。
四、余论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时期,耆英的海防战略举措经历了由“以守为战”到“水陆并重”的变化。同时,在鸦片战争后期,耆英提出了“师夷长技”“改革水师”“整顿吏治”以推动海防建设的举措;这一变化却并非孤例,鸦片战争后期的林则徐也提出变更传统的重陆轻海的海防方略,学习西方的造船铸炮技术,创建船炮水军以及“以民制夷”;著名学者魏源在他编撰的《海国图志》中总结了“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66)魏源:《魏源全集》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7页。他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67)魏源:《魏源全集》第4册,第1页。向西方学习武器装备技术,尤其是水师装备技术和军队建设方法,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远洋之师。遗憾的是耆英、林则徐及魏源等人的这些可贵海防战略举措与思想探索,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却并没有付诸实践。溯其缘由,除了历史活动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耆英等所思所行的局限之外,从整体上考察,还与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历史的环境相关: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创痛,清政府本应卧薪尝胆、振作有为,总结战争失败的沉重教训,吸纳耆英、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海防变革举措与思想,以启动一场深刻的政治、军事变革。事实却是,鸦片战争时期少数人弥足珍贵的海防变革思想认识,既没有汇聚成社会群体思潮,更没有化成政治军事实践的精神动力。《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68)中国历史学会编:《软尘私议》,《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9页。人们茫然无措,一切都恢复到鸦片战争前之旧观。这就是充斥道光朝官场弥久不散的“因循苟且”“尸位素餐”的懈怠之气;“结党营私”“贪渎成风”的污浊之气;“闭目塞听”“盲目自大”的慵懒虚骄之气。沈垚曾经这样评论道光年间以来的清末社会风气:“今日风气,备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时之轻薄,明昌、贞佑时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69)沈垚:《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湖州:吴兴刘氏嘉业堂出版社,1927年,第48页。世风的败落与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注定了鸦片战争前后海防变革方开其端、转瞬夭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