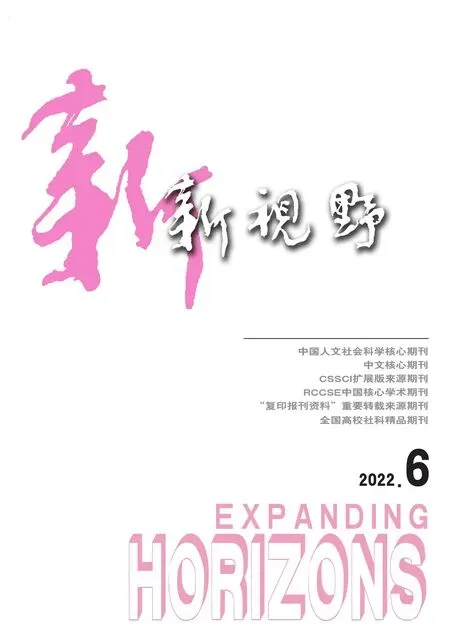透视资本世界的假象: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当代价值
文/刘召峰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1]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3]笔者以为,把握资本的特性、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需要我们透视资本世界的假象,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 资本世界的假象:从《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说起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以便说明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过高度肯定性的评价。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缺乏好感的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质疑:“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果真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倘若我们查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可以发现,上面这段话的译文原本是这样的:“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5]其实,在《共产党宣言》的更早译本中,用词也有“造成”与“创造”的差别。[6]此时,我们有必要追问:究竟是资产阶级“造成的生产力”,还是它“创造的生产力”?
上述经典语句的德文原文是:Die Bourgeoisie hat in ihrer kaum hundertjhrigen Klassenherrschaft massenhaftere und kolossalere Produktionskrfte geschaffen als alle vergangenen Generationen zusammen.[7]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翻译“hat……geschaffen”。“hat……geschaffen”是完成时,其动词原形是schaffen.schaffen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动词,在《资本论》中也有出现:Die Zirkulation oder der Warenaustausch schafft keinen Wert(意为: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8]据《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schaffen的首要义项是:创作,创造,塑造。[9]应该说,“创造的生产力”这一翻译没有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译文相比,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译文更加准确。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的确有“资产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之类的思想,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这一思想。
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0]笔者以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之类的思想,不属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而是“已经过时了”。恩格斯曾经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论断,否定《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论断,否定《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这一具体观点。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商品化了,活劳动被并入资本,劳动过程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属于资本的活动,所以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1]也就是说,资本具有明显的神秘性质。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还指出了这种神秘性质是如何加深的:(1)单个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社会结合,不属于工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同工人相对立;(2)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3)劳动条件的社会性质,表现为不依赖工人而存在的、完全独立的东西,表现为资本的存在方式,从而表现为与工人无关的、由资本家安排的东西。[12]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Fetischismus)。[1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谈到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好像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内在的生产力”)。[14]不仅如此,“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不需要代价的自然要素,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15]
立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高度,我们要说:“比过去一切世代加起来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并非资产阶级“创造”的,而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所以,这“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才看起来好像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资产阶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是容易迷惑人的假象,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透视的假象!为了透视资本世界的假象,我们需要对资本的本性、神秘性质(拜物教性质)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
二 资本世界:充斥着假象的颠倒世界
“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代表人物有托马斯·霍吉斯金、威廉·汤普森等)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对此,马克思批判道:“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作为资本的性质。”[16]在此,马克思想强调的是:“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17]资本不是物,而是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剥削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过,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佃农、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都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18]用这“共有的事实”还无法准确说明资本关系的独特性。
虽然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业已存在,但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关系并非建立在“商品交换”之上;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是“外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实现了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内在结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剖析了不同“剥削方式”的重大差别:“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19]马克思在此指明了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表现形式上的重大差别: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必要劳动和为地主的剩余劳动是明显地分开的,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雇主的劳动)也表现为必要劳动(为自己的劳动),从而资本主义的剥削被“平等交换”的假象掩蔽起来了(表现为没有剥削)。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种种假象都发挥着掩盖剥削的功能:“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产物,但在“工资”形式上,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别“消失”了,好像雇佣工人的全部劳动都是有酬劳动;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只是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但资本的流通过程造成的假象是:剩余价值来源于流通领域(它是在“贱买贵卖”的“交换关系”中产生的),资本有一个与资本的生产过程无关,从而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关的、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剩余价值只是可变资本增殖的产物,但利润好像是全部预付资本的“增加额”;无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还是利息、地租,都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商业利润却表现为好像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企业主收入和利息的分割好像只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生息资本好像是一个能够“自行增殖”的“物神”。地租则直接和土地这一自然要素联系在一起(从而好像是土地的“自然力”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扣除生产它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分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组成部分;但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所造成的假象却是: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构成”商品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一般与雇佣劳动实现了“合而为一”(一切劳动都好像是雇佣劳动);劳动条件在雇佣劳动者面前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与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本身实现了“合而为一”(生产资料好像天然地是资本,土地好像天然地是若干土地所有者垄断了的土地,资本和被垄断的土地好像是劳动条件的天然形式)。于是,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die Verdinglich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ltnisse),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20]由此可见,资本世界是充斥着假象的、颠倒的世界;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被层层假象掩盖了起来,资本是一种被平等交换的假象掩盖了的剥削关系![21]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遇到否认资本剥削的人,听到否认资本剥削的理论观点。有人把利润看作是“风险收益”。听到这种论调,笔者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对巴师夏“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的观点进行的批判:“如果人们几百年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22]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给我们的思想启迪是:只有先把所谓的“风险收益”创造出来,它才能被人以“风险收益”的名义占有。我们不妨追问:风险可否创造收益?若不能,那么,是谁创造了“风险收益”?“利润是风险收益”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23]
有人把利润视为资本家作为管理者的工资。这是一种“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的辩护。[24]对于这种辩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透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是由于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因为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器的所有者;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25]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对于资本所有者也可能是不利的: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本所有者就不应该有“管理工资”,从而没有资格占有“利润”;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本所有者,其全部“收益”也不应高于同类情况下职业经理人的工资。
还有人为了否认资本的剥削而鼓吹“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能够自我增殖,可以获得或分享剩余,具有同其他资本一样的特征(言外之意是,既然人力作为一种资本也获得了增殖收益,那么“其他资本”获得增殖收益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批判过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马克思评论说:“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对于上述“流行的观念”,马克思的揭露很犀利:“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26]“人力资本理论”并不新鲜,只不过是马克思批判过的上述“流行的观念”的当代变种。“人力资本理论”回避资本是对劳动者无酬劳动的剥削关系,回避资本增殖的根源,掩盖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真实关系;其实,人力不是资本,资本不是人力,“人力资本”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27]
三 假象的拓展与深化:资本关系的全球化与虚拟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大时期。20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经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大发展阶段。对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学术界有多种不同看法: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等。[28]虽然大家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分歧,但是资本扩张而导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29]资本没有限度的扩张、跨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对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学者约翰·史密斯以三种“全球性商品”(苹果手机、T恤和咖啡)的生产为例,剖析了GDP统计数据所产生的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得分离的反常现象,并指出这一反常现象的实质是把“价值掠夺”看作“价值增值”。他认为,GDP统计数据一贯地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人对全球财富增长的真正贡献,却肆意地夸大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产值。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生产苹果手机零部件的中国工人、生产T恤的孟加拉国工人和咖啡种植国的啡农,跟发达国家的公司员工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并得出如下结论:压榨贫穷国家的工人是富裕国家中大部分民众直接的经济收入的源泉。约翰·史密斯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GDP统计数据抹杀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人在价值创造中应有的地位以及对全球财富增长的真正贡献;在生产全球化即资本—劳动关系全球化的时代,发达国家公司是通过生产的外包而源源不断地获取高额利润的。[30]上述材料可以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剥削对象不再是本国的工人,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当代学者有必要运用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揭示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假象,批判人们头脑中产生的新的误认。
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根源于资本的本性。在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的循环”的一段论述之后,恩格斯补充说明了一种“狂想病”:“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31]“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这在金融领域有着异常明显的体现。
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可以在不完全依赖产业资本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直接获取垄断利润,表现出独立化、自由化的特征。国际垄断资本与金融资本融为一体,实现对全球资本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和剩余价值的全球剥削。剖析经济金融化、资本虚拟化,需要运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马克思说,在生息资本形式上,“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32]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资本的权证也商品化了。马克思认为,“有价证券不仅是对资本价值的所有权证书,从而也是对这种价值的未来再生产的所有权证书,而且同时是对未来的价值增殖的所有权证书”。不过,马克思告诫说:“不能把这种价值计算两次,如铁路的价值和股东手中的铁路股票的价值。”[33]在马克思看来,有价证券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34]虚拟资本是一种与现实资本对立的,能够定期确定收益,且在市场上买卖,作为现实资本的复制品的所有权证书。[35]虚拟资本把未来收益提前支取,这使之成为财富转移,而不是财富创造的特殊经济活动。[36]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随着国际金融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由“滞胀”型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当代金融危机的特点是,第一,首先爆发在虚拟经济领域,而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第二,实体经济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日益虚拟化;第三,民众包括工薪阶层超前、过度的透支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第四,波及范围不断扩大,从发达国家蔓延至世界各国。[37]世界性金融危机既是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由于美国劳动者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不足,住房资本过剩,才需要发展“次贷”,使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可以“消费”住房),又同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即金融自由化等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38]运用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明晰地区分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转移,剖析资本的虚拟化,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