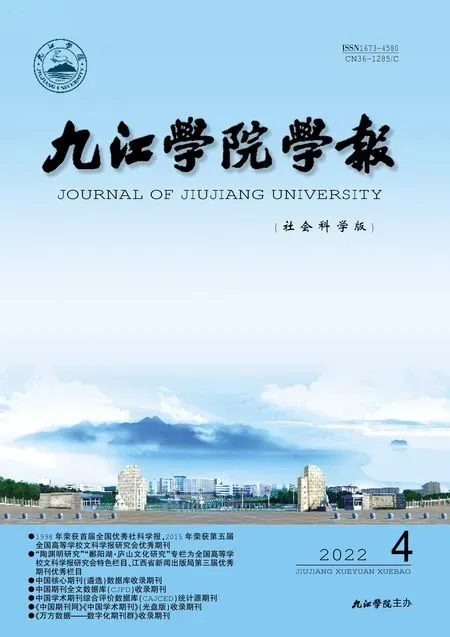唐人小说作者形象书写
孙 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2)
作者角色在唐人小说中出现,是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作者将自己的形象写入小说中,或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或佐证故事的真实性,为小说书写增添戏剧性。张稔穰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认为“(唐人小说)之所以有如此艺术效果,主要就是因为在情节的发展中塑造出了比较成功的艺术形象”[1]。不少唐人小说研究中,对特定群体的人物形象多有关注。就笔者目力所及,有唐人小说中胡人形象、狐形象、僧人形象、老人形象、女性形象、剑侠形象、侠女形象、妓女形象、妒妇形象、商贾形象等的研究,未有专涉作者形象的文章。若论及与其稍有关联,则有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唐人小说本朝人物书写研究》[2]一文,在分析唐人小说中对本朝人物书写时,偶有提及唐人小说的作者。
文学作品中作者形象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如华东师大袁圆的硕士学位论文《契诃夫小说<草原>中的作者形象分析》[3],四川大学池济敏《艺境无常形 朴实味悠长——析舒克申短篇小说中的作者形象》[4]等。文章则有汪余礼《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隐性艺术家形象——兼论“隐性艺术家”与“隐含作者”的差异》[5],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的文章有侯体健《幻象与真我:宋代览镜诗与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6],谈及诗歌作品中的诗人自我形象塑造。俄国文艺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一部作品真谛的集中体现,它囊括了人物语言的体系,以及人物语言同作品中叙事者,讲述者(一人或更多)的相互关系;它通过叙事者,讲述者,而成为整个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的整体核心。”[7]巴赫金认为,“作者作为审美主体,在作品中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8]这无疑表明了研究文学作品中作者自我形象的重要性。
一、智者——李公佐《谢小娥传》
论及唐人小说中的作者形象,李公佐极为重要。目前学界公认李公佐的作品今存《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一名《李汤》)四篇。在《南柯太守传》及《庐江冯媪传》中,李公佐的形象皆为“旁观者”与记录者,而在《谢小娥传》中,李公佐成为故事的参与者,为谢小娥解答疑惑,帮助其寻找杀夫杀父仇人。谢小娥大仇得报之后,李公佐在寺庙中见到小娥,不胜唏嘘,遂录为《谢小娥传》。
李公佐和谢小娥相识缘由直到小说中间部分得以提及: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9]
之后,李公佐为谢小娥的十二字谜做出了解答,认为杀害小娥父的“车中猴,门东草”为申兰,原因是“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杀谢小娥夫的“禾中走,一日夫”是申春,因为“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故此,李公佐得出“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的结论,为小娥的寻仇找到方向。这里也构成了文章的第一个高潮场面,作者被视为强有力的参与者。
在这里,李公佐的智者形象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一,僧人齐物“重贤好学”,可与李公佐友善,说明李公佐本人即为“贤人”;其二,寺庙高僧数载不能为谢小娥参透十二字谜,而李公佐“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仅片刻即有所得,可谓是从侧面表现其智慧与才能,即便是高僧也不可及;其三,在字谜的破解上,李公佐根据谢小娥梦中出现的内容,从文字角度剖析谜底,表现了李公佐知识丰富,博览群书。总之,《谢小娥传》的“解谜”环节,作者的出现,即表现着智者的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之后的故事中,李公佐的形象虽仅仅在夏天时过善义寺,被谢小娥认出且道谢的场面有提及。而实际上,在小说的第二个高潮,即谢小娥报仇的环节,作者的身份作为暗线依然在文中潜藏。结合事件发生的时间,小娥之父、夫被强盗杀害的时间大约在元和六年左右,谢小娥与作者即李公佐见面的时间在元和八年建业佛寺中。《谢小娥传》一文中提到,李公佐当时是“罢江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因此在段谢两家遇害时,李公佐应为江西观察使幕下从事,而谢家在当时的豫章,也就是江西观察室治所洪州“蓄巨产”。内山知也认为,谢小娥的复仇方法,应为李公佐提点。李公佐因为段谢两家被杀之事,知道凶犯姓名,无法检举,遂拔江西从事,与小说中“罢江从事”情节相符。
《谢小娥传》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离奇,在人物塑造上颇具特色,引人入胜。其后文本多有流变,如在《续玄怪录》中,李复言的《尼妙寂》与《谢小娥传》故事情节相类似,但其发生时间、地点、人物与后者有着显著不同。《尼妙寂》中保存了李公佐为复仇女主角解谜的情节,李公佐的智者形象得以展现。《新唐书·列女传》中亦保留有李公佐解谜一节,但较《谢小娥传》更为简略。后世文本如《类说》《舆地纪胜》《虞初志》《绿窗女史》中皆对《谢小娥传》或《尼妙寂》加以节录或全录。凌濛初在《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增加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人物描写,对谢小娥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也将李公佐这一故事主角体现在主题中。李公佐由原来的作者,成为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
后世文本的流变与《谢小娥传》相比,李公佐作为作者,同时又是事件的参与者与亲历者,他将自己描绘成文章中的智者形象,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又增加了故事的文学性以及真实性。谢小娥报仇的事迹由作者亲身经历,亲自记录,并且参与到事件发生的过程,具有在场性,承担推进文本发生以及加强文本可信性的作用。
内山知也认为:“《谢小娥传》是抱着史传式意图写作的,李公佐为了证明作为传奇素材的事件的真实性而出场。”[10]作者形象在这类传奇作品中得以展现,构成文本冲突的一环,增强故事整体的叙事性与真实感。李公佐在这类传奇作品的真实性方面表现的意图尤为明显,他既是作者,又是整体事件的参与者。
二、链条——故事的推进者
唐人小说中的作者有时可作为故事的推进者,参与到故事的发生中,承担着故事链条作用。作者是故事隐含的主人公,这类故事的发生围绕着作者展开。李公佐《古岳渎经》与题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中的作者有着这一特点,他们虽是作者,却以记录者与连接者的形象参与到故事的发展中。
《古岳渎经》中,李公佐的形象又成为故事的推进者,作为联系文本的一条线而存在于故事中,连接两个故事。李公佐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即与杨衡相遇,有所交流,为之后李公佐游历仙洞,发现《岳渎经》做铺垫。
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11]
其中,李公佐又有所衔接,阐明这个故事发生的连续性,表现出李公佐对这件事情的记忆深刻,为下文遇到《岳渎经》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对这一内容的解释做铺垫。
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
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12]
李公佐在神仙洞中发现了《岳渎经》一书,并找出其中相关记载,认为李汤所见、杨衡所描述之怪物,应当为《岳渎经》中的无支祁。这种探险解疑类的故事具有游戏性,情节曲折离奇,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古岳渎经》这类文本,并不是以考证为目的的记录,考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一故事充满了奇异色彩,又因为李公佐亲身经历,并记录流传,又为故事增加了真实性。作为两个故事的亲历者,李公佐用第二个故事为第一个故事提供缘由,让人不禁产生解谜效果的感叹。又因以作者本人为明线,更具真实感遇的可信性。与《谢小娥传》相比,李公佐在《古岳渎经》中扮演的形象更接近于链条,以自身经历将两个事情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篇有因果关系的文本。作为一篇虚构的唐人小说作品,《古岳渎经》既偏游记,又具有志怪色彩,李公佐作为作者的链条作用,对这一文本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周秦行纪》亦具有这种特点,但与《古岳渎经》不同的是,牛僧孺既是托名的作者,又是主人公。作为作者的“牛僧孺”,亲身经历了这些场面,为这一类型文章的写作增强了可信性,同时又作为亲身经历者,将不同画面联系在一起,具有连接作用。
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余却回望庙,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13]
作者自己则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见到绿珠、昭君、杨贵妃、薄后、戚夫人、潘妃、王嫱等,与其饮酒作诗,诉说幽怨。文本描绘作者的奇遇,以作者的眼睛观察世界。与李公佐小说中作者在场具有同样的特点,作者亦是叙事参与者,在文本中承担一定角色,具有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古岳渎经》《周秦行纪》这一类型的唐人小说中,作者在文本中作为一个角色出现,构成故事发展的主要脉络,在叙事中承担重要作用。正如欧洲十八世纪开创的叙事特征,卢梭的自传式叙事中主人公是一个彻底背井离乡的人,他创造或者生活的世界没有明显的标记,而是一个谜团,他们必须去探索它的运作方式,这些作者在与世界及其期望的复杂交涉中不断地发明和重塑自己。
三、记述与评论——史传文学特征
相当一部分的唐人小说中的作者仅仅是记述或评论这一故事,这类作品受到史书写作的影响,是对史书写作的承袭。《史记》中单独设置“列传”,在史书中描绘了一百多位历史人物,个性特征鲜明,作者以代言、拟言的手法对人物进行浓烈渲染,情感激荡,最终取得不俗的写人成就。这对唐人小说中人物的描写有一定影响。唐人小说的作者通过为人物或异闻作传的方式叙事,作为文学作品的记录者。以李公佐作品为例,如《南柯太守传》和《庐江冯媪传》。这类文本与上述类型不同,作者在此类文本作品中,作为记述者与评论者。文本写作原因大多是作传,让后世引以为戒。
《南柯太守传》中,李公佐描述故事发生的缘由:“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梦,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14]文本发生的契机是李公佐看到关于淳于生梦境的内容,因而编录成传,冀后世以为戒。《庐江冯媪传》:“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攒,河南字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15]李公佐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了解其事,因此记录。
纵观唐人小说,作者作为旁观者与记录者的文本并不少见。在陈玄祐《离魂记》中,作者写道:“玄祐少尝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16]白行简《李娃传》:“汧(音千)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吏白行简为传述。”[17]又提到其能详细了解这个故事的缘由:“于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暗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18]
《任氏传》中,沈既济与故事的亲历者“蓥”交游,在他的叙述中详细了解了这个事情,表明文本产生的缘由,增强文本的真实性。沈既济在文本最后,表达自己对此传奇的感慨:“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19]表现出沈既济对任氏、郑生的态度,表达自我心境。
以上所列的《离魂记》《李娃传》《任氏传》中,皆有作者参与,作者与文本中人物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于古人处闻得,或亲身经历。故作者亦作为文本的组成部分。
唐人小说中,不少作品的作者作为评论者,对文本发出感叹,表现自己对文中人事物的态度。与上文所列类型相比,作者的存在感并不显著。上述类型中皆有作者存在,而下面这一类型中的作者,并未在文中现身,而是在最后作出感叹。其中所谓的“作者”,不一定是文本的创作者,亦或为叙述者、记录者,在以下列举文本中,“作者”以评论者形象出现。
《无双传》作者在文章最后发出感叹:“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20]在这里,作者作为记录者与评论者而存在。又如李朝威《柳毅传》:“自是以后,遂绝影响。尝以是说传于人世。殆四纪亦不知所在。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吐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诛而不载,独可怜其意矣。愚义之,遂为斯文。’”[21]李朝威的描述并不能佐证故事的真实性,而是借讲述柳毅传书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叹。《柳氏传》文末作者评论:“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22]作者通过列述文本,抒发自己于事于人之叹。
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受到史传文学影响,更是受到了汉魏以来叙事传统的影响。刘向在撰述历史人物时首次单独抽取“列传”合书创作,形成了《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等类传小说的初貌。作为记录者与评论者的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行为表达自己的看法,记录他们的言行,受到正史写作中列传人物的品评影响,用文章结尾的评论对人物进行行为价值判断。这一现象在中唐以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小说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利用儒家伦理道德对文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判断。
四、结语
唐人小说的创作表现出较强的虚构性,其作者在文中现身,不仅对增强文章真实性有帮助,更有利于促进故事情节发展。作者作为小说中人物的主要构成参与其中,使作者不仅仅指导人物出场,在故事发展中亦有自己的作用,更具趣味性与游戏性,使读者本身亦可以代入到故事中。在这一点上,唐人小说与前代小说相比,进行了较大的创新。
无论多么纯粹的叙事性文本,都涉及到根据先验的道德、心理、认识论、文学和语言范畴进行最低限度的塑造。无论唐人小说如何具有文学性,它们还是直接指向或扎根于真实。作者参与到文本中,作为记述者与亲历者的作者,自叙个体遭际,或亲身经历,或为亲朋
好友经历,不仅表现了作者的在场性,增加故事的可信度,为后世研究者了解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提供详实的材料,更为后世小说、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手法借鉴意义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