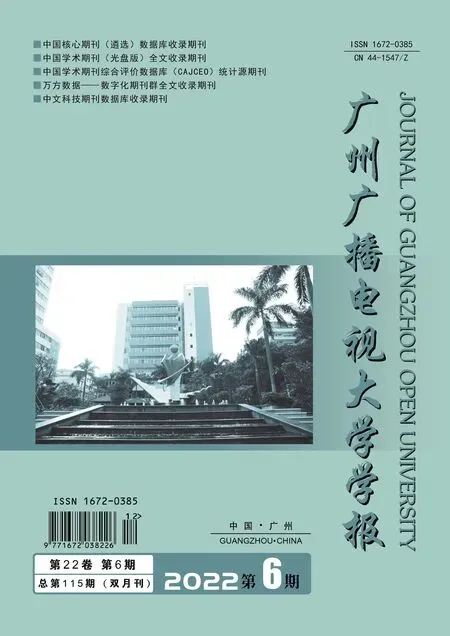跨文化视野下《大地三部曲》中 环境记忆的多维表达*
张 曦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基于深度的感官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异域者眼中的中国大地图景。在小说中,作家的视角跨越中国与外邦、土地与田野、乡村与城市,勾勒了一个中国家族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在宏大的时空背景转换下,赛珍珠不仅较全方位地展现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状况,更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中国农民形象在不同环境下意识活动、行为习惯、情感倾向等方面发生的转变,为我们揭示出环境记忆对人的巨大影响。因此,本文将尝试从环境记忆的独特视角对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进行解读,在跨文化背景下再探赛珍珠个人化的书写特色,挖掘赛珍珠这一异域作家对土地记忆、聚落记忆、中国本土记忆等环境记忆描写背后的深刻内蕴。
一、土地记忆与族群的共生和传递
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其彖辞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2]中华民族对土地的依恋与崇敬的渊源可推至上古。盘古开天辟地,混沌澄清,大地为浊气的沉降,给予万物以立足。女娲抟黄土以造人,人类诞生并汲大地之力,走向新的文明时代。而后先民们为生存而有了与土地的互动与交织,农事、农业就此诞生与兴起。土地开垦,农事伊始,汉民族族群因土地而站在了生命的原点。《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中记载,帝尧治天下时,“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3]《绎史》卷四引《周书》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4]由此可见,土地为农业之本,农业为族群生息繁衍之基。
劳伦斯·贝尔曾说:“‘环境记忆’是一个不常见的术语,没有固定的定义,我指的是环境作为第四维度的生活经验的意义(无论是否有意识,无论是否准确,无论是否共享)。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暗示,是在人类嵌入在某种持续时间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网中的背景下展开的,无论这些环境是有限的时间跨度(一生、一代、一个时代、一个王朝),还是无限期地追溯到遥远的史前历史。”[5]对于汉民族来说,土地记忆就是诸多环境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先民们对土地的依赖与崇敬使得土地记忆随着农耕、农事、农业的发展而逐渐沉积下来,成为了与汉民族共生共存的一种集体性记忆,并在代际间传递。
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中,作家在刻画主人公王龙时就着重地表现了其身上土地记忆的深刻烙印。主人公王龙的活动轨迹与心灵成长轨迹全部是以土地为圆心的。可以说,王龙是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缩影,更是汉民族土地记忆遗传图表中的凝缩节点。在赛珍珠的笔下,王龙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生产、生活活动,以及意识、情感活动都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以依附与敬畏为情感内核的汉民族土地记忆圈定了王龙的生命圆周。
由自然人到农民,土地确立了王龙的社会身份;由饥荒到果腹,土地产出的粮食满足了他生活的基本需要;而由生产到交换,土地满足了王龙更高层次的生活及精神需求。比如在小说开篇就有王龙“大手笔”地用耕地赚来的铜板和银元剃头、买猪肉等迎娶新妇的情节,体现了王龙组建家庭的精神需求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王龙在满足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两方面上对土地天然且本能的依赖体现出了土地记忆在他身上的深刻性与即时性。这种土地记忆已经伴随着汉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小农经济而在王龙们的行为中留下深刻的烙印。马尔科姆·昆特里尔在他的专著《环境记忆》中认为,环境记忆的时间成分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或渴望与以前的时期、社会和文化联系起来。在王龙的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数以万计的先民们在一片片广阔的田野中辛勤劳作的历史景象,他们前赴后继,在土地记忆的影响下顺其自然地踏着前人的脚步,倔强地坚持着那样一种规律而又一成不变的土地生产、生活方式。
伴随着土地成为王龙意识活动的中心,土地记忆也总是在他的意识和前意识中发挥着作用。在赛珍珠的笔下,土地记忆在王龙面对不同的现实情况时总会频繁地被唤起,对其主观意识行为产生安抚或训诫的双重作用。当王龙遇到灾荒不得不去南方的城市中讨生活时,艰苦的境遇使他不堪重负,“然而王龙总想着他的土地,因为久久不能实现他回去的愿望,尽管他很沮丧,但他始终千方百计考虑如何回去。他不属于这种依附于一家富人墙边的低贱的人,也不是那种傲气熏天的富家子弟。只有他觉得那种春天能扶着犁耕地,收获时能手持镰刀,生活才能充实。”[6]土地的丰收记忆此时成为了一种衣食无忧的隐喻,它以一种幻象的方式出现在了王龙的前意识之中,给予了他对抗残酷现实的精神力量。而土地记忆同样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深埋于王龙的前意识中,发挥着“稽查员”的训诫功能。“一个空间或建筑要象征某种超越表面效果的东西,它必须拥有自己真实的存在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精神,一个我们灵魂的印记”[7]。中华民族的土地记忆凝聚了众多优良的道德及精神文明内蕴,如勤劳、自勉、节俭、吃苦耐劳等等。这种精神力量是支撑民族发展的基石,更是克服骄奢淫逸的戒尺。前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担负着“稽查者”的任务,不准潜意识中过度的本能和欲望侵入意识之中。王龙在物质欲望与色欲的双重引诱之下,常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意识活动,而每当他将要滑入非理性欲望的深渊中时,土地记忆总会适时地出现在其前意识中使他悬崖勒马,回归理性。如在面对茶馆中画像上美女的引诱时,作者写道:“此时如若洪水退去,让水份在太阳底下蒸腾出去,经过几个炎炎的夏日土地就需要耕、耙、播种,王龙也许永远不会再到那家大茶馆去了。”[8]显然,土地记忆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在前意识中发挥了对本能欲望进行严厉的审查、训诫、阻挡的作用,成为了一种抵制私欲的行为准则。虽然在后期,已经摆脱农民身份的王龙其意识活动与生产生活活动都逐渐远离了土地,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留给了后人不要卖掉土地的遗言。王龙的生命圆周从未离开过土地的轴心,他的一生都笼罩在土地记忆之中。赛珍珠借由王龙的形象复现了汉民族土地记忆对生命个体的巨大影响,也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汉民族土地记忆强大的承继性。
“我们对周围世界事物的意识、对存在本身的意识,似乎与一种记忆能量有关,这种记忆能量储存着人类的集体经验,以便能够在我们的景观中被一代又一代获得。”[9]当某一实体建筑或某种景观得以跨越时空遗存下来时,环境记忆就不再属于个体,而具有了代际间的遗传效能。社会学家巴瑞·施瓦茨将集体记忆总结为一个连续与重塑的复合体,可认作是针对历史文脉的累积、穿插性建构。[10]对王龙家族来说,土地记忆就是融入到家族族群中的一种集体记忆。《大地三部曲》的叙事线索是以王龙、王龙的子辈、王龙的孙辈三代的生活景象为串联的。在动荡的时空变换中,土地记忆在家族的延伸中虽不断削弱却从未消失。王龙的儿子们忌惮于父亲的遗嘱,不敢轻易地卖掉土地,王龙的长子及二儿子在谈论土地买卖问题时,甚至都能感觉到父亲未亡的灵魂总盘旋在他们四周。与其说是父亲的亡灵不散,不如说是土地记忆早已深深地刻在他们的前意识之中,土地的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让他们不敢肆意地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到了王龙的孙辈,他们的行动随着眼界的开阔而不断向外部延伸,土地对他们的钳制已经减弱。但王龙的孙子在国家危机、个人价值取向迷茫的多重精神压力下,最终还是选择回到田野,以亲近土地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缓解精神压抑,土地记忆在物欲横流的糜烂社会现实中再次倔强地开出了生命力旺盛的花朵。土地是生命的起点,是万物生长复苏的自然力量,是穿越时空永恒不灭的物质及精神来源。这种生命力的延续是个人、群体、民族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支撑力量。王源在困苦抑郁之际走向土地,找寻个体存在的价值,就是土地记忆在代际间的挣扎与复活,它总是深藏于潜意识中,随时在现实中的外物刺激下被唤醒,并重新浮现在意识层面,给予活着的人以精神导向。
中华民族的土地记忆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诞生,并在历史、文化的远古记载中得以保存。而后,我们的先民在个体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中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记忆,并在这种记忆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性格及精神气质。赛珍珠通过对王龙及其家族的生活图景的详细勾勒,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土地记忆是如何与汉民族的族群共生共存,并得以世代延续的。
二、聚落记忆的危机对家园意识重塑的启示
聚落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聚落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他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11]原始聚落地出现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家畜饲养等物质生产活动。原始农业的出现将需要大量耕地以及大量劳动力、生产工具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较稳定的居所,成为聚落的雏形。到了母系氏族社会,在血缘宗亲的纽带之下,就出现了相对稳定的“聚”。“聚”是一个原始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基本单位。[12]目前,聚落的两种基本类型是乡村和城市,乡村是聚落的早期形态,城镇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更加复杂、多元的聚落形态。城镇的诞生可以追溯至黄帝时期,文献记载颇丰。而后炎帝、夏鲧和夏禹等也有相关建造城市的史料记载。城镇较之乡村增加了划分不同族群范围、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早期城镇就是在一个框定的物理空间范围内给予先民们基础生命权的保障,满足了他们对群居安定生活的企盼。
从乡村到早期城镇,聚落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物质资料需求、维系家族纽带、提供生命安全保障等诸多功能,聚落记忆也随之不断丰富。“我们强调意识的记录方面,因此把意识看作是刻有记忆的,可以在回顾中重新阅读。”[13]聚落给了先民们最基本的生存庇佑,聚落记忆也成为了人们家园意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赛珍珠的笔下,这种聚落记忆就像幽灵一般,游荡在她笔下的大地世界中。
“临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做好了准备。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好的收获,这个有三间屋的小房子每个角落都堆得满满的。”[14]王龙稳定而简单的家庭生活景象就是一种对聚落记忆最具代表性的复现。在小说中,赛珍珠还特意描写了过年时王龙去城镇置办年货、去亲戚家串门以及村落中每家每户相互拜年的场景,而这就是一个最能够表明聚落记忆在群体中的生活、生产中留下痕迹的缩影。村落中的人们依靠农田有稳定的物质资料来源,依靠简单的商业贸易足以果腹,依靠亲密的邻里关系精神富足,依靠稳定的家庭空间实现人丁兴旺。这一情节隐喻了聚落记忆在北方地区发展史中的延续,并表现出了在聚落记忆的承继之下,人们对家园的空前依恋与对世俗生活的满足。
而到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到来扭转了世界的样貌。工业代替手工业之后,生产及生活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现代城市逐步兴起。虽然城市聚落依然起着划分不同社会群体、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性作用,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此。现代城市中物理空间结构分布的逐渐细化、空间内部构造的逐渐精致化、人员构成的复杂化给原本的聚落记忆带来冲击。光怪陆离的城市中,何以为家?在小说中,赛珍珠通过描绘王源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历程向我们展现了古老的聚落记忆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的继承危机,也传达出对家园意识重塑的思考。
王源是王龙的孙辈,他的父亲王虎因为怨恨王龙而对土地、农村有着巨大的排斥情绪。但幼时的王源却热爱土地,喜欢与农民待在一起,迷恋乡村的恬淡与风土人情,聚落记忆在他身上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承继,并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习性。但这种记忆在五光十色的现代街景中却瞬时变得极其缥缈而脆弱,“他从未到过这样的大城市,也从未见过这种高楼,虽然街灯很亮,但他仍很难看到高耸入夜空的房子。然而,在这些高楼的底部,光线是充足的,人们像在白昼一样地行走。”[15]现代城市聚落的重要特征就是依靠现代化工业技术与建筑技巧,对空间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以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的生活需求。影院、歌舞厅、大型商场等现代化场所充斥在现代城市聚落中的每一个角落,满足着人们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逐渐高涨的需求。王源流连于喧闹而绚烂的城市街景中,也很快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节奏,遥远的乡村早已被他抛之身后,聚落记忆也在他的意识中变得陈旧而遥远。
“但现在春天又来临了,源觉得一种烦躁的感觉又袭上了心头……在和煦的春风中,源开始有点坐立不安。春风使他回想起土屋,回想起那个小村庄,他的双足渴望能站到某个地方的泥土上,而不是站在城里的这些人行道上。”[16]显然,现代都市布局的闭塞感与拥挤感,现代建筑创造出的人为的距离感与隔阂感都使得王源身心俱疲。初期现代聚落带给他的新鲜感与愉悦逐渐褪去,城市空间带给他的边缘化感受令他迷失而彷徨,家园意识早已消逝,只剩下无所归依的虚无。过去乡村那简单而牢固的家园氛围使他怀念,于是他只能在头脑中将过去的原始聚落记忆反复回想、重溯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痛。在赛珍珠的笔下,聚落记忆是一种强大的精神能量,它可以重新弥合冲击之下破碎的家园感,指引每一个迷途中的个体返回原初的家园意识起点。
最终,王源还是沿着记忆的轨迹逆行回了原始聚落。优美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忙碌景象都与他的聚落记忆相重叠,王源的家园意识得以重建。但很快,乡村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乡村原始结构的封闭、村民们的愚昧与排外等现实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王源再次陷入到了痛苦之中,原始聚落不再单纯是恬淡而美好的家园,而是迂腐与未开化的落后聚居区。聚落记忆曾经在王源身上表现出的正面精神激励与此时相对立的“排异反应”是具有典型性的,是赛珍珠为我们讲述的聚落发展乃至整个宇宙发展的深刻寓言。聚落记忆的内核始终未曾改变,它深埋于我们的前意识中,但我们的意识结构早已因为发展的社会现实而改变。原始聚落代表了最初的家园形态,因此聚落记忆必定在现代社会,在每个现代人的意识中遗存一个原始家园雏形的美妙景象,在家园感倍失的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来自远古的文明智慧与精神慰藉。但社会存在在技术的革新、经济结构的重塑等影响下已经改变,聚落记忆也就无法一成不变地被后世所承继。从王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聚落记忆在时代更迭中的逐渐弱化,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前意识中的群体记忆是无法轻易消失的,我们仍然需要家园感的精神力量,需要聚落记忆中凝缩的文明智慧。
原始聚落在中国拥有千年历史。赛珍珠在中国生活的漫长岁月中,见证了中国乡村、城镇、城市的变迁,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聚落记忆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聚落记忆是镶嵌在家园意识之上的珍珠,虽然它会暂时被埋藏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但在现代空间中的迷途人还是会重新挖掘它,填补家园感的破碎。赛珍珠最终让王源站在了回归乡村还是奔向城市的岔路口,却给我们暗示了一条中间道路:我们永不能真正地遗忘聚落记忆,也不该因为其与当下现实存在的错位而丢弃它,而是应该努力地在聚落记忆中继承那亘古不变的精神文化内核,寻找人类生存的启示。并且,我们还应该将当下的生存现实状况填补进古老的聚落记忆之中,增加聚落记忆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后人及未来人类聚落发展中更加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存在,引导他们守护家园,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三、中国环境记忆的跨地域表达与共情心理机制
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地》与第二部《儿子们》是其旅居中国时所写下的,而最后一部《分家》是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三部曲中唯一一部在美国本土完成的作品。[17]因此,赛珍珠在小说中对中国环境记忆的表现不仅来源于她身处中国大地上时的亲身体验,还有她回到本国语境之后在比较视野下对那段中国生活经历的追忆。一方面,赛珍珠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土地与农民的接触和了解极其有限,因此,她认知中的中国环境记忆存在时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赛珍珠作为一位异域作家,她对中国特有的环境记忆终究不是源于集体的无意识承继,必定无法描绘出中国环境记忆的全貌,深挖中国景观记忆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及文化内涵。但不可否认的是,赛珍珠对中国景观记忆的呈现具有其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异域特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首先是赛珍珠对中国环境记忆进行了诗性的审美。聚落记忆是一种人们为了达到抵御外敌、延续家族血亲、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等诸多现实性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地域群居记忆。而在赛珍珠表现乡村聚落记忆时,除了突出展现这些基本的特性,她也极其看重其审美价值。以第一部《大地》为例,赛珍珠对土地、田野、乡村的诗性描写数不胜数,只要涉及背景交待、烘托人物内心,赛珍珠就会不吝笔墨,以充沛的情感刻画美丽怡人的乡村田野风光。“播到地里的麦种由于干风不可能发芽,……空气既清澈又透出一股暖气,在平静而阴暗的一天,忽然间下起雨来。他们一家坐在屋里,心满意足,看着雨直泻下来,落到场院周围的地里,顺着屋檐滴答地往下淌。小孩子感到惊奇,雨落下来时,他伸出小手去捉那银白色的雨线。”[18]“暮色苍茫,灰暗的天空里一群深黑的乌鸦大声呼叫着从他头顶上飞过。他望着它们像一团云一样消失在他家周围的树林里,直奔向他们,边跑边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它们又慢慢飞起,在他的头顶上盘旋,发出使他生气的哑哑的叫声,最终,消失在天边。”[19]乡村聚落中的诸多自然景观之于大多数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是物质资料的来源。鸟兽、星光、云雨等在聚落记忆中更多的是一种农业价值意义,用来判断耕种农时、预估收成情况等,以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要。但对于异域作家赛珍珠来说,观察者的身份给了她足以悠然自得的诗性化审美视角,着重描写自己感官上的体验。赛珍珠对中国乡村聚落优美怡人的自然风光的表现,让千年来事关农民群体生存而略显沉重的中国原始聚落记忆多了些许诗画般轻盈的美感。
距离感与合适的空间感(空间及心理上的)往往会给身处于事外的旁观者以更加理性的他者视角。对于赛珍珠来说,她只是中国环境记忆的参与者、记录者、观察者,但这样的身份也能够使其跳脱出单一的封闭视角,从他者的旁观视角呈现出中国环境记忆的多面性。比如在呈现以血族宗亲为纽带的乡村聚落记忆时,赛珍珠就刻画了一类反面的村民形象。他们在饥荒时因为妒忌储粮殷实的王龙家而上门抢掠他们辛苦攒下的粮食。显然,乡村聚落记忆并不都是团结友善的正面样貌。赛珍珠就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揭开了聚落记忆中充满伤痛、排他自私的阴暗面。在赛珍珠冷静而批判的视角下,我们得以重新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反思承继了千年的环境记忆。
赛珍珠在离开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回归了自己本国的文化背景后,在天然的比较视野下对中国环境记忆的表达具有跨语境文学的典型性。身处中国大地上的赛珍珠在缺乏参照物的情况下,对中国土地记忆、聚落记忆的认知与思考会受到空间及视野的局限,具有单一化、单向度的特点。但当她返回到本国的文化背景下时,对中国环境记忆的追述就进入到了一种中美比较的视域之中,她笔下的中国环境记忆也就有了更加多元的内蕴。在赛珍珠返回美国创作的第三部《分家》中,她描写了盛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本是处于中国土地记忆、聚落记忆遗传谱系中的一员,但当他留学美国时,西方社会环境的现代化、先进化刺激了他,在对比的视野中他将自己意识中的中国环境记忆与西方现代环境作对比:“对于我们村庄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回忆都使我感到厌恶——人们肮肮脏脏,孩子在夏天一丝不挂,狗又野又凶,成群的苍蝇哪都是,令人作呕。我不能,也不愿住到别处去。毕竟西方人在追求舒适享受方面的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孟恨西方人,但我不能不承认,多少世纪以来,我们没有想到过使用清洁的自来水,使用电,看电影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我而言,这是一片适合我居住的乐土,我要永远地呆在这儿写诗、享受。”[20]显然,在对比的视野中,西方现代的聚落环境刺激了盛,使他开始强烈地排斥甚至要摆脱本国环境记忆对他的影响。这一身处新旧、中西交界点的人物形象与赛珍珠具有类同性。他的心理机制映衬的是赛珍珠本人对中国景观记忆难以摆脱的异域认知模式——西方现代对东方传统的俯视,以身处“高位”的批判视角看待朴素、略显落后、原始的中国乡村聚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异域作家对本国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同,对中国景观记忆及所蕴含的文化、文明和精神内涵的一种俯视。作为一位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回到自己的本土语境进行创作之后再次描写中国故事、追忆中国环境记忆的过程中忽视了中美在历史发展背景、自然条件、社会群体构成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种强行将中美环境进行不对等的非客观比较,反映了跨文化书写难以避免的一种局限与偏位。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跨地域作品是不同文化碰撞、交流的场域。在偏位的书写之下,我们更应该努力通过文本在伦理诉求、民族心理、文明发展史等方面寻找不同文化间的共通之处,以此发掘跨地域书写在文化融合、交流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中国独特的土地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赛珍珠独特的土地伦理世界。微观视角下,她对土地的关照与共情是由生存空间距离决定的。她自幼在中国长大,距离感的消除终结了旧有的西方对东方悬浮的物质想象,使她形成了对中国大地从初步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这样一个严谨的认知过程闭环。而从宏观视角来看,人类共同的土地情结则是赛珍珠表达土地情感的原始驱动力。亚当的名字来源于尘土,人类最初的乐土伊甸园因为肥沃的土地与充足的水源而果实丰硕,物资殷实。在西方人的创世观中,土地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同样十分紧密,是无法割舍开来的共生关系。虽然后来中西文明的发展之路殊途迥异,但从亚当到该隐,从原始的农业时代到高速发展的现代农业社会,再到后来农业社会的瓦解与重建,无论是土地记忆的溯源还是后土地时代的流变,西方世界的土地记忆几乎能够踏出与中国土地记忆重合的车辙。土地,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土地对人类的锻造以及土地与人类的互动使得全部的人类都处于土地共同体之中。面对这样的土地共同体,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对人类提出了树立土地伦理观念的倡议,即“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21]。为了人类的共同生存与代际延续,我们必须对土地加以伦理关照,这种关照是理念式的,是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人类共同的土地情结诱发了赛珍珠对土地强烈的情感倾向,催化了其作品中如此深刻而充满伦理情怀的中国土地记忆的表达,这也使得赛珍珠《大地》这部跨地域、跨种族、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有了超时空的价值与意义。土地情结是其中国故事展开的背景,是其展现中国图景的主角,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中西文化巨大间隙的符号。更关键的是,它是赛珍珠试图贯通中西读者之间伦理情感的精神桥梁。她使其作品成为了人类土地共同体的强有力注脚,达到了从土地记忆维度沟通中西文化的目的。
对于身处中国景观记忆遗传体系中的中国读者来说,寻找本源、回归原点是极其重要的阅读驱动力。因此,对《大地三部曲》的认同与接受是中国读者基于共同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心理而产生的阅读行为。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下,我们也需要重视跨地域文学作品背后对人类文明共同始源的定位与表达。处于历史此在中的中国读者不仅需要通过赛珍珠的作品回想、追溯本国古老的环境记忆,也需要以一种更加辩证而理性的阅读态度找寻作家在跨地域书写中所表现出的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伦理情感等,以更加全面且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