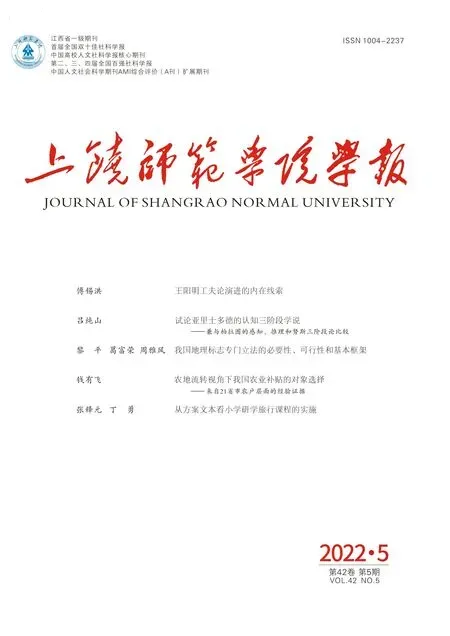论《庄子·应帝王》篇“混沌之死”的“他者伦理”向度
常丽娜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庄子·应帝王》篇末讲述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281
该寓言作为《应帝王》的结尾,是对内七篇的“总结”,憨山德清说:“此倏忽一章,不独结应帝王一篇,其实总结内七篇之大意。”[2]关于“应帝王”的题旨,郭象解释为:“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1]287对该寓言的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无为任化方面①关于“混沌之死”寓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夷夏之辨、生态伦理、美学、道教神话母题等方面,对该寓言的伦理维度的探讨尚显不足。参见:陈赟《“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吴先伍《混沌之死的生态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1期;时晓丽《混沌之美——庄子生存美学思想探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吉瑞德《早期道教的混沌神话及其象征意义》,齐鲁书社,2017年。,较少有从“他者伦理”角度加以阐释。值得注意的是,黄勇论证了《庄子》的美德伦理[3]和差异伦理[4]的“伦理”属性,并提出了《庄子》伦理的重要规则就是尊重其他存在者的差异性。赖锡三指出,《庄子》的他者伦理关怀,同时奠基在三根支柱上:一是对总体性的形而上学解构,二是对同一性思维的哲学批判,三是微观深描的文学书写[5]。本文以黄、赖二人的论述为前提,从庄子对自我中心化认知独断的批判入手,揭示该寓言在现代语境下的“他者伦理”意涵。
一、对自我中心化认知独断的批判
“混沌之死”寓言中,倏忽二帝因为“混沌待之甚善”,才有了“报德”的初衷,其行为动机是善意的,然而混沌的死亡却解构了报德的正当性,结果与初衷的巨大反差构成一种吊诡。这温情脉脉的报德行为,缘何会发展为一出混沌死亡的悲剧?
悲剧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倏忽自我中心的认知独断。由笛卡尔“我思”所确立的西方近代哲学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有极端唯我论的倾向,对自我的内在性、先验性的追求只会形成主客二元对立及理性原则的绝对化,而无益于社群伦理关系的建构。其造成的困境有:其一,忽视了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造成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其二,将主客二分关系扩展到人际关系上,引发自我与他人在伦理层面的一系列矛盾[6]。
故事的紧张始于“凿窍”,正是倏忽选择的“凿窍”报德方式,导致了混沌的死亡。倏忽将混沌对象化,从主客对立二分的立场判断“人皆有七窍,此独无”,而“七窍”可以“视、听、食、息”,可以开启感官知能,混沌“无窍”在他们看来就是个“异类”。混沌死亡的根本责任在于倏忽的认知专断,二者将自我认知绝对化、标准化,视无知无欲的混沌为改造对象,以“报德”的形式,将“七窍”知能系统强加给了混沌,实则桎梏戕害了混沌的天性。知能的开启会带来纷繁杂多的物欲,淳朴整一的天性会被物欲所撕裂,故《人间世》曰:“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1]109混沌本为“道未始有封”[1]80的无限存在,它处于倏忽所代表的时间之外,其天德就表现为“无窍”的浑全整一,“无窍”的天赋形象让混沌毫无机心,浑朴未凿,而能待人以厚。倏忽有窍有知,故以彼此同异的主客对立“二分”心态来塑造无知、无欲、“未分”的混沌,以求同一。他们并不认同混沌的“他者性”、异质性,其自我中心的认知独断转化为行动上的“暴力”——凿窍,混沌正是死于倏忽罔顾差异性的同质化改造过程,混沌之死无疑是对这种自我中心化的认知独断和“赋义”行为的否定和批判。
(一)认知独断的危害
《庄子》对自我中心的认知独断对生命构成的戕害进行了深刻批判,如“鲁侯养鸟”: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1]621
鲁侯虽爱鸟,却并不真知鸟,没有顺应鸟的天性,而以一己之好恶强加于鸟,导致鸟的死亡。人类在对象化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将他者变为“我知”的附属品,原因就在于“主客二元对立”所产生的不对称的权力结构,由“我知”而对“他者”作“标准化”“同质化”的功利性要求,如伯乐相马: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1]253
这种标准化、同质化的改造过程,却是扼杀天性和桎梏生命的悲剧,对此,庄子严厉批判道:“此亦治天下之过也!”[1]301《应帝王》借狂接舆之口对君主“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1]264-265的治天下之术提出批评:“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1]264-265出自一己之私的治天下往往是“师心自用”,自是自矜,不仅背离了物的天性,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灾及草木,祸及止虫”[1]354。因此,葛瑞汉指出:“对于庄子,试图把‘道’程式化为一套治理天下、家庭和个人的规则,乃是人生之大错特错。”[7]218庄子继承老子无为清虚—自化的原则,他主张:“圣人适应事物之运行,而不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其上,一如泳者之蹈瀑: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7]219庄子呼吁因顺物之天性,不以私意凌夺他者,“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而已”“顺物之自然而无容私焉”[1]223。
(二)自我中心化认知是否正当
庄子质疑绝对化、标准化的自我中心化认知的正当性,如: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1]93
所谓“正处”“正味”“正色”因物而异,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同样,天下也没有绝对的“正知”,任何人都不应该将自我认知绝对化并强加于他者,以免造成对他者的暴力。庄子批判儒墨以己见为必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1]62,彼此对立攻伐,是非无定,故“莫若以明”[1]62。柏拉图的“洞穴寓言”隐含了一条由蒙昧无知的奴隶状态而走向由精英启蒙大众的线索,这则“混沌之死”寓言也隐喻了中国在轴心时代的“精神启蒙运动”。余英时就读出了其中的“启蒙”意味:“《天下》所记述的历史(道术将为天下裂),是脱胎于庄子的这一寓言。因为两者皆以人的五官作喻,清楚地显示出庄子笔下的混沌,是代表原来合一的道体。庄子写下混沌之死这则著名寓言时,心中必定想着这场今天史家视为‘迅速’(倏)和‘突然’(忽)发生的中国古代精神启蒙运动。”[8]然而,混沌的死亡(道体有亏)无疑是对倏忽“启蒙”行为(诸子百家以其知相争鸣)的“反启蒙”,从而构成一种吊诡性冲突,庄子以滑稽的笔调对“神圣崇高”的启蒙权力进行了质疑。
汉斯·梅勒认为,这个故事重挫且颠覆了读者对创世神话的期待[9]。世界的原初状态是“混沌”,而“倏忽”所代表的时间演化则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史主要记载英雄圣王“开天辟地”、治水、教化民众的伟业,“六经皆史”,儒家所推崇的“六经”主要歌颂三皇五帝之功、三代圣王之道,其“治天下”的过程,是文明史开展的过程,也是社会逐渐秩序化的过程。庄子颇具深意的地方在于,他将“圣王治世”的神话反转过来,对文明演化和秩序化的过程加以反省和审视,在庄子看来,文明的实现是以质朴天性的丧失为代价的:“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1]253庄子认为,圣王以智治天下的过程就是淳朴离散、“道德退化”的过程,这无疑是对宏大“圣王”叙事和神圣神话的解构和颠覆。在这一意义上,“混沌之死”寓言超越了具体时空而具有了后现代的意味。
(三)“知”的异化
在庄子看来,战国时代,社会失序,价值颠倒,知识可能会附和机心和成心,堕落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名者,轧也;知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1]135知识没有用于追求幸福,却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凶器”。庄子的深刻在于他揭示了知识异化成为权力驯化的工具和手段:“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1]313世俗称颂“圣知”反而异化成了大盗窃国的工具,“盗亦有道”,不无讽刺意味!庄子所警惕的正是此类“知”被歪曲利用为冷酷的杀人工具的事例,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1]261
相比庄子对认知独断和认知异化的批判,他所推崇的是“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明镜”之知、“不知之知”,即自然、自发的感应万物而不以私智去损益万物。陈霞曾指出,道家的认知主体是具有无为精神境界和觉悟的人,他们使自己自然化、物化、道化,进入“伦与物忘”、与道同体,虚静自由的境界[10]。所谓虚静自由之境,即攘除自我中心之后而呈现的万物共荣共生的天地境界,我与他者构成差异化、多样化的生态和谐世界。
二、“他者”显现的前提: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境域——天均、天倪、环中、道枢
多样化、差异性的存在境域,为“他者”在多元格局中的显现提供了可能。《齐物论》开篇即由南郭子綦“丧耦(对待)”以入道,指明“丧我”的工夫论要旨,次则论及“三籁”,而最高层次的“天籁”即天机自发、万物自然的境界,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46在庄子的道物关系中,很难发现庄子将道处理为万物背后的那种无比强大、不可置疑的主宰力量[11]。道并非是外在于万物之上的造物主或上帝,道并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2]155,道遍在于万物之中,让万物如其所是地成为它们自己,自由发展。因此,庄子的立场是在承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3]即万物的殊别性和相对性的前提下,以道观之,不齐之齐,故“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1]50。从道法自然来看,万物齐同为一,万物的生命和价值是平等的,共生于同一境域。因此,庄子力图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视域局限,在他的笔下,“他者”指向了丰富多样的生命形态:既有扶摇直上的大鹏,也有腾跃蓬蒿间的蜩与学鸠;有大年如冥灵、大椿,小年如朝菌、蟪蛄,有人瑞如彭祖;有圣王尧舜、隐士许由,也有残畸者如树山无趾、支离无脤、瓮盎大瘿,更有游四海之外的姑射山神人;有河伯与海若,也有嫠牛、狸狌、蛇、夔、蚿,更有翩跹的蝴蝶与从容的鱼儿,忘生死的骷髅和朝三暮四的猴子。庄子并不拘泥于人世,他将目光移向广阔的宇宙,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视野的开阔使得他的笔下呈现出生命的多样性,鸢飞鱼跃,瞬息万变。我与他者之间可互相转化,或为蝴蝶,或为庄周,是为“物化”:“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1]833万物相尊相蕴,相因相生,彼此连缀不已,我与他者在大化流行中彼此流转变换,从而构成多样性的差异性的均衡生态。只有在这样一种万物既有差异又具有平等价值和地位的均衡生态中,即圆转无穷、应物无穷的天均、天倪、环中、道枢的境域中,他者才能自由显现!
三、“他者”显现的方式:“减损之道”——丧我、相忘、无己
要消除自我中心主义的认知专断及其危害,必须凸显“他者伦理”维度。让“他者”显现的方式,在庄子主要是指以“丧我”为核心的减损自我的心灵修养工夫。
人们面对他者,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去同化或者归化它,把它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使他异性可以被认识和理解,从而消除那种危险、不安的状态。同化和归化有时可能伴随着暴力,要消除暴力,就要去除自我专断化认知对他者的笼罩和遮蔽,承认他者的差异性。
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说,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一直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定位为主客体的关系:自我不断地消化、吸收他者,将其纳入自我的意识内进行感知和认识[14]。他者从来没有获得与自我对等的地位。列维纳斯的目标就是要确认他异性绝对地、无限地存在,不可被消化和吸收;同时他将他者的存在视为主体性建构的必要条件,主体性正是在自我对他者的回应中被给定的,因此他异性丰富了主体性,对他异性的尊重是真正道义生活的开始。列维纳斯认为,他者从不属于我们所构建的世界,而是处在外围的无限存有,是不可被遮蔽或者被构造的异己的存有。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囿于成心,师心自用,自是而相非,相互攻讦不已。王夫之《庄子解》对此批评道:“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偶,疲役而不知归”“不立一我之量,以生相对之偶,而恶有不齐之物论乎?”[15]现实纷争不断,其根本原因无非在于“有我”,如: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1]89
在舜看来,尧心不释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固执于私我成见,不能容受他者。人应该摒弃一己之私,从本原上等量齐观万物,如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开放自我,接纳他者,和谐共生!
彼此相待对立是自我中心化认知的产物,是由自我视角来观察、理解甚至塑造他者的运筹策略。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去中心化”[16]。庄子去“中心化”的根本方式是减损之道,即丧我、无己、忘我等。正如有学者所论:“先秦道家的‘自’论中隐含着‘不自’的思想,隐含着对自身的否定”,“不自”是“自”的异己性存在,也就是“他者”[17]。
绝对的中心化意味着一元化,也就意味着对他者和多元格局潜在的排斥和遮蔽。这样的一元中心格局往往容易形成自我封闭的保守主义。去己、忘己、丧己,去除自我中心,解消中心化附带产生的权力暴力(包括观念暴力、行动暴力),才会正视他人不可化约的存在和异质性,不把自我的观点强加于人。“混沌之死”对春秋以来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而兴起的效率导向性工具理性文化提出了质疑①此处特别感谢论文评审人提供的宝贵意见,至于庄子哲学所着力批判的对象究竟何指,笔者认为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先秦“显学”主要是儒墨两家,自孔子没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等,儒门内部出现思想分化。自唐代起,韩愈就认为庄子之学源自子夏、田子方,章太炎和郭沫若则认为庄子之学出自颜回,由此推测,庄子所批判的也可能是针对儒家内部,像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就与韩非法家思想渊源甚深。,这种以富国强兵为号召、推崇军功、以严刑峻法来绳墨民心的功利型文化,所导致的是军功官僚科层制国家的兴起,如齐、楚、秦、晋等大邦国,这种文化大盛于战国,最终的集大成者为“秦政”,即以申韩之术治天下。庄子对这种急功近利追求同一化和标准化的“前法家”思想做出了批判性反思。按照福柯对权力的解析,制度、体制往往会对个体进行各种潜移默化的权力规训[18]。从故事结果来说,“七窍”并不适合混沌本性,混沌正是死于倏忽企图机械地复制自我形式和结构的暴力规训。
倏忽的报德之举,是按照自我的方式增益混沌的知能,开启其视听知觉系统。这种方式在道家看来都是越发背离大道的方式,其所开启的不仅是混沌的知觉官能,还有随之而来的好恶、是非之知和被外物扰动的纷乱的情欲,而体道和入道的方法是“减损”,而非“增益其知”。一旦知欲官能打开,犹如开启这个世界的“潘多拉”的魔盒,种种是非争竟将纷至沓来。先秦道家充分认识到“情欲”对人心灵的摇荡,为了“心平,内保之而不外荡,成和之修”[1]150,宋钘提出“情欲寡浅”[1]949,老子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2]109,庄子则提出“心斋”“坐忘”和“吾丧我”等心灵涵养工夫。庄老都反对人们过度追求“知欲”,而主张有所不知、损知去欲,老子认为“知不知,上也”[12]172,庄子提出“养不知”: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1]224
庄子所谓的“建德之国”是:“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1]596《应帝王》开篇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1]261,这与结尾混沌因凿开七窍官能之知而死去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一种“反讽”效果,颇具讽刺意味!庄子反复强调要遗弃耳目之知、要以“不知”“忘”“丧己”即“非自我意识”[19]47的方式,也就是以无为的方式去体道: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1]663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竞,故寓诸无竞。[1]108
倪德卫指出:“孟子说修身,‘养’的是气和义。在庄子那里,‘养’的是道,道家的‘道’。在孟子那里,若是没有‘养’的过程,我们的气将‘馁’。庄子对此予以重估,把修身过程变为心‘斋’。”[19]251所谓“心斋”,《人间世》解释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137庄子认为,道体虚无,心灵以复返道体为根本宗旨,因此,体道的心灵必须是“虚”的状态,郭象认为“不虚,则不能任群实”,刘大魁曰:“‘虚’乃庄子宗旨,所谓‘无心’、‘无为’、‘无用’者是也”[20]。虚具有澄汰心境、净化心灵的作用,它清除沉积的是非成见,因为是非观念构成语言和传统的价值观念。“虚”为心灵创造空间,让道在其中扎根生长。
倏忽凿开混沌七窍知觉的过程是由内而外,这与庄子所提倡的“心斋”“坐忘”入道工夫过程恰好呈逆向状态。《人间世》中孔子告诫颜回:“循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1]150庄子继承了老子“涤除玄览”的思想,主张收视返听,“塞其兑,闭其门”[12]136,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让心灵回归虚寂状态。因此,庄子的“心斋”是一个由外而内、从有到无的过程,排除和忘却那些遮蔽道的认知方式。“忘”则要减损知欲,“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259,此处的“堕、黜、离、去”,都是减损之义,也就是老子的“为道之方”:“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12]117。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莫若以明”,都是让人丢掉主观成见、标准、框架和范式,用静因之道让事物本然地呈现出来,用内心的虚静观照事物的本然,让事物自己表达自己,而不是成为被陈说的对象。这颇有点现象学“朝向事实本身”的意味。当自我行减损的心灵修养工夫之后,万物不再是被“我”陈说或改造的对象,而是自发自然地成为它们自身,“他者”也由此而呈现。
庄子想要把生命从“名言”秩序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生命本有的自然形态,于是他提出“无名”“忘言”“去知”的主张,以解构名、言、知背后的权力形态。生命的意义在于“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上”,自由和幸福本是“天生烝民”赋予生命的本有之义,所有违背天性的不健康的规训和限制都是不合理的,“率性之谓道”,使所有生命得以尽其天性才是道之真义所在。在道的自由境界中,由于“照之于天”,并和以天均、天倪,每一种力量之间都保持均衡状态,我与他者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和对话,呈现出“万物共成于天”的和谐共生的态势!
四、结论
混沌的死否定并解构了倏忽“报德”的积极意义。倏忽以自我中心化的认知独断企图将前秩序状态的混沌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和结构内部,而罔顾混沌的“他异性”。该寓言展现了庄子对自我中心化认知独断的批判和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毕来德认为,庄子头脑中的阶序图式主要有天与人两个层级,最下层的是人,最上层是天,而人的精神意识就是错误、失败和死亡的根源,救赎之道就是要返归自然天道[21],以天提人,消除自我中心,让他者呈现,故庄子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1]524。返真之路就是要行“减损自我”的心灵修养工夫,消解自我中心主义的遮蔽,向他者敞开,才能复归朴素的道德之境(即混沌之境),我与他者及多样的生命才能和谐共生!这对于当前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