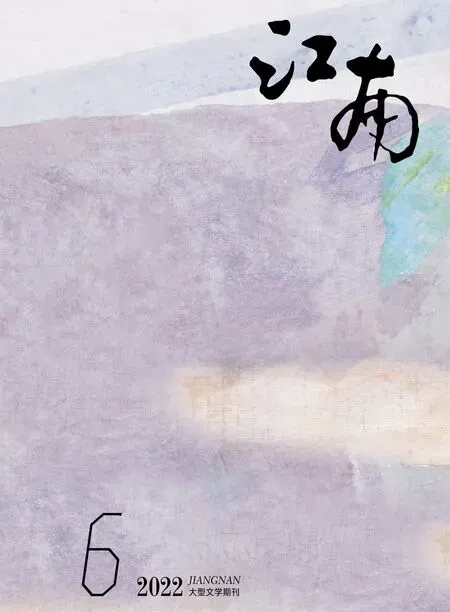一刹那
□ 裘山山
一
那一刹那,我脑子里出现的竟是电影镜头:车身侧翻,三滚两滚,撞向路边防护栏,然后砰的一声,开始燃烧……真是警匪片看多了。我都忘了当时在下大雨,就算油箱撞裂汽油流了一地,也很难燃烧吧。
其实翻车之前,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部电影,《穆赫兰道》。开篇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暗夜里行车,车突然停下,两个男人拿着枪逼女人下车,女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突然,公路上飞驰而来几辆赛车,疯狂的赛车党将他们的车以及车旁的男人撞得稀烂。惊魂未定的女人爬出车逃命,却被撞坏了脑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会在车上,于是好戏开始上演……
但我肯定不至于,我是一定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车上的。虽然车里的四个男人都是我今天才遇见的,叫不出名字,只知道一个是副站长,一个是驾驶员。但是这场车祸我是认识的,它先于发生潜入了我的大脑,虽然潜入得非常缓慢,如同花生酱——据说世界上流速最慢的液体是花生酱——但潜入后就逐渐凝固了,凸显出一场车祸的模样。
所以,当车子撞向山体的一刹那,我没有惊叫,脑子里想的是,你真的来了!就好像亡命天涯多年的逃犯,终于看到了拿着手铐的警察,释然大于恐惧,周身放松,意守丹田。
翻车之前我已感觉到了异常,车身突然不受控制地下滑,虽然我们原本行驶在下坡道上,但下行和下滑是不一样的。驾驶员死命地扳着方向盘,真的是用了洪荒之力,但车子根本不理他,继续失控。只听副站长大喊:刹车!踩刹车!驾驶员回:没有刹车了!
“没有刹车”这个表述是如此贴切,以至于让我有了触感:一脚死命踩下去,刹车踏板和车子是失联的,只是一块铁皮而已。我在他们的简短对话中怔住,但大脑并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充斥着愤怒,甚至还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嘛,不听我的嘛,这下你们如愿了吧。
我下意识地抓紧了上方扶手,身子听天由命地交给了那股巨大的来自虚空的力量,我完全没想到应该抱住脑袋俯下身。那一刹那,我在等着自己被弹起来,然后摔下去,顺应车意。
据说人的大脑是有偏好的,天生就爱关注突发事件,而对那些随时都在慢速移动的场景视而不见。比如我们翻车那会儿,山坡上的树枝一直在微微晃动,雨水在默默地流过石壁,喝了雨水的玉米又悄悄长了两毫米,风在雨里继续呼啸,甚至,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因为地壳运动而正在慢慢西移……我们只会注意眼前突如其来的快动作,注意一刹那。
一刹那之后,世界定格了。当然,世界是不会定格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南极,也有很多原子在运动。只有到了摄氏零下273.15度,原子才会停止运动,那就叫绝对零度。而绝对零度只存在于理论层面。所以我说的定格,不过是存在于我的感官世界里。
雨真的很大,感觉头顶那片天被两个交锋的大气团占领了,打得你死我活。天也是黑透了,以至于我们的车撞向山体接着一头栽下防洪沟时,都没有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像无声电影中的镜头,默默划过银幕,其中还有个特写:右前轮一撞之下与车体分离,腾飞起来,在马路上向前滚,滚下了左侧的山崖。山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而我,原本是坐在那个车轮上的。我在那个轮子上坐了十四个小时。此时是晚上八点。
屏幕上应该出现一行字幕:一小时前。
二
一小时前,我们爬上折多山,山顶海拔四千三百米,北京时间七点整。这个时间,比我们预期的晚了三个多小时。之所以晚,是因为前期的行程不顺,一误再误。
整座山都在下雨,整座山都被黑云笼罩着,能见度极低,我只能隐约看到车前灯照耀下的十几米路。车子小心翼翼地跟着那束光一点点前移。雨刮器开到了最快档,和雨水争抢着玻璃窗上的地盘,来来回回,无休止地摩擦。于是乎,下山的三十多公里路我们走了五十分钟。这五十分钟里,早上潜入我脑海的不祥预感愈来愈清晰,我的心为此揪成一团,紧得发疼。
好在,当夜幕彻底笼盖四野后,我们终于进入到了康定城。看到雨夜里星星点点的城市灯火,我稍稍安心一点,于是再次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建议:
这么大雨,这么晚了(快八点了),我们就在康定住一晚上吧。
我想我都如此疲惫,司机一定更甚。真应该停下来歇息了。我们已经连续行驶十几个小时了,人困马乏,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一路上遇到的塌方和翻车,比我进去的十天里遇到的总和还多。估计那天的黄道日历上一定写着:今日忌出行。
但没有人回应我。
这是我第二次如此说了。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两点才吃上午饭。那时尚无智能手机,我是凭来时的经验判断的,到康定肯定天黑了,从康定到雅安还有一百四十多公里。这样的山路实在不适合开夜车。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想,明摆着的事。
我说,咱们今晚住康定吧。
不料他们好像和我坐的不是一辆车,遇到的不是一样的经历,我的预测和建议,在我们饭桌上完全不能形成气候。他们意志坚定地表示要继续赶路,继续按原计划走。他们反复说,没问题的,他们经常这样走,肯定能在天黑前到雅安。四个男人,含驾驶员,每个人都把这句话说了一遍。那份笃定,不容置疑,让我无法反驳。
我只好顺从。毕竟,他们在这条线上已经跑了几十趟,而我才两趟。再毕竟,当时还是朗朗晴空。人都是受缚于自身经验的囚徒,关键是,他们的经验也把我绑架了。
大雨是五点开始下的,或者说,我们是五点进入大雨的。大雨一直在那儿下,是我们驶入了大雨。雨水令很多路段泥泞不堪,行车的速度和安全系数都大大下降,如此,不该重新考虑我的建议吗?安心在这个被情歌唱红的山城住一晚上,明天早上去雅安?
我完全没有打卡网红点的意思,我只是忍耐到了极限。腰酸,背痛,头晕,恶心,最重要的是,那个不祥之感愈来愈强烈,它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路上点点滴滴的遭遇累积而成的。如我前面所说,它就像花生酱,缓慢而又持续地涌入我的脑海,然后逐渐变得坚硬。等到大雨倾盆时,它已然坚硬到像一把手枪,顶在了我的脑门上。
车上沉默。四个男人没有吐出一个字,甚至连“嗯”“呜”这样表示思考的语气词都没有,他们以集体沉默表示不同意。我真恨不能把那把枪转而对准他们的脑门:停下!再这样赶路是会翻车的!
可是我没有超能力,那把枪只顶着我的脑门。车子就在我的恳求下和他们的沉默中,急速地从康定城穿过,雨水把车灯前的柏油路照得发亮,亮到发滑。
我想再争取一下,就说,驾驶员太疲劳了,应该休息一下。
不想驾驶员马上说,我没事,主要看你了。
驾驶员说这话的同时,脚下似乎还在暗暗用力。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软弱,就好像我是搭他们的车,不得不顺着他们似的。实际上,这辆车是专门送我下山的。沉默片刻后,我妥协了,退一步说,那,我们先吃晚饭吧。
我想这个要求总该被认可吧。吃晚饭时,司机可以休息一下,从午饭到现在,他已经连续驾驶六七个小时了。他的疲倦和不耐烦显而易见。
这次他们接话了。副站长先说:这个,现在才七点过(他竟然把七点五十叫做七点过),大家都还不咋饿,我们就不在康定停了,我们再往前赶一点,去天全吃火锅鱼嘛。另外两个男人马上附和说:对的对的,去天全吃鱼,那边的几家鱼都好吃,不摆了。驾驶员说,反正烂路走完了,剩下都是好路了。
我沉默,愤怒在心里燃烧,恨不能怒吼:吃个狗屁鱼!难道你们非要翻车才甘心吗?在我的愤怒中,车子像上了滑雪道似的,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急速离开康定城,重新上了公路。
如此说来,那一刹那,始于一小时前。
三
车祸现场。
撞进沟里后,我很清醒,想着必须马上离开这辆车,免得车爆炸把我也炸上天。我真是这么想的,来自电影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我努力向外爬,离开座位时,忽然想起背包没拿,转身拿上,顺带还摸了一下口袋,手机在。
我手脚并用,爬到门边时,先于我爬出去的三个男人,拽了我一下。原来他们已经爬出去了。不知道他们在最后一刻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后悔?有没有歉意?
大雨依旧猛烈,还伴随着强烈的风。那风的时速大概超过了我们的车速,我不得不蹲下,以免被吹倒。时不时划过锯齿般的闪电,闪电亮起的瞬间,我看到五个人站在公路边上,傻傻地看着沟里的车。所幸,五个人都全尾全须地站着,没人受伤,至少没有重伤。受伤的是车,车子以报废的模样卡在沟里,车的前保险杠撞断了,少了个车轮,还碎了一块玻璃,显然,没有大吊车来请它,它是坚决不会上来的,它瘫在那儿嘟囔说:不行,我散架了。
如果要给这场车祸命名,我想应该命名为明知故翻。是谁明知?车,驾驶员,还是副站长?反正不是我。我是明知要翻极力阻拦,没拦住。我因此而痛苦。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王小波如是说。我亲身体会到了。
我终于开口说,给牟主任打个电话吧。
当我开口说出这话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发颤,甚至发叉,腿也在抖,衣服湿透了。这辈子头一回用上了那个词:瑟瑟发抖。我拿出手机,用背囊挡着雨,想拨打电话。
副站长一步上前拦住我:别急,等会儿再说。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会儿?等会儿难道车子就能从沟里出来,像电影镜头那样回放吗?毕竟我这趟行程,是牟主任安排的。报告他是必须的。我希望他马上派一辆车过来,把我接到雅安去。此外,我还要,迫不及待地想要,吐槽。
副站长说,还是我来报告吧,我带车。
我明白了。我打这个电话,有点儿告状的意思。他打,算是汇报工作(突发情况)。虽然很不情愿,但软弱的本性让我依了他。
这个时候,我隐约发现我手上有血,抹了下额头,是额头出血了。很淡,被雨水稀释了,但毕竟是血。不知道撞到什么硬东西了,疼倒是不太疼,但生气。他们的固执,居然让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很想大声质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赶夜路,非要在大雨中赶夜路?
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继续瑟瑟发抖。
副站长向路的两头张望,期待有往来的车,但一辆都没有,没有上山的,也没有下山的。没有人像他们这样冒死在雨夜赶路,制造一场明知故翻的车祸。
绝望中,雨幕中忽然出现了光亮,一辆小车从坡下爬了上来,我又惊又喜,竟然也有人在这样的夜晚跑路。小车主动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男人探出头问:需要帮助吗?真是活雷锋啊。雨夜雷锋。
副站长连忙上前说,谢谢谢谢,需要帮助,我们的车出车祸了,能不能麻烦你先把这位女士带到康定去?男人说,没问题。我说,不好意思,我身上湿透了,会搞脏你车子的。他说没事没事,快上车吧。副站长又叫来我们车上的另一个男人,跟我说,我在这里等处理,让助理员送你去康定。安顿下来给我打个电话。
就这样,我再次上了陌生男人开的车。
但这一次,我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了,而是松了口气。毕竟前面铺垫得太狠了。等在车上喘匀了气,我才意识到今天还有个反常,以往一到晚上六七点,丈夫会打电话来问,走到哪儿了,是否安全。今天都八点了(都翻车了),也没有任何音信。
我满心不高兴,但还是主动打了一个,我急于和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获得安全感。不料丈夫上来就说,他六点半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都没打通。我释然,猜想那时正翻越折多山,信号不好。我努力淡定地告诉他,我们出车祸了,我现在搭了一辆过路车返回康定。
之所以努力淡定,是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比我还淡定。我若哭哭啼啼,惊慌失措的,会很尴尬。他果然哦了一声,然后问,受伤没有?我说,没有大问题。他说,那就好。今晚住康定吗?我说是的,目前是这样考虑的。他说,那你今晚好好休息。
不管怎么说,我和失联的世界再次联系上了。世界虽然没有热烈拥抱我,也还是正常的世界。
到达康定,助理员已经为我联系好了招待所。我一再向那位雨夜雷锋表达我的感激,我问了他的名字,留了他的电话。我也不知要怎样,但这是表达郑重的意思吧。
我浑身湿透地站在简陋的房间里,窗外大雨还在持续,但是风势弱了些。风也和我一样疲惫不堪了。我有些恍惚,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四
一天前。
中午吃饭时,我和站里的人闲聊,我说我的采访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打算过两天就返回总部。我还说这些日子麻烦他们了。
我上川藏线采访,除了跑路外,还选了几个点住下。塘坝是最后一个点。我已在此住了三天。
这时,一直埋头吃饭的副站长马上抬头问,你怎么下山?
我说我跟牟主任说了,他会派车来接我。
他马上一脸笑容地说,噢,简直是太巧了,我们站里明天有辆车要下山,你可以坐我们的车下山,免得麻烦牟主任了。
我有些缺少思想准备,明天下山?这不合我的计划。但是,他的建议又很难拒绝,有顺路的车不坐,让人家专门派车上山,再下山,显得有点儿摆谱。见我犹豫,他又说,我正好要去雅安办事,我亲自送你下山,保证安全。
我迟疑着说,也好。
他马上说,那就这么定了。
是我的犹豫害了我。正如我的前领导给我的鉴定:你这个人,第一理想主义,第二优柔寡断。理想主义已经被现实生活折磨得形销骨立,站不稳了,但优柔寡断却如中年体型,越来越敦实。
我想抓紧时间采访,便放弃午休出去找人。路过办公室时,听见副站长正在讲电话:人家作家老师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老待在我们这山上好无聊嘛……我送她下山之后马上就返回,不会影响工作的……就两三天时间,绝对没问题。
我这才明白,不是正好有车下山,是我正好成了他下山的借口。最近站长不在,估计上级不希望他离开。他便拿我当了理由。可是,这一来我更难推却了。因为,他比我更迫切地想走,他会排除一切阻力拉我下山的。
晚饭时,他果然很高兴地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牟主任指示我带车,把你安全送到。明天早上我们六点出发。
我吃了一惊,那么早?
他说,不早,六点走,晚上就能到雅安。
我又吃了一惊,这第二惊里有了害怕:明天晚上赶到?从塘坝到雅安,我来的时候可是走了三天,就算是越野快,也不至于快那么多吧?七百多公里的山路,起伏蜿蜒,处处有险情,起码应该分两天走吧?我弱弱地问了一句,能行吗?
他豪迈地回了句,没问题。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走的。
跟着他又加了一句,放心吧。你的生命宝贵,我们的生命也宝贵。
我有些不悦,但不再说话。其实我当时完全可以说,算了,我不坐你们车了,我还是想多待两天,多采访两个人。我这样说了,他还能绑架我不成?可是我竟然说不出口。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上了歧途。
一刹那的事情,并不是在那一刹那发生的。
当然,我也抱着侥幸心理(也算是为自己不得不出发做的心理建设):上山的时候我阑尾疼,很担心路上发作,到了山上不好办。可他们只是给了我一板阿莫西林,说问题不大,吃两颗就行了。两天后我还真的不疼了。每次遇到塌方,石头滚了一地,我提心吊胆地觉得应该后退时,他们总是若无其事地下车,把石头搬开接着往前走。或许这条危机四伏的路对他们来说,和城里的街道差不多。一天跑七百里山路在他们是小事。
早上六点,天还黑着,我拿上行李出门。车停在院子里,我习惯性地坐到后面,副站长走过来说,老师还是请你坐前面吧,我们后面要挤三个人。
挤三个人?不是说专门送我的吗?但转念一想,他们常年守在山上,好不容易有辆车下山,搭个顺风车难免。我便坐上副驾,把随身的背囊和保温瓶也拿到前面,堆在脚下。
果然又来了两个大男人,和副站长一起挤到了车后座。他们沉默寡言,连个招呼都没和我打。驾驶员也不苟言笑,五官端正,瘦而高,算是个帅哥。但是,我更喜欢送我上山的驾驶员,黑乎乎,胖乎乎,一脸笑容。身处陌生环境,亲和力远比颜值更重要。
我就这样十二万分不情愿地上了路。
车里很沉闷。我想说几句活跃一下,或者和他们闲聊,联络一下感情。毕竟,五个人要在狭小的空间里相处十几个小时。但是,除了副站长偶尔回应我,其他三个男人都一声不吭。尤其驾驶员,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不说话不是拘谨,而是不快。从侧面看始终板着脸,似乎对这一趟出车任务很不情愿。
我作罢,也陷入沉默。窗外掠过的一座座山,在渐渐明亮的天光里泛出浓浓的绿色,毕竟是六月。山腰缠绕着云雾,犹如仙境。川藏线的美名不虚传。可是这样的美,是从危险中孕育出来的。
果然,出发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见一辆翻车,车和人都很惨,再走没多远,又遇到塌方,车子堵成一条长龙。前面的司机都靠在车上抽烟,好像只要躺平路就会通。我们车上的三个男人只好下车,涉过泥泞走了好几里路,到前面的养路段叫来了推土机,将道路开通。再往前走,又见一辆翻车,翻在路中间,把路堵得死死的。又去找大吊车来将其移开,得以通过。
如此这般,早饭推迟到十点,午饭推迟到两点。驾驶员似乎有些心急,将车开得飞快。有段路被洪水冲断淹没了,他也不减速,冲过那段路时,被水下的一块大石头狠狠绊了一下,车子腾空而起,将我放在前面的保温瓶弹起来,砸在我的头上。他竟然连一句抱歉都没说,后面三个男人也一声不吭,好像没看到。
我感到不快,但忍了。毕竟这是川藏线。但接下来,车祸继续出现,简直邪门儿了,前后六次。要命的是,每次经过车祸路段都非常缓慢,几乎是挪过去的。让我想起沙漠的迁移,大部分是跃迁,小部分是挪迁。我们就是挪迁,从天上看肯定察觉不到我们在动。由于如此缓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直面现场,接受血淋淋的交通安全教育。
车祸外还遇到两次塌方,一次是山上的大石头毫无征兆地滚下来,还好没砸到我们车,稳稳地立在路中间,我们车上四个男人,加我,都推不动。后来又来了三个司机,才把石头推到路边。还有一次山体下滑,泥沙俱下堵了一半路,我们是挨着悬崖边儿挪过去的。
这样一路走下来,感觉糟透了。早上出发时那个隐隐约约的不好念头,开始蠕动变大,我极力按压它,不让它探头。我反复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辛苦归辛苦,不会有事的。
却不料,终于有了一刹那。
五
车祸三小时后。
夜里十一点,我终于放松下来,躺倒在了床上。虽然那床并不舒适,但好歹,一堵墙将雨夜和我隔开了。我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游荡的魂灵终于有了个龟缩的角落。
在此之前,助理员叫来一个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当然是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我除了额头擦伤,胳膊肘和膝关节红肿,背部有些疼痛(估计是肌肉拉伤),其他没有大碍。至于是否脑震荡,需要回到城里才能查了。但我感觉没有,我的大脑比撞车之前还要清醒。
再在此之前,餐厅给我送来一碗热面条,解决了饥肠辘辘。那个助理员还给我找了个电炉(六月的康定之夜还是挺冷的),让屋子里不那么湿冷了。
一切安顿下来后,助理员给副站长打了电话,然后又站到我面前,一再问我,还需要什么。我一再说不需要了。我希望他赶快离开,我好一个人生闷气。他似有话要说,支支吾吾半天,终于说了句“真不好意思,今天让你受罪了”。
我虽然没好气,但又觉得他不过是搭车的,跟他撒气不合适,忍着没吭声。他说他和另一个助理员是下山去领物资的。他又说,那个副站长,老婆孩子过来探亲,走到雅安时孩子突然病了,住院了,他很着急,所以就……
我明白了。他果然是比我更迫切地想下山。我笑了一下(估计像冷笑),我说你去休息吧,我没事了。本来我想说,你知道什么叫欲速则不达吗?可是觉得毫无意义,住口。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预感成真的事。以前也有过,都是小事。比如有一次天快亮时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开会,其中一位没来,我打电话问她,她说孩子病了,要去医院。醒来后我感觉奇怪,怎么会做这样的梦?然后我去上班,那个人果然没来,打电话去果然是她孩子病了。我不但没觉得好玩儿,还有点儿怕怕的。
每次感觉不好,我就努力不去想,当鸵鸟。似乎我们古老的民族有个说法,坏兆头是不能说出来的,说了要呸呸呸。可今天我并没有说呀,我一直忍着,只是在心里忐忑。当第二次他们拒绝我的请求时,我虽然气得要命,恨不能把脑门上那把枪扳过来对准他们,也还是忍了。不,不是忍了,是我没本事不忍。最终,是预感自己开了枪,一枪命中五个。
从客观角度分析,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刹车失灵,刹车之所以失灵,是因为驾驶员一路狂奔,大幅度颠簸,车子颠坏了。当然,还可能是,刹车早有隐患了,驾驶员出发前没检查车况。
我的气又聚集在胸口。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给牟主任打个电话。
刚拿起手机,副站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好像堵枪口似的。他一上来先说了三声对不起,然后说,老师,今天实在是让你受惊了,你多多包涵。
我说,这根本不是受惊的问题,五条人命啊。你们的命也很宝贵啊!我终于把这句话还给了他,感觉很爽。
副站长说,是是。我已经批评了驾驶员。
我本来也认为是驾驶员的责任,但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不应该由驾驶员一个人担责,他是带车的,他是决策者。我说,你就不该让他这么着急赶路,下那么大雨。应该住一晚上。他说,是是。我也有责任。我当时觉得那段路很好走,哪里想到刹车会失灵。
我正想继续问责,我有无数的理由问责,忽然想起助理员告诉我的,他孩子病了,他心急火燎是因为这个。斗志立马衰退。
在我迟疑之间他又说,不过呢老师,还是要请你原谅我们驾驶员,他今天心情不好,他奶奶去世了,他是个孤儿,是奶奶养大的。他想请假回去的,但实在走不开……
斗志进一步衰退,什么责任不责任的,都塌陷了,成了一盘散沙。我顿了一下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跟牟主任说什么的。你们也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他如释重负,和我道别。
好吧,一个是孩子生病了,一个是孤儿,没了奶奶。都有被原谅的理由,那么,只有我来做善人了。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权当是体验了一下生活吧。尤其是翻车这样的体验,可遇而不可求。既要体验,又要无大碍。得有神助才行。
再想,驾驶员在最后一刻还是理智的,他知道宁可撞山也不能掉到河里,他狠命扳方向盘,成功地把我们带进了沟里。当时左边的大渡河正咆哮如猛兽,自高而下,那流速,估计已达到每秒五米,吞噬掉我们这辆车和五个人,完全是小case。除非大渡河也像阿拉斯加河那样,瞬间冻成一条白色高速公路。
心里的怨气消掉了,便浮现出一碗鸡汤:什么是幸运?不是貌美如花,不是出人头地,不是大富大贵,而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如此,我就是个幸运的人。
突然又一个激灵:哎呀,翻车后我竟然忘了拍照!站在路边那么长时间,就知道傻傻地盯着沟里的车,这样有如神助的事,竟没能留下照片,实在是太可惜了!哪怕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也好啊。出来采访这十几天,我每天都在拍,就是今天没把相机拿出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唉,我也够呛,不是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我索性拿出安定吃了半颗,好让自己放下一脑门官司,潜入到梦乡睡个天昏地暗,以换来明天新的一天。
一刹那就让它结束吧。
六
二十年后。
这四个字的出现,应该是比较爽吧?时间飞速流逝,可以让故事情节陡然加快,可以看到物是人非的戏剧效果。
就算不追求戏剧效果,离开人类社会来看,二十年光阴在自然界的变化也是很可观的。喜马拉雅又增高了一百厘米,阿拉斯加冰川又向大海移动了两千六百多公里(科学家说它每小时移动三十厘米)。全球的平均气温又上升了零点五度左右,街道旁的杨树樟树银杏们,又分别长高了五十到六十厘米。
总而言之,肉眼可见和肉眼不见的变化,都是巨大的。
二十年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我见到了牟主任。
是一次新朋老友的聚会,什么名目我忘了,我们俩居然是参加者中最年长的,于是被安排坐在一起。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胖了,脸型变宽增厚,五官因此跟着发生了一些位移。而我,随身携带着二十年前没有的白发,和胶原蛋白不知所踪的脸,让他在见到我那一刻,也愣了一下。
然后我们都及时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马上握手,寒暄。
我说,牟主任您退休了吗?他说早退了,七八年了。你呢,还在写书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是的,在写。每次别人这样问我,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很没出息似的。他说,那个时候我请你过来,你还是个年轻姑娘呢。我说,也不至于,那时候我也四十了。他说,你是个很认真的人,为了写那篇东西还专门跑了一趟川藏线。
“川藏线”三个字,让二十年前的一刹那,忽地拉开大幕,劈到我的眼前。雨夜,折多山,康定,副站长,驾驶员,防洪沟,大渡河,明知故翻。这些不是名词,是动词,它们奔突到我跟前,跳跃着。我甚至有些激动,今晚真是来对了,居然遇见了牟主任。
我忍不住说,那次跑川藏线,太难忘了!实在是太难忘了!
之所以这么强调,是想继续这个话题。那些埋在我心里二十年的困惑,也许可以在今天解开了。比如,那个副站长怎么样了?他的仕途没有因为车祸受什么影响吧?他的孩子应该长大成人了吧?那个驾驶员呢?即使是孤儿,也该结婚成家了吧?他不至于因为那场车祸受处分吧?挨个批是难免的。
已经二十年了,再提这事就不算告状了,借用那个术语,已经过了有效追诉期,再提不过是谈资。要说私心,我无非是想表白一下自己当年是如何包容。当然,也想打探一下他们的下落。
于是我进入了话题。我说,您记得吧?那次返回的路上,我们出了车祸,还好有惊无险,把我吓得够呛。
我满面笑容,好像在说一件好玩的事。
牟主任很疑惑:车祸?什么车祸?
我说,就是您请我去的那次呀,采访完了,返回的路上,刚出康定没多久我们就翻车了,栽进防洪沟。
他依然一脸茫然:翻车了?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知道?我提示他:就是我采访结束的最后一天,您让一个副站长送我下山,我们从塘坝一路开到康定,晚上八点的样子,下大雨,我们下山的时候刹车突然失灵,就翻车了。
他还是茫然。
我继续提示:后来我搭了一辆过路车返回康定,在康定住了一晚上。副站长他们处理了车祸后,第二天从雅安重新找了个车,把我送回成都。
牟主任的脸上,始终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恍然大悟的表情,他沉吟片刻说,我确实不知道。我记得他们当时跟我说,你已经完成线上的采访了,要回家写作,写完了再和我联系。我就没打扰你。
这回轮到我茫然了。一刹那再次闪过我的脑海。那么清晰的深刻的事,只有我记得吗?难不成,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刹那,是我臆想出来的?难不成,那电影镜头般的一刹那,被彼时彼刻的狂风暴雨吹散到了大气层?不不,不可能。
牟主任端起杯子离开了座位,融进眼前热腾腾的气氛里。涨红的脸,喷出的酒气,满桌的菜肴,以及众声喧哗,与我脑海里的场景完全不相容。我仿佛入定。有个声音对我说,一刹那的事情,只存在于一刹那。此地此刻也不过是一刹那。二十年的岁月在宇宙中也不过是一刹那。你是一刹那里的尘埃,但你曾高高扬起。
于是,我也端起了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