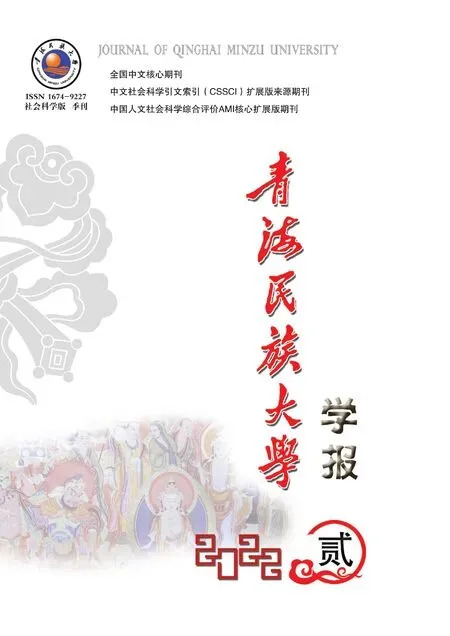旅游何以曰—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厘判
彭兆荣
(厦门大学,福建厦门 361005)
引 言
旅游名目“何以曰”看起来是小事,却隐含着重大的价值。大众旅游在中国的出现,原本是全球化的产物,很大程度上并非中国“自产”。从传统意义上说,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土地的“捆绑”决定了旅游和旅行的限制与限度。加上传统中“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伦理,千百年来以“和平安居”为理想目标,以“背井离土”为悲惨境遇。所以,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我国的旅游,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由于出现得过于仓促,许多事项、概念、理念、价值大多是直接从西方引入,甚至连“旅游”定义都来不及梳理、辨析就已经推上了市场。[1]至于那些旅游名目更是五花八门。随着国家的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在很短的时间里,旅游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日常活动”。然而,来不及厘清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我国旅游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形象,需要进行相关的“补课”工作。
一、“族群旅游”何以曰
对于游客而言,旅游是到旅游目的地去体验和了解不同的文化。比如“族群旅游”——对特定族群文化的了解和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族群”是人类学“制造”的一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特定群体文化进行表述的专门概念。人类学家巴斯认为:“族群认同的最重要价值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建立其上的社会组织同样受到来自族群内部活动的限制。另一方面,复合的多族群系统,其价值也是建立在多种族群不同的社会活动之上。”[2]因此,族群也是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基础性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如对特定族群、组织、亲属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和居落空间——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homogeneity)与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参与观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质性研究”。
虽然现代“族群”(ethnic group)具有特定历史时段语境中的特殊语义,但其原型源自古希腊的Ethics(即后来作为“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族群”等词汇的原始词根),原义为“人的言说”和“人的待遇”。所以,人类学一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叙述的意义,具有人类心理和体质两方面的意涵。人类学研究与其说是“人类的”,还不如说是“族群的”。因为,确认人类的基本单位为族群:人以群分。人类的群居方式,也是生物种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种群除了区隔生物差异外,相同的生物群体也会根据特定和特殊的群体特性形成独特的文化特点。这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所以,从根本上说,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族群性”的。族群旅游包含了两个基本的面向:游客—东道主。对于游客而言,旅游的一个最基本目的正是观察、感受、体验不同的文化;对于东道主而言,独特的文化正是不同的族群生成、创造、采借、融合、传承下来的认同价值。大众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对特定族群会产生自豪感,但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为了迎合游客的旅游动机和心理需求,东道主会在族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人为地加以改造,出现加速变迁的现象。这对族群文化内部独立的传承机制也可能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导致加速族群文化的“裂化现象”:一部分是给游客“看”的部分,另一部分是族群内部遵照执行的部分。这种“裂化”的情形考验着特定民族对内部权力阶层和权力机制控制的应对能力。
值得强调的是,大众旅游包括了人们常说的“吃住行游购娱”所带动的旅游商品化,出现了市场化情形。这无形中也对族群的文化认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商品的市场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将东道主族群文化引导到一个商品交换的方向上去。于是,“什么可以交换”也就被提到了东道主族群的面前:有些族群的文化具有特定的神圣性,这些神圣的东西和事物的“不可交易性”构成了族群传统文化内部规则和规律的要素和内容。可是,在商品市场的交换和交易原则下,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也被用于交易,用于交换,导致“原生性”的族群形貌受到了伤害。比如,在旅游纪念品中装饰了特殊的族群符号,使之从原来的“神圣性”转变为“世俗性”。甚至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不可外传、不可外泄的形象、物品、符号也被出售。
另外,在游客与东道主接触和交流中,市场交换有时成了一种无形的杠杆,建构出一种“不平等关系。”族群旅游以族群的传统文化为底色,这很容易理解。而族群传统文化以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为知识背景和历史依据,这也很容易理解。问题在于,“游客/东道主”在不同文化认同的历史背景下的交流经常并不是平等的。旅游作为一种消费性社会价值特征,游客很容易在现代社会中不由自主地趋附于一种媒体的广告宣传,并把追逐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弱小的、内部文化动力不强的族群传统就可能经受不住这样的冲击。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与主流文化,自己的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时候,经常会因此产生一种“自卑感”。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原因,便匆忙地将自己的全部文化“资本”拿出来做交换,包括尊严。至于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中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什么,剩下什么,已来不及思考。
旅游可以促使不同的族群文化在认同上出现巨大变化,尤其在东道主社会表现得更为强烈和激烈。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东道主社会和民众,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作为东道主在迎接来自西方的、或某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的游客时,其原先那些本来就很脆弱的族群意识和对所属族群文化的保护意识是很难在“洪水猛兽”般的游客到来之后仍然保持其文化的形貌。在这里,“文化形貌”既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如房屋建筑、服装样式、生产活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也包括那些看不见,却存在着的社会观念、伦理道德、认知系统、宗教信仰等。
既然族群旅游所突出的是族群文化,那么,“文化地图”(cultural map)也就被提升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内容。“地图”属于地理学上较具专业色彩的一个术语,之于旅行这一表述范式,它带有明确的人文地理学的指喻——既将一个具有地理空间的概念引入旅游文化,又可以反过来指旅游文化使某一些纯粹的地理空间具有特殊的文化色彩。比如游客通过旅游地图的指引和指示到达某一个旅游景区和景点,“地图”与“景物”建立起临时的协调关系。由于“地图”所引导的地理空间和场所被社会历史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地图”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叙事。简约的表述是:由旅游地图所引导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文化、族群认同的空间以及空间中的景物,构成一种特殊的、充满了的“边际性文本”(marginal texts)。[3]这一特殊“文本”所包含的政治化指示与人们理解地图与标志性景观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叙事和记录,并使之成为规范化的媒体表达。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曾借引克拉克洪一个文化概念的转喻:文化“作为一张地图”(as a map)。[4]虽然这只是众多文化概念中的一个比喻,却为我们理解和确认族群旅游提供了一个角度。“文化地图”有三个基本的表述依据:族群、地方和历史。文化地图的一个重要属性是所谓的地方文化,它的原生形貌以及由此构造的“地方知识系统”无疑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表述依据。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政治性话语的强势经常覆盖了不同族群文化的原生形态,变成了事实上“多元文化”的“一种声音”。当人们在面对民族-国家的主控叙事时,会很自然地将它与更具有实体感的“地方”,如村落、社区、人群共同体进行比照,并通过地方性原生形貌和具有实体边界的“自在单位”与之进行对话,它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表述场域。现在的问题是,不同单位表述的目标不尽相同决定了它们在对待历史时所采取的策略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所作的历史记录的不同。[5]“地缘旅游”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讨论的议题。
简言之,人类是群体性的生物种群,人类的活动是族群性的、逻辑性的,旅游也包含着明显的族群特征,特别是东道主-游客在遭遇中出现了以往从未出现过的新型关系,也使得族群文化面临新的检验和考验。
二、“地缘旅游”何以曰
无论什么名目的旅游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地方”。于是,人群与地缘的结合成为区分“我群/他群”的一道历史边界。它不仅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位的表述,而且为族群提供了一个更有实感的依据。这一切根本性的归属无不附丽于“一个地方上的人群”,也是“地方性力量”(regional force)的策源地。所以,在当今的旅游实践中,“地缘旅游”无疑是重要的支撑性说明。地缘旅游重在地缘文化。如何确认地方文化有两个认知点:首先,任何文化都有一个“地方性”生成的理由,它首先是指文化的“发生地”;其次,今天是“地球村”时代,必然会导致文化变化与变迁,即文化的“再地化”(relocalization)。游客一方面去往不同的地方旅游,共享不同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成为加速文化“再地化”的一种外在力量。
“地方”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对象。英文中“地方”(place)是一个具有多种认知和表述的概念。首先,它是一个地理空间。在西方“科学”的范畴内,常用经纬度予以精确地标注,以强调一个没有文化的地址(site)。其次,地方强调属地,经常与“领地”(territory)联系在一起,说明某个特定领域的归属性,既可以强调相对自然属性的空间(space),也可以延伸特殊的权力空间和位置(position)。第三,突出某一个地方的特色和特质,比如“地景”(landscape,即旅游界所使用的“景观”)。第四,日常生活中作为“场所”(locale)和位置来使用。[6]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地方”还是一种宇宙观的认知方式:“天圆地方”“天时地利人和”等赋予了“地方”特殊的空间语义。
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形制,包括通过分享某一个地方和群体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仪式以及创造共同的归属感来实现地方价值。一个特定的地方空间(“one’s location”),包括社会性别、年龄、种族/族性、阶级、宗教等,产生不同的记忆和意义。[7]所以,地缘旅游要尽力做到体验“小地方中的大历史”。它不但将“地方中的全球”(global in the local) 和“全球中的地方”(local in the global)同置一畴,也成为实现小型人群与人类学者互动关系的重要部分。[8]大众旅游也正是通过了解不同的地方文化认识地缘性差异。比如饮食,中国饮食的最主要分类正是地缘性,诸如“粤菜”“川菜”,“北京烤鸭”“兰州拉面”等。
地方有自己的一套知识系统。“地方性知识”是人类学家格尔兹的用语,作为一个极其平常的文字表述而获得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超出人类学的学科边界和范畴。[9]“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是认知世界的一种角度。其特点:第一,通过这一概念强调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在特定的群体中生成、认同并得以维护的。因此,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语境研究比关注普遍准则更重要。第二,“地方性”虽然与特定地域或地理特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指知识的生成与维护所依托和形成的特定的语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国家,“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10]构成了“地方性”最根本的特色。学界也称为“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或“草根社会”(grass-roots society)。按照一般的解释,其主要特征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窃以为,要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特点,“社”与“祖”是两个关键词。前者表示人与土地“捆绑关系”的发生形貌和“人/神”关系,它历史地延伸出了社稷、社会、社群、社火等,后者则表明土地人群在生殖、生产、传承观念上的期盼和行为上的照相,它延伸出祖国、祖宗、祖庙、祖产等土地伦理的意群构造。如果背离这样一个历史结构,也就背离了传统的规约与历史的归属。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强势的今天,“乡土社会”是考察政治经济运行是否处于“健康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是检验像我们这样具有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复杂的土地伦理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游客能否通过旅游了解特定地缘文化的核心要素。
地缘文化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指示:
程元敏先生检得北魏时引用《伪古文尚书》经、传者凡八人,分别为房景先、郦道元、邢峦、韩显宗、张普惠、李骞、王神贵、元恭⑥。其中,郦道元、邢峦、韩显宗、张普惠、李骞五人均系河北人物。结合诸人经历可知,至迟在北魏孝文帝朝,《伪古文尚书》已经北传。
地理-政治的空间。地理和生态空间是人们赖以支撑生命活动基本的物质形态。地理学家认为:“区域性的地理是地理学研究的最高形式。”[11]传统的地理学研究大多始于地理区域的划分,即根据特定区域内空间的标指进行。主要有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自然要素,如地质、地形、地貌、土地等;二是人文要素。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地理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这在我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就已经奠定的基础。所以,地理空间为历代王朝统治和地方社会自治提供了计量依据。中国古代就有所谓“分民不分土”基本行政区划原则。[12]
地缘-人文的空间。在传统人类学的观念中,文化和社会已不再局限于自然地理的空间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属性是“乡土”。那么,乡土社会的根本属性是什么?是土地。土地是人民的“命根”“是最近于人性的神。 ”[13]在这里,“土地”已经不再只是自然地理了,因此,地缘性人文空间属于“二度并置而不重叠”的空间范畴,即人文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并存。
认知-分类的空间。神圣世俗化场所包括:一是特殊的地点。在乡土社会,大凡重要的祭祀活动,比如神圣的仪式都要在神圣的地点进行,所以,有的地点(可区分永久性的和暂时性的)也就属于神圣空间,而非神圣空间的范围就是世俗性空间。二是相互的关系。神圣/世俗构成了乡土社会人们与他们的始祖、祖先圣灵、某些特殊的物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如山、石等)的特殊关系。三是人群的记忆。空间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表述,因而具有一种巨大的象征性,它是特定族群“记忆”的结果,而地缘旅游也就包含着明显的“怀旧”因素。四是教化的场所。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形制,比如私墅教育、耕读传家等主要生成于地方。
展示-体验空间。旅游行为包含着展示与展演的活动,无论东道主还是游客。比如传统的村落形态是根据自然的“形势”建构的,同中有异,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化中最重要的特点。旅游是一种体验,这是共识。笔者认为,如果当代的旅游活动不只是“吃住行游购娱”六字经的话,“体习”(体验、学习)无疑是深度旅游的重要指标。那么,地缘性旅游也就包括了对地方文化的“研习”体验。再比如,当今博物馆就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场所,它既是地方文化的特殊展示空间,也兼有“消费”的特质与特点(consumer orientation)。[14]
符号-结构空间。任何一种文化的表述又与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符号构造有关,比如族群性的亲属关系,而这些亲属关系的存在与表现无不与“家”(家庭、家族乃至宗族)有关。在这里,“家”已经不仅是一个姓氏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位,而与整个人群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关系纽带,这一关系纽带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又往往与各种重要活动,尤其是仪式活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结构的表述空间。
超越-固定空间。霍米·巴巴在《处所的文化》一书中以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处所”(location)进行反思性解释,认为我们在今天所讨论的处所的文化显然带有一种“超越”(beyond)传统的地方、居所、位置等的新的指喻。[15]旅游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处所的超越”行为,是在不同的“处所”进行各种体验的活动。甚至现代旅游还包含着重新建构空间的特殊形式,比如旅游活动中的“网红”,即引导游客前往的“处所”。因此,大众旅游也可理解为一种超越-固定空间的行为活动的实践方式。
简言之,任何旅游活动都要落实于某一个“地方”,所以,“地缘文化”也就成为旅游实践的基本依托。旅游无论打什么旗号,喊什么口号,地缘文化都是终极性的。换言之,“地缘旅游”是最为“落地”的旅游形式、形态和形制。
三、“生态旅游”何以曰
说起“生态旅游”,首先要从“生态”概念入手。“生态”(ecology)在今天已然成了一个“热销”词,同时也是被极度滥用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之前,英文中的“生态”使用频率并不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包含了当代历史语境与政治语义的特殊概念。从语词的溯源看,这个语词从希腊移植而来,原先的意思是指某个地方的特性,包括自然、生物等。今天,与“生态”概念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环境”(environment)。[19]在实际使用中,“自然”“生态”“环境”三者常常交叉混用,虽然三者之间从范畴到语义并不完全相同。而与生态联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联合国经常将“生态危机”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绑在一起表述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生态人类学还是旅游人类学中所提倡的“生态旅游”,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地球家园、生命共同体等新的话题内容与话语语境。
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开展旅游活动时都在大力提倡“生态旅游”(eco-tourism)。以旅游人类学的视野看,“生态旅游”一词由墨西哥学者谢贝洛斯·拉斯克瑞于1983年首先提出。在1986年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上,生态旅游被定义为“一种常规的旅游形式”。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代人们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而我国在1995年为生态旅游做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20]显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样的概念过于粗糙。2002年5月19—2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世界生态旅游高峰会,会议发表了《魁北克生态旅游宣言》。同年10月21—25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也举行了由联合国环境署授权的国际生态旅游年大会。这次大会还发布了《关于生态旅游伙伴关系的凯恩斯宪章》。总之,“生态旅游”无论是从旅游理念抑或是旅游形式,都会在未来呈现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一种趋势。生态旅游在整个旅游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态旅游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与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是人类文明进展的需要,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学本身的发展也为生态旅游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21]对于生态旅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各方面人士虽没有取得共识性的意见,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上是一致的: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旅游活动,有利于增强人们生态保护意识,将旅游对东道社会所形成的负面影响和作用降到尽可能的小,保留和保存地方传统文化和遗产,充分考虑旅游给东道主社会和民众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等。旅游决策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在旅游决策和管理方面会将生态保护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考虑。所谓生态旅游,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旅行中的安排,让游客尽可能与自然接触,与自然,与其他生物种类形成亲密的关系。所以,生态旅游包括诸如观察鸟类、水下生物活动等。显而易见,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作用比起其他旅游项目更小,更轻。[22]
虽说生态旅游是一项看上去在保持自然生态方面有着正面效益的旅游活动,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却会发现其中仍存在着一些隐忧,这种隐忧并非直接针对生态旅游本身,而是针对促成生态旅游的其他因素。生态旅游一般要以一个保护得较好、较为“原生形态”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些基础和条件,生态旅游只能是一句空话。大抵不会有人在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享受所谓的生态旅游,也不会有人在森林遭到大量砍伐、动物见人就逃避的环境中去体验生态旅游的乐趣。换句话说,生态旅游需在一个生态保护得很好的自然环境中方可进行,而要做到这一点,按照目前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让游客到原始的自然生态地区或者“自然保持区”去。平心而论,世界上现存的所谓原始生态,比如“原始森林”已经少而又少,况且,到那些地方旅游带有探险的性质,不可能满足广大游客的需求,剩下的就只有像到“自然保持区”这样的地方去进行“生态旅游”了。要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显然并非一般的地方政府、组织和个人可以做到的,这不仅涉及到了土地的所有权等问题,还涉及到资金以及人员等问题。所以,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的自然保护区都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任何活动以及由于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大都进入“国库”,或作为维持保护区的正常费用。然而,绝大多数的自然保护区又存在着一个“地方”问题,也就是说,进行生态旅游的游客有一个与东道主地方社会发生关系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戈德发(Goldfarb)在一项报告中分析到:在这种情况下,东道主地方需要承受由于生态旅游所带来的一列系问题、困难和后果,而由旅游所创造的利益和利润中的大多数被国家或者那些相关利益联盟所抽去,而这是制约东道主社会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3]而按照这一报告的描述,绝大多数从事生态旅游的目的地社会,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对生态旅游没有那么高的热情和兴趣。笔者在2020年春节期间到美国的夏威夷旅游,就遇到了当地原住民因旅游对他们家园生态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旅游收益惠及他们的不足而进行的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
虽然“生态旅游”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提出,但所制定的目标和原则却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而有所调整。比如,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生态危机”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旅游”也被注入了新的理念和价值。具体说,作为工具概念,“‘环境’用于人类学解释的各种途径——一个当前称为生态人类学的开拓中的领域。”[24]在很长的历史表述中,“环境决定论”一直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简单表述为:自然决定文化。这个原则迄今并未改变,只是或许这一理论被“说过了头”,或被“过度阐释”,在人类学领域里便出现了所谓的“可能论”,认为特殊的文化性质和形态的产生普遍基于历史传统而非环境,这一理论的基调主要来自博厄斯。此外,各种理论、观点甚多,此不赘述。概括而论,从人类的发展史看,如果说两个关键词可以最大限度地予以概括的话,正是自然-文化。我们可以将这一母题简述为:生态具有自然的能量,文化具备自在的能力。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面对生态危机这一世界性的难题,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中国采取有力政策行动。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并确定于2021年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25]大会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言中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26]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旅游”已经从既往的“以人为本”的旅游提升到了一种更高的要求:“以生命为本”——保护地球家园中所有生命的责任。这也是生态旅游在今天所产生的特殊的历史价值。
简言之,旅游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自然、人文活动的程度与限度。旅游本身包含着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体验与体认。今天人类正面临着“生态危机”与“生物-文化多样性危机”的重大挑战,旅游也越来越多地羼入了时代的因素,尤其是生态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