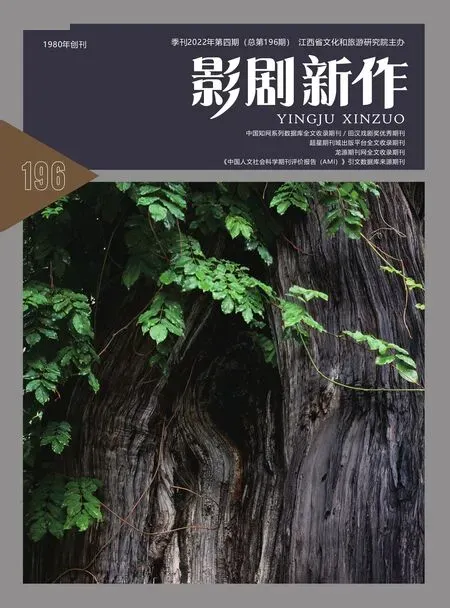漫游者·孤岛身份·双重生活
——刁亦男影片中人物的文化属性研究
曹 茜
2014年刁亦男凭借《白日焰火》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并开始得到了国内电影界的广泛关注,刁亦男的创作低产却优质。自2003年的《夜车》以来,17年间创作了四部电影,在数量上,和同时代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陆川、管虎等人比,未免相形见绌。但较低的产量也使得刁亦男能全力打磨剧本和电影制作,从而保证了影片的质量。
刁亦男的作品近乎极端地关注着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同第六代导演一样把镜头聚焦于底层的边缘人物,但他更为关注的是人物充满矛盾、又令人悲悯的精神世界。刁亦男的四部影片都是现实犯罪类题材的作品。他也偏爱这类题材,因为刁亦男曾经说过他的电影并不是以社会性见长,不一定要强调反应社会,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在电影里随着故事的发展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他更注重对人物内心及其精神世界的探索。刁亦男早期作品《制服》《夜车》和后两部《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在电影风格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后两部作品表现出浓浓的黑色电影和暴力美学的特征,但黑色电影的外壳之下仍然是以人物为核心的人性探索。在对人物深度关注的框架下,刁亦男影片中的人物也表现出了一系列的文化属性,他们处于不同的城市空间,但都是各自城市中的漫游者,在人际关系的建构上处于孤岛之中,不约而同的过着双重生活。
一、人物的空间状态——漫游
刁亦男影片中的人物在空间中都处于一种漫游的状态,无所事事的游荡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漫游者。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阐释了“漫游者”的概念,并将他们和对城市的现代性批判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人们对城市的现代化深度解读的目的。所谓“漫游者”区别于道路上的行人,他们步伐轻松地行走在街头巷陌,对城市空间的一切表示关注,与人群保持即密切又疏离的关系,漫游状态使他们与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城市空间始终持有冷静旁观的态度,使现代化的多种面貌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将城市内核外化为了一种可供人直接观察的景象。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漫游者的意象也逐渐多元化,我国城市现代化催生的小城镇空间也使电影空间中产生了与本雅明阐释的“都市漫游者”截然不同的“小城漫游者”的形象。“都市漫游者”被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他们在休闲之余漫步街头,独立在城市空间之外,成为一个彻底的空间观察者。当人们将自己置于这个空间之外的时候,就能够对空间景象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而小城漫游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是空间的观察者,还深深嵌于所生存的空间之中,是迫于物质生存或是精神矛盾的一个漫游者,这些都与他们生活的城市空间和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联。
作为银幕形象的小城漫游者本身具有较强的复杂性,这与现代化洗礼下的城镇空间息息相关。小城镇一边受城市文明的洗礼,一边又无法摆脱乡村文明的影响,现代化和城市化给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全新认知,但自身的生存技能和文明程度又很难跟得上现代化进程,这就使他们处在一个转型的矛盾点上,一系列的生存压力,使他们既游离于社会又因为生存问题而嵌入社会之中。刁亦男影片中漫游者的身体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人物经常是以沉默的状态四处游荡,从外表上看冷情又麻木,但却对外界保持高度的敏感,他们住在这座城市但又不属于这座城市。刁亦男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边缘人物的困苦生活,而是个体的心理状态,深入挖掘“小城漫游者”这个群体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
无论是王小建,张自力,周泽农这些男性⻆色,还是吴红燕,吴志贞,刘爱爱这些女性⻆色,在影片中无一例外都是漫游者。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男性拥有主导权,把女性放在“被看”的位置上,相反,刁亦男的电影中有时恰恰是女性引导男性完成了这个漫游的过程,这种外化的“性”的吸引力实际上有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女性的无意识引导使男性⻆色的漫游过程隐藏在叙事之中。最典型的就是刁亦男影片中“蛇蝎美女”的形象,“蛇蝎美女”作为黑色电影的标配出现在《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无论是吴志贞还是刘爱爱,她们都作为“漫游者”出现在刁亦男的影片中。电影中很少有把女性放在“漫游者”的位置上,因为“漫游者”拥有的是“看”的权力,刁亦男抛开了传统的性别划分,把女性放在了“看”的位置上。他影片中的男女同处社会底层,都是边缘人物,男女没有什么分别。影片对吴志贞生活空间的展现主要是在洗衣店、滑冰场、满是大雪的哈尔滨街头巷陌,而她的私人生活空间的展现仅仅是在影片开头,在她家里门帘下的一双腿,并没有身体的完整展现,这更表现了人物的一种“无家”状态,她可以完整的出现在城市的任何地方,但唯独没有在家中的完整身体影像。而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刘爱爱所出现的场所都是公共空间,陪泳女这个丝毫没有私密性的职业使她成为边缘中的边缘。她是周泽农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她有充分的理由游走在各个公共场所,如果说通过周泽农,观众看到的是男性世界的弱肉强食,那么从刘爱爱的视⻆上来看,她是对这个世界秩序的一次颠覆,她在无意识中掌控着叙事走向,决定着很多人的命运,也是在刘爱爱的视⻆下,观众看到了周泽农的另一面。与一般意义上的“蛇蝎美女”不同,刘爱爱的结局并没有以男性对她的制服终结,她的漫游者形象给了她主动的“看”的权力,影片中有很多刘爱爱的主观视点,她以第三视⻆观看并参与了这场利益⻆逐,实际上刘爱爱身上有男性因素的存在,所以她并没有延续那些男性因为阉割恐惧而将“蛇蝎美女”制服的结局。“蛇蝎美女”在影片中作为“漫游者”,她们一面与宿命抗争,一面成为了社会的观察者和见证者,她们与男性拥有共同的文化属性,她们的经历也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副面孔,并且通过她们的眼睛,观众看到了主人公身上的复杂性。
导演在影片中大量通过放大公共空间,弱化私人空间来完成对“漫游者”的身份塑造。王小建藏钱的高架桥、吴红燕的两城奔波、张自力的宿醉街头、周泽农的东躲西藏等等,影片中展现的人物的主要活动都是公共空间,以此来突出人物“无家”的漫游状态。《制服》里的裁缝王小建大量的时间都是游走在公共空间里,再加上他伪造的警察身份使他能够以一种“巡视”的姿态正大光明的游走在街道上。王小建的这种“空间观察者”的形象在影片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他观察着警察的行为姿态并进行有意识的模仿,并且把假冒警察而骗来的钱藏在高架桥的石墩下面。导演把藏钱这样一个私密性的行为放在一个及其开放的公共空间里,这样的设定再次弱化了王小建的私人空间,而突出他所生活的公共空间,给人一种无家可归的漫游感。在漫游的过程中,王小建一方面进行着自我身份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在受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情境的影响,导演以他和这个社会的密切接触和形象模仿来达到一种反思的目的。
《夜车》里的吴红燕最经常的一件事就是坐车从平川到兴城去参加婚姻介绍所的单身舞会,她不停的穿梭于两个城市空间,充当两个城市的空间观察者。人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这种漫游的状态,影片中多次把镜头给了吴红燕往返两地时在车里的状态,她看似是去寻找感情慰藉,实际上是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麻木的状态,导演在突出人物这种没有心灵归属的游荡感。她的住所是在一个阴暗的楼房里,房间一间间的紧挨着,空间的私密性并不强,她充当的不仅仅是空间观察者的形象,更多时候是人物的观察者,从而达到导演通过她的视⻆来探索人心的目的。
在影片《白日焰火》中,几乎没有对张自力私人空间的展现,家庭和事业上的打击都使张自力丧失了尊严和信心,像个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的游走在街头,而破案的本能又使他的漫游从漫无目的转向了具有一定社会观察意义的活动,他在吴志贞的引导下无意识的完成了体验社会、观察人物式的漫游过程。
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中,周泽农这个形象在影片中一直是处于一种犯罪逃亡的状态,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出现在火车站,筒子楼,野鹅塘等公共空间中,恰恰是他躲藏的这些公共空间形成了一个底层社会人狭窄的生存空间,他是一个被所有人都抛弃的人,包括他自己,逃亡状态使他必须不断地游荡在社会各处,观察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部影片的取景地在武汉,但是导演抹去了现代化武汉的特征,选择了一个在武汉边缘的“三不管”地区野鹅塘,它处在一个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又恰恰符合“小城漫游者”的生存条件,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碰撞的结果,它更能够让人看到现代化发展的另一面,这些地方空间逼仄、氛围压抑,这也是对漫游者的一种封闭和困锁,导演不仅通过周泽农的漫游者身份去看各色各样的人,还通过他去看生死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
刁亦男影片中的人物在不同目的驱使下游走在公共空间内,这意味着人物有意识地去融入社会,想跟社会走的更近一点。但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他们的能力、身份、性格、社会地位都使社会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想要得到社会认可,想要找到自身价值,甚至不惜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回归社会,但都近乎无功而返。他们是社会的体验者和观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社会规则的有序性,他们的经历让我们能看到现代文明的另一面,那些模糊善恶的事情一次次的在他们面前上演,仿佛他们应该看到的世界本就是秩序失衡的。但他们的身份注定对惩恶扬善没有丝毫作用,甚至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就与黑色电影有了相似之处,黑色电影中最重要的就是宿命感,人物始终无法逃脱的宿命感,所以漫游者的身份状态也为刁亦男的黑色电影美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人物的社会关系——处于“孤岛”之中
刁亦男的影片像是一面镜子,用它得以窥见现代化进程中阴暗的一面,人物的“孤岛”身份是刁亦男对社会底层人群生存状态的描写,也是他探索复杂人性的开端。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每个人都不是孤岛”,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总有一些人被发达的都市拒斥在外,处于孤岛之中。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的,而刁亦男在影片中却把人放到了孤岛之中来弱化人存在的社会属性,这种孤岛不仅仅是客观环境带来的,还包括人的精神孤岛。弗洛姆说:“一旦个人已变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1]在刁亦男的影片里,有着大段大段的沉默,主人公几乎不与任何人交流,人物的社会属性被极大弱化,当主人公不堪忍受孤独而努力去突破生存困境,寻求精神慰藉时,又往往是失败的。一方面他们无法改变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只能无力又无奈地生活在城市边缘;另一方面他们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交流的困境使内心的孤寂、压抑和无处宣泄不断堆积。刁亦男影片中的人物都是城市的漂泊者,是社会发展中高度的被困者。
刁亦男始终把叙事场景放在城市阴暗的⻆落,试图窥见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影片普遍影调阴冷,主人公活动多是在阴雨天气或者是夜间,几乎没有阳光普照的镜头,一方面与他想要表现的人性复杂、人物关系的暧昧性有关,另一方面与人物的生存处境、社会状态有关。《制服》中的王小建面临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在物质层面王小建的父亲瘫痪在床,一家人只有王小建有生存能力,由于时代发展,工厂改制,小人物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生活权力都被剥夺,现代城市的发展冲击着底层人们的生活,不断的有人被社会所淘汰,现代文明的发展与底层人们生活的矛盾是造成影片悲剧的关键性因素。在精神层面王小建就像是小城中的透明人,个人尊严因身份地位受到打压,他没有受到社会带给他的任何善意,仿佛是被整个社会所孤立的人,所以他把内心对权力和尊严的渴望寄托于能改变他身份和地位的警察制服身上,只有穿上了制服他才可能以警察的身份和地位在这个城市里获得一席之地。
在电影《夜车》中,女法警吴红燕是处于一种极端不正常的生活状态之中,丈夫去世多年,每天的机械工作使生活没有任何波澜,她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情感交流,身体和精神上的孤独使她不断试图打破这种困境,想通过相亲找到精神慰藉,甚至为此甘愿被骗。影片中还有大量的女主⻆麻木表情的特写,尤其是在往返平川、兴城的车上,两种身份的转换消耗了她大量的精力,我们从这些镜头中就能够看出人物内心是无比孤独的,连一个能跟她正常对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在她误以为想要杀她的李军是她的追求者时,几乎是心甘情愿的跟她走了。而李军的出场就道出了人物的“孤岛”处境,他的出场是极具身份象征的,浓烟滚滚的工厂,李军穿着染着灰的白色工作服,戴着帽子,护目镜,人物的面部特征基本都被遮盖住了,在整部影片中和他有过语言交流的只有吴红燕一人,他的处境是压抑的,被生活逼到了绝境,放弃了和这个世界做任何交流。妻子被判死刑,儿子也被别人带走抚养,这就意味着他不再有任何亲近的社会关系,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意义。他的再次出场是在一条无人的河上,李军独自一人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只小船上,气氛悲凉,接着就是李军因偷船被追打,划着船落荒而逃,人物的两次出场就把人物身上的压抑和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想要拼命划船逃走但又逃不开宿命。他最终的归处,那个人迹罕至的水电厂也就成了“孤岛”的象征。他不知道他的遭遇应该向谁发泄,所以只能找到了妻子死刑的执行者吴红燕,意图杀了她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底层生活的困苦逼着他走向了犯罪和暴力。吴红燕和李军的同病相怜构成了两人关系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在这段畸形的关系中,他们都像是被现实不断鞭打孤身而行的白马,想要抱团寻求一点精神慰藉,摆脱自己“孤岛”的处境。
《制服》和《夜车》中人物的“孤岛”身份更多的是由于个体身份与外界环境的冲突而被动生成的,但在《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中主人公的个人选择是“孤岛”身份生成的主要因素。张自力挽留妻子失败,在情感上孑然一身,又因为工作中失手打死人而从警察变成保卫科工作人员,身份转变无疑使他丧失了生活的尊严和信心,经常醉倒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这是一种近乎无家可归的状态。导演在影片中刻意去弱化张自力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突出了个体的精神状态。张自力的颓废和潦倒也使他无法融进的工作群体中,被同事嘲笑,生活上的孤身一人没有归宿,事业上的不得志都为接下来的他试图改变现状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吴志贞暗生情愫奠定了基础。而吴志贞作为典型的“蛇蝎美女”,她是张自力证明自己和找回权力以及男性尊严的一个道具,吴志贞的出场是门帘下的一双裸露的小腿,并且伴随着呜咽的哭声,腿的出现在电影里往往跟性有关系,这也预示着案件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吴志贞在影片中是男性欲望投射和化解阉割恐惧的对象,从梁志军的监控到张自力的背叛,吴志贞作为一个女性⻆色始终没有逃脱男权社会的掌控,她也曾试图抗争过,借警察之手摆脱梁志军,想要回归正常社会,但最终还是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张自力从失权到得权的过程是通过欺骗吴志贞完成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的捍卫,影片的最后张自力看似回到了以前的工作岗位,找回了生活的尊严,实际上他在排练厅的那段疯癫似的舞蹈和屋顶燃放的白日焰火都表明了他还是孤身一人,又回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孤岛”。
《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周泽农从开小偷大会时他就是独自一个人在最后面的⻆落里,呈现出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从他没收黄毛的枪,愿意赔付猫眼医药费,可以看出他在那么多人里是“守规则”的,不像是一个强盗,更像是被生活所迫走上了这条路。后来他失手打死警察被通缉逃亡,身边的人为了赏金而背叛他,使他彻底处于一座“孤岛”之中,他自己成为自身最大的价值,利益面前是没有朋友的,周泽农此时就像一头困兽,所有人都在围捕他,道义在金钱面前是相当脆弱的。刁亦男曾经说过人跟动物园里的动物区别不大,他也喜欢在影片中用动物来表达象征意义,影片中在警察抓捕周泽农的时候给了动物园里很多动物的特写镜头,动物仿佛在围观这一场捕猎行为,这时人和动物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对调,人类世界此时像是一个动物园,而动物站在了人类平时所站的观察者的位置,围观着一场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人类社会也在遵守着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此时的周泽农在精神上也是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他唯一的情感宣泄对象刘爱爱都问他你为什么不逃,其实周泽农这个人物他要自己完成自我救赎,他是站在了一个人性的翻转点上,从影片中人物“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上来讲没有人会真的理解他。周泽农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无疑是一个被困者,他看似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实际上怎么样也逃不开走向死亡的宿命,他和陪泳女刘爱爱的暧昧情感也同样是两个边缘人物的互相慰藉。而刘爱爱就是影片中男性欲望的对象和暴力奇观中的必需品,而她又是一个非典型的蛇蝎美女,她的孤岛身份源自于她的边缘地位和男性对她身体的掌控和欲望,但她最终消解了男性权力,当她和杨淑俊抱着30万现金向镜头走来的时候,刁亦男颠覆了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女”的形象,是对女性意识觉醒的表达和呼唤。
孤岛身份展现了人物与社会的格格不入,人的社会关系大大被简化,成为社会的“失语者”。他们生活在这座城市,但都很难真正的和城市建立关系,导演刻意的抹去了有关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影片的地点和人物便可以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它可以是任何城市,我们也可以在任何城市的⻆落里看到这些绝望、孤独又无力的人,在城市改革、时代变迁之后这些个体的迷茫与无助在影片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刁亦男影片中的主⻆被欲望操纵,被孤独浸泡,展现出的底层苦楚不是社会之苦而是人之苦,但是在小人物的孤独苦楚之中总能找到一丝人性的微光。
三、人物的个体存在——具有双重生活
刁亦男影片中人物的另一个文化属性就是他们都具有“双重生活”,这几个人物都有他们双重的一面,或者有些心灵阴暗面的呈现,或者有不同层面的梦,一直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内心的梦,这种双重生活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物在寻求身份认同。拉康认为主体是在与他者的认同关系中建立的,没有脱离他者而独立存在的主体,主体和他者的身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身份的变化与社会发展、人际关系、人物性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身份的变化也更利于深刻地反观主体。
主体的认同欲望从镜像阶段起就开始了,婴儿在镜子面前区分了自我和他者,消解了独立存在的主体,此后却又不断地在寻求着他者的认同来重建自我,并且这种认同的欲望伴随终生。刁亦男的四部影片中都有主人公在镜子面前的影像,这些镜头都表现了主人公想要通过镜像来探知自我,进行自我确认,然而镜子面前的自己也是在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就像镜像阶段的儿童在镜子中看到的并不是他们自身,只是一个用他人眼光来建构的影像,因此,自我生命便是在一个“误解”的迹象之下开始,而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被探知。刁亦男影片中的人物都是底层边缘人群,认同的匮乏使他们难以建构自我,所以他们渴望得到身份的认同,通过不断变换主体的身份来满足认同的欲望,从而得以建构自我。主体身份不断变化的背后表现的是人性的变化,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主人公对自我的主动探知,影片中人物的双重身份和双重生活最终都是刁亦男对人性的深入探讨。
导演在双重生活之中把人性的两面抛开给世人看,但这个两面性不能单纯的用善恶的道德观来评判,这种设定遵循着黑色电影的一贯准则,打破了常规意义上的道德观念,用人物的双重身份引出双重生活以及在两种生活之间相互转换所涉及到的伦理道德和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刁亦男在人物的⻆色设定上也随着拍摄经验的丰富经历了由浅显到隐晦的变化。《制服》中男女主人公的双重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双重生活都是非常明确的,王小建实际上是一个裁缝,但另一重虚假的身份是警察,郑莎莎是个售货员,同时也是个坐台小姐,他们互相隐瞒着裁缝和坐台小姐的身份,以更加体面的方式来寻求着身份认同,这两种身份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主人公深藏内心的欲望。作为裁缝的王小建在社会上到处碰壁,被看门大叔呵斥,被女孩子轻视,这些遭遇都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对权力、尊严、爱情的渴望,而警察的身份恰恰就是满足这些欲望的载体。作为警察的王小建追求权力、金钱,享受以虚假的身份带来的利己快感,消解底层生活所带来的自卑,而这种利己快感的获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性的快感。郑莎莎就是他享受正常男性拥有尊严权力的工具,在男性主导话语权的社会体制下,警察的身份无疑使王小建拥有了男性本该具有的话语权,他享受着郑莎莎的依赖和崇拜,这实际上是性欲望获得满足的过程。而郑莎莎就是男权社会下的附属品,他企图依靠男性来改变生活状态,但她所喜欢的王小建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就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样,“警察”王小建是那个蝉,裁缝王小建是那个黄雀,他们的双重身份都使他们在对方的生活里即充当着蝉,又充当着黄雀,所以当他们得知对方有隐藏身份的时候,都默契选择了秘而不宣,留给了彼此最后的尊严和体面。他们以原本的面目无法得到认同来建构自我,所以只能试图用更为体面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与社会接触来获得认同,由于彼此虚假的社会身份,两人最终还是没能通过建构他者来获得身份认同。刁亦男想要表现的人性的异变随着人物身份的变化而完成,双重生活之中揭示的是人最本能的欲望。
从《夜车》开始人物的身份就没有了明确的区分,而是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中表现出来。吴红燕机械理性的工作使她长期压抑自己的欲望,冷血、麻木、无情的背后是炽热翻滚的欲望。一个冷静理性的女法警,背后却是一个渴望得到精神慰藉的相亲者,她不断地在这两种生活之间转换,把自己耗得筋疲力尽。人前的吴红燕常年孤单,她的生活像是机器一样,不会起任何波澜,但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情感的渴望,所以才不断的去往另一个城市的婚姻介绍所。吴红燕的本能欲望一点点冲破束缚,从不敢看镜子里的隔壁女人到她开始独自一人对着镜子舞蹈欣赏自己,这是受压抑的本我的不断展现,是她开始直面自己的欲望,也是她试图在镜像中通过建构他者来确认自我。吴红燕的这两种生活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是对于欲望的极度压抑,一种是对欲望的毫不掩饰,我们不能说哪个是她哪个不是她,吴红燕想在双重生活中确认自我,通过寻找伴侣来获得身份认同,找到作为人的悲欢喜乐,而与李军的这场暧昧关系也是她想要回归“人”、与他者建立关系获得身份认同的最后挣扎。
《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从警察到保卫科干部,通过钓鱼的手法,把自己装扮成喜欢一个女人的男人,实际上也是双重生活,在跟这个女人和离开这个女人前后的身份是有所区别的。他一边是吴志贞的追求者,一边是一个渴望回归常态的破案者,张自力的这种变化是有目的性的,他企图用“出卖”吴志贞“来邀功,回归到警察岗位,实际上也是对身份认同的渴求。妻子的离开,工作的失误使他丧失了作为男性的尊严、权力和信心,再也找不到能够进行自我确认的他者,他的双重生活代表的一边是对权力、尊严的渴求,一边是妻子离开多年张自力潜意识里渴望拥有的情感归属,对感情和权力尊严的双重渴望使他不断地在双重生活之间转变,并困扰其中,本质上还是主人公通过不断变化的身份来寻求认同。最终张自力最终重获对人生的信心,而吴志贞在背叛与被背叛之中都是男性的掌中物,无论是对梁志军、洗衣店老板还是张自力来说她都是男性身份自证的工具,她也试图挣扎过回归正常社会,做回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但她始终没有得到过身份认同,因为她用以建构自我的“他者”张自力的身份是虚假的,只有她得知张自力“钓鱼者”的真实身份的那一刻,吴志贞才获得了建构自我的他者,最终完成了人性迷失的救赎,两人最后都卸下了心里的重负,走向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周泽农的双重身份表现在一方面他是个小偷,是个亡命之徒,另一方面他是侠义精神的殉道者,这两个身份无疑是冲突的,但在冲突之中是最容易揭露人性的。《南方车站的聚会》中构建了一个以“利”为中心的“江湖”,它写尽了人为利而做出的恶,但又通过刘爱爱的视⻆给我们构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周泽农。在这个江湖世界中,周泽农是唯一一个侠义精神的遵循者,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殉道者,区别于普通的亡命之徒,他心中有道义和家人,纵然也有凶狠暴力的一面,但这一切的动力是把悬赏金留给妻儿,这两种身份差异的对比颇有种“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味,人的残暴和柔软是一体共存的。他被宿命逼着一步步走向了逃亡之路,却在通缉之下选择让妻子告发他获得赏金,这种选择是他身份变化的起点,使这个形象有了英雄主义的色彩。周泽农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阴沟里,在这些人的眼里,道义和金钱是不值一提的,所有人都在为了30万而编造谎言,但周泽农在面对在劫难逃的命运时选择了道义,这种对比无疑是非常明显的,人性中的光明最后还是战胜了黑暗。正是通过刘爱爱这个他者视⻆,周泽农获得了身份的自我确认,得到了社会认同,尽管这个认同的“他者”只有刘爱爱和杨淑俊,廖凡饰演的刘队长最后或许明白的周泽农和刘爱爱的算计,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或许在他眼里的周泽农身份已经有了改观。周泽农的自我救赎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他身上也体现了刁亦男导演对个体生命的悲剧性思索,周泽农的双重生活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说中所阐述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他的第一重身份是对“生本能”的体现,例如他偷盗、装死逃过帮派清洗、失手打死警察,这些都是周泽农对生的本能渴望,而影片最重要的自我救赎过程是对死本能的悲剧性展现,他始终意志坚定地选择用死亡来弥补妻子和孩子,正如他回答刘爱爱问他“你为什么不逃”那样,他说“他不知道要逃到哪儿去,只知道要把赏金留给屋里”,对于挣扎在泥潭里的周泽农来说,当他知道他自己的最大价值是他本身的时候,并且这个自身价值量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抵抗的,这种对于死的本能渴望就是巨大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二元一体同样出现在《夜车》的女主⻆吴红燕身上,吴红燕想要获得正常人的悲欢喜乐这是一种对于生本能的体现,而影片的最后吴红燕知道李军要杀她却还是带着向死的心回到李军身边,这是一种死本能的表现,对生活的麻木以及难以逃脱的宿命感,使其产生了对死亡的本能渴望。
导演想通过人物的双重生活引发观众对复杂人性的思考,人物的双重生活都关乎本能欲望,蕴含了底层人群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探寻。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所处的空间是城市化进程的过渡体,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时代所忽视,认同的匮乏使他们不断转换身份来满足认同欲望,由此在双重生活中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实际上这是刁亦男探索人性的一个展现方式,因为不同的生活能够展现人性中不同的东西,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或者是某些选择之下,一些内在的不同以往的东西就会表现出来,刁亦男在人物的双重生活中完成了对边缘人物人性善恶的挖掘。人物都在双重生活中寻找一些东西,那些内心的渴望,命运之途的挣扎和徘徊在双重生活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在刁亦男的影片中,我们都不能用好坏善恶来单纯地评价人物,他影片中的人性都在绝望和挣扎之间撕裂,然后一次次地彻底颠覆,他想要观众通过影像去反思人性。导演执着的通过摄影机去窥视人心,揭开人物在面具下的另一种生活,影片中人物之间的较量难言胜败,胜利者未必胜利,失败者也未必失败,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表象,而电影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离奇故事把镜头对准人最深处的本我,来表现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