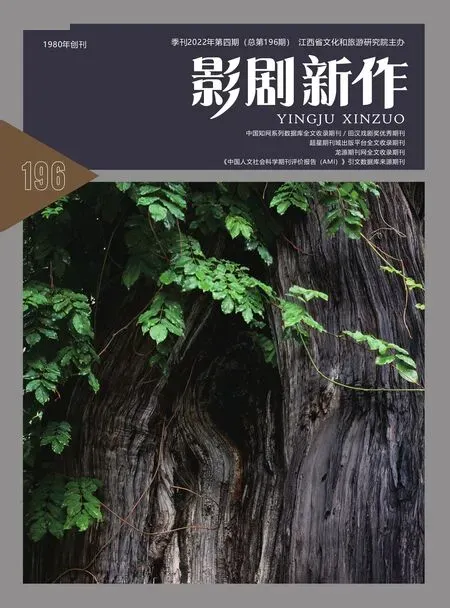非线性时间与疏离空间下的遗忘与共情
——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童一凡
“我感觉我的叶子好像要掉光了。”这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安东尼在混乱的时空、衰老的生命里无助的自白。当生命的严寒袭来,面对至亲的离去、记忆的撕裂、死亡的恐惧时——困在时间里的人们又该何去何从?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以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安东尼为全片的主要叙事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混沌、迷茫而又令人心碎的世界。影片的叙事把情节安排得如同迷宫般交互切换,使得现实与臆想交错并行,建构了独具一格的影像时空。
一、无序的时空:拼凑与重塑
时间和空间是电影艺术构造文本的依凭,一个优秀的导演总是能够出人意料地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中,将一个真切的故事以一种全然陌生化的方式讲述出来。电影的时间叙事通常指的是,把时间(及其对时间的操控)作为电影叙事和表达的主要手段。[1]时间作为一种叙事手法时,意味着线性或非线性时间的缩放、畸变、折叠、复原进入了电影的叙事和表达的每一个过程;而空间叙事则意味着电影通过对于空间的使用来组织和叙述整个故事,即“一是导演对空间的选择、表现和组合等工作;二是指电影叙事空间本身的叙事性以及叙事空间的选择和处理对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与叙事结构等的影响或制约”。[2]《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充分使用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叙述方式,用拼凑和重塑的方式,再造了一个无序的时空,安东尼置身于这个时空中,便如同被困于永恒困境之中。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本来是佛罗莱恩·泽勒自编自导的舞台剧,在从舞台艺术到电影艺术的媒介转换过程中,导演佛罗莱恩·泽勒对视⻆进行了巧妙的设计与安排,采取了特殊的时空构造方法。电影以一种含混而令人迷醉的方式讲述了日渐苍老而又不幸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安东尼在记忆与妄想的双重纠缠下,开始怀疑他所爱之人、他的信念、他的存在,甚至现实的故事。导演从安东尼的主观视点出发进行叙事,使得整部影片中所有的影像存在都带上了老人所特有的主观色彩,呈现出一种极不可靠的印象主义破碎感。在这种强烈的个人化纲领下,进行了空间感与时间感的营造。
在空间⻆度上,导演通过对安东尼的公寓、安妮的公寓、医院、养老院等地点的组合和选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状态。在这个失衡、混乱、破碎的空间中,随时切换、变化,使得观众在观影中会产生对于影像世界认知的无序感——观众的这种心理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间的内心失序,跨越了屏幕,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此外,导演对于空间的使用不仅停留在直观的感官层面——使习惯于生活中稳定空间的观众感受阿兹海默病人混乱的空间,进而基于人类相似的心理结构产生共情;空间还在这里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需要在情节的推进和观众的思考下缓缓呈现与还原。这些不同的空间呈现出了高度相似的布局、陈设,导演有意识地混淆故事发生的不同场景,但在这些场景之中,导演穿插了暗示故事发展和人物心理状态的大量线索。譬如,在以蓝色为基调的养老院中,安东尼房间的构造与两处公寓房间是几乎相同的——镜子,衣柜,窗户,床等家具的位置,这一空间构造便暗示了安东尼将养老院这一空间在记忆中与曾经居住过的公寓进行相似部分的叠加重组;除此之外还有悬挂在墙壁上的小女儿画作,钢琴,壁炉,黄色和蓝色的塑料椅子等等线索,每个线索都隐喻着影像世界里正在发生的空间的拼凑与重塑。这种构造空间的方法,不仅让观众被卷入迷乱的叙事中,迷失在安东尼的碎片记忆之海里,更能够以不同空间里的他人视⻆(女儿安妮、养老院的客观视⻆)来最终还原真相,让作为观者的观众得以逾越虚幻与真实的鸿沟,梳理出故事本来的样貌。
观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一场观众跟随主人公的视⻆,接受着看似合理但时序拼接错乱画面的奇妙之旅。导演时间重塑的叙事手法在护工劳拉来访、安东尼与女儿女婿共进晚餐的那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一天里,不同于普通人默认的“早 - 中 - 晚”时间发展的规律线性,影片为我们展现的是“早 - 晚 - 下午 - 晚”的被重组的非线性时间。电影拍摄安东尼早上见到护工劳拉,紧接着的便是晚餐前安妮向丈夫说明父亲病情严重的情节,安东尼与女婿进行了不愉快的对话之后,下午安东尼外出前往医院看病,随之而来的是晚餐间隙,安东尼听到女儿和女婿关于养老院的争执。这样巧妙的时间颠倒完成了一个叙事上的诡计,让观众和安东尼脑海中认为的相一致——安妮妥协于丈夫的要求,送父亲去了养老院;而直到影片最后的叙述,我们才知道故事的真相。
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在患病的安东尼眼中,这都是真实的;然而对于观众来说,观众可以有意识地感受到这是导演有意地对现实进行扭曲,拼接与重构后展现的景象。屏幕内,安东尼置于困境;屏幕外,观众努力获得失序里的真实。时间与空间的重构同等地对剧中人和剧外人发生作用,而这种神奇的体验,最终将会指向水落石出之后众人的惊奇与感动。
二、丰富的意象:受困与遗忘
除了精心打造的乱序场景,电影中的诸多意象,以不同的方式赋予了影片更为深刻的意义和直击灵魂的穿透力。在概念表述的层面上,影片选择了“手表”“家”等意象,来表现阿尔兹海默病人安东尼身上的永恒困境。在具体的视听语言层面上,影片精心设计了具有丰富意蕴的音乐,进行对情节的暗示与情感的抒发。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指出:“要更好地理解一部电影的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该影片是如何表现其倾向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展现“影片的倾向”的方式便是使用物象。例如,影片的主要线索是“困在时间中”,而时间这一意象最直观的表达就是手表的使用。一开始是父女对话引入“怀疑护工偷拿手表”这一猜测,以致于到了父亲、女儿、女婿的三人晚餐前场景,父亲与女婿的矛盾日益凸显:父亲怀疑女婿的手表是自己的。而在“女儿找到父亲的手表”这一情节发生之后,这些敏感、猜疑、呓语被证实为是安东尼记忆缺失、心灵错乱的表征,对于“手表”这一物象的反复寻求意味着安东尼对于时间的遗忘和内心的孤独。影片的末尾,身处养老院中的安东尼没能找到手表,表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被彻底困于时间之中。“手表”不仅串联起了情节,成为了人物冲突的线索,更肩负了隐喻和象征的作用,手表的丢失、寻找、彻底消失正对应着安东尼晚年时期记忆和自我的丢失、寻找、彻底消失。
“房间”与“公寓”同样是一组重要的意象,暗示了本片的母题之一“家庭”。它充分地展现了外在空间的辽阔、时间的变动与人物内心的孤独。铭记的终会被遗忘,遗忘的幻影般再度出现,使得电影蒙上一层超现实主义色彩。
影片大量拍摄了客厅、厨房、走廊等空间感极强的场景,还常常使用空镜头来捕捉公寓内饰细节的调整,进而营造时间上的错乱感。很多镜头的内容都在讲述安东尼的状态,即:在明亮与幽暗交织的房间里,孤独的安东尼徘徊着、踟蹰着、寻找着,无助又彷徨,原本处处熟悉的家庭在老去的安东尼的视⻆下变得陌生且诡异,错乱的空间、非线性的时间,使得不论是剧中的安东尼还是观影的观众,都无法确定,在原本为“家”的公寓里行走时,沿着走廊、推开那扇门,出现的会是无助呼喊的小女儿露西?还是平淡无奇的杂物间?这种陌生化的“家”是影片讲述的“家”这一意象的表层,暗示、渲染了压抑的情绪。而在第二层,“家”这个概念参与了叙事,并且不断变化:安东尼在女婿家里被驱逐时,我们会对“家”的概念产生质疑;在安东尼身处疗养院时,“家”在他心里已然变成了一种遥远和无法抵达的状态。在故事的推进过程中,安东尼由寻找家园,到被家园抛弃,最终永远无法返回家园。他不存在于家中,他的真实的生活空间只在一个被幻象扭曲了的、衰老的心里,安东尼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影片意象的选用参与了叙事和抒情的进程之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脉络,也成为人物状态、心理、命运的外化,在影片中与主题相互应和。
“人的视觉会受到影像呈现形式的限定,而电影声音作为观众感知电影世界的本体存在,则是一种无形的物质现实呈现形式。”[3]除去“手表”“家”意象的使用,影片还成功地选用了大量的具有丰富意蕴的音乐。音乐同样成为了理解电影的一把钥匙,音乐本身的使用在片子里成为了一种意象。如片头的古典音乐,便来自于普赛尔《亚瑟王》的选段《冷之歌》,是掌管严寒的精灵被丘比特唤醒后唱的一首咏叹调,象征了“冬”和“冷”的意象。空灵缥缈的长段音乐一开始就为电影增添了几分厚重感,步履匆匆的女儿,戴着耳机白发苍苍的父亲,内饰华丽的公寓,故事的大幕拉开,音乐戛然而止,而属于父亲和女儿的寒冬,才刚刚开始。在影片接近尾声,女儿走出养老院的大门,她背后矗立着破碎的面具雕像,配合比才的歌剧《采珠人》的咏叹调之《她在花丛中》—“我仿佛听见她的声音”,于美梦里最熟悉不过的场景。这里音乐的使用象征了“梦”和“幻”的意象,无限飘渺梦幻,无限孤独寂寥。
三、深刻的共情:凋零与落幕
“电影中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本质上都与情绪有关,对于叙事艺术而言,情绪居于中心地位。”[4]这是普兰丁格所秉持的观点。一部优秀的电影能够带来巨大的感染力,其通过塑造⻆色、讲述事件所引导、形成的情绪会触发广泛的观众的情绪,从而指向人类内心最深层的情感。
在观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的过程中,我们透过迷乱的时空、变换的意象、抒情的音乐,进入了安东尼的精神世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共情定义为“个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可以说,整部电影中处处蕴含着安东尼的个人感受,从每一个镜头、每一处配乐中,我们都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安东尼晚年的精神图景。例如,导演多次拍摄了安东尼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见证了安妮的离去、孩童的玩乐、郁郁葱葱的树木年年岁岁、枯荣相生。这些画面里,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东尼面对安妮的离开,心中无限的伤心和不舍;面对充满活力的孩童,他又怀有一种对于旺盛生命力的强烈羡慕之情;在安东尼感觉自己的生命力如同像树叶一样掉光了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能够体会到晚景降至、不知道还能看多久窗外世界的无限悲哀——“我的叶子好像要掉光了......风雨裹挟着我的枝叶,我已经搞不明白发生的一切,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再也没有栖身之处了。”
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对于一个老人来说就像是来到另一维度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患者把自己与原本熟悉的生活与人割裂开来,在虚幻的破碎中,只有生命的流逝最为真实。子女离开、家庭消逝、自我消逝,我们目击了一位老人的濒临死亡;而《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恰恰把这种个体从外至内的缓慢的死亡过程刻画地细致入微。安妮的赡养困境、进入养老院中的情节是安东尼外在部分的逐渐死亡——无法养活自己,无法获取和社会的连接,无法获得生命的主体性,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之中,被永恒放逐;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安东尼自我否定的细节则暗示着安东尼内在的死去,即人自我认同的错乱乃至消逝。安东尼的职业是工程师,但是在罹患阿兹海默症之后,却不断否定着自己的身份,坚持自己是一位在马戏团工作的踢踏舞者;他最常饮用的饮料是咖啡,然而却不断抗拒这个说法,坚称自己爱喝茶水。当自我的认知混乱,一个人便彻底地处于了无助之中,走向不可逆转的在世间的消逝——这种消逝的最后,安东尼彻底忘记了自己是谁,只记得自己的名字是妈妈取的;他想要妈妈带他回家,带他离开这里;温柔的护工凯瑟琳安慰像婴儿一样无助痛哭的他……生命的循环终将回到原点,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一个人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前一刻,离去永不止息地来临。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带领观众走完的这段旅程里,我们看到了安东尼自我的凋零与落幕,他的恸哭与悲鸣也是我们的恸哭与悲鸣。安东尼的叹息何尝不是每一个观众,无论年龄、性别、地域、种族、国家,面对人类所无法避免的死亡的叹息!
安东尼呆在养老院中,回溯着错乱的过去,看不到任何可能的未来。他活在自己的时间里,而真实的时间又决不为他停留片刻,于是只能走向必然的消逝。我们为这样的故事而惋惜悲痛,在阿尔兹海默式错乱的叙事中,我们仿佛也是同样的病人,在风烛残年坐在养老院的房间,默默地守护着残缺的记忆。在影片放映的每一刻里,我们都感受着生命的凋落,共情着生命消逝下人的孤独。
四、结语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尝试了对于电影叙事空间的拓展。它采用了非线性的时间来参与叙述,同时以空间叙事的方式,把人们日常所习惯的稳定空间进行扭曲和再造。此外,《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设置了大量的意象与细节,为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使得观众深切地共情安东尼的命运。
一部电影最闪闪发光的,不仅是精彩的故事呈现,不仅是多样的叙述方式,不仅是充满延伸意义的象征符号,更是那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上掷出的圈圈涟漪——真正情感内核的浮现。我们期待着更多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的出现,也由衷希望除了对艺术作品的共情外,加速老龄化的社会对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及其家庭的更多关注,能减少哪怕一丁点遗忘带来的痛苦,能够让每一个人带着欢欣降临、伴随着尊严与亲情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