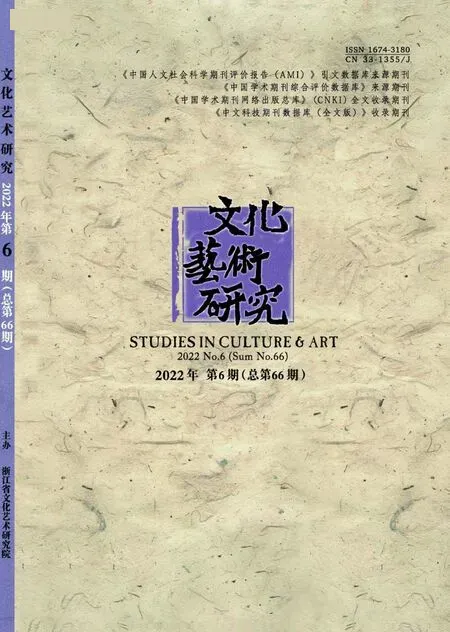“姿势”的意义:技术图像时代的“无根基之恶”
——从阿甘本到弗卢塞尔
姜宇辉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241)
尽管阿甘本的思想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但仍有可能且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种总体的、贯穿性的概括与阐释。只不过,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都致力于“统合(unified)”的工作①比如Alex Murray在Giorgio Agamben(Routledge, 2010)一书的开篇就明示了这个基本立场。,却鲜有人真正敢于展现阿甘本思想发展的内在的、看似难以调和的纷争与冲突,并进而由此展开别样的推进乃至批判。就后一点而言,内格里(Anotnio Negri)发表于2008年的短文《救赎的成熟果实》[1]中的看似极端实则锐利的评述,至今读来仍然颇具启示。他明确地将阿甘本置于德里达和德勒兹这鲜明对峙的两极之间,进而在否定与肯定、死亡与生命的张力之间呈现出其思想的最深刻的内在震荡与契机。
从否定性(negative)面向来看,阿甘本与德里达(乃至列维纳斯和巴迪欧)形成了呼应,因为他们皆致力于撕开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内部的否定性裂痕,甚至也不妨将阿甘本前期的一系列研究的基本方法大致归结为“解构”[2]。但他的思想同样具有积极的、肯定性的一面,那些关于“使用(use)”“行动(agire)”“共同体”等主题的深刻思辨,又展现出至为鲜明的抵抗乃至变革的力量①阿甘本思想的这一正一负的双重面向的对比,亦可参见Daniel McLoughlin: Agamben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age 51。。因此,面对阿甘本文本之中大量出现的如“未激活(deactivition)”“非实行(inoperativity)”这样的关键词,很多学者都望文生义地将其等同于逃避、隐忍甚至放弃,这似乎过于肤浅而仓促了。②阿甘本自己就明确指出:“非实行并不意味着怠惰(inertia)。”参见参考文献[6]。诚如阿甘本自己所言,他的哲思同样意在激活、召唤一种行动和变革之力,只不过此种力量不能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构建性的力量(potere constuente)”,而更是倾向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赤贫之力(potenza destituente)”③转引自Saul Newman: "What is an Insurrection? Destituent Power and Ontological Anarchy in Agamben and Stirner", Political Studies, 2016(2)。 “destituent”本文译作“赤贫”,主要基于三个理由:第一,“贫困”这个译法主要基于阿甘本中后期比较侧重的无政府主义这个脉络,尤其是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这样的表述;第二,“贫困”也显然是阿甘本写作研究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至高的清贫》;第三,以“赤贫”(而非单纯的“贫困”)一词突出那种从否定转向肯定的运动。。正如“赤贫”这个修饰词所展示的,此种力量或许首先呈现出浓重的否定性面貌(匮乏、欠缺、贫困),但进而发生了一种明确的转化,从否定到肯定,化无力为抵抗。
那么,遍览阿甘本迄今为止的思想发展,到底有哪一个(或几个)概念又真的能够切实且有效地展现出此种赤贫之力呢?那几乎唯有“姿势(gesture)”这个关键词了。
从时间脉络上来看,它早自阿甘本的第一本代表作《语言与死亡》之中就隐约显现,到《业:简论行动、过错和姿势》(以下简称《业》)这部近期的杰作,姿势这个主题的关键地位更是在开篇第一句话就得到明确断言。但姿势这个概念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贯穿性的力量,或许正是因为它得以真正在阿甘本思想的内部实现从否定向肯定的根本性转化。在《语言与死亡》中,语言在开端和本原之处所展现出来的否定、无力乃至“空(void)”与“无(nothing)”的形貌无疑是全书的主导基调。[3]但到了《业》中,姿势不但最终导向了“行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独特概念,更是由此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伦理和政治并非行动的领域,而是姿势的领域。”[4]由此,姿势不仅承接起否定与肯定这看似对立的两极,更是在艺术和政治这两个重要的社会场域之间形成了连接和互动。
但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是,阿甘本虽然也从姿势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不同艺术的门类,尤其是电影和舞蹈,但他却从未真正将批判性的洞察目光投向晚近以来整个世界越来越全面深刻转向的数字技术时代。而本文就尝试进行这样一个推进发展的工作,并试图以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为重要的对话者来建立起阿甘本与数字时代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二者之间呈现出众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比如对姿势的关注,对语言和图像的深思,对艺术与政治之关联的强调,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基本的哲学思路上来看,弗卢塞尔的核心概念“无根基(groundless)”或许恰好是对“去本原(anachos)”这个阿甘本中后期的重要范畴的最为深刻而有力的发展乃至修正。但所有这些线索或许最终都要汇聚于“恶”这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与哲学难题。阿甘本对集中营的痛斥,弗卢塞尔对纳粹暴行的反省,最终皆指向了数字的技术图像已经、正在、即将对整个世界所施加的“恶行”。
如果说“人类生存的无根基的本性”[5]xiv正是整个世界日益滑向的无底深渊,那么,阿甘本和弗卢塞尔之间的对话、艺术与政治之间的交织是否能够对此给出回应乃至疗治?我们希望在下文中探索答案,或至少是希望。
一、阿甘本思想的前后期转变:从“使用(use)”到“去本原(anarchy)”
关于阿甘本前后期思想演变的线索,学界固然早已有诸多的揣测乃至论断,但最为精当的其实还是他自己在《何为一种赤贫之力?》("What is a Destituent Power?")一文之中所做的自我总结。在文中,他不仅极为细致地梳理了自己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更是将向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和主题呈示得一清二楚。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正是他所拈出的、足以彰显从否定到肯定之转化的两个关键词,那正是从“使用”到“去本原”。
初看起来,以“使用”来概括阿甘本的前期思想似乎颇引人争议,但至少有两个明显的证据足以反驳这个选择。第一个证据正是来自《何为一种赤贫之力?》这篇文章,因为阿甘本在这里明确将“生产/制作”与“践行(praxis)”、“非实行”与“使用”彼此对照[6],而且在后文亦更突出了“使用”的那种积极行动的意味[6]。这显然体现出“使用”的那种从否定向肯定进行转变的趋势。另一个更为明显的证据就是,阿甘本在《身体之用》中对“使用”这个概念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解析,但很难说这本著作是否仍局限于他前期的框架之中。
不过,这两个一深一浅的印象或许尚经不起太多推敲。要想深刻理解一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作用,仅从文本的显豁表达来看往往并不充分,还必须深入背后的思想演变的脉络和方法转变的形态。那么,从方法上来说,阿甘本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关键要点何在呢?将他与福柯这位对他影响至巨的思想家进行相应的比照①在《万物的签名》开篇,阿甘本就坦承了福柯对他的巨大影响,参见参考文献[9],第7页。,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入口。
实际上,正如福柯前后期的思想方法的转换可以被概括为从考古学到谱系学一样,在阿甘本那里,这两种方法之间的更迭也同样是一条暗藏的主线。首先,有必要澄清考古学和谱系学之间的区别。关于这一点,福柯自己及诸多学者已经有众多论述,彼此之间亦有所出入,但大致说来可以概括为平面和深度这两个维度之分。②福柯自己对谱系学的“深度”的强调,尤可参见《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载《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考古学更关注的是在一个平面上尽可能地摊开各种差异性要素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此来动摇稳定的体制,模糊既有的边界,颠覆僵固的等级。借用德勒兹的极为精准的概括,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陈述,而“陈述领域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潜在性,一切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性都显而易见”[7]。但谱系学就有所不同,它已经不局限于平面上的关系和格局,而是试图探入深处,但又不是作为基础(foundation)和起源(origin)的深处,而是差异性的力量不断交织互渗,甚至冲突纷争的深处。对此,还是德勒兹的概括最为深刻准确。他在《尼采与哲学》第一章中虽然只字未提福柯及其方法,但对意义的“解释”和对力量的“评价”这两种方法恰好对应着考古学和谱系学之间的区分。考古学的研究是相对静态的解释,它致力于将差异的要素、隐藏的力量摊开展现在人们面前,令它们变得“显而易见”。但谱系学则正相反,它试图深入幽深曲折、混沌涌动的力量场域的深处,进而揭示出那些“可见”的格局和关系是怎样自“不可见”的力量的深处涌现而出、发生而成。
由是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以《神圣人》为代表的阿甘本的前期研究,所秉承的似乎恰好是平面化的考古学方法及其所探寻的对于意义的解释。如果一定要用一种力量的拓扑学模式来概括阿甘本早期的方法论范型,那似乎当属《神圣人》中明确总结出的那个介于“外部与内部、自然与例外、自然与约法之间”的不可能进行终极明确划界的“无区分地带”③参见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他在后面紧接着画出的类似韦恩图式的例示就恰是对此种“绝对的无区分性”的生动描绘。。实际上,这个无区分地带所运作的领域远不止于阿甘本在这个段落里面所列出的这几个两两相对的范畴。从zoe和bios,“生命”和“政治”,甚至一直到“制作”与“行动”,等等,阿甘本文本之中几乎所有的两极相对的范畴都可以且理应被纳入这个“界槛”式的拓扑学模式之中。这一点在阿甘本自己的论述和诸多二手研究之中得到了一次次的强调和认同。若如此看来,“使用”这个概念即便更为突出地呈现于他后期的文本之中,但它背后所依托的却仍然是考古学的方法。也正是在这里,得以对前文列举的两点质疑进行回应。首先,从《何为一种赤贫之力?》这篇文本出发,其初次集中论及“使用”的段落所重点援用的理论资源正是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的“中间语态(middle voice)”理论。除却其语言学的意涵,这个理论正是意在突出“被动与主动”,乃至“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不确定的区域”[6]。在《身体之用》的文本之中亦同样如此。在那里,不仅再度出现了对“chresthai”这个古希腊词的细致考证,而且,“无差异性区域(zone of indifference)”“既包含又纳入(exclusion, included)”“不可确定之界槛(undecidable threshold)”[8]这些说法也几乎与《神圣人》如出一辙。
既然如此,那么“使用”这个范畴也自然会带上考古学方法的“不足之处”①本文在此处加上引号,是因为只有将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进行比照之时,前者才会暴露出相对的“不足”。若仅就考古学方法自身而言,它多少是自足和自洽的。也即,一个研究者完全可以仅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描绘权力的机制和陈述的空间,而并不一定要兼顾谱系学的深度方面。。“使用”致力于揭示含混变动、交织互渗的绝对不可区分的地带,但对它来说仍然有两个困境难以回应。一方面,仅仅揭示出、描绘出这样的地带还远远不够,还应进一步展现出其背后所运作的、隐藏的、涌动的力量关系和场域。简言之,还理应从可见的表面探入不可见的深度。另一方面,既然“使用”之考古学无力揭示力量之“谱系”,那它也就由此暴露出最为致命的一个缺陷,即无法真正揭示变革的动力和行动的契机。考古学至多只能告诉我们“事已至此”,至于如何挣脱困境,打开可能,迈向变革,它既无力亦无意来回应,遑论解答。
阿甘本自己当然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两个颇为明显的缺陷,并由此给出了卓有成效的回应。最为直接的回应自然是主动求变,从考古学的方法转向谱系学的探查。这个转变当然最鲜明地体现于《万物的签名》这部阿甘本的“方法谈”之中。其中第三章的标题名为“哲学考古学”,但初看之下颇令人意外,其实文中所论述的显然是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比如,在一开始对“事实性的起源(origin)”和力量涌现的“本原(Herkunft / Entstehung)”进行辨析的重要段落之中,阿甘本就反复将其明确界定为福柯式的“谱系学”的范式。[9]83-84由此也就引出一轻一重的两重思考。从轻的层面看,确乎不妨说阿甘本所谓的“哲学考古学”无非就是福柯的谱系学方法的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但这样一来,他是否多少忽视了在福柯那里非常关键的考古学和谱系学之间的区分?当然没有。阿甘本之所以会将考古学和谱系学这两种方法等同起来,正是因为考古学这个词的词根“archē”本来就带有鲜明的谱系学的意味,因为它更突显出从不可见之力向可见秩序的转化。
但是,除了复述福柯既有的思想(无论用何种名号)之外,阿甘本的哲学考古学的独到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关键还是在于“本原(archē)”②之所以译成“本原”,也正是依据阿甘本对这个古希腊词的解释,它既是“根本(foundation)”,又是“原理(principle)”,参见参考文献[10],第57-58页。这个核心概念。或许在《万物的签名》中,它并未展现出多少别样的维度,但就在早一年出版的《王国与荣耀》中,它却已然展现出极具启示性的含义,开辟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点出了这个重要主题,即基督教神学传统之中对“存在(being)”与“行动(acting)”之间的内在张力的思辨,及其随后引出的对于权力和治理的深刻反思。在神学的思辨之中,上帝之“所是”这个本体论的维度与上帝之“所为”这个安济(economical)的维度,二者之间往往呈现出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由此亦引出了一个看似颇为极端的结论,即上帝对于世界的创制和治理本可以或本已经是“无根基(groundless)”“去本原(anarchos)”的。[10]55如果我们追问上帝“为何”如此创造世界,从根本上说,他实际上无法给出任何终极的“原因(cause)”和“理由(reason)”。这就引申出两个至关重要的思路。一方面,行动的去本原的特征本是为了给人的意志自由留出余地,进而为自我和主体性奠定基础[10]57,但另一方面,一个与本文的讨论更为相关的要点,即治理与去本原(anarchy)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说得直接一些,所有权力的运作根本上都是无根基、去本原的。[10]64
二、从“去本原”到“无根基”,从阿甘本到弗卢塞尔
我们看到,揭示权力本身的去本原之本性,这才是阿甘本的哲学考古学的真正要义和用意所在,也是他与福柯式谱系学之间的最根本差别。由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本原”和“去本原”这一对相关的范畴会日渐在阿甘本后期的思想中成为核心主题。它们不仅意在突破福柯的框架,更意在阿甘本思想发展的内部实现从否定向肯定的转化,从单纯对绝对不可分性的拓扑学描绘真正转向积极能动的行动。
然而,仅就去本原这个范畴而言,其实已经突显出一个有待进一步澄清和阐释的难题。如果权力的运作根本上是去本原的,那么显然会衍生出亦正亦邪的两个结论。
从正面来看,权力的去本原性无疑为积极能动的政治抵抗提供了极为直接而切实的动力。去本原,正意味着所有现存的秩序,从根本上说皆远非天经地义和牢不可破的。“事已至此”没错,但“何以至此”?在这背后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终极的原因和理由。既然如此,那么就显然为极端的变革和激进的行动留出了巨大的可能性[11],即“事已至此”,但“总可以变得不同”。我们看到,这不仅为阿甘本自己提供了一个从否定向肯定的转化契机,而且实质上是为政治行动提供了一个至为根本的动力和契机。也难怪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去本原这个关键角度来阐释、引申乃至发挥阿甘本哲学的积极、肯定的政治内涵,将去本原这个古老词汇与“无政府主义(anarchy)”这个近现代以来的激进政治运动明确关联在一起。实际上,阿甘本自己在《创造与去本原》(Creation and Anarchy)这部近作中也坦承,比起民主制,他显然对无政府主义更感兴趣。[12]54而在全书的收尾之处,他不仅再度明确将去本原视作权力的最根本特征,而且由此断言:“建构与毁灭在此不可区分地重合在一起(without remainder)。”[12]77这里,“不可区分”这个说法看似明显体现出阿甘本前期考古学的平面化特征,但实际上已经深刻展现出至为积极的行动力量。任何建构同时也都是毁灭,因为它的背后没有终极的根基,没有至上的目的,没有根本的理由,既然如此,毁灭这个根本的契机早已深深地打入建构的“本原”(或准确说是“非-本原”)之处。概言之,建构与毁灭之间的绝对重合,既非局限于考古学式的静态解释,亦非仅止于谱系学式的动态评价,更是指向了切实的行动,敞开了可能的空间。借用无政府主义的经典原理来阐释,正可以说,真正的“anarchy”并非是失序、无序或混乱,而恰恰是要揭穿那些强加的、胁迫的、压迫性的秩序的去本原性,进而以自主(self-direction)、自发的方式来一次次回归秩序之建构和毁灭的非-本原。[13]在《何为一种赤贫之力?》一文的最后,阿甘本在缕述了各种无政府、去本原的神学、政治和思想脉络之后,最终回归于“生命形式(form-of-life)”这个核心的概念。这里的形式恰恰并非来自外在的强加和压迫,而是源自生命本身所固有的那种创造与毁灭相重合、建构与赤贫相交织的行动之力。[6]正是在这里,当阿甘本的思想更为鲜明地转向肯定与行动之际,他的立场也确乎更为鲜明地从福柯转向了德勒兹。生命的形式,或许确乎与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vitalisme)之间展现出更为密切的关联。
但也恰恰在这里,体现出阿甘本所忽视(甚至无视)的去本原这个范畴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即更为阴暗和负面的形态。一切权力的运作都是去本原、无根基的,这既为积极的行动留出了空间,但难道不也同样为权力本身的任意妄为提供了最为邪恶的“理由”?与无理由的抵抗并存的,正是无理由的施虐。善是无理由的,但恶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此看来,阿甘本后期围绕去本原这个核心范畴所展开的积极抵抗的策略就要大打折扣,因为他难道不是忽视了恶的无根基性这一本不该忽视的相关面向?当然,基于阿甘本自己的思想发展,可以为此种看似致命的忽略提供一个有理有据的辩解。恶这个问题在他的文本之中虽然从来没有成为集中论述的主题,却显然是一个贯穿的潜在线索。尤其是在其前期对生命政治所展开的考古学考察之中,即便没有明确集中出现“恶”及相关概念,但几乎通篇皆在呈示现代性之恶的诸种形态、运作方式及相互关联。既然如此,当他后期更为集中地转向去本原之思的时候,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转换重心,从对恶的揭露和批判转向更为积极肯定的抵抗策略。
不过,这个辩解虽然在阿甘本的文本之中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但就去本原这个问题甚或难题而言,却很难自圆其说。一个显见的理由就是,对恶的批判这个否定性的面向和抵抗行动这个肯定性的面向,这二者始终是密切交织、难以分隔的。因此,即便在对肯定面向进行集中探讨之际,也一定且必然要关涉无理由、无根基之恶这另外一极。无理由之抵抗与无理由之施虐结合在一起,才是去本原这个范畴的全貌和真相。因此,以转向积极行动为理由,进而(哪怕是暂且)搁置对于无根基之恶的反思和批判,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无从捍卫的立场。当然,通观阿甘本后期的诸多文本,仍然可以发现恶这个问题的偶尔的闪现和潜在的隐现,但它与去本原之行动的密切关系,确实始终悬而未决,有待深究。
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就有理由转向弗卢塞尔这另一位思想家及其核心概念之一“无根基”①亦 有 学 者(如Andreas Ströhl)将“bodenlos”译 作“无 底(bottomless)”(Vilém Flusser: Writings, edited by Andreas Ströh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xix-xx),这样固然更贴近葡萄牙语原词的字面含义,但却多少错失了“无根基”这个译法之中的哲学意涵。“底”不仅体现出等级上的低微(高处/底部),更是展现出一种浓重的附属性的意味(底部作为支撑、衬托)。由此看来,更合适的译法似乎是“无基底”,但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译成“无根基”,是因为弗卢塞尔对“bodenlos”的荒诞性的第一重规定正是“无根(rootless)”。详见下文。,以此来更为切实地思考无根基之恶与去本原之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选择弗卢塞尔作为本文后半部分的论述重心,除了他与阿甘本之间的诸多显见的相似性之外,还至少出于三个重要缘由。第一,与阿甘本相近,弗卢塞尔自思考和写作之始,就将反思、批判现时代之恶作为自己的毕生研究主题。只不过,他不仅将恶作为一个潜在的线索和论题,更是作为核心的范畴和明确的问题进行多向度、多层次展开。第二,阿甘本对恶的批判,大多集中于历史的线索,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困境,而鲜有集中论述更为晚近的网络社会、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等所带来的困境和难题。在这一点上,对媒介领域进行过全面广泛研究的弗卢塞尔显然更胜一筹,而且,他极具启示性地提出的技术图像(technological image)这个概念尤其能够将否定与肯定、被动与主动、无根基之恶与去本原之力关联在一起,对当下的时代与现实展开极为深入而有针对性的批判。以上两点最后皆汇聚于“姿势”这第三个要点。仔细比照阿甘本和弗卢塞尔的姿势理论,既能够将相对宽泛的理论思辨带回到具体的现实论域,又得以由此细致生动地例示弗卢塞尔之洞见的深度与锐利。
“无根基”这个概念,在阿甘本那里虽也偶尔闪现,但其含义大致接近“去本原”②相关论述参见参考文献[10],第55页。,而在弗卢塞尔这里,它不仅有着颇为独特的内涵,更是基于特有的脉络。澄清这一点是理解弗卢塞尔的无根基之恶的相关论述的必要前提。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史的发展来看,这个概念首次明确出现并得到深刻阐释,还是在谢林的文本之中(尤其是《世界时代》和《对人类自由之本质的哲学探究》)。进入20世纪,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从列维纳斯到德勒兹,这个概念得到了不同方向的发展和引申。③关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无根基概念,可参见Lee Braver: Groundless Grounds: A Study of Wittgenstein and Heidegger, The MIT Press, 2012。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尤其第一章开篇部分)中亦有相关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也是从一开始就对弗卢塞尔有着深刻影响的两位哲学家,参见参考文献[5],第xvii页。不过,还是让我们先聚焦于弗卢塞尔的相关论述,再进而以哲学史为背景对其独特内涵进行深入阐发。
弗卢塞尔关于无根基和恶的论述,可说是遍布于他的早期文本之中,构成了他早期记述的两个最为关键的主题。先说无根基,他在同名著作的开篇就对这个概念给出了极为明确清晰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他一开始就将“荒诞”和“无根基”这两个重要概念关联在一起进行阐释。考虑到他对法国存在主义的熟悉和倚重,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荒诞感”的著名界定就注定成为首要的引线:“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①参见参考文献[14],第81页。弗卢塞尔在很多处都明确提及、引用了加缪的荒诞理论,尤其如参考文献[20],第10-11页。熟悉的生活背景的瓦解,支撑着整个世界从认知到行动的稳定框架之崩溃,这些既是荒诞感的起因,也是其本质。正是因此,“荒诞、希望和死亡互相纠缠的无情游戏”[14]84,也成为深刻理解荒诞概念的三个密切相关的要点。荒诞总是始于虚无的体验,而生活和世界的土崩瓦解也正是濒临死亡之绝境。面对此绝境,总有人要么起而抗争,要么顽强支撑,但最终都是为了重获希望。荒诞,就是在虚无和存有,绝望和希望,乃至死与生之间的持续不断的震荡。这也正是理解弗卢塞尔这一论述的正确起点。他援用来自植物学、天文学和逻辑学的三个案例逐次递进地解释了荒诞的三重特征,分别是“无根基(rootless)”“无意义(meaningless)”和“无理由(without reason)”。[15]19-20
第一重,被插进瓶中的花是无根基的,因为它被抽离出本该生长于其中的天然土壤,并被强行置入另一个人工的环境之中。这个形象的例子一开始就突显出无根基之荒诞体验的独特“氛围(climate)”:背井离乡,流浪漂泊,疏离,陌异。但所有这些归结为一点,那正是加缪所谓的熟悉和稳定的世界背景的瓦解。
从体验出发,引出了第二重更为深刻而绝望的思考,那正是对支配、掌控世界的诸多根本法则本身的质疑。人与世界之离异,敞开了虚无的裂痕,而正是在这个虚无的背景之上,呈现出所有法则、原理和规律本身的荒诞。世界失去了意义,那是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终极而永恒的意义,是因为支撑它的种种貌似终极而永恒的法则其实最终都注定会落入无根基的绝境。“事已至此”,但“何以至此”?没人能给出任何终极的颠扑不破的原因和理由。
由此就涉及荒诞的第三重界定,那正是无理由。看起来这进一步深化了无意义这个要点,但其实直到这里才明确展现出与“恶”这个根本困境密切相关的根本线索。“七点钟,在圣保罗,二乘二等于四。” 这句如此清楚明白且与日常生活一般平淡真实的陈述怎么就荒诞了呢?那正是因为,一旦生活失去了熟悉的背景,一旦世界失去了稳定的框架,一旦所有的规律和法则都陷入无根基之境地,那么,不仅我们所有的行动和选择将由此失去坚实的支撑,而且更令人绝望乃至恐惧的是,我们甚至无法对任何当下的事实和事件做出有效的评价和判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一切都是脆弱不安的,真会转化为假,善会堕落为恶,因为这一切背后都既无根基,亦无意义,更无理由。既然如此,人类又为何一定要捍卫真理、扬善抑恶呢?这些所谓的执着、信念和希望,最后不也同样是荒诞一场?或许正是因此,弗卢塞尔在论及“无理由”这一点的时候所使用的修饰词是“深渊(abyss)”[15]20,而并非只是“背景(horizon)”,那正是意在将虚无的体验深化为虚无的本原,将虚无、毁灭和死亡深深地打入根基(ground)之处。
也正是这里,体现出弗卢塞尔的“无根基”与阿甘本的“去本原”之间的两点根本差异。首先是体验之氛围的差异。阿甘本的起点是生命政治之诸种恶行,进而由此激发出生命自身的那种难以遏制的捍卫、创造自身之形式的赤贫之力。而弗卢塞尔则相反,他的起点是背井离乡的体验,是四处漂泊的凄楚。他所体验到的恰恰不是赤贫之力,而更是脆弱无力,是孤苦无依②“无根基就是孤独之体验。”参见参考文献[15],第21页。、四顾无援。其次,更为重要则是二者对于虚无的理解截然不同。阿甘本的诸多标志性语汇大都带有否定性的前缀,比如“in-”“de-”,但颇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不太喜欢使用带有彻底否定性含义的词缀,比如“non-”或“-less”。这背后的理由也很清楚,诚如他自己所言,那正是为了不仅仅停留于、深陷于否定性之束缚乃至陷阱,而更是要从否定转向肯定,从被动激活主动。①阿甘本自己对“as not”这个看似否定、实则肯定的说法的论述就很典型,参见参考文献[6]。另一个明证是,Saul Newman将阿甘本的“去本原”阐释为“de-grounding”,而非“groundless”,这颇令人寻味,参见Saul Newman: "What is an Insurrection? Destituent Power and Ontological Anarchy in Agamben and Stirner", Political Studies, 2016(2), page 8。但弗卢塞尔又正相反,他虽然从未丧失“寻找根基”[15]11的努力、希望乃至“实验”[15]21,但无根基的虚无阴影乃至暴力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由此,不妨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阿甘本和弗卢塞尔之间的根本差异。借用阿甘本对于巴特比的闻名分析,他对本原(archē)的处理虽然也带有鲜明的否定性的形态(an-archy),但最终还是为了再度激发生命本原之处的不可穷竭的“绝对而纯粹的潜能(potentiality)”②转引自Saul Newman: "What is an Insurrection? Destituent Power and Ontological Anarchy in Agamben and Stirner", Political Studies , 2016(2), page 12。。而弗卢塞尔则显然不同,他的关键词不是潜能,而是“深渊”。对于他,虚无不是激活生命的力量,也远非从否定转向肯定的契机,而是敞开着那种无法根除亦无可彻底回避的终极危险:所有人类,整个世界都随时有可能无理由地再度落入死亡、虚无和毁灭的深渊。如果说“去本原”是抵抗之号角,那么“无根基”则更是痛苦之警示。生命之真义,或许并非只是一次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抗争与创造,而更是一场如临深渊、战战兢兢的摸索与流亡。
三、无根基之恶
也正是在这个深渊之处,恶之无根基性得以清晰地、不祥地显现。这个“噩兆”在弗卢塞尔的著作之中的初次也是最集中的显现,当然是《恶魔的历史》一书。看似标题中出现的是“恶魔(devil)”而并非“恶”,但细观该文本,通观弗卢塞尔的思想发展,这部书的主题绝非仅局限于对西方历史上的那些典型恶魔形象的描述,而更是直接指向了那贯穿历史之中、震荡于人性深处的根本之恶。这部书中同样也自始至终回荡着弗卢塞尔对无根基之恶的一些根本性的剖析。③正是因此,我们将书中关于“恶魔”的论述大都替换为“极端之恶”这个说法,以突出其普遍性、哲学性的含义。在一篇自述之中,他首先将“纳粹”这个极端之恶的破坏性作用形容为“地震般的”,进而“吞噬了(devoured)我的整个世界”④转引自参考文献[5],第xii页。。吞噬,显然呼应着上节最后重点提及的关键词“深渊”。然而,弗卢塞尔对恶的剖析绝非仅局限于个体的生命,亦远远超越了纳粹这一次惨绝人寰的浩劫,而更是深入到本体论的普遍层次去剖析恶之哲学内涵。
在《恶魔的历史》开篇的几个令人惊叹的段落之中,这番对恶之哲学的剖析已然彰显出与“去本原”这个阿甘本式的概念的深刻差异。譬如,纳粹这样穷凶极恶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远非绝无仅有,而反倒是屡屡发生,难以根除,这就让人深思“恶”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恶,到底是在历史之中零星爆发的偶然事件,还是可以在历史的规律、人性的深处找到本质性、根源性的解释?而弗卢塞尔随即给出的解释从表面上看堪称惊世骇俗。他明确指出,历史上对极端之恶的看法往往倾向于将其归结为种种否定、负面的特征[5]2,比如,恶就是善之对立,恶就是人性之堕落,恶就是社会之倒退等。但有心的读者当然会反唇相讥:难道说恶还有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弗卢塞尔恰恰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进而指出恶之积极作用正在于“将整个世界维系于时间之中(keeping the world within time)”[5]3。这个命题看起来如此离经叛道,实际上却道出了一个向来为人忽视的关于恶的启示性要点。难以否认的是,就历史这个人类的时间性进程而言,它绝非单向的线性的进化,更难以用某个(或某些)法则来进行终极的限定。历史的时间绝不只是明晰的形象,而更是力量纷争的战场。对此要点,从尼采到福柯的谱系学研究早已展现得淋漓尽致。弗卢塞尔虽然并未明确征引福柯,但他的用意实际上颇为近似,即善与恶之间的难以终结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恰恰是推动历史时间的最为根本性的动力。片面地扬善抑恶,进而将恶仅仅视作偶然的、边缘的、次要的现象,这就等于闭上眼、转过脸,执意不去面对现实的残酷和历史的复杂。恶,也是推动历史的一种根本性的力量,甚至是与善分庭抗礼的另一种根本力量,这才是真正进入历史时间的入口。相反,执意将恶排除于历史与时间之外,这也就同时失去了历史的全貌与时间的真相。由此确乎可以说,“生命的演化所具显的也无非就是恶之演化”[5]5。弗卢塞尔进而毫不避讳地指出,进入去魅的现代世界之后,恶慢慢也在哲学的话语,甚至公共的舆论之中逐渐“消声(silent)”,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更令人焦虑的极端之恶吗?面对极端之恶时的失语,甚至无力去深思、无意去直面这个根本性的动荡力量,难道不恰恰是现代哲学自身的一种根本之恶吗?由此,在《恶魔的历史》第一章的结尾,弗卢塞尔大声疾呼:“为什么要害怕恶呢?为什么要逃避恶呢?这些才是本书将要或明或暗地提出的生存论问题。”[5]10
真正的历史,总是善恶纷争的场域,或者用弗卢塞尔自己的表述来概括,那正是“神性(Divine)”与“恶魔(Devil)”、创造与毁灭、生命与死亡这两极之间的持久纷争。[5]3当我们仰望神性,憧憬理想之际,也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走到历史之外、之上。这个时候,正是那些阵痛般爆发的穷凶极恶一次次地将我们拖回到时间之中,让我们痛并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和时间本身的无根基性。无论怎样美轮美奂的王国,都可能瞬间倾覆;无论怎样崇高伟岸的理想,都可能顷刻堕落。恶的无根基性和历史的无根基性,不仅相互映衬,更是彼此勾连。历史没有终极的说明,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药,面对无根基、无理由、无意义之根本恶,我们既要以无理由之勇气去抵抗,亦同样需要时刻对无根基之深渊保持警醒。毕竟,我们所有人都始终“在时间之中”。
弗卢塞尔的无根基之恶的学说看似极端,但确实能够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找到清晰的线索和背景,尤为突出的三个关键环节正是神正论(theodicy),康德的“根本恶(radical evil)”理论以及(与弗卢塞尔最为切近的)谢林对无根基这个范畴的深奥思辨。而这三个环节所围绕的核心难题都是同一个:能否从神学、科学或哲学的角度对人间之恶,尤其是那些穷凶极恶给出一个“原因”或“理由”上的说明?
实际上,在中世纪的神学之中,恶已经是一个突出的难题,却并未造成根本性的困扰。这既是因为《圣经》的终极权威不可撼动,又是因为在至善的上帝面前,恶毕竟始终处于一个低微和从属的地位。但转入近代哲学就截然不同了,人必须最终依赖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对恶进行深思和解说。但细观其中三位代表性的思想家——莱布尼茨、黑格尔和康德,他们对于恶的阐释已然形成了鲜明的分化。对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恶始终且最终是一个“存在本身的负面效应”①黑格尔语。转引自参考文献[16],第xii页。。从相对消极的方面来看(比如莱布尼茨),它无非是完备而普遍的理性秩序的欠缺、贬损乃至堕落;但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说(比如黑格尔),它亦完全可以被纳入理性精神的自我发展运动的过程之中,变成一个必要的环节,甚至内在推动的力量。[16]xiii-xiv然而,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恶在向善求真的理性面前,要么被排斥至边缘,要么被内化于后者之中,因而都谈不上具有什么样的“根本”或“本原”的地位。但到了康德提出“根本恶”这个概念时,思路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恶不仅变成了人性之中一种难以根除的基本力量,更是往往展现出与理性本身分庭抗礼的咄咄逼人的态势。[16]xviii当然,康德最终还是想尽办法化解恶的此种威胁之力,并令其最终从属、臣服于理性的道德律令。但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康德的“根本恶”这个概念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惑而非答疑。奥维莱(Dennis Vanden Auweele)就明确指出,康德试图给恶进行理性“奠基(rational proof for grounding evil)”[17]的各种尝试最终注定会宣告失败,因为如果他真的成功了的话,反而会导向两个更为令人困扰的结论:要么,恶由此就变成了人性之中的一种基本力量,而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在发展延续,那么恶就将始终存在,无法根除;要么,恶就从理性这个方面获得了一种“根基”,得到一种根本性的解说,那也就意味着不仅恶是一个无法根除的力量,甚至所有的恶行最终都是“有理由”的。康德对恶所进行的“奠基”,极有可能滑向他所不愿见到的反面,那正是对恶进行了理性的“辩护”甚至开脱。
而谢林提出“无根基之恶”的概念正是来自对康德的明确回应。固然,基于德国观念论的历史演进,确有理由说黑格尔的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已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康德的困境,但谢林对恶之深思却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超越了整个理性主义传统的框架:一是证明从理性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为恶提供一个奠基或理由;二是由此转向一个非理性的基础,经由“实存(existence)”与“根基(ground)”的复杂关系来理解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互动与交锋。然而,谢林对根基的思考与康德截然不同,因为他最终将恶之根基描绘为“混沌或去本原(anrchic)”[16]xx的根本形态,由此就导向了与阿甘本和弗卢塞尔之分歧相对应的两个看似相反的方向。一方面,它作为不可穷竭的生命力,总是可以瓦解既有的秩序,为人类历史的演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接近阿甘本的去本原这个概念;但另一方面,谢林意义上的根基又展现出下坠、回缩(withdrawal)[18]、潜隐的运动,因而又颇为切近弗卢塞尔笔下的那个幽暗的“深渊”。根基,既可以上升为生命,又可以回缩为深渊,既得以朝向善之理想,又每每落入恶之深渊,这才是谢林之无根基概念的根本要义。实存必然有一个根基,必然来自一个根基,但这个根基既非理性所能奠定,亦无法最终与实存本身形成和谐的秩序,正相反,这个根基之中早已经深深地打入了生与死之间的持久纷争,善与恶之间的永恒对抗。
在这里,弗卢塞尔与谢林之间奏响了强烈而持续的共鸣。甚至二者对于“宗教”这个根本问题的回应也是如此相似。谢林曾基于词源的考察将“宗教(re-ligare)”解释为“重建连接”[17],也正突显出贯穿人类历史的善与恶之间的不稳定的张力。同样,弗卢塞尔也曾明确地将“思想与生命、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争斗”①转引自参考文献[19],第17页。视作自己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还明确将其与宗教这个主题关联在一起:“我的一生,就是本无任何宗教信仰(religion),却始终探寻着宗教精神(religion)。”②转引自参考文献[5],第xii 页。我们将先后两个“religion”进行了不同的意译,正是为了突出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弗卢塞尔的哲学生命,正是不断突破各种宗教信仰的体制性束缚,进而在思想与生命的张力之中不断深入善恶持久纷争的宗教精神的至暗深处。
四、技术图像作为无根基之恶
经过上述这一番对阿甘本和弗卢塞尔、去本原和无根基二者的对比,反而平添了几分对于后者的质疑。
在阿甘本那里,从使用到去本原的转变,也就标志着从解构式的否定转向生命论式的肯定,由此亦为切实的抵抗和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本体论上的前提。毕竟,从《至高的清贫》开始的一系列著作,都已经展现出此种去本原式的积极抵抗的不同方式和向度。但反观无根基这个概念呢?此种对于根基所进行的充满否定意涵的处理,是否也就同时意味着消极怠惰,甚至放弃行动?毕竟,面对无根基之恶,除了苦痛和警醒之外,究竟还能做出怎样切实的回应呢?对此,有的学者也基于一定的文本依据将弗卢塞尔的“积极”的抵抗策略大致等同于德勒兹式的游牧主义。[19]73确实,很难无视弗卢塞尔的一些关键概念(尤其是“转译(translation)”和“意义之绘图(mapping of meaning)”)[19]70-71之中所洋溢的浓厚的德勒兹主义的气息。但要想真正领会他自己给出的切实的行动方案,还是要回归到起点——既是思想的起点,即“无根基”,同时又是研究的起点,即《语言哲学》这部早期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无根基与语言问题密切关联,并随之引出了对于图像和神话问题的相关思考,这就为“技术图像”这个弗卢塞尔最为闻名的概念之提出做好了铺垫。也正是基于这些根本的前提,才能够对姿势这个关键要点进行恰切充分的理解,也才能以姿势为核心再度领会阿甘本和弗卢塞尔、去本原和无根基所导向的不同的抵抗策略。
《语言哲学》虽然只是一部草创之作,但其中对先于语言的“无”之维度的启示已然出现了引导弗卢塞尔后续思想发展的主线。在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为该书英译本所做的重要序言中,开篇就强调了“无(nothing)”这个关键词。[20]xi将无与语言关联在一起,至少体现出三重意蕴。首先,“无”并非彻底的空无、断裂或鸿沟,而更是强调语言与其“本原”之间的差异性的张力。因此,说语言始于“无”,那无非是从根本上拒斥那些用因果性、历史规律、目的论等模式来对语言进行限定和框定之徒劳努力,而从本原之处就将其向那些外部的、差异的、多元的力量敞开。语言的本原,恰恰是不可明言、不可尽言之“无(unconfessed meaning)”[20]5。其次,“无”在弗卢塞尔这里也并非只是一个空泛的本体论范畴。他虽然明确论及了存在与非存在这些深奥的问题,但最终还是意在将哲学的思辨引向具体的语言现象和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会说“本体论最终就是神话学(mythology)”①转引自参考文献[20],第xvi页。。这里的神话,既指向着先于概念思辨的隐喻式思考,但同时又指向了“人类语言的种种非言语的方面(non-verbal aspects)”[20]xiii,比如声音、姿势、触觉、形象。就此而言,语言所源自的那个“无”,在这里尚未体现出多少“无根基”的内涵,而倒是更接近一种蕴藏丰富的创生性的本源。最后,或许也正是因此,弗卢塞尔才会明确总结说,“思考,就是一个对无的否定的过程”②同上,第xvii页。。但这里的否定,显然还是更为接近一个从无到有、从无形到有形、从不可言到可言的转译和转化的运动,其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否定性的意味。实际上,《语言哲学》中对无之本原的论述或许更为接近阿甘本的“潜能”,而并非无根基式的“深渊”。
但到了《迈向一种摄影哲学》这部真正的杰作和代表作,弗卢塞尔对于无和无根基的思考却开始发生明显的转折。一方面,他的思考范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不仅从语言拓展至广大的符号领域,更是由此对整个人类的媒介发展史进行了一番极为透彻的梳理和解析。另一方面,他经由这番历史和概念梳理所最终得出的技术图像这个核心概念,确实更为明显地展现出无根基的鲜明意味,也正是由此导向了他在后续的《技术图像的宇宙》一书中对数字时代的无根基之恶的深刻批判。
那就先从历史的脉络入手。弗卢塞尔首先将媒介史的发展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即神话、历史、技术图像。三者的关系有点接近辩证法式的否定之否定③“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也确实是弗卢塞尔在第一章中所明示的基本方法,参见参考文献[21],第12页。,但又体现出极为迥异的细节。首先,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区分,可以概括为三重对比:神话的时间性是循环的,而历史的时间性是线性的;神话的思维是想象式的,而历史的思考则是概念性的;神话的主导媒介是图像(image),而历史的基本媒介则是文本(text)。这些普泛的论述,似乎算不上有多少原创性。但弗卢塞尔的真正创意正在于由此引出了“技术图像”这个令人醍醐灌顶的概念。
什么是技术图像呢?弗卢塞尔的界定极为简明,那正是“由装置生产出来的图像”[21]14。那什么是装置呢?“简言之,就是模拟思考的各种黑箱(black boxes),它们用数字化的符号来进行组合式的游戏(combinatory game)。”[21]32这个界定中的几个关键词也恰好对应着弗卢塞尔在第三章中所清晰界定的技术图像的六个基本特征。
其一正是“危险”。技术图像本质上是一种图像,因而必定多少带上了神话式媒介的种种特征,但它又与神话有着根本区别。神话图像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技术图像则正相反,它指向的是各种各样的文本。因此,如果说神话图像是前历史的,那么技术图像则恰恰是“后历史的(posthistoric)”[21]14,它看似再度唤起循环的时间和开放的想象,以此来替代线性的历史和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它所整合的只是历史演变流传下来的各种文本,这已经跟现实之间隔着一层难以跨越的鸿沟。进而,它又以技术媒介和平台为主导,对这些文本、概念和符号进行共时性的、网络化的编程、操作和处理,从而完全丧失甚至清除了它们原本所带有的历史线索和背景。由此,弗卢塞尔将技术图像的想象总结为两个本质特征,即次级的想象(因为它跟现实隔着文本的间距)和编程(programs)。[21]17
那为何这就一定是“危险”呢?为何不能从辩证综合的角度将技术图像视为对神话和历史的扬弃和超越?这就涉及“黑箱”这个关键特征了。前历史的神话式媒介,它以万物交织、互渗的整体性宇宙图像令人与世界难解难分地交融在一起。它所运用的符号虽然充满着种种神秘莫测的气息,但其中既涌现着宇宙之伟力,同时又展现出人类的蓬勃的想象力。但技术图像对于各种信息和文本的编程式整合则正相反,它背后的运作规则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一套机械的规则和数字的算法。而且更为致命的是,所有这些规则和算法的运作都深深地隐藏在各种黑箱式的装置之中,一般的用户既难以理解,更难以触及。[21]16这已经远非神秘,而更是一种疏离和陌异。面对原始人创造的神秘图像,我们会赞叹其中难以穷尽的想象力,但对于今天的各种装置所生产出来的各式技术图像,我们几乎只会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冷漠的距离。技术图像也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宏大的无尽延伸的“宇宙”,但那个宇宙之中既没有生命,更没有精神,而只有循环相因、无限重复(endlessly repeatable)[21]20、冰冷运作的编程之逻辑。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卢塞尔最终将技术图像式的整合讽刺为“无形的一团(masses)”,它甚至失去了各种历史性文本所展现出的方向、目的、发展等特征,而将整个世界最终化为一片没有方向、没有秩序,甚至没有意义的混沌涌流的数字汪洋。①对数字海洋的论述,参见姜宇辉:《数字海洋中的崇高与创伤:重思数字美学的三个关键词》,《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固然,各种装置可以从这个无形的汪洋之中不断生产、变幻出难以穷尽的有形的秩序,但所有这些秩序都仅仅是编码操作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是无根基、无理由、无意义的。世界可以这样编码,也完全可以那样编码,至于不同的编码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理由上的高低和意义上的深浅,最终都是毫无依据的。所有一切的编码,规则和算法最终都只是无理由、无目的的“组合的游戏”,最终都注定要一次次跌落到那个无根基的本原之处。这正是弗卢塞尔以看似平淡的笔调所描绘出的技术图像时代的绝境。
但在《迈向一种摄影哲学》之中,他虽然暗示出了此种绝境之深重,却并未全然展开其极端之“恶”的面向。而这个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工作,随后在《技术图像的宇宙》一书中得到坚定而持续的推进。该书的前六章大致都是对前作的复述,但从第七章开始,他的语调骤变,开始直接触及无根基之恶这个根本的问题。“互动”这个标题看似意在突出数字图像与传统媒介相比的独特优势,但在弗卢塞尔看来,此种所谓的互动却最终会导致两个极度令人忧虑甚至恐惧的结果。一方面,这里的“互”仅仅是一个编码操作的结果,说到底它只是技术图像对用户、玩家、消费者施加的单向度的“渗透力”:“它会使人们承受压力,诱导他们按下按键,从而让图像在角落里浮现。”[22]35表面上看,是你在主动地、平等地跟图像互动,但实际上你早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程序和算法所操控玩弄的傀儡。看似人与图像之间达成的是一种交互而平等的“共识”,但实质上二者之间最终所形成的却只是一个“闭环式的反馈回路”。[22]36-37由此便造成了另一个方面的恶果,那正是最终会导致神话式想象的衰亡和历史性意义的枯竭。而所有这一切最终所带来的几乎唯有一个终极的无根基的恶行,那正是人类自由的丧失。[22]38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绝境,弗卢塞尔到底又能提出怎样的对治之道呢?仅就该书而言,大致有三个要点。
首先,当然是要改变技术图像的单向度的、闭环反馈式的渗透,而真正让它成为一个人与人、人与技术,甚至人与万物之间平等开放之交互和“对话”的基本平台。
其次,“这种对社会的对话式重构,这种‘对话式存在’的关键,在于它的游戏性”[22]66。游戏的本性,无非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以人和人的平等参与为前提,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游戏者的能力和自由。如果我们注定已经深陷技术图像的装置之中,那么唯一的解脱之道或许正是以游戏的精神加以回应乃至对抗。对于技术图像所敞开的这个游戏性的自由,其实弗卢塞尔在《迈向一种摄影哲学》中已然明示,并明确以此为要点区分了历史性文本和技术图像。如果说前者还只是一种沿着线性的秩序所进行的循规蹈矩的“劳作(work)”的话,那么后者则进一步演变成相对自由地对数字符号进行操控组合的“游戏”。[21]29
但最后,祭出游戏性这个法宝看起来仍然难以拯救技术图像的无根基之恶,因为置身日益游戏化世界之中的每一个玩家,他们看似每一步都在进行“自由”的决断,但在这些决断背后所进行操控的却仍然是、始终是、不可能不是算法和规则:“这样看来,远程通讯技术似乎不仅能在创造的过程中,而且能在决断的过程中替代人类。 ……现在,我们发现这些步骤再度走入了虚空”。[22]88如果看似自由的决断背后也是无理由的程序,那么游戏性就难以真正对治数字时代的无根基之恶。我们再一次被抛进那个幽暗的深渊。
五、重归姿势:弗卢塞尔与阿甘本的另一次对话
那么,是否还存在一线解脱之生机和希望?如果有,那么或许还是要回归姿势这个要点。既然在阿甘本那里,姿势是连接否定与肯定、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键纽带,那么是否也能在弗卢塞尔这里找到相似的对应?在全文的最后,就让我们再度围绕这个要点在二者之间展开对话。
二者之间的一个明显趋同正在于,在《业》一书中,阿甘本明确将姿势视作自己中后期的一个核心主题,同样,弗卢塞尔在去世之前亲自编撰的最后一部重要文集,也正是《姿势》。这个概念在二者思想发展之中所起到的凝聚、总括甚至归宿的作用昭然若揭。但除了文本上的接近,其实二者的基本思路更能形成一种互补乃至相得益彰的作用。还是先回到弗卢塞尔。他关于姿势的启示其实在《迈向一种摄影哲学》中就已经清晰呈现,而且相当重要,因为在《摄影的姿势》这一章中,姿势恰恰构成了对技术图像的无根基之恶的一种有效的、根本性的回应。
摄影,当然也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图像,甚至不妨将其视作技术图像的真正起点。[21]17既然如此,它当然也就同样深陷于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图像游戏之中进退两难。一方面,与之前的媒介形态(尤其是书写和绘画)相比,摄影显然体现出极大的自由度,以及人与媒介之间的相当深度的“融合(merge)”[21]39。但另一方面,在这场看似自由洒脱的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游戏之中,对种种规则、可能性乃至决断进行操控的却仍然还是程序和算法。[21]37这些批判性反思当然与《技术图像的宇宙》并无二致,但弗卢塞尔接下来密切贴合摄影之“姿势”所给出的具体深入的解析却顿然间带给读者全然不同的解脱乃至自由的道路。要点正在于“量子化”的“颗粒(grains)”[21]38这种摄影所特有的姿势。
其实不必身为一位技艺高超的摄影家,平常生活中俯拾即是的拍摄行为都能让我们清楚领会这个要点。弗卢塞尔对此的解释是,在摄影的过程中,视角是不断变换的,姿势也在不断地调整,甚至每一步的操作、最终按下快门的“决断”都充满着偶然随机的特征,这就让整个看似由机械程序所掌控的过程出现了很多人为制造的间断和裂痕。很多人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因为在别的传统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这种量子化的行为可能也同样存在。或许不尽然,不妨对比文学和绘画。在一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之中,始终还是线性进程在主导,虽然也存在着很多平行分岔的可能性,但这些往往都只是停留于作者头脑之中的想象。摄影创作就不同了,在每一步取景和调整的“姿势”之中,技术装置同时就已经给拍摄者明确提供了众多共时、并存的路径。再对比绘画。虽然二维的画布显然比一维的文字增加了一个共时性的维度,但无论空白的画布在落笔之前是怎样充满着各种涌动变幻的不可见之形①“认为一位画家面对的只是一个白色的表面,乃是一种错误。”参见吉尔·德勒兹:《感觉的逻辑》,董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一旦落笔,画面就逐渐倾向于凝固、成形。摄影又与此不同,尤其是数码摄影,不仅在空间上提供了平行分岔的路径,更是从时间上提供了拉伸、回放、重复、延迟、叠加等各种“弹性(plasticity)”的可能。因而,弗卢塞尔说摄影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单一的时空范畴所固有的限制和“障碍(hurdles)”[21]37,这其实并不为过。这也为后来的电影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前提。
概言之,摄影的姿势,正是在既定的时空框架内去最大限度地撕裂出一个个微小的、量子化的跃变和间隔。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论完全可以自摄影拓展至整个技术图像的范域。或者说,唯有以姿势的方式,才有可能真正从装置的单向度渗透的闭环中挣脱而出,实现人的自由,实现万物的交互。
但由此又引申出下一个关键问题:在姿势的时空颗粒之处所激发出来的到底是人身上的何种力量?是身体还是心灵,是理性、意志还是欲望?在《技术图像的宇宙》中,弗卢塞尔给出了明确的回答,那正是苦痛之“共情(sympathy)”:“但是,机器人不能代我们受苦。 …… 所有创造力的来源正是苦难。”[22]106-108正是在这里,无根基这个概念的意蕴再次明晰呈现,并展现出一种恰与阿甘本相反的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向。面对技术图像的无根基之恶,首先必当戳穿其自由游戏的看似积极肯定的虚假表象,迫近其本原(或非-本原)之处的那个虚无的深渊。面对这个终极之虚无,种种传统的抵抗方式自然无效,但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也于事无补。弗卢塞尔由此提供了另外一种基于“无”和否定的抵抗方式,它接受根本恶这个前提,并进而竭力在铺天盖地的技术图像的内部去撕开一个个微小的否定性裂痕。“自由不是永远拒绝,而是永远保有拒绝的可能性。”[22]88这个可能性就在于每一次量子化的否定性决断的姿势之中。
所有这些启示性要点在《姿势》这部弗卢塞尔的终结之作中呈现得更为明晰而丰富。他在开篇就给出了关于姿势的基本界定:“姿势就是身体或与身体相连之工具的某种运动,对它不能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因果性解释。”[23]2其实,用“因果性”这个说法还是有些狭隘了,真正作为否定性决断的姿势从根本上不服从于任何一种技术图像的装置性逻辑。如果说它真的“表达”了什么的话,那唯有自由之“情动(affect)”[23]164。
由此就来到了弗卢塞尔说过的关于姿势的或许最为重要的一段话。在《姿势》一书的附录中,他不仅对姿势给出了四种分类,更是将第四种(自指性姿势)置于根本地位。[23]166真正的姿势既没有明确的目的,也不遵循既定的程序,作为量子化的跃变,它是自由的表达。但这样一个个微小的自由的姿势显然既不基于人类的普遍本质,也不朝向宏大的理性理想,它几乎只呈现为一种样态,那正是仪式。但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仪式,也不同于中世纪的宗教仪式,甚至不同于任何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仪式(入职、生日、毕业等),因为它没有任何外在的指向、目的、意义和功能,它只重复自己,一遍遍重复自己,以此暴露技术图像时代的无根基之恶,进而对其进行无理由的微观抵抗。
我们发现,至少就“姿势”这个概念而言,阿甘本与弗卢塞尔的思路展现出惊人的相似轨迹。根据勒维特(Deborah Levitt)的经典概述,阿甘本的姿势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生命政治的困境,到审美领域的拯救,最后再到解放性的政治行动。[24]这个发展线索看似与弗卢塞尔有所不同,但从基本的思路推进来看,却与弗卢塞尔颇为接近。首先,在文集《潜能》中的《科莫雷尔,或论姿势》("Kommerell, or On Gesture")一文中,姿势的引入并非仅仅是对生命政治的痛斥,更是将姿势从根本上视作“潜能与现实、本真与造作、偶然与必然”[25]83之间的绝对不可分的区域。这一方面当然是对前期的考古学拓扑模式的再度运用,但另一方面,姿势的那种挣脱于目的和手段、制作与行为的二元框架之外的“界槛”之“用”①在《业》一书中,阿甘本明确将姿势界定为介于制作与行为之间的“第三种模式”,参见参考文献[4],第169页。同样还展现出一种鲜明的解放性的力量[25]85,这也是他会在全文最后引入尼采的永恒轮回概念来进行解说的重要缘由。
而对于此种解放性的力量,他后来在《论姿势的笔记》一文中给出了极为明确的阐释。姿势何以挣脱种种既定的框架,进而回归自身?它回归自身所展现出来的又到底是何种力量?那不是别的,正是“媒介性(mediality)”本身:“它让一种手段自身变得可见。”[26]然而,当手段令自身可见之时,它就不仅挣脱了手段-目的之二元性,也同样不止于揭示自身原本被遮蔽的种种运作的过程,而是以一种回归自身的近乎仪式性的运动来制造出极端的变革和行动的可能性。
诚如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的精辟阐释,作为纯粹手段被展现出来的姿势确实就是一种自指,但此种自指并非只是机械的重复,更是“建立起一种将自身当做他者(Other)的关联”[27]。随后,阿甘本在艺术领域(绘画、舞蹈、电影)及政治行动(德波的情境主义)中进行了种种尝试,试图敞开此种内在于姿势的自指仪式的差异性张力。但与弗卢塞尔对于技术图像时代的种种姿势的细致入微、全面广泛的剖析相比,阿甘本的这些论述就多少显得苍白而含混。不妨说,弗卢塞尔的姿势理论恰好可以给阿甘本关于姿势的“笔记”提供一个切实的深入现实的维度。
但反过来说,阿甘本亦有一个要点足以构成对弗卢塞尔的有力补充,那正是时间性。我们已经看到,姿势所撕裂出的量子化的微小时空裂隙,是其得以回归自身、表达自由的基本前提。遍观弗卢塞尔的文本,对时间性的论述固然散布各处,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有对于姿势的时间性的集中阐释。而阿甘本在《剩余的时间》中对弥赛亚时间的深刻阐发又恰好可以补充这个缺失的环节。弥赛亚时间,既符合“在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此世与来世之间”的“一个绝对不可辨认性的区域”这个前期的拓扑学模式[28]40,同时又已经展现出对“建基和起源”进行批判的中后期的“去本原”的趋向[28]141,最终则回归于并展现出“在时间之内”[28]93撕裂出微小断裂的量子化契机。这条时间性的线索,显然为我们进一步剖析和批判技术图像时代的无根基之恶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参考。阿甘本和弗卢塞尔的对话,也显然还有可能、有必要向着未来不断地引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