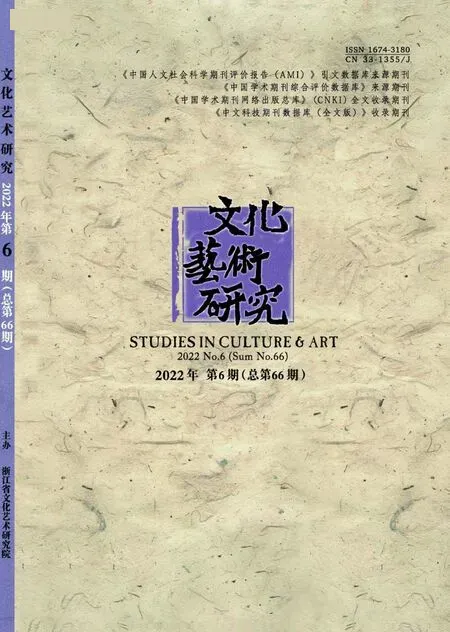动画中文称谓的历史沿革及其文化意义图景*
赵 易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成都 610207)
动画来到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中国动画从发轫到确立民族风格再到产业大发展,走过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具有明确西方起源的现代艺术形式,它既是技术和媒介,也是一种视觉文化传统。鉴于动画在现代全球文化中的渗透性影响,从文化研究角度把握动画正成为全球动画研究的一个趋势。这种研究方向强调更开阔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框架,重视采用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符号学等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询动画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性。[1]现阶段的中国动画史研究,基本以作品分析为立足点,关注作品的美学、制作特征及影响,宏观性地回到社会文化大背景中去的研究尚不多见。[2]
作为对此现象的回应,本着语言实践是社会文化多元力量冲突和博弈的场域这一宗旨,本文试图跳开具体的动画作品,以动画进入中国以来出现的诸多中文称谓为切入点观照中国动画史。对于所涉及名词,无意进行过多词源学或翻译学的探讨,也不对其作价值评判,而是以其作为桥梁,发现动画与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文化风向之间的关系。动画这类外来物的称呼,本质上也是一个国内外文化交流和协商的结果,从动画称谓上也可看出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持续变化的翻译态度和策略。
文化研究者刘禾特别关注20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文化翻译问题,关注在不对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在交流中如何挪用和翻译过去的思想资源,产生既不同于中国过去的思想,也不同于西方思想,但又与二者有着深刻联系的新的文化思想符号。对此,她提出“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强调:“跨语际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3]39跨语际实践并非要把历史事件化约为语言实践,而是要扩展历史的观念,把语言及其相关的话语变迁视为真正的历史事件。本文观照动画中文称谓的目的和方法皆源出于此。诸多中文动画称谓的兴起、流通和获得(或失去)合法性,背后是更大的社会话语行为对历史真实的构建,是中国本土和西方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话语诉求中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对动画中文称谓的梳理,不仅能反映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更能折射出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
在百余年来的不同阶段中,动画在中国出现了若干个被广泛接受的中文称谓,它们的出现和流通在时间上比较清晰地对应了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将按此划分方法对中文动画称谓的历史沿革分阶段地进行观照和梳理。
一、1918—1949:中国动画的“卡通”时期
动画电影在1918年首次进入中国。面对这个全新的文化事物,中国人调用已有的文化经验和想象对其加以理解的努力,生动地体现在对它的中文命名上。动画最早的中文名称五花八门,包括滑稽画影片、活动滑稽画片、钢笔画影片、活动影片、墨水画片、活动画片等,基本是对当时动画的英文名称“animated cartoon”的意译。[4]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观众基本沿袭了西方观众在动画的技术新奇期的体验方式,强调动画在图像和媒介上的技术性和创新性。同时,一些中文名称中的“影”字又体现出对传统影戏的指涉,反映出中国观众独有的观看和认知角度。就这样,动画开始了在中文中持续不断地被重新表述和重新语境化的历程。
“cartoon”一词原指用墨水硬笔快速绘制的用于出版的讽刺画。早期的讽刺画家们创作了第一批影院动画,也确立了后者的墨水硬笔勾线的画面形式。20世纪20年代末,“cartoon”的中文音译词“卡通”开始出现。1927年万氏兄弟的动画短片《大闹画室》完成制作和放映后,《申报》在当年5月10日、5月11日和9月30日的3篇报道文章中,分别使用了“活动滑稽画片”“墨水片(cartoon)”“活动墨水画(cartoon)”的称呼方式,可见当时已开始带上“cartoon”一词,但还很不统一。同样是万氏兄弟的作品,当1935年《骆驼献舞》上映时,海报、广告和报道中的称谓就都是“有声卡通”了。[5]29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的宣传海报上,使用的也是“长篇卡通”一词。①1936年,万氏兄弟在《明星月刊》上发表文章,介绍美国、德国和苏联的动画片,鼓吹中国的民族风格探索时,标题就叫《谈谈卡通片》。1937年,他们制作的抗日宣传动画短片《抗战标语卡通》,也直接以“卡通”为标题。
相比其他的意译方式,“卡通”一词简单明快,带有异域情调,很符合当时动画在市民社会的娱乐和消费属性。不过,该词一直缺乏来自官方的明确和规范。1937年,17岁的张爱玲在《凤澡》发表《论卡通画之前途》,开宗明义地说:“卡通画这名词,在中国只有十年以下的历史……‘卡通’(cartoon)的原有的意义包括一切单幅讽刺漫画、时事漫画、人生漫画、连续漫画等,可是我要在这里谈的卡通是专指映在银幕上的那种活动映画。”[6]因为可以指代多个对象,“卡通”在指代动画时经常要搭配定语以避免歧义。中国最早的动画教科书之一,中华书局1947年出版的《活动卡通画法》,就以“活动卡通”来命名动画,以免产生歧义。
从中国动画启蒙时代的称谓可以看出,中国本土动画的创作,是在把握和吸收西方外来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卡通”一词就明显带有对标美国的意味。初生时期的中国动画从理念、技术、形式到生产模式无不模仿美国的同业者,这符合新生事物的发展逻辑,也合辙于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层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响应姿态。从《大闹画室》到《铁扇公主》,中国卡通作品都采用了美国动画片单线平涂的绘制方法、简练夸张的视觉风格,以及“突梯滑稽”的喜剧、闹剧的剧作观念和语言程式。中国的动画制作的市场行为性质,其觅资、组建团队、成片和宣发的制作步骤,也遵循了美国动画行业的成例。中国动画先行者们也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以个人经营为主,身兼创作者、管理者和发行者多职。从短片《大闹画室》到长片《铁扇公主》,完成了类似于美国动画行业的从个体作坊到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的升级。
尽管如此,中国动画从脱胎之日起还是表现出了“本土”的基因,在借鉴西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既有模式进行了改造,在人物造型、肢体动作、故事结构中带入民族性的思考。只不过在“卡通”时期,这种本土化努力是在对西方外来的动画话语框架的接受下进行的。而20世纪上半叶动荡的中国社会留给中国动画人实现商业成功和艺术探索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与此同时,“动画”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文中也开始出现。一般认为,“动画”和许多现代中文词一样,是日文借用词。西方动画进入日本的时间与进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同,其最早的日文称谓包括“漫画”“线画”“线画映画”“线画喜剧”“漫画映画”等。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动画之父”政冈宪三设立“日本动画协会”,第一次提出“动画”这个译名,但是该译名并未立即被日本社会接受。[7]1942年,中国的《铁扇公主》在日本上映时是被称为“漫画”的(见图1)。

图1 《铁扇公主》的中文和日文海报
持“动画”本土发展说者认为,中国动画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钱家骏是此词的提出者。1945年,钱家骏在南京创立“中华动画学会”,明确地以“动画”一词取代“卡通”。1946年12月,他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刊《艺浪》上发表《关于动画及其学习方法》一文。这篇中国最早系统论述动画理论的学术文章颇多动画称谓之辩。将“众素所周知的电影卡通”更名为“动画”这一“不相识的名称”,虽然可能“既使人感到莫名的麻烦,又会引起一阵名词争执的动荡”,却是有必要的,因为“学术文化名词的重要,相等于人们的姓名一样”,“动画本身也需要它确切得当的名词”。[8]他特别从跨语际实践的角度对“卡通”和“动画”两词做了比较:“而我国自来就沿用着电影卡通来叫它,关于这种错误,是过去接受欧西文化生吞活咽的征示,因为那时要大量吸收,不容我们咀嚼,将就借用着,殊不知会形成了习惯的名词,这对于我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掺入了人家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容的健全。这是说:一种名词的音译没有意译来得更适合国情。因为动画二字的单独意义,是具有更深的认识的必然性。”[8]
钱家骏对“动画”一词的推崇挑战了“卡通”的合法性和流通性,这似乎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一场大规模的语言改造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关于中国动画的名词开始了第一次更迭。
二、1949—1988:中国动画的“美术片”时期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成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下简称“满映”)[5]55,下设的动画分支依照当时的惯例称为“卡通组”,实现了动画在中国领土上最早的体制化生产。1945年10月,随着东北解放区的敌伪电影机构被“延安电影团”接管,“满映”被改组为东北电影公司(后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原卡通组被改组为该厂技术组美工科卡通组,这是新中国动画工作的起点。[9]1949年,卡通组更名为“美术片组”。“美术片”一词从此诞生,标志着中国动画新时代的开始。美术片组下设动画组和木偶片组,“动画”一词成为对以二维手绘方式制作的动画电影的特指。1950年后,随着美国文化影响在中国社会的消退,“卡通”一词很快被边缘化,在其后很长时间的中国文化生活中消失了。
“满映”卡通组被收编后,有近百名日本技术人员选择继续驻留工作,其中就包括日本知名的定格动画工作者持永只仁(中文名方明)。[5]55持永只仁与当时的卡通组组长、之后长期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特伟关系密切。①从1979年起,持永只仁多次访华并组织中日动画界之间的交流活动。
持永只仁在他的回忆录《美术电影成为我毕生的事业》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改组更名情况的:“该如何称呼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呢?我向来是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待日本的卡通片的,虽然也认为它还远远称不上美术作品,但我觉得应该从重视美术的角度来制作影片。特伟同志也认为这是美术范围的电影,就说:‘那么就把它叫美术电影吧。’同时又把过去称之为卡通片的漫画电影改叫为动画电影,从属美术电影。这些名词就这样确立下来了。”②参见《上海电影史料》编辑组编:上海电影史料(6),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1995年版,第136页。
新词语的创造和合法化过程,是一个“多层次的交叉与纵横的地带”[3]3,其中个人的和偶然的历史因素,都必然反映出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如福柯所言,体制性实践和知识/权利关系将特定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其他的认知方式。“美术片”以美术风格和美术元素作为动画认知和创作的基础,有意识地背离了“卡通片”所表征的电影的流行文化属性,对动画概念实行了一次本土再创造。“美术片”由官方创立并合法化,对应的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政权交替带来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转变,由此激发出动画的民族想象新空间。
新中国动画在新体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道路和机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集中管理和统购包销,集合了稳定的动画创作人员,也消弭了制作的商业和市场压力,为艺术探索提供了条件。[10]同时,在“以政治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集体理性和民族认同的强调,也使民族化道路成为创作必然。从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迁至上海,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1957年改组扩建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9],再到20世纪80年代,在30多年时间里,中国动画是世界范围内动画艺术实验的重要场地之一。“美术片”时期的“美影厂”建立了一个包括多种媒介和体裁的作品体系,还衍生出了另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名词——“中国动画学派”。
观察“美术片”时期的中国动画作品,语言实践对现实和行动的反向形塑力量是清晰可见的。在“美术片”这个概念的引领下,传统美术形式被积极地、有意识地引入动画实践中,新美术风格与强调意境和诗性的叙事,使美术片从形式到主题都脱离了之前的卡通范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术片的民族性并不是一个固化和既有的存在,静止地等待着捕捉和萃取就得以呈现。即使处于当时粗糙刚性的政治框架下,中国美术片也从来不是在一个封闭和孤立的场域中运作的,而是“西方的电影语言与革命性的民族传统这两种不对等的视觉结构之间的持续协商和妥协的结果”[11]26。一方面,美国动画在这一时期仍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为中国动画提供参考和借鉴①新中国成立前引进的迪士尼动画片,如《幻想曲》《白雪公主》等一直是美影厂的内部学习材料。;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体制包括动画片厂制度本身就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动画在创作理念、技术、设备和人员上也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保持了密切的合作。②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影厂团队组织翻译了苏联动画艺术家瓦诺的理论著作《动画电影》,并反复临摹苏联动画片,派人赴苏联学习。苏联动画被认为“与腐化儿童、并使儿童走向堕落的美国电影完全不同,苏联的影片是用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美学观点来培养下一代的”[12],这些也成为中国美术片起步阶段的标杆。③比如1956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学习了苏联的知名作品《灰脖鸭》;另一部知名作品,1954年的《小鲤鱼跃龙门》则借鉴了苏联动画《春天的故事》。苏联和东欧动画的形式特征、叙事结构、诗意和教化性对美术片从卡通风格中脱离,走上自身发展之路也起到了指引性的作用。④自1952 年起,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了多项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新中国公派留学的第一人就是去捷克斯洛伐克学习木偶动画,第一次派美术电影工作者出国考察的目的地也是捷克斯洛伐克。
中国美术片始终抱持着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野心,这也鲜明地体现在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积极参与国际影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⑤从1956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影厂摄制的美术片共有44部76 次在国际影展中获奖。尽管其动机可能是具有政治功利性的,与国际平台的相互审视、评判和期许,对美术片在艺术上的反向塑造是不容小觑的,这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美术电影的“一个更复杂、更不具目的性的影响过程”[11]21。
综上所述,中国美术片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双重环境作用下持续交流、反馈和修正的过程。“美术”一词对动画称谓的介入,指认出在新的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下中国动画的现实要求和自觉响应,同时也指认出来自不同源头的异质语言和异质文化的影响。⑥“美术”一词本身也说明这种情况。1958年由高名凯和刘正琰合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指出:“美术”是个外来词,是先由日本人用汉字组合,去意译欧美语言中的“art”一词,再由中国人引进并加以改造成现代汉语。1871年,在日本明治政府对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展览说明附件的翻译中,多次出现了作为分类名称的“美术”,这是“美术”一词第一次在日本出现,被广泛使用后在晚清被中国引入。文化理论学者早已指出,文化实践不存在一个从本源到目标的单线程和单向度的转化,对其观照必须还原其多维度的路线、话语及动态交互。在中国动画的民族化讨论重新激烈的今天,“美术片”时代因其里程碑式的意义仍然经常成为焦点议题。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刻意悬置某一方面的影响而强调另一方面的影响,无益于对历史的把握,也无益于未来新思维的展开。
三、1988年至今:中国动画的“动漫”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动画的发展及语言实践迎来了又一次历史转折。虽然美影厂在“新时期”仍然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但是随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美影厂也不复其事业单位性质,在经历了机构和人员重组后,将主要的生产能力集中在以经济收益为目标的外包加工和电视系列片的生产上,原有的艺术创作模式渐告终结。[13]1988年的《山水情》作为最后一部水墨动画,可以看作整个“美术片”时代的绝响。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美术片”一词内涵中的旧体制色彩,以及商业性和娱乐性意指的匮乏,使其不再在中国社会继续广泛使用,而成为承载着关于过去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名词。此消彼长,“动画”一词成为指代动画整个门类的官方名词,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85年中国动画学会在上海成立。此外,“卡通”一词也重回历史舞台,一般被用来特指公共电视频道(如开播于2003年的上海炫动卡通频道和2004年的湖南金鹰卡通频道)中播放的面向低龄儿童的动画作品。
随着中国的文化市场逐步开放,在见证了动画引进产品的巨大市场反响后,国人开始认识到动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力上的双重战略意义,关于动画的民族想象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维度,动画的中文称谓也迎来了新一轮变革。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在世界其他语言中都没有对应词汇的新词——“动漫”,在汉语中出现并开始被广泛使用。有研究者考证,这个词可能源于台湾地区的“动漫画”一词,最早可考的使用见于1998年成立的“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原意可以理解为“动画+漫画”。[14]聂欣如分析2000年至2011年“动漫”一词在中国各级行政机关文件中出现的频率后指出,动漫概念是依靠官方的发起,尤其是在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等10个部级单位发展动漫产业的联合文件后,才在中国大陆开始广泛流通的。[15]这份题为《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政府文件,从产业角度对“动漫”一词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动漫产业是指以‘创意’为核心,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包含动漫图书、报刊、电影、电视、音像制品、舞台剧和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种等动漫直接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播出、演出和销售,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产业。”[16]可以看出,“动漫”是个涵盖广泛、具有极强产业属性的称谓,在具体使用中,可以根据上下文指代动画、漫画、游戏、数字技术与产品等不同内容。聂欣如认为,2006年是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之年,“动漫”一词被官方选中,可能是为了应对其在国家发展纲要的制定考量中,对整个新兴文化产业的定位问题。那为什么要在中文语言实践上将“动画”和“漫画”结合,并延伸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主推方向呢?这仍然与跨语际实践的问题有关。而这次,异质文化的主要来源是日本。
现代汉语中的“漫画”也是一个日源词。①“漫画”一词在中文中原指一种水鸟。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日文开始用“漫画”指用笔简练的浮世绘作品。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漫画”一词在中文中的使用源于丰子恺1924年的《子恺漫画》。现代意义的日本漫画业已有百年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形成以漫画产业为龙头,带动动画和游戏产业的产业链。[17]日文与动漫最接近的词汇是MAG,即manga,anime和game——日语“漫画”“动画”“游戏”三词的首字母,体现出日本动画和相关产业分工协作、高度整合的产业结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动画制作和输出国,影响从东亚辐射全世界,显示出巨大的规模效应,并在整体经济进入滞胀后仍然保持强势增长。对于同样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的东亚邻国来说,相较于美国,日本动画产业因为文化的相近性对我国更具有示范意义,将“动画”与“漫画”绑定在一起的“动漫”正显示了中国政府参考日本产业链的政策取向。“动漫”在民间和个人语境下的使用,也经常倾向于指代日本文化产品或与之风格相近的产品。与这种更狭义的用法相对应,另一个词语“中国动漫”被用来特指中国本土产品,并在使用中逐渐被简化为“国漫”。还有一些来源于日文的词汇如“二次元”“御宅族”等也都本土化为汉语中的显词。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动画生产由传统的漫画动画化路径,逐渐扩展到电视原创动画、轻小说动画、游戏漫画化等多种渠道,产业界形成集漫画、动画、游戏、轻小说、广播剧、真人版、绘本、模型玩具、角色设计等全领域、跨媒介和多渠道的组合态势。在政府举措激励下,自2009年起,我国的动画产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但是领域内的整体产业链尚未形成,基本还处于一种以动画,特别是剧场版大银幕动画电影来带动一切的模式,目标消费群体也存在着定义和形态上的“漂移”。所以,目前在我国的传播语境中,从产业角度上看,“动漫”一词无论在语感上还是实际使用上,都还算最切实的一个概念。“今后随着我们自己的产业逐渐充实,想必‘动漫产业’一定会随之被重新定义或被新词取代。”[14]动画中文称谓的演变将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行下去。
结语:动画称谓衍指符号的文化意义图景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索绪尔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概念,指出语言词汇的能指对所指的指代关系具有任意性,是社群习规的结构性产物。[18]相对于索绪尔的符号两分法,皮尔斯将符号分割为三个元素:“再现体”相当于能指,而所指在皮尔斯的理论中则指向两个不同的客体,一个是“对象”,一个是“解释项”。通过解释项的加入,皮尔斯强调意义除了指向物质的确凿的对象,还可以是解释行为的产物,随时代、文化、语境而变化。解释项的存在明确了符号表意延展和衍生的潜力。刘禾在对跨语际实践的研究中,将皮尔斯的意义衍生的思想纳入对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关联的考量中,对现代中文中的异质语言现象提出了“衍指符号”(super-sign)的概念。在这里,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一种跨越不同话语系统的词语意义链,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运动轨迹,是语言向文化敞开的方式,“引诱、迫使和指示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19]。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文动画称谓的历史沿革所形成的“卡通—美术片—动漫”这一名词链接可以被视作一个衍指符号链,这个符号链接所携带的意义场已经超越作为对象的动画本身,而延伸为百年来本土文化在内部和外部多元力量接触、协商和碰撞下不断嬗变的缩影,对应了不同制度和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同的社会主导话语体系,折射出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本文将动画称谓衍指符号的文化意义图景在图2中进行直观地呈现。

图2 动画称谓衍指符号的文化意义图景
梳理动画中文称谓的衍指符号意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形式的确立依赖于多元的、流动的和当下的社会话语协商。这种认识有助于突破常见于以往动画史研究中的原创/复制、本土/外来、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体系,也有助于形成对中国动画和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