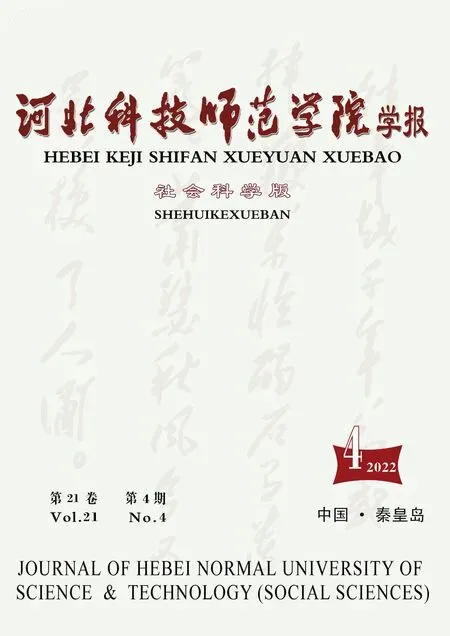“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韩宏韬,娄翔宇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3)
从简牍的产生时间来看,安大简《诗经》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诗经》版本,比传世《毛诗》的产生还要早。在简本《诗经》的内容上,安大简《诗经》虽仅存六国“国风”57篇,但出现了大量的异文、异体字,甚至部分篇章章句的字数也存在不同。在编排体例上,各国“国风”篇外的编排次序、篇内章次的编排次序也存在着异于传世《毛诗》的现象。深入研究安大简《诗经》,不仅有助于窥探早期《诗经》的原始面貌,还有助于对照研究传世《毛诗》文本的流传演变。
关于安大简《诗经》,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该批简牍,2019年安大简简牍整理小组将相关《诗经》整理成果汇集并出版为《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1]一书。时至今日,已有诸多研究者发表不少相关研究成果,且研究综述也已发表两篇,分别是:汤漳平的《近百年来出土文献与楚辞研究综述》[2]和李丹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研究综述》[3],而涉及对安大简《诗经》相关研究进行汇总的仅《<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研究综述》一篇,汤漳平的文章只是将安大简作为一种出土材料与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简牍并列叙说。李丹则主要从“文字考释”和“诗文文本的训释”两大部分,对已有的安大简《诗经》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上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随着时间的变化,新的研究成果迅猛递增。其二,该篇研究综述所涉及的研究论文数量略有不足,李丹归纳的研究文章总数为45篇。迄今为止,安大简《诗经》相关研究成果已多达80余篇。其三,该篇综述的分类范围有嫌粗略,“文字考释”和“诗文文本的训释”的分类方式,实际上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诸如安大简《诗经》文本结构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价值研究等。这样看来,根据上述的综述研究,近年来安大简的整体研究动态仍然无法向学界全面呈现。因此,对于安大简的研究现状,有重新反思和梳理撰写的必要。
一、常识性介绍
2015年安徽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该批竹简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包含了《诗经》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献。经“安大简”整理小组整理后,共计发现《诗经》篇目57篇(含残简),涉及六国《国风》:有《周南》10篇、《召南》14篇、《秦》10篇、《矦》6篇、《鄘》9篇,《魏》(唐)10篇。关于已整理简本《诗经》篇目的基本情况,黄德宽道:“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侯风》,所属六篇诗《毛诗》则归《魏风》,而《魏风》除首篇《葛屦》外,其余九篇则是《毛诗》之《唐风》。各国风内部所属诗篇排序和数量也与《毛诗》略有差异。”[4]另有研究者根据简文内容推测简本《诗经》为58篇,应为七国国风。马银琴认为:“这部《诗经》抄本的基本特征: 总共包括七国国风,其中《周南》10 篇、《召南》14 篇、《秦》10 篇、《侯》6 篇、《鄘》9 篇、《魏》10 篇,介于《秦》《侯》之间完整遗失的‘某’……《鄘》9 篇,不包括《载驰》。”[5]此外,简本与传世毛诗本相比,还存在大量异文现象,或是通假,或是讹误。这些异文的出现使得人们在一些传统看法和观念上有了新的理解。
二、字词研究
因与传世毛诗本的内容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安大简《诗经》一经出土,在文本字词方面便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对简本字词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细分为两类:其一,对字词的考释;其二,对简本字词偏旁省略的解读,且以第一种研究居多。
(一)字词考释
在安大简《诗经》中,对字词考释的研究成果众多。
1.《秦风》相关篇章
对《诗经·秦风》字词考释的有:曾富城从同源词的角度分别对《鄘风·君子偕老》《秦风·小戎》《魏风·陟岵》中的“玼”“俴”“岵”字进行新的训释,认为“玼”字义当为“玉色白”,“俴”字义为“马无著甲”,“岵”字义为“山无草木”[6]。董露露认为,训简本“蒙伐有苑”为“盾上的杂色文饰华美繁盛”[7]。同样对《秦风·小戎》一篇进行训释的,还有周翔,他认为,《秦风·小戎》中的“驾我骐馵”的“馵”与简本中的“馺”有别,二者并非异体、通假或古今字关系;同时训“馺”当为千里马义的 “骥”字初文,简本“馺”字的出现有可能为文本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8]。郝士宏则对同属秦风中的多篇异文进行了考释,他认为:“《毛诗·秦风》中‘驷驖’本应作‘四牡’,‘溯洄’‘溯游’应读作‘溯违’,‘有条有梅’应读作‘有柚有梅’。”[9]在《诗经·君子皆寿》篇的相关研究中,徐在国对“蒙彼縐絺”的“縐”进行考释,认为简本中的“縐”字形当训为从“玉”,“翛”聲,与今本“縐”音近可通[10]。
在与《毛诗》本的对比研究中,汪梅枝通过对比毛诗本,对“於”字的词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此处把“於”看作介词更加合理[11]。同样是与《毛诗》本的对照,郑婧、王化平则从词义训释、字形字音等方面,将“羔羊之缝”“于嗟乎驺虞”“四驖孔阜、四马既闲”“於我乎”和“谁之永号”等五处异文进行了详细训释[12]。
在简本《秦风·晨风》篇的研究中,刘刚对“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之“郁”字,以及在简本中写作“炊(吹)字的现象作了探讨,他认为,《毛诗》中的“郁”可能是误字[13]。高中华则对简本异文“息、思”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息”是“思”字的假借[14]。禤健聪对“夨”字体偏旁战国文字作出训释,认为简本“ ”字与今本《卷耳》篇“不盈倾筐”之“倾”对应[15]。陈伟武则依据简本,训释今本中的“樛木”在简本中应假借为“流木”[16]。
2.《魏风》相关篇章
在《魏风·硕鼠》篇的研究中,朱彦民对“硕鼠”一词作了训释,他认为,传本《诗经·硕鼠》篇中的“硕鼠”在简本中写为“石鼠”,“石鼠”实则是“鼫鼠”的一种异体写法,在古代也存有“石鼠”“鼫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一类[17]。
3.《周南》相关篇章
关于《诗经·葛覃》篇的字词研究也有不少。徐在国对《葛覃》中的“刈、濩”二字重新训释,认为《诗》中“刈、濩”属于同义互换[18]。姚小鸥则对整理者徐在国先生已论定的“濩”字进行重新训释订正,认为《毛传》以“煮”训“濩”并无不当[19]。同样,耿可可从《诗经》中的“是A是B”句式分析和“穫”字所存文例分析,认为“濩”也当读作“鑊”,训为“煮”[20]。
在字词的训释中,《诗经·关雎》篇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较大关注,如杜泽逊谈到,“要翟”二字,应训释为“姣好之貌”[21];徐在国则以为,简本中的“要翟”应读作“腰嬥”,即细而长的腰身,“腰嬥淑女”,就是指身材匀称美好的女子[22];孙可寒从异文、构词与语境等角度对该词的训释进行了考察,认为“要翟”应该是“窈窕”的异文[23]。在简本《关雎》字词训释研究中,除对“要翟”的训释外,还有对“寤寐”二字的关注,徐在国从字形分析,认为早期《诗经》版本“寤寐”作“寤寝”,是出于“寐、寝”二字同义互训,后因秦时战火,文本仅得口口相传,汉时学者可能因形体相近,故将“寤寝”写作“寤寐”[24]。华学诚认为,毛诗本《关雎》篇中“左右芼之”的“芼”同简本中“左右教之”的“教”不应解释为通假,教可训释为“解释”[25]。相宇剑认为,今本《关雎》中的“悠哉游哉”在安大简中作“舀才舀才”,“舀”和“悠”通假,“哉”“才”可通用[26]。同时,相宇剑对“关关雎鸠”的异体作了训释[27]。此外,周翔、邵郑先则对简本中出现的“专字”进行了考释[28]。
4.其他篇章
夏大兆对传统命题“言”当“我”讲的使用状况进行了确证,“《诗经》中‘言’可当‘我’讲可能是方言成分的遗留。”[29]
(二)字词偏旁省略
除上述对字词的训释外,还有研究者关注到了简本字词的偏旁省略现象。如俞绍宏、张青松训释“人”为“飤”的省去“食”的写法,认为:“省去偏旁现象在楚简等战国文字中大量存在”,同时,他们将这种省略现象的现象归结于是古文字偏旁的漏抄[30]。
三、韵读研究
在安大简《诗经》的研究中,关注《诗经》韵读研究的研究者也有数位。如俞绍宏、宋丽璇从韵读的角度将毛本的韵读和简本《诗经》的韵读进行对照,认为在韵读上的一致性表明二者的亲缘关系很近,可能都来源于孔子整理过的本子[31]。程燕则关注到了毛诗本和简本用韵的不同之处:“虽然安大简《诗经》大部分诗的韵例和所押韵部与《毛诗》相同,但韵脚部分用字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其余用韵的不同。”[32]俞绍宏对《陟岵》一篇的用韵作了探讨,认为“行役夙夜无寐”之句原本可能不入韵[33]。
四、文本性质研究
在现存的安大简《诗经》研究中,对简本文本性质研究的也有不少。如张树国对简本《诗经》的原型做出探讨,认为其产生与历史上身为魏文侯讲师的子夏西河有关[34]。马银琴则认为安大简《诗经》是流传到楚地的抄本,极有可能与早年魏文侯推行霸业有关,而且简本《诗经》的编排或为魏国早年改制《诗》乐、强化本国影响力的反映[35]。夏大兆对简本“矦”风篇诗的文本产生进行了讨论,认为矦即是晋,矦六篇均为晋诗[36]。他后来又进一步对简本《诗经》的产生进行考证,认为“安大简《诗经》底本可能是晋国的一个抄本或摘编本”[37]。除上述研究外,沈培从句读入手,对简本重新断读,并以简本为对照,揭示毛诗本在诗旨、断读及字词方面的不同,了解古人主注释的正误及其产生原因,把握古代文本流传的复杂性[38]。
五、文本结构研究
在目前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对安大简《诗经》文本结构的研究也占了不小的比重,主要包括简本《诗经》的句式研究和编次研究,其中编次研究又可细分为章序研究和篇序研究。
(一)句式研究
截至目前为止,单纯对安大简《诗经》的句式进行研究的仅李林芳,他认为简本句式的整齐性要高于《毛诗》,推测《毛诗》虽产生于汉代,但其版本来源可能更加古老[39]。
(二)编次研究
1.章序
对简本《诗经》章次的研究如下:杨玲、尚小雨对57篇简文《诗经》中出现的8篇章次不同的异文成因和价值进行研究,认为互易的章次均发生在使用了复沓章法的诗篇中,而异文章次在文学表现力上多逊于今本《诗经》[40]。不同的是,郑婧通过对比,发现,简本《诗经》与《毛诗》共有14篇在章次方面存在差异,大多篇章的不同章次变化,对诗旨表达、诗意理解并无影响,但《驷驖》《绸缪》两诗的章次互换后,在表达上或许更合理[41]。赵海丽则对《螽斯》的章次互易问题进行了单独的探讨,认为互易后的章次对以祝祷子孙众多为主题的《螽斯》而言,更能形成逻辑和诗意上的层层递进[42]。可见,对章次的互易现象,学者们大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2.篇序
简本《诗经》所涉国风的篇目编排,与传统毛诗本相比,也不尽相同,因而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如,陈民镇着重探讨了“侯”“魏”“唐”之间的次序及关系问题,认为,“侯”即是“唐”,安大简抄写者因误抄,故将“侯(唐)”“魏”的风名分别安到《魏》和《侯(唐)》之上[43]。王化平对安大简《诗经》中“侯风”“魏风”的篇目编排归属进行了探析[44]。此外,还有徐在国从整体上对简中异文和编排次序进行了概述[45]。
六、价值研究
首先,从简本产生的时间上来看,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发现最早的《诗经》抄本,其本身的存在就具有极大意义;其次,从内容上而言,简本《诗经》出现了大量不同于《毛诗》本的异文和编排现象,这对现有的《诗经》研究,无疑具有新的启发意义。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安大简《诗经》的价值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其一,关注简本异文的解题价值以及对诗旨的重新阐释;其二,以安大简《诗经》为对照材料,从其间异文看毛诗本中的讹误及毛诗本文本的流变;其三,分析安大简《诗经》中的女性本位意识;其四,关注安大简的补证价值。
(一)异文的解题价值和诗旨揭示
在安大简《诗经》的研究成果中,有部分研究者根据简本异文新释诗旨及分析解题价值。如,赵培依据简中出现的“驺虞”字形,对《诗经·驺虞》篇中“驺虞”的几种传解进行新的分析和界定,他认为,“从安大简《驺虞》的主旨可能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46]程燕对“茨”字重新训释,认为:“用居于墙上、活动于夜间、丑恶的蜈蚣起兴,引起夫妻夜间枕边所说之言辞,于诗意更为吻合。”[47]宁登国、王作顺则将关注点放在了该篇异文的解题价值上,认为,该篇有“增字、减字、章次互换”三种异文现象,并探究该异文现象生成背后的原因,确证《江有汜》为单纯的“美媵”诗[48]。
(二)从安大简异文看毛诗本中的讹误及毛诗本文本流变
作为与《毛诗》不同体系的安大简《诗经》,对传世毛诗本的文本流变及讹误的订正,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有不少研究者以安大简《诗经》为参照材料,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如,徐在国以安大简《小戎》为订正材料,对《毛诗·小戎》的“乱我心曲”句重新训释,认为毛诗本中的“乱”字应当为“挠”字[49]。刘泽敏则认为,简本《小戎》的 (乱)我心曲之 ,可能是“乱”的讹字[50]。在《秦风·终南》篇的研究中,徐在国从字形字音角度分析,认为《毛诗》本之“丹”在安大简中写作“庶”,应当是毛诗出现了讹写[51]。同样,徐在国还对毛诗《摽有梅》篇进行了订正,认为“摽”应为“囿”,《毛诗》中的“囿”应为流传中的误写[52]。刘刚对《魏风·葛屦》《秦风·晨风》两篇进行订正,认为《诗·魏风·葛屦》的“宛然左辟”本作“俛然左倪”,是描写新妇行为特点的句子,《毛诗》作“宛然左辟”,可能因转写错讹所致;而《诗·秦风·晨风》的“軟彼晨风,郁彼北林”,本作“軟彼晨风,吹彼北林”,意为“早上迅疾的风啊,在北林里呼呼地吹着”,且最早对“鴃彼晨风”做出正确解读的是宋代的戴侗[53]。王挺斌对《小星》篇进行训释,认为毛诗本中的“嘒、喵”字对应简本中的“季、李”,前者为假借关系,后者是讹误关系[54]。赵敏俐则对简本讹误的原因做出推测,他认为简本讹误现象如此严重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底本本身存在问题;其二,抄写者不够严谨,从而出现抄写之误[55]。此外,吴洋对简本八篇异文进行分析,从中管窥毛诗文本的流变[56]。赵敏俐再次对安大简《诗经》出现的文本诸多问题做出探讨,最终认为简本《诗经》并非善本,对其中的一些文字上存在的问题,不宜作过高的评价[57]。
(三)从安大简《诗经》看女性本位意识
除上述价值研究外,还有研究者将安大简《诗经》和女性联系起来,张瀚文关注到简本《诗经·卷耳》“维以永伤”和《毛诗》本中“维以不永伤”的差异,认为古代文学作品中正面描写女性多为坚贞不屈、舍己为人等“悲壮、崇高”的价值观和形象,而简本《卷耳》却折射出不同的意境和思想,它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同情思考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显示出简本《诗经·卷耳》所蕴有的浓厚的女性本位意识[58]。
(四)补证价值
安大简《诗经》作为新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对现有的先秦楚地文字研究具有极大的补正价值。目前将安大简《诗经》作为补证材料,用于补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补证《清华简》;其二,补证《书》;其三,补证《世本》;其四,补证《孔子诗论》;其五,补证字词。下面将逐一对上述五种补正进行阐释。
1.补证《清华简》
作为同属战国时期楚地的出土简牍材料,安大简《诗经》的出土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战国楚字研究的资料库。因二者在产出时间和地点上的相近,因而可以互相补证。如,侯瑞华以安大简《诗经》为材料,补论上博简、清华简等楚简牍中的“刈”字,认为,楚文字中的疑难字 为“刈”的异体字[59]。冯聪根据安大简《诗经·小戎》篇的 字,对清华简 字进行考释,认为,该字是 的异体字,应读作“载”,训为动词“重”[60]。蒋伟男认为,安大简《诗经·殷其雷》中的 字即清华简《成人》中“ ”的异体字[61]。张树国通过安大简《诗经》,补证清华简《耆夜》组诗为子夏所造的魏国歌诗[62]。此外,黄锡全将安大简《诗经》中的“ ”考释为“髡”的异文,进而论证《清华简》中推测的“淋郢”,有可能就是楚国位于今纪南城遗址或附近的“南郢”地区[63]。
2.补证《书》
作为先秦出土材料的安大简《诗经》,还有研究者将其用来补证《书》。宁镇疆认为《毛诗》中的“之子”在安大简中写作“寺子”,其中的“寺”读为“时”,理解为指代词“是”,与“之子”的“之”相同,这一现象在清华简的《书》类文献中均有所见[64]。
3.补证《世本》
在现有的安大简《诗经》研究成果中,还有研究者利用安大简《诗经》补证《世本》。原昊对《世本》楚世系远追颛顼得到印证,同时借助安大简出土简牍,将《世本》中楚康王、楚考烈王世系名号也得以确证[65]。
4.补证《孔子诗论》
季旭升通过比较《毛诗·鄘风·柏舟》中“母也天只”、《安大简(一)·柏舟》“母可天氏”的语气词“也、只”及其固有句式,认为,《上博一·孔子诗论》中的“……溺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评的应是《鄘风·君子偕老》,而非《鄘风·柏舟》。[66]
5.补证字词
借助安大简《诗经》补证楚字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夏大兆对安大简72号简中的“焚”字进行补论训释,他认为,安大简《诗经》中的“苂”字虽在金文和已公布的楚简文字材料未见,但上承接甲骨文,应释为“焚”字,读作“汾”,揭示了安大简具有早期性的特点[67]。徐在国依据安大简《诗经》出土材料,对楚文字“ ”进行新释,认为,该字当释为“兕”[68]。程燕则对简文“古、希”字进行训释,认为安大简“纟谷” 之异文可作 “希卩”[69]。徐在国以安大简《诗经》为补证材料,对“倾”和“矛”及从“矛”的一些字进行论证[70-71],依据安大简《诗经·周南·卷耳》中“不盈倾筐”之“倾”字,释楚帛书中“ ”字为“倾”的异体。此外,李松儒以安大简为材料,将之与清华、上博等简牍放在一起进行对读[72]。
七、余论
从目前研究成果的整理结果来看,学界对安大简《诗经》的研究渐趋成熟,研究成绩的突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在安大简《诗经》的现有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简本《诗经》作了研究:从文字学的角度,对简牍文字的训释;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文本的生成、性质、编排现象的研究;从音韵学的角度,对简本《诗经》的用韵做出探讨;从考据学的角度,对文本文字的讹误进行订正等。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采用对比研究。安大简《诗经》作为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其内部的编排体系和文本内容与传世《毛诗》本相比,都存在极大不同,因而不少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在这一方面,将简本《诗经》与《毛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拓展了《诗经》研究的途径和内容。第三,注重安大简《诗经》与楚文化研究的结合。简本《诗经》产生于战国末期的楚地,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先秦古楚文化的痕迹,安大简《诗经》的出土,丰富了楚文化的研究资料,因而有部分研究者利用简本《诗经》对涉及楚文化的疑难问题进行补证。多角度的切入,对照研究方法的使用,拓宽了《诗经》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使得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安大简《诗经》。
目前,安大简《诗经》的研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内容占比不均衡。在安大简《诗经》相关研究中,其中对字词研究、价值研究的比重较大,对简本文本性质、文本结构、韵读等方面的研究比重较小,研究数量略显不足,原因或许在于安大简《诗经》异文大量出现,研究材料较为丰富。第二,对安大简《诗经》地位的探讨不足,安大简《诗经》虽然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诗经》抄本,但其在文本质量似乎低于《毛诗》,因而在今后的《诗经》研究中,应赋予它怎样的地位,是遵从《毛诗》本,还是遵从简本,亦或是二者兼从,哪些方面从《毛诗》,哪些方面从简本。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深入讨论。第三,对简文的异文现象成因探究不足,截至目前,有大部分学者认为简文异文的出现是出于抄写者的不认真,从而导致讹误的出现,可是试想,在近60篇简文《诗经》中,若仅有三五处讹误出现也可说正常,但目前发现的大量成因不同的异文,都归结于讹误,难免缺乏说服力。是以往的解读出了问题,亦或是简本《诗经》所展现的是另一种文字现象,亦或是其他原因。这些都值得反复思考。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对简牍文本的考据和释读。文本是研究的基础,还原文本的本来面貌、提高文本质量,是产生优秀研究成果的前提。安大简《诗经》作为最早的《诗经》抄本,本身的存在对于《诗经》研究就具有极大意义,只是碍于本身展现出的不少讹误,严重损害了它应有的价值和地位。如果将讹误内容一一订正,那么不仅将有助于还原先秦《诗经》的本来面貌,还能为此后的《诗经》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善本。第二,继续拓宽研究视角,加大对比研究。其一,将安大简《诗经》与上博简、清华简等同类材料放置一起,进行同类比较,更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同;其二,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毛诗》等“三家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关注其中的变化,这样不仅有助于对安大简《诗经》的了解,还有助于研究传本《诗经》文本的生成流变。第三,加强对已整理安大简《诗经》的二次训释。安大简整理小组虽已对安大简《诗经》进行了详细而严谨的训释,但人力有穷尽,安大简《诗经》出土文本近60篇,数量较大,且受学术领域的限制,整理者对简文的释读难免有所遗漏和偏失,因而研究者在使用该材料时,应谨慎地对待已整理的材料,重新审视已整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