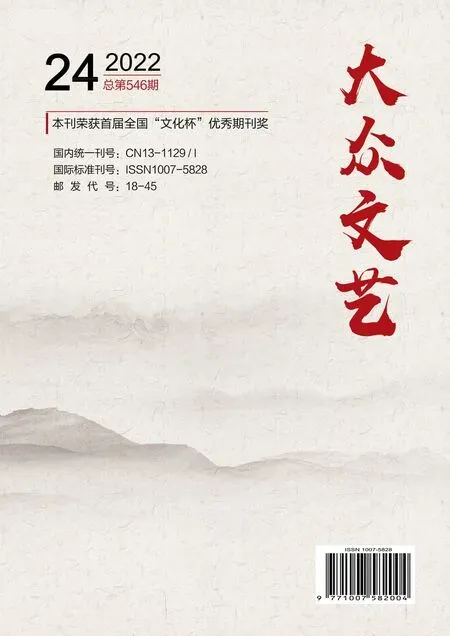媒介交互视域下大足石刻的“剧场性”研究
陈彦孜
(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1331 )
数字交互媒介在信息化时代下研发并普及开来,如今已进入成熟阶段。中国虚拟现实设备的出货量实现逐年递增;《2019-2020年VR游戏技术及行业应用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虚拟现实硬件市场规模在80亿美元左右,硬件出货量达570万台。[1]然而相较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态势而言,数字媒体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的研究也是基于数字媒体的技术问题及其应用予以展开。媒介服务于信息传播,而信息是文化流通的载体,中国大地文化遗产丰富,在如今时代探讨媒介之于信息传播的作用绕不开媒介对文化遗产的促进作用。
大足石刻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善的禅宗造像与密教道场,也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对于佛释道文化、唐宋社会风俗的研究有特有的价值。二十一世纪以来,从数字媒介领域对大足石刻开发的成果颇多,本文将延续前人研究线索,从“剧场性”角度切入,以大足石刻为研究对象,对数字交互媒介的内在美学形态展开剖析。
一、数字交互媒介的“剧场性”诠释
剧场性概念最初来源于戏剧学,尽管在该学科的发展中剧场性的概念经历了嬗变,不同学者对其侧重点有不同的理解,但逻辑起点仍然是“受众本位”的,剧场性不仅限于演员的表演过程,更强调观众与演员在此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在该范畴下,剧场性与戏剧性相对立,不同于戏剧性对假定情境的强调(包括演出中演员戏剧化的演出以及冲突性的情节),剧场性强调观者的介入与参与为剧场带来的能量,以及观者体验中主动的感受状态。
现代主义批评家迈克尔·弗雷德首次将剧场性的概念援引至艺术评论中,他认为剧场性是极少主义艺术背离了康德审美自律的物性体现,极少主义作品之所以存在剧场性特征是由于空间的持续变换导致的,由于媒介自身具备物性,观众、空间、媒介三者共同构筑起特殊的剧场性情境。[2]在极少主义艺术之前的价值框架中,艺术品是审美自足的,它将自身的意义封闭于其中,观众需要在现场观看作品,进行现场的静观与想象才能完成对应的审美活动。而极少主义乃至之后出现的装置艺术、交互艺术等把“观众”置入了作品完成的必要环节中,艺术品的意义需要通过观众来阐释,作品的自主性与封闭性被消解。弗雷德把艺术自主性的瓦解理解为剧场性的开启,艺术的意义阐释于由媒介自身“物感”特征,及其与观众间关系的建构过程中。
数字交互媒介作为一种新型的装置艺术形式,具备延伸的剧场性效应,它所营造的空间是在现实空间基础上,由二进制信息代码构建的数字化的异质空间,在该空间下现实与虚拟交叠,传达出异于传统装置艺术的全新物感。数字交互媒介基于抽象的编码基础,创造的空间是不具备实体的,只能存在于电子屏幕的另一端,但它又是可以被感知,乃至转换、变形与复制的。光影的布置与变换,形体的堆叠与破坏等,可以制造出或是有序或是无序的空间,而它自身又是虚拟的,这种由物质性到非物质性,从有限性到无限性的转化,就是数字空间的异质性。同时,由信息代码形成的异质空间可以实现并突破物理规则引导的交互体验,观者或能超越日常认知处于超重或者失重状态,也能突破地域与时间的边界,触摸与来自过去或是未来的对象,置身于丛林或者海底。数字交互媒介制造的异质空间能引导观者进入可能出现的任意一种场景中去,无论该场景来自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想象。数字交互媒介所产生的异质空间能实现无限自由性,使人类的视知觉实现大跨度的延伸,将有限的个体空间跨越为可感知的立体虚拟空间。由此可见,数字交互媒介展示出的剧场性是由非物质信息组织下营造下可感空间,它以充分的解放媒介的物感,以高度的构想性与沉浸性给予观者剧场化的体验。
除此之外,剧场性的空间强调的是一种关系性的对话机制,即交互客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并展开交流的关系。剧场化的对话关系从观众的心理反应以及行为活动出发,以“反馈”作为信息传播中的核心环节:此时观众与空间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看”与“被看”的关系,观众的行为充当推动情节展开的信号。该理论基于媒介技术的识别功能,数字媒介将观者的声音、动态转化为数字信息,并在空间中呈现出对应的变化,较为常见的为语音识别与手势识别功能。以新媒体艺术家林俊廷2011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山水觉”展览为例,他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用数字媒介巧妙的重构:观者对画中人呼喊,画中人便向观者挥手;观者拿起展台上的酒杯,画面由乌云密布转为拨云见日。可以看出,“山水觉”的完成是由观者主动推进的,最终呈现效果实现了观者与古人跨越670年的对话。可以说,“山水觉”用数字媒介制造了一种主导在观者心理上幻觉,重塑了《富春山居图》与观者的关系,创造了观者与传统文化交流对话的剧场。
数字交互媒介体现了剧场性的审美,涵盖在自身物性的外化,和交互主体与客体的对话过程中。林俊廷“山水觉”的剧场性构建无疑是成功的,它的创作经验一定程度上也能应用至数字化大足石刻的剧场性构建中。
二、大足石刻的叙事话语与剧场性
罗兰·巴特曾提出,任何材料皆可用于叙事,构建叙事的媒介有且不限于语言、文字、画面、手势等。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善的禅宗造像与密教道场,它借用石刻的造型手法将佛经文视觉化,传达了佛家宣扬的孝道思想、善恶因果思想以及苦行悟道思想。可以说,大足石刻通过石像群雕的方式构建起一套本体叙事话语,并基于该叙事话语形成大足石刻观演剧场。
大足石刻的叙事话语从形式来看可划分为点性叙事与线性叙事。展现为点性叙事的造像普遍为单龛,自身有独立的题材与情节,不与四周造像产生联系,具有代表性的为北山水月观音龛。此类造像更多的是借助形象本身的隐喻的符号特征,起到规范世俗伦理,教化信徒的作用,它并不直接展现情节,相较于线性叙事的群像而言其剧场性的体现也较弱。
大足石刻分布最广的为体现线性叙事石刻群像,其较多分布于北山与宝顶山的摩崖石窟中,按照题材的不同有展现三界众生,传达善恶因果论的经变图,也有传达世俗伦理,讲述佛教故事的经变图。线性的叙事话语体现了“异时同构”的特点,将不同时间与地点中出现的人物、情节统一在一个题材中,情节前后形成较强的连续性。例如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造像“父母恩重经变相”,群像分为三层,中层逐一通过浮雕组合再现佛经中父母养育子女成少的全过程,是该造像的核心区域。[3]该层中部“投佛祈求用息图”为情节展开的序幕,雕刻了一对夫妇在佛前虔诚地向佛求子的场景,左右分别有十恩图与之并置,每一组造像设计有二至三个人物,对应孩童从出生到成人的十一个时间点,均选自具体的生活化情节来展现。“父母恩重经变相”体现了中国孝文化的凝练,赞美父母养育子女的不易,对不孝行为进行批判。宝顶山第3号造像“六道轮回图”的四层圆环,在第三层、第四层中以环形的线性叙事手法,分别展示人界的十二因缘与生灵六道生死轮回的过程。在六道轮回的教义下,六道中的前三道为三善道,是与善业相应的三个趋生之所;后三道为三恶道,为作恶业者受生的三个去处。六道从首到尾形成闭环,众生便处于此生彼灭的因果循环中。又如大佛湾第30龛“牧牛图”,由右至左共十组造像展现牧人驯牛的历程:牧人从寻牛、得牛、驯牛,到人牛两俱忘,顿悟至“无我”的境界。“牧牛图”以牛比心,展现佛门弟子苦行修为,最终得以悟道的过程。可以看出,大足石刻群像传达的主题源自佛家孝道、善恶因果、修行悟道的宗教伦理道德体系下,在大足石刻中,佛家思想的体现都是基于线性的叙事方法得以视觉化。
大足石刻的线性叙事以图像化的形式将连续的、完备的情节逐一再现,具备一定剧场性的表演性质,这种剧场性的形成是基于单一维度的。濮波对“单一维度”有以下阐述:单一维度的剧场有看似优雅的空间,但其本质是静止的,激发的是经过文本的设计而假定的空间审美体验。[4]大足石刻营造的观演空间是观者单向的观看空间,石刻与观者的互动只能存在观者的想象中,这对于剧场感的塑造形成一种限制。受制于石刻材料的属性,大足石刻对于佛经中故事感情节的诠释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父母恩重经变”的中心第五组造像“推干就湿恩”中,佛经原文表述的情节为:孩童夜里尿床,母亲将孩童挪至床沿干处,自己卧于湿处。但在石刻的表现上,其呈现的为侧卧的母亲怀抱仰卧的孩童躺在平地上,观者如不参考注释,较难仅凭图像还原情节。
本文认为,数字交互媒介能将大足石刻单一维度的剧场进行延伸。依据数字交互媒介功能的不同,可将大足石刻构建为交互性的动态影像,抑或者搭载复杂人机交互功能的体感游戏等,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把文物从一个静观、低交互的场域转移至动态、高交互的场域中,文物自身单一维度的剧场性得以较为全面的展现。
结语:数字交互视域下的大足石刻——延伸的观演剧场
在数字交互媒介的重构下,大足石刻单一维度的观演剧场可得以延伸,此时剧场性的建构由“间性”所引导。周彦华在对介入性艺术的剧场性研究中提出主体间性这一概念,认为主体间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方式中与它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包含了多重主体之间的多种关联方式与作用方式。[5]虽然周彦华对间性的阐述是基于主体与主体,也就是艺术家与观者,观者与观者的角度而言,但该理论沿用至人机交互的数字媒介艺术上仍然成立。只不过此时的间性关系由于数字交互媒介具备的识别与反馈功能,从“主体-主体”转换为“具有一定主体性质的客体-主体”关系。在此基础上,主体(观者)的对于大足石刻的感知是由表及里的,即是对表层的空间剧场的感知向深层的文化剧场的感知逐步延伸。
大足石刻的空间剧场具体指在数字化异质空间中,观者对于石刻文物的遥在体验的剧场空间。数字媒介所产生的遥在体验基于遥在技术的基础,观者面对石刻艺术的传统视点被另一种可分享的关系所取代,虽然二者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依然能借助数字媒介所感知。通过佩戴的虚拟现实头盔,或者手持的移动端远程设备,观者身处现实空间与大足石刻的数字化空间相融合的异质空间中,其对于空间的感知被压缩,产生异于现实空间的剧场性体验。届时,受众可借助如VR头显等设备进入到虚拟的大足石刻数字空间中,基于交互系统形成与石刻文物间的“交流与互动”,受众在模拟环境中可对数字石刻文物进行“触摸、点击”等交互行为,并从虚拟环境中得到对应的反馈。受众在进入大足石刻数字交互空间时,通过作品传达的情感、观念等而产生不同的情绪状态,体验者的心理感受与作品沟通、融合,使作品的表达更加鲜活、多元。
大足石刻的剧场性更重要在于其文化剧场的呈现,也就是由人机交互引导的佛教文化与观者间的“间性对话”的观演关系。大足石刻剧场性的实质,是佛教提倡的孝道思想、善恶因果论以及修行悟道思想借助数字化媒介与观众进行的间性对话。文化剧场建构了“佛教文化-数字媒介-观者”三个维度的交叠,经由数字媒介的交互技术使得佛教文化与观者双向对话,改变了作为石刻媒介中“佛教文化-观者”的单线呈现效果。观者在数字化的大足石刻中,可以与父母恩重经变相中的父母实时交流,甚至身份转换成为佛教角色,演绎对应情节,其对于佛教文化的理解由“转述”转变为“体验”,在体验的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剧场。由此可见,置于文化剧场中的观者成为叙述故事的一个载体,自身在同空间、作品以及人的交流互动中,产生剧场化的体验,体悟整特定时空感受和记忆。
意境属于东方艺术、哲学的话语体系,它指无意识主体用意向创造的虚拟空间,主体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获得美的愉悦。意境中的意为意象之意,包括有意象化的审美对象的想象、观念、经验等内容,通过大脑的无意识将这些意象构建成境。由数字交互媒介构建的大足石刻文化剧场同时也形成了的虚拟审美的意境,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因心造境的观念相似,以观者的主观意识去感受美,通过意象创造虚拟空间,最后让体验者以互动形式让他与周围的事物产生一种超时空的感受。总而言之,数字交互媒介的剧场性还具备更多可挖掘的空间,对于本土文化遗产也存在更多应用的可能性。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资源、文化符号与数字交互技术整合,也能创作出具备更高美学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