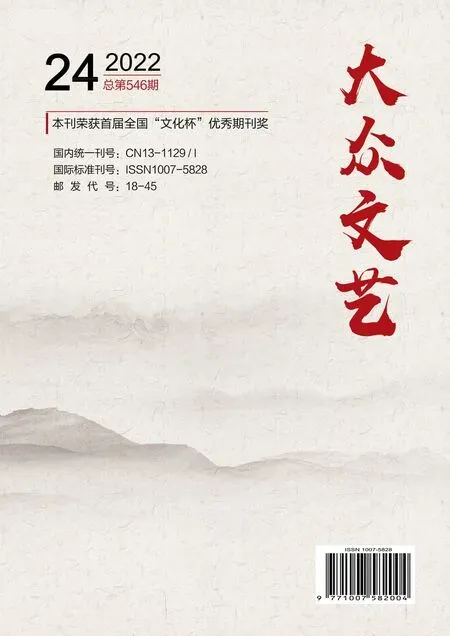《西游记》与泰州王门心学
杨翌琳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孔学堂书局,贵州贵阳 550018)
一、《西游记》批判现实的讽刺和吴承恩的身世背景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是“经历数百年演进,最后在明人吴承恩手里完成的章回小说”[1]320。是一部融合“儒释道”的皇皇巨作。清代著名道士悟元子(本名刘一明,公元1734—1821)在《西游原旨序》说:“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2]601《新说西游记》的作者,清代著名作家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批》言明:“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三层并行,毫不相背,奇莫奇于此矣。爱理学理,究其渊微;爱热闹者,观其故事;好文墨者,玩其笔意。是岂别种奇书,所可得同日而语也?”[2]625
作为我国古代小说顶峰的优秀作品,《西游记》包络丰富的内容,借神话的演绎方式,实则映射了许多现实矛盾。该书揭露了明中叶时期种种丑恶腐败的社会现实。在演义方法上,除了挥洒作者浪漫的想象力,内容多取材于作者对社会现实掌握的见闻材料与对社会的感受理解,其运用存乎一心之妙,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总结来概括,是古代人民“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3]26的表现。
《西游记》里的仙境宫阙、西方佛地,都不是干净的桃源方外之地。充斥着官官相护和官本位特权。翻开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这里面生动讲述了崔判官因为生前常在皇帝周围行走,又收到了当朝宰相魏徵的求情信(崔判官和魏徵是八拜之交),崔判官私改生死簿,把“贞观一十三年”加了两横,改为“贞观三十三年”,让李世民延续寿命,以及其戏剧化的方式嘲讽了“圣人贤君”们假公济私的嘴脸。[4]124—126而在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中,师徒四人组克服九九八十一难来到历尽来到西天取经的最后一站,就因为没有给传经的和尚“好处”,传经和尚便只给白纸伪作真经。若不是半路经文被风吹开,他们便要被蒙在鼓里,西行种种艰辛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当四人重上灵山求诉冤屈,如来知道来龙去脉后还帮腔传经和尚们,曰:“经不可空传”,并举之前的例子“三升三斗米粒黄金……忒卖贱了”,连如来都是这般贪婪市侩嘴脸。唐僧不得已,只好送了紫金钵给阿难和迦叶,才取回真经。[4]1195-1196《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中更提到,妖怪在害死乌鸡国王后,变作国王的模样霸占朝廷和后宫,老国王的尸体被困在井中,而魂魄却无法状告天听,原因竟然是那妖怪“神通广大,官吏情熟”,“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4]452-453
这些其实是对当时明代社会中一系列腐败现象的夸张化和“戏剧化”。《西游记》中描述的统治阶级,要么昏庸无能、荒淫残暴;要么作威作福、专横独断;要么是妖魔所化,沉湎女色,没几个好东西。这种种痛快辛辣的背后,折射的何尝不是作者在现实大环境中感受到的悲愤心酸。至于唐僧师徒一路上所碰到的妖魔鬼怪,有许多象征着统治阶级的伥鬼,是这个菩萨那个神仙的坐骑、童子或是姻亲。孙悟空每当打败妖魔,找到他们主人来“处置”时,这些主人都是打着“收服”的旗号,行保护之实,常常在孙悟空打杀之际,喊出“大圣手下留情”云云。这些妖魔祸害人间,生杀予夺,最后的结局除了被主子领回去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这实则反映当时明朝封建社会里的黑暗景象,统治阶级和下面的爪牙互相勾结,肆意欺压劳动人民的社会现实。《明史》言及此时的社会现状,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5]5928。
吴承恩(约1500—1582)正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才华横溢。鲁迅评价为“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6]141。吴承恩的父亲好读书,“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然而社会地位只是个没落官员的后代,经营小本生意。从祖辈高贵的读书人,落魄为最低下的“士农工商”的“商人”,平时“卖采缕文穀”,不善经营,常遭官府吏胥勒索。(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射阳先生存稿》卷三,故宫博物院影印本,转引自《西游记资料汇编》)[2]646-648在这样家庭背景中出身的吴承恩,早慧聪颖,才华横溢,但因“没有门路”,考过七八次科举不中,直到四五十岁时,由江南学政推举为“岁贡生”,他才得以进入国子监读书,等待朝廷分派官职。但很不幸,在国子监“注册”十几年后,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吴承恩才被任命为正八品的长兴县丞。
二、泰州王门的流派特色和传人
明朝中期,程朱理学进一步僵化,思想的压迫和封建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相辅相成。在这种社会现实下所催生的阳明心学,就像横空出世划过晦明天际的一道闪电,在思想界引发了震动。许多人投拜阳明门下,阳明后学又分衍出各具特色的流派,其中泰州学派继王学而起。泰州学派无论其思想还是其学风都有深刻的平民特点,泰州诸位传人的出身经历各异,但大体上倾向于社会草根阶层,向平民化,乃至于向目不识丁之人传道。
泰州王门是王门学派中十分有特色的思想流派,影响力也非常大。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便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7]703。泰州学派的传人王艮致力于发展平民教育,不区分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便传之。黄宗羲在《处士王心斋先生艮》中评价说:“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7]710这里的意思是王阳明之下,论辩最佳的是王龙溪,但论起教导更多的人相信该学说,还是王艮点化觉醒的人最多。
这反映出泰州学派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传道的对象是大众平民。泰州学派继承了孔子和先秦儒家“有教无类”的平民传统。泰州学派另一位传人王栋也十分强调儒学的平民传统。他说:“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皆无知鄙夫耳。至秦汉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7]741这是对其平民儒学教育思想的总括。事实也如此,作为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出身盐丁,壮年才读《大学》《论语》等书,泰州门下占多数的,有许多社会上的樵夫、灶丁、农夫、佣工、陶匠、商贩等等“底层”。王艮重视教育,认为“论学则不必论天分”。[7]704-711泰州学者周流天下,传道讲学,以启市井愚蒙;他们多有“深入田间,与农民班荆跌坐,以倡道化俗为己任”。
在《明儒学案》肯定泰州学派将阳明之学“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因为太过平民化而“渐失其传”的风险。[7]703在泰州学者把经书转化为普通百姓的日用之学的同时,其通俗化的解读,随意的谈论,必然导致经书原意在一定程度上被“曲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就蕴含这种近乎动摇瓦解儒学经传本意的风险。一方面看,这种精神力量能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的平民思想,但另一方面看,如果走向极端,便会让受众陷入“空想”“幻象”阶段。
于是,不管泰州学派本意如何,在百姓的日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幻想”成为虚幻精神支柱的同时,也加强了其唯心主义。这对于日用生活来说有致幻、沉迷白日梦,不切实际的风险,但在文学创作中,这种近乎神话般的唯心主义力量,恰能增加小说家的想象力,让其“人定胜天”的理念更坚定。想来《西游记》中典型的“明年皇帝轮流做”的酣畅淋漓的呐喊,也正出于其中。
泰州学派上述特点,反映出明代平民儒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风貌。也客观说明,在交叠的时空背景下,泰州学派的思潮在宏观上影响经济文化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在微观上,影响吴承恩个人思想的可能性同样很大。
三、泰州学派思想和《西游记》的轨迹交织
吴承恩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一带),又在应天府的国子监(今南京一带)做过几十年的“太学生”,晚年赴长兴(今浙江西北)上任,主要的生命轨迹在江淮活动。泰州学派的活跃的大本营——安定书院在泰州,是王艮传道讲学的重要基地之一。
从淮阴到应天府,虽然并无吴承恩投拜阳明门下的直接证据,但从几十年前后相近的生卒年(王艮:1483—1541;吴承恩:约1500—约1582),相近的地理活动范围(山阳、应天府、泰州、长兴),泰州学派流寓广传的传教特点来看,即便吴承恩没有直接投拜阳明门下,但他在时间和空间的轨迹上都和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传播区域有极大的重叠。检视吴承恩的思想历程和其反映在《西游记》中的文本,也可看到大量直接间接被影响的痕迹。
先是与阳明心学相关的思想观,在《西游记》中有大量“心本论”的宇宙观,第一回的题目叫作《灵根孕育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菩提老祖所住的地方叫“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4]10,灵台、方寸都是“心”的别称。斜月像心字的一勾,三星像心字的三点。《西游记》中不少人名、地名都有类似隐喻。作者在书中也不止一次提到,悟空拜师修炼,实则修心也。
文中多次将孙悟空称为“心猿”。比如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在作者看来,西天取经路,是孙悟空“心归本正”的一个历练。而“六贼”从名字(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来看,就是眼、耳、鼻、舌、意、身的幻象。恰可以对应王阳明《传习录》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9]7孙悟空打杀这六个“毛贼”,就是在心中与外物纷扰决裂。契合阳明心学的法门。明代著名的闽派作家代表谢肇淛在《五杂俎》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之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10]312
再者是西游记中朴素的民本思想政治观,很契合泰州学派中的相关理念。吴承恩科场失意,遭到过势利小人的侮辱。他对现实社会很不满。虽然囹圄于封建时代的思想局限性,他在《西游记》里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讽刺批判的同时,仍然脱不出幻想贤君、为理想中的圣贤天子歌功颂德的框架。但他毕竟借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勇敢的挑战。这和泰州王门中后期好些代表性人物(如李卓吾)的疾恶如仇思想是一致的。
比起阳明其他学派,泰州一脉更多表现出狂者胸次,李贽《藏书》,曾经因“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11]1的惊世骇俗,被《四库全书总目》批判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12]455。这与吴承恩借孙悟空手中那根大闹天宫的金箍棒,来代替自己胸中扫荡封建社会中种种吃人的妖魔鬼怪,是何等相似。最典型的,在书中的反映,比如在小说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车迟国猴王显法》中,孙悟空布置雷公电母龙王打雷下雨时,曾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4]562
除了心学精神、反叛精神外,《西游记》的平民化特征也与泰州王门一致。心斋的讲学宗旨是“……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3]865在当时大众都读得懂的白话文小说中,吴承恩把阳春白雪的儒释道思想以神话演绎的方式转为通俗的戏剧形象冲突,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潜移默化传播平民化的读书人思想。
在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批判的时候,吴承恩通过《西游记》表达了对人民朴素的关怀,也和泰州王门重视平民性格与平民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在三借芭蕉扇灭火焰山的大火时,孙悟空是为了百姓的“求将来,一扇息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你这方布种收割,才得五谷养生”[4]725。又比如在过比丘国时,闻说国王要取一千个小孩心肝做药引,孙悟空找来土地使神通,把小孩藏进山坳里保护起来。
总结
有人说《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有人说该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演绎着心学理论。从《西游记》批判现实的讽刺和吴承恩的身世背景、生命历程在时间空间上和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重叠轨迹来看,很难不说吴承恩受到了大量阳明心学、泰州王门的思想影响。《西游记》这部由明代吴承恩创作的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中有大量对社会现实的反照和批判,而泰州王门正是奔走在该时代下最为活跃的传道平民化、理论简易化与草根民本思想的鲜明存在。其一虚一实,共同映射出时代的雪泥鸿爪、思想的吉光片羽,不可不谓是师出一脉、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