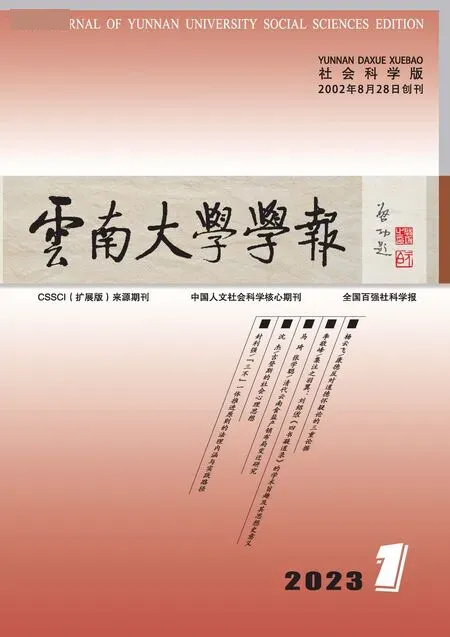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哲学关系探析:从想象力入手
毛林林
[山东大学,济南 250100]
在从德国观念论到早期浪漫主义的发展脉络中,费希特与诺瓦利斯是至为关键的两个人物。前者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不容置疑的先驱,后者是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最为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然而有意思的是,前者是坚持启蒙理性的观念论的代表人物,而后者则以诗化哲学反抗极端片面的理性,对理性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这种矛盾性凝结在诺瓦利斯对费希特哲学的继承与批判之中,其中最具有可挖掘性的就是“想象力”。一方面,想象力在理论中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尔伯特·威廉·莱维就指出:“在批判哲学中……没有什么比想象力的最终角色的确定更成问题的了。”(1)Albert William Levi,“The two Imagination”,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25, No.2, Dec. 1964, p.190.但对哲学理论而言,想象力又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和能量的概念,正如白璧德所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拒绝幻想就是忽略人性中真正的驱动力——想象。”(2)[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怀疑论者迈蒙就指认想象力为知识之来源:“为了扩大和整顿知识而发明出虚构的东西,乃是理性的一项工作,把这些虚构的东西表象为实在的客体,则是想象力的一项工作。”(3)[德]转引自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梁志学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72页。在康德的理论中,想象力概念及其所代表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开始显现,但它在费希特理论与浪漫主义的衔接处的突出,才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想象力所代表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的关系,恰是观念论与早期浪漫主义之间关系的核心与缩影,由此,从想象力入手的对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哲学之间关系的分析,将有助于梳理与呈现从观念论向浪漫主义转变的哲学发展脉络与逻辑。
一、想象力之所是及其结构

亨利希认为费希特前期理论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提出了想象力,他深化了康德关于想象力的创造性作用的理论。这种深化指向一个目的,就是澄清康德“知觉是心灵活动的结果”的观念。(6)参见[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乐小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27、328页。这几乎是观念论最不可能的主张之一。而费希特认为,通过想象力,他能够为这个主张进行论证,因此,费希特的想象力理论是基于以下信念,即知觉得以产生有赖于想象力及其活动。这无疑是直面由“物自体”导致的二元论问题,并以排除物自体所代表的理论维度为取向。一旦知觉之产生不需要借助“物自体”的“悬设”,单凭心灵就可以产生,那么知识之可能就内在地得到了辩护。将问题内化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但是这也是一种后退——费希特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心灵中异质物,即知觉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费希特在其知识学理论中确定绝对主体的绝对活动之后着手处理了该问题。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它在第二原理下被讨论,其他版的知识学,如《知识学新方法》,也有相近的论述。
费希特将知识学的第二原理表达为:相对于自我,直截了当地对设起来一个非我。(7)[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514页。按照知识学的结构,第二原理在内容上是有条件的,即它依赖一个已经通过自身的行动被绝对无条件地设定的自我。因此,在非我被相对于自我设定起来之后,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或者说一对关系就被建立起来:自我—非我。所谓“内容上有条件”是指,非我之被建立,本质上是自我将自身的实在性转移(übertragen, transference)了一部分给非我,非我获得了相对于绝对自我而言有限的实在性。这里就构成了一个二重自我:绝对自我——具有全部的实在性;有限自我——具有部分的实在性。与之相对的,就有形式上与绝对自我相对的非我范畴,以及内容上与有限自我相对的非我。按照倪梁康教授在《自识与反思》中对自我的分析,绝对自我作为规定非我的自我,是实践自我;有限自我作为被非我规定的自我,就是理论自我。(8)参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2-233页。想象力使得这种自我的界分、亦即自我的活动得以可能:“大写自我不可能是受到限制的;除非在那个限制性中有一定数量的实在性,否则这里就没有限制性。大写自我把实在性转移到C的活动就是想象力。没有这种转移,表象(C)将是不可能的。”(9)[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第328页。表象对于自我而言,是自我的绝对活动受到限制而被迫折返时在心灵之中产生的“有物存在”的感觉或者说信念。“物”则是与自我相对的、通过自我产生的非我。
因此,在费希特的理论中,想象力首先是一种使得实在性的转移得以产生、从而构成自我与非我的对立的能力。实在性的转移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操作,它的理论意义在于,以实在性为内涵的、与自我对立的“物”仅仅是自我通过想象力的构造的产物,“非我的一切实在性都只不过是一种从自我让渡过来的实在性”,(10)[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586页。通过想象力的运作过程:“汇合,或者说界限,本身就是正在和要去把握的把握者的一个产物(想象力的绝对正题,因而它绝对是生产性的)。由于自我与它的活动的这种产物是被设立为对立的,所以汇合的双方被设立为对立,而在界限上双方都没有被设定(想象力的反题)。但是,既然双方重新被统一起来——自我的上述生产性活动应当归属于自我——进行限制的双方本身就在界限上被结合起来。(想象力的合题,它在想象力的这种反题与合题的活动中是再生产性的)”,(11)[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628页。一个与自我相对的外在世界的观念,通过想象力“内在地”在理论上得到说明:“要寻找我们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信念的基础,我们必须集中讨论想象力的结构。”(12)[德]迪特·亨利希:《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第342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想象力本身并不生产或者说创造实在性,它的生产仅是对已有的实在性进行加工,从而建立起对立物之间的相互规定(Wechselbestimmung)。在费希特的理论中,这种相互规定并非静态的关系,而是想象力在对立端项之间的不断的运动,它被称之为“摆动”(Schweben):“想象力,由于它的本质的原故,一般地摆动于客体和非客体之间。”(13)[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656页。想象力的摆动就是它的生产和创造:“想象力是这样一种能力,它摆动于规定与不规定、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中间地带……想象力的这种摆动就是我们刚才所谈的那种想象力的合题。——想象力恰恰通过它的产物表示这种摆动。想象力仿佛是在它自己的摆动期间并通过它的摆动而把它的产物制造出来的。”(14)[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629页。
想象力不生产实在性,且实在性也并非自我的本质;自我的本质是不断设定对立物,并在对对立物的克服中获得表象,即知识内容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力生产了自我,并构成知识以及其他一切之可能的依据和条件:“绝对对立的东西应当通过思维能力被统一起来却又不能统一起来,于是它们就通过心灵——它起这种作用时就叫想象力——的摆动而获得实在性。”“因此,在这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教导:一切实在……都仅仅是由想象力产生出来的。……现在既然像在目前这个体系得到了证明的那样,证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为我们的存在,即我们的作为自我的存在,其所以可能,是以想象力的这种活动为根据的,那么,我们如果不想抽掉自我,也就不能丢掉这种想象力的活动。”(15)[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640、641页。
想象力对知识与体系的基础性地位在诺瓦利斯的理论中得到回响。首先,诺瓦利斯明确地指出:“统一——全体——为了获得全体我们必须从统一出发并且它就是想象力。全体是想象力的产物。”(16)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184.其次,想象力的生产同样并非是对存在的“生造”,而是一种作为中间项进行的连结的活动:“想象力是连结的(verbindende)的中间项——综合——转变力(Wechselkraft)。”“完成往复运动的正是想象力,它具有绝对综合的能力。”(17)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86&168.或者说,所有的对立项都存在于想象力的范围之中,想象力包含了存在的所有形态,无论它是可能的、现实的还是必要的,都不可避免地与想象力发生联系,并由此被界定:“确定的是,所有可关联的东西都在现实(Wirklichkeit)或想象力的领域中,包括那些已经被关联的东西。可能性、现实性和必要性是同一的。现实性的概念是与直观相连的——必要性是与想象力相连的——可能性是与表象相连的。可能性的概念的基础存在于表象中——因此,它是真实的命题。现实的概念在直观中被奠基,它是反题,因为它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必要性的概念的基础在想象力中,它是综合——可能性是一个在第三者中的双层关系——作为在必要性和现实性之间的摆荡(schweben)它是无。”(18)Novalis: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77-178.
按照这里列出的关系,现实性与直观相关,是反题;可能性与表象相关,构成真实的命题;而与想象力相连的必要性则构成综合。对诺瓦利斯而言,直观是想象力与感觉的产物,表象是想象力与概念的产物,有的只是想象力——感觉和理智。(19)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67.由此,想象力统合了所有的要素,理论则是由这些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正是基于无论功能还是地位上的本质性的相似,诺瓦利斯《费希特研究》的英文版译者才断言:“诺瓦利斯并没有远离费希特,毋宁承认已经存在于费希特自己对想象力的解释中已经固有的东西,并由此将美学放在他的哲学的中心舞台上。”(20)Novalis:Fichte Studies, ed. by Jane Knell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xxv-xxvi.既然想象力在费希特与诺瓦利斯的理论中具有如此的一致性,那么从观念论到浪漫主义的转向又如何在其中得到洞察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费希特与诺瓦利斯对想象力与理性和理论之间关系的不同观念,也涉及诺瓦利斯对费希特思想的批判。
二、想象力作为理性之补充
尽管在《费希特研究》中,在许多观念,特别是在关于想象力的观念上,诺瓦利斯与费希特保持了一致,但是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诺瓦利斯就已经表明了对费希特哲学的批判与扬弃。其中最为重要且著名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费希特试图基于单一原理建立基础哲学体系的努力的质疑:“费希特岂不是任意地把一切都纳入自我的囊中?凭什么?没有另一个自我或者非我,自我如何把自身设定为自我?”(21)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107.诺瓦利斯的质疑表明,他并不认同费希特哲学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自我的设定活动并不是自我存在之原因:“自我并非通过自我设定,而是通过自我放弃而存在。”(22)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96.那么自我放弃是否意味着一般认为的对“主体性”、从而对“理性”的放弃呢?事实上,对问题提出的追问或许比对问题的回答将会更有成效。拜泽尔批判地指出:“对很多人来说,早期浪漫派是未具名(avant la lettre)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怀疑基础主义的可能性、批判的普世标准、完备的体系和自明主体。”(23)[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黄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9-10页。然而这个被广泛认同的观念并非是没有问题的。“后现代”的要素在诺瓦利斯的《费希特研究》中的确都能够很好地被找到——如果以对号入座的方式进行阅读的话。但是,尽管要素众多,它仍然不能构成对诺瓦利斯哲学样态的概括。在另一方面当拜泽尔将早期浪漫派称作“启蒙之子”(Kinder der Aufklärung)的时候,他又有其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在诺瓦利斯那里,对体系、基础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对并不使他走向与之相对的极端,或者说,诺瓦利斯理论中表现出来的批判,恰恰是他出于对问题的反思而试图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解答,“去实现理想、解决启蒙运动的突出问题”。(24)[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第75页。启蒙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彻底批判与教化的理想。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摆脱人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够自主地使用理性。对理性的自主使用,发挥它彻底批判的能力,是摆脱蒙昧与偏见、实现教化的最为有效的途径,而教化指向的是更高的道德、政治和美学的理想。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启蒙的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最终导致哈曼和雅可比著名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彻底批判对于教化所遵循和追求的道德、政治和美学原则所起的是消解而非建构和辩护的作用。
在诺瓦利斯看来,矛盾的解决并不是对理性和至高追求的放弃,而是通过强调感觉、爱等以往被理性主义排除在理论之外的部分,来弥补理性与理论的缺失,构建一种整体性。诺瓦利斯认为:“我不知道的,却能够感受到。我相信,自我感受作为内容的自身。”(25)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II,S.105.感受不仅仅是认知的补充,甚至就哲学而言,它具有相比于反思更为基础的地位: “哲学的原初是感情。感情的边界也是哲学的边界。感情似乎是第一位的,反思是第二位的。”(26)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14.基于这个信念,诺瓦利斯几近重构了费希特的本原行动:“本原行动将反思和感情结合,它的形式是反思,它的内容是感情。它发生在感情中——其方式是反思的。呈现感情的纯粹形式是不可能的。”(27)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16.将感情纳入本原行动,作为其内容的来源,诺瓦利斯试图平衡理性与感情的权重,并由此限制理性的边界,以为更多的可能、为生活留下空间:“哲学在此止步,也必须止步于此——因为这里正是生活的所在,生活无法用概念理解。”(28)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106.
概念对生活的无能为力也就是哲学的无能为力,但并不能因为这种无能为力就放弃哲学追求,相反,正是这种有限提供给哲学不断追求的目标:“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无能为力(unvermögenheit)去触及、去认识、去寻找那个绝对。给予我们的绝对只可能以否定的方式被认识。”(29)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270.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理论的定义就得到了改变或者更新:“哲学必定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当我做哲学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对基础进行反思。因此,做哲学的基础是一种追寻关于基础的思考的努力。然而,基础并不是文字意义上的原因——而是一种构建——与整体相关联。因此,所有的哲学活动必定以绝对的基础告终。现在,如果这个基础没有被给予,如果这个观念包含一种不可能性——那么去哲学的冲动就会是一个无限的活动——没有终点,因为有对绝对基础的无限的驱动,而它只能被相对地满足——因此它将永远不会停止。”(30)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269-270.哲学作为对目标的不断追求而始终处于正在形成的状态,封闭的体系由此被打破。按照加比托娃的观念,“追求一个开放的、‘不成系统的’哲学体系,表示要从认识论上证明哲学认识一个无限的过程,这是浪漫主义的重大理论成就”。(31)[俄]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王念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不成系统的哲学”排除单一原则,“所有对一个单一原则的追寻都像是寻找一个圆的方”,(32)Novalis: Schriften.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S.270.因为单一原则仅仅是一个调节性的观念,不能依据它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封闭体系,否则其结果就是以理性为准则,将它无法把握的生活排除在理论之外,从而造成整体性的丧失。此种“整体性”被认为构成浪漫主义对费希特的超越:“费希特处处努力把自我的行动的无限性排除在理论哲学的范围之外,使其隶属于实践哲学范畴,而浪漫主义者恰恰要使它对他们的理论哲学乃至他们的整个哲学具有建构意义。”(33)[德]本雅明:《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王炳钧、杨劲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也就是说,不是拒斥费希特哲学的行动自我的第一原理,而是通过扩展这个原理的内涵与应用领域,从而实现对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才是诺瓦利斯的理论目的。实践哲学在诺瓦利斯这里意味着根据真理、依照渴望去行动:“纯粹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是能指路的。因此,唯一重要的是把某人引上正路,或者确切地说,给他指出一个朝着真理的确定方向。只要他渴望达到真理并付诸行动,他就会自行达到目的。”(34)[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真理与行动之间并不存在断裂或者鸿沟,只要依凭渴望去实践,目的就必然会达到。因此,实践对理性而言是去完成和去实现,然而在整个序列之中,理性与真理相对于实践而言,起的是消极的作用: “我在寻找怎样的一种理论?我寻找一种使我们的思考有秩序的理论——使我们之间的变化有法则的理论——建立一种直观的和概念的大全(Ganze)的理论——之后,我就能够规整和说明我的内在的现象——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图型(Schema)。”“所有的理论都应该被完全地给予,除了排列顺序,哲学什么都不会。想象力为判断补充材料,以便它在未知的领域停留。”(35)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249-250.
理性的消极作用表现在,它并不进行创造,而只是对材料进行规整以提供思维的秩序。因此,认识的确离不开理性,但更为重要的要素是想象力,想象力是生动的、积极的创造力,“感情、知性和理性都较为被动……相反,唯有想象力是一种——能动的——驱动的力”,(36)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167.想象力为判断提供材料,由此使得主体能够向前行动,从而拓展未知的领域。正如拜泽尔指出的:“他们(青年浪漫派——笔者注)似乎赞同康德和雅可比的理性批判背后的一个根本点,即理性没有创造事实的能力,而只有通过推论来联系事实的能力;事实本身必须从某种别的源头被赋予理性。在浪漫派看来,这个源头只能是创造性的想象。”(37)[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黄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第84页。对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依赖,用弗兰克的说法,是“把它的不可表现性当做不可表现性来表现”。(38)[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聂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是艺术,尤其是诗。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诺瓦利斯所采取的理论形态而轻易断定,他面对一个无法理论化的问题而躲入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之中:诗的理论形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力量:“诗的感觉颇近于神秘主义的感觉。这种感觉乃是针对那种奇特的、个人的、未知的、神秘的、需要敞开的、必要而偶然的事体。它表现不可表现的。它窥见不可见的,感觉到不可感觉的……”(39)[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127页。因此,诗从本质上是对哲学体系的补充,整体性(Totalität)是哲学与诗共同作用的结果:“诗提升每一个别物,乃是通过将它与其余的整体独特地联系起来——如果哲学通过立法,才使世界对接受有效的思想有所准备,那么,诗仿佛是哲学的钥匙、目的和意义;因为诗建构美的社会——世界家庭——美的宇宙家政。哲学靠制度和国家,并且以人类和宇宙的力量强化个体的力量,使整体成为个体的器官,也使个体成为整体的器官——诗同样如此,只不过是靠对生命的直观。个体生存于整体之中,整体也生存于个体之中。通过诗才可能产生最高的同情和同心,以及无限者与有限者最紧密的联合。”(40)[德]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第133-134页。可以看出,艺术与诗实现的是启蒙的另一个信念,即教化的信念,而教化指向被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所拒斥,严格地来说,被理性的彻底批判所解构的美和善的辩护:“艺术则是一种积极和生产性的力量。它具有通过想象来创造整个世界的力量。道德和宗教信仰,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统一,这些曾在一个天真的层面被给予早期人类的东西,业已被批判的腐蚀能力所破坏;如今的任务则是通过艺术的力量在自觉的层面来再造它。”(41)[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第83-84页。
三、理性之自由与浪漫之自由
通过艺术再造道德和宗教信仰,就是要发挥艺术所具有的教化力量。在诺瓦利斯那里,教化在于发展自由:“一切塑造(Bildung)皆引向此者,人们只能将其称作自由,当然以此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而应是一切此在的创造的根基……恰恰这种涵盖一切的自由、技艺或主宰,才是良知的本质和本能。”(42)[德]诺瓦利斯:《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自由不仅是创造的根基,同时也指涉良知,因此,在良知、自由与创造之间就建立起了等同性。自由与创造之间的关系根植于想象力。在诺瓦利斯看来,自由仅仅表示摆荡的想象力的状态,所有的创造都是想象力之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诺瓦利斯指出要训练想象力以及其他能力,并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找到前进的正确道路(43)Siehe 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257.,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道德命题。
教化依赖于以诗为代表的审美活动之内涵也由此得到澄清。当诗与艺术不单纯是一种审美活动,而与教化相关,那么浪漫派通过对艺术的倚重来试图弥补而不是取代由启蒙的理性批判造成的虚无在逻辑上就是可把握和理解的。在诺瓦利斯的理论中,理性作为一种规整性的力量,它仅仅提供认知的图型,不提供内容。对理性的无限推崇本质则是对形式的过分注重,由此导致内容的丧失、对感性的忽视——理性并不生产,它是一种消极性的力量,而非积极的行动。诗或者艺术,作为“对模糊的整体的感觉”和“对对象的神奇直观”,真实而完整地呈现了世界,诗人“无所不知”。相对于哲学家,诗人具有对世界的整体性视角,自由就是这一视角的基础:“整体的成员越多样化,绝对自由的感官(empfunden)就越生动——越相关,越整全,越是有效、可直观和被承认的,所有基础的绝对基础,即自由,在其之中。”(44)Siehe 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270.
诗人之所以能拥有这种“整体性”,不是因为他对世界的静观——这是理论的、理性的方式,而是通过积极地行动:“一个无限的存在的实现过程应该是自我的使命,它的努力(streben)应该是去更多地存在(mehr zu sein)。”(45)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S.267.因此,“整体”是一个通过无限的行动逐渐获得的过程,在过程中,理论和哲学的界限被打破,“通过想象,最终通过其最高的想象,即想象者的想象,自我在理论上得到完结、填充。这些想象是对非我的想象。这一非我,如引言所表明的那样,具有双重功能:在认识上引导回归自我统一体,在行为上引导走向无限”。(46)本雅明:《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王炳钧、杨劲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所以,也可以说,艺术对教化的作用,在于对行动的鼓励,这正如拜泽尔指出的:“艺术对于席勒和浪漫派变得如此重要,正是因为他们视艺术为化解这一危机的唯一手段。他们认为,哲学不能激发行动,而宗教无法说服理性,但艺术却有能力鼓舞我们根据理性来行动。艺术如此强烈地诉诸想象,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感受,因此能感动人们按照共和国崇高的道德理想来生活。”(47)[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第139页。如果说诺瓦利斯是将想象力放置在艺术的中心,那么教化就是对想象力的鼓励,来激发行动而不断追求自由:“自由的概念已然存在于活动的概念之中”(48)Novalis: Schriften. Hg. v. 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 Darmstatt, 1966.ff. II, S.205.。
如已经阐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在对立之间的摆荡。按照弗兰克的解读,“摆荡”的创造或者生产,归结于一种时间中的前后相继:“那种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无条件转换’,即那种在相互限定之间的‘漂游’使得自我不能同时与自身共在。在这种情况下,实践就是初始被称为从有限到无限从无限到有限的表面跨越之间的‘来回方向’的完整结构。”(49)[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第261页。在弗兰克看来,在端项之间的来回活动并不是一个瞬时性的完成,因此“原本统一的想象活动只能在一个‘前和后’中‘进行’”,(50)[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第259页。这就是意味着想象的统一是过程性的、时间性运作:“那个把现象世界里的抽象物集合在一起的范围,其真正内在的东西就是时间——这就是主观性的真正本质。它是‘创造一切的力量(…),如同破坏一切——联合一切——分离一切一样’。这里把想象力的基本功效归于了时间:联合能力和分离能力(即把力量统一和分开),此外还有绝对所独有的创造力。”(51)[德]曼弗雷德·弗兰克:《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第259页。弗兰克对想象力的时间化解释,与海德格尔具有一致的地方。海德格尔就认为先验想象力与时间是同一个东西,并且“生产性的想象力是主体性的能力的根源。它是主体此在自身的绽出的基本机制。由于想象力从自身中释放了纯粹实践,正如我们显示的(这意味着想象力包含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纯粹时间),所以它是本源的时间性,并且由此是存在论知识的根本能力”。(52)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7, S.418.
然而,在诺瓦利斯的理论中,时间与想象力的关系并非是想象力最终被归属于时间。诺瓦利斯对时间与空间的说明的确与想象力相关,“时间是想象力中空间的形式”,“空间是被移动的东西的条件,时间是运动的条件”,然而时间和空间更多的是与经验相关的: “经验的(empirisch)涉及时间和空间”,尽管时间构成认识的形式,但它本身并不是永恒之物:“永恒是时间性地被意识到的,尽管事实上时间是与永恒相矛盾的。”(53)Novalis: Schriften. Hg.v.Richard Samuel in Zusammenarbeit mit Hans-Joachim Mähl und Gerhard Schulz,Darmstatt, 1966.ff.II,S.170, S.183, S.270.因此,作为最高综合的想象力,也就是自由,不能被通过时间来理解。
在费希特的理论中,情况与此类似,即想象力并不等同于时间,也并不以时间性为本质:“自我自己并不在时间之中。是通过思维活动自我才第一次将自己在时间中延续,也正是用这个方式自我产生了时间。……时间仅仅是我们的直观形式。”(54)J.G.Fichte, 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von Reinhard Lauth und Hans Gliwitzky, Kollegenachschriften Band 2, S.187.“通过想象力在对立双方之间的摆荡,自我的直观活动原初地在每一个时刻(Moment)获得持续(Dauer)。多样性的事物通过想象力才被理解,在对立物之间的摆荡在这里产生,通过这个摆荡,出现包含在每一个时刻中的持续时间(Zeitdauer);事实上,时刻本身也正是通过这个活动的持续而第一次出现;同时,通过时刻彼此之间的序列,持续时间(Zeitdauer)也得以产生。”(55)J. G. Fichte, Gesamtausgabe,Kollegenachschritten Band 2. S.220.因此,时间是想象力“摆荡”活动之意识结果:“如果不依靠想象力来作这种扩展,时A和时刻B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分别出现。”“只有对想象力来说,才有时间。”(56)[德]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第621、629页。想象力的本原性使之成为一个超时间的瞬时活动:“在因果性概念中没有时间,有的仅仅是通过想象力对多样性的领会。”(57)J.G.Fichte, Gesamtausgabe, Kollegenachschriften Band 2, S.221.因此,弗兰克的解读——将“摆荡”活动的本原和先在性去除或者或归之于时间的序列,以使得这种无法表象或者被理性化的活动能够被意识所把握、被理论所解释的理论努力,无论对诺瓦利斯还是费希特而言,都是对“想象力”作为生动的自由的本质的取消——它是作为对理性束缚的抗拒手段被提出的,自由并非一个时间之中的、经验性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是对反思的缺陷和片面性的补偿,想象力是自由之可能或者说自由的形态。
这种想象力的自由形态与批判哲学的自由之间存在区别。根据批判哲学,自由是道德的根本概念。然而,根据理性彻底批判的原则,道德会在批判之中被消解。为了挽救道德,康德限制了理论理性批判的领域,以为道德和信仰留下空间。然而即使是将道德划归为实践理性中处理的问题,道德也仍然是一个未经批判的观念,因为我们只能从行动中推断它的应然性存在。基于道德法则的实践,即出于绝对命令对自由的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理性为自由立法之本质,是以其有限性为有限主体的行为指明更高法则之必要性。在此局面之下,自由就沦为一种消极观念,即它之获得是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或者如黑格尔所批判的:“这种自由首先是空的,它是一切别的东西的否定;没有约束力,自我没有承受一切别的东西的义务。所以它是不确定的。”(5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0页。导致此结果的根本缘由仍然在于康德的二元论的理性主义进路,费希特则试图基于自我建立绝对统一的体系来超越这种二元论。
在费希特的理论中,自我以绝对行动的第一性作为其自我决定的本质时,他就在自我与自由之间划上了等号,道德因此是内在于自我的“事实行动”的内涵之中的。因此,费希特对自由和道德的论证采取一种内在性的方式,即他并不是外在地构建自由,并将之赋予以存在为本质的自我;相反,自由是他用来论证自我的方式:自我是绝地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设定,通过这种设定,一个自我被建立起来。自由所具有的先在性在逻辑上十分明显:“对他来说,主体是自由的、有自我意识的活动。”(59)[英]古纳尔·贝克:《费希特和康德论自由、权利和法律》,黄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页。绝对自我之行动既然是凭借想象力才得以可能,那么自由与想象力之间的等同性论证在理论之中就丝毫不显突兀。由此,费希特的自由理论更偏向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而非康德所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
这种偏向反映了从批判哲学的理性主义到浪漫主义的哲学发展的逻辑。费希特对“想象力”的倚重已然说明他对于理性的片面性和有限性的认识,追求在非理性的、而非反理性的层面上来弥补由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导致的哲学困境。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基于单一原理建立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努力,对体系的信念贯穿在他的哲学生涯之中。这种努力是必要的,因为以理性为地基构建一个哲学体系,以助于人对自身地位的确定,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处理与他人和世界、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从事有效而真实的实践,对于个体而言必不可少。这种必要性同时也是理论的必要性。但理性并非理论的全部,而且理论本身也并非人的全部。这个基本事实在被启蒙运动开启的“唯理性主义”排除之后,在批判理论的断裂与无能处再次显现出来。
康德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想象力理论的减重是一种反讽性的暗示,费希特接过了这种暗示,并在理论中将这种暗示以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抗的方式彰显出来。正是在这里,他建立了与早期浪漫主义,特别是诺瓦利斯的关系。诺瓦利斯作为费希特哲学的热心者,既看到了费希特对理性主义的坚持,又看到了他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亦为诺瓦利斯所继承,无论从诺瓦利斯所选择的理论形式来看,还是他所使用的术语以及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可见的冲突来看。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观念论和浪漫主义进行斡旋的调和主义者,这种调和之结果最终成为一种与观念论的体系哲学不同的、以期望在未来实现和谐的理论形态:“卢梭曾一度置于自然状态中的光景——与自我、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和睦——如今则被浪漫派视为未来的某个理想社会。”(60)[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黄江译,第53-54页。
通过重新建立自然与人的亲密关系,恢复自然在理性发展中被祛魅的美好、神秘和魔幻,通过强调想象力所具有的相对理性的积极的创造能力,诺瓦利斯试图以浪漫主义的诗学弥补理性主义和二元论哲学的“清晰”导致的启蒙困境:对自然的机械化认识、教化目的的丧失、美的失落、自由的非现实等等。从笛卡尔而来的“清晰明了”到这里,需要被限制并以体会、领悟、爱和信仰补充之。诺瓦利斯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清晰可认的理性知识的取代,所以诗化哲学不能单纯地被归之为启蒙之后的复魅。应该看到,理性主义仍然是它的核心之一,它并不是反理性主义的。在理性主义依旧盛行的时刻,提出“世界必须浪漫化”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推进理性主义的理论尝试:它的理论要素——自我、反思以及更为重要的想象力——来源于费希特,并且是对费希特未能清晰的理论努力的进一步尝试,尽管其结果似乎呈现为一种理论的反叛。因此,将以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放置在于理性主义相一致的发展线索上的理解,相对将二者放置在对立面的理解,无论是对发掘早期浪漫主义的深刻的理论内涵,还是把握从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转变的哲学逻辑,都是更为有效和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