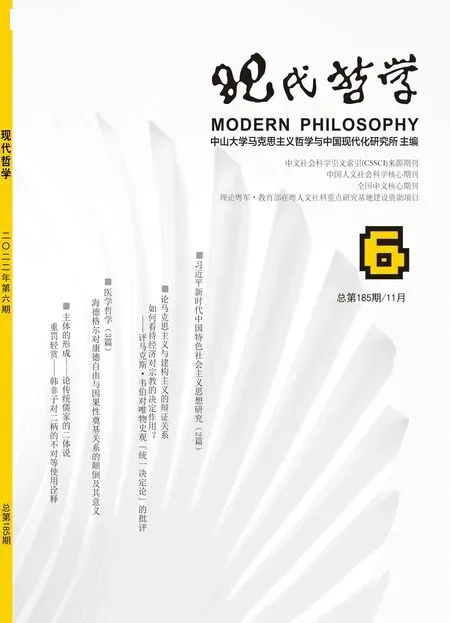汉语哲学语境中的Being难题
——评王路教授的“一是到底论”
詹文杰

王路教授的“一是到底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这样来表达:应当把英文哲学概念being(德文das Sein,古希腊文to on)翻译为“是”,而且这种译法要贯彻到底,不仅针对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文本和不同语境,而且针对古今所有的西方哲学家,不仅针对“S is P”句型中的is,也针对“S is”句型中的is,还针对to be(德文sein)的合成词(如Dasein应当翻译为“此是”,等等)。王路教授为他的“一是到底论”提供了多方面的理由。针对这些观点和理由,我在许多方面有不同意见,下面试给出我的评论。
一、Being仅仅是一个系词吗?
王路教授“一是到底论”的理由之一是:being的系词用法(“S is P”中的is)是核心用法,而存在用法(“S is”中的is)不是基本用法。他提出,“语境论者过于注重being有多种含义,以为由此being的翻译注定不能一是到底。而一是到底论强调being的系词含义,认为being的通常用法是系词,而且它的存在含义也是来自它的非系词用法,因而与系词相关”(2)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40页。。“只要把being翻译为‘存在’,就在字面上阉割了它的系词特征,因而消除了所有关于其系词以及与系词相关理解的可能性。”(3)同上,第334页。“一是到底论……可以保证正确地理解being的存在含义,而且可以保留其产生存在含义的语境,从而保留了正确理解being的可能性。”(4)同上,第340页。王路教授当然注意到“S is”和“S is P”这两种句式是不同的,不过他对待这两种句式有不同态度,因为他把“S is P”这种句式看作正常的句式,里面的is是正常的系词,而把“S is”这种句式视为不太正常的特例。例如,他认为海德格尔举出的例子“Gott ist”和“Die Erde ist”这两句话“不是日常表达,不具有普遍性,因而说明不了……关于Sein的论述”(5)同上,第299页。。他经常表示,“S is”的句式是罕见的,“God is”是一个特例。在他看来,“能够说明being含义的还是‘S是P’这种句式的例子”,而“‘a是’这样的句式就不行”(6)同上,第 301页。。
王路教授的这个理由是可以质疑的。首先,“S is”句式中的is跟“S is P”中的is一样是正常用法,而不是罕见的例外。如果说在现代语言中“S is”句式比较少见的话,那么在古典语言中,尤其在古希腊语中,这种句式是很常见的。“God is”这种句子决不是个特例。其次,更为关键的是,to be首先是个动词,然后才被视为一个系词,而且动词含义是更本源的含义。从形式上看,to be与其他动词一样有人称、数、时态、语态、语气等的变位形式,可以有相应的分词和动名词,完全符合动词的所有特征。从含义上看,to be与其他动词一样可以表达特定的活动、事件或存在状态,只不过这种活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活动。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to be(sein)的词源含义主要表示“自身站立”,或者“自身从自身中站出来并维持站立”(7)M.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Tübingen: Niemeyer, 1987, S.54-55.中译本参见[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1页。。作为动词的to be可以表示某种活动,这本不值得奇怪,不过它确实有区别于其他动词的特别之处。我在《真假之辩:柏拉图〈智者〉研究》中曾有一个说明:有些动词(例如“打”“捉”“建造”)表达某个东西(自身)对另一个东西(他者)的“作用”,有些动词(例如“走”“飞”“生长”)表达“自身”在某种意义上的“运动-变化”,然而,to be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不表示“自身”针对“他者”的“作用”,也不表示“自身”的“变化”(因为“变化”总是让“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者”),而表示“自身维持自身”,“自身”“作为自身”而“在场-出现”。(8)詹文杰:《真假之辩:柏拉图〈智者〉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这样,就动词的本源含义来说,“S is”表示“S自身维持其自身”,而“S is P”表示“S作为P而显现自身”。中文的“存在”“有”和“是”之所以在相应的语境适合于翻译to be,乃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关联于“自身维持自身”这个含义。(9)同上,第184-185页。哪怕我们把这些is都翻译为“是”,那么这里的“是”也应该被解读为有表示活动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系词。例如,“The earth is”表示“大地自身持存”,“The sky is blue”表示“天空自身显现为蓝色的”。“The sky is blue”的is不仅在语言上表示谓词对于主词的“谓述”,在心理上表示说话者的“肯定判断”,而且首先表示一件事正在“出现—发生”。
王路教授批评熊伟先生把海德格尔的例句“Der Hund ist im Garten”翻译为“狗在花园里”,认为应该翻译为“狗是在花园里”,并且说“狗在花园里”中的“在”是介词,所以这是个有严重语法错误的翻译。(10)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160-161页。在这点上我需要为熊伟先生做一些辩护。“在”确实可以表示介词,例如“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但是,“在”也可以表示动词,其中一个含义是存在、生存、活着,例如“他的父母都还在”,另一个含义是出场或出现于某个位置,例如“你的铅笔在桌子上呢”。汉语词典还会告诉我们“在”的其他动词用法,这里不详细说。(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29页。总之,“狗在花园里”这句话中的“在”不是介词用法,而是动词用法,表示出场或出现于某个位置,它是对ist的翻译,而不是对im的翻译。熊伟没有犯低级的语法错误,他显然很清楚中文“在”有这种动词用法,就像另一个例子“地球在”(Die Erde ist),这里的“在”也不会是介词用法,而是动词用法。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处处表明Sein是个动词,表示某种特殊的活动,而熊伟不可能不知道这点;他选择“在”而不是“有”或“是”来翻译它,与其说是一个错误,不如说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方案,只不过这个方案仍然不能十分完美地应用到所有的西文例句中。例如,“Das Buch ist mir”需要翻译为“这本书是(ist)我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当然是“是派”乐意拿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但是,“在派”或“存在派”仍然可以解释说,这里的“是”实际也可以转换为“在/存在”,即“这本书是(ist)我的”可以被解释为:这本书作为我的所有物而“存在-出场”。只要不把ist单纯理解为系词,而是理解为有实义的动词,那么把它翻译为“是”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它的实义。
英语to be在古希腊语的对应动词是einai。我们在古希腊语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einai作为实义动词表示“存在”“在场”等含义的例子。这里只举一例,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0c8-d1:“ēngar pote chronos hote theoi men ēsan, thnēta de genē ouk ēn”(曾有一段时间诸神存在,而有死的物种还不存在)。(12)王路似乎反对通过举出反例的方式来反驳他的“一是到底论”。但是,为什么通过举出反例的方式不能证伪一个普遍论断呢?合乎逻辑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举出哪怕一个反例,也可以证伪一个普遍论断。想要捍卫“一是到底论”显然不能通过从原则上否认反例具有证明力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说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例来实现。实际上,王路自己就是通过举出一些反例来说明有些语境的being翻译为“存在”是行不通的,从而否定“存在译法”的普遍有效性。(参见王路:《一“是”到底论》,第275页。)这里的ēsan和ēn是einai的未完成时形式(相当于英文was),它们显然表示实义的“存在”或“存有”,而非无实义的系词。实义动词einai可以派生出很多合成词,例如ap-einai、par-einai、syn-einai、en-einai等;这些合成词中einai的意思更接近中文的“存在-在场”而非“是”。Apeinai的意思是“不在场”“离场”,pareinai的意思是“在场”“出场”,syneinai的意思是“共在”“共处”,eneinai的意思是“存在于其中”。这些词如果用中文“离是”“共是”“是于其中”之类的来翻译,就会显得莫名其妙。从上述情况我们也不难发现einai这个动词的实义性,它远不是“系词”这个标签可以涵盖的。
二、“一词一译”原则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应用吗?
王路教授的另一个论证是:being是多义的也不一定导致它要用多个不同的汉语词来翻译,因为being的多义性可以被我们说成“是”的多义性;“把being看作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它也是多义的”,因为“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依其自身的意义上说事物‘是’”。(13)同上,第319-322、322、321页。总之,being的多义性在这里被王路教授解释为系词用法内部的多义,而不是与系词用法并列的多义;同时,他主张关于being应该采取“一词一译”的原则,而不能一词多译。他进一步论证,英文being和existence是两个不同的词,假如我们需要用“存在”来翻译existence,那么就一定不能将being翻译为“存在”,否则就无法区分being和existence,而且将两者分别译为“存在”和“生存”也行不通;“存在”这个中文词适合用于翻译existence,而existence异于being,因而“存在”异于being;“是与being,存在与existence,乃是对应的词,因此可以互译”(14)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07-313、313页。。他还举例说,“God is”应当翻译为“上帝是”而不是“上帝存在”,因为“God is”和“God exists”是两句不同的话,如果把后者翻译为“上帝存在”,那么就不能把前者做同样的翻译,否则原文两个不同的句子在中文里变得无法区分。(15)同上,第 294-295页。
然而,王路教授的这些主张也可以商榷。首先,being的多义不完全是系词用法内部的多义。亚里士多德的确谈论了系词用法内部的区分,但还谈到与系词用法相区分的其他用法。当亚里士多德说“可以在偶性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依其自身的意义上说事物‘is’”的时候,这里的is的确还都属于系词用法。但是,系词用法仍然仅仅是is的多种用法中的一种。亚里士多德还提及is的其他用法,其中一种表示“真”,另一种表示可以被潜能和实现限定的is。至少后面一种is就不单纯是系词用法的is,而根本上表示一种活动。如果说这种活动的类型还不是那么清楚,那么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亚里士多德以类比的方式用“认识”(epistasthai)和“休止”(ēremein)这两个动词所表示的活动来说明to be(希腊语einai)这种活动也有潜能和实现两个方面(《形而上学》1017a7-b9)。(16)W.Jaeger(ed.), Aristotelis: Metaphys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仔细阅读亚里士多德文本,不可能不注意到to be的这种用法,而且也难以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系词用法或谓述用法。这种用法的to be或许更接近于动词“存在”的意思,至少中文“存在”适合于表示某种活动。即使我们勉强用中文“是”来翻译这种用法的to be,也需要解释说它不是单纯的系词或判断词,而是表示某种活动,而这实际上扩充了中文“是”的功能,让它担负起了它本来没有的职责。
其次,“一词一译”原则不能无限制地得到应用,尽管译名的统一性是良好翻译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某个译者把同一部外文哲学著作中的同一术语翻译为不同的中文语词,那么读者很有理由抱怨该译者没能坚持“一词一译”原则,从而质疑其翻译的质量。但这种指责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一旦把“一词一译”原则变成毫无限制的原则,那么它的不合理性将变得非常明显,因为真正应该得到坚持的其实是“一义一译”原则。我们需要区分语词和它的含义。翻译活动表面上是将一门语言中的语词转换为另一门语言的语词,但实质上它是要把一门语言中的特定意思通过另一门语言表达出来,因而,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语词转写,更重要的是语义传达。如果某个语词是单义词,那么关于它的翻译就相对简单,“一义一译”和“一词一译”不会有明显的冲突。如果某个语词是多义词,那么翻译者就必须留意这个词到底表示什么含义(尤其是在某个语境对于词义的限定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然后在目标语言中为这个特定含义找到相应的语词来传达,这时候固守“一词一译”原则反而是成问题的。
让我们假定有一门语言L1,其中有两个语词A(a)和B(b,c,d)。这里的A和B是语词符号,a、b、c、d是语词的含义。不难看到,A是单义词,B是多义词。再设想有另外一门语言L2,而且我们需要从中寻找某些语词来翻译L1的A和B。那么,理想的情况是,语言L2中恰好有“甲”(a)和“乙”(b,c,d);这样,我们可以顺利地用“甲”翻译A、用“乙”翻译B,至于“乙”究竟表示b、c还是d,译者某种意义上可以交给读者自己去领会。然而,实际的语言很可能没有这么理想,譬如,有可能我们只能在语言L2中找到“甲”(a,e)、“乙”(b,c)、“丙”(d),诸如此类(17)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无法在L2中找到任何现成的语词可以用来翻译L1的某个词C的含义。这时候,为了在L2中表达C,就可能需要把C当作外来词直接引入到L2中,要么通过音译或转写(transliteration)的方式(如“披萨是从意大利传到中国的”),要么通过混说的方式(如“我实在不清楚海德格尔讲的Dasein是什么意思”)。假如人们不满足于音译或混说,那么可能就需要在L2中构造新词来传达C,如“我实在不清楚海德格尔讲的‘此在’是什么意思”。。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用“甲”来翻译A,但是仅仅取其含义a,同时需要排除含义e;另一方面,当B表示含义b或c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乙”来翻译,但是当B表示含义d的时候,就需要用“丙”来翻译它。由此可见,只要语词并不都是单义词,而且有待翻译的语言(L1)和目标语言(L2)在词汇上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一词一译”的原则就决不可能得到无条件应用。例如,古希腊语的logos一词根据不同语境可能需要超过10个词语(如陈述、句子、言语、定义、理由、理性、比例,等等)来转译它。英语的bank需要用“银行”“堤岸”等不同词语来翻译。动词的情况也类似,例如英语的call,想用一个中文词来统一翻译它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说be也是多义的,不能强行用同一个中文词来翻译,为什么这就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呢?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说,由于being和existence是两个不同的词,就不能用同一个中文语词来翻译;因为这还是取决于它们的含义,而如果在特定语境中它们的含义相同,那么用同一个词来翻译就是可行的。
实际上,王路教授对于词语和含义的区分有清楚的认识,只不过他从这个认识推出的翻译方法跟我上面提到的翻译方法恰好是相悖的。按照我前面的意思,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含义的转译,而不仅仅是语词的置换,因而采用什么译名取决于译名原有的含义,而且我们可以用不同译名来传达原语言中同一词语的不同含义,也可以用同一译名来译原语言中不同词语的同一含义。但是,王路教授似乎主张另一种翻译原则,即翻译首先是语词符号的置换,而译名的含义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通过解释来“赋予”的。他说,我们要“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18)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37-338页。,“是”和being只是一个语词,是“语言形式”,它区别于“它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只是用“是”这个语言形式来替换西方语言的being这个语言形式,可以暂不涉及being所表达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王路教授的终极理由了。他主张在所有语境中都用“是”翻译being,实质上是就“语言形式”而言的,不是就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思而言的。说白了,being是一种语言的符号,“是”是另一种语言的符号,我们可以用“是”这个符号来替代being这个符号,至于being和“是”这些符号“指什么”、表达什么意思,“那是可以讨论的”。按照他的意思,我们用这些符号来指什么,似乎并不取决于这些符号自身,而是取决于我们怎么解释它们。他反问:“为什么用同一个词(引者补:‘是’)翻译了being之后,就不能做出多义的理解呢?”(19)同上,第338页。所以,王路教授的观点是,一方面“S is”句型中的is应当翻译为“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S是”解释为“S存在”。这里,王路教授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解释而赋予了中文“是”以存在含义,即中文“是”除了系词含义之外还可以表示“存在”。王路教授认同表述P——“being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而且认为表述P不能转换为表述B——“‘存在’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但是P可以转换为表述A——“‘是’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另一种表示存在”。(20)同上,第278页。对此我要说,王路教授的这个观点已经突破了把to be和“是”仅仅理解为系词的狭隘观点,他实际上承认了to be具有存在含义,只不过“一词一译”的原则阻止他采用“存在”译法来补充“是”译法,从而使他转去寻求对中文“是”的含义进行改造或扩充。正是在后面这点上,“一是到底论”的反对者会有不同的主张,即“是”这个中文词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如果它的“非系词用法”或“存在用法”还没有得到我们这个语言共同体的广泛接受,那么像“上帝是”这样的句子对于说汉语的普通人就几乎无法理解,因此,“存在”译法即使不是普遍成立的,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而“一词一译”的原则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三、形而上学的含义和西方哲学的“一脉相承”问题
王路教授主张“一是到底论”显然不仅仅是关心一个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其背后实际有某种哲学观在起作用,它涉及如何理解哲学这门学问的性质。按照他的观点,我们需要在语言和逻辑维度上来讨论有关的西方哲学问题,抛开这个维度将妨碍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精髓。(21)同上,第7-9页。如果我们用中文“是”而非“存在”来理解和翻译西方语言的being,就能够发现关于being的讨论直接与“S是P”的句法形式相关、跟逻辑问题相关,从而明白西方哲学家的讨论离不开语言和逻辑方面的考虑,离不开关于判断的肯定和否定的考虑,离不开关于真假的考虑。如果我们仅仅用“存在”来翻译和理解being,那么我们很可能完全错失西方哲学家在语言和逻辑方面的考虑。他还说:“西方哲学中有关‘是’的研究乃是一种最宽泛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研究,即与人们的认识相关的研究。这也充分显示出哲学研究的特征,或者说,这就是形而上学,它充分显示出形而上学的特征。”(22)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48页。他认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没有实质性区别,“形而上学乃是关于人的认识的研究”(23)同上,第370页。。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研究人的认识,而人的认识由语言表达,由句子表达,这样关于句子的意义及其真假的研究(即逻辑研究)也就是关于人的认识的研究(认识论),从而也就是形而上学研究。(24)同上,第370-371页。
我认为,一方面,王路教授强调being的系词用法、重视句法问题、强调需要在语言和逻辑维度上来讨论有关问题,这些的确非常重要,缺了这个维度可能就没法准确理解很多哲学家的思想;另一方面,语言和逻辑维度的问题只是复杂的being问题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全部,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完全混同起来谈论也是不合适的。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里似乎试图以逻辑学的名义构造一套形而上学体系,但他的“逻辑学”在什么意义上可算是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学,仍是可疑的。通常所谓逻辑学研究的是有效推理的条件或者正确推论的结构和原则,而黑格尔所谓“逻辑学”谈论的却是“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范畴被另一个范畴所包含,并由此发展为它的对立面”(25)[英]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而且这种思想过程被认为是世界中现实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本质结构。通常所谓形而上学,“指对实在的最基本的成分或特性的研究(ontology),或者对我们在说明实在时所用的最基本概念的研究”(26)同上,第614页。。形而上学的目标在于讨论实在或世界的本质结构或基本构成方式,它要讨论什么东西存在、存在的东西如何存在(按照“是派”的译法:什么东西是,是的东西如何是),等等。这里的“是/存在”与语言和逻辑问题相关,但不完全是语言和逻辑问题。
逻辑学家关心“S is P”中的is,因为它似乎是句子中的逻辑常项。这个is经过名词化处理,被称为being,它指的还是那个作为系词的is。逻辑学家关心的这个is主要与句法和逻辑问题相关,也就是看重is的谓述和断真的功能。但是,哲学家不仅仅关心“S is P”中的is,而且关心作为“that which is”的主项S和谓项P。当某个哲学家谈论being(古希腊语on)时,有时指的是“S is P”中的is,这时他会关心句法和逻辑问题(从而表现为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思考者);有时他用being指的实际上是S和P,这时他关心的不是那个is,而是“that which is”(古希腊语to on)或者复数的“those which are”(古希腊语ta onta)。西方哲学中的ontology字面上就是关于on(复数onta)的理论,也就是关于“that which is”(复数those which are)的理论,用德文来说就是关于das Seiende(复数die Seienden)的理论,因而是关于“诸事物”的理论,而不单纯是系词理论或逻辑学理论。逻辑学特别关注“是”和“S是P”这样的句子结构,而形而上学关注的实际上是万事万物(尤其是它们的根本结构或原理),只不过古希腊人恰好用“诸是者”(ta onta)来统称万事万物,所以他们的形而上学大致等同于“是者论”(ontology)。西方形而上学会跟逻辑学密切相关,确实从“是者”和“是”的密切相关可以看出端倪。中国古代也有研究万事万物之根本结构或原理的学问,也可以算是某种形而上学,但它不能被说成是ontology,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从“是”和“是者”出发来讨论形而上学问题。
柏拉图在讨论to on(是者,实在)时,常常把它跟持存性、自身同一性、真实性关联在一起,从而把它跟生成变化的东西、假象、虚假的东西相对置,而to on之所以有这些方面的含义,与动词einai的词源含义“自身维持自身”是密切相关的。古希腊形而上学主要不是探讨事实和命题之真(这主要是逻辑学的任务),而是讨论实在和事物之真。真实的事物首先就是自身维持自身的、具有自身同一性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被视为真正知识的对象,无论柏拉图的理念(idea,eidos)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ousia)都是这样的东西,它也是狭义的“是者”(to on)。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中,最广义的“是者”指一切,它可以包括作为实体的“苏格拉底”“马”、作为性质的“白”“甜”、作为数量的“三尺”“五升”等,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范畴。这些范畴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就是实在之最基本成分。在这种作为范畴论的“是者论”视野中,系词所表示的某些逻辑关系(例如等同、从属)本身也属于一类范畴,即“关系”范畴,从而也可以被当作某个“是者”。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代哲学家分享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即世界是“诸事物”(诸是者)的总体。当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27)[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页。,这显然超越了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因为这样一来,事实和命题之类而不是实体和属性之类成为哲学探讨的关键话题。这样,似乎更重要的是句子和由句子所表示的东西,而非孤立的词语和词语所表示的东西。
当海德格尔说传统哲学关注“是者/存在者”(das Seiende)而遗忘了“是/存在”(das Sein)本身,他的意思不是说传统哲学关注“是者/存在者”而遗忘了语言层面上的系词,而是说传统哲学关注名词化了的das Seiende(作为在场者的“是者/存在者”),关注对象化了的“事物”,而遗忘了作为动词本身的Sein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即某种特殊的活动,也就是自身在场、自身出现、“自身从自身中站出来并维持站立”;这种活动尤其指生命活动,即“生存”(die Existenz),而且最根本的是当下活着的自我的生存,这就是“此在之存在”(das Sein des Daseins)。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传统形而上学作为“是者/存在者/实体”之学根本上是对象化的事物之学,而他要做的工作是转向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或者说一种生命现象学。当我们仅仅从语言层面的系词来理解“das Sein des Daseins”,把它解读为“此是之是”,显然就完全错过了海德格尔所说的意思。如果说“是”只是一个符号,我们首先可以拿它来翻译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然后把它解释为有“生存”的含义,那么这种说法固然突破了系词理解的弊病,也会遇到上面提及的那种尴尬,即普通的汉语言说者并不把中文“是”理解为“生存”或“存在”之类的意思。按照一是到底的翻译方式造就的许多术语(例如此是、“在-世界-中-是”“有罪欠是”“恶是”“向死而是”“能整体是”等(28)这些译法见于熊林(溥林)翻译的海德格尔《是与时》,未出版电子稿。熊林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贯彻了一是到底论,尽管他似乎没有像王路这样从理论上为一是到底论提供辩护。另外,从他使用“是着”来翻译古希腊语分词on这点可以看出,他自觉从动词来理解“是”,而非把“是”视为只具有句法功能的系词。),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妨碍就很难说了。
此外,王路教授在《一“是”到底论》中试图分别讨论从古至今的多位西方哲学家关于being的论述,而且他不认为这些哲学家关于being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或者说,他不认为关于being的理解在哲学发展史上发生过重大的断裂。他说:“与being相关,语境论展现的乃是一种断裂的历史。别的不说,人们看不到从‘是’到‘有’到‘存在’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充其量是解释出来的,因为至少字面上是没有的。一是到底论展现的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29)王路:《一“是”到底论》,第339页。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如果西方哲学的历史本身具有断裂的情况,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维持“一脉相承”的假定,而不如实呈现这种断裂呢?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由于使用了一贯的术语(to on、das Sein),就必定是“相承”大于“断裂”吗?通过一是到底的译法从“字面上”呈现出来的一致性是否可能只是非常表面的一致性,反而掩盖了它们实质上的差异和断裂?为什么我们不能说,being概念本身具有内在张力和丰富性,不同时代或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实际上只是各自强调了其中某些方面或某些维度?这点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四、结 语
汉语学界的学人遭遇到的直接问题是,在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中出现的being(to on,das Sein)这个词及其派生术语,如ousia、ontology、essence、Dasein、Sosein等。但是这个问题立即被转换为:我们应该用哪个汉语词来翻译being及其派生词?这个转换蕴含了某些或明或暗的预设,而这些预设可能改变了原有的问题。这些预设可能有:(A)being在汉语中是可译的,即有某个汉语词能够充当being的译名;(B)只有一个汉语词(最)能够充当being的译名;(C)being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我认为,预设(A)是可疑的,而且预设(B)和(C)是更加可疑的。王路教授的“一是到底论”基本上不谈论跨文化理解和翻译的可能性问题,而是默认它是可能的。“存在派”或“语境派”中有些人对跨语言的思想转换的可能性也缺乏反思,不过也有些人对此有很自觉的意识。“是派”与“存在派”(或“语境派”)之间的分歧不是最根本的,因为它们共同预设了being的中文翻译是可能的。最大的分歧是“可译派”和“不可译派”之间的分歧,承认还是不承认being的不可译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我总体上同情不可译派的立场。在《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的“后记”中我表达过这个观点,即to be在西方语言中承担了多种不同角色或功能,而汉语词汇中没有一个词能够同时担当这些不同的功能。
……西方语言中to be这一个词同时担当了多种不同的角色,而汉语中没有单独的一个词能够同时担当这些角色,于是,我们只能让“是”担当一部分角色,让“存在”担当一部分角色,让其他语词担当一部分角色。但是,“部分”不能取代“整体”,当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表示整体的、尚未区分的to be的时候,在汉语词汇里就无法找到了。有些人认为自己找到了,但实际经不起推敲。我们可以“解释”它,如我在本书里尝试的那样,但是我们无法简单地“翻译”它。(30)詹文杰:《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第291页。
同样在这篇“后记”中,我还表达了一个观点:我们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异质性”有一种自觉,对跨文化翻译和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有一种反省,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哲学的所有问题都一定是汉语哲学的问题,西方哲学的所有概念一定能够在现成的汉语哲学中找到严格对应的概念。“‘to be’和‘being’属于‘希腊-西方’的语言,不属于传统汉语;它们蕴含的思想方式是‘希腊-西方’的,不是传统汉语的;这些语词引起的哲学难题本来只属于‘希腊人-西方人’,而不属于传统汉语言说者……‘to be’与‘是’和‘有’有相通的地方,但不能等同;‘not to be’与‘非’、‘无’也有相通的地方,也不能等同。”(31)同上,第291-292页。然而,有些人对汉语可以翻译being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他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使用“是”“有”或“存在”之类的中文词,而且认为这些词是完全恰当的,能够充分传达西文的being。不管在具体翻译作品中我本人是如何处理being及其相关词的,在理论上我同情不可译论,即认为being作为哲学概念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现成语词可以直接对译,而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得不译”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且都是不完美的。在翻译实践上,我赞成依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容许在不同语境(尤其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写作者的著作)使用不同的译法,并且认为应当尽可能在给出特定译法的同时说明该译法的局限性,提醒读者being还有别的用法或含义。让我用“和合本”《新约·约翰福音》的开头作为最后的例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en archē ēnho logos, kai ho logos ēnpros ton theon, kai theos ēnho logos),这里的“有”“在”和“是”乃是对同一个希腊语词ēn(相当于英文was)的翻译,而且这种译法看起来很合适,至于汉语读者根本看不出来原文是同一个词,那就只能依靠翻译者给予提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