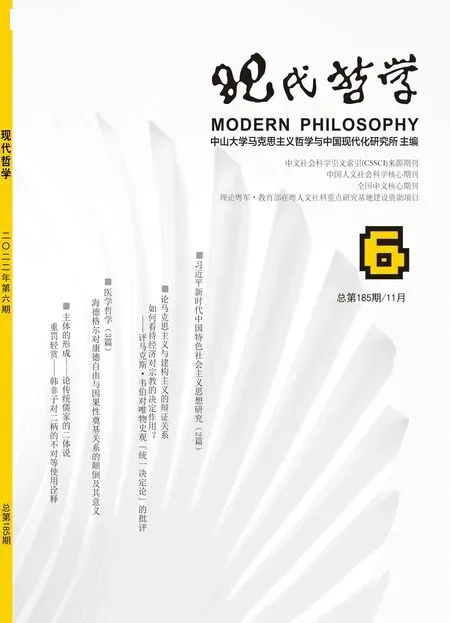论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辩证关系
包大为
在当代的哲学讨论中,不乏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或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但是,在学界大谈特谈建构的同时,深究建构之内涵与思想史源流者却寥寥。事实上,从培根到康德,是建构之为哲学方法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哲学史,也是一部既为了人之自由,又向着确定知识的哲学史。自由意味着主体之于自然与他者的能动与自觉,确定知识则意味着主体能以自身之故通达对象。在一般的哲学史见解中,康德哲学是建构之完成,其“哥白尼式的革命”使得知识的可靠来源不再是表象而是对象,进而在可感且可知的知识范围内使得批判哲学成为一种可能。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后世思想史中基于建构的批判哲学必然是康德主义的呢?是否存在其他界定科学的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建构方法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历史的解答,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得到了实践的解答。
一、由建构而批判
康德的建构,不论其成果还是其方法,都对后世哲学影响至深。康德哲学所确立的不仅是形而上学的合法形式,更是思考道德实践之有限性与规范性的必要准则。在这个被后世命名为建构主义的思想史进路中,人们似乎看到解决困扰近代哲学的两类矛盾的希望,即笛卡尔以来的反思的主体与世界的矛盾,以及弗朗西斯·培根以来的经验的主体与理性的矛盾。通过重新界定主体与客体之关系,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为知识找到了兼具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基础,既使得曾经因理性之绝对而独断的理性主义的“狂妄”黯然,也使得曾经因经验之实在而满足于特殊与感性的“肤浅”赧然。主体不再是因理性而与感知对象“为敌”的圣物,而是在直观形式下能够建构——因而认识对象的能动者。
康德的建构克服了旧形而上学的模糊、独断和潜在神秘主义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在一些后世的粗心读者那里时常被加诸于康德),在形式上完成了近代哲学趋向于科学的建构主义冲动。在前建构主义的哲学中,认识即是表象(represent)的过程,但是关于表象本身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却是不可能的,不论是身心二元的理性主义或更早的唯理论都无法论证知识的普遍必然的基础,也无法使得主观世界与具体客观世界相恰。霍布斯和维科以降,未被命名为建构主义的建构的意图开始显现,知识的对象开始逐渐取代理性的或经验的表象。夏甄陶认为,近代哲学在注意到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片面性之后,康德率先试图把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并试图区分认知过程中的两类判断:一是区分了不依赖于经验而具有真实严格的普遍必然性的先天判断和依赖于经验而不具有严格普遍必然性的后天判断,二是区分了不能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的分析判断和能提供关于事物的知识的综合判断。这一区分使得先天的分析判断和后天的综合判断成为唯一可能的知识来源,也就是“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唯有通过概念,或是通过直观;但这两者本身要么是先天地、要么是后天地被给予出来的”(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先天综合判断所构成的认识论前所未有地指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的过程是从感性直观形式提供经验开始,然后把杂多的经验归属于判断中的概念,即用先天的知性概念(范畴)对经验进行综合,达到先天综合知识。(2)夏甄陶:《认识论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康德的建构主义最为直接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出形而上学乃至道德科学化的路径,即批判的方法。为了引导读者在思辨和实践中能正确运用纯粹理性,康德试图将作为“消极”方法的建构跃向批判的方法。在这一方法之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未来与批判哲学的前景是一致的。从建构始,以批判终。建构使得形而上学被简化为基于纯粹理性的知识。当这种知识作为“在一切纯粹先天知识方面检查理性的能力的一种入门(预习)”,将构成批判的哲学;相反,当其作为“纯粹理性的(科学的)系统”,成为“出自纯粹理性并系统关联起来的全部(真实的和虚假的)哲学知识”,则将构成形而上学。(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84页。结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独断论之为“专制者”和怀疑论之为“游牧民族”的隐喻,不难看出康德的建构的最终意图不是缔造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将批判——这一“自救”的方法提供给现代形而上学。因为到了启蒙时代,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不经论证和实验的知识都将遭受科学的“最终审判”。纯粹理性批判所呈现出来的批判方法是一般且普遍必然的,正如建构方法所阐明的人类认知结构是一般的,“不是对某些书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4)同上,第3页。。故而康德的由建构而至批判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方法论之学,也正因为如此,其关于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先验条件能够与实践理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上帝、道德、自由等“非法”的科学思维对象的辨识和排斥,成为论证几何学方法的必要环节和现实目的。
由于其一般性,作为方法论之学的康德建构主义得以在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发挥着奠基性的影响。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论证了我们将自然的基本法则施加于显象这种做法至少在实在的一个更深层次上为自由保留了可能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补充说我们对于实行道德法则要求的义务的意识在更深的层次上,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根本的自由的可能性而且还意味着它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在于先天的分析判断和后天的综合判断分别赋予了人类认知以普遍必然性与客观实在性,而这种被命名为科学的知识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主体或者道德实体,进而使得自主或自律(autonomy)成为道德哲学之核心概念成为可能。基于建构主义的一般方法和批判结果,康德将自主性视为基本的道德价值,为自由的实践原则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同时又确立了理性——而非欲望在这个空间中的支配地位。(5)[美]保罗·盖耶尔:《康德》,宫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由科学知识之自主性到实践理性之自由结果,康德的建构主义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这在启蒙运动中以哲学与宗教为革命主题的普鲁士尤为明显。在为《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初次辩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打算直接从“先验哲学”进入到他的“形而上学”的修正形式,将在前者中所获得的经验的先天综合的原则应用到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最为基本的概念中去,其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拒绝在知识的领域为信仰留下地盘。(6)[美]保罗·盖耶尔:《康德》,第37页。赖尔(Peter Hanns Reill)就直言,康德以其方法论的自信,拒绝成为上帝的羊群,甚至早在1763年的《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Der einzige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一文中就已经试图调和莱布尼茨和牛顿之间——而不是教派之间的关于上帝本质的争论,以其颇为熟悉的当时的力学原理力求改造出一种具有物理学形式的神学。(7)Peter Hanns Reill, Vitalizing Na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160.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费希特就认为,康德哲学证明了“作为经验基础的独立不倚的非我或自然界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没有一个部分完全等同于另一部分”,以至于不论是人还是其它理性生物都是完全平等的成员。(8)[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页。
然而,康德所期许的一般的方法论之学的依据却面临着普遍性的匮乏。回顾近代以来欧陆哲学史,不难发现康德的建构主义最为核心的批判对象是唯理论,而不是经验主义或者怀疑论。构成康德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要素事实上几乎完全被以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为主要工具的唯理论哲学所占据。在所有批判唯理论及其独断认识论的过程中,康德最为自信的论据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正如李泽厚指出:“康德精通当时的自然科学,对于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并不怀疑。康德相信欧几里德几何和牛顿力学能适用于一切经验对象,即普遍必然地客观有效。欧几里德几何和牛顿力学当然都是一种’综合判断’,即依靠感性经验提供材料的,但它们又偏偏具有无往而不适用的普遍必然性。”(9)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页。因此,先天综合判断的起点无疑是自然科学之有效性,其目的则又是回到自然科学,其所依靠的却是在科学之外论证认识论结构的有效性。这就使得康德不断地将哲学的普遍必然性与自然科学已然呈现的有效知识形式嫁接起来。比如,“康德非常重视数学,认为只有数学在其中,自然科学才成其为科学,因为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它构成了所谓纯粹的要素以作为基础。康德甚至认为,如果化学还不能把分子运动计算和表现在空间(数学)里,就不能成为科学。至于自然科学本质,康德认为其中也包含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基础……”(10)同上,第68页。然而,问题在于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依赖知识的有效形式,而是同时依赖经验所提供的感性直观,但是康德对于感性直观本身并不信任。康德所承认的经验仅在于为纯粹的直观形式提供客观实在性:“即使是空间和时间,尽管这些概念摆脱一切经验性的东西而如此纯粹,尽管它们如此肯定地在内心中完全先天地被表现出来,但如果它们没有被指明在经验对象上的必然运用,它们就毕竟是没有客观效力、没有意义和所指的……经验的可能性就是赋予我们的一切先天知识以客观实在性的东西。”(1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15页。在康德建构知识的有效形式和批判的一般方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所真正面对的经验(Erfahrung)事实上被替换成哲学的“经验的”(empirisch);弗朗西斯·培根以来所确立的从经验之实验入手的分析判断被视为同义反复。(12)康德认为:“经验判断就其本身而言全都是综合的。若把一个分析判断建立于经验基础上则是荒谬的,因为我可以完全不超出我的概念之外去构想分析判断,因而为此不需要有经验的任何证据。说一个物体是有广延的,这是一个先天确定的命题,而不是什么经验判断。因为在我去经验之前,我已经在这个概念中有了作出这个判断的一切条件,我只是从该概念中按照矛盾律抽出这一谓词,并借此同时就能意识到这个判断的必然性,它是经验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7页。)康德真正信任的事实上仍然是思辨形而上学,这正是他与同时期苏格兰启蒙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休谟对思辨形而上学的辛辣嘲讽尽管启发了康德,但是后者并不打算追随前者彻底摈弃思辨形而上学,而是以自然科学之论据对形而上学进行积极的重构。当自然科学以及由其推动的客观世界逐渐超出了建构主义所规定的范畴,针对批判的批判,或者对建构的建构也就成为思想史的必然。
二、来自思辨的不满
李泽厚认为,黑格尔展示的是人类主体性的客观现实斗争,而康德抓住的则是人类主体性的主观心理建构。后者在20世纪趋向科学范式的研究中似乎产生了许多具有“家族类似”(family similarities)的方向,例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最终把语言机制归结为某种人类普遍具有的先验理性;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最终也把社会民俗结构归结为普遍的“脑”即人所共有的某种普遍的心理深层结构。(1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第57页康德哲学当然无法与科学本身划上等号,但新旧康德主义都试图将建构转述为具体科学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具体科学是以客观世界之运动探寻特定的物质原理,而建构则是以人类意识之范畴探寻所谓的纯粹科学。这种科学事实上是以科学命名的关于科学认识论的讨论,其与具体科学构成了两种通向科学的路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而言,客观主义的一些特征或许并不陌生。客观主义认为知识不是来自于主观的心理或范畴,而是源自生产的社会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对事实的建构,而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客观世界。如果说作为主观主义的纯粹科学的建构所要提供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知识,那么客观主义所追求的则是客观世界之本真样态的说明,而“科学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命题就是用来提供这些原原本本的描述”(14)[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页。这种无疑外在于具体科学的关于科学认识的定义不尽然是康德的本义,而是新康德主义影响下心理主义与心理科学杂糅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康德的建构通常被理解为拒绝本体论的(例如“物自体”概念)纯粹的认识论传统。这个传统在后世使得费希特的唯我或谢林的同一都成为了在纯粹的主观性中寻找客观性的哲学,并且最终在黑格尔由精神而至历史与自然的逻辑学中完成并且扬弃了自身。
黑格尔对康德的建构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最为系统的。这一方面由于建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由于黑格尔所要完成的不是摒弃建构所代表的理念论传统,而是要为这个传统的现代完成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先刚所指出:谢林所说的“否定哲学”是包括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在内的“纯粹唯理论”(Reinrationalismus)传统,即把“理性”“思维”“逻辑”等当作最高本原,并从理性出发解释一切存在者,把一切存在者(包括理性和思维本身)都理解为通过思维而建构出来的东西,而黑格尔哲学是“否定哲学”的最高代表——他一方面把“否定哲学”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却企图把“肯定哲学”的内容包揽在自身之内,使自身同时成为“肯定哲学”。(15)先刚:《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 以及黑格尔的可能回应》,《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4 期康德试图以人类建构对象的过程呈现出知识的普遍客观的基础,但这在黑格尔看来是虚假与残缺的普遍客观性,具体而言体现为三个问题。
一是从结果来看,建构的知性是无思辨的。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只是一种显白学说(die exoterische Lehre),其所主张的“知性不可以超越经验”,使得超越经验的认知能力所产生的只能是“脑中幻象的理论理性”。黑格尔并不反对知性与经验的关系,而是反对因经验有限之故束缚了理性之潜力,尤其反对康德的建构主义“从科学方面为那种放弃思辨思维的做法作出了论证”(16)《黑格尔著作集5:逻辑学I》,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丢失了思辨思维之后的后果是颇为直接的,即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的“辩证阐述”实际上完全扼杀了辩证性。作为普遍理念的“假象的客观性和矛盾的必然性”将自在之物规定为理性不可思维的对象,进而就把客观普遍性连同假象的客观性推到了理性之外的领域。但事实上思维和自在之物的矛盾关系不仅体现为理性的内在否定,更体现为理性思维原则本身就已经“兼顾到自在存在着的东西”。因此,将理性与知性、思维与自在之物对立起来的建构主义,只是“停留于辩证因素的抽象的——否定的方面”,进而迫使理性承认自身无法认识无限者。(17)同上,第34页。既然无限者是合乎理性的东西,即先天的可以提供范畴的东西,那么无法认识无限者就是悖论性的,因为理性是从“有条件的东西”出发去把握无限者的能力。黑格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建构主义代表了没有经历训练、不自由的思维能力,正因其无法摆脱感性的、具体的表象活动和推理活动,故而只能牢牢抓住各个概念的规定性来进行认识和自我训练——而真正的辩证思维是在主客观的统一之中把握矛盾,以及在否定性中把握肯定性。
二是从原则来看,建构的逻辑是陈旧且无生命的。在黑格尔看来,形式逻辑是“各种规定和命题的汇编”,其“幸运”之处在于“它遥遥领先于其他科学,老早就达到了完满”。相比之下,康德的先验逻辑是否实现了逻辑的彻底改造呢?黑格尔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先验逻辑之于形式逻辑,其创新之处“只是把一些东西省略掉而已”(18)《黑格尔著作集5:逻辑学I》,第29页。。虽然按照一般的理解,形式逻辑的普遍性在于形式本身,而先验逻辑更多地与内容之真假有关;先验逻辑将自身进行了认识论的改造,使得本体、认知和表象等成为逻辑的新主题,进而使得经由逻辑检验的综合判断能够拓展新的知识。黑格尔认为先验逻辑所关涉的形式之下的内容本身仍然是形式的,即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都受制于某种先天的形式。他甚至直接指出康德并没有扬弃形式逻辑,而是“出于一种本能重新发现了三段式,并且将这种尚且处于僵死状态的、尚未概念化的三段式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意义,使得真实形式伴随着它的真实内容同时建立起来,随之得出了科学这一概念”(19)《黑格尔著作集3: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页。。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以没有生命力的范式、不折不扣的线条轮廓取代了三段式,进而“把一个科学的有机组织降格为一张图表”。这使得“按图索骥”的简单推论和判断能够上升为所谓的“科学”,亦即“只要把范式的某个规定作为一个谓词陈述出来,就已经把握并说出了一个形态的本性和生命”。(20)同上,第31页。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主义的坏处在于无法提供新的可靠的知识,那么先验逻辑的形式主义的坏处则在于假装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知识,但事实上仍然浮于感性和想象。
三是从论证来看,建构的科学性是外在且片面的。黑格尔并不认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所依赖的并不是与具体的、生动的世界同行的真知,而是在这个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凭借这种形式声称实现知识革命的康德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就如同只会死记硬背和应试考试却不会举一反三和创新思维的教条。康德以数学作为普遍性的尺度来评判科学,而黑格尔讽刺道:“就数学的真理而言,我们更不会把那样一个人看作几何学家,他熟记欧几里德定理,却不知道其证明,借助于一个对比来说就是,他仅仅外在地,而不是内在地知道这些定理。”(21)同上,第26页。黑格尔指出,建构主义的核心是运用“外在的、空洞的公式”,无法触及内在生命或实存的自身运动,只是道出了感性知识中关于直观的单纯规定性。即使就康德哲学中格调不高的感性知识而言,建构所做的也只是把捏在一起的“静止的感性事物”当作了概念,“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即将感性表象的概念或意义陈述出来,却被省略了”。这是事实并没有认真地探寻知识的真理性,而是越过真理性,直接以形式与范畴来对知识的本质进行规定。黑格尔不提倡将事物的形式与质料分离,更反对将运动的事物作为静态的标本进行切割并装入贴着标签的“密封罐”。他认为在康德范畴表里,“事物的活生生的本质同样也被剥离或者掩盖了”,而建构不过是“一种单调的绝对绘画术……沉沦在绝对者的空洞性之中,以便制造出一种纯粹的同一性,制造出一种没有形式的白色。一方是范式及其僵死规定的单调同色,一方是绝对同一性,尽管双方相互之间也有着过渡,但都是同样一个僵死的知性,都是同样一种外在的认识活动……科学只能通过概念之固有的生命而形成为一个有机体。在科学里,范式把一个外在的规定性黏附在实存身上,而这个规定性就是一个已然得到充实的内容所具有的灵魂,它自己推动着自己”(22)同上,第32-33页。。
但是,黑格尔本身是否仍然行进在继续建构的道路上呢?如果以康德最初的理论意图的“元建构”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黑格尔在表面上将作为精神外化之历史作为客观性的来源,进而论证知识通达客体与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黑格尔的意图是将斯宾诺莎的实体哲学和康德的主体哲学统一起来,以此来补充排斥实体的费希特、莱因霍尔德以及笃信理智直观的谢林。尤其在黑格尔的时代,建构的意义更多地已经从康德哲学转移到了谢林哲学,后者的哲学建构(或作为科学的哲学)试图在先天的理智直观中呈现特殊的客观世界,进而呈现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的统一。而黑格尔最焦虑的问题在于:行进到近代历史的人类文明业已呈现的人类思维之精深、伟力与变动不居的活力,已经迫使一切先天的理智直观或者范畴向精神外化出来的万千世界屈服。继续建构当然仍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因为非如此,就无法以人的视角来理解世界。但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精神经过两千多年的持续劳作之后,对于自己的思维,对于其自身内的纯粹本质性,必定已经具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实践世界、宗教世界、科学世界的精神已经在每一种实在意识和观念意识中以各种形态崛起,如果人们把这些形态和逻辑———这是精神对于自己的纯粹本质的意识——置身其中的形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如此巨大的落差(尽管那种最肤浅的观察还不会立即注意到这一点),即当前的逻辑根本就不适合、也配不上精神在那些领域里面取得的各种成就。”(23)《黑格尔著作集5:逻辑学I》,第29页。
三、历史的真理与建构的真正扬弃
如果说建构主义之立论基础的问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部分地暴露出来,那么建构主义的现实困境则更为直接地体现为受到其影响的政治哲学。如上文所述,康德为知识“立心”的伦理意图是为主体“立命”,亦即以知性的真实主体维度来推演出实践主体的应然价值,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自主与自由。故而在近代政治哲学史中,康德的建构主义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从先天之客观与经验之普遍的批判视角出发,康德既摈弃了唯意志论与形而上学的应然尺度,将存在却不合理的“任性”“为所欲为”驱逐出现代价值规范,也否定了合理却无效的旧道德形而上学,提出人类能够且应当以主体先验的道德能力来制定法和秩序,最终实现看似由人法主导、实则客观必然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如同卢梭所畅想的理想城邦,合乎理性的法已经替代了过去一切自然法与非法,为人类社会塑造出了一个新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如同自然属性那般,如同主体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而不是外在强加的枷锁。康德与其所崇拜的卢梭相似,都认为通过道德形式(如理性、自爱)就能够设计出良法善治的价值结构,从而克服现实社会中理性与意志、必然与自由的矛盾。然而,相比于关注现实政治条件与物质基础的卢梭,康德的任务是将形而上学重建为一门包括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科学,其关注的是不受外在条件左右的理性本身,这就使得从康德直至罗尔斯的漫长的建构主义政治哲学中,理性都如同是与经验相矛盾的法庭,只承认或判定其认为能够自主解释的对象,否则就会导致自由的丧失或理性的僭越。桑希尔(Chris Thornhill)认为,“支撑康德道德世界的是经院哲学道德世界的倒置”,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宇宙中假定了一种道德秩序,这种秩序源于上帝的旨意并且在自然法中得到延续,而康德所认可的法律则拒斥了看起来外在于主体的宇宙或自然。(24)Chris Thornhill, Germ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Metaphysics of Law,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04.倒果为因观之,康德所认可的形式的法与道德所隐含的是与客观对立的“普遍者的我”。这在黑格尔看来显然是冒牌的,但那种拒斥感性经验的确定性而只接受形式的确定性的“科学”同样如此。黑格尔认为,“如果有人要求科学推衍出、建构起、先天地发现(或者随便换什么说法)所谓的这一个物或这一个人,并把这当作科学的试金石,那么这是科学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建构主义所不承认的感性确定性实际上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他者之间辩证且真实的关系,感性确定性经验到“它的本质既不是在对象里面,也不是在我之内,同样,直接性既不是对象的直接性,也不是我的直接性。因为就本质和直接性而言,我所意谓的毋宁是一种无关本质的东西,而且对象和我都是普遍者”(25)《黑格尔著作集3:精神现象学》,第65页。。与之相反,仅与自身相关的自主或自由的价值规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最高的、与普遍自由最为对立的现实性,或更确切地说,普遍自由将要面对的唯一对象,是一个现实的自我意识本身的自由和个别性……普遍自由的唯一事业和唯一行为是死亡,一种没有任何内容和意义的死亡。任何被否定的东西,都是那个绝对自由的自主体的一个未得到充实的点。”(26)《黑格尔著作集3:精神现象学》,第364-365页。
当然,建构主义所缺乏的真实的普遍性,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中也没有真正涌现,因为黑格尔止步于将否定性的哲学进行肯定性的转述。对黑格尔关于建构主义的批判“接着讲”的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与建构似乎又是脱不开干系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建构或批判的方法对建构主义传统的发展。在宏观层面,朱利安·阿加(Jolyon Agar)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吸纳了黑格尔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与活跃的唯心主义相剥离,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哲学站在康德哲学之上,克服了纯粹的主观性,其辩证的现实主义(dialectical realism)所受到的是潜在的本体论唯心主义的推动,为科学探究和现象学经验提供主题的物质世界在本质上被视为观念的外化(externalisation)。(27)Jolyon Agar, Rethinking Marxism: From Kant and Hegel to Marx and Engel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60.盖瑞斯·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则认为马克思在1844 年的创新是将唯心主义的洞见应用于对劳动的理解,一方面讨论“社会问题”和无产阶级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提出与《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相一致的改变世界的意义——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与人类的自我活动联系起来,而这种活动肇始于康德完成的哲学革命。(28)Gareth Stedman Jones,“History and Nature in Karl Marx: Marx’s Debt to German Idealism”,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2017 Issue 83, pp.98-117.更具体来看,误解主要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戏仿了康德的科学形式。例如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还原论的阶级斗争概念,得出革命实践中互斥的两种主体形式——群众与阶级,以“戏仿康德”(parody Kant)的路径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是空洞的;没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是盲目的——只不过这两种主体形式之间没有普遍且先天的范畴将其联系起来。(29)Etienne Balibar,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trans.by James Swen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171.而更为典型的则是恩格斯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恩格斯所使用的形容词认识论(erkenntnistheoretisch)正是新康德主义者用来限定知识问题的词,与之相似的还有《反杜林论》中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而不是Anschauung der Welt。尽管恩格斯试图反驳科学形式的唯心主义,但是却似乎与康德“殊途同归”地诉诸主体发现客观规律的认识论或实践论,甚至为将“进化规律”(抑或发展规律)增添为主体建构对象与知识的新内容,巴里巴尔认为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显然比康德更亚里士多德”(30)Ibid., pp.107-108.。同样的问题还出现于对《资本论》的解读。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认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经过交换中介的事物化和颠倒(Verkehrung)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是对生产关系中完成的形式的再现,只不过在意识形态中这种再现的表象(Erscheinung)成为幻象(Schein)。为了说明这一过程,马克思将这种幻象类比为康德的先验幻象,并且经常谈及“错误和混乱”。当然,比岱并没有偏离太远。他也指出,当马克思回到确定的历史生产方式中,与康德的类比也就随之结束,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将现象范畴与科学范畴等同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不再与心智的普遍结构相关联,而是通过断言其特定的范畴来建立超越现象的真实秩序。(31)Jacques Bidet, Exploring Marx’s Capital: 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trans.by David Fernbach, Leiden: Brill, 2007, pp.212-213.
当然,熟知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读者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的“暧昧关系”实际上并不复杂。只不过像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这样的“半截子”唯物主义者无法接受思想史的事实,只能感叹道:“在积极的方面,马克思接受了唯心主义的精神现象学原理,在费希特、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中,心灵是推动现实向前发展的主观推进剂,理念是将现实带入未来的原初动力;在消极方面,马克思是唯心主义的批评者,因为唯心主义没有正确评估现实本身的推动力。”(32)Norman Levine, Marx’s Rebellion Against Leni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117-118.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最初是何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建构的理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历史——思想史的视角,进而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错觉”(康德、费尔巴哈)或对现象必然性(黑格尔)的批判,从而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独创性,即“通过拷问其行为模式、权力和统治效果来确认各种理想性的原因和必然性”(33)Etienne Balibar, Masses, Classes, Ideas Studie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efore and after Marx, p.92.。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在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中来处理建构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康德认识论的理论基础的评价也是颇为辩证的(或者说矛盾的)。
一方面是对建构的方法及其结论的肯定。在方法论层面,俞吾金认为,“通过深入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但从中剥离出‘实践’概念,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34)俞吾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6页。,即哲学应当不再附着于对象去解释世界,而是应当改变世界。而诺曼·莱文则略显夸张地认为,“尽管马克思认为康德过度关注心灵,但他仍然采用了康德的批判方法。正如马克思必须被视为黑格尔的学生一样,他也是康德批判工具的忠实实践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康德如出一辙,只不过其目标是具有民族主义形式的德国唯心主义,试图为这种仍然特殊的形式找到具体的内容与更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形式。(35)Norman Levine, Marx’s Rebellion Against Leni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118-119.而在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将康德视为近代哲学的分界点,“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至多只能在与简单范畴纠缠之余杂糅一些“自然科学的材料”。(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在结论层面,恩格斯对康德的星云假设给予高度的肯定,认为“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且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62页。。而在1874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更直接地将康德视为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家:“就回到真正思考问题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人们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页。
另一方面则是对建构的历史局限和唯心主义特征的否定。这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密切关系,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的观点的认同。阿维内利(Shlomo Avineri)认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摆脱康德之后困扰德国哲学的“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是因为他熟悉了黑格尔的著作。(39)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这个观点见诸马克思在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坦承:“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有着坚实的基础。”(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年马克思被黑格尔的哲学所吸引,因为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改变现实的(尽管枯燥的)有力的工具。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更直接地指出,黑格尔的伟大成就是用具体的、辩证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术语来看待人类的意识、意志和理性,坚持认为,实践与道德、政治与理想不是先验理性运作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这就需要既承认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又要承认意识、意志和理性在自在之物中的积极作用——而这正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共识。(41)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8, p.97.这个“共识”体现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而蒲鲁东“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的企图只能体现为“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当然,恩格斯对建构出来的科学的批判更为简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总之,历史的路径让马克思主义最初与黑格尔主义成为了批判建构主义的同路人,只不过前者的意图已经超越了对哲学革命之胜果的争夺。在恩格斯看来,工业生产和劳动实践所驱动的社会革命“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7页。。当前之所以仍然有人倾向于以康德的口吻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试图在当代科学与技术进展的加持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建构主义的改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化解读之风尚大行其道。一些人或许难以跟上马克思(更遑论列宁)的步伐,不仅难以超越社会结构所造成的道德形式,而且试图将革命、解放或阶级等活跃的历史要素塑造成不可知的抽象之物,进而塑造出道德和审美的教条。然而,正如费尔巴哈所设计的适用于“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论,这种徒有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标签的道德“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因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4页。,而在当代世界上所生活的是具体的、历史的人——而不仅仅是具有同等先验能力的主体。二是无法认识到历史的建构是一个悖论。生产力、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不是先天的范畴,无产阶级不是建构某种知识或道德的主体,共产主义更不是现实主义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的构想。历史的建构是一种悖论,历史也不应被当作外在于主体的对象。在每一个实践向命运“投降”并且将历史交给命运的低潮时刻,就会出现屈从于阶级社会所强加的各种范畴的“建构”,或者在纯粹思辨的层面滑向客观主义的决定论。而建构历史则更是一种狂妄,脱离具体科学和革命实践的“建构”最终所遭遇的是失败或者假装为成功的失败。历史的发展当然是由矛盾驱动的,但是这个矛盾不是抽象的概念。如果对历史提供的新知识和新矛盾一无所知,只是从自由、解放等范畴出发去推演科学、道德和政治的理想模式,最终只能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1页。的纯粹理性的运动。理性的证成如果只能依靠无知之幕这样的理论假设,那么理性在现实中注定永远无法遭遇其合理的却不可能的条件,犬儒与失败将成为这种理想模型的宿命。政治自由主义者并未料想到理性多元论(rational pluralism)在当代成为了现代身份政治和犬儒主义的理论奥援,然而马克思却早已察觉到了建构通达历史的困境:“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52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建构出来的,在未来也将仍然行进在实践所创造的主客体矛盾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不断问题化与理论化的道路上。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观念欠马克思主义一个新的理想,即具体的自由”,但是有待实现的具体正义、自由和真理要进入现实,显然无法依靠观念,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与斗争实践的密切联系。(48)Henri Lefebvre, Problèmes actuels du marxism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0, pp.14-15.换而言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的结论就已经否定了新旧版本的形式上的科学建构或者实际上的经院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