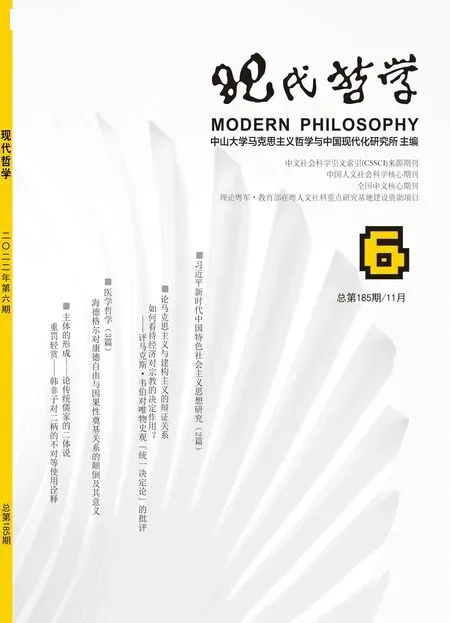黑格尔与马克思
——百年回眸*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著 孙海洋/译
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自19世纪末以降,每个时代似乎都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马克思去世后不久,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联甚少。人们往往承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影响,以及康德的相关性。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则被忽视了。(1)关于康德对马克思影响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这方面的确凿依据可参见H.J.Sandkühler and R.De La Vega(eds.), Marxismus und Eth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直到《巴黎手稿》的发现使人们对青年马克思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显著改变,引领学者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追寻黑格尔思想的踪迹,直至其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们很快认识到,后者的结构也渗透着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深刻影响。(2)一个例子是Herbert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reprinted in Schriften,Vol.1.zu Klampen: Springe, 200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最初集中在异化和物化等主题上,他们彼此理论之间的其他联系也开始被发现。现在,一个核心问题是黑格尔关于精神必然自我异化为自己的他者的观点。这些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遭到了阿尔都塞的坚决反对(3)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New York:Verso, 1969.,他提出了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之间存在“认识论的断裂”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成熟的经济学著作从黑格尔的影响之下彻底解放出来。今天,流行的观点再次走到了它的反面。有人甚至可能会说,这两位思想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一种更加相互影响的方式得到解读。黑格尔的著作不仅像卢卡奇时代那样被视为马克思哲学灵感的来源,而且被视为社会理论的宝库,可以用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的学说。
这种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新评价是由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不太显著的解释上的变化所促成的。例如,查尔斯·泰勒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他的《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一书)使得如下观点对我们来说更加自然,即黑格尔不仅是致力于从总体上理解世界的体系建构者,而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社会理论家。(4)Charles Taylor,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今天被视为诊断现代社会之动力和危机的一种尝试,其中包含了社会分析的萌芽,预见到了这一当时尚未存在的学科之核心观点。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是如何将作为相互承认行为之结果的社会整合概念化的(例如,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5)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Suhrkamp, 1992.,米夏埃尔·宽特的《精神的现实性:黑格尔研究》(6)Michael Quante, Die Wirklichkeit des Geistes. Studien zu Hegel, Berlin :Suhrkamp, 2011, S.231-252.)。与过去的解读相比,这也使得黑格尔理论的社会学维度变得更加清晰。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已经采取了一种审慎的方式,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他们自己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竞争者。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今,甚至有所增强,因为现实情况越来越没有理由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哲学本身的革命性替代,或理解现代性的纯粹解释性路径的替代方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习惯于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从其政治和实践语境中分离开来,并视其如既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种试图理解现代社会之动力和危机的尝试。由于这些不同解释的转变,我们不再假设二者关系存在着彻底的断裂或非连续性。相反,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作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竞争性的分析,因此当我们询问一方可能从另一方那里学到些什么时是有意义的。
我的目标就是从这一稍显不同寻常的视角比较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我的出发点是关于历史哲学的假设,它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现代社会诊断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第二步,我将讨论黑格尔社会理论相比马克思而言的优点所在。第三步,我将反转这一视角,并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优点。最后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可以使这两种方法实现卓有成效的相互补充。
一、共同的历史视界
从当代的视角回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社会分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依赖于关于历史哲学的前提。今天,这些理论共性使我们可以从比较的视角来看待这两位思想家。诚然,许多其他19世纪的社会理论家共享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目标,即揭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量和运动规律。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以及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代表了整个的观念谱系。但是,即便抽象出这三位作者之间的显著差异,黑格尔和马克思依然可以凭借二者为了理解他们时代的社会挑战因而都依赖于一种历史哲学这一事实进一步与他们分隔开来。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共享一个特定的假设,即现代社会是理性在外部世界显现自身这一发展过程的最新阶段。
众所周知,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解释依赖于这样一种历史哲学,它假定历史就是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他指责康德和费希特都未能正确理解理性的本质。尽管两人都承认理性是一切现实的基础,但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理性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能力,而是一种综合一切的实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展开,直至其完全实现自身的潜能。这种本体论假设使黑格尔能够把整个人类历史解释为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精神首先通过自身的自发性活动在自然界中实现自身,然后复归自身并通过自我决定来形塑整个世界,这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7)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Theorie-Werkausgabe, Vol.1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S.32.。今天,这一框架似乎在全部人类历史的背后预设了一种自由不断实现的客观目的论,这对我们而言似乎相当陌生。(8)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能否被解读成世界历史为确保自由的实现而表现出一种“客观的”目的论,目前正在争论之中。许多相关段落也允许一种更为康德式的解释,大意是说,只有从一种致力于理性的哲学观的视角,才能在人类历史上发现这种目的论。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尤为明显。然而,如果没有它,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就无法得到恰当地理解。对他来说,现代的制度和实践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自由意识不断实现之最高阶段的体现,这一阶段标志着每个人真正自主生活的一切前提都得以实现。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漫长且冲突不断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对他来说,现代社会是自由的制度化实现。(9)关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目标,参见Axel Honneth,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Berlin: Suhrkamp, 2010.
尽管马克思并不赞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这一结论,但他从中汲取了自己理解现代社会特定结构的基本要素。出生在黑格尔之后近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不再是一个坚持一切现实都是自我决定的精神之实现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初,他身受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影响,而那种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理性展开过程之产物的观点,对他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10)Karl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Hamburg :Meiner Verlag,1978, S.78-136.对马克思而言,作为人类的我们首先被自然所包围,而且我们必须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同自然保持联系,以便维持自身。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能够使用工具,这使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特殊地位正在于他们通过相互联系彼此的意图进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不可还原的社会阶级的精神活动,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合作的能力。(11)参见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关于这一主题,更一般的论述参见布鲁德尼:《马克思告别哲学的尝试》,陈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五章。——译者注辅之以最近的实证发现,这一基本观点为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人的理论指明了道路(12)Michael Tomasello, 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Mor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3.,他认为合作劳动的确立促使我们人类能够发展出基本的道德形式和多视角思维。
尽管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存在这样的距离,但马克思对人类基于他们的合作能力通过劳动来改造自然的过程的描述,近乎再现了黑格尔关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解释。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学会了通过相互接受彼此的观点来合作使用工具,自然就开始逐渐被我们所形塑,并反映出我们自身的理性决断,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自由领域的逐渐的扩展。(13)参见马克思的名言,“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译者注)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性精神力量,即我们类(species)的合作能力,在结构上与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之特征相似。尽管“理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种人类能力,对黑格尔来说则是一种理解一切的精神特性——但他们都认为理性是一种只有通过在外在于它的事物中实现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东西。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假设使得他确定了理性之自我展开过程的起点,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一起点已然是理性在自然中实现自身的结果。但是,像马克思一样,黑格尔也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精神性力量的劳动,自然的限制逐渐减少,相应地,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由逐渐增加。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马克思始终是黑格尔的门徒,特别是关于他的核心假设:社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构成了“自由意识的进步”。通过合作实践,我们通过在周遭自然界中的劳动,赋予我们自己的精神以客观现实性,这样,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归宿,从而为形成社会规范和制度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核心假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得不将现代社会描述为社会结构历史演变的最高阶段。马克思著作的许多章节表明,他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看作是一个克服自然限制和束缚的过程,这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相对自由的实践中得出了初步的结论。(14)参见《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之“非常革命的作用”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页。——译者注)
然而,就现代社会的自由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其利弊得失的评价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被视为精神的自我异化过程——毕竟有某些不同的构想。马克思将这一过程首先看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增长的支配,即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而黑格尔的构想更为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方式的逐渐转变。对黑格尔来说,克服自然的限制总是会对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规范产生影响,而马克思则将这种克服更为狭义地界定为人类生产力的扩张——广义的理解则包括控制我们的环境和自身动机潜能的方法。这一根本差异表明,尽管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遵循了精神的自我异化模式,但他们对异化过程的实质和特征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不论是关于理性的内容,还是关于理性在历史中实现的机制,他们之间几乎毫无共识可言,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现代社会的成就作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果更密切地关注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特征的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将更容易地认识到黑格尔社会理论相较马克思的优势所在。
黑格尔和马克思似乎都接受了这样的假设,即人类历史是一个逐渐实现自由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因为精神在自然界中实现了自身,然后又复归自身,它力图在社会制度的世界中体现自己的决定,这种决定存在于不受外在限制的自我实现中。因此,精神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表现出来,即它逐渐产生所有社会成员之自由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制度性前提。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种观念论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如下思想,即精神或理性只有通过将自身异化为外在于它的东西,才能实现自身。但是,根据他的自然主义假设,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解释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过程。由此使得他毕生致力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合作潜能将自然界转化为一个反映我们的理性目标,并进而能够满足这些目标的地方,我们作为人类就能够使自由变为历史的现实。
在我看来,不管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有何不同,那都是他们将理性的社会实现置于不同领域这一事实的结果。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置于精神与我们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中,因为精神已经先验地对自然世界发生作用。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将这一过程置于人类理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因为他无法接受一种未经社会实践中介的自然的先验的精神化(a prior spiritualization of nature)。这一差异也可以表述如下: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所引入的发展模式来描述社会的进步,但黑格尔的初衷却是表现精神在自然界中实现的先验过程。这种对黑格尔图式的倾向性接受的结果,或许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忽视了理性活动塑造我们受管制的社会生活之规范秩序的方式。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起点——即,人类合作这一事实——使其致力于社会规范的系统发生,但他对我们类历史(our species history)的重建仍然局限于我们的理性能力如何导致人类对自然支配的扩张。因此,马克思将理性的实现完全等同于我们相对自然界而言日益增加的自由。哈贝马斯所谓的“我们社会交往的内在框架”(15)Jürgen 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70, S.9-48.对自由实现方式的相应的忽视,使得马克思的理论,相较于黑格尔哲学对社会理论的影响而言,稍显逊色。
二、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优点
黑格尔社会理论的第一个优点在于,他的“社会”概念使其能够比马克思更为广泛地考量制度形式的谱系,因为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显然,当黑格尔试图将社会理解为“客观精神”时,对他而言,这势必包含那些人类学着满足仅仅是“自然的”需要的一切社会形式。只有在精神产生了允许人类世代繁衍的制度时,精神才能实现其客观性,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变得自在。当黑格尔谈及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时(16)黑格尔自己对“社会”一词的使用仅限于“需要的体系”,在《法哲学原理》中,他也提到“资产阶级社会”。在亚当·斯密之后,他用这些术语指称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这一近代历史结构。在当下语境中,当我谈及黑格尔的社会概念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尤其表现为“民族精神”),就是说社会分化的过程可以归因为最一般的单元。,他心中所想乃是社会实践的总和,通过文化与规范的共性相互校准,但同时,重要的是,它必须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撇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假设,“客观精神”这一概念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预见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说,社会是被规范地整合起来的诸单元,各种稳定的、制度化的、相互联系的实践在其中发挥着社会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一系列功能。相比之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侧重,使得他接受了一种更为有限的社会概念。“生产关系”这一术语,经常被他用来当作“社会”的同义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自然。但是,不论政治统治还是家庭繁衍,这两个社会活动的领域,都无法仅仅诉诸经济目的来充分理解它们的规范结构。
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在术语选择上不甚充足,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研究时,后者表明只有少数前资本主义社会知道类似的与众不同的独立的经济再生产领域。如果我们相信波兰尼(17)Karl Polanyi, Ökonomie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9, ch.2.和其他经济史学家(马塞尔·莫斯)的话(18)Marcel Mauss,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Norton, 1969.,劳动与交换的经济关系过去曾经如此彻底地嵌入其他社会功能之中,以致于它们既不能被经验为独立的活动,也不能被规范地调节。如果追随马克思将所有社会都理解为“生产关系”,理解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制度化表现,或许会使人有所疑虑。黑格尔的进路在这里则更有说服力:“客观精神”概念仅仅表现了这一事实,即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包括那些致力于不同生命机能的表现,首先是一般规范的表现,从而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尽管这些规范的具体内容以及不同功能领域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人类历史的进步。鉴于最近的哲学进展,这一概念的唯心主义残余——它包括如下观念,即这些规范是被称为“精神”的自我决定的实体之产物——可以被轻而易举的涤除。我们可以像约翰·塞尔和其他社会理论家那样,将“精神性”规范的产生视作相互合作的主体所展开的认知活动。于是,“唯心主义”所剩下的就只有这样一种主张,即社会依赖于其成员就不同功能领域的规范调节所达成的一定的主体间共识。(19)奥斯特里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并从黑格尔式的视角对塞尔进行了批判。(See Sebastian Ostritsch, “Hegel and Searle on the Necessity of Social Reality”, Rivista di Estetica, Vol.57, 2014, pp.205-218.
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进一步比较,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如何思考自由进步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问题,产生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就此而言,这位唯心主义者似乎比其唯物主义后继者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位思想家都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即这一过程应该被视为精神过程的逐渐外化或异化的结果,就是说,精神与某种异于自身的他者相互作用。在黑格尔的理论中,出于体系的原因,这一“他者”包含了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所有制度。另一方面,对马克思而言,精神的“他者”则是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我们可以通过合作能力逐渐控制它们,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而变得自在。
如果我们现在要问这两位哲学家各自对这一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之驱动力的解释,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解释策略稍胜一筹。尽管他认为理性的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受到理性本身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自主的发展,他也需要至少提供一种大致合理的解释,来说明这一人类历史的进步如何被理解为一种世俗的社会事件。在此,他依赖于这样一种启发性的创见,即当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形式不再能够为个人要求——产生于这一生活形式的伦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提供充足的规范性空间时,这种生活形式就终结了。(20)这一解释模式参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索福克勒斯的解释。关于这里的解释,更一般的论述参见A.Särkelä, “Ein Drama in drei Akten.Der Kampf um öffentliche Anerkennung nach Dewey und Hegel”,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Vol.61, 2013.因此,对黑格尔而言,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包含了自我转化的种子,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致使一些群体产生出道德上的希望和期望,而这些希望和期望无法在现存的制度框架内得以恰当地实现。诚然,这一“道德的”解释在社会学上是差强人意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对于这些结构上无法满足的要求以何种方式产生于社会冲突的语境之中一无所知。黑格尔只是在少数地方表明,他将这种冲突视为争取承认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对自由——全新的以及此前未知的自由——的社会实现的渴望与内在地产生这些渴望的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冲突。但这一简短的概述足以表明,黑格尔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他试图为精神在客观制度中的自我实现这一自我驱动过程寻找一种日常的社会补充。在社会学假设的充实下,黑格尔的基本进路得以发展出一种卓有成效的观念,即推动自由实现之历史过程的是为以前被排斥群体的社会融合而斗争。(21)继黑格尔之后,杜威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See J.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3, pp.64-71.)
相比之下,马克思为了说明我们自由的逐步扩展而提出的关于社会机制的阐释看起来不太令人信服。正如许多人——如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22)Cornelius Castoriadis, Gesellschaft als imaginäre Institution. Entwurf ein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84, ch.I.2.——已经观察到的,他的解释方案往往依赖于一种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倾向于掩盖而非阐明他所断言的(人类)对自然的日益掌控与其不断增加的自由之间的联系。这一解释模型的出发点仍然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合作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占有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但是,在解释实现自由的进步动力时,马克思只关心后者,即我们与周遭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用“生产力”这一术语指称我们在任何时候对自然的这一方面的统治,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任其支配的现存自然资源之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和。第二步,马克思认为,我们不断改进和提高合作能力的过程,就蕴含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越往前发展,对自然界予以生产性占有的社会技术能力就越强。马克思解释方案的决定性步骤是第三步。他断言,所有社会的制度结构——他试图将其统统归入“生产关系”这一术语之下——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惯性和刚性特征,以致于任何生产力的提高都会导致这些制度结构对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滞后性调节。因此,马克思解释方案的精髓在于,随着操纵自然的技术能力的内在进步,必然经常地引起社会交往方式的规范性改进。
关于这种模式,一个不甚清晰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在每个阶段都将使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技术进步会增加我们的活动空间,而不是自然的限制,但若由此推出社会自由的自行增长还是相当可疑的。通常情况恰恰相反,改进的技术将会危及先前所获自由的持存。就内在于生产力发展的规范性潜能而言,马克思对自由的逐步实现所作的解释略显乐观。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本身能够将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从社会统治和继承而来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缺陷,于是他在第一种解释方法之外补充了第二种解释方案,至少发展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23)关于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的张力,参见Cornelius Castoriadis, Gesellschaft als imaginäre Institution. Entwurf ein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4, S.52-59.第二种方案认为,推动社会自由实现的动力,不仅是我们技术能力的内生性增长,而且是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自身需求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尤为突出,这一替代方案并未完全独立于第一种解释,因为马克思将不同阶级争取统治地位的利益与特定阶段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施加影响的机会联系起来。正如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开始争取社会统治地位时,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也日渐增强一样,一旦新的工厂体系创造出必要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也会夺权上台。显而易见,关于社会进步的第二种解释,聚焦于阶级斗争的变革力量,仍然未能使社会实践的历史变迁独立发挥作用。相反,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的进步最终来自于受压迫群体为各自经济利益的社会优势而斗争——好像我们有权这样假设,所有前现代社会都已然确立并以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生产领域为中心。因此,马克思的第二种解释方案与黑格尔的方法相比仍然有所差异,后者将社会等同于精神在社会制度中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没有明确阐明,在任何特定社会群体的斗争中,究竟哪种社会包容和承认是有争议的,他只是简单地假设了经济利益的优先性,但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撑。这就强化了先前的看法,即马克思将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还原为单一的“生产关系”范畴是不明智的。
当我们把马克思对现代社会成就的分析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经济还原论的第三个瑕疵。如上所述,这两位思想家都认为,现代社会秩序是理性的自我实现之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高阶段,因为现代社会制度已经大大扩展了个人自由的空间。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对封建和贵族社会秩序的克服,就等于是从继承而来的依赖关系和隶属形式中解放出来,使得现在的人们享有更广泛的个人自决的机会。(24)Frederick Neuhouser, “Marx(und Hegel)zur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eds.by Rahel Jaeggi and Daniel Loick, Nach Marx. Philosophie, Kritik, Praxis, Berlin: Suhrkamp, 2013, S.39.但是,当谈到对这些新创造的自由提供更详尽的阐释这一进一步的理论任务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已经简要提到过。黑格尔的观点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其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系列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将会使他们在相互承认的条件下自由地实现他们的个性。对黑格尔来说,这包括新社会秩序的所有核心制度:建立在相互同情基础上的家庭、市场、国家。综上所述,黑格尔认为这三个活动领域相当于一种现代形式的“伦理生活”,他用这一术语来表示,个人自由是在现存实践的共同作用中实现的,而不是在私人的选择行为中实现的。(25)Frederick Neuhouser, Foundations of Hegel’s Social Theory. Actualizing Freedo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然而,尽管黑格尔主张交往自由高于个人或私人自由,但他从未怀疑过现代法权结构的规范性意义。相反,纵观其著作,黑格尔继续将当时才刚确立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成就,因为这些自由要求国家保护每个人在不受他人干涉的情况下有机会检验并巩固其道德决断。
关于如何定位自己,这对马克思而言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伦理生活的整个学说抱持深度的怀疑,因为他认为黑格尔掩盖了现存社会结构的缺陷。我将在下面对此详加说明。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也怀疑,现代自由权利是否真的应该被赋予规范性意义,就像他的先驱们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是如何描绘自由得以在世界中实现的历史进程的,我们就会对现代社会的成就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一新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不是自由在人与人关系领域的扩展,而是自由在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领域的扩展。马克思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自由,体现在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上,尚未充分反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自然的进程并使其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就要求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前制度秩序的社会自由。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社会的惯性,这些当前的安排反映了一种纯粹私人的与利己主义的自由概念。大规模改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以更宽泛的合作概念取代这种狭隘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概念。目前,唯一与现代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使劳动组织和产品的分配服从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之共同意志。但是,不管这一社会主义的愿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有前瞻性,它还是使马克思没有充分发掘现代自由权利的民主潜能。在他看来,这些权利所提供的对个人自决的保护过于注重私人利益,因此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无二致。因此,他并不把它们看作是新社会秩序的规范性成就,而是视作一种衰落秩序的残余。(26)参见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更详细的评论参见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Versuch einer Aktualisierung, Berlin: Suhrkamp, 2015, S.60.
就这一点而言,黑格尔的优势要胜过马克思。的确,像马克思一样,黑格尔对于自由主义倾向也深持保留态度,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等同于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自由。像他的唯物主义继承者一样,黑格尔尚未意识到这些自由权利对于促进平等公民的民主政治决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黑格尔认为,赋予所有社会成员以平等的个人自决权这一新原则是现代社会的一项不可逆转的成就。与马克思不同,黑格尔深信,任何其他更具交往性或伦理性的自由形式,都将继续要求把个人受保护的权利作为其规范性基础,以发展和追求自己的特定目标。(27)Frederick Neuhouser,“Marx(und Hegel)zur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Nach Marx. Philosophie, Kritik, Praxis, S.25-47.
三、马克思的洞见及其在黑格尔社会理论中可能的位置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似乎让人觉得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一种足够复杂的社会概念而言,就确定自由实现背后的驱动力而言,就对现代性之规范性成就的诊断而言,黑格尔提供的解释无疑更好或者对我们今天的目的来说更有成效。然而,这种初步的比较极具误导性,因为它完全聚焦于以一种历史哲学作为补充的社会理论的概念资源。一旦我们将注意力从这些基本问题转移到这两种竞争性理论的经验内容上,事情就会变得有所不同,而且马克思社会分析的优点也显露出来。在这最后一节,我将概括呈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样做的时候,重要的是记住,马克思有额外50年的时间来观察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黑格尔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初就提出了他的社会理论,而马克思写作的年代则处于这一发展的顶点,这就使得他对现代经济秩序的毁灭性潜能处于一种有利的认知地位。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相较黑格尔来说的优点,可能部分地要归功于这一富余的历史经验,但也要部分地归功于马克思对权力和统治的更为深入的分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假定“自由意识的进步”之世界历史进程至少在现代伦理生活的社会结构中得出了初步的结论。他有权作出这一判断,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这三个领域——基于互爱的家庭、资本主义市场、现代宪政国家——为这一社会的成员通过与他人自由合作来实现他们的个性提供了制度前提,这建立在对他们个人的自由选择予以法律保护的基础上。(28)与此同时,黑格尔在确定国家是一个实现自由的主体间性领域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托伊尼森对这些困难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确处理。(See Michael Theunissen, “Die verdrängte Inter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Philosophie des Rechts”, eds.by D.Henrich and R.-P.Horstmann, Hegels Philosophie des Rechts, Stuttgart: Klett-Cotta,1982, S.317-381.)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社会的想象是马克思所不愿也不能接受的。基于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黑格尔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市场,这一三元结构的第二个要素,包含着同时危及个人自由与其他两个领域之规范性自治的破坏性力量。诚然,黑格尔对市场体系(他称之为“市民社会”)也持怀疑态度。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建议通过管制与合作机构来遏制市场过度的威胁。(29)Hans-Christoph Schmidt am Busch, “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De Gruyter, 2011, part III.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允许经济产品和服务进行自由交换的领域之存在,可能会破坏整个伦理实践网络,这与黑格尔不同。然而,这正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试图展示和说明的,而且他的努力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我们可以用来极大地丰富黑格尔的社会理论。
通过发展这一批判性计划,截至目前所讨论过的马克思理论的比较劣势反而对他有利。将社会概念还原为一套“生产关系”使得他完全聚焦于经济领域,并从政治或制度影响的抽象中研究其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注意到了几个重要的现象,这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即便有,也只是被模糊地预见到了。因此,他认为,作为新经济秩序的规范性基础之一,雇佣合同根本无法实现其关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允诺,因为那些靠工资谋生的人被迫同意合同的条款,而根本没有替代性选择。此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他们的生产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但他们却没有得到报偿,因此,他们受到了结构性的和不合理的剥削。由此获利的企业家不断被迫要求将其所得进行再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这要求他不断为自己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这就为资本主义市场带来了扩张性动力,从而致使所有生活领域都逐渐服从于市场原则,马克思称之为“实际上的从属”(real subsumption),还导致了资本主义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政府变成了阶级统治,法治也屈从于“阶级正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这四个要素,补充解释了为什么卷入这一经济体系中的人难以理解其有害机制。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将现存的一切合法化、隐匿化、模糊化,马克思把这样的解释称为“意识形态”。他的目标之一就是阐明经济交换的实践何以必然产生出这样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所有这些基本假设,并不是都经受住了他的理论所遭受的那种批判性审视。由于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反对,有些主张需要加以改进,有些主张则不得不完全放弃。例如,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存在争论,而这构成了他关于雇佣劳动者遭受结构性剥削的观点的基础。同样有争议的还有他关于意识形态认知效果的假设,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经济实践本身。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两个核心要素——他关于雇佣工人不自由的观点和他关于竞争市场的内在扩张动力的观点——在后来的发展中被证明是有弹性的,这几乎不容置疑。特别是在目睹了过去几十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打破经济壁垒之后,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在我们的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压力,它往往会逐渐破坏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生活领域的个人选择自由。但这一审慎的观察应该促使我们再次转向黑格尔的社会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其哲学上的优势,黑格尔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的介入,并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危险动力。因此,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如何才能在不完全破坏其内在结构的前提下被整合进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最后,我想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设想。
每一次试图以刚才暗示的方式调和这两种理论的尝试——通过保留德国唯心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缓和版本,并补充以他的唯物主义追随者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结果——都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障碍。最大的挑战当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使其免受由于其他目的而改变的尝试。在黑格尔的影响下,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和扩张动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描绘出来,仿佛它们是由“资本”的自主活动所引起的,形成了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封闭循环。不论人们选择何种方法论阐释,不论人们认为这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还是《精神现象学》的模仿(30)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它都不能与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直接兼容。毕竟,在黑格尔看来,社会结构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由共同社会规范所构成的“客观精神”决定的。
为了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整合进黑格尔社会理论的框架,我们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描述方式。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资本”,像黑格尔的“精神”一样,是自主运动的,并通过其内在动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相反,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概念,给那些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的影响以应有的地位。只有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定位,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追逐利润原则的机会随着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今天就比四五十年前大得多。(31)Wolfgang Streeck, Gekaufte Zeit. Die vertagte Krise des demokra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Suhrkamp, 2013.
第一个修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被视为部分地依赖于黑格尔用“客观精神”一词所指认的制度规则的内容。要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受黑格尔启发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还需要第二处修正,这里涉及的不是其解释性内容,而是其社会学框架。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观念将所有社会领域描述为直接或间接地与控制自然的目标相关。在他分析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时,他将缺乏概念资源来确定究竟违反了何种规范。(32)Jürgen Habermas, “Literaturbericht zur philosophischen Debatte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2nd e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1.描述这种缺陷的另一种方式是说,马克思缺乏对社会功能复杂性的理解,这种社会功能复杂性要求不同的活动领域受不同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允许这些活动实现其各种特定的功能。因此,他无法解释,当资本主义的利润和市场化原则开始影响并最终主导以前不受经济因素影响的其他社会再生产领域时,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危险的或有问题的。因此,在这一点上,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要想成为黑格尔社会理论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因素,也需要一定的修正。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市场只是社会活动诸领域的一种,而且每一领域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要求其活动受它们自身的一套特定的规范所支配。
我刚才所说的表明,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满足为实现充分吸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洞见所需要的全部要求。如果马克思缺乏对现代社会功能复杂性的理解,黑格尔也就无法认识到在各种功能专门化的社会领域之间存在着深度的规范性紧张。黑格尔的伦理生活学说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国家的失败或其成员的理性缺陷,可能会导致支配特定领域的规范趋于枯竭,就像过去那样。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些不同规范中的一种可能会侵入其他社会领域,并破坏或使适合它们的规范失效。我们可以说,黑格尔认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既定的过程,不可能被未来的发展所改变。无论一个理性有序的现代社会可能面临何种内部风险,家庭、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功能分化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现代社会新秩序的永恒特征。然而,这一假设使得黑格尔的理论丧失了马克思试图通过描绘资本关系对一切社会领域的“吸纳”来分析不同过程的概念资源。黑格尔从未考虑过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侵入非经济生活领域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一方面,他的理论需要根本的修正。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不应被视为一种永恒的经验的给定物,而仅仅是一种规范性目标,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或多或少地在一种社会制度中完全实现,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斗争。
如果黑格尔的理论要在今天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概念框架的话,这并不是其社会理论中需要系统修正的唯一要素。进一步的修正涉及黑格尔对如下观点的依赖,即契约观念为市场经济体系提供了法律基础,从而确保其普遍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契约双方的义务是自愿承担的。这种情形的错误不在于下述观念,即契约是新经济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它允许每个人自由决定如何利用其经济资源与服务,这与此前经济制度对个人关系和从属关系的依赖形成了鲜明对比。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极为清晰地阐述了以契约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的规范性美德,因此黑格尔在这一点上能够完全步其后尘。(33)Lisa Herzog, Inventing the Market: Smith, Hege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黑格尔观点的问题出在如下方面,即他简单地将商事双方之间的契约特征转化为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他天真地忽视了胁迫与强制的影响,这证明他更倾向于忽视权力与统治的现象。黑格尔的伦理生活学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个人对现存的“伦理”义务的赞成,可能并不是出于理性的考量,而是由于缺乏替代方案,武力威胁,抑或是巧妙地说服。然而,这些正是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时想要将其置于核心位置的因素,他将雇佣合同的表面自愿视为纯粹的幻觉,因为那些依赖工资生活的人别无选择,要么表示同意,要么身陷贫困。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伦理结构赋予自由理念以制度上的现实性,这使他完全忽略了那些持续至今依然在助长对特定人群的强制和压迫的社会机制。他错误地将争取包容和承认的斗争之终结定位在了现代性的起点,并以一种自愿和非强制性合作的乐观态度来描述此后的社会关系。
修正黑格尔社会理论的这一严重缺陷,需要的不仅仅是用武力和强迫观念来补充他的现代伦理生活模式。毋宁说,它要求我们运用黑格尔自己的范畴来解释每一社会领域中的哪些内在机制使得其中的一部分参与者支配了其他的人:例如,男人如何利用爱与相爱的规范来压迫妇女,或者忠于国家的规范如何通过对相关职责的“归化”与固化来用以动员民众。只有做到这一点——就是说,只有表明当相互承认的不同制度形式能够产生一定的排斥和强制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结果才能被恰当地融入黑格尔的社会理论。因为只有这样,市场对自由的剥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才能被整合进对现代社会的更为全面的描述之中,这一描述的焦点也会扩展到其他的压迫形式。
我所概述的各种修正,仍然只使我们朝着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进路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影响关系的目标迈近了一半。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及这种观念的和解所必然面临的最大挑战:即修正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使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接近马克思的理论起点,也就是说,嵌入社会的个体之间的合作。尽管我呼吁双方都进行修正,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人在自然界中的形象与对自我决定精神的呼吁之间的和解。但就这篇文章的目的而言,我希望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有嵌入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之中,才能有所获益。如果年轻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的宝贵见解被转换到他的前辈所提出的框架中,这些见解可能会更好更准确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