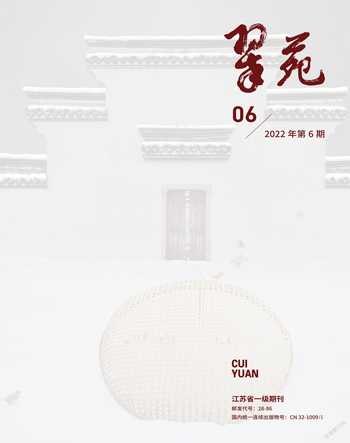最后的水手
一
凡是和大斌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对他的豪爽和义气印象深刻。大斌一张标准的国字脸,额头袒平,两耳高阔,口鼻眼分布规整,轮廓清晰。他的身高从初中就固定了,中等身材,腰背挺直。他在人群中,不突兀不张扬,而自信的态度给人以信赖。超过三十岁,这几年他的发量在减少,留着蓬松的发型。
千禧之年的北方,8月一个暑气盛大的日子,我们成为光荣的中学生。中学近观水库、远眺青山,位于一条省道的北侧。烈日炎炎。校园里,梧桐树硕大的叶子茂盛无边,遮不住少年们的兴奋、激动和紧张。叶子与叶子之间,弥漫着绿色的气息。
我们躲在树下乘凉。老谭走过来,把教室的钥匙交给大斌,把宿舍的钥匙交给我,就这样,把那个班交给了我俩。
三年里,大斌当班长,我做团支书。合作中,我们形成的默契,就像风吹草木在山谷里引出回响,这种默契一直持续到现在。漫漫人生路,进入初中,只能算作一次演习。今后的人生,我们将完成更多、更惊险的跳跃。
年少求学,读书的意义所在,正是读书本身。
那时我们精力充沛,泉水从山间汩汩而出,源源不竭。熄灯以后,寒冬雪月,冷风侵肌透骨,我们掇条马扎坐在雪地里,借着路灯的微光看书。此事在学校里传为美谈,大家都知道了四班的学生学习之刻苦。对知识的那种强烈渴望,在今后的岁月里不复出现。那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激情。
人与人情感的加深,一定是共同经历过难忘的事件。支撑事件的情节,作为双方共同的记忆点,成为日后心照不宣的触发机制。
北方乡村学校,基础设施落后,学校没有专门的保卫,传达室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作为一种象征存在。据说一女生起夜,看见窗台上趴着一个脑袋,头发像鞋刷的毛一样短。那女生摸了摸自己的长发,忽然反应过来。女生凄厉的惊叫,甚至传到了几百米外校长的家中。
女生宿舍偷窥事件闹得人心惶惶。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声言一定要抓住偷窥者。此后,各班派出学生轮流巡夜,每个月会轮到一次,就像月盈月亏,潮涨潮落,朔望轮转,非常准时。
我、大斌、启东、彦伟四人一组守前半夜,另一组守后半夜。学生们睡下后,月明星稀的夜晚,暑气燠热的夜晚,以及其他一些躁动的夜晚,我们扛着滑溜溜的橡木棍子,仿佛揣着绣春刀,在校园里巡逻。我们是暗夜的守护者。
走着走着,夜色被踏得越来越深,像是从深潭中打捞出来的水草,带着湿漉漉的暗泽。微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在夜里幻化为巨大的声响。偷窥者很有可能藏在暗的后面,一切细微的声音都变得夸张而庞大。
在寻找偷窥者的夜巡中,我们建立起信任,可以把安全放心地交付于对方的信任。
冬天,保卫处生有炭火炉子,我拿火棍拨弄红通通的炭块,消解夜晚的寒寂。更深露重,我们围坐在火炉旁,用不锈钢快餐杯煮面条,只加一点盐,没有其他配料。而后热气弥漫,蒸腾袅袅。
鲁迅先生在《社戏》里说:“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二十年后,我们一致认为:再没吃到过那夜那么好吃的面条了。
一个夜晚,我和大斌站在满天的星光下,晚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长满青春痘的脸颊。月光洒落人间,广袤而博大,我们向月亮致以问候,月亮也向我们致以微笑。月色如水如丝如滑,我忽然觉得夜色像是刚出浴的美人,冰凉中透着深深的神秘气息,远处黑魆魆的连绵的丘陵,像是女性凹凸的曲线。我的心脏忍不住悸动了一下,就像猛踩刹车,后备厢里的物件由于惯性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那夜过后,我知道了什么叫作自我的觉醒。那夜大斌有没有觉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那夜或前或后不长的时间里,也是觉醒了的。
在觉醒的一些年后,我才触摸到觉醒的肉身。那也是在一个夜晚。我和她坐在小河旁,身后垂下万条柳丝,月亮识趣地躲到柳树后面,夏天的虫鸣一波一波贴着水面飘过来。那晚在月亮的見证下,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听到了两颗心合奏演出的二重唱。看着河面上月亮的倒影,我觉得那晚的月色特别的美。
小学五年级,有一次做广播体操,大斌的手指碰到了一个女孩的手指。他说唯一的那次接触:“像有一股电流顺着指尖传遍全身。”从他的讲述中,我能察觉到他对那个女孩有过朦胧的情愫。他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好学生,三年里,他只与我谈过这一次关于异性的话题。
进入初三,中考是绕不过去的大河。累了的时候,同学们以唱歌的方式放松和打气。启东的左脸上有一块硬币大的胎记,他握着歌词,站在教室里唱《水手》的时候,那块胎记起起伏伏,一会紧缩起来,一会氤氲开去。那种起落的状态,像极了躁动的青春。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大海上最勇敢的水手,纵然风大雨大,依然可以破浪前行。只要再努力一些,就可以把船头驶进可眺望的未来。那未来,虚空而缥缈,美丽而迷人。
初中毕业后的几年,我们回过两次学校,后来随着外出求学、生活变故和聚散离合,中学渐渐地偏安于记忆深处了。每次乘车从校外匆匆而过,虽是短暂一瞥,仍能看到学校数年间的变化。一年又一年,新的学生进来,老的学生离开,学校就这样在迎来送往中,伫立于时间的风霜雨雪里。她像一个守在故乡的母亲,默默地等着远方的儿女回家。
二
县城有四所高中,大斌去了四中,我到了二中。高中几年,聚少离多。一次会考,我们被分到同一所学校。中午一起吃饭,17岁的他已经表现出超越年龄段的成熟,倒茶布菜,妥帖周全。
我喜欢过一个女孩多年,大斌对我说:“等你不再喜欢她的时候,你就长大了。”那时我觉得他的话简直不可思议,我喜欢了她那么久,怎么会有一天就不喜欢她了呢,我相信我会一直喜欢她到永远。
后来的事情印证了大斌的预言。他总能看到事情未来的样子,而我只能不断地返回过去。他在思想和行为上的成熟,有如神迹。
一封2004年大斌写给我的信,记录下一个十几岁少年思考。他在信中写道:
“整个社会大环境总是好的,新渐生起的一些不良习气却弄得我很混乱,有些疲惫,有时发觉理想已被淡漠,自私、自负占主角了,心里也很气愤,常常责备自己,太不争气了,忘不了曾经豪言,只是心里有些茫茫然,太可怕了,或许也太现实了。”
以成人视角去反察少年的想法,可能会觉得有些不自量力甚至矫揉。可是啊可是,那是17岁才有的真实心态,那份赤子之心难能可贵。我们都有过那样一段理想主义的时期,那时我们以为自己法力无边,可以匡扶社会、改变世界。后来,再长大一些,我们发现并不能改变世界,甚至连坚守初心都非常困难。
只是,我们要承认那颗赤子之心的可贵,如若人人坚守年轻时的理想,那些关于真诚、善良和美好的图景,就像七彩的阳光照进房间。
我和大斌的大学时光,在烟台那座海滨城市度过。在学校附近寻一家小饭馆,一盘辣炒蛤,一盘土豆丝,几瓶啤酒,就那么喝着聊着。对一些话题的思考,他常常可以另辟蹊径。比如关于怀旧,大斌说,小时候,吃到一包泡面,读到一本新书,感觉都是幸福的。我们之所以怀旧,不是因为过去丰富,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所能得到的太多,并且容易。当获得满足变得轻易,那满足也来得没那么充分。
种一棵树什么时间最合适?当然是十年前。十年前种下一棵树,现已经亭亭如盖矣。如果十年前没有那样的先知先见,还有一个时间,就是现在。因为离过去和未来最近的,只有现在,我们无法抵御时间的流逝,但可以在时间的两岸种下草木,总有一天会繁花夹道。
如今看来,那样的交流不过是心接青冥,纵以清谈,两个书生扮演起指点江山的角色。在那座城市,我们仍是十几万大学生中微不足道的存在。我们都在积蓄力量,等待一场涅槃,破茧而出。
毕业后,大斌去了淄博,换了三份工作。初出茅庐,这是试探的代价。他就职的一家管材公司位于郊外,靠近广阔的山林地带,卡车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有一次,大斌押车去山西,来到曾经“农业学大寨”的晋中大寨村,抚今追昔,那个烈烈扬扬的年代不过才过去了几十年。他在大寨村给我打电话,我站在烟台清泉寨的阳台上,望着海面上澎湃的夜色,与他聊了很久。
更多的时候,大斌会到院子周边走走,他看着太阳从朝阳变成了夕阳,看着天空从蓝色慢慢变成了紫葡萄色。他从诺基亚手机上获取外部资讯,小小的屏幕成为他与外界联络的隧道。隧道的外面,是一个高速运转的世界。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一日三餐,日落而息。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他仿佛蛰伏在地下的蝉的幼虫,等待着一朝破土,羽化飞升。他还记得《逍遥游》中“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句子。他在聚粮,准备一场远行。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写道:“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成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還好,24岁的大斌,没有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他也没有被劁掉。他还有热情,他想去看看隧道另一头的世界。
三
写下“北京紫竹院”这五个字,像是写下了一种豪迈。正如李敖的《北京法华寺》,这类城市加具体地点的命名,充满了空间上的纵深和历史上的延展,读起来有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虽然,紫竹院只是一个闹市中的公园。
2012年,除夕的鞭炮余响犹在,大斌乘上了北漂的列车。他在北京西五环的城中村,租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房间位于一栋二层建筑的上层,铁质楼梯置于楼房外侧,上下楼时发出当当的踩踏声。屋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一衣架而已。下雨的时候,雨点敲击屋顶的声音顺着墙缝传到他的耳朵里,晴天的时候,沙尘会钻过小小的气窗飘到屋子里。北漂的艰辛与苦涩,在这间屋子里一览无余。
他在一家职业培训机构工作,据说他们的客户都是小有所成的经理级人物。大斌与同事拿着几千块的工资,培训那些收入远远高于他们的人,现代文明下的一些工作,充满了荒诞。公司位于紫竹院公园南侧,午饭后,大斌喜欢到公园走一走,那个公园接纳了一个北漂者的孤独。
两个月后,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四月的一个中午,我们约在公园附近的一家小店碰面,吃的是河间驴肉火烧,喝的是驴杂汤。饭后,他第一次带我走进了紫竹院。春日的紫竹院,竹叶萧萧,幽篁深深,碧水悠悠。京城的大爷大妈们在卖力地踢毽子,抖空竹,拉二胡,唱京剧。一群挂着单反的学生,在老师的指点下,对着盛开的桃花调整着焦距,记录下一幅幅虚虚实实的春景。游人们买了鸟食,洒向空中,鸽子扑棱着翅膀准确地衔住食物,像是受过特殊的训练。情侣们手牵着手,头贴着头,窃窃私语走在竹林的幽影里,把春天酿造成一个幸福而甜蜜的季节。
而公园的外面,是一座奔跑的城市,车流穿梭,楼宇林立。这样的公园,在城市地图上会以绿色的模块标注。走进这片绿色,不管是居民还是游人,都能在这里获得想要的轻松与舒适。
我向大斌感慨,在北京这样喧闹的大都市,能有这么一个公园,真是难得啊。大斌告诉我,每个工作日的中午,他都会绕着公园走一圈,漫步之间,仿如能走掉一身的劳累与烦心。就像史铁生形容他的地坛那样:“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紫竹院公园,成为大斌北漂生活的见证。
很多年里,我们总能相聚在一起,这不是一个人追随另一个人的脚步,而是两个人在选择和性格上的契合。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在他的小屋里挤了半个月。床上只铺了一张木板和一张薄薄的褥子,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翻翻身子,床板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对大斌说,隔壁不会以为咱俩在干什么吧。
北京城还是冷冷地关上了城门,我最终也没有到北京读书,我从慢慢闭合的城门缝里,看到了一个步履踉跄的孩子,一个孜孜苦学的少年,一个带着苦笑泪花的青年。后来大斌推荐我读野夫的《乡关何处》,看到作者“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时,我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一年,大斌的母亲身体有恙,这让他不得不审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他是一个孝子,他不想留下不能尽孝的遗憾。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在北京,他只是一片蒲公英,就那么飘着游着,他不是一棵树,他的根扎不下来。他说他的根在故乡,在山东。他总是要回去的。既然要回去,那就早些回去吧。一年后,大斌回到济南,此后一直在银行业深耕,结婚生子。
他也迷惘也自问,难道人生就这样度过吗?人生终究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大斌说,结婚之前,他关心社会、大众与自我。有了孩子以后,他的心态变了,他的根牢牢地扎入了大地。经营好家庭、婆媳间和睦、孩子茁壮成长,他热爱这些现世的幸福。那些宏图大志和伟大构想,不是消失了,而是被藏起来,被贮藏在一间特别的屋子里。“我把自己经营好了,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四
2019年大年初一,我和大斌回了一趟中学。年关当下,校门大开,我们径直驶了进去。原来正对门口的花坛已不见踪迹,一条大道直通底部的院墙。过去我们挑灯夜读的老教学楼也消失了,那座楼曾是镇上唯一的三层楼房。90时代,有的孩子为了看楼,从远处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前来观瞻。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沿着塑胶跑道走着,冬日和煦的阳光洒满操场,一群青年在绿茵上踢球,汗水淋漓,阳光落在他们的球衫上,汗珠里映照着初春的校舍。他们带着青春的气息奔跑着,就像多年前的我们。
无须太久,我们便走完了一圈,记忆中的学校缩小了,就像一只漏了气的气球。从13岁到16岁,这个学校就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蛰伏在此,觉得它是无比的广阔与曲折。我们在楼道里嬉闹,在雪地里奔跑,提着长棍顺着围墙夜巡,学校里有那么多的房间,房间里有那么多的桌椅,甚至连每一棵树和每一朵花都充满神秘。如今回来,学校怎么会变得那么小了呢,难道是我们的脚步太快了吗?
14岁这年,大斌在课堂上向全班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斌左手托着笔记本,右手拿着笔,带着少年的老成问道:十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其实是一道简单的职业规划题,这题目若是放在大学时期,一点都不足为奇,但那时我们刚刚迈入青春期的大门。大家感到新奇而激动,回答得积极而热烈,大斌也认真地做了记录。大斌说他想成为一名战略指挥家,我说我想成为一名作家。
在大斌提出那个问题后的十年,我成了一名记者,他成了一名银行职员。同窗之中,有的读研深造,有的进入体制,有的身陷囹圄。而大部分人,成为所谓的“打工人”,在这个遽然变化的社会中,汇入了人潮人海。
做了两年记者后,我去上海读研。“到北京,上大学”的理想终究没有实现。就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2018年我到北京出差,住处位于展览馆路,离紫竹院公园只有两站。也是一个中午,不同的是,这次是一个秋日,我又走进了紫竹院。
故地重游,我和紫竹院已经是老朋友了。我拍照片发给大斌。他说,没变,还是过去的样子。在一棵巨大的栾树下面,一对中年男女悠然舞蹈,步伐轻盈,他们踩在金黄的落叶上,像踩在秋天的色彩和韵律上。
时间这艘大船,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挺进。曾经在京城里清谈阔论的我们,此刻被山水和云雾阻隔。借着理想的余晖,在黄昏面对着大江大河之时,我还能看到在紫竹院漫步的那对青年。大斌说,有那么一个地方,就像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让我们常常想起,可以让我们在听到簌簌竹声时,想起年轻時的日子,这足矣是一件美妙的事了。“那个公园里住着我们的青春。”
从过去到未来,大斌永远是一个符合中国式理想的人物,一个严以律己的君子。他待人真诚、周到、熨帖,彬彬有礼,他坚守着一些牢固的规则和道德律。他曾经豪情满怀,走向远方。当返回生长他的土地,他的身上依然有闪闪发光的东西。他是我身边最后的水手。
作者简介:
朱未,本名朱军,文艺学硕士、江苏省作协会员,作品见于《散文选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青春》《文学报》《文艺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