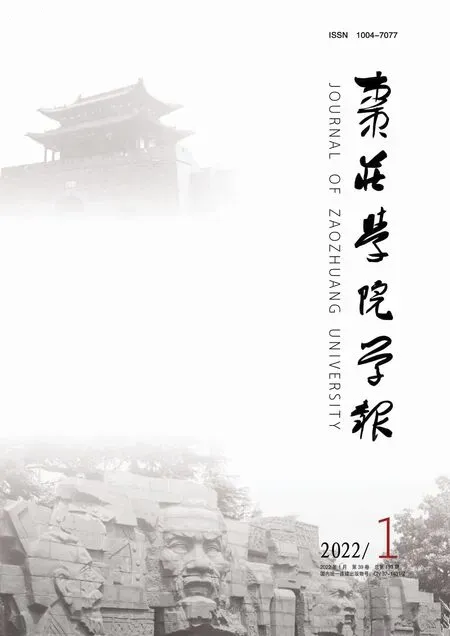关于夏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读《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书后
王 宁
(枣庄广播电视台,山东 枣庄 277100)
夏代是一个见载于文献的朝代,对于夏代的历史,历来讨论者不可胜数,大家都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就是希望能有个像殷墟那样的考古遗址来证明夏朝的存在,以考察其详实的历史,这也是我国考古学界在一直努力的方向。孙庆伟先生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以下简称《鼏宅禹迹》)一书[1],就是用考古学成果印证、补充、建立夏代信史的力作,研究夏代史的最新著作,作者在《序言》里说:
“本书以‘鼏宅禹迹’名之,也是旨在强调探索夏文化、重建夏代信史实在是中国考古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1](序言P16)
问题在于,夏代既然是古书中记载的朝代,就应当对古籍文献对夏代的记载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合理的解释,再用考古成果去印证它,而不能用文献去比附考古成果。没有文献的支持,考古学只能是自说自话,无法成为历史。也就是说,正确解读文献记载是基础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出现问题,那么全盘就会出现问题。多年来笔者也进行了部分夏代史的研究,这里就个人的一些认识谈谈有关夏代史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
孙先生此书开始也是作的文献梳理分析工作,是接受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即认为夏人是兴起于西方:
“就上文分析来看,姒姓各族确实集中分布在豫西、晋南、关中等西部地区,祝融和有虞之后主要分布在豫东和豫北地区,而东夷各族则遍布于豫东和山东。有学者指出,殷墟武丁卜辞和清华简《尹至》篇中的‘西邑’,《礼记·缁衣》和清华简《尹诰》篇的‘西邑夏’等称呼都是指‘夏’;甚至有人主张‘夏’的本义就是‘西’,大禹之族起源于关中的渭水流域,由此可见‘夷夏东西’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即已有端倪。但另一方面,夏与其他部族在空间分布上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犬牙交错之势。特别是夏代早中期,就总体态势而言,夏人是逐步向东方推进,在豫东、豫北和山东地区或设有都邑,或建有封国,夷、夏和祝融之族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以致李学勤先生有‘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的论断。终夏之世,异姓国族或夏人互通婚姻,或在王朝出任卿士,或直接介入王朝政治斗争,从而与夏族水乳交融。”[1](P80~82)
以上是孙先生对文献梳理的大致看法,所以,此后孙先生论述的考古学文化就遍布了豫西、豫中、豫东、鲁西、皖北、豫北、冀南、晋南等今天河南周边的大部分地区,涉及面积非常广大而又分散,但是感觉里面有许多问题。
首先是“夏文化”的界定问题。黄石林先生曾经指出:
“夏文化包括着两个涵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如果说夏族文化,则在文化面貌上应具有一定的特征性与典型性;如果说夏代文化,则在文化面貌上应呈现综合性与多样性。”[2]
黄先生把“夏文化”区分为“夏族文化”和“夏代文化”,他指出“所说的夏族,是指夏王朝统治区域的夏民族。”笔者认为,所谓“夏文化”应该就是指黄先生所说的“夏族文化”,即夏王朝时期以夏人为首的方国联盟所占据、活动的区域内所创造的文化,它和“夏代文化”有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夏代文化”只可看做一个考古文化的分期,只要是我国境内时期相当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都可以称为“夏代文化”,但是他们和夏民族不一定有关系。所以,讨论“夏文化”,首先就是要对夏族活动的年代、区域及范围进行界定。王玉哲先生说:
“所谓‘夏文化’主要是指商汤灭夏以前(不是同时的先商人或其他什么少数族人)在其发展阶段中所创造的文化。自然,这就牵涉到夏族所处的地域和夏朝的绝对年代问题。”[3]
这个确定,就必须靠文献梳理分析来做到。而感觉孙先生的著作,恰恰是在这一基础环节或者说关键环节上出了问题。其讨论的区域不仅分散,涉及到的范围竟然比后来殷商占有的区域还广大,这个首先是让人生疑的,孟子曾经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公孙丑上》),夏代的地域绝不会超过商周的疆域范围。最主要的就是“夷夏东西说”的问题。
358例报告中ADR/ADE累及器官最多的为全身(195频次,占28.97%),其次为呼吸系统、皮肤和附件系统。见表3。
傅斯年先生提出这个观点之时,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杨向奎先生首先表示反对,先后写了《夏代地理小记》[4](P14~18)《夏民族起于东方考》[5]《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6]等文章,对“夷夏东西说”进行了反驳,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拥护,程德祺先生在杨先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夏为东夷说”[7],此后程德祺[8]、杜在忠[9]、杨子范[10]、胡悦谦[11]、沈长云[12]、温玉春、张进良[13]、景以恩[14]等学者纷纷撰文,力主夏民族起源于东方或山东说。正如温玉春、张进良两先生所说:
“自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刊发《夷夏东西说》一文以来,‘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的夷夏东西的观点遂渐成定论,以致考古学家在西方考夏墟,历史学家在西方论夏史。然而细究于地上、地下材料,仍觉得‘夷夏东西’说破绽百出,令人疑窦丛生。还是在30年代,杨向奎先生就提出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不同观点。数十年来,随着文献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13]
笔者认为夏人起于东方说是正确的。就目前所得到的有关夏史的资料看,凡是与夏朝相关的地名大多在豫东、鲁西和鲁东地区,而与夏人有关的一些方国,除了一些在东部的国家就是“夷”,笔者非常赞成程德祺先生的“夏为东夷说”,曾经写过一篇《夷夏关系新论》予以补充论证,认为“夷”就是“人”,是夏人及其附属方国的自称,就像商人称“方”、周人称“国”一样,夏代没有夏、夷之分,夷人其实就是夏人[15],说夏人起源于西方而东渐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史实可能正相反。
实际情况是,学界在赞成“夷夏东西说”的同时,也很迷惘于夏、夷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各种猜测和推想,最后不得不用夏人西渐、融合说来解释,但是夏人何时兴起、何时西渐又无法说明白,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先祖鲧、禹时期就已经与东夷的关系十分密切,或者说从夏人产生的时候起,就已经与东夷的关系不可分割,那么他们的“西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孙先生大约也是对这个问题无法回避,所以又提出了“夷夏轮流执政”的说法[16],如果夏、夷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在同一个上古时代两个不同种族轮流执政,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夏为东夷说”却可以完美地解释这个问题,夏人和夷人本来就属于同一个方国部落联盟,或者说夏人本来就是诸夷中的一个,因为它比较强大成为联盟的盟主,其首领为夏后,就是“王”。那么夏本身就是夷,他们和夷人关系密切就是个无须解释的问题。那时候有后益、后羿、寒浞相继篡夺夏政的事情也就非常好理解,是联盟中强大起来的部族出来夺权,发生了内讧而已,根本就没有“夷夏轮流执政”之说。
根据先秦史料,夏是继承了虞的天下,《史记》的记载是《五帝本纪》之后是《夏本纪》,认为是禹从有虞氏的舜那里继承来的帝位,虽然这个说法还有待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至少在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里,夏代之前曾经有个虞的朝代,杨向奎先生[17]和王树民先生[18]专门有文论述这个问题,应该是对的。夏人认为自己是虞的延续,所谓“虞夏同科”,所以《墨子》中把“虞、夏、商、周”统称为“三代”,虞、夏算一代,《尚书》也把《虞书》《夏书》合编在一起称《虞夏书》。
从先秦文献记载来看,虞这个朝代的确是存在的,据笔者考察,他实际上传了四代五帝:帝尧、帝挚、帝韩流(乾荒)、帝颛顼、帝丹朱,到了帝丹朱的时候,被后稷流放,丹朱的儿子苗民不称帝而称王,故禹伐有苗,夺取了天下,虞朝才是真正古传中的“五帝”时期[19]。根据古书的记载,帝尧都于陶丘(山东定陶)、帝挚(少昊)、帝颛顼都于穷桑(山东曲阜),另传作为有虞氏首领的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说明有虞氏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在今天的豫东、鲁西一带,夏人取代虞人也当是发生在豫东鲁西一带。
所谓“夏”和“西”本无关系,杨宽先生早就指出“夏”本是作“下”,指“下土”,是针对“上天”而言的,夏人认为上天的统治者是上帝,而下土的统治者就是自己,所以自号“下后”,即下土之君的意思,周人转写为“夏”[20]。笔者认为夏人的国家本来叫“下土方”,就是“下土之国”,简称“下(夏)”,其国君号“夏(下)后氏”。夏朝灭亡后,夏人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和许多附属的方国一起逃到西北,变为戎狄,在晋地继续立国,仍自号“下土方”,殷人在卜辞中称之为“土方”,其实那就是夏朝灭亡后的夏国。根据殷墟卜辞,一直到殷商的武丁时期,土方仍然在和商人发生着激烈的战争,所以后来晋地才有“夏墟”之称,也有了有关夏人的传说[21]。夏在西方的观念始于殷人,因为夏亡后的夏迁徙到了殷商的西边。那里的所谓“夏墟”、夏的传说和夏的遗迹,均是夏朝灭亡后的夏文化,可以称之为“后夏文化”或“戎狄文化”,已经与夏朝的“夏文化”无关。这本来是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但是在“夷夏东西说”的左右下,被解释得不可理喻。现在很多人仍把晋地的夏墟认为就是夏朝的故国,那是本末倒置。
“夷”为异族异类的观念也是起于商人,夏人战败后,许多方国西迁(主要是在豫东、鲁西地区的夏朝方国),但是还有许多原来夏人的方国部族没有西迁,而仍留在原地,这就是山东半岛到淮河流域的夷人,在殷墟卜辞中称之为“人方”或“尸方”,到了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称为“东尸”“淮尸”,传世文献中称为“东夷”“淮夷”,所以,所谓的“东夷”本来就是夏朝的遗民。
关于“西邑”或“西邑夏”的问题,笔者也有专文做了讨论,笔者认为“西邑夏”的说法是夏末夏桀的时候才有,夏桀本都于山东东部的斟寻(山东潍坊),后来迁到有仍(山东济宁),在有仍作都,并在这里朝会诸侯,所谓“夏桀为有仍之会”(《左传·昭公四年》)。有仍的夏邑相对于东部斟寻的夏邑是在西方,所以才被称为“西邑”或“西邑夏”[22]。夏桀因为从斟寻迁都到西部的有仍,所以《尚书·汤誓》里商汤才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多方》里载周公说夏人“劓割夏邑”,都是分裂夏邑的意思。那些根据商人的地域概念推测说夏人在商西的说法都是望文生义的附会,不足据信。商汤灭夏的战争也是发生了豫东、鲁西一带,他先灭了豫东地区的韦、顾、昆吾,然后向东去攻伐西邑夏,即清华简《尹至》里所说“(汤)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最终灭夏成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夏人的活动区域,必定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而渐及冀南、豫东亦即苏皖北部的淮河以北地区。夏朝早期在禹、启的时代,是在豫东、鲁西一带接替了虞的政权建立了夏朝,所以《山海经》记载夏后启(夏后开)的故事都是在《海外西经》或《大荒西经》,因为《山海经》的《海经》部分记述的地域就是以山东为中心,而渐及冀南、豫东亦即苏皖北部的淮河以北地区,和夏人的疆域相合[23]。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说明到了启子太康、羿的时期,他们又迁徙到了山东东部的斟寻为都城,羿篡夏政之后,又西迁到了有穷(今山东曲阜),即《楚辞·天问》所言“阻(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夏人的势力再次被分裂,这是发生在夏朝初年的事情。此后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豫东、鲁西和鲁东一带,到了夏朝末期,夏桀先都于鲁东的斟寻,后又西迁到了有仍(山东济宁),其政治中心再次西移到鲁西一带,并在这里灭亡。夏人的主要方国显然流动性很大,经常沿着古济水流域东西来回迁徙,鲁东地区是他们兴起的故地,而鲁西、豫东地区则是他们夺取有虞氏的地盘,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夏朝初年夏人已经在山东最东部的斟寻作都邑,显然这不是用夏人起于西方“逐步向东方推进”可以解释的问题。
那么可以知道,从考古学上看,夏朝的“夏文化”应该就是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并没有像孙庆伟先生涉及得那么广泛。张国硕先生认为:
“岳石文化的年代问题,学术界目前已取得共识。其相对年代晚于山东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上层;绝对年代约公元前2000~15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至商初。此外,在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岳石文化延续的年代可能要长些。”[24]
方辉先生认为:
“(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河南东部,南及江苏和安徽淮北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约始自公元前1900年或稍晚,到公元前1650年前后为商文化所取代。”[25](P2)
这个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和夏朝的时代和疆域范围基本上是吻合的。岳石文化的持续年代是300~500年左右,而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朝从禹到桀,共持续了471年,二者的时间长度也是相当的。方先生同时也指出“岳石文化的创造者是东夷”[25](P48),而且他还指出岳石文化的一个奇怪现象:“相对于此前的龙山文化而言,岳石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下降了”,显著特征就是遗址少,制陶工艺落后[25](P56~57)。说简单一点,岳石文化比较奇特,它不同于此前的龙山文化,而且相对原始落后,也就是说,岳石文化的居民实际上对于龙山文化人来说,是一支外来的野蛮落后的民族。
对于岳石文化的来源,张国硕先生曾有过概括:
“在距今4000年之前,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自己的方国。由于气候转向‘干冷’,该民族的一部分被迫南下发展,首先占据了辽东半岛小珠山上层文化民族居住区(此即小珠山上层文化与于家村下层文化之间‘突变’之原因)。之后,继续南下,渡过渤海海峡,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通过与山东龙山文化民族的战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渐占据了山东龙山文化民族的生活区域,从而造成山东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过渡上的‘突变’现象。山东龙山文化被取代,其居民中的一部分被迫向西迁徙,流落到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分布区以及江淮地区。因此,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主体系来自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此外还应包括部分辽东半岛土著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文化因素。”[26]
张先生的这段论述,很完整地阐释了夏人的来源:他们本来就是北方的野蛮民族,可能是一支游牧民族,因为气候的变化南迁,在山东半岛登录后,在山东东部发展壮大了势力,形成了诸多方国部族,他们都自称为“人”,也就是商代“人方”的“人”和周代的“东夷”“淮夷”的“夷”,他们既是夏人的先人(夏人只是诸人中的一支),也是商周时期东夷人的先人。之后他们中的一些部族开始西进,其中势力较大的一支就是有崇氏,所以鲧被称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禹也被称为“崇禹”(《逸周书·世俘》),有崇氏应该是西征夷人的首领方国,也是夏人前身。
到了鲧、禹时期,他们在鲁西、豫东地区与有虞氏诸部发生了接触,既有融合也有战争,其先祖鲧被有虞氏所属的祝融所杀(《山海经·海内经》),禹攻伐共工(《荀子·议兵》)、征有苗(《墨子·兼爱下》)有天下,伯益“作革”夺取禹的政权(《楚辞·天问》),启又攻益夺回政权(《竹书纪年》),经过这样不断的战争,夏人战胜了有虞氏,虞退为夏的属国,夏人最终成为整个山东地区和豫东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夏王朝,并把他们的势力向南扩展到淮河以北地区。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夏人”是指夏的先人,就是以有崇氏为首的夷人联盟,这时候还没有“夏”的称谓。应该是从启开始,他把自己的国族命名为“下土方”,意思是占有下土的国家,简称“下”,即后来的“夏”;他自号“下后氏”,也就是下土之君的意思,即后来典籍中的“夏后氏”——“夏”这个名称是从夏后启开始的。
正因为夏人是在豫东、鲁西地区取得了统治权,所以在这一带也留下了大量的岳石文化遗存,张翠莲先生通过研究后指出:
“学术界公认岳石文化属于东夷遗存,那么大体相当于夏代和商初的豫东东部地区岳石文化应为东夷文化的一支大概不成问题。”[27]
其实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存就是夏人西渐之后留下的遗迹。这样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战国秦汉的文献如《世本》《史记》记载夏人是出自帝颛顼,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夏人谱系却是“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海内经》),他们是从黄帝(即上帝)直接出来的一支,和有虞氏的世系全无关系,这应该才是真正古传的夏人世系,因为夏人曾经和有虞氏发生过融合,夏人接受了虞人的“上帝”观念,所以也认为自己是出自“黄帝(上帝)”,但和有虞氏的世系无关,出自帝颛顼云云都是战国时代人的编排。夏人承认的第一代祖先是骆明,然后是鲧、禹,骆明的“骆”是黑鬣的白马,骆明之子鲧也是白马,《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骆马黑鬣”,似乎夏的先人有对白马的崇拜,仍能看出其游牧民族的特征。如果猜测一下,骆明的时代是夏人到达鲁西、豫东与虞人接触、融合的时代;鲧、禹时期则是为了争夺方国联盟与有虞氏斗争的时代。直到禹的时代,夏朝还没建立,建立夏王朝的是禹的儿子启,所以周代夏人的后裔在追述祖先的时候,直接把禹当成高祖,而骆明、鲧就被排斥在外了。
夏人的文化比有虞氏的文化要落后,却是战胜者,这也是一个野蛮落后民族战胜文明先进民族的实际例子。有虞氏应当就是豫东、鲁西地区龙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夏人就是岳石文化的创造者,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就是真正的“夏文化”。所以,夏朝灭亡后,一部分西迁变为戎狄,一部分留在原地称为东夷,而戎狄文化和东夷文化相对于中原的商文化也要落后,其实他们都是夏文化的延续,也就是张国硕先生所说的“在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岳石文化延续的年代可能要长些”的主要原因。
总起来说,岳石文化的年代、范围与典籍记载中夏朝的年代、疆域范围是高度吻合的,其产生、发展、衰落过程也与典籍有关夏朝的相关记载能统一起来。而二里头文化等其他地域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时代上与夏代相当,恐怕都与夏文化关系不大甚至无关。
孙庆伟先生的《鼏宅禹迹》一书结构宏大,涉及面广,但因为在梳理文献时信从了“夷夏东西说”,认为夏人起源于西方,所以在讨论相关考古学遗址时主要着眼于中原及偏西的龙山文化遗址,而对于真正夏文化遗存的岳石文化竟不著一辞,其实仍然还是处于一个漫无目标的阶段,所讨论的考古文化多与夏人无关,要谈“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恐怕仍然是遥遥无期。个人认为,把文献记载和对岳石文化、东夷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才是重建夏史的唯一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