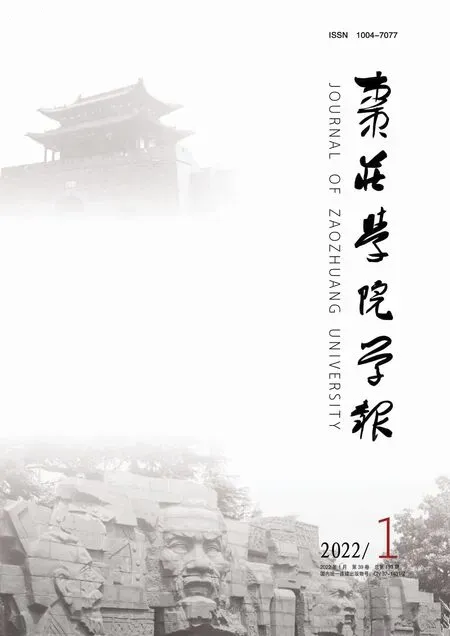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维度
陈光磊 李 莉
(1.菏泽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2.菏泽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中国高等教育自信,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已有基础和未来发展的自信,是对自身拥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方式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坚定信念。谈到中国高等教育自信,自然就会有“中国高等教育何以自信”的诘问,那是因为大学排行榜,总是让人感到中国高等教育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差距。近几年接连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大学排行榜,使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在人们的想象与思维中形成了固有的表象,因此一谈到世界一流大学,其总的印象就是差距。世界一流大学的表象体现的是“符号意义”,这种符号的意义强化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认知合法性。[1](P65~71)正是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的“理性神话”,使我们感到的是自身差距,而不能对中国高等教育自信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有利于我们树立和确认自信。
一、从历史基因与历史时空来看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有着悠久的文化积淀、优秀的育人文化基因,有着人才培养的优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将进一步成为“文化自信乃至高等教育自信的历史根基、文化基因”。[2](P42~45)从欧洲大学的形式上来看,中国“古代没有大学即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所被冠名为‘大学’的具体教育机构”,[3](P73~80)但如果把社会的教育培养分层次的话,无疑作为文明的中国也有着对高层人才的需求,因而存在着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培养相应人才的机构譬如辟雍、泮宫、国子学、国子监等可以视为最早的大学。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名实互指的大学,但存在过一种古代大学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或可称之为中国大学模式。[4]
从培养高层人才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有一套符合自己社会实际的复杂、完备而详尽的高等人才培养体系,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国家的经济社会繁荣而为邻近国家效仿,甚至有更远的传播扩散,如汉代、唐朝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府的地位就是如此。汉朝汉武帝在长安设立的太学为中央官学,是最高大学学府,其教师称为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或太学生。唐代“六学二馆的设立”显示着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备性,大学教育发达,外围辐射影响大,外国学生纷纷到唐朝的学校来学习,可以视为古代亚洲版图上的高等教育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不仅在高层次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包括科举制度在内形成了以汉字基础上的儒学教育为主要特征的“东亚教育圈”,推动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5](P13~34)从历史时空的视角看,如果说我国古代已经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兴起,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欧洲大陆,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代表。之后,由于大学的迁徙,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到英国,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标志。19世纪初“洪堡模式”的建立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德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等教育中心吸引了一批美国留学生,应该说柏林大学的模式给美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末,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外来影响是德国,大量留学德国的学生,会带着德国印象开拓美国高校科学研究的新领域。[6](P3)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使大学的研究成果走出象牙塔,越来越多地为国家服务,随着大学服务职能的确立,美国高等教育得到更好地发展,因而发展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至今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正因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留学生的集中地带。现在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但是,从日常的民众生活和大学生对美国大学的认知态度看,留学美国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正在被深入地认同。2016年就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3万名留学生在华学习。2018年进入我国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的留学生,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增长比例为0.62%(以上数据均不含我国港、澳、台地区)。[7]如今,我国大学在各种排行榜上位次是逐年上升的。“我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全球第三的留学目的国”,[8]留学目的国位次的前移,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从而吸引着国外留学人员的目光。可以认为对国外留学人员目光的吸引,也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吸引力所致,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空间中的地位。
二、从发展速度与体量来看中国高等教育
相对于西方的“早发内生”,中国高等教育属于“后发外生”,参照西方的大学制度建设话语体系,中国大学历经百年历史。在百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中国大学制度建设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不足到完善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规模上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内涵、质量等都在稳步提升。正如赛跑一样,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不仅成为我们日常的话语,且正在变成具体行动,说明了我们的发展速度。关于“并跑”即我国高等教育水平与西方国家处于“并肩”水平,关于“‘领跑’,即表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充满发展自信,也表明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探索,并希冀具备‘带领’我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前行的能力”[9](P10~14)。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公众心目中的那些世界耀眼、知名学府几乎都历经了数百年岁月的洗礼。但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即便从学者争论的几个起点中最早的时间算起至今也不过159年的历史。①2003年,潘懋元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众所周知,肇始于19世纪末,举其大数,也就有百年历史。”[10](前言)
时间是发展速度的重要计量方式。相比之下,中国近现代大学的起步、发展较之于经典大学如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剑桥大学等在时间上要晚得多。若从被认定为1088年算起,博洛尼亚大学诞生的时间距今已有千年。[11](P5~16)牛津、剑桥大学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于1636年建校的哈佛大学距今也是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大学是1895的北洋大学堂和创办于1898年的“国批国办”的京师大学堂,都是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晚期。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历经百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自身的探索,始终坚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经过改革开放的创新探索,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要建设富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更加注重内涵建设,更加强调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建设。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1%,2020年中国高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按照马丁·特罗的入学率系数标准,中国正在接近并将要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快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且在同一历史时期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两者同时发生且体量巨大,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12]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和制度深受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影响并脱胎于欧美高等教育文化,但历经百余年的探索发展和锻锤,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自成一体,形成了覆盖人口最广、规模最庞大的体系”,“中国高等教育涵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13](P19~41)
高等教育大众化,充分显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从重点大学建设,到“211工程”“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大学建设,显示出内涵的提升与发展,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14]中国对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培养国际一流人才充满自信。
关于“体量”,我们不必列举中国大学的数量,也不必列举在校大学生的人数,从拥有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的大众化就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关于内涵的提升速度,随着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不仅体现在中国大学位置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提升,还体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高等教育是认可的,信得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8]
三、从发展道路来看中国高等教育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15]“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6]“中国共产党自独立探索创办新型高等教育起,就具有坚定的传统文化自觉和民族教育自信。”[17](P1~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始终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大学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着艰难的选择;[18](P25~35)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新时代以来,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明确提出向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迈进,一系列的改革发展实践,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基础。
梳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能清楚地看到两大脉络:一脉是以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为代表的近代高等教育;一脉是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为代表的红色高等教育。两大脉络都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都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1937年陕北公学创立,到1939年初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时,她已经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形。到华北联合大学时期,学校的学科设置与现代大学已基本相同。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党独立创办的学校成长的历史表明,我们党有能力创办自己的大学。由于当时没有统一入学考试的要求,有人质疑陕北公学的质量。毛泽东认为,青年能从西安走到延安,经600里冒着枪林弹雨和死亡的威胁,就是最为严格的考试。[17](P1~3)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浓厚的赶超情结源于最初的路径选择。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启动了向西方各国学习、模仿与借鉴其先进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与制度的进程。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地道的舶来品”,虽然19世纪末康有为提出“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最终还是只能师法日德。[19](P8,14)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确立了新形势下“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20]这一方针的目的是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事实,集三种不同的传统于一体,即是从民国时代传承下来旧有高等教育有益的传统;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政府的经验;在20世纪三十年代引入的苏联模式。[21](P196)
“如果说1952年以前的发展历史与当时的选择是当代高等教育赶超型发展道路的起点,那么可以认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赶超发展的情结越来越浓厚,并一直延续至今。”[22](P1~12)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在赶超方面存在部分非理性制度设计,但这种制度的实践与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性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富有自信,就是因为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性发展,正在推进和实现高等教育宏观治理转型,进而实现高等学校发展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全面改革,提出改变管理体制、扩大办学自主权、改革高等教育结构。《决定》开启了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在理论层面引导人们思考高等教育治理的探讨,在实践层面引导高等教育治理的深化。
1992年至1999年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使中国高等教育始终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道路上扎实前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等教育自信是中国自信谱系的自然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立足基本国情,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朝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前进,为进一步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高等教育和红色高等教育两大脉络路径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都为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都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为代表的红色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历史发展表明,我们党不仅能够创办出色的大学,而且党的领导是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四、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来看中国高等教育自信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同时也是大学制度创新与扩散的历史,大学个体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催生大学制度创新,由于大学从创始就带有的国际性因而具有传播性、扩散性。大学制度的扩散既有整体性的、也有部分性的。整体性扩散即大学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之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部分性扩散即某类大学组织内部的一些制度安排和实践被其他大学所模仿和移植。[1](P65~71)
百余年来,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大学制度建设来看,最初具有模仿、“移植外生性”。大学发展的模式、高等教育制度曾经学习过欧洲、日本、美国的模式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以“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和大学理念”“苏联模式”“红色高等教育模式”三种大学制度为基础,进行大学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学的精神基调,是大学精神的基石。”苏区解放区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各种环境的艰苦性,其高校设置也有特殊时期的独特性,最为明确的目标指向就是坚定的政治性、革命性,因此必须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权。这也是“红色高等教育模式”的意义所在。[23](P45~5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的探索与实践进程中,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但不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高等教育自信心的坚守”。[24](P47~52)
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的成功,特别是企业改革的经历对研究中国大学治理问题有很大的现实启发性。[25](P1~12)也正是有了中国整体改革的自信和发展,高等教育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进行,深化改革、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对自身不足的承认,表达着自信。从重点大学建设到“双一流”大学建设,就能感到中国大学建设正在发挥大学自身的改革动力,犹如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于底层一样,“双一流方案”的提出,是来自基层的初始制度创新通过无数次改革主体的竞争博弈直至千锤百炼后的认同,让来自中国大学的符合国家民族时代需求动力成为制度构建的“第一要素”。“‘985工程’是传统重点大学建设模式的延伸”,而传统重点大学建设模式已经无法兼容于现代科技创新模式这一全球高等教育创新大势,“双一流方案”应运而生是新常态下大学制度创新的重要转折。[26](P11~19)
从重点大学制度到“双一流方案”这一转折意义在于发挥底层的改革动力、大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因而需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需要进行“放管服”改革,需要进行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建设。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大学就开始有了“给高校一点自主权”的诉求。[27]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高等教育迎来了“放管服”。2017年,《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就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学科专业、编制、岗位、进人用人、职称评审、薪酬分配、经费使用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是一种深层次的改革,其改革放权是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自信,是一种充分理解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自信,是一种“强政府”状态下,大学自主办学的自信。
中国大学成立伊始,就背负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任务,因而形成了一种“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公立大学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政府机构的延伸。中国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强政府”,但“强政府”并不一定是“大政府”与“弱大学”的局面。“大政府”是事无巨细的包办,从而大学失去自主权,弱化了大学自主能力,使大学成为“弱大学”。[28](P41~46)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步提出“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目标是“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29]2017年,提出“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30]同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重申“依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31]“放管服”改革,是政府对自身的自信,也是对大学的信任,显示出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自信。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既取决于自身的实质性改革创新和高等教育宏观环境的根本改变,“还取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深层次变革”。[32](P10~17)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自信,是中国“自信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高等教育自信不仅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源自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教育制度的积极情感体验、态度赞同、理性认同、意志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必然成为高等教育自信的制度优势。
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二是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三是坚守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是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鲜明特征。[33](P95)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深厚实践、现实巨大成就、发展新境界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15]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坚持党对高等教育领导的具体表现。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最大特色,也是与西方高等教育的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出发,对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论述,充分展示出中国高等教育自信。
新时代,中国自信谱系建立,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四个自信”谱系要转化成为高等教育自信,需要高等教育的新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是不是强国教育,必须在国际视野下看我们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感召力、有没有塑造力,是不是开始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有没有贡献中国方案。遵循教育规律,借鉴有益经验,才是应有的选择。检验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标准就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前列。不仅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人才、拥有世界一流“大师”,还要有世界一流知识的产出。在实践的基础上,显现中国的贡献能力和创生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注释
①我国高等教育从何时算起,就百年史来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桩公案。但就百年史而言,黄启兵认为主要有六种观点。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起点,这样应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参见:黄启兵著《中国高校制度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