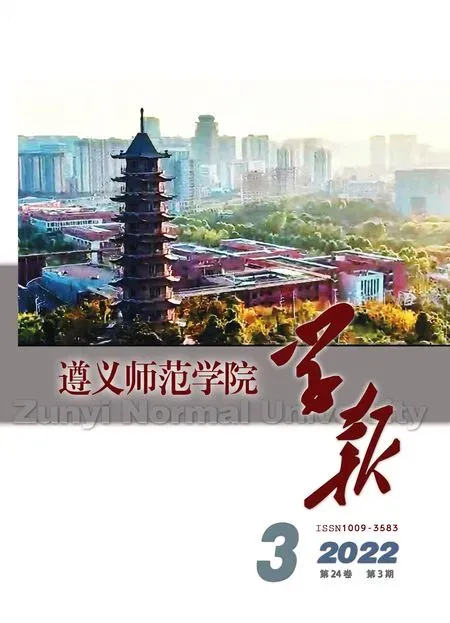中国西南土司遗存考古研究回顾
周必素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04)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因中央对边疆地 区鞭长莫及,无力直接管理,于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衍生并发展了一种羁縻·土司制度,即对边疆地区实行“松弛有度、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管理,更利于对各边疆民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尊重,维系着版图辽阔、民族丰富的泱泱大国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到土司制度阶段得到加强。中国西南地区是元明时期实行土司制度管理的最主要区域,留下了丰富的土司遗存。
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但最初是在宋元明考古或民族学的视野下开展的,2010年开始为配合“中国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工作的开展,才置于“土司考古”视野下推进。土司遗存相对丰富的几个省份陆续开展了部分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如对湖南永顺彭氏、湖北唐崖覃氏和容美田氏、重庆酉阳冉氏、四川平武王氏、贵州遵义杨氏、云南景东陶氏、广西南丹那地罗氏等土司家族遗存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分类研究及回顾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工作,随着土司遗存发现的不断丰富,研究工作也不断推进。特别是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三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对土司遗存更多从土司制度文明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实际上是一次“土司考古”的学理探索。同时,还掀起了一次“土司学”热潮,从中国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以及“土司遗址”的申遗、管理、利用、宣传等方面,进行了文献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基于本文的篇幅和主题,仅对土司遗存考古研究按内容进行以下分类梳理和回顾。
(一)土司考古综合研究
赵衍垣率先从土司考古的角度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类别间的宏观综合考察。[1]湖南、湖北、贵州三省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是对土司遗存考古研究的一次深入推进,孙华对三处提名世界遗产土司遗址的概况以及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新发现、新研究和保护进行了归纳总结,促进了西南土司遗存的研究。[2]周必素、李飞对近年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取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划分了司治、关囤、田庄等遗存类型,体现了土司政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特征,并尝试提出了“土司考古”课题,目的在于拓展思路,力图今后将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纳入全国“土司考古”的总体框架中进行,以推进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3]湖南在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中,深入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结合聚落考古、动物考古、碳十四测年、古建筑研究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地获取土司时期的考古信息,提炼出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是对土司考古的一次深入探索。[4]
(二)司治研究
因播州晚期司治穆家川地点明确,且叠压于现遵义老城之下,无法做考古工作,对其研究主要从文献的角度涉及,而穆家川之前的播州司治白锦堡,因踪迹难寻,是探讨的热点,谭用中根据杨粲墓“葬于本堡”墓志铭文,推断白锦堡即杨粲墓所在地为皇坟嘴[5],遵义县(今播州区)志办对白锦堡作了专题考察,再次确认了白锦堡在皇坟嘴。[6]王炎松等对唐崖土司城格局进行了探讨,[7]并对唐崖土司城宫殿区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8];刘辉对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空间布局与结构进行了分析[9];陈飞对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与营建进行了专门讨论[10];李德喜等对唐崖土司城衙署区建筑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11];王晓等分析了唐崖土司城规划与建筑特色[12];康予虎等对唐崖土司城址给排水系统进行了专题研究[13];王焕林对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的兴废、迁徙历史,对集政治、军事功能为一体的老司城选址、修建理念以及老司城在复原土司社会结构、研究土司制度、中央与地方民族关系治理等方面展开研究。[14]杨庭硕将永顺老司城遗址与国内同类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15]并对湘西永顺老司城遗址的历史见证价值进行了提炼和总结。[16]许葳结合土司遗址,对湘鄂西土司园林营造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17];孔觅根据老司城考古遗迹遗物,对永顺土司的居住文化特点进行了剖析。[18]
(三)军事遗址及防御体系研究
海龙囤的关名,因战争的破坏和历史的变迁,部分关隘遗址已不存,目前研究仍不能概括所有关口之全貌。[19]李飞对全囤格局以及一二期城垣的发展作了梳理。[20]孙华对海龙囤关隘、“新王宫”衙署遗址建筑的布局、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是中国古代山城的杰出代表,[21]同时,他还认为播州杨氏土司以海龙囤为中心,利用山隘险阻修筑层层城堡关寨,控扼出入播州的各交通线,形成多层级、纵深的山城防御体系。[21]李思睿对《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22];吴孟珊等在海龙囤申遗过程中,对海龙囤的突出价值进行梳理和提炼[23];周必素等认为播州杨氏军事防御体系是以海龙囤为核心的由外而内的三道防线[24];赵丛苍等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土司军事遗存进行研究,对于推动和深化土司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可行性与必要性[25];崔镐玹对西南土司遗址与东北高句丽山城进行比较研究,分别将两地山城进行分类和比较,指出两地均存在平地城(行政中心)和山地城(军事中心)的现象,但西南仅见于播州杨氏土司,在东北则是普遍现象。[26]黄慧妍对播州整体境域、遵义老城和海龙囤三者在明代平播战役以前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总结土司制度对播州城邑营建提升、独立性、独特性和防御性等的影响;[27]杨旭通过对播州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变,播州城邑类型、城市形态、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点”与“面”体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播州“土司城堡-城市”的嬗变关系,从而探讨地方与国家、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28]
(四)墓葬及出土器物研究
宋世坤对早年发现的遵义7座土司墓进行了综合梳理[29],谭用中对杨粲墓出土墓志进行了全面考释[4],赵衍垣认为杨粲墓可能是淳祐七年(1247)杨文执政时为其祖父重修的一座大型石刻迁葬墓[30]P75,宋世坤结合杨粲墓出土文物,对墓主进行了再次推定。[31]周必素对杨氏土司墓葬形制[32]、腰坑葬俗[33]、出土陶俑[34]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其以及相关家族墓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将墓内外出土器物与形制、墓葬堪舆与宗教信仰进行综合考察[35],在对其进行系统全面梳理后,与川渝地区宋墓[36]、播州其他宋元明时期墓以及周边地区土司及职官墓进行比较[37],同时对贵州遵义高坪土司墓地五室墓出土的金银玉器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器物的功能以及墓主的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8]李飞以杨氏墓葬为中心,对黔北宋元明时期墓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39],彭万等对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进行了整体观察,对其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40],韦松恒等从祭祀空间及葬仪的角度对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墓葬进行了分析[41],付永海对1953年高坪地瓜堡五室墓出土凤冠工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42];秦大树认为“杨价夫妇合葬墓中各随葬了一套香具和酒具,属墓主生前珍宝玩好,反映出其饮酒、品香的雅好”。[43]云南省对景东陶氏墓地历次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编撰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23]四川对早年清理发掘的平武土司墓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成果。[44]
(五)碑铭及雕刻研究
刘锦对杨粲墓雕刻技法、风格以及几幅重要雕刻进行了叙述,认为“雕刻技法纯熟,作风严谨,造型逼真生动,具有五代、北宋以来高度写实主义传统”。[45]周必素对其中的卷发贡使进行了粗浅的阐述[46],曾春蓉认为杨粲墓中的部分雕刻“在形象和衣饰上表现出来的特色,相比之下更接近于少数民族风格”。[47]罗正兵对杨粲墓石刻艺术从时代背景、整体格局、石刻内容及形式、寓意、石刻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48],王洪分遗址、墓葬、石雕刻、建筑构件、器物共五个类别对湖南永顺老司城图形符号之装饰纹样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解析[49];满益德等对唐崖土司城的建筑石刻艺术进行了研究[50];李梅田等对唐崖土司城张王庙石刻进行了考述[51];鲁卫东对永顺老司城的碑刻进行了梳理和五类辑录,提供了关于永顺土司家族婚姻、与“流官”交流、参与军事活动与朝贡、汉化与国家认同等方面的重要碑铭史料。[52]
(六)宗教考古研究
张合荣对播州地区石真、镇墓石、神兽、仙境铭刻以及八卦等道教题材雕刻进行了梳理[53];张勋燎考释了杨粲墓墓主人像为道教葬仪有关生墓代人以祈长寿之“石真”[54];龚杨民、白彬对杨粲墓道教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55];陈季君对播州地区佛道史迹做过分类系统梳理。[56]赵川等对鹤鸣洞摩崖进行调查和研究,探明系播州杨氏27世杨斌刻于不早于正德十三到十五年之间的24则道教二十四治、二十四炁、二十四节气题刻和诗刻[57],并对永安庄遗址附近的天师誓鬼石敢当碑进行研究,提出播州道教派别的初步想法。[58]瞿州莲等对明代永顺土司道教的兴盛及原因进行了分析[59];周必素等对贵州北部地区宋墓“四神”雕刻进行了类型学研究。[60]
(七)公众考古
为配合考古工作,海龙囤公众以系列公众考古活动为代表,开展了大量公众考古宣传活动,并形成了系列成果,如《土司,考古与公众:海龙囤公众考古的实践与思考》[30]《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61]以及刊布的系列公众考古成果,形成了良好的公众效应和社会影响。[62]
(八)动植物考古
姚凌等通过观察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牙齿表面植物微遗存,表示该时期气候环境温暖湿润,老司城遗址部分家养动物可能存在半圈养或放养的现象。[63]
(九)科技考古与保护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老司城遗址发掘过程中,边发掘边保护,完成保护设计方案、规划和施工,科学保护遗址。[64]李玉牛、黄琬在《田野考古三维测绘在建筑基址遗址中的应用——以贵州省遵义市海龙囤明代土司遗址为例》一文中探究三维测绘在海龙囤遗址考古中的运用。[65]朱伟在谈到对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保护的对策时,提出要维护文物的历史空间信息。[66]郭伟民总结了湖南省在考古与文物保护全面融合和多学科合作新的文保理念与模式,老司城遗址是成功案例。[67]杨檬以湖南永顺县老司城为例,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进行了专题研究,从遗址范围的确定、用地功能的合理调整、交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立法与管理制度的建构等诸多方面对老司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进行系统全面分析。[68]李政对海龙囤遗址发掘之后如何保护提出相关意见。[69]李林就海龙囤遗址申遗后的保护和利用现状进行了追踪考察。[70]
三、结语
羁縻·土司制度,是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的制度文明和智慧。羁縻之治发端于秦汉时期,制度形成于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更加成熟和完善。土司制度的发展,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由弱到强的管理,伴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开启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西南地区土司遗存考古工作,为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和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窗,生动揭示了土司制度下的社会和生活。土司考古学,开辟了对羁縻·土司制度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领域,架起了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间的桥梁,在细节中解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特征和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