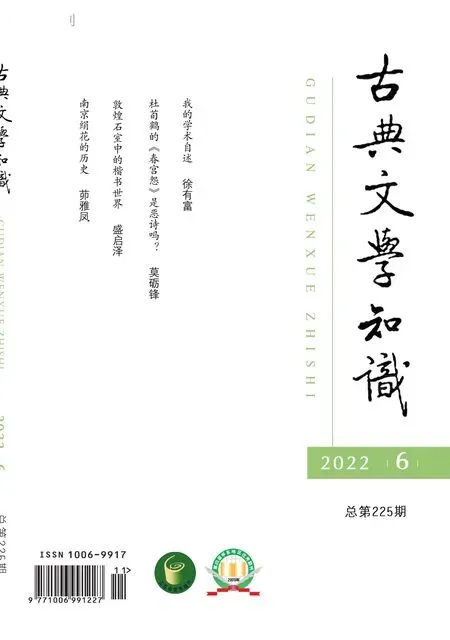魏晋名士的隐逸情怀(下):名士归隐的社会生活与衣食住行
——《世说新语》之二十一
宁稼雨
名士归隐的社会生活
人生活在社会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把个人交给社会,还是傲然独立于社会,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人们不外从入世和出世两个方面考虑自己的选择。于是很早便有了孔夫子的“立德、立身、立言”和老庄清静无为的主张。不过在秦统一以前,人没有固定的君王,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还不那么明显,所以个人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自秦统一以后,个人第一次要面对一个帝王,而且要在各方面服从皇权的绝对意志。人的个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与窒息。所以从东汉起,随着门阀世族的兴起,个人的愿望和利益开始受到重视。
从隐士自身的特点看,隐士从产生那天起,就是作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间离物而出现的。清高孤介、洁身自好这些隐士的基本特征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隐士身上的比重不同,但没有它即不可称为隐士。尤其在世族兴起、个人意愿高蹈的汉末至魏晋间,隐士的这种基本素质更是如鱼得水。迅速膨胀,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重个人、轻社会的风气与汉末以来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危机互为因果。“自然”是指老庄崇尚人性自然之旨。至于“名教”的理解,学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陈寅恪认为是指“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余英时认为名教应是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整个人伦秩序,其中君臣和父子两伦被看作是全部秩序的基础(《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取余说。余氏所提到的君臣之伦的危机表现在君权思想与君臣关系的淡漠,对君权已从怀疑而走向否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臣民观念的动摇;另一方面,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礼法至东汉后期变得更加虚胎和高度形式化,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唾弃,并追求符合人的自然心性的人伦关系。于是人们逐渐从名教的束缚中挣扎出来,徜徉于自然的境界之中(宁稼雨《魏晋风度·从生活行为看魏晋文人个性》,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蔑视社会旗帜的旗手是嵇康和阮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谈到辞官的理由时,举了七不堪、二不可,全部是从做官如何妨碍个人自由的角度来拒绝为官,最后说:“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这可视为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具体陈述。阮籍也明确提出“礼岂为我辈设也”(见《世说新语·任诞》)的口号,并且在行动上毫无顾忌地与礼教对着干。《礼记·曲礼》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偏要经常和嫂子聊天;按常礼母丧不食荤,可他在母丧期间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礼教对男女的交往严加限制,阮籍却经常和邻妇饮酒,并醉卧其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连他的两次做官,也是与名教开的玩笑。因为知道他放达不羁,不愿作官,司马昭也就不勉强他。可一次阮籍主动提出去做东平太守,司马昭赶忙答应。可阮籍上任后唯一的政绩便是让手下人把官府的墙壁全部打通,使内外可以相望。然后便整天无事可做,待了十几天,便骑驴而去。后来又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存酒数百斛,又要求任步兵校尉。来到官府后,便只顾大饮,不问政务。传说他就是在酒厨中与刘伶痛饮并大醉而死的(见《世说新语·任诞》及刘孝标注)。
西方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认为:“人的一切社会成功都意味着他作为个人的失败,而表面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是成功。”([苏]伊·谢·科思《自我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从社会的角度看,嵇康和阮籍是失败者;但从个人角度看,他们却是成功者。在这两面旗帜影响下,许多魏晋间的隐士放弃了社会权贵富庶的诱惑,去品尝那个人之果的稀奇味道: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张翰的话已经把他们对名利富贵与个人自由的看法,说得清澈见底,真不愧是阮籍第二,“江东步兵”。就是这位江东步兵,在洛阳齐王手下任东曹掾时,一次见秋风乍起,便想起自己家乡的美味莼菜羹和鲈鱼脍,说:“人生最宝贵的就是自由快乐,怎么能为了官爵把自己拴在这千里之外受罪呢?”于是便辞官回到家乡(见《世说新语·识鉴》)。这与陶渊明的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的举动完全一样,表现了这些隐士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清醒。又如: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临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礼之,故辟为府掾。廞得笺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世说新语·栖逸》)
既然人生贵在适意自由,那一顶乌纱怎能换去如此宝贵的东西?又如骠骑将军何充的五弟何准也是一位高洁隐士,当何充劝他出来作官时,何准说:“我虽然排在老五,却不比你这个骠骑将军差!”(见《世说新语·栖逸》)把隐士之乐,看得高于做官。有了这种价值标准,仕途之人才被隐者视如粪土: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阻。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世说新语·栖逸》)
是什么使二位旧友反目呢?是对仕隐、名教与自然的不同看法。又如:
孟万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阳新县。万年游宦,有盛名当世,少孤未尝出,京邑人士思欲见之,乃遣信报少孤,云“兄病笃”。狼狈至都。时贤见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谓曰:“少孤如此,万年可死。”(《世说新语·栖逸》)
可见那些崇尚自然的隐士,比起效力于名教的官人,更容易得到世人的青睐。
抛弃了名教的束缚后,隐士们所获得的,便是个人行为的极大自由: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刘孝标注:《中兴书》曰:“徽之任性放达,弃宫东归,居山阴也。”左诗曰:“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间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王徽之在夜深人静之际的举止,完全凭随心所欲、兴之所至的意念驱使。这种自由,是蝇营狗苟、碌碌无为的做官者所不敢想的。有了这样的自由,才可以去遍尝那人生中真正的快乐:“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见《晋书·王羲之传》)有了这样的自由,才会有那种气吞宇宙,俯视群小的气度: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
这种境界如同尼采所说:“对于时代的、合时宜的一切,全然保持疏远、冷淡、清醒;作为最高的愿望,有一双查拉图斯特拉的眼睛,从遥远的地方俯视人类万象——并看透自己……为这样一种目的——何种牺牲、何种‘自我克服’、何种‘自我否定’会不值得?”(尼采《瓦格纳事件》)嵇康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嵇康集·赠兄秀才入军》第十五首)说的也是这种境界。
名士归隐的衣食住行
人们的衣食住行虽多不经意而为,但却好比是一面折射镜,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品位。隐士的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态度等,均不同程度地在衣食住行中有所反映。
古代的隐者多是在贫困、简朴的生活中去表达一种高洁的志趣。如巢父以树为巢,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等。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山林隐士的高洁之风仍不乏其人。如嵇康在汲郡山中所见到的孙登,“无家,于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见《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嵇康集序》)。阮籍在苏门山所见到的隐者,也是只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见《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但随着魏晋时世族的兴起和很多世族文人仕隐兼通格局的出现,隐士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贵族化的趋势。但这并没有改变隐士们在生活上追求高雅情趣的基本内核,反而把这种情趣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了。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写的兰亭,可以说是这种新的隐居环境的代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隐士们对这种高雅环境的营造: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世说新语·栖逸》)
又如: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刘孝标注:《遂初赋叙》曰:“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世说新语·言语》)
由于移情作用,隐士们对那些山水田园中的激流湍水、松柏修竹似乎有特殊的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寄托自己的志趣,观照自己的人格。所以他们很注意隐居之所地点与环境的选择。除了环境幽雅、山水灵性这些自然因素外,还十分注意环境的修饰,康僧渊在轩庭中搞上一片芳林,孙绰在房前种上一棵松树,王徽之连暂时借住别人的房子,也要赶快种上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见《世说新语·任诞》)都反映了隐士们这种高洁雅兴。
比起前代的隐士,魏晋隐士们似乎生活环境显得优厚了,但与很多当时贵族比,他们仍显得清贫。而且他们没有丢掉古代隐士们的精神内核,仍然以贫洁为荣,倚贫而凌富: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绣。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世说新语·任诞》)
面对贵族们借晒衣的机会大肆炫耀家财的庸俗之举,阮咸针锋相对地挑起了粗布围裙。在这强烈的反差对比中,阮咸以贫为荣的自信和对贵族们的蔑视,已经呼之欲出。更有意思的是许询。他在永兴隐居时,住在洞穴之中,却经常接受四方达官贵人所赠送的各种礼物,有人问他:“听说隐居之人并不这样贪心!”许询却振振有词地说:“比起尧让给许由的天子之位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见《世说新语·栖逸》)这个巧妙的回答不仅表明了隐士之初衷未变,而且也为当时隐士们生活条件的部分改变,找到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