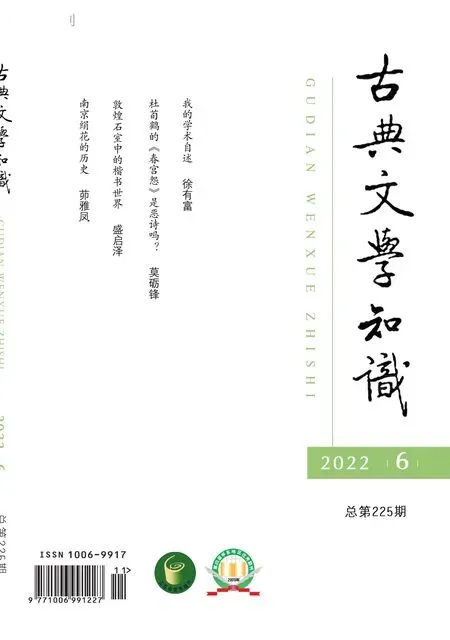陈智超先生及其家学对我的影响(四)
朱天曙
陈老师为《中国书法史》和《周亮工全集》两部书撰文
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的书法史课程的讲稿《中国书法史》,当时我请恩师卞孝萱先生赐序。此书出版后,在学术上有较好的评价,一时都订不到书了。2016年,中华书局决定增订此书,重新出版。中华书局的编辑希望我再请位名家为新版写序,我跟陈智超老师说了,他欣然同意了。
陈老师在序中说,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神符号,它以汉字为表现对象,渗透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区别于世界各国的文字和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字体演变、流派风格、书学文献为特色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他在序中提到卞先生在原序中征引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弁言中“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又把卞先生论此书“述书史之变迁,扬书艺之精神,有承先启后之功”语引用出来,表示“我是十分赞同的”。
陈老师在序中指出:“这部书法史,囊括了各个时期书法的技法、审美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其中如早期的甲骨文、金文的分期,‘隶变’的内涵,汉代书体的嬗变与文人书家的兴起,三国的禁碑风气、魏晋书法精神、南北书风的融合、刻帖与金石学的发展,元代少数民族书法、碑学的兴起与实践等,虽未具体展开详细讨论,但这些书法史上的重要现象,都做了扼要明了的梳理,可谓金针度人,启发后人进一步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一部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精彩导读之作。”又指出:“这部《中国书法史》在艺术风格上的讨论之外,尤其重视吸收文献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的成果和研究方法,考镜源流,评骘精审,非惟拘于点画技法之论。如书法史关于‘金’‘石’与‘帖’、‘碑学’与‘帖学’、‘刻帖’与‘著录’以及附录书学文献举要、中国书法史基本书目等内容,精审校理,门类贯通,体现了他在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上的用力和关注。”这些评介,都是陈老师从一个历史和文献学家的角度对小书的鼓励和嘉许,是特别值得感激的。书中很多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陈老师用包容的态度肯定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他对后学的爱护和提携。他在序中曾引用传为东汉蔡邕《笔论》中“沉密神彩,如对至尊”语,表现他对书法艺术和文化的敬畏之心。陈老师虽未专门研究书法史,但他对书法史的认识是极高的。他在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中,就涉及很多书法史的知识。陈垣先生十分重视书法,多次在信中教育子女和学生要学好书法,了解书史。
陈智超老师精心为我的《中国书法史》增订版写序,和卞孝萱先生的序一起见证了我这本书的两次出版,两位先生都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卞先生在北京工作时,曾多次拜访陈垣先生,又与陈智超老师是多年的挚友,陈老师在南京讲学,我曾陪他夜访卞先生,两位老师相谈甚欢,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在学风上都很朴实,重文献,重实证,我研究书法史也受到他们这个学风的影响。
我编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十八册,2008年12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后,2009年的2月,凤凰出版社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行了出版座谈会,出版社领导倪培翔总编和王华宝编审专门来北语主持座谈,邀请了陈智超老师和傅璇琮、彭庆生、薛永年等先生出席。陈智超老师专门为这次座谈会撰写了《〈周亮工全集〉的双重价值》一文,对我研究的内容加以评价和鼓励:
周亮工(1612—1672)是明末清初一位多才多艺多产的文人、学者、艺术鉴藏家,但在现行的《四库全书》中竟没有收录他的著作。其实,乾隆四十七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时,曾著录周亮工著述五种,存目三种。但乾隆五十二年覆勘《四库全书》时,详校官发现他的《读画录》有“违碍”之语,于是周亮工著述已著录者一律撤出,存目者一律扣除。不但如此,陈垣先生根据四库全书总纂纪昀的亲笔改订的精缮《提要》底本,还证实《四库提要》原引周亮工语多达数十处,并称他的《书影》“记述典赡,足为文献之征”。至乾隆五十二年,与从《四库全书》中撤出他的著述同时,已刻《提要》之有周亮工名者也一律抽改(见《〈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正因为周亮工著述遭此厄运,后人要全面研读他的作品困难很大。朱天曙先生编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皇皇十八册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为读者解决了这一难题,是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好事。
《周亮工全集》全面包涵了散见各处的周亮工著述,包括他的诗文、笔记以及他编纂的书籍。既有成本的著作,也收罗了散篇的序跋、祭文等。能影印的影印,没有条件影印的则排印。可以说,经过编校者多年辛勤搜访,现存的周亮工著述,包括一些稀见的内容,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不仅如此,天曙先生还在编校者前言中对每种著作的内容、著录情况及版本源流一一作了考订及说明,排印部分还加了标点符号。除了周亮工本人的著述外,编校者还在“传记篇”中收录了周亮工的传记资料;“序跋篇”中收录了他人为周亮工及其著作所撰序跋、题记;“集评篇”选录了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周亮工其人其著的评论。这就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周亮工全面的、翔实的、并经过一定加工的资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周亮工及其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亮工在政治上历仕明清两朝,因此在《清史列传》中被列入“贰臣传”。他的仕宦生涯复杂曲折,在那个矛盾错综、风云变幻的年代,具有某种典型意义。他的贡献主要在文化领域。因此《周亮工全集》兼具政治史与文化史两方面的价值。
陈老师亲自出席出版座谈会,发表了这个书面演讲,指出周亮工著作的文献价值,也对我编校整理和出版的方法进行评议和鼓励,他说这部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周亮工全面的、翔实的、并经过一定加工的资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周亮工及其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对我研究工作的肯定,也是我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清代文人著作进行编校整理的一次实践。他的文章后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报》发表。
陈老师赠我陈垣先生手稿
2013年7月,陈智超老师赠我陈垣先生珍贵的墨迹两帧,此两页内容均为陈垣先生手书目录,写于1929年。
一为民国十七年度日本之史学界论文数目,内容包括:
上古时代文化之研究 4
年代学的研究 古代天文学研究 2
政治史 4
经济史 5
通商史 交通史 1
外交史 3
史地研究 13
宗教史 13
信仰史 2
学术史 4
小说戏曲史 3
言语学史 2
美术史 工艺史 工作史 14
考古学 16
一为民国十七年国际史学会第六届大会宣读论文的内容。这次会议在挪威京城召开,分十四组。内容包括:
史学之书目及辅助科学
先史时代及考古学
古代史
中世史
欧洲现代史
美国史 远东各国史 欧洲殖民发展史
宗教史
法律政制史
经济及社会史
科学与文学史
美术史
史学之理论与研究方法
史学教学法
北欧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史
这两件作品的目录,体现了陈垣先生对世界史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二十世纪前期,他能与长期生活、留学国外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大家并驾齐驱,成为公认的世界级学者,许多著作发表在胡适主持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他的著作很快就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尊重,同他一开始就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关注国际学术动态有关。
1929年,傅斯年从国外回来,写信给陈垣先生。傅先生在信中说:“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之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世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傅斯年先生所谓“异国之典型”,是指欧洲汉学方面有一些杰出的学者,相比之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很惭愧。他说的“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主要是指斯坦因和伯希和两人。“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因为伯希和等人在法国巴黎。要改变这种研究中国学问中心在欧洲的状况,中国学者要努力把汉学研究的中心回到中国,外国学者才不敢轻视中国学者。这里他寄厚望于王国维和陈垣两人,“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是指王国维在日本影响很大,“先生鹰扬河朔于后”就是指陈垣先生,他一直在北平。
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陈垣先生对他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西京即日本的京都,两个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陈垣先生和当时的胡适、陈寅恪等先生都有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陈智超老师在《殊途同归——励耘三代学谱》中,介绍了三位历史学家的回忆,可以看到陈垣先生是如何激励和培养学生“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
第一位是郑天挺先生。1922年,陈垣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当时他是国学门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明清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的副校长。他在1980年的时候回忆,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院举行恳谈会,陈垣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郑先生说:“这几句话对我影响很深,一直到今天,我还经常喜欢说我们要努力,要使中国学问的研究水平走在世界水平前沿。我讲这个话实际上就是重申陈老师对我的遗教。”
第二位是翁独健先生。1928年,陈垣先生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当时他是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回忆说:“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而且正是因为受到老师的启发,因为中国的元史研究比较薄弱,所以我才开始研究元史。”后来他成为有名的元史专家,培养了一代一代元史学者。
第三位是柴德赓先生。1929年,陈垣先生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他是史学系的学生。1959年,柴先生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他经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的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钻研。”后来,柴先生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
陈垣先生1913年定居北京后,与学界有广泛的交流,十分注意国际汉学界,特别是日本汉学界的动态,随时了解日本一些重要史学杂志的目录,重要的请人翻译。他的第一篇正式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就参考了日本和法国学者的著作。陈垣先生常请人翻译日本学者的著作,上面还有不少批语。他对民国十七年日本史学界的论文进行分类统计,标明数量,从中可看出研究的重点所在。陈垣先生的学术研究在海外有重要影响,与伯希和和桑原骘藏关系十分密切。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 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希和与陈垣先生相识始于摩尼教研究。1923年4月,陈垣先生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伯希和看到此文后,即致函陈垣先生,查询有关宋元间摩尼教入福建的情况,陈垣接信后即把樊守执代为查访。1930年,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中自序:“(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此“劫录”两字表明其愤慨之意。三年后,伯希和来华,对陈垣先生此书极为推重,并与其在元史研究上有深入交往。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陈垣先生说:“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怅然。”
1917年10月,陈垣先生随梁士诒访问日本,将增订再版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线装一册赠送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并应日本学者之请,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此文,得到中外学者的称赞。12月8日,陈垣从日本大阪致友人慕元甫函,说:“拙著《元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他日所得,当不止此。”他还注意在日本收集研究资料,又说:“垣此行目的已达大半,心所欲得之《贞元释教目录》,已在西京得之,此书言景教与佛教关系有确证,惜中国无传本,唯日本与高丽有之。”“《破邪集》为明季攻击天主教之书,在中国久成禁本,其中颇多关于教争历史,为考古者所万不可缺之书,不得以其狂吠而弃之也。日本有翻印本,然亦在禁书之列,垣在东西京遍寻不获,今在大阪得之,亦奇遇也。”“唯《宋元镇江志汇刻》,此书日本尚未有传本,当仍在国内求之。”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先生的代表作,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桑原骘藏在1924年写的《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的对象;其二,氏之方法为科学的也。”桑原骘藏是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比陈垣长10岁,1931年病逝。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设有“桑原文库”。日本学者竺沙雅章认为:“陈垣的研究特色,事实上正是桑原自己的研究特色。桑原的代表作《蒲寿庚之事迹》是一部译成英文和中文的名著。”“桑原文库”藏有1924年陈垣赠送桑原的除《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外,还有《心泉学诗稿》六卷、《钓矶诗集》四卷。陈寅恪先生曾高度评价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在中外学人中的价值,1935年为此书重刊本作序时他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元西域人华化考》由美国学者钱星海和古德里译成英文并加注释,作为《华裔学志》专论第十五,于1966年在洛杉矶出版。
此外,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完成于1942年9月,是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学书,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1957年6月,教授佛教史的日本友人野上和小笠原访华,曾谈到该校教师用此书作为讲义。
陈垣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深受乾嘉学术影响,同时又注意借鉴和吸收新学的思想与方法,为国家争得世界汉学中心地位。陈智超老师知道我关注中国艺术的国际传播,特意选择陈垣先生的这两件目录手迹赠我,这是对我学术和艺术的嘉勉,也是对陈垣先生最好的纪念。我把这两件墨宝装裱好挂在书房,时时鞭策和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