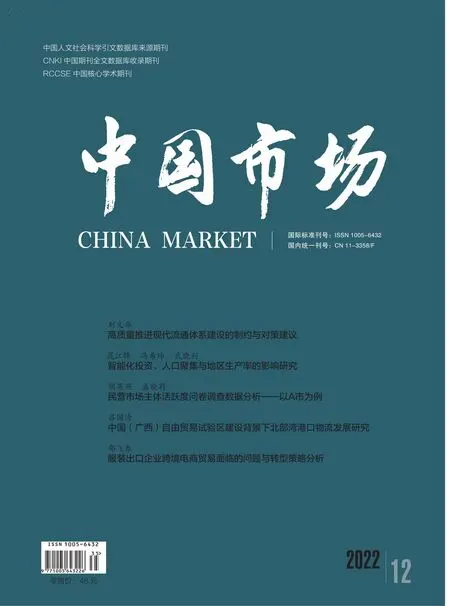论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
——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的角度探讨
陈远茵,宋 敏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1 引言
近年来,消费者在网络打车出行、外卖配送、酒店预订和购票购物等领域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经媒体不断曝光,引发热议(1)如《淘宝“大数据杀熟”翻车事件:一款洗面奶5个价,VIP比别人更贵一点》,载《互金商业评论》,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087157.html。2020年3月7日媒体曝出经用户对比发现一瓶洗面奶在天猫超市的售卖价格在不同的用户端显示不同的价格,可谓“千人千面”,最低价与最高差相差一倍多,并且天猫88vip会员购买商品时比普通用户的价格更高。。2020年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一篇打车调研报告中提及“苹果手机用户平均仅获得2.07元的打车优惠,显著低于非苹果用户的4.12元”的发现让公众对算法价格歧视的讨论再度进入白热化阶段(2)《复旦教授疯狂打车800次,发现大数据杀熟的秘密!》,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56476514_609133,2022年5月12日访问。。无论是对老用户购买同一产品或服务在相同条件下设置更高支付价格的“杀熟”行为,还是消费者负担的“苹果税”,其本质都是经营者借助算法,分析消费者信息以得到针对个人的“数据画像”,针对不同的画像实施差别化定价,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算法价格歧视行为。
不同于传统商业“看人下菜碟”的公开溢价,经营者以“算法”为技术支持实行价格歧视以攫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3)消费者剩余又称为消费者的净收益,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衡量了买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经营者通过预测消费者对于价格上限的承受范围推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消费者剩余,从而设置合适的价格。,歧视手段更加隐蔽。经营者借助算法预测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频率及消费能力以生成“各自的价格”,消费者囿于专业知识受限,难以在价格如此“通情达理”的情况下察觉到被歧视,面对算法拟定的价格,唯有接受或拒绝。即便察觉权益受损,但是由于算法拟价随变量输入的不同而快速变化,消费者难以固定价格歧视的证据[1];证明所需的相关材料由经营者掌握,经营者面对消费者协助提供证据的请求时,往往以特别优惠、商业秘密、市场供需变化等理由搪塞,因双方信息不对称显著,消费者难以提出强有力的反驳。消费者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其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权利极易遭受损害;经营者的歧视行为也因消费者作出的“自愿支付”而得到进一步掩盖,游离于监管之外。
为打破算法价格歧视的“隐身”属性,从源头遏制差异化定价,需要从算法价格歧视如何形成入手以辨清歧视隐蔽的缘由,使得法律规制有的放矢。由此,本文首先将释明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逻辑,其次在得出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实质的基础上,分别从信息收集、处理两大阶段规范经营者的信息处理行为,探讨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依据来防止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发生的可行性。
2 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逻辑
研究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逻辑,首先需了解驱动该行为的底层原因,从底层原因发端,经营者为实现该目的从事系列行为。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今迈入数字经济,经营者开展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外乎追逐利益,其中对每一单位产品或服务收取不同的价格实现“一人一价”是经营者最理想化的追求(4)在“一人一价”中,经营者通过算法预测出每一个消费者对产品所意愿支付的最大货币量,并以此决定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每个消费者的全部消费剩余。“一人一价”因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而成为经营者的理想追求。。因数字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收集消费者海量信息为基础、利用算法分析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最高价格的“算法价格歧视”使得理论意义的“一人一价”成为可能。
实现“一人一价”,要求经营者以个人信息为质料、以算法为核心驱动开展信息处理活动。第一步,收集信息。经营者凭信息服务协议、隐私政策与消费者协商,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收集的信息包括性别、常住地、地理位置等个人属性信息以及搜索偏好、浏览记录等行为信息。第二步,分析信息。运用各类算法过滤、筛选、组合收集而来的信息,为各类消费者“打上标签”,精准描绘每一消费者的“信息画像”,推测其支付意愿以及可以接受的价格上限,以期索取消费者能够支付的最高价格。第三步,应用算法自动化决策结果,实现价格歧视。对于同一产品或服务,依据消费者“画像”设置不同的价格,将拟定了不同价格的商品或服务推送给目标消费者[2]。
从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逻辑可知,经营者借助算法工具实现了“完美”的营销,既能够面对高支付意愿的消费者制定更高的定价,也能够对价格敏感的低端消费者群体机动性推送合适的价格[3],而互联网交易成为价格对比的天然“屏障”,除非消费者花费精力仔细比对,否则很难发现自己被价格歧视。从行为的本质来看,歧视性价格是经营者凭借算法过度收集、不当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而造成的结果。算法价格歧视以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等权利为外在表现,实质侵害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4]。基于此,从源头上防范算法价格歧视,可以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入手,规范经营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2021年8月20日,专门规制个人信息保护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通过,其中第24条第1款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正式将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纳入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范围。笔者将从《个保法》(5)《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简称,若无特别说明,本文以下称《个保法》均指《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目的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的帝王条款[5]为着眼点,研究经营者的个人信息处理(6)此处的个人信息处理为广义理解,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应用等。下文若无特别说明,个人信息处理均作广义理解。规范。
3 收集信息限于实现目的的最小范围
经营者以个人信息为“生产资料”实施差别化定价。经营者作为运用算法系统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主体之一,理当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者群体所应遵守的规范。从个人信息收集、处理的运作机制来看,可知一切信息处理活动围绕着处理目的进行。消费者信赖相关信息处理者会以其告知同意的目的为限处理个人信息,并透过处理者告知的目的知晓信息去向,预估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损害,[5]最终在利益与风险的权衡后同意处理者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相应地,要求处理者开展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守契约诚信,回应消费者信赖,以处理目的为限实施相关行为。《个保法》第6条“目的原则”明确表述信息处理活动应受目的的限制,贯穿信息收集、分析与运用的全阶段,常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的帝王条款而使用。基于此,笔者以为,对经营者信息处理行为的规制可以立足于第6条条文开展分析。
《个保法》第6条第2款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要求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为实现目的所必需。“处理目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追求的处理目标和结果,对于目的的实现,消费者与信息处理者追求的结果各异。消费者期望其提供的个人信息能够经过处理使其获得相应的信息产品或服务,处理者希望通过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获取经济利益,双方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业务功能上达成一致,业务功能成为双方联系的桥梁,因此,依照“处理目的”而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实际为依照业务功能开展活动,对目的的要求实为对业务功能的要求。
按照《个人信息安全规范》(7)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业务功能以基本业务功能和扩展业务功能为两大区分,基本业务功能指提供消费者签约时最期望获得的产品或服务,如地图导航、即时通信等;扩展业务功能则为实现基本业务功能之外的其他目的,如定向广告推荐、精准新闻推送等。算法价格歧视是经营者收集信息的隐藏目的,不属于上述业务的任何一种,事实上经营者不会宣称自己“非法性”的目的,而是以实现个性化服务等笼统目的请求消费者概括授权,实现最大限度的信息收集。为防止消费者过度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经营者应当遵循《个保法》最小收集范围之规定,收集个人信息的类型直接关联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没有相应信息的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就无法实现;收集信息的频率和数量应为可以实现目的最低频率和最少数量;收集之后应遵循最短存储时间(8)GB/T 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依据《个保法》第13条之规定,收集个人信息需取得个人的同意。个人同意既是信息处理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也是建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任的关键,消费者难以接受没有目的或是超越“告知目的”的合理范围而收集自身信息。最小收集范围即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且属于实现处理目的所必不可少的范围。对前文“目的”的理解,应当限于经营者同意的范围,经营者围绕消费者同意的目的进行相关活动。
如前文所述,算法价格歧视的隐蔽在于算法的不透明性,由此,突破算法“屏障”、提升个人信息处理的透明度是关键之策。在信息收集阶段,为了保证消费者作出真正的同意,经营者应当具体表述“处理目的”,以便对方了解实现目的所必要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型及收集信息后的处理去向。为提高信息处理的可理解性,在内容上,经营者可以告知消费者其结果是基于何种信息分类标准、方法模型作出,披露操作的逻辑程序及其他有意义的信息;在解释方法上,可以使用因果解释、反事实解释等方法进行解释(9)因果解释方法,即帮助消费者识别输入变量与特定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事实解释方法,即改变输入的前提观察输出结果的不同以理解信息的处理。;此外,可以运用技术手段将信息使用的步骤可视化呈现,如在弹窗中运用文字导读、视频演示等形式清楚展示。对于个性化服务等容易模糊表达、概括授权的扩展业务功能,收集信息时应当在信息使用的具体场景中再次获取消费者的单独同意,且逐一告知消费者需要收集的信息,获得信息获取权限的逐项同意。实践中,判断某一场景收集个人信息是否符合“最小范围”,可以比照《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10)《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就30余种常见服务类型所需的最小必要个人信息作了详细列举,载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21-03/22/c_1617990997054277.htm,2022年5月12日访问。出具的示例进行评估。
4 处理信息直接相关处理目的、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我国《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11)GB/T 39335—2020,《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将个人信息处理的权益影响概括为四个维度,维度之一的“引发差别性待遇”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不公平对待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导出歧视性的决策结果。算法价格歧视以算法拟定歧视性价格,构成对该条款的违反,算法价格歧视既然是个人权益损害类型的表现之一,理应受到信息处理规范的规制。
《个保法》第6条第1款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要求个人信息处理围绕目的开展,采取的处理方式是实现其处理目的的唯一方式,或者是对个人信息权益侵害风险最小或损害最小的方式,引起的风险与消费者获取的信息服务利益符合一定比例[6]。个人权益影响对应个人信息权益遭受的侵害风险或损害,以“影响最小”凸显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同时“影响”作为程度评价语词有利于信息处理行为在具体场景判断的灵活运用。
为了正确适用《个税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需要理解“直接相关”与“影响最小”的含义。就“直接相关”而言,如前所述,个人信息处理的系列活动围绕处理目的开展,处理活动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是确认经营者的行为符合目的原则的第一步。我国《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个人信息控制者“使用个人信息时,不应超过与收集个人信息时所声称的目的具有直接或合理关联的范围”;欧盟第二十九条资料保护工作组第3/2013号意见书提出:个人资料必须为特定的、明确的及正当的目的而收集,以及不得作出与该等目的不相容的进一步处理。相容性根据个案进行评估需特别考虑以下要素:一是初始收集目的与进一步处理目的的关联;二是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境及用户对其信息被进一步使用的合理预期;三是个人信息的性质及进一步处理对用户的影响;四是处理者是否采取保障措施以确保信息被公平处理及防止任何对用户的不利影响(12)欧洲联盟第二十九条资料保护工作组第03/2013 号意见书,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办公室官网,https://www.gpdp.gov.mo/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12&id=12,2022年5月12日访问。。综合来看,“直接相关”要求的关联度是指处理活动与处理目的具有合乎预期的联系,以一般理性人在阅读条款时的认知标准判断处理活动是否有助于目的的实现、是否为消费者同意的目的所涵盖。“直接相关”注重处理活动对消费者权益的影响,要求处理者进行信息利用时遵照处理目的,后续的处理活动不能创造出与实现目的不匹配的风险或者提升风险[5]。
就“影响最小”而言,在经营者的信息技术和安全防护技术所能实现的范围内,要求处理的个人信息应为最低识别度的信息、处理信息的频率最低、处理的信息数量最少、处理活动限于最小的共享范围;在实现处理目的后应当及时删除、销毁信息,恢复到个人信息未进入处理活动前的初始状态,擦除个人信息在相关应用程序、网络平台等的存储记录;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全过程,运用符合处理者信息技术水平的数字科技手段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篡改,例如采用匿名化措施、分散存储信息等方式。同时给予消费者自主决定退出处理活动的权利。
5 结论
最新一期《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3.0%(1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载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t20220225_71727.htm,2022年5月12日访问。,网络算法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人。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在“算法”的支持下力图掠夺全部的消费者剩余以转化为经营者利润,此举不仅直接损害消费者的权利,令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土崩瓦解,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作为算法负面利用的表现,引发公众对“算法黑箱”(14)由于算法部署者知悉掌控核心算法以及算法逐渐具备自主学习能力,从输入至输出的过程由于难被公众理解往往被描述为“黑箱”( black box) 。参见杜小奇.多元协作框架下算法的规制[J].河北法学,2019,37(12):176-190.的愈加担忧,公众对于信息利用的怀疑将阻碍大数据的创新发展。因此,有必要规范经营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防范算法价格歧视的发生。通过分析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逻辑可知,该行为的本质是经营者对消费者信息的过度收集与不当使用,从歧视形成的源头入手,在风险防范阶段设置一道“阀门”,以保护消费者的信息权益的手段达到保障消费者权利的目的,有助于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个保法》第6条“目的原则”起到了贯彻立法目的、立足个人信息保护的代表性作用,笔者选择该条款开展论述分析,希望通过对该原则的理解为经营者的个人信息处理规范提供方向指引,也为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提供一个值得研究的角度。
对算法价格歧视的法律规制关涉市场经济活动对于算法和个人信息的使用,未来的互联网生态可能就算法和个人信息使用开拓出其他经济、人文和科技等发展的议题,对于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探讨可以作为一个深入研究算法利用和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契机,期待未来数字时代延伸人类发展的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