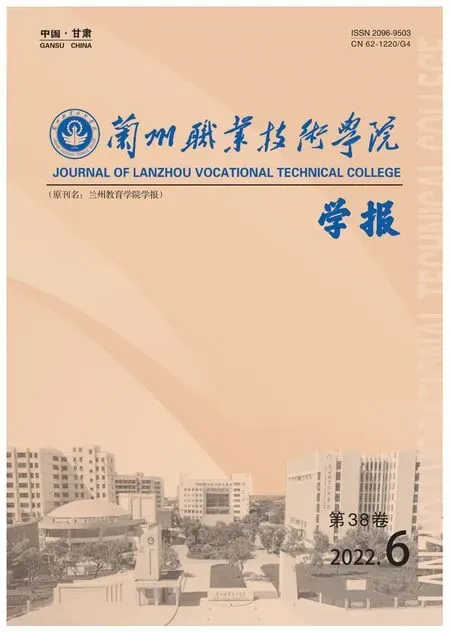清代部费陋规及其根源探析
张 晨
(南昌工学院 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8)
官场陋规这一吏治痼疾在清代尤为突出。中央有部费,布政司、按察司有司费,巡抚衙门有院费,道台衙门有道费,知府衙门有府费……公务办理中几乎无事不费,给国家治理带来极大挑战。清政府通过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集团实现统治职能,随着皇权不断削弱,制度缺陷逐步显现,表现为治理能力不足、政策难以施行、行政效率低下、贪腐大行其道等症结。因此,寻求清朝部费陋规的治理之道,需对其产生和依存的制度根源进行深入探析。
一、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
清初康熙和雍正朝分别设立南书房及军机处等辅政机构,使皇帝完全掌握执政大权,形成稳固的集权统治。中央通过以六部为核心的政务机构掌理地方政务。由于行政办公过程文牍繁冗,办事书吏掌握了审批核查实权,产生了借公务办理挟制地方索要部费的可能。
(一)行政办公经费严重不足
国家财政划拨中央机关的办公用费及俸工银非常有限。如吏部筹办京察大典,划拨经费只有三百两,办事书吏只能先设法赔垫,京察之后再借办理外官考课“大计”的机会,从地方官身上索取部费填补缺口,“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1]。
(二)文书制度过度因循“例案”
六部行政过程文牍繁冗,部中官员却多不习部务,因此非常依仗熟知例律和成案的办事书吏,从而使部吏掌握行政审核实权,产生弄权索费之弊。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各部司官不习吏事,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故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六部亦曾设法革除书吏弄权之弊,如令部中笔帖式学习部务以分胥吏之权,但这项举措未见收效,公事之权仍在吏胥。
(三)文牍案卷管理不严
六部档案文牍均由书吏管理,为了达到长期利用例案挟制司官的目的,部分书吏甚至将部中文档私藏家中,使下任官员无法查阅,只得对其惟命是从。由此,书吏任意援例假公济私,或伪造、窜改、抽换、毁坏文书档案,扰乱规范政务秩序,增加地方的财政负担。
国家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设官分职,建立行政制度和规范,颁布政令来履行统治职能,形成了稳固的集权统治,掌握节制地方大权,其特点是导致中央部门权力极大,而地方政府自主权很小,六部书吏得以在公务办理中恃权索费,这是部费问题出现的行政制度根源。
二、僵硬的财政制度
清代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并无清晰划分,通过设立以奏销为中心环节的严密审查制度,确保财权高度集中。但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比例严重失衡,赋税支配权完全由中央掌握,“国家的财政收入首先要满足中央的需要,因此,作为维正之供的田赋,大部分都被地方运送至京都,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存留下来供地方开支”[2]。这种分配方式极大限制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性,导致弊端出现。
(一)地方财政收入严重不足
因清代中央与地方不合理的赋税起运和留存比例,大部分钱粮上交中央,使地方政府可供支配的赋税非常有限,收入长期缺乏弹性,地方经费自主权严重受限。康熙元年(1662)规定:“州县钱粮先尽起运之数全完,方准存留。”这种做法弊端很大,地方财政经费无着,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治理职能的发挥,地方官吏为筹集经费,出现了私征、加派加剧,挪移侵欺库帑的现象,造成钱粮亏空的恶果。
(二)地方财政自主权不足
中央为强化户部权威,推行全国统一的法规条文且长期未进行校对增补,导致忽视各地各区域差异而弊端丛生,奏销程序与地方实际脱节。乾隆十年(1745),耗羡归公已经实行多年,地方存留耗羡银的任何动支都必须报部,动辄遭遇部驳,导致耗外加耗,孙嘉淦奏报:“每有动支,无论多寡,必先报部,不准则不敢擅动矣。随同正项造册报销,不合例则驳令追赔矣……然则耗成正项,耗外加耗之弊。”[3]
(三)地方赴京办理奏销需缴纳部费
地方办理钱粮奏销必须备好部费以免遭部驳。部驳的理由很多,一是奏销册内账目不符,不合奏销条例。因地方财政用费不足,各类预算外支出很多,钱粮奏销册内数字确实存在不符情况;二是即便册内数字吻合,部内书吏也会恃权借故驳回,索要部费。因此奏销事务中部费银必不可少,所谓“上司各项陋规等于正供,不能短少”,造成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
可见,由于清代地方财权总是被强势的中央财政所剥夺,从中央到地方均以陋规体系应对不合理财政体制,在中央用部费陋规冲破规范的奏销制度;在地方通过私征加派增加收入,以耗羡、节礼填补公费支出的缺口,弥补钱粮亏空。僵硬的财政制度成为滋生陋规的土壤。
三、选官任用制度缺陷
选官任用制度包括官员选任和监管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制度缺陷也源于此。
(一)科举选官不习政务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愈加严格和程序化,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典籍,逐渐与时代和政务实际脱节,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往往缺乏实际任事能力。例如,部分中央部院衙门官员,起家文史,不习律例、司法、会计等部务,只能全权倚仗办事胥吏,李慈铭云:“部寺长官不知曹务,惟任诸司,诸司一委之吏。”
(二)捐纳入仕侵蚀吏治
国家在财政困难的时候往往通过捐纳取官增加财政收入。据韦庆远的《中国官制史》记载,康熙十三年(1674),朝廷因用兵平定三藩之乱,宣布开捐纳官,三年间便有五百多人捐为实职知县,占全国知县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种做法虽然可解一时之经济困难,但这批人员素质堪忧,花钱买官势必会在任上利用职权多方牟利。朝廷后来虽然屡次禁捐,但清朝中后期捐纳之风依然盛行。捐纳任官变官场为市场,从官员体制内部侵蚀吏治,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
(三)监管机制效用虚化
国家虽建立起多重监察网络,设监察机关都察院及六科,并颁布《钦定台规》等监察法规,但监察机构作为皇权的附属,监察者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群体之一,因此无法有效实施监督职能,监察机构形同虚设。
1.言官隐忍不言,不愿承担风闻弹奏风险
顺治谕督察:“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近来各官弹章其中多摭拾塞责,将他人已经纠参之事随声附合,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4]康熙指斥:“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人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5]
2.地方上监督权“责归督抚”,出现瞻徇包庇
地方上公务的监督权“责归督抚”[6],在任日久难免对共事官吏产生瞻徇包庇的情况。清朝《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八年(1651),吏治敝坏……至于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转换上下,与吏役通同作弊贻害百姓。督抚不行纠察,大乖法纪。”[7]更有甚者,督抚只检举地方上的小官,真正的巨贪官员反而受其包庇。魏象枢云:“(督抚)所劾不过小官,苟且塞责,大贪大恶反多徇纵”。
3.官员任期流官制度的弊端
清朝为监管汉官,唯恐其任期过长而培植地方势力,因此在地方州县和各级部门间实行“流官制”,而且“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县官为例,“平均任期从清代早期的1.7年缩短至后来的1年,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因任期缩短,任职期间既不可能钻研例律,也难以确知各胥吏的人品和背景,也难以对其进行节制”[8]。
4.陋规名目繁多,官吏共同分润
陋规取自于民,但地方官绝对不会独享,而是将其中很大一部分陋规收入以规礼、规费的名义致送上级,同流合污。管官与犯官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分润,在利益的驱使下敷衍塞责,因而更加难以监控。官僚系统从上至下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监管制度终成一纸虚文。
四、低俸制的局限
所谓“俸禄所以养廉也”,俸禄不敷使用必然会造成官吏恃权谋利、贪婪需索的恶果。张纯云:“臣闻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9]
(一)官吏俸禄微薄不足使用
清代沿袭元明以来的职官低俸制。顺治十年(1653)正式颁行俸禄定额,作为沿用定例。在京文武官员年俸禄为:一品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一钱。可见清代官员的薪俸待遇极其低微,仅凭俸银几乎难以维持生活与用度。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奏到:“(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粮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10]
本已微薄的俸禄有时还不能足额兑现。如吏部司官何刚德称:“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尚可不换也。”
(二)官员支出用项甚广
地方官的开销用项繁多,主要包括:延请幕友、赡养家小、接济亲属,公务应酬、人情往来,本人车马、衣饰、饮宴、仆从等。佐伯富云:“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官多数均家口甚众,日常开支已极浩繁,而且还须负担未领俸给之胥吏的费用,及衙门的一切设备、消耗等费,那不是一年不满二百两的少数俸薪所能支付的。”[11]清代低俸制与官吏支出需求的巨大差距,必然导致谋求俸禄外收入。顾炎武云:“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之二三。彼无以自赡,得而不取诸民乎?”因此,寻求陋规收入是势之必然。
(三)奢侈之风与物价上涨的影响
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清代中后期崇尚奢华的风气渐渐兴起。康熙十六年(1677),给事中徐旭龄称:“试观今日之池馆园亭、歌舞宴会,视顺治初年不止十倍。”乾隆在统治后期,他频繁狩猎、出巡、举办庆典活动,其“供需之侈,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时”,上行下效加剧了官场的奢侈腐化。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中后期物价也开始逐渐攀升,乾隆时物价出现急剧上升的局面。嘉庆十九年(1814)罗桂芳云:“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弊轻己甚矣。”照他的说法,康雍乾一百多年间,物价翻了三倍[12]。乾隆谕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日用日间加增。康熙年间,朕在冲龄时即闻乳保等物昂贵,度日艰难之语,今又七十余年,户口滋生较前奚啻倍蓰?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势断有所不能。”[13]
物价持续上涨,银两不断贬值,官员的俸禄却始终维持原额,这使其更加不敷使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乔治·斯丹东称:“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员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14]为改变这一情况,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但官员依然入不敷出。乾隆初年,两广总督马尔泰称按察使养廉银不足用,“案犊繁多……岁延幕友多人,束修供给,费用稍广,原定每岁养廉银六千两实属不敷”[15]。各级官吏最终不得不依靠陋规系统,千方百计地寻求体制外收入,低俸制实为滋生部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立法缺失与量刑不确定
(一)部费陋规行为立法的缺失
收受部费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大清律例》中对此并没有针对性的条目,罪与非罪之间界限十分模糊,只在《刑律·受赃》中“官吏受财”“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两律下,以附例的形式对部费、程仪、土仪礼物、门包这四项陋规个案作了有罪规定。
“官吏受财”律下,包括两项内容:一是部院衙门书吏收受部费。雍正年案例:“书吏指称部费招摇撞骗,知情朋分银两者,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乾隆五年:“各部院衙门书办有辄敢指称部费,招摇撞骗干犯国宪,非寻常犯赃可比者,发觉审实即行处斩,为从知情朋分银两之人,照例发往云贵两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二是上司收受属员下程。乾隆五年规定:“凡上司经过,属员呈送下程,及供应夫马车辆一切陋规,俱行革除。如属员仍由供应、上司仍有勒索者,俱革职提问。若督抚不行题参,照例议处。其上司随役家人私自索取,本官不知情者,照例议处。如知情故纵,罪坐本官,照求索所部财物律治罪。”
“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例下,亦有两项规定:一是接受部署土仪礼物,“若接受所部内馈送土仪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若因事而受者,计赃以不枉法论。其经过去处供馈饮食及亲故馈送者,不在此限”。二是家人收取门包,“凡出差巡察之员,所到州县地方,如有收受门包,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该督抚不行查察交部议处”。
户律中对惩处漕粮征收中普遍存在的陋规积弊作了处罚规定。“踢斛淋尖”一条有:“踢斛淋尖,多收斛面者,杖六十。若以附余粮数,计赃重者,坐赃论。”[16]
值得留意的是这四条关于部费、程仪、土仪礼物、门包陋规的律例都是在雍正年间制定的,之前的顺治、康熙两朝都没有相应的立法,乾隆朝及以后,在针对专项陋规的立法方面也无新的建树。
(二)量刑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在量刑方面,对于陋规案件的处理并没有一定之规,因人、因事或全凭皇帝意旨,宽严不一,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如康熙朝噶礼贪污案,噶礼在山西任上推行以火耗填补亏空,实际上却将四十万两耗银贪墨入己,直至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江苏巡抚张伯行抵牾,酿成朝野轰动的督抚互参案,这才揭发出之前的陋规贪贿案[17]。雍正五年(1727),巡察御史博济勒索驿站规礼,被立即革职交由当地大员审理具奏;雍正七年(1729),原任山东巡抚塞楞额,“既不能禁约属员,革除陋规,又复纵令家人索取门包,被处以绞刑”[18]。乾隆在处理性质相近的陋规案时,处罚明显轻重不一,例如台湾海口陋规案和厦门陋规案均涉及地方要员,地域也都在福建省沿海一带,但前案只处理了十几名涉案官员,主犯闽浙总督杨廷璋竟获从宽处置,还“著恩赏其来京效力”;后案的审理却用了五年多时间,涉及百余名官员,勒令追缴款项一百二十九万余两,阵亡及病故者要由家属代其赔还,负有连带责任的上司也要摊赔。两案相较,可见执法之随心所欲[19]。
因缺少针对陋规行为的专项立法,案件处理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援引,有限的律文条例根本不足以应对层出不穷并且牵涉愈加广泛和复杂的陋规案件。在“乾纲独断”以言代法的时代,审理处罚从宽从严都依据统治的需要,或因时因案而量刑不一。立法的缺失和执法的随意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以及对部费陋规的威慑惩戒作用。
综上所述,清代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制度缺陷导致了部费陋规的出现与长期存在,因此必须从制度根源上进行改革与完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杜绝官员滥用职权,从而提高国家机关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