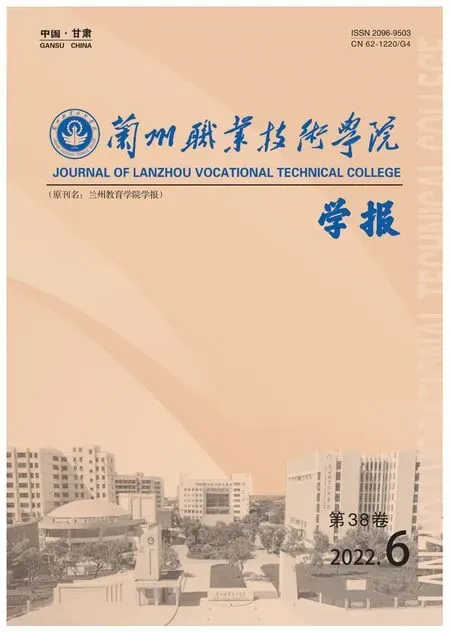论孙频中篇小说集《盐》中的女性意识
李改婷,黄菲菲
(河北传媒学院 a.国际传播学院; b.中国语言文学系, 河北 石家庄 051432)
孙频,女,1983年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县。她的文学创作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延续严肃风格,关注个体命运和人生,多以刻画女性形象为主,中篇小说集《盐》是其代表作。《盐》由六篇小说组成,主要揭示女性的生存困境,探讨女性的出路。
一、《盐》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孙频在小说中直白地叙述男女之间的情爱过程。通过对性事的描写来表现女性意识,表现出性观念的苏醒,由此凸显独立的女性精神,寻找女性的自我价值。
(一)苏醒的性观念
“贞洁观作为传统男性话语对女性的单向设置,……以几千年的长龄沉淀为人们的一种社会心态和文化心理。”[1]但是,《盐》中的六篇小说都通过描写男女之间的性事对传统的“贞洁”提出了极大的质疑。孙频利用“性”这一本能使笔下的女性获得了尊严,展示出人性。
《乩身》中的常勇从小就被伪装成男性,但从本质上来讲她还是一个女人。她想做回真正的女人,她希望通过他人的强奸来证明自己的女性身份。《东山宴》中的采采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少女,却宣扬继父强奸自己,村里人猥亵自己,但这些都是她内心的幻想。面对来家里做棺材的小木匠,她内心充满渴望。采采的性观念是懵懂的、直白的,是她自我成长的表现。《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杨国红主动勾引李天星,但是她并不沉溺于其中,她以对李天星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作为获取性行为的报酬。杨国红的性观念是理性的、独立的,是她与李天星进行的等价交换。《无相》中的于国琴性观念苏醒得较早,她的母亲在家里做拉偏套的生意,让她对性事十分熟悉。在廖教授提出看她的身体时,她的反应极为强烈,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侮辱。《因父之名》中的田小会,14岁就遭受学校多位老师的强奸,为寻求保护,15岁和残疾老人同居。她把性行为理解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也理解成对离家出走十年突然回归的父亲的报复。《祛魅》中的李林燕具有诗人的品味,她将性看做一件浪漫的事,认为性应该与爱情一同发生,所以她与外籍诗人的一夜情成为她坚守爱情的证据。后来她鼓起勇气与诗人男友未婚同居,再与自己的学生结婚,她依然在心中坚守爱和性的完美统一。
(二)独立的女性精神
孙频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在意自己的感觉,遵循自己的内心。
1.坚强的母亲形象
《东山宴》里的寡妇白氏一生操劳,最终躺进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棺材里。她的一生都在“扮演”母亲的形象,为了儿子,为了孙子,甚至为了第二任儿媳带来的“拖油瓶”采采,她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承担了生活中所有的苦难。生活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外在表现,白氏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生存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和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迎难而上,表现出精神的独立性。
2.执着的“剩女”形象
执着“剩女”形象的代表是《祛魅》中的李林燕。大学时期,她屡次发表诗歌,拥有众多的崇拜者,这让她清高孤傲,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形成了独立的意识。但这种气质同时也让她陷入了孤独的境地,直到和旅美作家相识,她才遇到了自己所谓的真爱。李林燕有着诗人的独特气质,坚持追求理想爱情,在28岁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旅美作家欺骗,但是依然等待着诗一样的爱情。其后,作家余有生让她再次看到了自己向往的纯洁爱情,可惜她又被现实打败。这时的她看淡了生活反而活得愈发洒脱,不再追求华丽的外表,而是更加遵循自己的内心。42岁时,她嫁给了自己的学生蔡成钢,因为丈夫的背叛她走向绝望,杀害了丈夫的情人。李林燕女性精神的独立性就表现在她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绝不向生活妥协而随波逐流,她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内心,坚守着自己的爱情观念。
3.理性的妇女形象
《我看过草叶葳蕤》里的杨国红是一个理性的女性形象。她与李天星第一次见面时就断定对方会同意她的“邀请”。一开始他们之间不存在爱情,后来她逐渐爱上了李天星,与丈夫离婚却不要求李天星和她结婚,因为她离婚的真正目的是要拥有自由,实现自己的女性价值。杨国红拥有独立的精神,不甘心做一个没有爱的女人,把全部爱意都用在了李天星身上,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了自己和李天星,她通过这样的行为表现出了独立的女性精神。
白氏、李林燕和杨国红虽然经历不同,但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处事方式,面对困难不会退缩,坚韧不拔,充满了独立的女性意识。孙频通过这类女性人物的塑造,向读者表达了独立、自强、遵从自我的女性精神。
(三)清醒的价值认知
《盐》中女性人物的底色大多是苍凉、孤独的,但是这些人物又都对自己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做所为的后果,并愿意为之负责。
《东山宴》中的白氏秉持女性身为“人母”的角色,将自己的价值定位为养育儿子、拉扯孙子、养活自己。白氏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母性,并且将自己的母性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粪坑里的鲇鱼,白氏都散发着母性的力量,“母亲”就是她对自己价值的认知。
《乩身》中的常勇认为只有被强奸时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女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她无法通过“性”而获得生命价值的时候就处于崩溃绝望中不可自拔。后来她在乩身中找到了对自己新的认知,她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地方自己只有装神弄鬼才会有生存的意义。杨德清死后,常勇在波街拆迁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阻挡了正在进行拆迁的挖掘机,用死亡展现了自己的价值。
《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杨国红对自己的价值一直非常清楚,从百货大厦的售货员开始到之后自己经营文具店,都是她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杨国红所做的一切是她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她想走出小县城,但是也清醒地知道这已无可能,于是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全部交付到李天星的身上,一直鼓励他、帮助他。杨国红对自己的价值定位为李天星回家后的港湾,所以她给对方关心和温暖,不需要回报,只为让他可以代替自己离开这个小县城,在外闯荡出自己的天地。
二、《盐》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手法
孙频短篇小说集《盐》中的女性或生长在沉滞的山村,或生活于落后的小镇,深受乡村观念的影响。孙频将这一特点转化为优势,通过对社会时代背景的描述、对男性形象的弱化,以及意象象征的使用,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女性意识。
(一)社会时代背景反映女性意识
孙频笔下的女性大多来自于闭塞、落后、贫困的乡村或是县城,《盐》中大多数故事的发源地都是吕梁山这样一个偏远村庄。书中的人物也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群体:渴望得到女性身份认同的盲女,将所有重担集于一身的寡妇,遭到男人背叛和旁人讥讽的女教师,被屈辱和仇恨支配的女大学生,以及缺少父爱的单亲女儿。这些女性人物虽然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县城,并受到落后思想的影响,但是她们勇于跳出精神的樊笼,展现出逆境中的女性意识。
《乩身》中的盲女常勇受家人遗弃后,被年迈的爷爷收养,一直用男性的身份生活,因为她一旦暴露自己的性别,就无法避免来自异性的侵犯。爷爷去世后,她小心翼翼地活着,谨记爷爷的教导:
一堵墙一扇门根本挡不住别人,你不知道,你以后其实就是时时刻刻都活在灯火通明的戏台上了。你做什么都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有让别人相信了你是男人,你才能活下去啊。[2]8
常勇的不幸,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残疾,另一面来源于落后的思想观念——以男性为尊的社会常态,这是造成常勇痛苦的根源,也是让她一生都生活在虚假身份中的根本原因。直到最后,她坐在雪地中死去,她的身体曲线被满身的汽油勾勒出来的一刻,她才活成了自己。以死抗争是她对命运的反抗,是她自尊的表现。
《无相》中,封闭的山村养育出一个个以“拉偏套”生意供养全家的“妓女”,在山村里这样的职业是受人尊重的,所以于国琴的母亲也就成为这些“妓女”中的一员,成为支撑全家生活的经济支柱。于国琴考上了大学,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做“拉偏套”生意的母亲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耻辱,是她自卑的根源。她认为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着妓女的基因,这让她失去尊严,感到不安,尤其是她同意廖教授欣赏自己的身体后,这种耻辱感达到了顶点。于国琴的女性意识表现为隐忍、成长,多年后,她理解了廖教授当初的行为,所以她在“奇异的声音里”脱光衣服,将她的身体渐渐淹没在夜色里。
落后的社会环境会让女性变得脆弱、自卑,孙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她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创造出勇于做出改变的女性形象,并将自己的女性意识赋予这些角色,通过现实的社会背景,反映出自强不息、独立坚忍的女性意识。
(二)男性形象的弱化凸显女性意识
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男性主体往往通过赋予男性“正面” 品质,同时赋予女性相对应的“负面”品质,来将女性边缘化[3],但是《盐》中对男性的描写少之又少,甚至存在缺失的现象。即使出现男性,他们也没有呈现出阳刚、坚强的气质,而是表现为一种残缺、弱化的“矮小”形象。
1.残缺的男性形象
孙频小说常常出现残缺的男性形象,在《盐》中主要表现在《乩身》这篇文章中。男主人公杨德清无家可归,他偷盗,他丧失男性功能,这都使得男性形象呈现出不完美性。孙频利用杨德清这一残缺的男性形象引导常勇认识到自身的女性身份和人物价值,凸显出常勇的女性意识。
杨德清的存在是帮助常勇成长的,小说中没有对杨德清进行细致的描写,只是简单地叙述了他的生平。孙频以一种残缺的男性形象作为陪衬,但是绝对不让男性掌控整个叙事,她从女性视角出发,更好地展现了具有女性意识的盲女形象。
2.弱化的男性形象
如果《乩身》中的男性形象是一种附和与陪衬,那么《东山宴》中的男性形象则被无限弱化。女主人公白氏的生命里,出现过四个男性形象,全都软弱矮小,与彪悍高大的白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部小说中出现的几个男性形象完全居于从属地位,退化成为反衬角色,在文中仅仅起到衬托的作用。
可以说,由于村内环境的落后,孙频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所展示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不健全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中的女性角色更加鲜明。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随波逐流的现状使得男性角色无奈而软弱,最终凸显了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
《盐》这部小说集中的六篇小说多从女性视角进行叙事,只有《我看过草叶葳蕤》这篇小说是以男性视角的叙述,但是这篇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与传统中的男性形象不同,他软弱、胆小,虽豪情万丈却一事无成,只有在女人的帮助下才得以生存。作者对男性形象的弱化主要是为凸显杨国红敢作敢为、勇于担当,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
总的来说,《盐》中的作品几乎不存在完美的男性形象,孙频利用男性形象的弱化和变形,进一步突出其中的女性形象,凸显她们的女性意识。
(三)使用象征意象表现女性意识
孙频的小说充满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也为其作品增添了浓重的文学色彩,其中的女性意识也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意象表现了出来。
《乩身》中常勇炕上油毡上的牡丹花恰恰象征了常勇本人。牡丹花从开始的幽静、平和到后面的怒放、妖艳,再到最后变得祥和宁静,这都暗含着常勇性格的变化。常勇用生命建立女性意识的时候,油毡上的牡丹花呈现出一种祥和感,仿佛真的变成了常勇的“莲座”。
《东山宴》则将粪坑里的鲇鱼作为白氏的真实写照。从外地带回来的鲇鱼被养在粪坑里,依然可以长得个大肥美,恶劣的环境并不能对它造成影响,反而使它更加放肆地生长,白氏就是如此。她所处的环境贫穷落后,生活的不如意并没有打垮她,她努力生存,不比村里任何人活得差,像粪坑里的鲇鱼一样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白氏死后,大家以纪念其的功德为由,将粪坑里的鲇鱼全部捞出来吃掉了,鲇鱼和白氏一同消失在水暖村。白氏如同鲇鱼一样在困境中生长,表现出她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独立自强的女性意识。
《无相》中的象征意象是于国琴手中的饭卡。饭卡是于国琴和廖秋良之间的纽带,也是压在于国琴心上的石头,使她无法拒绝学校让她去照顾廖秋良教授的任务,同时也让她难以拒绝廖秋良欣赏她的身体的请求。毕业时于国琴离开学校,这张卡也交回学校,她的这段经历自然埋藏在了这张饭卡中。对于于国琴来说,这张饭卡精打细算地使用,烫手山芋般的羞耻感,以及最后交回学校,都让她的心灵经历了炼狱般的折磨和如释重负的解脱。她把卡里的三十二元钱连同饭卡交回学校,意味着于国琴由开始使用饭卡产生的羞耻终于得到释怀,她理解廖教授的行为,也说明她女性意识的逐渐成熟。
《祛魅》中的象征意象是窑洞。“窑洞”与前几篇象征意象不同,它意味着李林燕对自己的束缚,意味着李林燕将自己关在心中的“窑洞”内。窑洞是李林燕的精神寄托,是她逃避外界对她指指点点的“安全屋”,更是她憧憬爱情发生的地方。直到丈夫背叛她并寻求她的帮助时,她终于走出窑洞,用斧子砍向第三者的脖子。李林燕走出窑洞,标志着她解开了对自己长久以来的束缚,直面生活的打击,表现了她的女性意识。
象征意象的使用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加深了小说的意蕴,小说中的象征意象都与其中的女性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凸显了其中的女性意识。
三、《盐》中女性意识的文学价值
孙频的小说集《盐》运用多种手法表现女性意识,对女性的生活现状进行剖析,引发读者对底层女性生存困境、自我救赎的深层思考,呈现出极强的文学价值。
(一)剖析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
孙频的作品从社会底层人物出发,揭示了她们的生存现状,尤其对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剖析,这种困境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在《盐》中,孙频用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多位精彩的女性形象,对她们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描写。孙频笔下的女性多出生于社会底层,所处的环境愚昧落后,这是造成作品中女性人物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这些女性又具有身体或者精神上的残缺,包括残疾人群、孤儿、寡妇、单亲家庭、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孙频通过塑造这些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揭示了社会现实问题,剖析了现代社会中底层女性不如人意的生活状况。同时,底层女性也陷入到极深的精神困境中,这主要来自于男尊女卑的世俗态度和固有的社会观念。《乩身》中的常勇之所以多年来都女扮男装,就是因为要避免男人对她的侵犯。这样的做法透露出一种“女性好像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而存在”的观念,只有“成为”男人,才可以免受侵害,“男人”这个名词既是保护又是枷锁,“男性”身份将她的女性欲望牢牢压制,她既害怕又渴望挣脱这一身份,最终导致她的自虐行为:爱上了强奸她的男人。
《东山宴》中的儿媳不能认识到女性自身的独立性,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用婚姻来给予自己安全感,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无法脱离“男权社会的辅助品”这一定义。
《因父之名》中的田小会生活在父爱缺失的环境中,这使她的成长方向发生了变化,被老师强奸,母亲偷情对她的心理产生了不健康的影响,她需要寻求保护,致使她和一个老人同居,呈现出一种用性连接的扭曲的恋父情结。
《无相》中的于国琴凭借努力考上了大学,因自己的生长环境和饭卡里每月如期增加的资助金而感到自卑,以母亲“拉偏套”的职业而感受到耻辱,她无法摆脱这既定的事实,只能将它以诉说的形式宣泄出来,通过对母亲的“出卖”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廖教授理解并尊重于国琴母亲的职业,同时也尊重于国琴,只是他认为男性对女性最大的欣赏和爱慕就表现为“对她身体的崇拜”。当廖教授提出要看于国琴的身体后,她出于回报教授对她的馈赠,将衣服一件一件脱了下来,她好不容易挽回的一点尊严也如同这衣服一般再次滑落到地上,难以捡起。于国琴这种妥协又对抗的状况是女性面临的复杂困境,她们一边想自我独立但又无法摆脱历史惯性和文化惰性这些根深蒂固的影响,这就让女性在精神上担负了双重压力。
女性的生存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固有观念,女性的依附意识,都使女性从一出生就被打上悲剧的烙印,无法摆脱,命定终身。孙频通过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故事叙述,剖析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二)唤起女性的自我救赎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自古以来就低于男性,尽管当今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但是某些地区,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女性似乎已经将男性本体论内化成一种日常的伦理观念、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充斥于自己的言行与内心,形成了一种自觉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女性与生俱来且难以察觉的。
孙频曾在书中指出,女性的内心深处可能没有意识到“她们是时刻准备着取悦男人的”,但是作者却对女性的这种无意识心理,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由此在她的作品中产生了诸多对这一意识进行抗争的女性形象,且这类女性形象带有一定的自我救赎的意义。
《乩身》中常勇用结束自身生命的形式,完成了自我救赎。《祛魅》中的李林燕,从一个时髦、漂亮、满是活力与希望的女诗人,变成了一个“把油腻腻的头发在脑后胡乱的搓成一条辫子,身上套着一件男人穿的的确良衬衫”[2]191的邋遢女教师,进而变成杀人犯。在李林燕逐渐凋零的过程中,外界给予她的只有议论、排挤和嘲讽,没有人想过帮助她,她的自我毁灭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中其他女性的缩影。
孙频笔下的女性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这就注定了她们只能用自戕的方式去对抗社会的不公,尽管这些对社会道德规则的抗争注定会失败,但是她们在某一时刻所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也可以令她们获得足够的尊重。孙频所创造出来的女性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倔强、顽强、自尊和孤注一掷的自我救赎,足以令世界为之动容。可以说,孙频笔下的爱依然是扭曲的、受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她的某些作品里读到一种向上升华的精神力量[4]。
孙频的写作揭露了现实社会中女性存在意义和生存方式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思考,怎样才可以让女性从黑暗悠长的历史轨道中摸索出来,见到公平、公正的曙光,女性何时才能完成自我救赎,摆脱历史惯性所带来的困境,真正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迎来真实的、和谐的幸福之地,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