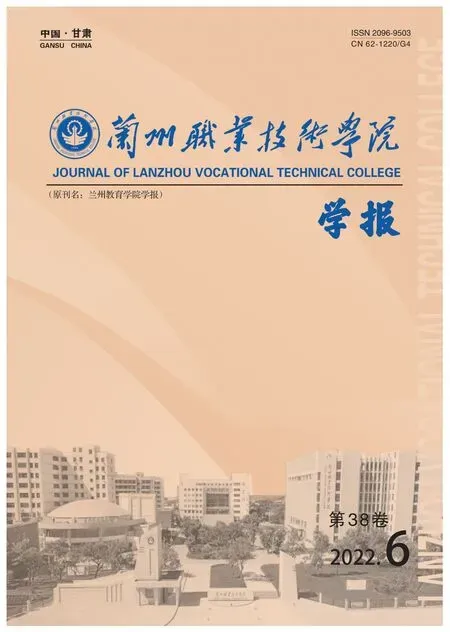试论《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叙事建构与伦理书写
郭梦诗
(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6)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发表了《野草在歌唱》《金色笔记》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自传、散文、诗歌作品五十多部。她的作品探讨两性主义、生态主义、殖民主义、种族矛盾等多个主题,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多丽丝·莱辛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曾获得毛姆短篇小说奖(1954)、法国普立克斯·麦迪西奖(1976)、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5)、英国皇家文学会荣誉奖(2001)、诺贝尔文学奖(2007)等多项大奖。多丽丝·莱辛的创作具有多样化特点,她的作品始终能够充分展现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她在《小小的个人声音》中说到,要在小说中寻找“那种温暖、同情和对人民的热爱”[1]69,希望“面对人类的忧虑、恐惧”时,作家可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70,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她通过审视特定时代的社会制度、主流观念与伦理书写,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与判断,试图用情感引导读者树立新的伦理观念,建构新的伦理秩序。
英国作家拜厄特(A.S.Byatt)曾对《卫报》记者说:“莱辛是极少数天才文学预言家之一,她预见的很多问题,后来的确成为现实。”《幸存者回忆录》是莱辛的后期代表作品,是一部极具幻想主义色彩的小说,标志着莱辛的创作风格由现实主义逐渐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幸存者回忆录》通过多重叙事建构描绘了幸存者们在大灾难中的生存状态:灾难来临时,城市不断沦陷,人们在焦虑、恐慌之中纷纷向安全地带逃离,寻找食物和水源。此时,一个无名无姓的中年单身妇女在废墟中的清冷公寓楼里观察着周遭的一切。某天,一名陌生的男子出现,留下一个12岁的少女和一只半猫半狗的动物。在公寓的墙上,莱辛借助主人公“我”的视角不断穿入“墙内”充满象征、堆积回忆的神秘空间,并同“墙外”逐渐瓦解的“乌托邦”世界并行思考,借助少女的成长与经历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同时又依托双重“他者见证”的叙事策略,将少女个人经历转换为具有警示意义的社会经验,号召大家通过实际行动探索生存之道,建构和谐的伦理秩序。
一、陌生化叙事——在反乌托邦情节中凸显伦理困境
《幸存者回忆录》创作于1974年,当时“人们还未走出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又遭遇了生存的困境和全球性毁灭的威胁: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的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核武器的大量实验和生产、物资的严重匮乏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化,生活忧虑加剧”[2]。这样的创作背景暗示了小说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引导读者在“国家松散”“宗教堕落”“科技倒退”等灾难状况和伦理困境中反思。作者通过“欲立先破”的反乌托邦叙事建构深化了《幸存者回忆录》的叙事主题,凸显了社会伦理困境,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进程中伦理秩序和道德准则的思考与判断。
国家乌托邦的瓦解。《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局政府统治能力退化,各项职能陷入瘫痪,但为了满足特权阶层的需求,社会中的不公现象仍在延续,“尽管日常生活简直都快消亡了,或被新的形式所取代,笨重、迟钝、更加难以协调统一的政府机构却一直在继续运行”[3]173。长期存在的社会危机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的社会伦理壁垒,使富人与穷人之间产生了更多攻讦和矛盾,社会已经深陷伦理困境之中。尽管如此,统治阶层仍坚持违背社会道德原则,利用手中的特权享受着社会的剩余公共资源,整个社会陷入极度不公平的状态——中层阶级装聋作哑,通过贿赂上级获得高层专属运输工具;穷人的地位越发低下,“来自地铁的孩子帮”像“老鼠”[3]164一样生活在地下,在当前的国度完全丧失了受教育权。多丽丝·莱辛将本应出现在伦理混沌的社会中的场景转换为在大灾难中出现的伦理困境,目的是指出体制管理的重要性,强调邪恶的价值导向会在社会丧失体制管理时成为所有社会伦理困境和悲剧的根源,重视社会伦理建构有利于国家领导阶级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划分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作者通过《幸存者回忆录》传达了对未来社会伦理现实的忧虑,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伦理认知,为读者提供了社会伦理建构的视角。
宗教乌托邦的瓦解。爱尔兰工人和波兰难民这一对夫妻加上他们所生的十一个孩子组成了“瑞安一家”,夫妻俩是忠实的天主教徒,却酗酒、性情粗暴且神经质;孩子们偷窃、早孕、劣迹斑斑,数次进出监狱和少管所。但是,“瑞安一家”在现实环境中的伦理选择是艰难且双面的,他们为了填饱肚子和维系生活降低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即使“圣徒和哲学家的目标他们生来就有”[3]116。在外界看来,“瑞安一家”已经丧失了应有的教徒精神,他们“受尽贬损,意志消沉,道德堕落”[3]117。然而,“瑞安一家”和友人们组成的家族却能够在以肤色划分人群等级的社会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肤色的人们,无疑是对宗教内涵的高度诠释。在《幸存者回忆录》中,多丽丝·莱辛对宗教乌托邦的描写不仅能够让读者生发出强烈的道德反差,还能够产生对乌托邦瓦解的唏嘘与思索。
科技乌托邦的瓦解。《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的电梯、公车、汽车等工具大部分时间处于停运状态或是变成了为富人提供特权的方便之物,“这个城市有不少仓库都堆满了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电器”[3]104,科技在作者描绘的未来社会中丧失了它的魅力和效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我”在现实困境中通过变卖电器获得平底锅、搪瓷壶和塑料碗这些更实用的东西,因为先进的技术产品在这个未来世界中一文不值。科技脱离了社会生活,无法获得经济效益,导致科技发展停滞不前,阻碍了社会整体发展。尽管灾难之中“幸存者”们得以存活,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气候处于极热与极寒两种极端状态,空气混浊,水资源严重匮乏,人们无法继续使用电力与汽油,只能依靠蜡烛照明,通过双手保证最原始的生活条件。科技乌托邦瓦解的背后“隐含着多丽丝·莱辛对人类生存状态以及未来世界的深沉忧思”[4],体现了她自身的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
二、非线性叙事——在时空建构中复兴伦理意识
在《幸存者回忆录》中,多丽丝·莱辛以故事内容为主线,依托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创作理念对时间因素进行非线性处理,使故事内容占据文本叙述的主导地位。通过回忆与现实双重时空并置的叙事方式,使看似相互排斥的两个平行世界同时存在,让读者在“墙内”和“墙外”世界不断穿梭,不断审视着主人公在“墙内”经历的屠杀和在“墙外”得到的救赎,通过主人公的成长和蜕变将个人伦理意识觉醒上升到社会伦理意识复兴。
《幸存者回忆录》没有采用小说常用的纵向时间叙事方式,而是从回忆特定时代开始,慢慢将视线拉向衰败的城市,转而描述“我”无意中穿墙而过后又回到现实世界的场景。作者通过多角度描写,将“我”在“墙内”世界与“墙外”世界频繁穿梭的所见所感描写得细致入微,“对墙后世界的叙事与‘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叙事随着‘我’的越过与退回交叉进行,并置而存”[5]。
墙内,“我”一步步走向艾米莉的童年,看到她在白色闷热的幽闭房间内渴望母亲的拥抱和关怀,渴望父亲的问候和陪伴。然而,母亲总是在给她脱衣服时“手指弄疼了她,刮伤了她”[3]41;母亲和女仆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陪着屋内的男婴玩耍。父亲总是在睡觉道晚安时只顾和小男孩亲昵而忽略她,对她仅有的安慰是把她抓到两膝之间胳肢,玩一种“睡觉前的‘游戏’”[3]82,艾米莉不断遭受着父亲的性骚扰,但她的母亲却漠不关心,对于她所受的罪熟视无睹。“墙内”世界“人格上的屠杀”由此产生。作者通过多次空间转换来铺陈艾米莉成长中的细节,以时空建构的方式重现了艾米莉所处的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和重重伦理困境。艾米莉遭受父母的嫌弃、欺凌、冷漠和拒绝,产生了人格窒息感,导致肮脏的、负面的情绪和思想扎根于她的伦理意识中,她认为“爱的要求”就是如此,因而她不再向母亲索要拥抱,变成一个小心翼翼又非常淘气的“坏”孩子,以至于当她出现在“我”的客厅时是性格残缺的、戴着面具的个体。“家园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6],对于艾米莉而言,这场“人格上的屠杀”正是通过将其幽禁在这个白色闷热的封闭空间里来实现的。
墙外,多丽丝·莱辛描述了艾米莉“人格上的救赎”。作者同样通过时空建构的方式向我们娓娓讲述了艾米莉从一个受到创伤的少女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公社负责人,并最终实现伦理意识觉醒和重新定位自我价值的过程。艾米莉刚出现在“我”的客厅时,她似乎沉默地接受着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她带着“冷冰冰的防御态度”急于寻找自己的房间,认定“那将是她的避难所,是呵护她的四壁”[3]14。接下来的日子里,她走出公寓,想要通过与人行道上的群体相处来开启新的人生。起初,她试图加入到男子群体中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来,她依附于人行道上最受欢迎的年轻人——杰拉尔德。此时的艾米莉虽然极具领导才能,但由于她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舍弃了自己的理性和责任,因个人情感降低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进而将理想设定为“做公社首领的女人”,丧失了拯救自我的机会。因此,作者通过“我”的视角一次次访问墙内的世界,去探赜艾米莉成长的空间,观察其中的问题,并一次次对应着现实世界进行修复。两个并置空间将故事内容与艾米莉的人格统一为一个整体,让读者得以充分理解她的伦理意识走向。在《幸存者回忆录》的结尾,艾米莉发现自己不是杰拉尔德唯一的“女伴”,他的新欢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此时的艾米莉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并因此激发了自身意识的觉醒。她意识到“杰拉尔德之家”出现了权势等级且自己正困于这个机制之中,她的生理与心理开始显现独立女性的特点并试图逃避、挣脱这个笼罩在扭曲的伦理关系中的现实世界。“艾米莉和杰拉尔德的情感关系表达了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对伦理秩序的新的理解和探索”[7]。当杰拉尔德固执地接纳“地铁帮”的野蛮孩子,毁灭了自己的小政权并受到暴力攻击时,坚强勇敢的艾米莉挺身而出扮演了保护杰拉尔德的女性角色,实现了自我救赎。
多丽丝·莱辛通过墙外成长生活和墙内童年场景的时空并置叙述,展现了艾米莉对于女性身份归属的伦理困惑和怀疑,并借此描述了主人公走出伦理意识困境、探寻完整维度的成长之路。这种叙事建构不仅能让读者对艾米莉这一类弱势女性的经历感同身受,还能通过艾米莉在女性权利方面进行的伦理思考体现出她对父权、男权的反抗,充分展现她走出混乱无序的性别困境和女性伦理意识觉醒的过程。
三、多视角叙事——在双重“他者见证”中建构伦理秩序
在《幸存者回忆录》中,多丽丝·莱辛运用双重“他者见证”的叙事手法,从两性伦理和社会伦理等方面揭示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呼吁对分裂、破败的世界秩序进行和谐重建。作者通过“我”的视角“见证”艾米莉的蜕变和成长,她在破损的家庭伦理环境中度过童年,后又被现实环境、人性灾难充斥着的社会伦理结构所桎梏。在作者建构的两性伦理秩序中,艾米莉通过自身的努力重塑了伦理道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人格救赎”,这种“他者见证叙事”打破了主人公自我与世界的隔阂,勾勒出艾米莉蜕变过程中多维、动态的成长历程,表现出她已经完全摆脱了性别的枷锁,能够认清并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巨大转变。艾米莉不仅是独立个体层面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社会的言说者,充当着整个人类的言说渠道这一角色。她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见证着未来社会中脆弱的人类文明和人性的灾难,而多丽丝·莱辛正是借助艾米莉揭示了人类伦理意识的式微,并尝试建构良性的伦理秩序。
“地上到处扔着骨头、小块毛皮和碎玻璃,后面废弃的空地经肆意践踏,已污秽不堪”[3]36。这些场景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艾米莉所处的世界被破坏的、混乱的社会伦理秩序,这样的城市环境明显不适宜人类居住,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和理性也逐渐随着生存环境的破坏而丧失。借助于令人窒息的背景,多丽丝·莱辛用细腻的文字引导读者跟随艾米莉的视角走进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更广阔的角度摄取故事内容,见证集结成群的流浪者、人行道上的徘徊者、非法占有住房的幸存者、公寓窗边的观望者、顶层集市的交易者、底层野蛮的“地铁帮”和制造假象的高层等不同角色的百味人生,探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时的社会伦理秩序,进而更加深入地探寻人性的双面性与自我革新。
多丽丝·莱辛希望通过与艾米莉相关的人物关系以及她目睹的人物成长经历揭示大灾难过程中混乱的社会伦理秩序,并借此表达对重建伦理秩序的希冀。莱辛通过艾米莉的行为作出了建构微型社会伦理秩序的尝试。比如,艾米莉和“地铁帮”的孩子们有着类似的成长环境,他们都被置于社会秩序混乱、道德败坏的伦理结构中,缺失了选择、树立正确伦理观念的这一必经过程。面对这样一群随时会对社会发起攻击的孩子,艾米莉仍然对他们给予了个人的关怀以及自己童年缺失的爱与温暖。莱辛“将艾米莉的个人经历放置于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思考”[8],在凸显叙事主体价值取向的同时,将个人经历转换为具有警示意义的社会经验,这种“他者见证”的叙事方式根植于社会伦理秩序内部,又裹挟着未来的文明,能够更加充分地指出人类摆脱伦理秩序混乱、重构伦理秩序的道路。
四、结语
多丽丝·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运用独特的叙事建构策略,赋予小说独特的艺术效果,在揭晓主题的同时呈现了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和伦理取向。首先,她通过反乌托邦叙事展示了人类在遭遇生存困境和全球性毁灭时陷入的国家、宗教、科技等方面的伦理困境,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和反思隐含在瓦解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的背后。其次,她采用双重时空并置叙事方式,通过不断移置叙事空间,多次改变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伦理距离,有助于读者走进文本、沉浸式地感受文本、与文本对话。最后,她采用双重“他者见证”的叙事策略,尝试突破传统社会道德秩序的藩篱,完成两性关系的伦理秩序建构,并试图通过激发人类的生存伦理意识,号召大家在灾难中进行自救,通过实际行动和人文主义关怀探索生存之道,建构和谐的伦理秩序。可见,被置于大灾难这一特定伦理环境中的《幸存者回忆录》负载着作者崇高的伦理道德理想,能够启迪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从而使人与社会统一发展的伦理价值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