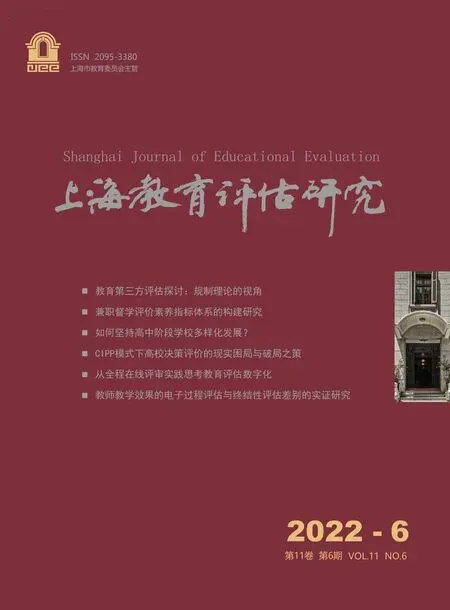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推动路径
——基于ASD理论的分析框架*
姚志友,邹 雪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 “双循环” 发展格局,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全新的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改革阻碍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倾向,吹响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号角。高等教育评价在引导高校明确办学定位、改善办学条件、加强资源利用、规范培养过程、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起到了调节阀的作用,但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相比、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要求相比、与 “双一流” 高校建设成效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以评促建异化为以评代建、以评促改畸变为以评代改、以评促管让位于为评而管,[1]教育评价实践日益成为一种 “评价性负担” 。[2]本文试图跳出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碎片化之路径,构建基于ASD理论的 “行动者—制度—环境” 三维分析框架,在全面分析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环境要素面临的深层困境探赜索隐,提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推动路径,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 “指挥棒” 问题。
一、ASD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逻辑
运用ASD理论分析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全面分析评价主体、系统解读评价制度及动态分析评价环境,三者在互动交流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的新质元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进程。
1.ASD理论: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分析框架
西方社会理论学派 “规则—系统理论” 代表人物汤姆·R·伯恩斯,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描述中,将 “行动者” 与 “系统” 结合起来,发展和完善了 “行动者—系统—动力学” 理论(The Theory of Actor-System-Dynamics,简称ASD理论),并将其广泛用于各种社会问题分析。ASD理论认为社会系统变迁的动力主要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和环境要素,以及要素与系统间的合理张力与辨证互动。本文运用ASD理论分析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并非要求评估主体机械地执行政策,而是通过采取创造、解释、运用评价规则等手段,突破原有制度、技术或环境系统的制约,对评价规则进行修补和添加,推动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创新。

图1 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三维分析框架
从ASD观点出发,高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可以有图1给出的结构。图1中,(Ⅰ)表示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的制约及协调因素。具体而言,有制度系统(ⅠA),是指建立在社会共同规则系统上的评价制度,对教育评价改革起到程序性制约作用。其次还有环境系统(ⅠB),是指教育评价活动受社会风气、政策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影响,起到隐性或实质性制约作用。最后是技术系统(ⅠA、ⅠB),通过技术将制度系统与环境系统耦合,为评价改革提供技术支撑。(Ⅱ)指高等教育评价的行动者,主要包括政府、高校与社会等行动主体。(Ⅲ)指高等教育评价的实践结果,是行动主体互动博弈产生的多重后果,如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或是外延式发展、获得成功经验或是失败教训等。同时,博弈结果会反馈至评价主体,评价主体通过多次互动,修正并改变制度系统、技术系统及环境系统,保障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良性运行。
2.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内在逻辑的理论阐释
(1)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主体要素分析
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主体包括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参评高校以及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决定着评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则,在教育评价改革发展中扮演着评价政策制定者、财政支持者及资源分配者等多种角色。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教育评价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对高校形成显性制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评价政策的属地管理者,起着推动作用,但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往往对评价规则进行策略性解读。高校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体,起着基础性作用,是高等教育评价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在共同利益驱动下,高校与属地政府间易达成 “共谋” 行为,运用评价规则形成显性规避,获取更多的政策 “红利” 。正如伯恩斯认为的, “虽然行动者在行动和互动中要屈从于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但同时他们具有能动性,主要是创造力或破坏力,塑造着或重塑着文化形态、制度以及物质环境。”[3]
(2)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要素分析
组织社会学语境的新制度主义认为,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是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4]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要素就是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以及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育评价的文化与认知,它们共同构成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推力,也对其形成程序性制约。其中,法律法规及政策规范赋予了评价改革以合法性,就国家层面而言,主要包括宏观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等。就高校内部而言,指导教育教学工作的具体办法也涵盖在内,如重大事项决策制度、人才选拔评价制度等。在教育评价实践中,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有时并不能覆盖全体教育活动,人们对评价活动本身的认识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教育评价活动中的认知文化,它伴随着评价实践逐渐被默许。就本科教学评估而言,评估方案评什么,高校就建什么,把主要的精力花在迎接评估专家、写自评报告等工作形式上。在此后的几轮评估中,政策部门不断调整设计新的评估方案,逐步缩减高校的策略空间,抑制高校的策略性行为,直至达到新的政策平衡。
(3)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环境要素分析
在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社会大环境对评价主体及其决策责任机制的形成和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环境要素能够推动或限制教育评价活动的进行。阿什比认为: “大学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5]所谓遗传,指的是大学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作为隐性制约因素,高校内部是否就教育评价改革达成了共识、是否致力营造良好的教育评价生态,这些都会对教育评价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所谓环境,指的是高校对外部需求的回应。随着与社会联系的不断深化与多元,大学渴望在科学前沿、技术创新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更为人们所关注,人才培养职能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教育评价则是保障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道防火墙。
综上,政府与高校间的动态博弈推动教育评价持续变革,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将评价问题、评价解决方案进行 “编码” ,将教育评价改革问题变换为使用不同的政策文件;被评高校同样采取因应方式,用特定的技术、资源以及策略对政策文件进行 “解码” 以形成 “适应性” ;教育行政部门则因事而化、因时而进,不断调整政策方案,进一步强化显性制约,并通过营造评价环境氛围加强隐性制约,保持评价主体、评价制度与评价环境间的平衡,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
二、ASD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问题分析
审视当前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进程,在评价主体、评价制度及评价环境方面仍面临实践困境。
1.主体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进程体现出政府主导的特征,教育评价是教育系统内部 “关起门” 的评价。如高职高专评估、专业认证、审核评估与学科评估,高校虽有一定的评价自主权,但本质上仍是政府主导的外部评估。大学排名作为社会评价的代表,表面上拥有充分的评价自主权,但由于存在信息偏差或商业行为,一些大学排行榜乱象丛生,不能真实反映高校办学实际,严重误导了社会与公众,近来也受到部分大学的抵制,教育主管部门也以各种形式呼吁社会各界淡化大学排名,要求高校加强内涵建设,不能盲目追求排名指标,认为这些做法会逐渐削弱社会评价的策略空间。当然,社会评价发展应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毫无疑问,社会机构担任裁判,能够为审视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办学提供全新的 “打开门” 的评价。
2.制度问题
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价改革进程中,主要以强制性政策工具为主,激励性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如教育部、科技部2020年出台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强调 “按照正确的导向引领学术文化建设,不发布SCI论文相关指标、ESI指标的排行,不采信、引用和宣传其他机构以SCI论文、ESI为核心指标编制的排行榜,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科研人员、学科和大学评价的标签” 等,这些语句的语境中释放出强烈的破 “五唯” 信号,但实际执行中还存在 “破” 后如何解决 “立” 的问题。
高教评价政策执行碎片化是制度困境的又一表现,集中体现在评价主体、评价活动及评价资源碎片化。一方面,教育评价主体各自为评。本科教学评估、高职高专评估和专业认证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学科评估由学位中心负责,不同职能部门仅能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开展评价,造成评估主体碎片化。另一方面,教育评价活动相互割裂。高等教育评价本是一个整体,片面追求评价可比性,人为地将其分割为相互孤立的评价活动,不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的均衡发展。此外,将评价结果与教育资源分配挂钩,导致了 “强者愈强” 的评估困境,强化了高校间的纵向分层,加剧了评价资源的碎片化。
3.环境问题
高等教育评价既是一种教育现象,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质量保障文化与评价决策文化之间的隔阂愈发难以融合;本该坚守教育底线的评价,在评价实践中愈发丧失对教育活动的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高等教育评价正在陷入功用性陷阱。无视质量文化建设,将感性的实践活动变成冰冷的数字,无疑是在弱化教育评价的教育性;企图通过完善各类评价指标体系达成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不啻为徒劳。 “随着文凭的贬值,注水式的大学教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不再是阶层向上流动的充分条件,而是一种被迫的‘防御性’开支。”[6]当大学里的学科和科学不再是文化的载体,而成了彰显资源与利益的发展工具,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式微不可避免。
三、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推动路径
基于ASD理论视角,针对性地完善评价主体、评价制度及评价环境各元素是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评价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
(1)政府放权赋能,调动评价主体积极性
纵向来看,明确央地评价的权责边界,是有效化解教育评价主体困境、稳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前提。中央政府作为教育评价政策和教育资源的供给者,要不断细化和压实主体责任。根据本地的教育资源状况,做出切合实际的教育评价改革行为,探索各具特色的教育评价改革模式,是省级政府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任务。横向来看,教育评价权力多中心化是深入推进 “管办评分离” 的正确走向。对高校而言,政府要合理调整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格局,给予高校应有的办学自主权,把高校大部分具体的评价事务和基本决策留给院校,调动高校开展自我评价的积极性。对社会而言,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评价,对高等教育评价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真正为教育评价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概言之,通过简政放权,优化调整评价主体的权力义务,促使主体间的互动与制约成为 “新常态” ,完善政府管教育、高校办教育和社会评教育的 “管办评相对分离” 的评价格局。
(2)完善政府宏观管理,实现评价主体深度协同
高等教育评价是多元利益主体在协商合作中达成的价值共意,绝非教育行政部门单向度的绩效问责。完善宏观管理,政府要加强对教育评价工作的宏观指导与间接调控,切实行使监管职责,但要逐渐从具体的评价事务中退出。一方面,政府要设立专门的评价管理机构,加强组织保障。近期,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原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由主要负责高等教育评估调整转变为全口径、全学段、全类型的教育质量评估监测专业机构,表明教育评价机构建设逐步走向专业化道路,但管理职责仍相对较弱。鉴于此,可考虑在其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赋予其监管职能,如将教育质量评估中心拓展为 “教育质量评估与管理中心” 。另一方面,政府要重视培育社会中介机构,通过制度保障评价机构的独立性,使之能独立、自主地行使评价职能,政府则加强对评价机构的资质水平认定。总之,通过完善政府宏观管理,逐步破除政府对高校和社会的钳制,平衡政府、高校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张力,激发多元主体间的活力,促成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合力。[7]
2.评价制度从联系松散转向紧密耦合
(1)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评价配套机制
加强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设,落实法制精神,是高等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了政府评估的权力,但对与评估相关的组织、权力、责任等未作详细规定,因而推进教育评价法律法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另一方面,强化持续改进,应建立精准问责和有效反馈的评价工作机制。高等教育评价的最终目的是提高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关键在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能否被很好地贯彻落实,这就需要健全的问责与反馈机制的保障。政府要转变责任泛化的评价和监督方式,转变评价主体缺位或参与不足的现状,构建完备的教育评价监督反馈及问责机制,畅通元评价的反馈渠道,强化对高校评估及整改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教育评价工作中产生的负向效应,助推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
(2)聚焦破 “五唯” 主题,加快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从评价本质看,评价是要在 “唯” 与 “不唯” 之间取得平衡,建立科学有效的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评价体系。[8]一方面,质量贡献导向是建构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应然之道。学科评估的目的在于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积极回应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需求,促使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真正做到 “顶天立地” 。另一方面,分类分层评价是建构高质量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持守之道。第一,要构建适用于高等教育的分层评价体系。如职业高等教育现行的 “诊断式” 合格评估模式已不能满足国家发展对新型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可借鉴本科教学评估中的审核评估方案,在强化办学资源改善的同时,突出职业教育的应用性,给予不同类型的职业高等院校更多的评价策略空间。第二,要构建适应于高等教育的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专业分别制定符合专业实际的评价标准,增加凸显专业特色的指标权重,引导高校根据不同专业的评价重点形成专业发展优势。
3.评价环境从被动规训走向主动建构
(1)坚持 “质量至上” 的教育评价文化
首先,高校要秉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评价理念,破除功利化评价理念的束缚。对大学质量文化的理解或许存在差别,但以人为本、开放创新、兼容并包、追求卓越等价值理念并无不同。质量理念的选择应与自身文化系统主动衔接,激发评价主体的质量意识,激励评价主体重视人才培养及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在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中培育教育评价文化。其次,高校要建立多元的高教评价标准。学术型与应用型高校定位不同,产出的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也不同,但无论科研型成果抑或应用型成果,都应采用适切的评价标准来体现自身的质量特征及在教育评价中的重要性。此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创新,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应更加突出创新性评价指标,引导高校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最后,从为了问责的结果评价转向基于信任的过程评价、发展评价和增值评价,[9]用高质量的高教评价范式引领质量文化建设。
(2)构建 “以文化人” 的评价育人机制
大学作为求学问道之所,自身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影响着人才培养。换言之,人才培养的本质是文化育人,文化育人是从事 “以文化人” 能动的实践活动。[10]一方面,高校要健全教师师德评价指标体系,发挥评价育人机制的 “濡化” 作用。高校要加强对教师师德的考核与激励,引导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形成行为示范,通过课堂教学涵养学生学识,充分发挥教师在 “以文化人” 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评价立德树人成效的指标体系,发挥评价育人机制的 “内化” 作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评价着力破除重科研轻教学、重智育轻德育等不良倾向,重点评价在以往评估中不能量化但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高等教育能力。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正确评价导向,着重考察高校是否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及社会实践各环节。由此,将从外到内 “濡化” 的涵养文化与从内到外 “内化” 的内生文化相结合,促进质量文化渗透到大学的骨髓之中,凝练为个人品格,形成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