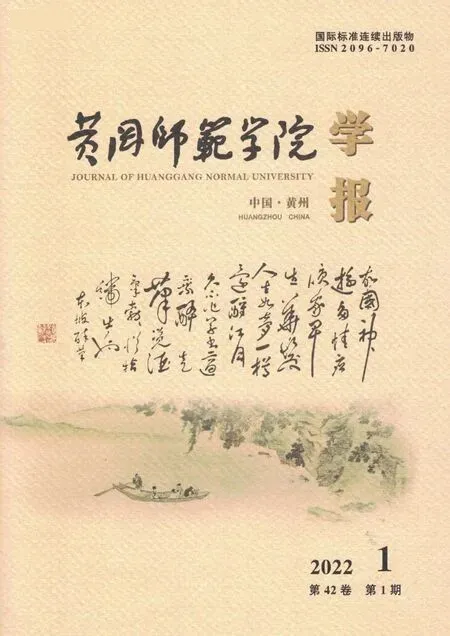地方文化记忆:唐宋文人的黄州书写
方向红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6800)
黄州,作为历史地理概念,今天指的是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下段北部一带。虽然黄州地域历史悠久,在漫长荒远的岁月里,曾哺育了三苗、扬越、荆楚等远古先民,留下螺蛳山和鼓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杰作,但作为区域,它一直未能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可以说,唐代之前的黄州,文化上寂然无名,描写黄州的诗文鲜见古籍。然而,自唐后,情况大为改观。正如宋人陆游所说:“(黄州)最僻陋少事……然自牧之(杜牧)、王元之(王禹偁)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张耒)谪居,进为名邦。”[1]194以杜牧、王禹偁、苏轼、张耒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名人,因各种因缘驻足黄州,留下大量对这片土地的书写文字,黄州也因此大放光彩,成为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地域。
关于唐宋时期文人笔下的黄州地域研究,前人已有不少讨论,但大多集中于单个文人的黄州活动与创作,如杜牧、王禹偁、苏轼、张耒等人黄州时期的心态、文学创作之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个体研究①,关于黄州一个时期文人群体研究及对黄州地域文化整体、持续性影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匮乏。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探讨唐宋时期文人群体对黄州地域书写的多方面呈现,以期丰富黄州地域文化研究的内涵。
据《舆地广记》记载,“黄州,春秋战国属楚,秦属南郡,二汉属江夏郡,晋初属弋阳郡,后属西阳国,宋因之,齐分置齐安郡,北齐兼置衡州,后周因之。隋开皇初废郡,改衡州曰黄州,大业初州废,置永安郡。唐武德三年复为黄州,天宝元年复曰齐安郡。皇朝因之。今县三,望黄冈县,上黄陂县,中麻城县。”[2]新旧《唐书》,一致将黄州列为下等州。北宋时期,黄州属淮南西路,为下州;南宋时期,黄州处于与金、蒙对峙之地,黄州属军事州。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3]55一批批文人来到黄州,留下不朽作品。翻检《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等典籍,作于黄州、描写黄州的地域文学作品不仅数量较前朝大幅增长,而且各体兼备,名篇倍出。毫无疑问,唐宋时期的黄州,是文人密切关注的对象,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化地理现象。
一、“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诗意空间的黄州
黄州,自唐代文人杜牧始,首先是以自然景观的形象出现在文人笔下。会员二年(886-888年)自请外任于黄州的杜牧,虽坦言黄州是“孤城大泽畔”(杜牧《雪中抒怀》)、“萧条井邑如鱼尾”(杜牧《即事》),但仍以欣喜之情赞叹黄州带给他的最直接的外在感触。杜牧笔下,黄州风景优美,“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兰溪》)、“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齐安郡后池绝句》)。此外,黄州自然环境舒适,如“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齐安郡中偶题》其一),“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縠燕差池”。春雨、兰花、溪桥、落日、轻烟、柳影等极具“江南”柔美特征的物象,无一不展现出黄州诗意的审美空间。
至宋代,更多的文人书写着黄州,黄州仍展现出她独具魅力的一面。宋代最早抵达黄州的知名文人当属王禹偁。据《宋史》载,王禹偁性格刚直不阿,因修《太祖实录》,与宰相不和,咸平二年(999年)被贬黄州。王禹偁喜游历,“平生诗句多山水”。他在黄州留下脍炙人口的《题浠川八景》,其诗曰:“兰溪时雨和甘棠,石壁回谰映塔光。陆羽荣泉金鼎冷,右军墨沼兔毫香。龙潭澈底明秋月,凤顶当空背夕阳。乘得绿杨春晓兴,玉台井畔泛霞觞。”王禹偁首题“八景”之说,兰溪时雨、石壁回谰、陆羽荣泉、右军墨沼、龙潭秋月、凤顶夕阳、绿杨春晓、玉台丹井等八处名胜,黄州浠川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和谐的体现,让人神往。王禹偁爱竹,竹为古代士人品行高洁的象征。黄州多竹,这给晚年的王禹偁以精神上无穷的寄托。“黄州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王禹偁因地制宜,“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相通”,竹楼景致“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寥敻,不可具状”,作者欢愉之情溢于言表,归于“皆竹楼之助也”。王禹偁晚年自号“王黄州”,黄州成为他晚年的栖息之所,“咸平初来于齐安,在郡政化孚洽,作竹楼、无愠斋、睡足轩以玩意。”(《小畜集序》)
最让黄州名声大噪的文人当属苏轼,苏轼震铄古今的别号“东坡”诞生于黄州。黄州印象,对于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来说,大抵来自前人的间接经验,“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过淮》)、“黄州小郡夹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九死一生后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死里逃生的苏轼,带着惊恐踏上黄州的土地,却由衷发出“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的赞叹。黄州,临大江,位于长江中游下段,水系发达,大小湖泊星罗棋布,适合鱼类及各种水生生物繁育生长,有鱼米之乡美誉。苏轼对黄州的印象,带着强烈的赞美之情。黄州物产丰富,苏轼评价“黄州风物可乐”(《答吴子野七首》之四)。鱼,是苏轼的美食,“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鳊鱼》)。鳊鱼是长江鱼类一种,肉质鲜美。苏轼也常用鲫鱼、鲤鱼,“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混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煮鱼法》)寻常的食材,不一样的做法,尽显美味。鱼羹,也是苏轼擅长的美食,“予在东坡,尝亲执枪匕煮鱼羹以设客,客未尝不称善”(《书煮鱼羹》)。
除了黄州鱼之外,苏轼还发现黄州猪肉的独特美味。猪肉,本是黄州寻常食材,“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黄州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猪肉价格低廉,富人不屑吃,穷人不懂烹饪猪肉的方法。“东坡肉”,是苏轼在黄州的另一道美食。苏轼总结猪肉做法,“净洗锅,少著水,柴头寻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样煮出来的猪肉,“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苏轼笔下的黄州,毫无疑问充满温情的一面,其作品反映出的黄州物产之丰盛、自然景致之美与前人的赞叹几乎同出一辙。相形之下,诸多描写黄州地域的作品,苏公更有想象力,他的妙笔简直让黄州熠熠生辉。春季,“楚乡春冷早梅天,柳色波光已斗妍”(《黄州春日杂书四绝》),“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安国寺寻春》),“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栋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其一),“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春末夏初、雨后天晴,又是一番景象,“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初夏雨后的农村小景“风物之美,足以终老”“江山久居益可乐”(《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此外,文人笔下黄州的江面,姿态万千,或平静,宛如镜面,“江流镜面净,烟雨轻幂幂。孤舟如凫鷖,点破千顷碧”(苏轼《晓至巴河迎子由》);或波涛汹涌,“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长江水之气象,让人神往,“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黄州长江边的生活,苏轼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与范子丰八首》)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长江“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风雨雪月,阴晴早暮,态状千万”(《答上官长官》)。
继苏轼之后,贬居黄州的张耒也认为“黄在大江上,风土食物却相得”(《徐仲车书》)。“江上鱼肥春水生”(《齐安春谣五绝》)、“江鱼如切玉”(《冬日放言二十一首》)等诗句皆为张耒对黄州物产的赞叹。黄州的自然景观,四时风貌,张耒也留下诸多诗句,如“柳黄花白楼台外,紫翠江南数叠山”(《十八日》)、“杨柳弄春藏不得,雪絮点点吹人来”(《齐安春谣》)、“桃李虽云过,林塘老景浓。幽花冠晓露,高柳饰和风”(《暮春游柯市人家有作》)、“江蒲芽白江水绿,江头花开自幽淑”(《江南曲》),这些生动细腻的黄州春景丰富充实着黄州之美。
毋庸置疑,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物产,这些带有浓厚黄州地理印迹的物象,经过了唐宋文人的吟咏,在作品中被赋予了桃源乐土般的想象。自然山水,与尘世相对,其远离俗世纷争之意,成为文人精神的避难所。在穷乡僻壤的黄州,贬居于此的唐宋文人,发现了黄州山水奇异之美。黄州,俨然成为适宜人生栖息的诗意空间。
二、“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鄙陋恶地的黄州
毋庸置疑,黄州秀丽的自然风貌给唐宋文人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回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州在宋代名扬天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贬谪到此地的一群士大夫文人们。自唐代著名文人杜牧外放于黄州后,黄州就成为知名贬谪之地。从北宋到南宋初年,贬谪文人几乎是“前赴后继”纷至沓来,如王禹偁、夏竦、苏轼、吴居厚、张耒、陈过庭、丁宝臣、王歧、张从惠、张怀民等②。贬谪,“特指古代统治者凭借政治权势、运用法律的手段强迫当事人迁移居住地或为官之地,通过改变个体生存空间环境的途径来实现对他们的政治打击与经济惩罚”[4]226。古代文人遭受贬谪的原因虽不尽相同,但共同的是被贬谪者无一不是政坛上的失意者,被贬谪本身就意味着政治追求的失败。黄州,何以在北宋时期频繁成为贬谪之地?宋代之前,森严的地域等级观念已建立。发轫于先秦时期的贬谪、流放制度,其实质便是确定华夏中心论和“五服”差别论,以确立天子的权威。《唐会要·刺史上》记载“京职之不称者,乃左迁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6]1418,唐代得罪官吏多迁往河西、黔中、剑南、岭南等地,宋初沿五代旧制,罪犯率配隶西北边。但后因贬谪流放之人,多亡投塞外,诱羌为寇,宋太宗乃下诏:“当徙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郡。”[7]5017故南方成为宋代流人、贬谪之地。黄州属于荒蛮之地,远离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容易成为贬谪之地。至南宋,政治中心及经济重心已经南移,黄州得到了较大的开发,将罪官贬到黄州已经失去了惩戒的意义。另一方面,此时以淮河为界,北方都属于南宋的敌对势力,黄州距离边境太近,已不适宜作为贬谪地出现。于是,北宋时期的贬谪地黄州在整个宋代显得尤为突出。
谪臣们贬居黄州,其不幸遭遇、痛苦情感体验是他们作品中常见的内容,苦闷抑郁、愤懑不平的心态也是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因此,黄州不可避免地被文人们涂抹上晦暗的色彩,僻陋、恶地是黄州地理形象的又一突出特点。
唐宋文人笔下,黄州的恶地形象首先源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晚唐杜牧称黄州为“葭苇之场”“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黄州刺史谢上表》),这应该是杜牧对黄州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主观上,杜牧对自己外放于黄州耿耿于怀,“会昌之政,柄者为谁? 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祭周相公文》),外放的主要原因,杜牧认为受“权柄”李德裕宰相的排挤[8]。杜牧日常生活中的黄州,“萧条井邑如鱼尾”,荒凉贫困,心中又增苦闷之感。杜牧在黄州有诗云,“腊雪一尺厚,云冻寒顽痴。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雪中抒怀》),黄州是“孤城大泽畔”,人烟稀少,连找排遣内心忧愤的朋友都没有。北宋人称黄州“人户不满一万,税钱只及六千”,且“去国千里,长淮一隅”,又是“楚之东北鄙陋”“齐安在江、淮之间最为穷僻”。苏轼评价“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而黄又陋甚”,内心自然充满悲情。“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被贬谪至楚地黄州,苏轼把自己比作楚囚,坐困愁城,无计可施。张耒也有“齐安荒僻郡,平昔处放臣”,“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日作二首》)的悲苦感慨。
其次,黄州变化多端的气候也让贬居的文人们心有余悸。黄州地处长江中游,是典型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旱涝交错,夏天闷热,冬天又极寒冷潮湿。黄州雨季时,突如其来又昼夜不停的暴雨,让人猝不及防。张耒对黄州接连不断的暴雨深恶痛绝,他的《厌雨》诗淋漓尽致表达暴雨带来的困扰,其诗曰:“夜来雨声倒百川,老农起坐不敢眠。曰疑涨潦卷屋去,又恐涌水兴床前。旦视山川一泥泞,流沛千顷新秧田。虾蟆相呼动百千,不念两股充庖煎”(《厌雨》),暴雨导致房屋倒塌,百姓担惊受怕,坐卧不安,庄稼被毁,一片狼藉。与多雨相对,黄州极端天气的另一面就是干旱。干旱又使得深井中都没有水,水稻因缺水不能抽穗,张耒对此忧心忡忡,如《不雨》:“齐安一郡雨不足,稻畦土坚不入谷。城中赤日风吹沙,老鸦衔火烧竹屋。百尺长绳抽井底,井中泥渣多于水。谭边龙祠悬纸钱,谁令霹雳警龙眠?”此外,黄州夏季炎热,时常高温不下,体型偏胖的张耒感受尤其强烈,“最愁三伏热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齐安游”(《齐安行》)。至于黄州的冬天,虽不是冰天雪地,但也不好过,“淮南苦寒不可度,积雪连山风倒树。长淮冻绝鱼龙愁,哀鸿傍人飞不去。雪中寒日无暖光,六龙瑟缩不肯骡。老惫孤舟且复止,坚冰三尺厚于墙”(《苦寒行》)。因天气水土因素,谪居于此的文人们多患疾病,如苏轼在黄因多次患病,与黄州名医庞安时交往比较密切。
再次,黄州的部分民风习俗让贬居于此的文人们难以认同。苏轼较为详尽记载黄州杀婴弃婴现象,“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江南尤甚”(《黄鄂之风》),“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与朱鄂州书》)苏轼对此“闻之心酸,为食不下”,但他对作出此行为的百姓并未过多谴责,而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法,“追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与朱鄂州书》)。究其主要原因,皆因贫困所致。
黄州在唐宋文人作品中的恶地形象,固然一方面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人内心对贬谪地域的排斥感。作为生活环境存在的黄州,与这群贬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失意的文人远离京城,远离家乡,来到黄州,不可避免会产生排斥的心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在黄州风物、人文中又发现了黄州之美,逐渐产生一定的认同感。贬官们与黄州之间,形成既排斥、又认同的矛盾复杂心态。王禹偁在黄州,建竹楼,闲居惬意之情溢于言表,如他所描述“公退之暇,披鹤笔,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王禹偁贬谪有此体验,在他看来,是意外收获了。苏轼在黄,也有努力顺应现实的心理,“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首》)黄州风物景致,让苏轼忘怀尘世烦忧,“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与司马温公》)。张耒虽对黄州极端恶劣的气候表示过深恶痛绝,但在黄州的生活,也曾让他满足,“有屋可以读书,有竹可以忘忧。采庭之菊香有余,烹园之蔬甘且柔。贤哉二子,又复何求”,对他而言,黄州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呢?
谪官们离开黄州时的留恋,也能说明他们对黄州有着一定的认同感。苏轼离开黄州的时候,在舟上闻黄州鼓角,不禁怆然涕下,“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又如张耒感叹“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离黄州》),“几年鱼鸟真相得,从此江山是故人。”(《发安化回望黄州山》)黄州俨然已经成为他们心中形成难以磨灭、挥之不去的心理印迹。
三、“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承载赤壁古战场传说的黄州
黄州,声名远播的另一原因,便是作为三国赤壁之战古战场之地频频出现在久负盛名的文学作品中。较早清晰而明显地将赤壁古战场与黄州联系起来的文学家当属杜牧。杜牧脍炙人口的绝句《赤壁》,作于他任黄州刺史时。诗人杜牧在黄州长江边的一次闲游中,偶然拾到前朝战戟,由此联想到三国赤壁之战,其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引发读者浮想联翩。此外,杜牧黄州时期又接连有“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早春寄李使君》)、“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齐安郡晚秋》)等诗句提及“赤壁之战”。黄州有山名“赤鼻”,较早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中,“江水左经赤鼻山南,山侧临江川”,其名称的来历,古人解释为“赤鼻者,乃一大石突出于外,行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广阳杂记》)。北宋人张耒在《续明道杂志》中说:“黄州,江南流在州西。……去治无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颇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矶也。”北宋张文潜在《续明道杂志》中说:“南人谓山入水处为矶,而黄人呼赤鼻讹为赤壁。”南宋陆游《入蜀记》云:“黄州人实谓赤壁曰赤鼻。”黄州赤鼻山,与“赤壁”谐音,在文人笔下与三国赤壁之战结下不解之缘。
至宋代,黄州赤壁更因苏轼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而名噪天下。赤壁之战古战场究竟在哪里?这个疑问也一直争论不休。陆游《入蜀记》归纳较为全面,“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败曹军’,不指言在黄州。苏公尤疑之。《赋》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乐府》云‘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盖一字不轻下如此。至韩子苍,云‘此地能令阿瞒走’,则直指为公瑾之赤壁矣。”[1]赤壁古战场之地,李白、苏轼并未说明是在黄州;与之对立的是,宋末韩子苍,又下结论为黄州。不管历史上真实的赤壁之战究竟是否在黄州,黄州毋庸置疑承载着赤壁之战的传说,赤壁也蕴含着多种复杂文化内涵。
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是确立三国鼎立局面最重要的一场战争。这一时期,风云际会,英雄辈出,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显身手。黄州赤壁,在文人心中自觉或不自觉充当着历史的想象和记忆。正如凯文·林奇所说:“景观也充当着一种社会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5]黄州赤壁,逐渐成为一种人文景观,蕴含着文人对英雄的追慕之情。无论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还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瑜形象,赤壁之战文学意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谪居黄州的文人笔下。
赤壁之战的文学意象,有对英雄的追慕、景仰,自然也会引发文人另一层情感,对自身处境的不满,不被重用、怀才不遇的深层痛苦。杜牧感慨“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苏轼“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出作者浇心中块垒之感。苏轼“赤壁之游”后的赤壁二赋,更是成为表现文人超脱、自由人格的独特符号。苏轼发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无奈浩叹,赤壁之战将思绪指向历史深处,追问历史与人生的价值意义,“赤壁二赋,一洗万古”[9]。
四、“惟有东坡居士好,姓名高挂在黄州”:蕴含东坡文化的黄州
作为文化奇才的苏轼,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诗文名作,他在黄州的所作所为、所歌所咏,经时间的沉淀和后人的追忆,形成丰厚的文化宝库。苏轼的别号“东坡”诞生于黄州,黄州是东坡文化的源头,是东坡文化的发祥地。东坡文化增加了黄州的历史厚重感,提升了黄州的文化品位,黄州文化也因东坡而更绚烂。
东坡的名人效应,让苏轼在黄州的遗踪,成为无数后人凭吊追忆的载体。骚人墨客、文人学者慕名前来黄州瞻仰、游览,又因此留下大量诗文等文化作品,黄州文化的积累越来越深厚。南宋文人陆游是苏轼仰慕者中极为突出的一个。苏轼离开黄州八十余年后,陆游曾专程到黄州,寻访苏轼在黄州的生活轨迹。陆游《入蜀记》描述在黄州所见的东坡遗存:
“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南面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杖,是为雪堂。堂东大柳,传以为公手植。……坡西竹林,古氏故物,号南坡,今已残伐无几,地亦不在古氏矣。”[1]
陆游目中所见,颇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感。他能够见到的东坡旧物,只有雪堂数间,苏轼像、四壁雪景等,似乎诉说着东坡居士当年拄杖往来于雪堂与临皋亭之间的生活情景。陆游见证了苏轼贬谪心路历程的去处,发出“惟绕寺茂林啼乌,似犹有当年气象”[1]感慨。苏轼的赤壁之游地点,是否为赤壁之战遗址,陆游曾做过一番翔实考证。虽然陆游并不认可黄州为赤壁之战所在地③,但体验苏轼的黄州赤壁之游,俨然成为追忆怀念苏轼的一种方式。
南宋文人张孝祥非常喜欢苏东坡,有“小东坡”美誉,其词风格与苏轼相近,豪放爽朗。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记载,张孝祥“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如何’”,可见他喜爱苏东坡程度之深。张孝祥有诗《黄州》,其诗曰“平生闻赤壁,今日到黄州。古戍参差月,空江浩荡秋,艰难念时事,留滞岂身谋。索索悲风里,沧浪亦白头。”赤壁与黄州,在张孝祥笔下形成紧密联系。黄州与赤壁的紧密联系,不能不想起苏轼贬谪黄州时所作的一词二赋。南宋另一文人戴复古,路遇黄州作《赤壁》,有诗句“白鸟沧波上,黄州赤壁边。长江酹明月,更忆老坡仙。”因黄州赤壁边是“坡仙”苏轼生活过的地方,诗人寄予别样深情。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怀着朝圣的心情,期望经由亲临践履,实地体验赤壁的风月”[10],一方面收获黄州美景带来的愉悦感,另一方面追忆怀念苏轼,从苏轼相似的宦海沉浮中获得认同感。苏东坡“通过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人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11]。
唐宋以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黄州这座小城渐渐进入文人的视野,受到文学家关注,且经过杜牧、王禹偁、苏轼、张耒、陆游等知名文人的描绘点染,黄州呈现出多彩的面貌。黄州这片土地,也不断被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而生机勃勃!
注释:
①关于杜牧在黄州时期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姜永满《外放蒹葭之场 心忧国民之难——黄州时期的杜牧论略》(《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杜牧黄州时期诗歌创作艺术成就鸟瞰》(《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拙作《杜牧贬居黄州时期心态及诗文创作》(《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略论杜牧的黄州纪游诗》(《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王禹偁在黄州时期的研究论文,主要有程秀利等《从〈竹楼记〉看王禹偁在黄州的复杂心态》(《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方星移等《王禹偁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面貌概论》(《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蔡龙威《王禹偁贬谪诗创作及诗史意义——以商州、滁州、黄州诗为例》(《学术交流》2017年第2期);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研究论文十分丰富,中国知网收录约190余篇,如潘炜《新时期以来关于贬谪黄州时期的苏轼研究综述》(《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概括对苏轼研究的主要成就,其后研究苏轼在黄州的论文及硕博学位论文仍接连不断;张耒在黄州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周进《苏轼、张耒黄州文学创作比较研究》(2011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方星移《谪官憔悴来天涯——论张耒谪居黄州期间的诗歌内涵》(《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②据《宋史》、明弘治《黄州府志》、清光绪《黄州府志》、清乾隆《黄冈县志》、清光绪《黄冈县志》统计。
③陆游《入蜀记》“又尝谓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表明陆游是对赤壁在黄州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