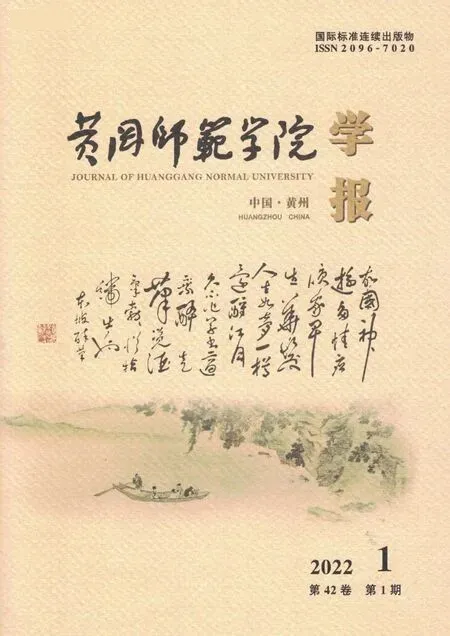中西勇德观及其现实意义和养成途径
荣延庆
(1.仙桃职业学院,湖北 仙桃 433000;2.仙桃市第三人民医院,湖北 仙桃 433000)
当今的和平年代,勇德似乎已经沦为故纸堆里的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作为道德的勇不过是一种过时的骑士精神式的历史残留物,在文明社会派不上用场的军人品质。对于某些人来说,勇德不仅不是一种品德,还暗示着暴力、战争或主宰他人的令人不愉快的状态,是与粗鲁相关的概念。”[1]但是,和平的多元发展的年代,或许是一个更需要勇德的时代,只不过这种勇德不是用来应对威胁,更多地涉及个体追寻个人认同、价值理性的坚毅。和平年代,人们不用为贫困、生存危机所困,然而,现代人常常为价值理性的没落、自我认同的危机所折磨。这样的状态中,需要一份从安全的混沌状态抽身而出的勇气,打破周遭安全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精神视界,人生归属感与责任感也由此生发。这种勇德是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良性进步的动力源泉之一。
勇,最早见于金文。《说文解字注》曰“勇,气也。从力,甬声”[2]。段玉裁注:“气,云气也,引申为人充体之气之称;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即人敢作敢为不畏惧的一种气魄。在包尔生看来,“勇敢是出于保持基本的善的需要而抵制对于疼痛和危险的本能恐惧的道德力量。”[3]
学界对勇德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勇德被视为一种结果性的成德、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勇”与正义的关联[4-6]。第二,强调勇德的理性层面,经由道德理性对欲望的控制,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坚定,上升为一种道德信念和德行[7]。第三,将“勇”视为一种内心状态,融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及道德意志为一体,在心理上达至情感与意志的协调[8]。第四,注重主体性的实在本体,肯定理想人格中的“勇”形成的一种精神风貌[9]。统观对于勇德的探讨发现,已有研究基本上是在对古文献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于勇德“是什么”的分析研究,偏重“勇”的内容分析,对继承勇德的途径探讨不充分。本文尝试从儒家经典中勇德的内涵及儒家勇德的三重境界出发,通过比对中西方文化中勇德的类同及差异,揭示勇德的特殊意义及当下价值,进而从生理层面及心理层面探讨勇德的继承途径。
一、中国文化中的“勇”
中国勇德在儒家思想中体现最为丰富,先秦时期是勇德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可见“勇”在儒家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在儒家道德规范中“勇”终究在于形成一股(勇)“气”,致“勇”之路经由“持(善)”。宋明时期勇德内涵继续发展,多了一份智慧与理性。近代国学与西学碰撞,传统勇德与新文化思想交融。
(一)勇德的形成:先秦儒家经典中“勇”的内涵及勇德三境界 儒家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仁”也是最高的道德范畴,“勇”是这一范畴中的子概念。《论语》:“刚、毅、木、讷近于仁”,即刚毅的精神接近于“仁”。《荀子》:“刚毅勇敢,不以伤人”,具有刚毅勇德的人能践行“仁”道。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是践行“仁”德过程中的勇敢行为。勇德是一种指向“仁”的道德实践。“勇”在《论语》中出现了16次,大多与“礼”“义”“仁”等同时出现:“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子曰:‘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勇”总是关乎仁德中的“义”与“礼”,儒家强调“知行合一”,“义”与“礼”之知要达至勇不可缺少“为”之行。
1.勇必有礼。“礼”是儒家伦理的重要要素之一。《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而致福也。” “礼”由一种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做人的准则、规矩、制度。“礼”范导个体人文化、道德化,从而整合为社会的一套仪式规则,在道德方面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礼”和“仁”是《论语》的两个核心概念,“礼”是通向“仁”的重要途径,“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就是培养“仁”之德。“仁”和“礼”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是道德品质,是理想人格;“礼”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具有外在仪节的规定性,是国家的法律或者地方的法规或者是部门的规章,“礼”具有调控人的行为、为个体进行定位的作用,约束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在社会规范上起到一种维系作用。笃守“礼”的规范让个体在道德践履中不失相应的度。也就是说,“勇”要循“礼”而行,以“礼”制勇。《国语·晋语六》:“勇以知礼。”可见“勇”中必有“礼”的制约和规范。“子曰:‘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这段话可见君子之“勇”与小人之愚蠢鲁莽的界限。也就是说“勇”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勇”就不合道德之要求,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因此,“勇”必有“礼”。
2.勇必有义。《说文解字》:“义,己之威仪,从我从羊。”《中庸》:“义者,宜也。”朱子解释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义”可以理解为一种适宜的、合理的道德准则。“义”在孔子看来,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的品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学而》篇第十三章首次出现“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它的解释是:“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10]也就是说,“义”是衡量一个人的品行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社会价值的一种行为准则,是一种恰当、合宜的具有一定外在强制性的准则。《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勇”没有“义”的制约就可能产生“乱”的结果。勇作为一种善德,应包含“义”的成分,正如孟子所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认为要靠正直来培养浩然之气,即要与正义、正道相辅而行。荀子认为士君子有真正的“勇”,因为士君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11]从儒家伦理来说,“义”是道德践行的最高准则,“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12]体现道义的原则,勇中有义,才是真正的勇德。君子之“勇”不是意气用事的鲁莽冲动,见“义”才可以“勇”为。“勇”中有“义”才是一种善的力量。勇敢中含有道义,符合“义”的要求,“勇敢而协于义,谓之义勇”[13]故,“勇”以“义”为规范,“义”是“勇”是否合宜的关键,有勇有义,见义勇为,才能称得上勇德。
3.勇必有为。义,勇之源头;礼,勇之规则基石;为,勇之落实点,为即做,即孔子说的“行”。“勇”不仅是义礼之上的不惧不恐,还是理性指导下的果敢决断。《礼记·乐记》:“临事而屡断,勇也。”在思考之后,迅速做出正确的抉择,有所行动,才是“勇”。《荀子》:“折而不挠,勇也。”勇敢的人在困境中能承受痛苦,坚持到底。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知道是正义的事,没有勇气去执行,是没有勇气、怯懦的表现。“勇”的核心要素是超乎常人的承受力,藉于此,在遭受痛苦时仍然能够笃定信念采取行动。“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君子当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君子在言行上从不苟且。《宋史·欧阳修传》中有一段关于“见义勇为”的阐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见义勇为的人,天赋其刚健勇猛,不管前方是地雷陷阱,还是万丈深渊,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见义循礼若无为,则为人格反例。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为”包含着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故能称得上于社会有益的勇德。“勇”落地为一种对抗与自我肯定相冲突的因素而“敢于”行动的能力。
先秦儒家经典中“勇”者的代表人物:北宫黝与孟施舍、子夏与曾子,还有孟子。本文尝试用这几位经典勇士来解释分析儒家经典中勇德的三重境界。
1.守气。北宫黝是勇士中最直观的代表:“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14]这表明北宫黝是为了维护道义,威武都不能使之屈服的人。孟施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具备勇士的勇敢无惧。朱子说:“北宫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动心。”[15]这两人的勇就是强制自己不惧,主要凭借一种外界约束力,死守住一股气,表现出无惧与必胜的气势,并以此威慑敌方,“粗”在于其主要是一种生理上的锻炼,心里没有义理的支撑。孟子的“勇”与“气”紧密相连,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气”是志气、气节,是一种精神风貌,需要长期的、艰苦的道德积累和道德践行,凝聚道德之善的长期的自觉的过程,是一种意志内省。自春秋战国始,好勇之风在儒家道德规范的社会体系中盛行,勇敢受到高度推崇,齐庄公甚至设“勇爵”以待勇士,《左传》:“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身为贵族却被人视为无勇,是莫大的耻辱。《礼记·檀弓上》记载了一则以死来证勇的故事: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这一阶段的勇主要功夫是憋住一股气,展示出一份“气壮”(但是还没有“理直”),所以权且称之为“守气”。
2.守约。子夏在回击北宫黝时说道:“所贵为士者,上不摄万乘,下不敢敖于匹夫…是士之所长而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16]相较之下,北宫黝对待平民百姓与君主,都是采取粗暴无礼的方式,只是“你不给我自由,我就游离于律法礼制之外去暴力争取自由”的侠客[17]。子夏以“义”为前提,以“礼”为规范,以“礼”视君,以仁爱之心待民,将“勇”之为与“义”“礼”结合起来,具备了义礼的勇就不再仅仅是勇“气壮”之“虚”,填补了“理直”之“实”。朱子把曾子的“缩”解释为“理直”。孟子曰:“……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赵岐解释“缩”为“义”也,“自反而缩”即通过自省觉得自己的行为符合“义”,从而无所畏惧[18]。曾子的“勇”是用“理”主宰了“气”,“理”是内质,“气”是顺势的外显,这一阶段的勇“气”不需要憋,不需要守,需要守的只是“自缩而反”的过程。福林把“缩”解释为“实密”:“缩之意蕴当有实密之意。若形容心理,缩是一种踏实、不空虚之态……这与理直气壮的状态应当是接近的或者一致的……”[19]故孟子把曾子的“勇”称之为“守约”。
3.大丈夫养浩然之气。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即儒家之理想人格。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既是理想之人格,也是勇者之最高境界:“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为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现实世界不管是困顿还是通达,都不能改变大丈夫行正道的志向,无所畏惧。这一境界的勇建立在对义理深刻认同的基础上,已成为一种道德力量。“血气之勇已化为道德之勇”,不仅在于战胜敌人,而是身心的充分统一并觉醒,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所畏惧[20]。孟子说:“我善养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 (《孟子·公孙丑上》)“志”指人的志向、信念与追求,“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气”指人有了志向与追求以后所展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气”与“志”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孟子认为,人只有做到“明道不移,集义(行每一件当为之事)既久”,浩然之气应然而生,因此孟子自称“吾善养浩然之气”,在孟子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养”出来的。浩然之气是孟子所提出的“大丈夫”所具有的一种信念和意志互相交融的心理状态,或说是一种精神境界。大丈夫善养浩然之气即是儒家勇者的最高境界。
(二)勇德的发展 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基础即儒家哲学体系,朱熹提倡的勇德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在承继儒学的基础上,从理学的角度完善勇德,突出思辨性,强调形而上。一方面强调伦理道德,突出纲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义理,对儒家道德的部分内容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朱熹对“知仁勇”三达德的解释是: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中庸· 章句》)在朱熹看来,知、仁、勇是通达之道,而不是目的性的“德”,那么,这三者便具备了相互通达的关系,这种关联性赋予勇德“知”与“仁”的成分,体现出勇德的知性之美。
近代,中国传统勇德在维新派思想和革命派思想体系下的发展演变也不尽相同。维新派以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梁启超认为“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勇德思想体现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主义中。严复提倡西方的实践精神,强调道德需要制度的把控,勇气不能超越制度。革命思想派以孙中山、胡适为代表。他们不仅提倡勇德需要“义”,而且对勇德表现方式及实施途径有明确表达。《孙中山全集》(第六卷)有载:“军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义,为世界上之大勇……军人之勇,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胡适融新文化思想于传统勇德,其主要在思想道德领域宣扬勇德精神,认为在社会改良的过程中,在对社会落后现象的摒除时需要社会大众的勇气。
(三)以今之价值体系反观中国文化中的勇德 “勇”由孔子提出时,只是说“勇者无惧”,“无惧”未必是一种品德,更不是一种肯定性的品德,而是中性的。勇在此时只是一种本真性的存在,一种个人气质状态,本质上尚是一种“为己”的儒学精神,属于修身养性的范畴。所以孔子的言论中并没有对“勇”的赞颂,或者说孔子并没有单独言“勇”,《论语·阳货》中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用而无义为盗”。“勇”在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上升为一种暗含当时政治价值标准的正面的德性,与使命感、社会道统以及民族大义等相钩联,“为己”不再是勇德的关注重点。礼义等古典行为规范成为“勇”之美德的支撑性内涵。中国当今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古人用以支撑“勇”的礼、义在某些方面已不适应社会的转型发展,或者说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沿用经典内涵标准来规范当今社会的勇德。古人所知,由于科学水平的限制,在今日之知看来,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愚昧的。建立在认知体系之上的礼、义带有的封建等级色彩,有些是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不相容的。对于勇德之经典内涵的批判性继承应当结合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客观需要,建立新的价值内涵及判断标准,也需要为勇德确立新的价值方向。这也是一个呼唤勇德的时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价值多元化,“勇”更多地指涉追求价值认同的坚毅与耐力。勇气体现在内心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在自我价值的建设过程中。勇德向“为己”的回归可能正当其时。
二、西方哲学中的勇德
西方的勇德最先体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中。出于当时的战争需要,希腊盛行英雄主义的尚武之风,荷马史诗把英雄的尚武勇敢视为最高美德。
英雄主义之后,希腊哲学对勇敢的阐释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与构成行动力的非知识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勇敢,勇敢是一种灵魂秩序;柏拉图对勇敢的定义是:勇敢是在认识什么是可怕的和什么是不可怕的后灵魂的坚定[21];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在过与不及之间,在两端的恶之间……勇敢的人,怕他所该怕的,坚持他认为正确的目的、方式及正确的时机”[22]。
中世纪之后,基督教文化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基督教义中的勇大致有两种:一是为信仰而献身的“勇”,这种信仰建立在对上帝的笃信之上,基督徒坚信上帝,虽然基督教并不提倡个人修养,提倡完全依赖上帝,但基督徒的终极目的是救赎自我灵魂;二是为了维护基督教的利益而战斗的勇敢,骑士是典型的勇士形象,骑士的行为准则深受基督教影响,为信仰而战。
从文艺复兴至当代西方社会,规则意识日益凸显,德性被边缘化。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重拾古希腊的德性传统,从不同的角度对勇敢做出思考。斯宾诺莎从情感的角度认为“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的思维趋势”[23];康德从理性的角度认为“勇敢是心灵通过思考后镇定地承担危险”[24];保罗·蒂利希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勇敢:“勇敢就是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不顾非存在这一事实,是个体行为,自我承担对非存在的焦虑,肯定个体的自我”[25];安德鲁·派恩认为勇敢是渗透着个人的意图、信仰等无所畏惧的行为[26]。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关于勇敢的论述,一般指向个人价值、心灵。
三、中西文化中勇德之异同
(一)中西文化中勇德之类同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勇”都以无畏、不惧(英雄主义)为出发原点。但无畏、不惧尚不能成为德,必须有其他“知”的因素加以引导或规范。中国儒家经典中的礼、义等都是使不惧成为勇德的条件,只有符合义、礼要求的行为才是合乎社会价值规范的;西方则从理性、宗教、律法的角度来规定勇,只有基于理性、皈依教义、合符法规的勇才是可以称赞的德性。随着律法社会的发展,社会规范的完善,社会律法、公众利益对勇德的制约性越来越强。
中西方文化都肯定勇德的多重价值,核心内涵是从外向内走向自治。勇敢的初始作用在于胜敌、克难,但最终指向个人品行修养、自我灵魂救赎。儒家传统中的勇德服务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遵从宗法制度的社会秩序,冒险创新的勇性精神往往是悖离封建等级性价值体系的,勇由对外不惧的力量向内发展,在社会价值的认同中演化为自我德性修养的控制力量;西方文化中尚武的英雄主义,本是用来克敌制胜的外部力量,经由基督教义的灵魂救赎,再到理性主义、本体论等,逐渐趋于对自我灵魂的叩问。
(二)中西文化中勇德的差异 中西方勇德的本质不同在于其背后的价值观的差异。西方文化中的勇比较直观,从克敌制胜到依赖上帝、虔诚奉献致救赎灵魂得到永生。对于大众来说,“勇”是简单直观的,这种“勇”对个人并不要求有多高的学问修养,只是要求信念坚定,是大众很容易达至的目标。
中国文化中的“勇”比较抽象。儒家文化中的勇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包含在“仁”之中,建立在“礼”“义”之上,靠正确的行为来支撑。儒家文化重视内心修养,崇尚礼仪规范,儒家虽然敬畏天道天命,但从未将美好品德的养成视为天赐,而是强调自我修养。中国文化中的“勇”是一种君子品格,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很高,大众很难达致,是少数君子经由严格的修身养性才能达到的道德境界。
四、勇德继承的当下意义
首先是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承担。中国农耕文化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以家族及地域为界限的自治的“熟人”社会被现代工业打破后,陌生人通过利益关联形成群体,通过完善制度来规范群体行为。社会道德陷入一种困境:善知但不勇为,但求自保。这其实是社会人对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采取的回避态度,明哲保身,理性算计,即一种不勇敢的态度。比如,人们能够意识到各种危机和困境,但敢于越过个人利益、冲破制度障碍为此战斗的只有少数尚存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勇士。作为现代社会人,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这些勇士一样具备担当“授命”的勇德,但应该鼓励对社会责任的勇于承担,对正义的勇敢维护。儒家勇德重视在道德规范下的个人修行,蕴含道德内涵的勇德是弥合善的认知与担当社会道义之行动的桥梁。
其次是精神上的自我担当。文化的融合,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个人的生活习惯、价值标准以及物质生活保障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冲击,转化为物质压力及精神压力。调节情绪、舒缓压力,认同自我,坚守信念,都需要通过自我修行来具备一定的勇敢精神,安抚灵魂,积极健康地生活。
五、勇德的形成路径
亚里士多德把人分为三种:鲁莽的人、怯懦的人和勇敢的人[27]。勇敢的人就是要去“鲁莽”、去“怯懦”。鲁莽即北宫黝与孟施舍的“粗勇”;“怯”字从“心”,不“怯”即不动心,“不动心”正是孟子对大勇之道德境界的解释,朱子说:“‘养气’一章在不动心,不动心在勇,勇在气,气在集义。”[28]由此,勇德的形成途径可以依据儒家经典中勇德三境界循序渐进。
(一)身有定力,即守气,令自我情绪有秩序 中国文化一贯注重“慎其独处之所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慎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其实质是将修身作为第一要务,在自我经验领域挺立善德的威严与绝对性,以坚决的态度统摄个体行为,指向至善,贞定、规制个体约束自我情绪,令行为合乎秩序。实际上是道德形上学之求得方式,讲究通过修养工夫引导个体抵达善德之境,“工夫”弥久以至于“气”,坚定追求之,能够理性地控制自我的情绪秩序时进入勇德的第二境界——
(二)心有认定,即守约,正确认识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士大夫往往是道德的优秀代表,在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能够大义凛然,源于他们对义理的深刻认知。其生存意义不仅仅在于追求个人美好生活,还有义务造福人类社会,为社会的公平公正而努力,为解决社会问题及人类困境而奋斗,成为社会“善”的一股力量。“个人善意追求和实现必须诉诸于城邦的共同善,社会的公共秩序是首要的善。”[29]勇德的义理内涵就是“公共的社会秩序”中善的内容。学习义理本质上就是一段道德认同的心理历程。通过教育接纳社会的善的秩序,比如,公平与公正、尊严与正义等,并愿意维护之,也就是说心中认定“善”,维护“善”,是勇德培养的必经阶段。
义理维护的是国家、民族、阶级、集体的利益,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正确认识公共的善的社会秩序。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存理灭欲”“杀身成仁” 等道德行为,经过道德教化和个人心理机制转化,将道德主张内化为道德情感和道德追求,达到道德认同。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凸显个体本位,追求最大可能地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不可厚非的。但在积极主动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冲突时,主张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并尽可能实现最大化,同时能对国家、民族、阶级、集体的利益保持一种公正的态度并能理性处理,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善”勇。认可合理的利己利他的思想,避免思想教育的教条,亲近个体心灵,让“善”勇与心灵需求达至契合,形成一股道德情感,进入新的勇德境界——
(三)情有执定,即养浩然之气,自造内心心灵秩序 当人的道德意志与社会公正的善的秩序融合为一体的时候,人的精神品质达到了最大的自由,善德也达到了最高的显现。孔子论人生的最高阶段“随心所欲不逾规”,为什么随心所欲却又不违背心中的道德呢? 美国积极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的概念是一个适恰的解释:心里的念头就像一条条钢筋洪流,浩浩荡荡但是又井然有序,势不可挡但是又能从你心所欲,喷涌而出但是又不会四处散落,而是汇聚成一条水龙,冲荡开一切泥石砂砾,创造、奋斗、整合,你不需要去特意控制这个过程,但一切又在你的掌控之中[30]。把自己的行动整合成一个心流体验,这是一种心灵的秩序。心流中的关键概念是:“心里的念头”。在勇德的形成过程中,心里的念头就是对正确的善勇的情感认同。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知言”是对天下事无所疑,养气是对天下事无所惧。养浩然之气之最高境界的勇强调对外观世界的充分觉解,面对任何人与事都无所畏惧,并且顺乎自我本心、顺乎社会规范,心灵秩序契合道德秩序、社会秩序。
经此三步,以养浩然之气!达夫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穷神知化,德之盛世[31]。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