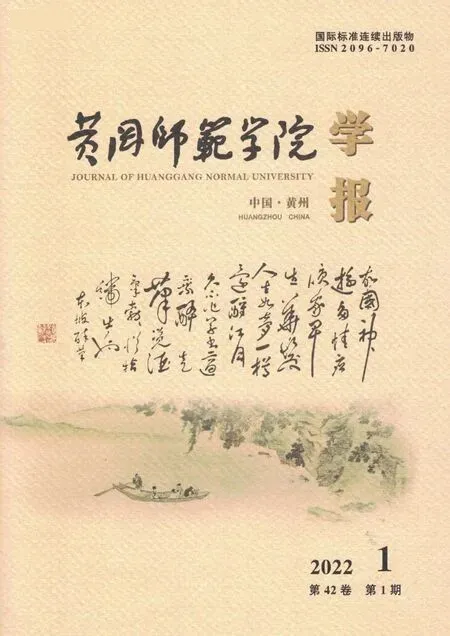点校本《苏轼诗集合注》缺误补正
彭文良
(重庆大学,重庆 401331)
清代冯应榴(1740—1800)的《苏文忠诗合注》(简称“冯注”)①集之前的王注②、施注③、邵注④、查注⑤、翁注⑥等众家所长,参稽辨补而成,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集大成之作。后虽有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⑦,实际是剪裁冯注而成,成就并未超越冯注。冯应榴的孙子冯宝圻认为王文诰的集成实乃“剪截移易”冯注而成[1];当今著名苏轼研究专家曾枣庄先生也认为“王文诰注实际主要利用了冯应榴注的成果”[2]353。冯注经黄任轲、朱怀春整理出版[3],为苏学士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献,实为学林盛事。然由于冯注搜罗的资料尚有遗漏,整理者惮于寻绎,以及冯注自身的注文多有错误,整理者疏于核实,致使点校本缺误甚多。具体说来,主要问题有:
一、冯注所收前人注释不全,点校者未进行补辑工作
冯注所收五家注里,施注是最早的编年注本,故最为重要,但施注散佚最为厉害(冯注所收另外四家注全)。宋刻施注(计42卷)原有嘉定本(1213年刻)和景定本(1262年刻)两个版本。施注至清初已经不全,嘉定本仅剩30卷,景定本剩32卷。冯氏所见仅为嘉定残本,故冯注至少缺12卷施注(其中嘉定、景定两本皆缺者6卷,嘉定本佚而景定本独存者6卷)。
首先,关于嘉定本、景定本共缺的6卷部分,清人所见有限,自然无法苛求他们补辑,但随着域外资料的发现,今天是完全可以完成补足工作的。比如点校本《雪后书北台壁二首》题下所引施注全缺[3]581。此诗在施注第九卷,嘉定、景定本此卷皆佚,故冯氏亦缺。但是日本诗僧大岳周崇的《翰苑遗芳》(1423年)卷七保留了此部分施注,可补:
王荆公《临川集·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眉山集》,东坡之文也。是时所在板行,荆公次韵盖第二首‘车’字韵诗。既和五首,又《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云:“靓妆严饰曜金鸦,比兴难工漫百车。水种所传清有骨,天机能识皦非花。婵娟一色明千里,绰约无心熟万家。长此赏懐甘独卧,袁安交戟岂湏叉。”介甫于文章未尝下人,况东坡因论新法,极口抵之。介甫可挤之者,亦不余遗力。至其文章叹赏乃独如此,信乎如精金良玉,市有定价,虽心惎恶,有不容掩也。介甫和篇固未尝示坡,后坡自黄移汝,过金陵见之,介甫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谓叶涛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乎哉?”赵德麟《侯鲭录》谓《雪》诗在黄州日作,误矣”。
补注共259字。所补内容极其重要,涉及到苏诗在当时的传播、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可以说所缺的施氏题注部分比后世的任何注释内容都有价值。
今凭借域外资料所补清人未见部分可以厘清前人诸多谬说。仍以嘉定本、景定本共缺的卷九中诗作为例,《苏州姚氏三瑞堂》题注部分,点校本所引冯注为:
王注任曰:熙宁六年癸丑,先生在杭州作。查注:《中吴纪闻》云:闾门西姚氏园亭颇足雅致,所居有三瑞堂。《吴郡志》:三瑞堂在枫桥,孝子姚淳所居。家世业儒,苏文忠往来必访之。尝爲赋三瑞堂诗,姚氏致香爲献,公不受。又慎按:此诗施氏本譌编密州卷中,今据《外集》改正。榴案:先生《答水陆通长老书》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是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又云:枣子两罨,不足爲报,但此中所有只此耳。玩书语,意似言枣为密州所产,则此诗竟似在密州作。施氏原编不误,王本注转不确,查氏改编亦误也。今姑从之,而附辨于此。至《外集》并不载此诗,查氏云“据外集改正”,亦误。
我们简单分析王注、查注、冯注内容:王注最简单,只注了此诗的编年;查注引了两部文献,特别注明三瑞堂的位置,当然地名注释是查注的长处,也是全书最具价值的地方。查注同时对此诗编年提出异议,并加以改编;冯注从苏轼文集中发掘一篇书信,以此为内证,推翻王注、查注之说,但又云“竟似在密州作”,语气模糊。点校者对上述诸家疑似之说当加以考论,当然限于材料不足,未进行此项工作,亦不宜苛责。今从《翰苑遗芳》可以辑录施注内容如下:
三瑞堂在闾门外道间,密迩枫桥水陆院。初姚氏之先墓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遂以“三瑞”名其堂。枫桥水陆长老通公者,东坡倅杭时往来吴中,舟必经枫桥,识通。姚氏子,名淳者,因通以求诗,而坡盖未始识淳也。坡守高密,答通二帖,淳亦并。《三瑞诗》刻于堂中。第一帖乃十二月十二日所作,其词云:轼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髣髴矣。后批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恶诗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是岁熙宁七年甲寅也。第二帖乃后一岁八月廿四日,词云:承开堂未几,学者日增,吾师久安闲独,迫于众意,无乃少劳,然以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也。后批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佳,然不须以物见遗也。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千万勿讶。三瑞堂者,考于《吴郡图经》皆无所见,屡访郡人而不可得,最后属平江观察推官赵君珌夫穷究得之。且云地已易主,诗刻亦不存,而以东坡二帖刻本相示。虽石已湮泐,而刊刻甚工,秀润可爱。
与前所引三家注相比,其详略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施注详细交代了三瑞堂位置,比以擅长地理名词注释的查注还详赡;发掘了此诗写作详情,苏轼原本不识三瑞堂主人,此诗写作仅是受与之熟稔的水陆院通长老所托而为,且堂之主人亦通过长老转托给苏轼礼物以示重谢,但苏轼退回,足见其高义;最重要的是,施注借墨帖中苏轼亲书时间确定了此诗的写作时间,破除王注、查注之误;最后还详考了南宋中期以后三瑞堂的存毁情况,其史料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诗注内容。诸如此类,凡嘉定、景定本皆佚之六卷部分、冯注失引者均可用日本注《翰苑遗芳》补,可为苏轼研究提供全新资料。
清代所有注家,包括冯应榴在内均只看到了嘉定本施注残卷,而较晚重现人间的景定本保留相对比较完整,其中有6卷内容为嘉定所缺,清代诸家未见,点校本亦未能借之补全。如《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题下所引施注全缺[3]2290。此诗在施注第三十九卷,嘉定本已佚,但今存景定本全,可补为:
器之姓刘氏,名安世,魏人。从司马温公学,得尽心行己之要。公得政,荐为正字。既薨,宣仁问光平日最所予者何人,宰相以器之对。遂擢右正言,迁右史,进左谏议大夫,以直谏奉祠、召为待制都承旨,出知成德军。绍圣间贬官,安置英州,徙梅州,投荒七年,至是北归。后知郓州真定府。蔡京入相,连七谪,覊管峡州。稍复官,卜居宋。卒年七十八,淳熙间赐谥曰忠世,号元城先生。器之在言职累岁,正色立朝,面折廷诤,人目之为‘殿上虎’。东坡与器之归自岭外,在章、贡相从甚久。两舟同发,江水忽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至吉之永和,器之始解舟先去。
补注计212字。此篇注文相当于一篇刘安世的小传,不仅有助于疏通诗意,甚至可补正史之缺。类此,景定本独存之六卷今皆可依之补全。
另外清初始见的30卷嘉定本亦非完帙,在流传过程不断损毁,至冯氏所见时比清初更为残缺,所以冯注动辄云“残缺太多”“残缺不可辨”,点校本皆仍其旧,实际上缺者皆可补。如《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诗冯注引施氏题下注为“东坡后谪齐安,王禹玉为相,挤于神宗。神宗意谓不然,子厚□□□□因解之。宣仁帘听。榴案:以下残缺不可辨补。”[3]621此处在施注卷十,嘉定本不存,但景定本和《翰苑遗芳》皆全,所缺内容为“子厚在政地,从旁因解之。宣仁帘听,两苏公皆进用。子厚时知枢密院,以子由论罢,致怨。子厚绍圣初相哲宗,东坡遂谪岭海。徽宗即位始归。子援字致平,东坡知贡举,擢居首选。还至京口,致平在焉,不复见,以书自通”,所补者达74字。
又如《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题下冯注此处云“此诗题下施注前半残缺太多,不可辨,大略指公择疏言常平勒民出息,神宗诘王安石,安石请诏常分析,公择以非谏官体,不肯对事”[3]623,冯氏描述与今存嘉定本残卷情形吻合,景定本此处完整,其辞如下:
李公择名常,南康建昌人。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介甫与之善。既秉政,以为条例司检详,改右正言、知谏院。介甫立新法,公择预其议,不欲青苗収息,至疏言:“今均输买贱卖贵,青苗取息敛怨,傅会经义,何异王莽?”神宗诘安石,安石请诏常分析。公择以非谏官体,不肯对。
施注,特别是其中的题注部分,涉及诗作背景、典章制度、时政史料,不只是研究苏轼文学,甚至对整个宋代文史研究而言皆具价值。但是因其残缺,上下文义中断,影响今人阅读,这尤需整理者广加搜求和补充。如《寄刘孝叔》是苏轼作品中反映王安石变法最集中的一首,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对变法的具体法令内容已经很陌生了,诸家注中唯施注在此方面最详细,然因其残缺,实为一大遗憾。此处部分,今点校本引为:“施注:刘孝叔名述。举进士。知温、耀、真三州,提点江西刑狱,荆湖南北、京西转运使。神宗擢侍御史知杂事,数论事剀切。会孝叔兼判刑部,与王安石争谋杀刑名。勅下,封运之。安石白帝,诏开封推官王克臣劾罪。孝叔率御史刘琦、钱顗共上疏弹奏:‘安石执政以来,未踰数月,中外人情,嚣然胥动。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惊骇物听,动摇人心。首以财利,务爲容悦。愿早罢逐,以安天下。’疏上,先贬琦、顗爲监。当开封狱具,以孝叔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司马文正、范忠宣力争之,乃以知江州。踰岁,提举崇禧观。东坡倅杭,与孝叔会虎丘,和其二诗。吴兴 六客堂,孝叔其一人也初,神宗即位,起安石于金陵,付以大政。而是时帝已有诛灭西夏意,遂用种谔以开边隙。安石逢迎帝意,且谓:‘鞭笞四夷,必财用丰裕,然后可以行其志。’于是终帝之世,以理财爲急,兵连祸结,南征西伐,几至于乱。帝虽欲改爲,而诸臣系其用舍,执之愈坚。晚岁始大悔悟,然无及矣。故此诗首言征伐之意。熙宁七年九月,韶开封府界、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枢副蔡挺之请,故云‘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先是,熙宁三年,管勾开封常平赵子几乞以乡户团爲保甲,觉察奸盗,各立首领部辖。□而推及天下,将爲万世长安之术。乃下司农寺详定条例行之。上尝问:‘如何可以渐省正兵?’安石曰:‘当使民习兵,则兵可省。’然其后保甲不能逐盗矣,故云‘保甲连村团未遍’。五年,司农丞蔡天申请委提举司均税而领于司农,始立方田均税之法,诏司农以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有奇爲一方,岁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计量,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委,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爲地符。故云‘方田讼牒纷如雨’。七年春,上以大旱,忧见容色,欲罢保甲、方田等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当益修人事。’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者,正爲人事有所未修耳!’初,吕惠卿建爲手实之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产,而官爲注籍。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八年十月,乃罢。故云‘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侧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苏子由□爲条例司检详,与安石议□□□罢。□□曰:‘苏轼如何?□□□□□□□’曰:‘轼兄弟□□□□□□□事,若朝廷□□□□□□则能合流俗□□□□。’故曰:‘平生学问止流俗’。是时安石凡议其新政者皆以流俗诋之也。孝叔年七十二卒。绍兴问録其风节,赠祕阁修撰。榴案:此条施注残缺尚多,内赵子几一条从《续通鉴长编》校补。”
此处注见于嘉定本卷十,景定本不存。今存嘉定本此处比冯氏描绘情况残缺还严重。今通过《翰苑遗芳》,缺处皆可补:“枢副”前二字为“副从”;“而推及天下”前一字为“因”;最后一段残缺部分为“苏子由初爲条例司检详,与安石议不合,乞罢。帝曰:‘苏轼如何?学问亦相似?’安石曰:‘轼兄弟皆以纵横捭阖为事,若朝廷是非决于流俗,则能合流俗者为有利。’”补足后,上下文义贯通。
以上因嘉定本散佚或者残缺而导致冯注失引、在点校过程中需要补辑的多达十余万字。
二、冯注注文存在很多错误,整理者只是简单点校,而未加核实
冯注注文错误,较常见的是援引原文且沿其错误。点校者没有核实原文,以致保留冯氏之误。如《送刘道原归觐南康》“世人共弃君独厚”句注,冯注引作“施注:杜子美诗:纵饮已拚人共弃”[3]236。此处嘉定本、景定本施注确实皆作“已拚”;然查《杜诗详注》[4]449、《杜诗镜铨》[5]181皆作“久拚”,故此处实为施注误,冯注未核,而整理者亦未查,皆误。《和章其出守湖州二首》其二“卞峰初见眼应明”句引施注作:“张元云:吴兴山墟名卞山。峻极,非清秋爽月,不见其顶。”[3]623查嘉定本施注作“张玄云吴兴墟名卞山峻极非清秋爽月不见其顶”(卷十,页29)。施氏原注其误有二:第一,作者当为“张玄之”,将“之”字误作“云”字;第二,书名当为“吴兴山墟名”,而漏一“山”字。至清代冯应榴原注,为避讳改“玄”为“元”,而点校者不明就里,仍之,且以为作者即“张元”;冯氏原注已经将施注中误引书名改正,但点校者未解其为专用名,故此处正确点断应为:“张玄之《吴兴山墟名》:卞山峻极,非清秋爽月,不见其顶。”冯注简单沿用前注而误者非常多,如《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君如汗血马”句注为“王注演曰:《前汉·大宛传》: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3]359,此处王注误,实出《汉书·西域传》[6]3894;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三:“吴儿生长狎涛渊”句注为“施注:《左传》昭公三年:郑子产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3]456,此处施注误,本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7]1421。这些错误,在点校本中皆未更正。
另外一类是原注本不误,冯注反改误,而整理者未核实而沿冯氏之误,比如《刘贡父》诗题下冯注引施注作“初以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与王介甫考开封试,因争《小畜》二音,语言往复,为御史弹奏,罢礼院及考功矣。”[3]267“与王介甫考开封试”,嘉定、景定本皆作“与王介考开封试”;考《宋史·刘攽传》作“考试开封举人,与同院王介争詈,为监察御史所劾罢”[8]10388。按:《宋史》所载与施注卷十一《同年王中甫挽辞》题注:“王中甫,名介,三衢人。与王介甫同学。会考开封试,与刘贡父言语往复,御史劾之,罢判鼓院”吻合,故施注原本不误,冯注误引或者误改。他如《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唱和四绝句戏用其韵跋之》其二中“欲问君王乞符竹”句注引施注作“《汉·武帝纪》:二年,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3]490,查施氏原注作“《汉·文帝纪》”本不误,反被冯氏误改;又如《胡穆秀才遗古铜器似鼎而小上有两柱可以覆而不蹶以为鼎则不足疑其饮器也胡有诗答之》“不如学鸱夷,尽日盛酒真良计”句引施注为:“《汉·陈遵传》: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3]492,其中“腹大如壶”,施氏原注作“腹如大壶”,与《汉书》[6]3713吻合,显然是冯氏妄改。除了援引他注有误外,冯氏自己的有些注也是有错误的,但整理者亦未核实,比如《圣灯岩》“何必吐光芒”一句,其注为“榴案:《史记·天官书》:填星,其色黄,光芒”[3]593,查《史记》实为“九芒”[9]1320,非“光芒”。
另外,冯注常常把邵注与施注、王注混为一谈,但整理者未加核实,简单相信冯氏,致使很多注释的归属权有误。比如《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微官似马曹”句注冯氏引为“邵注:《世说》:王子猷为桓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3]241事实上,此处句注嘉定和景定本施注皆全,明显是邵长蘅抄了施注而已,冯氏误以为是邵注,整理者未明就里,仍沿其误。类似例子很多,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中“效颦岂不欲”句注作“邵注:《庄子·天运篇》: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3]398,此处实际是邵注沿用了王注而已。同样,如《和张子野见寄三绝·见题壁》“山僧未忍扫黄泥”一句,冯注作“施注:小说:有富家子杜四郎,尝戏为诗章,号杜荀鸭,以比荀鹤。每有诗,即题屋壁。亲宾或污墁之,即云:‘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一杴泥。’”[3]626今查嘉定本卷十,此处正文“泥”字至注文“有富家”之“有”字前已经烧残,考其版式当还有数字,但绝非“小说”两字空距。查阅诸本,发现冯注所引施注实际抄自邵注,但邵注中作“常戏为”,而非冯注所引的“尝戏为”。查阅《翰苑遗芳》,此条注作“高若讷《后史补》:梁国有富家子杜四郎,常戏为诗章,号杜荀鸭,以比荀鹤。每有诗,即题屋壁。亲宾或污墁之,即云:‘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一杴泥。’”我们认为这才是施氏原注的内容,所补数字正好和今天烧残处位置吻合。明显,因为嘉定本施注此处至清初已残,邵氏删补时候查访未遍,无法找到准确出处,故瞒天过海,简称其出处为“小说”,这很不符合施注的体例;冯注仍邵注之误,又误将邵氏所抄施注之“常戏”妄改为“尝戏”,与下文“每有诗”抵牾。这些错误处,整理者皆未洞悉。当然作为整理,推敲到此,并不能算结束:虽然我们依据《翰苑遗芳》,知道邵注、冯注所谓“小说”,在施氏原注中实作“高若讷《后史补》”,但是《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后史补》,前进士高若拙撰”[10]324。所以,《后史补》的作者,到底依施注,还是依陈振孙之说,还需要考辨;即使不能确考,起码应该作一交代。然此类,冯氏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地方,整理者皆未逐一核实。
三、标点错误
标点失误,几乎是所有古籍整理皆难以避免的,此点校本亦如此。比如《述古以诗见责屡不赴会复次前韵》:“多谢清时屡推毂”句注为“王注:《前汉·郑当时传》: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也。”[3]488查《汉书》为:“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也。”关于“间说”形式和内容,颜师古注云“候天子间隙之时,其所称说,皆言长者也。”[6]2324显然,《汉书》的点断更合理一点。又如《再游径山》“觉来五鼓日三竿”句注为“王注:《南齐·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主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黄,日晕。”[3]475查《南齐书》标点为“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黄,日晕”[11]208,似更合理。又如《东阳水乐亭》“不须写入熏风弦”句注为“施注:《家语》: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3]459,按照此书体例,此处“南风”应当加波浪线;同书《张安道见示近诗》“欲和《南风》琴”句注“施注:《礼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3]846,此处“南风”即加了波浪线,推知前例亦当加。
四、对冯注妄改正文处,疏于出校,不符合整理规范
对于诗作正文,冯注存在直接改动而不出校的情况,整理过程中是有必要以校记的形式告诉读者具体的传抄实情的,但遗憾的是点校本在此方面缺乏基本的规范。比如《甘露寺》诗中“狠石卧庭下”“典型垂不刊”[3]280,宋刊《东坡集》、明刊七集本、邵注分别作“很石”“典刑”,王注、查注作“狠石”“典刑”,纪评作“很石”“典型”,王文诰集成本与冯氏同;如《赠孙莘老七绝》其二“碧澜堂上看衔舻”[3]384,宋刊《东坡集》、王注、七集本、邵注、查注作“堂下”,唯纪评与王文诰集成本与冯注同;《祥符寺九曲观灯》“纱笼擎烛迎门入”[3]400,王注、邵注、查注、纪评作“迎门”,宋刊《东坡集》、施注、明刊七集本、王文诰集成本作“逢门”;《山村五绝》其三“迩来三月食无盐”[3]412,王注、《东坡集》、七集本、邵注作“尔”,查注、纪评、王文诰集成本与冯注同。诸如此类,冯注未出校,已属粗疏,今人整理很有必要加以补充,以符合基本的规范。冯注妄改正文后,导致与注文不合,遂删注文以迁就正文,此等处尤需整理者出校说明。比如《和张子野见寄三绝·见题壁》“醉墨淋漓不整齐”[3]626,冯氏原注在“漓”下云“一作浪”。显然,此处冯注相当于出了简单校记,但需要整理者进一步展现历代传写情况以辨其真伪。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宋刊《东坡集》、嘉定本施注、王十朋集注本、明刊七集本、邵注作“浪”,查注、纪评、王文诰集成本与冯注同,皆只作“漓”。相比之下,冯氏原注相对比较严谨,毕竟还出了简单的校记,但整理者未作任何考辨和取舍。就此处而言,通过前面梳理,我们发现清初邵注及以前各注皆作“浪”,反倒是从清代查注以后皆作“漓”,从文献可靠程度上讲,当然应该采用前者,特别应该取信苏轼手订的《东坡集》。同时从注释角度反观,此处仅施注有注释云:“韩退之《醉后诗》:淋浪身上衣,颠倒笔下字”。至冯注,因其认定正文当作“淋漓”,故仅云“淋漓,见前《将往终南》诗注”,刻意删去了施注。冯氏在注释方面功夫甚巨,但关于苏诗正文的考校方面颇为粗疏,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冯氏主要盲从于之前的查注,而冯氏疏忽处正需整理者加以完善。比如点校本中《次韵曹子方龙山真觉院瑞香花》“纫为楚臣珮”[3]1667,前仅查注、之后仅王文诰集成本作“珮”,余皆作“佩”;《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录五首》之五:“不到双双燕子时”[3]1649,仅查注、冯注、纪评作:“燕子”,余皆作“燕语”;《祷雨张龙公旣应刘景文有诗次韵》“英气冠东莱”[3]1727,仅查注、冯注、纪评、王文诰集成作“英气”,余皆作“英风”。在诗作正文方面,冯注盲从查注,并影响后面的纪评和王文诰集成本。故综参诸本,可见冯注本身的问题很明显的,遗憾的是,需要整理者考校的工作皆未做。
冯注经整理出版,为苏学士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文献,本为学林盛事。然整理者只是简单忠实于原注,对缺者未补,对误者未改,亟需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补正。
注释:
①(清)冯应榴辑《苏文忠诗合注》,惇裕堂藏板乾隆刻本,乾隆五十八年(1793)。
②(宋)王十朋注《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景印本。
③(宋)施元之,顾禧,施宿注《注东坡先生诗》,1213年。
④(清)冯景,邵长蘅,顾嗣立,宋至补注《施注苏诗》,康熙三十八年(1699)。
⑤(清)查慎行注《苏诗补注》,香雨斋刻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
⑥(清)翁方纲补《苏诗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⑦(清)王文诰辑《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
——嘉定竹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