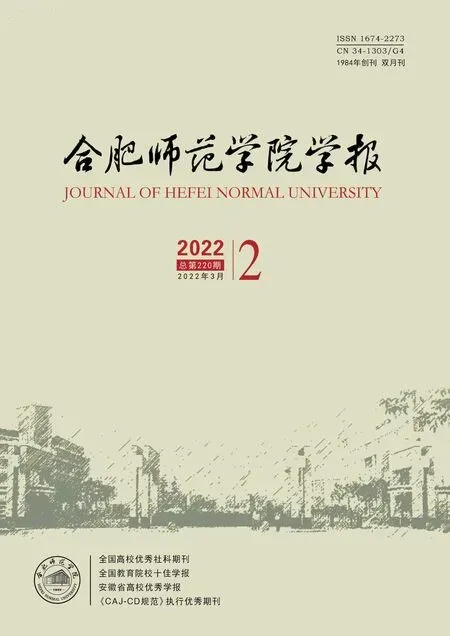上海叙事
——以《都市风景线》和《上海》为例
刘 婷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目前,学界的多数研究者认为横光利一的新感觉小说创作影响了穆时英的创作[1],却忽略了第一个将新感觉派引进中国的刘呐鸥。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于讨论刘呐鸥的台湾身份确认、性爱剥离以及创办《无轨列车》杂志等方面。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对现代摩登城市上海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海派”文学描写的基调。横光利一作为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2],《上海》更是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巅峰之作[3],历来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日本国内也是通过横光利一、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人的笔下世界来了解上海以及中国[4],从民族主义出发摆脱几百年来学习中国文化的落差感[5],为日本的近代化寻求合理的新位置与优越感。这两本小说同样是以上海为背景,描写都市中男女群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挖掘,本文将通过对中日作家笔下的上海城市背景进行文本比对,表现上海的两极分化,描述背后的原因,讲述同一城市留给读者的不同印象与文字描述,尽可能展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全貌。
研究横光利一和刘呐鸥二人笔下的上海,首开先河的是卢瑞忻[6],他将横光利一与刘呐鸥描写的上海城市风貌、都市男女形象进行了比较,分析二人因为切入的视角以及所处环境、自身立场的不同,勾勒出近代大都市现代气息与穷街陋巷的上海形象的差异,最直观、精简地看到两位作家笔下上海的区别。关于横光利一的研究成果颇丰,多为日语文学的研究,也涉及中日比较文学,多集中在中日新感觉派和对现代主义的学习两个方面。海外汉学研究对此也多有著述[7]。同样是描写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心的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有什么意义?二人描绘的上海图景为什么不一样?哪一个上海才是真正的上海?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两部小说的比较范围扩大到外部的国家、城市背景和明清小说中常常涉及的旅行者叙事,以都市男女形象的性别、种族以及在上海这个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为切入点,进行多角度研究。
一、作为“他者”的想象
爱德华·赛义德从西方对伊斯兰的研究中探讨东方学带有的强烈而专横的政治态度,之后整个东方包括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他者”一直被想象[8];葛兰西又以“文化霸权”这一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来建构西方的话语权力;20世纪50、60年代,以费正清、李文森为代表的西方研究者提出固化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将中国置于落后、被启蒙者的位置上;话语权力的主导权从欧洲崛起开辟大航线以后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他们对东方、对中国的看法充满了固执、偏见和想象。大部分西方作家对中国的了解是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的,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到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再到杜赫德神父的《中华帝国通史》[9]97,中国的形象一直被“传说”、被想象,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只知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想象她是第二个巴黎,上海是中国的所属,她连带着她的国家一直作为“他者”存在于异国者心中,上海的繁华、摩登、现代景象也是异国者的想象之物,以自我为中心,上海永远只能是异国者的“他者”。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现代化,不愿承认中国长达几百年的影响,想要极力摆脱这些过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力量出现并膨胀,在货币、殖民地等诱惑下,日本开始向往本土以外的空间,中国自然也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怀着对“天朝上邦”的想象与割裂,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登陆中国最发达、最现代化、最具有异国情调的上海,开启了他们新的想象,与中国作家描写的“摩登上海”截然相反的城市——上海。
横光利一的上海游记为日本对中国、对上海的想象增添了一份日本人主观臆想事实的可信度,以异国者、文化考察记者的眼睛游览“魔都”上海的城市布局、景象[10],认为上海既符合帝国晚期城市的典型特征又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11],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行走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现代化的摩登大楼、百货公司内商品琳琅满目,但他还是将上海描绘成一幅充斥着肮脏杂乱与不堪市井风气的画面,中国人也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站在街铺前闻着臭鱼、烂果的贫民[12]。正如酒井直树认为,涉及了日本性(有关日本人独特性的话语)的游记采用了一种“主观技巧”,通过一种“帝国主义的优越感情结”,将日本自身定位为中国的他者,同时又将中国的国民性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冷漠无情、一盘散沙的基础之上(1)见酒井直树在“想象日本:民族文化叙述”会议上提交的发言,斯坦福大学,1993年5月13日。。如果仅仅从草蛇灰线的城市连贯图来看上海,上海在他者眼中是那样的不入流,但文学中的城市是艺术的,不能只由单一的城市地图联结,人的活动才是中心。想象他者,以他者为镜构建日本的话语权力与来自殖民者的道德责任感,横光利一的“他者”身份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半殖民地上看世界的“帝国眼”和回写日本的文学想象。所以列文森说:“(上海)是无可救药的布尔乔亚的城市,它夸张的反封建姿态带有革命的色彩,尽管它看起来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或者至少也是半殖民地,如果不是半封建的话……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布尔乔亚是民族主义者,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布尔乔亚是最终走上了一条反动道路的国际主义者。”[13]上海以她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交相融合着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都存在于这座神秘的东方城市之中,没有明确的界定,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多种国家主义成分混合其中,她既戴着东方鬼魅的面纱,又以现代的姿态诱惑着西方,行迹不定,却同时影响着本土与异国者的心绪。
周作人曾评价上海:“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什么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14]上海代表着繁华和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因为他者的想象使上海成为妖魔化的象征。《都市风景线》暴露了上海资产阶级男女糜烂、空虚的堕落生活,把一切都视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男女之间的恋爱也都是性欲望的简单表达,情感是短暂的,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性在他们的潜意识描写中沦为寻欢作乐的工具与单纯的游戏行为,是和吃饭喝茶一样的日常活动。上海抛弃了一切有关乡土社会的淳朴、恬静、美好,陷入了撒旦的魔爪之中无法自拔,摩登上海就此成为人人向往的现代城市,灯红酒绿、万人空巷、熙熙攘攘,她也一直被想象着。“1949年以前,上海在西方文学中作为危险、异国风情和性爱的所在一直占有主要地位。”[15]上海的城市印象被定格在那里,被解读、被重构,亦真亦假,无法捉摸。
二、上海——城市风景
(一)城市风貌差异
1.刘呐鸥:摩登上海
刘呐鸥用街道上的电光、街灯填充着上海这座“不夜城”。汽车、火车为上海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作为现代化的产物,汽车的出现既能彰显主人的身份,又能俘获摩登女郎的芳心,恰好《都市风景线》台湾版的封面也是用汽车来表现他笔下的都市“风景”的;电影院内“紫色的黄昏支配着场内,一层薄烟的轻纱罩住着人们的头上,辨不大出他们的正体……”[16]32。西方文化进入上海,电影这种现代产物和电影院的布景都带有西方神话色彩,不论是堂文这样的公子哥还是镜秋那样的普通工人都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可见上海已融入了西方世界,现代是她的外在形象,内部的围城也在逐步向摩登靠近,一点一点地被蚕食,直至完成半殖民地化。
上海不止有刘呐鸥尽情描绘的商业街、租界这样摩登、充满异域情调的地方,还有藏在街边小巷中的弄堂,同样代表着上海,她褪去了华丽的外衣回归到了她半殖民地的“真实”,弄堂里有的是“阿摩尼亚的奇臭”,门店里吐出的令人发冷的阴森森的气味,油脂、汗汁、尘埃混合着味道[3]107,这一切都让摩登男女厌恶,“忙把一口厌恶的痰吐了出来”。这是刘呐鸥构建的上海城市景象,虽然也有弄堂这样背面的“风景”,但总体是对上海繁华表面与现代化场所的描写,电影院、舞厅、咖啡馆、百货商店这些才是他想象的上海,也只有这些才能代表上海的摩登。
2.横光利一:东洋垃圾场
横光利一“将上海形容为一个包含了怪异、道德堕落和污秽的具体体现”[17]292。他将上海城市风景描绘的重点建立在苏州河以及河岸之上,“每当满潮时,河水暴涨,便出现逆流……苦力身上湿漉漉的,残破不堪的黑帆随着钝重的波涛东倒西歪地吱吱嘎嘎地向前移动”[18]3。河岸上的苦力、俄国妓女对上海市民阶层的构造进行了补充,原来上海不是只有混迹于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光鲜亮丽的都市男女,也有迫于生计的压力不得不选择出卖力气和身体的社会底层人民。“破败坍塌的砖砌的街道。狭窄的马路上挤满了身穿长袖衣裳的中国人,他们就像海底的海带那样沉积在那里。乞丐们蹲在小石头铺就的路上。他们头顶上是店家的屋檐,屋檐下挂着鱼膘、滴着血的鲤鱼肉段。旁边的水果店里堆满了芒果和香蕉,一直堆到马路上。水果店旁边是猪肉铺。无数头剥掉了皮的猪,蹄子耷拉着,形成肉色的洞穴,幽暗的凹陷……从这猪肉铺和水果店中间直到挂着土耳其浴场招牌的店家门口,便是一条由歪歪斜斜的砖砌柱子支撑起来的长长的弄堂。”[5]24河岸边街道里的中国人,有乞丐、车夫、食客、占卦者、老太婆,街上的水果店和猪肉铺也和霞飞路上的百货商店相差甚远,上海的底层社会与上海的摩登风貌格格不入,在他们二人的书写下,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城市在现代化与不发达区域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空间分野[19],在这个奉金钱为万事标准的上海,穷人简直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只能祈求他人的怜悯和良心,好让自己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二)都市男女风貌
1.摩登女郎
摩登女郎作为现代主义的产物,是从西方世界引进的“一种好莱坞式、法日文学中的外国女郎的中国化身”,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特有的一种女性形象,带有中国人反对西方东方主义想象的性质。上海的现代化表现也是由摩登女郎这种独特形象展现出来的,是现代性城市的一张名片[20]。刘呐鸥的摩登女郎形象是“反男权制度、自主独立、都市风味和混血现代性的化身”[4]312,她们的横空出世突破了原有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化印象,转而与时代和现代主义接轨。作为异域产物,上海这个包容量巨大的城市将她们融入其中,“大部分在沪外国人都是日本人,这一事实打破了建立在种族界限基础上的殖民等级制度,而白俄居民低下的经济地位也成为打乱种族权力标志的另一个因素”[4]267。上海因她的摩登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群,由此摩登女郎的形象也带有了种族、国籍、职业等多方面的差异性。
(1)普通摩登女郎
追求自由、刺激,穿着时尚,高腰旗袍、高跟鞋、短发,吸烟、喝酒,喷香水,看电影、听音乐会、吃西餐,这些都是摩登女郎的标志性特征,摩登女郎在刘呐鸥的描绘下充满了肉感和大胆,常常表现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周作人认为上海的文化就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上海人对待女性的变态心理说明“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2)周作人:《上海气》,载《语丝》第112期,1927年1月1日。。上海的现代性伴随着女性群体的自我确认,传统的中国人在一时之间还无法接受这个嫁接的文化,对上海产生的一切都处于观望状态。也有像周作人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批判上海负面的“现代”,城市喧嚣,都市男女有别于乡土儿女的纯朴、自然,女性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有着“理智的前额”“随风飘动的短发”“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圆形的嘴型”“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是“鳗鱼式的女子”[3]6。新感觉派作家在小说中增加了对女性身体的描写,这些对外貌、脚踝的描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影星形象,虽是本土女性却被装饰为异域想象。摩登女郎通常不表露自己的感情,“H忙把她的手腕握定,但她却一点不露什么感情,反紧紧地挟住了他的腕,恋人一般地拉着便走”[3]84。她们爱得若即若离,对待男性不再是一味地单方面付出,牺牲自己在家做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她们开始寻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职业,不再将情感完全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她们拥有选择权,甚至可以游走在男性之中,已经开始出现了现代独立女性的影子。
(2)革命者
芳秋兰是横光利一“想象”出的革命女性形象,她有着东方温婉、标致的样貌,“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但这样一位集美貌、权力、革命和左右逢源的能力于一身的女性形象是横光利一作为一名日本人对中国女性的符号性想象,于是对于芳秋兰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否存在有三点疑问:一,作为革命者的身份被高重这样的日本监工猜测且宣传,她的生命和生活没有遭到危险和盘查吗?二,作为中共的同志,她可以和参木以流利的英语交流,说明她的学识和背景可能不是普通的党员,但另一方面,她又以纺织工人的身份出现,这两者之间不是有矛盾吗?这有些不太符合现实,当然不排除她是作为动员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领导人物的可能性,但这样引人注目的行为难道不是更容易引发他人的怀疑吗?三,五卅运动时,她让参木这个日本人来传递消息是否符合当时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背景?她以不同寻常的美貌吸引着甲谷、参木等人,借他们之口表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但她的行为和身份的构造又不太符合革命者的形象,也许只是横光利一为了反映五卅运动时的革命活动,恰巧女性革命者又比男性更具有吸引力和神秘感,所以创造了这样的革命女性形象。
就像中国留日作家笔下的日本女性形象通常是美好、体贴、顺从的模样一般,作家由日本女性造成的情感苦闷、受歧视没有影响到他们对日本女性的爱慕、怀念[21];出于同样的想象,日本作家对于中国女性的塑造受汉文化的影响,将她们美好化、飘渺化、神秘化,参木爱恋着芳秋兰但无法得到她的爱,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的男性作家达成了一致。
(3)白俄贵族女性
20世纪20、30年代流落到上海的白俄女性,基本上都是因为俄罗斯帝国内部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封建贵族阶级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亡命于远东地区甚至移民到上海来求生存。过去坐享其成的生活导致他们丧失了自我劳动能力,在花光积蓄的情况下,一些贵族女性不得不从事卖淫工作来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上海》中的奥尔加和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中的丽莎就代表着这样另类的“摩登女郎”形象。
一心等待死亡的丽莎回忆追溯着自己这十年来的上海流亡生活,“现在我确确实实地明白了一切。我的明白就是我的绝望。我已经不能再回到俄罗斯去了……我既不能回到俄罗斯去,而这上海,这给了我无限羞辱和无限痛苦的上海,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一定要离开它,迅速地离开它……唉,完结了,一切都完结了”[22]。丽莎从彼得格勒—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上海这一路上的迁移,她的身份也从贵族女性—流亡者—裸体舞女—妓女演变着,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魔力使得她变成了今天这样吗?曾经她向往着到上海、罗马、巴黎等大城市旅行,“上海是东方的巴黎”,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气息,它既有现代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富丽堂皇的商店、电车、汽车、电影院、舞厅、咖啡馆,也有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落后面貌的特征。作为异国流亡者,她以外国人的眼光审视着这座想象中的城市,缺乏本土化的焦虑感和思考,她没有把上海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内心深处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再回到她的俄罗斯帝国,这些异乡人常常伴有这样的思绪,无可厚非。上海对于丽莎只是短暂的落脚点,她的主观意愿不是融入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而是以路人的方式看待神秘的上海,甚至没有想了解这座城市,她流亡于舞厅、花园、旅馆只是为了挣到面包,可以生存下去。曾经的种族主义让她在内心中歧视印度人、中国人的想法都因为钱而不得不发生转变,上海这样的“魔都”确实让人欲罢不能,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在无形之中改变着人的命运,丽莎也只能顺着社会发展被卷入其中。
相比之下,奥尔加是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域外摩登女郎形象。莎伦·马斯库的《公寓故事》将城市空间与性别相关联,研究表明,“家庭私人空间中的女性是某个男人拥有的财产,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则成为其他男性临时租用的对象,常常被视为道德堕落的女性(妓女或邪恶的公寓女老板),或者被追逐、处在危险边缘”[23]。在私人、公众空间身份发生转变的奥尔加,被日本人几经转手出售交易却毫无寻求改变自身处境的意愿,她和丽莎的流亡有着相似之处并且最终也沦为相同的境地,这应该不仅是个人的经历情况,而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白俄贵族女性的一般状态,否则也不会有多位作家以此为故事的中心或次中心对这些女性在上海的生活、遭遇进行描写,来传达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阐述上海和摩登女郎之间的关系。但奥尔加又和丽莎在对待自身处境上有很大的差异性:奥尔加被村上赌马输给了山口,山口玩了几天玩腻了又让参木和甲谷来陪她,她实质上已经从明确具有“妾”身份的地位转变为任意被支配的身份,虽说两者之间的地位并未有较大的差别,但所属人物的不同导致她完全沦为了工具或者是交易物品,失去了主体意识却没有反抗意识,这也是白俄贵族女性沦落为上海的底层人物和子君、娜拉们的区别吧。
比较奥尔加和丽莎的形象,她们的种族特征、身世经历、个体生活有相同性,有作为外国旅居者的共性存在,二人也在成为性工作者的结局、渴望归乡的思想上有着一致性,但她们对于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化的城市存在不一样的见解:丽莎因为贵族革命的失败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上海只是她流落在外的暂居地,是异乡模糊的代表,换成巴黎、纽约、罗马中的任一城市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奥尔加对上海的想象是她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回到俄罗斯她也无法独自生活,只能回忆过往,上海和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给了她依靠,她已不再幻想回到祖国了;一个是被动留居上海,上海只是他乡,另一个则是主动地融入这座鱼龙混杂的东方城市中,把她当作自己的城市,一点一点地寻找缝隙将自己嵌入其中。
2.都市漫游者
上海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五大都市,从1843年开埠以来就被纳入了现代化进程中,当时半殖民地城市的现状又将上海的身份复杂化。生活在这样的上海,寓居于城市某一角落的外国人参木是“都市漫游者”的代表,他毫无目的地生活在这片纷纷扰扰的喧嚣之中,青年时期的暗恋者竞子已嫁作他人妇,在土耳其浴室喜欢的阿杉因为他的表态被老板娘解雇,因为厌恶继续为专务董事做假账而被辞退,种种的不顺遂致使他更加感觉到生活的无意义,他像行尸走肉一般漫游在异国他乡的上海,每天想着死亡。
刘呐鸥小说中的都市漫游者通过主人公的“新感觉”眼光,摄录下都市的瞬间碎片和新鲜体验,来表达新感觉作家笔下的都市超验叙事,将上海的十里洋场以漫游者的目光所及汇集到一起,呈现上海的现代风格以及都市男女的生活[24]。
刘呐鸥和横光利一塑造的都市漫游者形象大部分都是男性。主要以视觉为切入,用眼睛将读者带入上海的大街小巷中,目睹上海的繁华景致,勾勒城市的娱乐地图[25],又将主人公的朋友或者是偶然相遇的陌生人一起拉到电影式的镜头之下,他们漫步于街头巷尾,毫无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当下的美好,和美丽的女子走在路上也是一种美的风景,可以向路人炫耀他有一位美貌的伴侣;又或是闲来无事逛一逛生活的这个城市,以路人的眼光游览着上海的一切,却与之无关,是纯粹的看客,用脚步丈量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感觉,也不知该去往何方。
三、旅行者的“上海”
1699年,传教士李明出版了他的《现时中国》,批评西方的旅行家和商人关于中国的记述中充满了道听途说和庸俗的无聊之谈[26]。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大航海时代以来直到现在都处于盲目、想象、偏见的阶段,其中有过赞赏性的描绘,赞叹中国的儒家文化、哲学思想的理性化、物质上的富裕、帝国的大一统状态,也有过停滞、专制、野蛮的丑化形象,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样建构在对上海的城市想象之上。通过游记这样的虚构/非虚构叙事文本将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融入旅行记中,读者接受在此基础上又会有不同程度的想象与传播,因此各种各样的游记不由自主地将“实录”变成了“传奇”,对中国、上海的想象也出于自己的立场发生了或好或坏的改变。
乔治·罗伯逊说:“旅行叙事本身就是一种隐喻。”通过旅行描写叙述人的活动轨迹以及心理想法甚至是传达作者本人的心声,这一切人的活动皆可由旅行过程完成。列维-斯特劳斯在《热带的忧郁》中说,“旅行通常被认为是在‘空间’中进行,但同时也是‘时间’与‘阶层’的转换,任何印象必须与这三者相连,才能看出意味”。空间和时间上的旅行是表面与实质上的活动,但阶层是潜在的,将三者结合在一起,让旅行不再是单一的地理环境移动,而是笼罩上了文学叙事的含义。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中也注意到了“旅行者的叙事功能”这一环节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叙事方向。横光利一创作《上海》,一是因为应芥川龙之介的邀请为报社撰写新闻稿,二是他想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向日本社会及广大国内民众传达上海的实际情况[27],将自己的军国主义思想建立在山口、甲谷、参木这些日本人的形象之上,借他们之口表达自己作为日本国民的优越性和自豪感。这也是横光利一以自己的实际旅行见闻为素材的艺术加工,他作为旅行者对上海的描写既有客观的城市景象,但也因为某些原因对上海的现代化进行片面的勾勒,笔下摩登的上海也是真实的上海。这就不得不引发出到底哪一个才是上海的真面目的问题。
马可·波罗在13世纪从威尼斯出发到元大都传教,从此开始了他旅居元大都的生活,他将十几年来的见闻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形成了《马可·波罗游记》广为传颂,西方人也从他的游记中开始了解神秘的东方,满足自己对中国遍地是黄金的设想;《利玛窦中国札记》使得“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从传奇进入历史,然后又被再次传奇化”[2]136。中国一直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之中,又由于物质上的财富使西方的帝国主义力量对此觊觎已久,由“黄祸”产生意识形态上的恐慌持续不断地升温,中国作为他者吸引着西方、日本的异国者的好奇心,间接地出于经济贸易、文化考察、个人兴趣等多方面的原因,他国旅行者展开了对中国的观察。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现代化典范的上海,他们经过自身的家国利益、民族偏见、寻找侵略他国的合理借口等考虑将上海描绘成他们脑海中的想象的面貌,旅行者出于个人化的原因描绘他们看到的、想象的上海,鉴于两者的不同叙述,从两位作家的妙笔中辩证地看待真正的上海就成为了题中之义。
20世纪20年代,刘呐鸥经由台湾、日本回到大陆生活,他在日记中提及自己无法适应上海的生活,“上海真是个恶劣的地方,住在此地的人除了金钱和出风头以外,别的事一点也不去想的。自我来上海了后愚得多了,不说灵感,睿智,想象,就是性欲也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变成一个木人了”(3)转引自彭小妍:《浪荡天涯:刘呐鸥一九二七年日记》,《中国文哲集刊》第12期,第16页。。虽然刘呐鸥回到祖国,但对于他本人来说,上海其实是他旅居的城市,他对于上海的描写也是旅行者的叙述,这样一来他和横光利一的叙写前提达成一致,都是他乡遇上海。不同的是,作为本土作家,刘呐鸥竭力想要刻画上海的现代化——五光十色的摩登城市风景以及永新、大世界、卡尔登这样的时尚潮流聚集地,刘呐鸥将他见到的城市表面建筑、饮食、街道、摩登的行人以“感觉”的笔触记录下来;另外,可能是因为刘呐鸥作为资产阶级作家这样的身份本身,他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咖啡馆、电影院、跑马场、舞厅这样的地方,描写起来比较容易。而横光利一是出于考察外国城市的目的,活动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以脚步丈量着城市的各个区域,意图将整个上海尽收眼底。“但不管如何,海派小说没有仅仅把外滩、南京路诠释为上海全体,是它的文化观之大幸。弄堂也是上海,而且是一头连着世界潮流,一头连着中国本土的那种上海。”[28]167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刘呐鸥和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一个写的是上海的繁华,另一个写的是乡土上海(尽管带有某种偏见),不论是否真实,上海作为半殖民地的城市代表,摩登或肮脏都是她的本来面目,不必刻意隐藏,也不过分张扬,她仍旧以她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以上海为叙事背景,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中日两部文学作品,以上海的城市风景、都市男女形象、旅行者眼中的上海为叙述点,展开论述两国文学中描写的上海的不同与形成此不同背后的原因,将横光利一对上海的他者想象书写展现半殖民地处境下的上海风貌和刘呐鸥笔下十里洋场的上海形成对比,以此尽可能地完善读者对上海城市的印象。
横光利一对上海的描写注目在她的滞后性,以半殖民地城市、工人阶级暴动、人民生活贫苦为设定条件,通过视觉认知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着重勾勒旧上海弄堂的破旧、拥挤、杂乱;苏州河和黄浦江交界处的鲜明对比,一处连接着国际性大都市无尽的繁华、艳丽,而另一处则是底层人民生活的地方,臭水沟、污泥到处都是,就像骆无涯声称的那样“繁华两字的背后就是黑暗,表面上越繁华内幕里越黑暗”;而刘呐鸥的本土文学创作,借新感觉派的思想、艺术手段表现上海大都市的繁华景象,注重都市“异国情调”的诗意渲染,他频繁使用西方现代流行语来描述中国的都市图景,想把上海塑造成他想象中的现代城市,对上海的城市、现代化生活充满了迷恋和憧憬,以至于李欧梵说刘呐鸥描写的上海“不全是上海现状的真实写照,而是一组‘超现实’的狂想曲”[29]。
那时的上海,是都市现代性和爱的场所,摩登女郎的大胆、狂放与这座扑朔迷离的城市相得益彰,摩登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摩登女郎不再囿于“五四”时期的女性纠结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桎梏,她们成为社会的强者,将男性的权力进行了解构,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意义。她们性感的身体、放荡不羁的性格、大胆的行为举止都是反东方主义的想象,上海的摩登女性在城市空间和地域中将自己的身份明确化、肯定化;作为半殖民地城市的上海,她是帝国主义剥削和种族主义盛行的场所,外国人到中国的旅行、采访、考察活动是为了收集中国文化材料,为他们的他者想象增添所谓的亲眼所见与亲身感受,将自己的见闻组织成文学作品昭然于世,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和走在时代前沿的摩登上海。横光利一的《上海》呈现出来的强国对于弱国的轻蔑和俯视,是带有民族偏见的,近代日本全盘学习西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不再是臣服于中国的番邦,他们急于摆脱中国在文化、思想上对日本的影响,在经济、政治层面上的优先致使日本国民产生对中国的蔑视心理。作为帝国主义者的日本有大量的民众移居到中国来开拓疆土,为了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掠夺,横光将上海的工人运动描写为无组织的阶级暴乱,革命者芳秋兰的结局也是不明确的,参木在等待日本陆军的登陆,可能明天的他就有了国家的庇护,他“都市漫游者”的身份也就消解了。
多方面因素致使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在中日作家眼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想象和描绘,但不论是出于帝国主义者的偏见还是有意识地将上海描绘成“东洋垃圾场”的横光利一,上海的破败、肮脏、落后已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中国人仍会对刘呐鸥笔下的摩登上海记忆犹新,甚至从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旧上海的印记。日本文学中的上海带来的影响对现在的研究依然是有帮助的,它提供了多角度看待问题和两面性比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