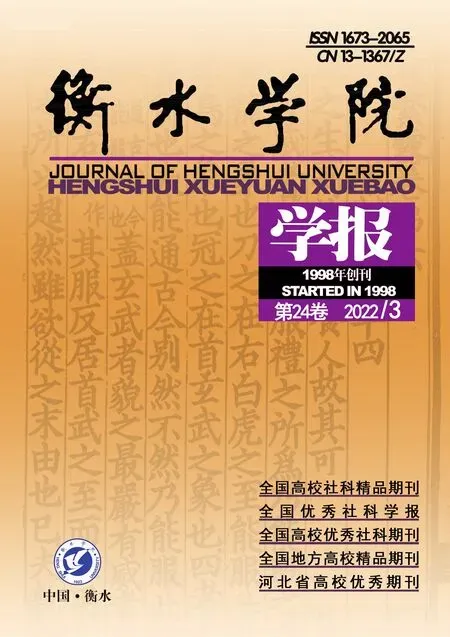“文本于天”——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刘国民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
“文本于天”——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刘国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奉天而法古”是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奉天”即法天道,“法古”即法圣人经典之道,这蕴含着“文本于天”的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来源。其二,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即天人在道德、情感等方面相感应、感通,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追求。天人同类相应不仅仅是隐喻方法,更是思维方式,把古人的内心世界(德性、情感)与天地的外部世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三,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中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文本没有恒常不变的原义,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文本。其四,董仲舒指出《春秋》文本的基本特征——“微言大义”,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一是《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深层义有间距性,解释者由文辞的字面义入手,又要突破其字面义而把握其深层义,“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二是《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背离,即“微言”“讳”,要求解释者推见至隐,以把握事实的真相及其隐含大义。
董仲舒;哲学思想;文学;文本于天;天人合一;《诗》无达诂;微言大义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的哲学,第二部分是春秋公羊学思想,学人对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阐述。但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学人关注不够,论述较少[1]。究其原因大略有三:一是学人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法天道”与天人感应,天是人格神之天,天人感应有神秘性,且“天道”“人道”主要指自然法则、道德法则,与文学之道没有什么联系。二是学人多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论述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的含义广泛,包括文学,但文学置于其中,不能独立出来[2]。三是学人也注意到“《诗》无达诂”对文学阐释的影响,但理解似乎绝对,即解释者可根据主观之意任意曲解[3];也未能运用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掘发“《诗》无达诂”学说的现代意义。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讨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不当之处,方家正之。
一、奉天、征圣、宗经的文之枢纽
“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以下只注篇名)[4],是董仲舒基本的哲学思想。所谓“奉天”,即法天道,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根据。《天人三策》云:“道之大原出于天。”[5]所谓“法古”,即法圣人经典之道,《春秋》是圣人的经典,孔子体察天道而作《春秋》;《春秋》是人道之大者,“法古”即法《春秋》之道,法圣人之道。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义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天人三策》)
天是万物的本原,故圣人法天道而立人道:天生育万物,布德施仁;人君养育万民,仁爱万民。孔子作《春秋》,上法天道,下切人情。由此,天人相应,古今同道。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
董仲舒认识到天地的大美,表现出对美感的欣赏和追求。天地的大美,不仅指日月星辰的明丽之美,而且指天地养育万物的仁德之善。天道是天地的自然形态之美与仁德之善的统一,而侧重于仁义之善。《俞序》:“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王道通三》:“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地的仁德之善是人伦道德的终极根据。
天道、人道的内容丰富,包含为文之道,故董仲舒“法天道”的哲学思想蕴含着“文本于天”的观念[1]。“法天道”,不仅包含对天地自然形态之美的体认和描写,而且包含对天地仁德之善的赞颂和效法。这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天地自然之美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对天地仁德之善的重视。天地的仁德之善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具有感发人心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后世文学对道德内容的特别重视。唐代文人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明确地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此“道”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
天道深微,圣人体察之而著书立说,上达天道而下切人情,成为经典。《俞序》:“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春秋》上深察天道以为王道的根据,正人君以正万民;下建立是非得失的标准,而为后圣所法则。《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董仲舒认为,《春秋》之义是“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道包含为文之道,故为文要宗圣人的经典,经典之道以天道为根据。因此,董仲舒说:“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楚庄王》)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包含为文之道要法天道、经典之道的内容。
董仲舒“文本于天”的观念对汉大赋的创造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大赋以巨丽雄奇、包举万端的气势,极力铺陈天地、山川、园囿等大美,表现了对天地自然形态之美的重视。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同时,汉大赋的道德劝谏内容正是对天道、圣人经典之道德意义的诠释。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首先极力铺陈豪华奢侈的生活与新奇的美景,具有强烈的美感,唤醒了人们追求生活嗜欲和新奇美景的强烈愿望;接着规劝天子要提倡儒家“六艺”,修明政治,“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而实行仁义之道。赵明等主编《两汉大文学史》曰:“汉代经学昌盛,不但以宗经、征圣、原道的理论影响了汉人对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从而影响了汉赋的内容和意识倾向,而且经学风气影响了汉赋的文风,影响了汉赋的创作特点。”[7]
董仲舒法天道、圣人经典之道的思想,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征圣、宗经”的依据。《序志》是《文心雕龙》的序言,阐发了刘勰作此书的目的、意图和内容安排。《序志》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原道》《征圣》《宗经》等,是文之枢纽,而置于《文心雕龙》的首三篇。
“原道”之“道”的含义是什么?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原道”之道是指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原道”即本于天地之道[8]。《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日月之明丽、山川之焕绮,是天道之文(外在的文采之美),文学作品法天道之文而有辞采、藻饰的美丽。“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文心雕龙·原道》),仁孝是天道之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要之,刘勰的为文之道本于天道,天道包含人伦道德的内容,即董仲舒所谓“文本于天”。
刘勰认为,圣人能把握天地之道,且体察之而为文,所以作文必须以圣人为师、以圣人之道为证验。《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圣人立言作文而成为经典,经典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故建言为文须宗经。《文心雕龙·宗经》:“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问丽而不淫。”文章六个方面的要求皆根据圣人所作的经典。《文心雕龙·宗经》:“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认为,楚骚之艳、汉赋之侈的流弊,就是因为没有宗经,故为文立言必须“征圣”“宗经”,以达到“正末归本”之目的。
综之,董仲舒认为,人道要法经典之道、天道;刘勰认为,建言为文要征圣、宗经、原天地之道。因此,他们的思想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董仲舒之人道、经典之道、天道偏重于政治和人伦之道,也包含为文之道;而刘勰之道偏重于自然之道、为文之道。章培恒说:“刘勰这里所说的‘道’与后来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不尽相同。他是指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9]“奉天而法古”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性格。
二、天人合一的境界
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凊;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
人受生命于天,即为天所生,故天与人同类。一是“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天人在仁义道德上合一。二是“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有春秋冬夏,春秋冬夏之气是暖凊寒暑,人之喜怒哀乐之气与它们相应,这是天人在情绪上合一。《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其一,天人在道德上互相感应、感通:天地的仁德之善感发了人的善心,人的仁善之心省察、体认了天地万物的美德,这构成了天人在道德上合一的境界。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王道通三》)
天生成、养育万物,终而复始,不辞劳苦,天有仁德之善,天与人在仁德上合一。
董仲舒的《山川颂》,描写了山川的自然之美,但董仲舒之目的是通过自然之美以阐释山川的人伦道德之美,自然山川获得了人伦美德的内涵。
董仲舒首先描述了水的自然特征,然后予以人伦道德化,水具有了“力者”“持平者”“知命者”“善化者”“勇者”“武者”“有德者”等优良品格。这正是君子所具有的美好德性,董仲舒在山水之间寄寓了君子深厚的道德内涵。因此,人们在观照山水时,不仅陶醉于山水的自然之美中,而且受到了山水道德之美的感发教育,澄汰了内心深处的私意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侧重以人伦道德意识来解释自然山水的特性,而淡化了山水的自然之美,加强了山水的道德教化之善。这种观念无疑受到了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
其二,天人在生命情感上互相感通。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阴阳二气的运行形成四时,四时之气与人的生命情绪紧密联系。
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阴阳义》)
春喜、夏乐、秋怒、冬哀,四时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与人之喜乐怒哀的情绪相互感通,融合为一。
阴始于秋,阳始于春。春之为言,犹偆偆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偆偆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忧悲之状也。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王道通三》)
春天,阳气出,温暖和畅,万物开始萌芽生长。春与人的喜乐之情相应。秋天,阴气出,寒冷肃杀,万物衰老凋零,秋与人的悲忧之情相应。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构成了中国文学“春喜秋悲”的永恒主题。
是故天之行阴气也,少取以成秋,其余以归之冬。圣人之行阴气也,少取以立严,其余以归之丧。丧亦人之冬气,故人之太阴,不用于刑而用于丧,天之太阴,不用于物而用于空。空亦为丧,丧亦为空,其实一也,皆丧死亡之心也。(《阴阳义》)
冬天到来,太阴之气出,寒冷肃杀,万物凋零,空空如一。四时之冬及其衰空之景与人之衰死而葬的悲戚之心感通、感应,使人产生无限的悲伤。
要之,天人合一,即天人在道德和情感上相感通,早已深植于先民的内心之中,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经过董仲舒的诠释,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化、理性化了,成为人们自觉、理性的追求。李炳海先生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古代作家普遍的审美追求。天人合一理想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到汉代又有新的发展,并且在各个领域更加具体化。汉代作家都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创作的宗旨,努力去营造他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理想境界,在各类的文学体裁中,都可以见到作家的执着追求。”[10]
今日看来,天人并不是同类,而是异类。董仲舒之天人在性情与道德上合一实际上是异类比附,即隐喻。从表面上看,隐喻是文学创作的方法。深层地看,隐喻是古人的思维方式,即隐喻性思维,把人之内心世界(德性、情感)与天地的外部世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这是对《诗经》之比兴和《楚辞》之香草美人之托喻的理性化和理论化。《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之艳丽多彩与少女之靓丽姿容及“宜其室家”的德性美融合为一。《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僻芷、秋兰是香草,又指人之美好的道德品质。这是通过隐喻把香草与美人之德容相融合。杨义先生谓之“芳草喻”,“把自然芳草和人生美德这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二者,关联在一种所指和能指互相生发的特殊情景中,以其一点相通(‘芳草’)而联想到全部,把难以言说的人的本质化为自然生物现象”[11]。这种文学创作的手法及隐喻性思维渊源有自,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现在和未来的思维方式。
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文学创作、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秋风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自然之秋的萧条零落与人生短促、佳人难得的哀情互相感发。《陆机·文赋》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四时物色的变化引起感情的激动。《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气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四时不同,风景不同,人们所感发的情感亦不同:春天悦豫,夏天郁陶,秋天阴沉,冬天矜肃;这与董仲舒春喜、夏乐、秋怒、冬哀的情绪是一致的。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春风、夏雨、秋蝉、冬月皆感发人之情感,“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欧阳修《秋声赋》:“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以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秋声赋》受到了天人同类相应思想的重要影响。董仲舒说,秋天,少阴出,万物零落,天人相应,人在秋天始行刑,“伐有罪,讨不义”(《五行相生》)。按照五行相生之说,秋配金,《五行顺逆》:“金者秋,杀气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钺,以诛贼残,禁暴虐,安集,故动众兴师,必应义理。”《五行五事》:“金气也,其音商也。”董仲舒从情绪和理性上揭示了秋天的特征。欧阳修侧重从情感的层面描绘秋景,抒发秋情。他先描述了秋之色,“其色惨淡,烟霏云敛”;秋之容,“其容清明,天高日晶”;秋之气,“其气凛冽,砭人肌骨”;秋之意,“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之声,“其为声也,凄凄切切”等秋景;接着他抒发了“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的生命短促、零落之感。天人同类相应,天人合一。
三、“《诗》无达诂”的解释理论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固然受到春秋时赋《诗》言志与汉初三家说《诗》的影响,而主要是他在解释《诗》《春秋》经传之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它肯定了解释者的创造性与经典之义的多元性、开放性,但经典之义并非“什么都行”,可任意曲解;“《诗》无达诂”揭示了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相似,而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从《春秋繁露》《天人三策》三十余处引《诗》来看,董仲舒往往引一首诗的几句,以证明他的观点。例如《玉英》曰:“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难,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诗》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德輶如毛”见于《诗经·烝民》,其语义是德轻如毛。《毛传》解释此诗的主旨:“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此句之义与整首诗的意义相去甚远,这是断章取义。董仲舒由此句的语义“德轻如毛”,引申为“易为”的抽象义,而发挥“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的隐喻义。《荀子·强国》:“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荀子征引“德輶如毛”阐发政教功名积微至著的含义。郑玄笺:“德甚轻然,而众人寡能。独举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三家的解释不太相同,《诗》义表现出多元性、开放性的特点;但董仲舒谓“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与郑玄云“政事易为”有相似性,也体现了变中有常。
再例如《竹林》曰:
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
“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于《诗经·谷风》。其表层义:葑菲之菜,上善下恶,食之者取其枝叶之善而弃其根之恶。董仲舒认为,葑菲之叶可食而根不可食,但不因其根不可食而不采其叶,即“取其一美,不尽其失”。他进一步以之阐释司马子反的事情:司马子反私通敌情,有“内专政而外擅名”的过失,但他有仁爱民众的美德,故应取其仁爱之德而弃其专政擅名之失。这是以隐喻的方法把葑菲之菜与司马子反之事联系。《度制》:“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采葑菲之叶,不能连根都拔除,从而隐喻“君子不尽利以遗民”(以余利遗民)之义。关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董仲舒两次阐发的意义不同,表现了“《诗》无达诂”的思想,但他的解释也是有依据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文公与先轸有一段对话: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12]
《左传》引此两句,隐喻用人取其善节,例如桓公重用管仲,取其才能卓越的善节,而不计较管仲曾与之为敌的行为;这与董仲舒第一种解释是相似的。
要之,董仲舒说《诗》义,不主张通与一,而有权变;他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概括出“《诗》无达诂”的解释方法。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精华》)
达,通也,一也;《诗》《易》《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辞、通义。《竹林》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楚为夷狄,根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应称楚为“楚人”以贬斥之,这是常辞、常义。但《春秋》在此称“楚子”而褒扬楚为君子,这是变辞、变义。因此,《春秋》没有通辞、通义,是常与变的结合,变与常相矛盾,但变是合理的。董仲舒解释说,楚在邲之战中表现出仁义之善,故称楚子以褒之。奚齐是未逾年之君,应称“子”(常辞),但是《春秋》谓“君之子”(变辞)。董仲舒解释了其变辞的合理性:“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精华》)
综之,《诗》《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辞、通义,而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常为主而变为辅;变与常相对立,但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常,坚持《诗》《春秋》之辞、之义的经常性;变,表明经典之辞、之义的变化性和多元性。董仲舒在解释《春秋》的实践中反复运用和阐释之。《精华》:“《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义有常变,常辞表现常义,变辞表现变义。《竹林》:“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变义不合常义,表面上相矛盾,但深层地看,变义有合理性,故不能否定变义。《竹林》:“《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之道,是常道和变道的统一;常产生于一般的情境,变生成于特殊的情境;二者不相妨碍。
《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否定了经典之义的一元性和恒常不变性;经典之义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常义是经常的意义,易于理解,而变义具有权变性、灵活性,难以解释。因此,董仲舒在解释实践中特别重视对变辞、变义的分析。因为变背离了常而没有一定的标准,故解释者对变的阐释需要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对变作出合理的、创造性的解释。这给经典之义带来了变化性、开放性。但是,变并不表明解释者可以任意曲解,而要受到常的一般限制,经典之义绝不是“什么都行”。
董仲舒为何提出“《诗》无达诂”的思想呢?
第一,《春秋》本身没有恒常不变的通辞、通义,而是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对立统一。《公羊传》正是根据常与变对立统一的观念解释《春秋》。此种例子在《春秋》中不胜枚举。例如,鲁国十二公即位是同类之事,但《春秋》未书隐、庄、闵、僖即位,其他诸公书即位。《公羊传》在类比类推中归纳出《春秋》书与不书鲁公即位的常辞、常义:人君正常即位的,书即位,如文、成、襄、昭、定、哀;继弑君而立的,不书即位,如庄、闵、僖。据《公羊传》归纳的常辞、常义,隐公非继弑君而立,应书即位,桓公、宣公继弑君而立,不应书即位,但此三公皆书即位。《公羊传》认为这是变辞、变义。《公羊传》隐公元年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返之桓。”“公何以不言即位”是对变辞的质疑,接着解释变辞的义理根据:隐公即位是为了桓公,将返位于桓,《春秋》褒隐公有让德,故不书隐公即位。《公羊传》运用常与变对立统一的观念,合理地解释了《春秋》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因此,“《春秋》无达辞”是《春秋》本身的特点,也是《公羊传》和董仲舒解释《春秋》的基本方法。
第二,董仲舒解释《春秋》,一方面阐发《春秋》的本义,另一方面又要建构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论证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故其解释的主观性较强。如果他坚持《诗》《春秋》之义的恒常性,就不能为其主观思想的发挥提供合理的依据。他肯定权变的重要性,即肯定《诗》《春秋》之义的变化性和开放性,也肯定解释者之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因此,他明确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思想,且充分运用到具体的解释实践中。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13]
《公羊传》的解释较为平实。董仲舒精心达思,推见大义: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其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人三策》)
“春”代表天,其次序在“王”之先,表明天比王尊贵,所以王必须尊天、法天;“正”的次序在“王”之后,表明王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他由此阐发了尊天、法天的重要思想。人君法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人三策》),即天道是人道的终极根据。这是董仲舒天的哲学的重要思想,正是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中发挥出来的。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中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相似,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经典没有恒常不变的一种本义,经典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经典。经典之义是常与变的对立统一,变表明经典之义的多元性,常坚持经典之义的稳定性,经典之义在变通性和灵活性中坚持常。
四、“微言大义”的书法
董仲舒之解释《春秋》,揭示了《春秋》文本的基本特征——微言大义。“微言”有两层意义:一指《春秋》文辞简约,一指《春秋》文辞隐晦。一般而言,文辞简约而意义单薄,文辞隐晦而意义深微。但董仲舒认为,《春秋》言辞简约而具有丰富深刻的意义,即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谓“辞约而旨丰”;《春秋》言辞隐晦而大义著明,即《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因此,解释者要从简约隐晦的言辞而推见丰富显明的《春秋》大义。
《春秋》“微言大义”的表征之一,是《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深层义的间距性。仲舒认为,《春秋》之辞有字面义与深层义两个层次,深层义即《春秋》之义;字面义与深层义没有逻辑的联系,而产生了间距化,通过字面义很难理解深层义,故深层义即《春秋》之义是深微隐晦的。董仲舒说:“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竹林》)“辞”,即文辞字面义;“指”,即《春秋》之义。文辞字面义与《春秋》之义产生了间距,这就不能直接从文辞字面义把握《春秋》之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故解释者必须由文辞的字面义入手,但又要突破其字面义,即“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春秋》“微言大义”的表征之二,是《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背离,即“讳”。董仲舒认为,“讳”与掩盖事实真相不同,它在记事中已暗示了与事实真相不合,从而启发解释者推见至隐,以把握事实的真相及其蕴含的深刻意义,这即“讳而不隐”。《春秋》之讳的主要原因是“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公羊传》定公元年,何休注)。孔子生活于定公、哀公之世。定公、哀公恩义深厚,孔子不忍彰显他们的罪恶,而且直接揭露他们的罪恶,也恐招致杀身之祸。但掩盖他们的罪恶,又违背“《春秋》之信史也”的实录原则。因此,孔子运用“讳而不隐”的书法。董仲舒说:“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也。”(《楚庄王》)
“微言大义”的书法对史学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史学家,司马迁必须具有实录的精神和勇气,不畏惧当代的政治和学术权威而敢于揭露事实的真相,但这势必冒犯权势者的忌讳而引起灾祸与阻挠。在此两难困境中,司马迁运用《春秋》“讳而不隐”的书法。《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司马迁多采用“微言”“讳”的笔法,以隐约暗示他的真实思想,故解读《史记》者必须推见至隐,才能深察司马迁之意。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彰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表面上看,“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是对刘邦受天命为帝的褒赞。实际上,汉得天下,既没有像夏、商、周积善累德十余世,又未能像秦用武力数世,故汉没有得天下之理,只能归结到不可理喻的“天命”。“大圣”,即超过圣人之圣,是不能以理性加以理解的。这正是怀疑刘邦得天下的合理性,此即“微言”所在。
在楚汉相争中,韩信是一位“得之即得天下”的军事统帅。他为刘邦取得天下立下了汗马之功,但终以“谋叛”的罪名而被诛杀。《史记·淮阴侯列传》用“微言”的书法暗示了韩信被冤杀的悲剧命运。其一,韩信幽于长安而与陈豨密议谋反之事,不可信。韩信与陈豨避人携手之语,谁人知之?这种纪录的矛盾,即所谓“微言”,暗示了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符。其二,韩信平定三齐,威震天下,项羽使武涉劝诱韩信背汉助楚,全文有二百四十余字,《史记》详载之;齐辩士蒯通规劝韩信自建三分之业,全文有一千一百字,《史记》详载之。这两段文字竟占了《淮阴侯列传》的四分之一,即“微言”,表明司马迁深辨韩信谋反的冤屈。清人赵翼说:“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乎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14]其三,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论韩信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即“微言”;韩信在威震天下时不谋反,而在“天下已集”时谋反,这实不可信。因此,司马迁通过微言的书法,暗示韩信之谋反实出于吕后的诬陷而成为汉家的一大冤案。新儒家徐复观说,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以“微言”的书法暗示韩信被冤杀的悲剧命运[15]247-248。
关于《史记》“微言”书法,学人多有论述。韩兆琦说:“所谓特殊书法,是说它不像一般书法那样一目了然,毫无争议,它是用了一种奇特的,一种委婉含蓄的,甚至有些看来是近于离奇荒诞的方法来写人叙事的。作者有褒贬、有是非,但不易看清楚,稍不经心,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学术界之所以对司马迁的思想观点、对《史记》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争议,也常常与此相关。”[16]徐复观说,《史记》多用微言侧笔,暴露人与事的真实[15]251。
《春秋》微言大义的书法,也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
《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鷁”,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
首先,《春秋》一字见义,即公羊家所谓“一字褒贬”。《文心雕龙·史传》:“(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其次,董仲舒认为,《春秋》之辞的先后次序有尊卑贵贱的深层意义。定公二年夏五月,火由两观起,灾及雉门,但《春秋》先序雉门而后及两观,因为雉门尊而两观微,即刘勰谓“‘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这表明《春秋》之义深微,“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其三,《春秋》之辞的字面义明白易晓,而《春秋》之义深微难知,“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其四,《春秋》“微言大义”的书法与刘勰主张为文之道“辞约而旨丰”一致。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主张文学作品的创作应遵从“以少总多”的原则,而避免汉赋“繁而不珍”的罗列方法。其五,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谓“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肯定了《春秋》之讳、“微其言”的书法。
[1] 刘怀荣,苑秀丽.论董仲舒的文学思想[J].东方论坛,1997(3):60-65.
[2] 潘世东,邱紫华.“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终极理想设定[J].中国文化研究,2000(秋之卷):12-16.
[3] 张峰屹.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J].南开学报,2000(1):45-49.
[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13.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18-2519.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7.
[7] 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140.
[8]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著[M].济南:齐鲁书社,1995:21-24.
[9]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69.
[10] 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境界[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31.
[11] 杨义.楚辞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4.
[12] 李学勤.春秋左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77.
[13] 李学勤.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8.
[14] 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72.
[15]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6] 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8.
“Text Originating from Heaven”: The Influence of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Literature
LIU Guo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089,China)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ical thought hav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First, following the Heaven’s will and imitating the ancients” are the basic thoughts of Dong Zhongshu. “Following the Heaven’s will” is to follow the way of heaven, and “imitating the ancients” is to follow the way of the classics by the sages. This contains the concept of “text originating from heaven”, which, in Liu Xie’sis the source of the thought that writing should follow the way of heaven, the way of the sages and the way of classics. Second, Dong Zhongshu believes that humans and nature are of the same kind, that is, humans and nature are responded to each other in terms of morality and emotion,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s people’s literary creation and aesthetic pursui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s not only a metaphorical method, but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combines the inner world (virtue, emotion) of the ancients and the outer world of heaven and earth into an organic whole, thus constituting the realm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ird,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poetry defying fixed interpretation” reveal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ext interpretation, which forms his interpretation method. The text has no constant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meaning of it is pluralistic and open; the interpreter can interpret it creatively. Fourth, Dong Zhongshu points out that subtle words with profound meanings,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text inalso constitutes his interpretation method: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words in, and the interpreter should start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words but breaks through it to grasp its deep meaning, that is, “If you grasp what it means, you can ignore its word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ngs recorded indeviate from the truth, that is, “subtle words” and “unreal things”, which require the interpret or to speculate and reason so as to grasp the truth of the fact and its hidden meaning.
Dong Zhongshu; philosophical thought; literature; texts originating from heaven;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poetry defying fixed interpretation; subtle words with profound meanings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2
刘国民(1964-),男,安徽肥西人,教授,文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等研究院重大课题“汉代公羊学之解释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
B234.5
A
1673-2065(2022)03-0008-09
2021-09-0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