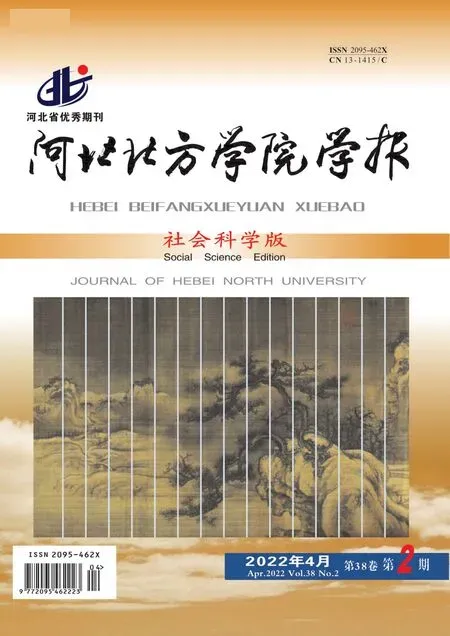近代文化博弈与县域教育行政工作重心的转移
周 璇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时期都存在着文化博弈。各种文化在博弈中通过相应的策略选择,边缘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扩展自我文化的生存空间,实现自我文化的张扬与凸显,从而在文化场域中处于优势序列和占据主导地位。”[1]传统社会亦曾有百家争鸣的文化博弈时代,最终儒学脱颖而出成为官方思想,中央与地方官学多授儒家经典。近代多次的文化博弈打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县域教育行政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呈现出儒学署重科举选才与化民成俗、劝学所重私塾改良与推广新学以及教育局(科)重社会教育和义务教育的特征。
一、儒学署重科举选才与化民成俗
在儒学为尊的传统社会,一县之学的工作重心是开展儒学教育。有学者认为,在清末设立劝学所之前不存在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因为明清之际的县学主要负责科举岁考,而不负责教育行政事务[2]。目前,学界公认劝学所是近代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开端。然而,传统社会对教学事务和教育行政事务的区分并不明显,“政教合一”和“庙学合一”是常见现象。如“宋代国子监所管辖的学校系统中,尤以国子学与国子监关系密切,二者经常合并。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又是全国最高学府”[3],兼具教学与教育行政的职能。县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自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距今已存在两千余年,是传递上级政令和规划地方工作的重要枢纽。既然县内有行政单位,即便没有设立专门且成熟的教育行政机关,也应有与之类似的机关代行部分学务管理之权,或履行类似职责来规范并管理县域内的各项教育工作。
县学是一县的地方官学,受中央管控和领导,县之下不再设行政单位。因此,乡和村的教育多由宗族村落自行组织,以伦理规范教育族内子弟或本村村民。如果学生想走科举正途,便须进入地方官学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子夏有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途”与“学途”都同地方官学关系密切。一,普通民众欲入“仕途”大多需逐级参加考试,故需入地方官学学习;二,为官者欲教化百姓,需下令整饬地方学风,故需关注地方官学情况。一县之学,上承为政者意志宣传主流文化,下选佼佼者为国储备人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有对县学进行学务管理的必要。“汉唐以前,地方教育由地方行政监管,负责人统辖地方州府县学、推行文教政令、负责考试选拔及祭祀活动;北宋时期,中国开始设立专管地方教育的机构和行政长官,专管州县学务管理的专门机构谓之提举学事司,长官谓之提举学事使,负责审察和委任教师、监督生员学业以及学校经费管理等事务。元明时期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谓儒学提举司,清在每省设学政衙门以统领全省府、州、县、卫的学校,长官谓之学政。”[4]清朝时,儒学署常与县学并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学务管理的重要作用,工作重心为科举选才与化民成俗。
儒学署主持县学事宜时,兼顾教学与管理之责,并体现出以儒学为重心的教育价值取向。
在教学方面,其一,儒学署所主持的县学课程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同时,亦讲解宋明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和注疏,以及本朝史实、典礼、律令和八股文等①。学生学习儒家的治国安民之策,日后在为官执政时会进一步巩固儒学的统治地位。其二,除专讲经学之外,儒学署的明伦堂还因其地势宽阔能容纳较多百姓而发挥着社会教育作用,有化民成俗之效。其三,儒学署的布局设置和学堂称谓属于一种“隐性教育”,亦表征着传统儒学文化。儒学署居正中的明伦堂是正殿,是学校讲学和弘道的主要场所,这符合传统社会以中为尊的文化特征。教谕宅(署)和训导宅(署)则分列在明伦堂两侧,两者与县学的官职相关,均为县学的官职名,《教育大辞典》中对教谕和训导作释义:教谕一般为正学官,掌管文庙祭祀等活动;训导为副职,居于辅助地位,协助教谕教导所属生员。因教谕为正而训导为副,故教谕署在东为尊。训导署在西为卑。可见,儒学署中的明伦堂、教谕署和训导署的布局都谨遵礼法,潜移默化地向生员及百姓传递传统社会的尊卑礼制文化。此外,明伦堂的“明伦”二字取自《孟子》中的“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一言。明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社会人际交往之道。“教谕”与“训导”二字均有“教育训诫”之意,主张教育多用循循善诱和因势利导的方法,少用惩罚措施,这体现出儒家重德治和重教化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管理方面,儒学署统筹一县之学的祭祀、科考以及选聘教师、招收生源、监察生员学习、考核生员功课和筹备办学经费等事务。其一,儒学署主持祭祀事宜。古时设立学校必祀奉孔子,若文庙、县学与儒学署设在一处,便会形成庙、学与署一体的格局,由儒学署中的教谕和训导掌管文庙春秋二季的祭祀活动。由于儒学署内所供奉的多为孔子及历代诸贤,因此祭祀活动主要是祭孔。清代各帝将祭孔作为一等重典,每年春秋仲月,即农历二月和八月为祭孔时节,上自朝廷下至府县都要拜祭孔子[5],儒学署通过祭祀孔子的活动可以加强县域内民众和学子对儒学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其二,儒学署主持科考事宜。县学最主要的科考事宜是童生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3步,考生只有通过了3级考试才能获得生员资格。县试就是在县学内举行的考试,考察内容为儒家知识,多为5场,即八股文、试贴诗、经纶、律赋和策论。通过县府院三试的学子可以进入地方官学即县学,成为一名官学生员。生员进入县学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县学内部依然会进行成绩考核,择优送试。以诸城县为例,该县学实行“三岁两试诸生”制度,即县学内有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3类学生,“先以岁试以等第高低,附生补为增生,增生补为廪生。再经科试,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①,被选出来的生员在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过后的次年可以参加在京城举办的会试,最终进入国家的人才储备队伍。儒学署通过主持科考发挥了挑选与输送人才的重要作用。此外,儒学署还负责教师选聘、生员招收、学业考核和经费筹办等事务。在经费筹集方面,儒学署也体现了儒学所提倡的勤俭思想和劝学文化。儒学署会以租佃学田②的方式筹备办学经费,所筹经费物资用来举行祭祀活动、为教师补薪以及帮助读书人等。尽管儒学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行政单位,但它代表着儒学在文化博弈中的胜利,代表着传统社会官方选择的价值取向,维系着儒学的官方文化地位。
二、劝学所重私塾改良与推广新学
近代以来,中国原有的以传统儒学为主流价值的文化秩序被打破,新一轮的文化博弈拉开序幕。伴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中国难以再延续闭关锁国的旧状况,被卷入复杂的文化洪流中。传统儒学与各路文化对抗的过程就是文化博弈的过程,这与知识分子加快了与西方的交流密切相关,“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各种文化因其独特的生成和发展特性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征,由此使文化的交往呈现出相互交流与碰撞、对话与交锋的共生样态”[1]。在中西学之争中,知识分子也曾试图实现文化共生,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来改造传统儒学,但最终还是新学在“中西学之争”中更胜一筹。受此影响,县域的儒学署变更为劝学所,并进行私塾改良和新学推广。
近代中国文化的博弈不止一次,有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博弈有洋务与守旧之争以及维新与洋务之争等[6],这两次文化博弈为新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其一,洋务与守旧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学西学。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希望将西学引入中国。然而守旧派坚持忠信礼义的道德文化,对西学嗤之以鼻。尽管守旧派极力反对学习西学,但也未能阻挡洋务运动兴办西学的步伐。洋务派于1862年立同文馆开西学课程,并不断增设新学科,“在英、法、俄文馆外增设布(德)文和东(日)文馆,并自同治五年起相继开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多个科学馆”[7]来培育人才。知识分子对洋务运动的人才培养效果评价不一。“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仅初习皮毛……而奕劻等奏称同文馆设立20余年……实属卓有成效。”[13]洋务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是一次融汇中西之学的尝试,是中学与西学两种文化在文化博弈与冲突中找寻平衡支点的初步探索。
其二,维新与洋务之争的实质是怎样实现中西并重。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知识分子进一步反思自身对中西之学的态度,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总有相通之处,教育亦需中西皆学,提出“凡学生皆当通习也”。当时,清朝县域内儒学署中的地方官学主推儒家之道,由于地方官学的生员名额有限,且教授内容集中于儒学知识,故书院与学堂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肩负起更多的西学教育之责。在提倡“中西兼学”的文化博弈结果下,“戊戌变法期间,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8]。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教育逐渐从“中西学并重”转变为“西学为重”,主要表现为中学课程的经学比重逐步减少以及学习科目倾向于分科化等,西学似在文化博弈中占了上风。然而,在科举制仍存的情况下,有的学堂出现了荒谬的景象:在平时,学生都到学堂中学习西学等技术知识,而在科举考试期间,学生便纷纷忙于参加科考,依旧希望通过科考来改变出身并踏上仕途。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博弈虽然会带来教育风向的转变,但政治层面若不作出相应变动,教育变革依旧步履维艰。一言以蔽之,科举不废则新学难推。
20世纪后期,废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1903年,袁世凯和张之洞上疏奏请渐行罢废科举,“使天下士子,舍学堂别无进身之路”[9]。1904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上奏折言“科举未停……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能专心向学”[10],再次申明科举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新学的推广与实行。清廷迫于形势于1905年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令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西学之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它间接影响了县域学务管理工作的重心。科举制被废后,儒学署和县学的教官不必再负责教学及选材工作,若只典守文庙和奉祀孔子则显得大材小用;若弃离儒学署,则县学名存实亡。可见,不必再主持童生试的儒学署失去了其存在的核心意义,加之清政府令各县推行新学广设学校,需另立新的县教育行政机关进行学务管理,故儒学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劝学所应运而生。
1905年,《山东官报》颁布了《紧要事件:直隶学务处拟定各属劝学所章程》,指出“劝学所为各厅州县全境学务之总汇,以本地方官为监督”。1906年,清政府正式将“劝学所”作为新的县级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一县的学务工作,并制定了《劝学所章程》。据统计,“从1906年学部明令推行劝学所到1909年学部进行第一次教育统计时,全国已有五分之四的州县创设了劝学所”[11]。依据《劝学所章程》的要求,劝学所设总董一人,总理各学区之事务;在县域内划定各个学区,并设品行端正且热心教育的绅衿充任劝学员,以推行新学事宜。科举制度虽废,然其影响力仍存。在推行学务方面,劝学员遇到了来自塾师等群体的阻碍,改良私塾并安顿塾师成为劝学员新学推广工作中遇到的首要难题。因此,1909-1910年,清政府相继颁布了《学部通行京外凡各私塾应按照本部奏变通初等小学简易课程办理文》和《改良私塾章程》,欲将私塾改为学堂,逐步推广新学。但私塾改学堂并非易事。私塾先生多是教授传统儒学的知识群体,其知识储备以及教学方法等与新学差异较大。而私塾教育本身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废止,于是,政府“采取改良的办法,通过培训塾师、开设新课程内容、改革教学与管理的方式方法等来逐渐达成与现代学校的统一。一些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私塾教育逐步走上新式学堂的道路,但是偏僻地区的塾师依然难以摆脱封建思想”[12]。为了更好地使劝学员明确自身职责,加速私塾改良与新学推广,1906年颁布的《直隶学务处各属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区劝学员应先于本城劝学所会齐开一教育讲习科研究学校管理法教育学”,对劝学员进行讲习教育。
劝学员肩负多项职责。其一,是劝学之责。《劝学所章程》第六条规定劝学员需“按户劝学”,要随时登记适龄儿童的名单,劝勉学生入学堂学习,每年两学期劝勉学生入学堂的数量多寡甚至成为评定劝学员是否履行职责的重要标准。《劝学所章程》第十条“明功过”提出,倘若劝学员办理学务是合法且有成效的,会记作功绩;倘若劝学员有办理不善的情况,要裁撤身份。《劝学所章程》的相关规定说明,学堂招收学生数量愈多愈好,政府力求开新学之风,培养新式儿童。其二,是兴学之责。劝学员需努力兴学设校,要“计各村人家远近,学堂须立于适中之地”,以便县域内的儿童都能就近入学;要“定名某地学童须入某学堂”,采取严格措施督促儿童入新式学堂;要结合当地实际人性化地“设立半日学堂”③,以便于贫寒之家的学生半工半读。除此之外,劝学员还要鼓励和劝导地方人士出资建学堂,以推广新式教育。其三,是筹款之责。劝学员要负责筹款以维持学务工作的顺利进行,采取“绅富捐资,学生适度缴纳学费”的方式筹集款项以解决经费不足等问题。其四,是开风气之责。劝学员要发挥榜样作用,积极鼓励学生学习,开新学之良好风气。其五,是去阻力之责。由于私塾仍存,因此常有塾师阻碍学生入学馆的事件发生。劝学员须协调好私塾与新式学校之间的关系,并逐步引导塾师接受新式教育,促进私塾转变为学堂。可见,在中西文化博弈过程中,科举的废除导致了县教育行政机关学务工作重心的转移,劝学所主要负责改良私塾以及推广新学的工作。
三、教育局(科)重社会教育和义务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传统儒学与新式文化作斗争的重要时期,也是各路教育思潮的萌芽时期,新立的民国政府亟需在各路文化中寻求精神支柱,但在对待传统儒学时,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极端方式打乱了文化博弈的正常秩序,使得民国初年的文化选择既反复又混乱。起初,教育总长蔡元培欲进行教育改革,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口号,希望改变传统教育历来以儒学为主的局面。然而,袁世凯很快逆流推行“尊孔复古”教育,以外力强势干扰文化博弈的进程。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法孔孟、重自治”的教育宗旨,将中国的教育重新拉入以儒学为尊的历史起点,他在《特定教育纲要》中指责“近日学子厌弃旧学,丧失独立之精神”,并提出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尊孔复古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出现,近代中国的新旧文化博弈达到了顶峰。
受文化博弈的影响,县教育行政机关劝学所也历经了反复调整,并最终被教育局取代,工作重心也从开设新学转移到督促教育的进一步落实,即对县域内的群众进行社会教育以及对适龄读书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民国初年,县教育行政机构仍沿用“劝学所”制度,并于每县设县视学1~3人,以监督新学的推行工作。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下令裁撤各县劝学所,并令县公署设立第三科专管全县教育事宜。但制度上的一刀切并未给学务管理工作留下足够的交接时间,县域内部的学务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依旧需要推行新学、设立新式学堂并改良私塾,甚至还要推行义务教育,这些学务管理工作不可能随着劝学所名称的废止就立刻中断。因此,有的县就继续沿用劝学所制度。1913年7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又通令各省暂留劝学所,并于1915年12月15日公布了新的劝学所章程,以恢复各县的劝学所工作。1923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设局长一人,县督学、城乡学区教育委员及事务员若干人负责县内的教育管理事务,教育局不断完善其督学职责,逐渐发挥了普及教育的重要作用。
从机构名称变化来看,中国近代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确立和变革大致分为劝学所时期(1906-1923)、教育局时期(1923-1939)和教育科时期(1939-1949)[13]。教育局时期内民国政局相对稳定,自1923年《县教育局规程》颁布后,县教育局就负责起全县事务,并划定学区,设立教育委员和设董事会以协力推进地方教育的进步。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县教育局暂行施行细则》指出,“县教育局长需调查学龄儿童及义务教育进行事项、社会教育之进行事项、推广职业教育事项”。可见,县域内的主要教育工作向发展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倾斜,这与该时期教育救国思潮的高涨密切相关,因为教育救国思想是寄希望于民众智识提升的,所以政府也意识到了扩大教育、普及教育以及推动人民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在部分县域建立伪政权,企图实行奴化教育以钳制中国人的思想,从精神上进行“文化殖民”。此举遭到了国内爱国人士的强烈抵抗,抗日救国的呼声高涨,以爱国文化为核心的抗日教育和战时教育等在社会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县教育行政机构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陈友松指出,“战时县政之当前大任为民众组训与生产建设,是必以民众教育与生产教育为前提。因此教育行政之强化成为县政强化之一主要问题……须厉行普及教育,增加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14]。在教育为战争服务、县教育行政机构需扛教育大旗以及除弊兴教以救亡图存的呼吁下,全国各县纷纷调整县教育行政机构的学务、经费和权责等工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上来。山东地区还发展利用田间地头教育百姓的“庄户学”,切实提升了民众的抗战素养,是教育科(文教科)开展社会教育的一大成果。
庄户学是在各村中开办的教学组织形式,具有出“民办、互教、自学”的特点。办学主要依靠村中的文教委员会,他们负责教师的聘请、学生的动员与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经费的筹集等各项学务管理工作,县文教科也会派出一部分教员辅助庄户学进行群众管理和社会教育。“庄户学”的成功是一县之学或一村之学的缩影,是县教育行政机构、村庄文教委员会以及教师与人民相互配合的成果。虽然该时期教育局多改称教育科,甚至被置于其他科之下成为地方政府的辅助机构,但其在抗战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指导着县域教育及相关工作。
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于1947年下令各县恢复教育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下的新生活,县教育行政机关逐渐肩负起监督学校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管理工作。时至今日,社会教育与普及教育仍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中国要想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就必须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全民教育,尤其要重视基层教育的发展。
近代文化博弈是各路文化互相碰撞并争夺民众思想空间的过程,文化博弈的结果也辐射到整个社会。不论是洋务与守旧之争、维新与洋务之争,还是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新思想与传统儒学为代表的旧习俗之争、各种教育救国思潮之争、奴化教育与抗日教育之争,实际上都是借文化之力影响国家政体的选择、经费投放的侧重以及教育价值的取向等。故在各路文化博弈之下,传统的科考制度被废除,儒学署走向衰亡,劝学所成为专门的县教育行政机关,肩负改良私塾和推行新学之责,后又调整为教育局(科),为新时期的社会教育和义务教育服务。21世纪以来,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加剧,导致实力不同的国家间产生文化的竞争与合作,最终形成了相互同化或融合的国际文化博弈格局[15]。全球性的文化博弈愈演愈烈,文化安全成为一个重要论题。近代文化博弈史启示人们:不论是器物文化之争、制度文化之争还是思想文化之争,都应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只有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使其在文化博弈中不被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才能为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让管理者与教育者们在社会主义的文化信仰下开展各项教育工作。只有落实好县及乡村等地的基础教育,才能建立起上下一致和全国一心的文化信仰和教育价值取向,培育出万众一心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为诸城县教育志编纂办公室所编写的《诸城县教育志(1840-1985)》,1986年版。
② 学田制度自北宋即设,指用于兴办教育的田地。学田的来源丰富多样,或是皇帝赐予,或是官田拨给,或是私人捐赠。学田享有免除国家赋税的特权,不得出卖,大多以租佃的方式租给佃农,所收取的租金可以用来弥补地方办学资金的不足,尽可能为地方提供较好的教育质量。
③ 半日学堂是为贫寒子弟所设,因为家境贫寒,学生或难出学费,或因农活工作占据时间,故根据贫寒子弟所需开设半日学堂,可以视作工读学堂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