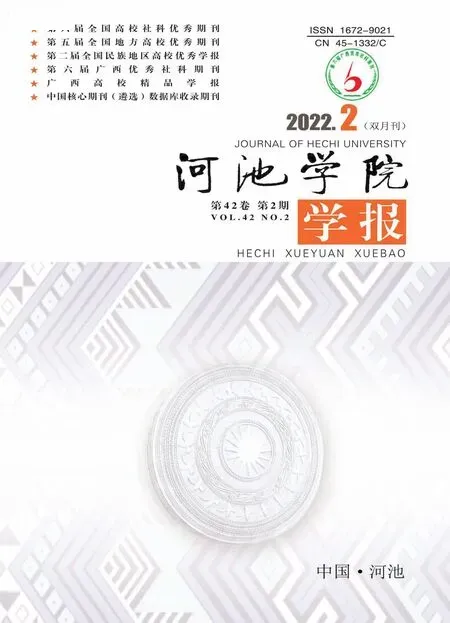论老舍长篇小说《牛天赐传》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之关联
邢 岳,李升锐,陈殊颖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杨浦 200082)
《牛天赐传》是老舍1934年于山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纵观老舍的长篇小说作品,连载于《小说月报》上的《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6年)、《二马》(1929年)三部是为老舍在国内文坛打响名气的作品,《小坡的生日》(1930年)、《猫城记》(1932年)各自因其题材内容特殊性受到瞩目,《离婚》是老舍“重返幽默”的成功尝试,《骆驼祥子》(1936年)、《四世同堂》(1941-1948年)更毋庸赘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相比之下,《牛天赐传》在老舍的一众长篇小说中显得平平无奇,连老舍自己也说《牛天赐传》——“匆匆赶出,无一是处!”“就是和我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可吹的地方。”[1]478然而,且不论老舍此言是否出于自谦,文学质量与作品的研究价值也并不必然相关,如果以古今文学演变的视角去考察《牛天赐传》,并将其与老舍的其他长篇进行比较,便会发现《牛天赐传》的独特之处——它是老舍长篇小说中受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部作品,熟悉、欣赏外国小说形式并因此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老舍在自身创作的中段时期却写出了这样一部传统色彩浓厚的小说,不得不引人深思。
纵观目前学界的研究,虽已经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了中国古代文学资源对老舍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但缺少聚焦单篇作品的细致分析;关于《牛天赐传》,已有的溯源研究也只关注到了卢梭、狄更斯等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而没有论者注意到《牛天赐传》深受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影响的特殊性。基于此,笔者将从语言形制、创作手法、文化精神三个层面去探究《牛天赐传》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关联,并尝试结合老舍同时期的文坛境况,从近现代小说形式演变的整体视野去分析《牛天赐传》受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影响显著的原因,以期更好地理解古代小说资源对于老舍乃至与老舍同代的现代小说作家的意义和影响。
一、语言形制——传统的承续
(一)小说形制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
《牛天赐传》受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影响,鲜明直观地体现在小说的外在形制上。
首先,从小说题目来看,《牛天赐传》以“传”为篇名的落点,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的影响。同样是集中叙写某一人物的人生际遇,老舍的下一部长篇《骆驼祥子》就仅以人物名称作为题目,被认为影响了《牛天赐传》的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亦是如此。如果再结合小说文本来看,《牛天赐传》第二节的小说叙述者就自称是“写传记的”[2]10;在全书的结尾,小说也写道——“天赐后来成了名,自会有人给他作传,——不必是一本——述说后来的事。这本传可是个基础的,这是要明白他的一个小钥匙……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2]229,作者在此特别强调了小说的“传记”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老舍是有意采用为虚构人物书写传记的形式来展开这部小说的,而这种形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追溯这一传统前,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小说”作一些阐释澄清:其一,现代所应用的“小说”这一文体观念是在西方的文学观、文体分类观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中国古代小说”对应到中国古代的文学语境中实际上囊括了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笔记、传奇、演义等多种传统文体形式。其二,中国古代小说整体上都与史学关系密切。由于中国古代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史学实录传统,导致小说一直被看作是史学的附属或补充,比如在如今看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一部小说,但在当时相当一部分批评家都将其视作正史《三国志》的通俗版本,或者是为补正史之缺而存在的野史。
正是在史学本位的思想背景下,“史传”传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这一传统以历史性(野史性)、传记性(杂传性)和传奇性(奇异性)为基本特征,发轫于先秦诸子史传,其后变异为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宋的传奇小说、明清演义的章回小说等多种文体形式[3]12。单从题目上来说,《牛天赐传》这种“某某传”的命名方式在唐传奇中便比比皆是,例如《柳氏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等,其中又尤其像《南柯太守传》《任氏传》《李娃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一类的作品,叙写虚构的人物故事却仍佯装史录以“某某传”来命名与写作,可以看作是《牛天赐传》写作模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的范本。
唐传奇之后,明清时期在“史传”传统影响下生成的古典英雄传奇小说,也大多延续了“某某传”的命名方式,这类小说通常采用章回体,描绘某一位英雄或一组英雄群像的传奇事迹,比如《说岳全传》《说呼全传》《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等。而《牛天赐传》形制上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整部小说24个章节中的每个章节都有整齐的四字词语作章节名概括本章内容,这在老舍所有长篇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小坡的生日》虽然也使用章节名简单标示每章内容,但章节名是三、四、五个字参差不齐的词或短语,其他篇(部)即使如《四世同堂》那样上百万字的长篇也只是用数字标题进行分章。虽然《牛天赐传》的章节名和传统章回小说回目名称那样的前后两回单句对偶或者一回自身双句对偶的形式存在很大差别,但相比于完全不设标题或者标题字数参差不齐来说,可以从中看出老舍是着意模仿了古代章回体形制的。另外,牛天赐在整部小说中总是被长辈管教,被同辈欺侮,他个人也是逃避,性格软弱,人生20年未曾见义勇为也未曾建功立业,但小说中叙述者却一直称呼他为“咱们的英雄”。这显然也是《牛天赐传》与古典英雄传奇小说存在“血缘关系”的有力证据。
至于《牛天赐传》模仿章回体制的原因,像老舍自己所说的,一定程度上是《论语》杂志特约而造成的。“我的困难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顾到故事的连续,又须处处轻松招笑。”“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书中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许信其自然的发展。设若一段之中我只详细的描写一个景或一个人,无疑的便会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处处有些玩艺。”[1]479所以,除了老舍自己有意如此安排设计外,应该也有一部分是出于小说连载发表的考量。
(二)浅俗语言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白话传统
虽然老舍最初是受外国小说的影响正式走上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道路,但他的小说语言却并没有出现当时文坛常见的欧化弊病,且由于老舍自己很注意白话的运用,到了《牛天赐传》时,他的小说语言已经基本不存在文白混杂的问题,而是俗白浅易,生动传神。例如,小说第二十四节对端阳节前后牛天赐与虎爷夫妇一同为水果摊生意奔忙的书写:
节下的前一天,街上异常的热闹。虎爷在太阳出来以前就由市上回来,挑着樱桃桑葚红杏,月牙太太包了半夜的粽子。天赐也早早起来,预备赶节。满街都是买卖的味儿,钱锈与肉味腻腻的塞住了空中。在这个空气里,天赐忘了一切,只顾得做买卖,大家怎么玩,他会跟着起哄的。他头上出了汗,小褂解开钮,手和腕上一市八街的全是黑桑葚的紫汁,鼻子上落着个苍蝇。他是有声有色的作着买卖,收进毛票掖在腰带上,铜子哗啦啦的往笸箩里扔,嘴里嚼着口香蕉。稍微有点空儿,便对着壶嘴灌一气水,手叉在腰间,扯着细嗓:“这边都贱哪,黑白桑葚来大樱桃!”他是和对过的摊子打对仗:“这边八分,别买那一毛的,嗨!”虎爷是越忙越话少,而且常算错了账:“又他妈的多找出二分!”天赐收过来:“那没关系,我的伙计,明儿个咱们吃炖肉!哎,老太太要樱桃?准斤十六两,没错!”[2]221
这一整段文字全是短句,没有繁复的语法结构,也没有冗长的修饰语,简明有力,节奏明快,对于虎爷、月牙太太、牛天赐三人各自如何行动,老舍三言两语就交代得清楚明白。描绘街市“色、香、味”俱全,叫卖的人声、苍蝇声与哗啦啦的钱声仿佛一首交响乐,热闹无比,尤其是那原汁原味的叫卖口语,只要有过逛街市经历的读者便不会感到陌生,虎爷的粗话老舍也没避讳,正符合虎爷爽快急躁的性格。老舍的叙述本身也是口语化的,比如“塞住了”“只顾得”“灌一气水”“对过的”。总体来看,这段文字呈现出的语言特色基本上也就是《牛天赐传》的语言特色——多短句,多口语化表达,也多人物口语再现,且人物口语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浅俗而生动。
《牛天赐传》的白话语言能够如此自然纯熟,当然离不开作者老舍自身的提炼加工,但这并不完全出于老舍个人的天才创造。中国古代小说中白话传统的积累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古代小说按语言分类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其中白话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的俗讲、变文等;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生活的丰富,“说话”艺术蓬勃发展,话本作为“说话”表演的底本逐渐案头化,成为一种新的小说形态;宋代之后,又有大批的文人参与到话本创作中,其成果即为鲁迅先生所称之“拟话本”,其中优秀代表作有明代的“三言”“二拍”等;到了明清时期,白话小说的体量篇幅大大扩展,长篇的历史演义、章回体小说诞生,代表作品为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及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由于上文提过的强大的史录传统,小说这一文类在中国古代地位一直不高,即便有大量优秀的作品涌现,白话小说还是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通俗性被士大夫所鄙夷和排斥。
到了近现代,先是19世纪末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提升了小说的整体地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又出于反封建的启蒙立场在文学领域反对文言文,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价值才逐渐被看到。像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提出应该改良的“八事”大多是针对旧体诗文,对于古典白话小说反而赞美有加,尤其是在第八点“不避俗字俗语”中更是“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4]198。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肯定主要也是就其活泼生动的语言而言,对小说中封建思想道德观念的批评还是非常尖锐的。
老舍自己对于古代白话小说在语言方面对现代小说的影响认知也很清晰。20世纪40年代老舍访美时曾发表过题为《现代中国小说》的演讲,演讲中老舍指出,现代中国小说继承了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所谓‘现代’中国小说,是指用白话(即普通人的语言)写成的小说。”“早在唐、宋之时,甚至可能更早,已经有白话小说出现。从这点看来,‘现代’中国小说也并不是那么新的。”[5]
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以及自身精心锤炼的双重作用下,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了起来,形成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的语言风格,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同时也为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6]216。
二、创作手法——技巧的借鉴
由于外国小说的创作手法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截然不同,其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也格外明显,比如俄国小说之于鲁迅,近代日本“私小说”之于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老舍谈起自己的创作经验时也自言“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7]629。另外,由于在中国古代,小说不被视作正统的文学,未被纳入教育体系中,这就导致现代小说作家们虽然不乏国学功底深厚者,并且多少会创作些旧体诗文,但有过旧体小说创作经历的却寥寥无几,像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念书时就一直在学习仿作陆游、吴伟业的诗歌和桐城派的散文。
因此,人们常常会误以为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手法完全是从西方舶来的。但事实上,正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所论:“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形式变革中,散文基本上是继承传统,话剧基本上是学习西方,那么小说则是另一套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不是同化,也不是背离,而是更为艰难而隐蔽的‘转化’。”[8]138在《牛天赐传》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对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甚至体现得格外明显。
(一)说书人的叙事口吻
虽然像本文第一部分第一节中提到的,在《牛天赐传》的开头与结尾,小说叙述者都自称是在写作传记,但这种跳出来直接与读者进行“对话”的方式,其口吻与其说是传记作者的,不如说更类似于一位说书先生的。这位说书先生般的叙述者拥有“上帝视角”,即现代小说所谓的“全知叙事视角”,《牛天赐传》第一节开篇第一句便是——“要不是卖落花生的老胡,我们的英雄也许早已没了命;即使天无绝人之路,而大德曰生,大概他也不会完全像这里所要述说的样子了。”[2]1在牛天赐还未正式登场前,叙述者便摆出了一幅对牛天赐的“英雄”命运与一生际遇的前因后果了然于胸的姿态。而且叙述者一边向读者讲述牛天赐的经历,一边还时不时地跳出来发表议论,比如在开头写牛天赐被老胡发现时,叙述者认为刚降生人世不久的牛天赐不会言语反而是件好事,便评论道:“这时候他要是会说话,而很客气的招呼人,并不见得准有他的好处,人是不可以努力太过火的。”[2]1比如第四节写到纪妈私下拿不会言语也没有反抗能力的牛天赐出气时,叙述者感慨——“自然,我们无须为这个而悲观;可是生命便是个磨炼,恐怕也无可否认。”[2]32
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故事,明显借鉴了从宋代“说话”艺术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讲史小说叙事手法;同时,《牛天赐传》所采用的全知叙事视角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最为常用的叙事视角。说书人的存在以及全知叙事会强化读者和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感,也有利于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自由地表达观点。老舍创作《牛天赐传》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展现牛天赐从出生到青壮年的成长历程,促使读者观察与反思家庭、学校、社会如何形塑一个人。而一个存在感极强的叙述者和全知叙事方式会迫使读者与牛天赐保持距离,营造出一种旁观的感觉,起到提醒读者去观察和反思的作用。而且,考虑到小说前六个章节也即整部小说四分之一的篇幅中牛天赐都处于无法言语、无法自我表达的幼年期,借助说书人的口吻去介绍牛天赐幼年的经历与成长环境也便利了老舍的创作,正因如此,说书人只是在小说开头几节比较活跃地出现,等牛天赐长大有了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后,说书人就隐身退去了,直到小说结尾才再次现身为整篇小说作总结。
再者,《牛天赐传》既是一部传记形式的小说,主体采用的便是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为常见的顺时叙事顺序,叙述者将牛天赐人生的前20年按时间顺序娓娓道来。与之相对应,小说采用了古代小说中常用的“串珠式结构”。相比于截取生活片段及人物关系来描写的“横式结构”(如鲁迅的《孔乙己》、曹禺的《日出》)、以纵横交错的笔法展现宏阔复杂画面与生活的“网状结构”(如《红楼梦》、茅盾的《子夜》),串珠式结构线索单纯集中,故事性强[9]49。《牛天赐传》对串珠式结构的运用是很出色的,就像日本学者藤井荣三郎总结的那样:“这个小说每段都有小主题。每个小主题又无不和总主题相呼应,有如一首乐章,一个主旋律反复出现。在这个结构里,安排着失望和幻灭的故事。微小的希望和较大的失望交替地光顾了主人公,直至以最大的幻灭,结束了这个故事。”[10]375
(二)“草蛇灰线”与“大团圆”的情节设计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是指长篇古典小说一种埋伏笔的技法,蛇穿过草丛、线掠过炉灰,虽然并不明显也还是会留下一些隐隐约约的痕迹,就像是小说作者有意留下一些后文情节发展的暗示,待到整条故事线索被展开时便给读者一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阅读感受,这一技法体现出作者对小说整体情节结构的控制力,否则就容易虎头蛇尾。
在《牛天赐传》中,最能体现“草蛇灰线”的,是小说结局的设计。本来在小说后半段里牛天赐的人生呈现出的是不断下落的趋向,因搅入新旧主任换届风波被学校开除、母亲被学校的事气病后撒手人寰、战火烧毁了父亲的铺子、随后不久父亲去世、家产被抢骗一空,到小说最后一节时牛天赐已落得家破人亡的境地,只能靠虎爷夫妇照顾着他。但就当读者以为牛天赐未来也就是和虎爷夫妇合作卖水果维生时,就像是最后一节篇名“狗长犄角”暗示的那样,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早在小说第十一节时就退场的王老师——牛天赐的第一位家庭教师王宝斋,奇迹般地路过了牛天赐的水果摊。从王老师刚出场,老舍就交代过他并非正经的教书先生,这位老山东儿只是想借这个工作机会获得牛天赐父亲牛老者的资助做点买卖,而十几年过去,王老师竟然真的凭着牛老者给的一千块做买卖发了家。作为一名老山东儿,王老师是典型的讲义气和知恩图报,在了解牛天赐的现状后,没过几天,他就帮牛天赐尽最大可能挽回了家产,还送牛天赐去北平上学,《牛天赐传》故事的末尾便是虎爷在车站送别牛天赐。王老师前后出场在小说中相隔了十几个章节,真可谓是“伏脉千里”。他的再度出现也使小说的情节走向一转颓势,甚至让人有猝不及防之感,但回过头去重读前文,老舍确实对王老师这一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描写充分,为结局做足了铺垫,因此这样设计也算是合情合理。
除了“草蛇灰线”的技法外,《牛天赐传》的结尾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大团圆”式结局。“大团圆”结局与传统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很是相符,会在结尾给读者以愉悦的阅读体验,因此常见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作品中。但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创作“大团圆”结局不免有偷懒、敷衍了事的嫌疑。《牛天赐传》的结尾虽然合理,但过于突兀和仓促,而且牛老者的善良兜兜转转最终为牛天赐留下了绝处逢生的人生转机,这种传统意味浓厚的、善有善报的情节逻辑,不免过于简单庸俗。起码在这部小说中,“大团圆”的结局方式是对小说艺术的一种损害,阻碍了作家和读者面对和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机会,限制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将《牛天赐传》与老舍随后的长篇《骆驼祥子》对照来看,不难发现牛天赐与祥子同样不断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祥子从一开始就比牛天赐健壮,对待生活也比牛天赐努力得多。但老舍并未因此就为祥子安排一个“救世主”。《骆驼祥子》最后一节,祥子打架、逛窑子、染病,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和小说开头年轻力壮、意气风发、步履坚定的形象完全判若两人,这样对比惨烈的悲伤结局反而更能激发读者对祥子的悲悯,促使人反思病态的社会对底层民众的戕害,也会使读者更加迫切地思索祥子这样一类人物实现自救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是老舍小说创作艺术上的进步。
除此之外,老舍小说创作手法中还有幽默的风格以及白描的技法与古代小说传统密切相关,前者受“婉而多讽”的《儒林外史》及晚清谴责小说影响,后者受到民间说唱以及古典白话小说常用的铺张描绘手法的影响[11],但这两点在老舍的其他小说中也多有体现,并不独属于《牛天赐传》,本文因此暂不对其展开详细论述。
三、文化精神——底色的晕染
在访英之前,老舍自幼接触和阅读的都是民间通俗文艺与中国古典小说,即便后来外国文学文化让他反思与重构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但传统文艺作品对他审美趣味乃至道德精神的形塑痕迹都是不可磨灭的,这也构成了老舍小说作品文化精神的一层底色。在《牛天赐传》中主要体现为下文的两点。
(一)侠义的思想观念
侠义精神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史传传统中自《史记》起便有专门的《游侠列传》,而中国古代小说中,《虬髯客传》《昆仑奴》《红线》等唐代传奇均以侠客为中心人物。到了宋代话本、明清小说中,以武侠为题材的更是不在少数,比如话本《杨温拦路虎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比如上文提到过的《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一类的明清英雄传奇。一些本与侠士主题无关的小说,如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施公案》中的小说人物的侠义性也非常鲜明[12]。侠士们大多出身不高,但往往诚信、勇敢、乐于助人、嫉恶如仇,救他人于水火之中,维护着世间的公道正义。
而中国古代的这种武侠文学,对老舍本人的道德观、审美趣味、创作趣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老舍回忆,在少年时期,他最先接触的就是《施公案》一类的小说,小学时,他总和同学罗常培一起在放学后到小茶馆里听评讲《小五义》和《施公案》,并且对武侠文学深深着迷,甚至“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7]501。成为作家后的老舍的小说中始终存在侠客式的人物或人物行为,比如《老张的哲学》里王德行刺老张、车夫赵四拳打蓝小山,比如《黑白李》中白李砸电车轨道、黑李替白李牺牲,比如《离婚》中丁二爷暗杀小赵、拯救张大哥全家,等等[13]31。甚至在1934年,老舍曾答应过上海大众出版社要创作一部《洋泾浜奇侠传》,可惜未能实现;而1935年老舍创作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本来是他构思的武侠长篇小说“二拳师”中的一小块[1]475。
创作于1934年夏天的《牛天赐传》虽然不是武侠题材,但其中受中国古代小说影响产生的武侠元素,可以说是除了《断魂枪》这部专门的武侠作品外,在老舍所有小说中最多的。尤其是《施公案》这部作品以及《施公案》中的主要人物黄天霸,在《牛天赐传》中被反反复复地提及。
首先,在小说里,主人公牛天赐被塑造成了一个热爱武侠小说、怀揣侠义理想的形象。牛天赐最初是听虎爷即四虎子讲了《施公案》——“其实四虎子并不会说笑话,不过是把一切瞎扯和他的那点施公案全放在笑话项下。他的英雄也成了天赐的英雄;黄天霸双手打镖,双手接镖,一口单刀,甩头一子,独探连环套!据天赐看,四虎子既有黄天霸这样的朋友,想必他也是条好汉,很有能力,很有主意。”[2]74自此开始,黄天霸变成了牛天赐的精神偶像,丰富着他的幻想,也指导着他的种种行为。在小说第十四节“桃园结义”里,进入高小的牛天赐就像是完全沉浸在传统小说塑造的武侠世界里面。刚开始时,牛天赐模仿着《三国演义》,和同学结拜、称兄道弟,但后来他自己有了能力,“开始自己读《施公案》,不专由四虎子那里听了。他学会了‘锄暴安良,行侠仗义’”[2]122,于是牛天赐觉出同学之间的合纵连横没有意思,愈发渴望能够习得一身武艺去行侠仗义。无奈牛天赐的身体和性格都是软弱的,所以他终究成不了侠客,但是《施公案》与黄天霸给予他精神的力量,牛天赐之前因为过于害怕教书先生而落泪,但想起黄天霸来,“心气壮起了点”[2]88;学校里面大家因为他是“私孩子”而孤立他,排挤他,他就沉溺在幻想出的武侠世界里自我安慰;跟随纪妈去了一趟乡下了解了底层民众生活的不易后,他就想象着自己能成为黄天霸,在夜里给纪老头送去几块钱。
比起一直耽于武侠幻想的牛天赐来,虎爷反而更像是传统侠义小说中的侠客。在《牛天赐传》中,虎爷作为牛家的佣人比牛天赐大了不少,但他对牛天赐——这个小少爷,始终以兄弟朋友相称,在牛老太太的丧事上,牛家的各路亲戚吵嚷着要将牛天赐赶出家门,虎爷挺身而出,护着牛天赐躲开人群避风头;牛家最后家破人亡之时,虎爷夫妇也没有抛弃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牛天赐,反而如往常一样照顾他,尊敬他。虎爷就类似于唐传奇中的红线、昆仑奴等形象,虽身份低微,但是对主人忠心耿耿、不离不弃。
总之,在《牛天赐传》中,侠义的道德观渗透在人物塑造、情节内容等各个方面。
(二)通俗的书写立场
老舍自小在民间通俗文艺的包围中成长起来,这点与同时代的现代文学作家很是不同,像鲁迅、郭沫若等人是在童年时由于较偶然的机缘才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而刘大白、刘半农等人是在成年后为了新诗发展的需要才回过头去寻找民间文艺的形式[14]8,因此,对于老舍来说,通俗性是他自然而然形成的近乎本能的追求。通俗性本身可以有众多的体现方式,事实上,像上文提到的白话语言、说书口吻、“大团圆”结局、因果报应的情节逻辑以及侠义的思想观念,都是老舍通俗书写立场的不同体现。此处笔者想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老舍采用通俗的书写立场,他在向中国古代小说取法时,更多地也是向其中通俗性较强的作品学习,而像古代小说传统中非常重要的文言笔记类,对老舍的小说影响就不大。
在现代小说界,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小说生成发展的早期,老舍的这种通俗写作立场是难能可贵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叙述常常会给我们一种错觉,即自“五四”时期起,现代小说便统治了中国文坛。但事实上,至少在二三十年代,旧派小说仍有相当的势力,当年最畅销的小说也是旧派小说。因为自“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现代小说基本上都属于精英文学的范畴,虽然使用白话语言创作,但受外国小说影响的翻译腔明显,且因为以启蒙主义文学观为出发点,许多现代小说作家的写作立场往往离民众有明显距离。请试以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驱鲁迅和老舍作对比。鲁迅虽然开创了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题材的新文学传统,但他的农民题材小说中往往会有一位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作为叙述者自上而下地审视一切,从而批判底层民众的麻木和愚昧;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同样入木三分,在他笔下,我们也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保守、自私、敷衍等等,但他的书写视角始终是平视的,与其说读者在观看底层人物的命运,不如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直接成为底层人物本身,这从而能够让读者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悲悯。
在《牛天赐传》中,虽然主人公牛天赐是一名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但当小说写到牛天赐随纪妈前往农村以及最后牛天赐与底层的做小买卖、拉车的民众住在一起时,老舍借牛天赐之眼书写的内容都饱含“同情之理解”。小说原文叙写如下:
他们的买卖方法不尽诚实,他们得意自己的狡猾,可是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像朋友。为一个小钱的事可以打起来;及至到了真有困难,大家不肯袖手旁观,他们有义气。他们很脏,不安静,常打孩子。天赐看出来,这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并不是天生来的脏乱。他们都有力量,有心路,有责任心,他们那么多小孩都是宝贝,虽然常打。他不如他们,没力量,没主意,会乱想。他们懂得的事都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远一点的事一概不懂。他们是被一种什么势力给捆绑着,没工夫管闲事[2]220。
正因如此,老舍的作品能够收获许多知识分子以外的读者,老舍也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当然,通俗的书写立场肯定与老舍本人出身底层的人生经历有关,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通俗传统对老舍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就像上文分析中提到的,这些影响对老舍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有时也会使他的作品显出平庸、幼稚和肤浅的倾向[15]30。
四、结语
总的看来,《牛天赐传》的形制承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史传”传统、语言承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话传统,创作手法上说书人的叙事口吻、“草蛇灰线”和“大团圆”的情节设计方式都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常用技法,整部小说的文化精神又以中国古代小说的侠义道德观与通俗文艺的民间立场为底色,这些因素既促使《牛天赐传》呈现出通俗生动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小说的思想艺术深度。
而《牛天赐传》受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影响显著的原因,上文在分析其与古代小说的关联时已经涉及了一些,比如类似章回体的形制与连载发表的形式有关,说书人的叙事口吻是基于牛天赐幼年时无法自我表达的考量,这里笔者再做一些补充和总结。
从外部因素上来说,《牛天赐传》创作于老舍在山东济南任国学研究所主任期间。济南是老舍成年以后除北京之外,真正静下心来对其加以体会的第一座国内城市。在海外漂泊五六年之久,定居在诞生了儒家文化的孔孟故里、蕴藏着丰厚中华文化传统的齐鲁大地,对于老舍来说,无疑更加有利于观察和思考古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状态[16]146。国学研究所主任的教职想必也会推动作为现代小说作家的老舍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
而从内部因素上来说,一方面,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老舍个人自幼便对中国古代小说以及民间通俗文艺感到熟悉和喜爱,中国古代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的审美趣味甚至是道德精神,其影响自然会体现在他的创作当中;另一方面,结合整个现代文坛的背景来看,便会发现从近代的市民通俗小说到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通俗文艺再到建国后的“革命通俗小说”“革命英雄传奇”这样一条脉络下来,中国古代小说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一直在不断显化,《牛天赐传》即可视作是老舍基于这样一条脉络所作的一次有意尝试,是他有意承续古代小说形制传统、借鉴古代小说创作手法并将其运用到现代小说写作中的创作试验。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就不难理解老舍为何会在创作中期呈现出这样一部与他的其他长篇小说风貌迥异、传统色彩浓厚的作品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资源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重视与思考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资源对于现代小说生成发展乃至成熟产生的意义与影响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