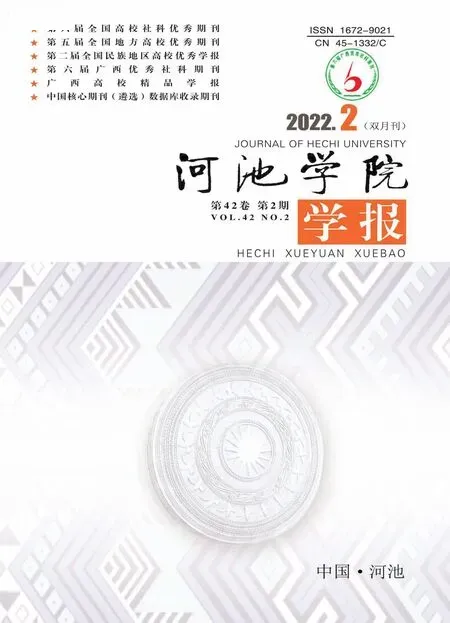基于传奇视角的老舍作品叙事艺术及其意蕴探析
王 兴
(河南财经大学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传奇传统与现代文学形成之间有很强很密的文本上的“互文性”。现代文学经典作家老舍深受“传奇”等文化传统的熏陶与影响,其作品带有鲜明的“传奇气味”。而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传奇传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性的当代,文化与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到理论前沿,以传奇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重现和表征着“我(们)”的形象,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中对传奇等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探源与现代承传探讨,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当下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知人论世:老舍与作为文化传统的传奇
作为中国传统文学重要的文体类型与叙事模式,“传奇”内涵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传奇”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小说体裁(一般指唐宋文言短篇小说如《李娃传》)、传奇小说集、戏曲形式、中世纪欧洲长篇叙事诗等几种典型。”[1]1619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传奇”是一个多元概念,其与时代发展亦步亦趋:“传奇之名,实始于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为传奇之第一义也。至宋则以诸宫调为传奇……则宋之传奇,即诸宫调……元人则以元杂剧为传奇,《录鬼簿》所著录者……至明则以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乾隆间……遂分戏曲为杂剧传奇二种,余曩作《曲录》从之。盖传奇之名,至明凡四变矣。”[2]64起源于神话、志怪的“传奇”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核心元素,在文学发展历程中被不同的时代注入新的不同的元素,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基本叙事模式与传统。“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变异之谈,盛于六朝……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70“传奇”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唯奇能传、无奇不传的审美旨趣追求贯穿古代文学多种体类、多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话语与叙事模式,内涵丰富且有“中国经验”意味的“传奇”并不仅限于古代文学,它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对历代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虽以反叛传统为旗帜,但对传统而言并非断裂性存在。因此,现代文学转型与中国文化传统承袭常常成为热点话题。老舍作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其小说及其文学风格因带有传奇色彩而广受现代读者喜爱。“郑西谛说我的短篇小说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无论他是警告我,还是夸奖我——我以为是正确的。”[4]312老舍小说中的传奇色彩除了其取材具有传奇性外,还在于老舍自幼受到的传奇等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三侠五义》是老舍童年时期最喜欢的启蒙读物,他少年读书期间“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施公案》一类的小说”[5]。他的课余娱乐生活则是最爱去小茶馆听评书。“我十二三岁时读《三侠剑》与《绿牡丹》也是那样的起劲入神。”[6]29民间传奇故事蕴含的侠义内容与理想精神等都深深地吸引着成长中的老舍,他甚至达到痴迷的境地——“有一阵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7]246以传奇传统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为老舍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老舍不仅从小热爱评书、相声等民间通俗文艺,还乐于结交社会上的各色江湖朋友,热衷于极富侠义精神的传统武术。他在济南生活时期还曾专门走访号称“山东第一杆枪”的拳师马永奎,与之相谈甚欢并拜师学艺,从他那里获得不少武林界的传奇素材。1931年,老舍受邀在美国加州学院为广大师生作《唐代的爱情小说》的专题讲座。1934年,他还专门写了《洋泾浜奇侠传》(《小说半月刊》约稿)。由此可见老舍对传奇传统的深厚造诣与古典文学素养。因此,老舍作品中的传奇叙事特征与现实主义风格中的浪漫主义色彩便也是自在情理之中。
《老舍选集》自序中有其夫子自道——选集内作品皆“讲到所谓江湖之事的:《骆驼祥子》是讲洋车夫的,《月牙儿》是讲暗娼的,《上任》是讲强盗的,《断魂枪》是讲拳师的”[8]194。其中,《黑白李》是“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8]194,而极富江湖传奇色彩的《断魂枪》则是老舍先生谋划许久的武侠传奇长篇《二拳师》篇幅中的“一小块”[8]194。在其文学世界所展示的现实人生中,他为读者讲述着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评书式的传奇讲述方式、坎坷离奇的人物命运,都是作家对当时现实人生的思考与文化反思,与传奇传统中“游戏成文聊寓言”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极富“中国经验”意味的传奇传统深刻地影响着老舍的个人成长、文学创作与审美追求,其对传奇传统的承袭、转换与创新造就了老舍小说的传奇色彩与独特艺术魅力。
二、人文关怀价值旨归:主题内容的传奇特质
老舍作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因其对包括传奇等民族文学传统的承袭创新,造就了其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接受度,比如老舍先生于20世纪风云变幻的30年代所创作的《赶集》《蛤藻集》《集外集》等即如此。“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一直处于推崇现代、反叛传统的思路中,包括老舍也时刻警醒自己是现代作家,要创作现代小说。然而‘中国小说的形式’作为一种强大的民族无意识力量,老‘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9]226以启蒙救亡为使命的现代作家虽时刻不忘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但其创作总是有意无意地承传着由来已久的民族文学传统。郑振铎认为老舍小说的传奇性在于其强烈的故事性特点,其实,同为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如果说鲁迅习惯在平实故事讲述中深挖思想寓意,那么老舍则侧重于用曲折离奇的故事来引导现代读者自己探寻小说文字后面的寓意。因此,文学叙事的传奇性特征并不是老舍的最终目标。老舍的传奇文学世界中,“从内容上说,传奇不只是谈神论鬼与英雄侠客的专利,更是对历史沧桑与世态人情的真实演绎”[10]。老舍作品将现实融入传奇故事,其文学讲述兼顾故事吸引力与深刻寓意,所展示的现实悲欢离合与世态炎凉,正是旧中国时代语境下社会各阶层群体真实生活状态与各样精神风貌的深刻呈现。这不仅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时代容量与社会内涵,也自然契合传奇以小见大的文学传统。
在小说主题内容上,老舍总是把文学视点聚焦于俗世底层中小人物不平凡的经历和遭遇,通过为现代读者讲述曲折离奇的市井江湖故事,揭露启蒙救亡时代语境下旧中国的社会现实,深情关注底层民众命运,兼顾小说的哲理性与通俗性。比如,在大家熟知的《柳家大院》《我这一辈子》《抱孙》《邻居们》《不成问题的问题》等小说文本中,老舍总是能够从小人物的现实生活着眼,让事件发展常悖于正常境遇,故事情节多有巧合且结局又极其荒诞。作品读来给人以现实中极富传奇荒诞色彩之感,作家在文学实践上真正做到了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显然,这极容易让人想到以唐传奇、宋元话本为典型的市井传奇小说,老舍也像其作者一样为吸引读者而突出强烈的故事性,他常在文本开始或情节推进中间多次精心设置各类悬念、制造意想不到的包袱,用说书式话语讲述引导现代读者展开丰富想象,而最终故事结局与人物命运常超乎想象。显然,老舍在文学实践中继承了传奇等传统小说侧重情节转折、强调故事性与传奇性的常用模式。
以《我这一辈子》为例,小说以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讲述“我”作为一名社会最底层巡警的并不轰轰烈烈的一生。这里有读者所熟知与习惯的文学叙事审美接受经验:故事讲述有头有尾、侧重完整,情节发展多变不一,命运结局出人意料,底层市井小巡警奋力挣扎生存的曲折人生悲剧讲述中,依然充满了传奇色彩与荒诞意味。本来做着体面裱糊匠职业的“我”与俊俏的妻子育有一儿一女,生活简单平凡,然而不知怎么的,妻子就和傻大黑粗的师哥私奔了。这也成为“我”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结与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直到如今,我还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当时教我差点儿疯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11]62出人意料的生活变故与事业打击突然改变了“我”看似一帆风顺的一生,也成为“我”无可把控的命运的转折点。意外与打击一次次不期而遇,贫苦的巡警生活还因上司局长毫无征兆的一句“有胡子的全脱了制服,马上走!”这一极其荒唐的缘由而被终止,使“我”丢了唯一可以果腹的饭碗。小说中荒诞不经的情节与人物戏剧性突转的命运,也似乎让“我”与读者们认识到,无论你多么坚强,再怎么努力挣扎,都宿命般地无法改变这多灾多难的生活与不可捉摸的荒诞人生。小说借市井小民现实生活的传奇生命,也表达着作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无常与荒谬的揭露。
老舍有着将市井小民世俗生活荒诞化、戏剧化展现的超凡能力。《抱孙》中的王老太太为了能够实现抱孙子的愿望而经历了数次大起大落的人生,其心理从期盼、兴奋、担忧、痛苦再到希望、暗喜与心死。小说情节也从王少奶奶怀孕、难产、生子再到人财两空,小说最终揭示——老太太因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而害了儿媳与孙子。一个底层市井家庭生孩子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与离奇不定的人物命运走向所加持,大起大落的故事推进总是能够让读者为王少奶奶与孩子捏一把汗。而《柳家大院》为读者讲述了小王媳妇被虐惨死的故事,讲述方式也是借不寻常的笔法展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出人意料的故事。尤其是小说中的小姑子也是迫害其嫂子的帮凶,最后意外地被其父亲戏剧性地卖掉,这深刻展示了近现代中国男尊女卑观念对女性的戕害。《听来的故事》则用荒诞幽默的笔触,借助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为读者讲述孟智辰不可思议的步步升官史,其能步步升官竟是因为他出人意料的“默默中抓住种种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深谙熟悉了这“没办法就是办法的时代”的处世精髓。《邻居们》中毗邻而居的明家与杨家因鸡毛蒜皮的“葡萄事件”“寄错信事件”等生活误会与各种不凑巧,闹出了一系列明争暗斗、啼笑皆非的故事,而多次的误会与争斗事件后面则是作家对人性暗河的揭示。《邻居们》小说文本中所产生的戏剧性都是由作者精心安排的一次次误会与不凑巧所带来的。小说的故事叙述虽娓娓道来,情节发展也层层递进,但故事却是按照非常规逻辑结束而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作者似乎也在告诉读者无常的人生才是常态。
老舍也擅长通过故事结局突变给读者制造“惊喜”,从而赋予故事传奇特征。比如《黑白李》中,人们都会按照故事既定的讲述推理出一定是白李在暴动中牺牲了,而实际上,牺牲的却是黑李。情节戏剧性的突转与突兀的结局安排,使读者诧异后又瞬间能够恍然大悟。《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最后也是农场人事管理上“劣币驱逐良币”,实干勤勉的尤大兴终被只会带来亏损的丁务源替代,故事发展荒诞可笑却又契合人情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逻辑。而在老舍的《一筒炮台烟》《恋》《爱的小鬼》等作品中,同样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突变,结局出人意料而蕴含引人深思的主旨。如果说传奇传统叙事注重情节的出乎意料是为了引起读者关注,那么老舍将传奇因素加入市井生活而使情节出人意料则能够为其小说文本带来荒诞与戏剧性,进而旨在展示生命无常与人性的不可捉摸,其文字背后是肩负启蒙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对时代语境下旧中国社会的理性思考与人性探索。
老舍作品中也有对旧中国社会中另类特殊职业,诸如镖师、拳师、暗娼、劫匪、骗子等江湖传奇的讲述。比如《小铃儿》借鉴唐传奇《谢小娥传》替父复仇的传奇程式,为读者展示了小铃儿充满武侠情怀的复仇故事。《杀狗》则为现代读者讲述了一位不畏强暴、铁骨铮铮的老拳师奋勇抗争、抗日爱国的传奇故事,语言风格极富传统民间武侠传奇风味,如“一道白闪猛孤仃的把黑暗切成两块……白光不动,黑影在白光边上颤动……白光昂起,黑影低落”[12]38。小说借助武侠传奇的讲述方式为现代读者展示着民族个体抗日爱国的故事。《浴奴》是烈妇复仇传奇,《月牙儿》是神秘奇异的暗娼传奇,《兔》则是一个刺激而复杂的江湖社会生存传奇故事。《上任》为现代读者讲述由匪而官的尤老二企图“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未果的官匪传奇故事,《断魂枪》中则始终笼罩着隐秘的江湖传奇氛围。老舍于此借江湖传奇故事反映社会现实——“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13]270在老舍的现代小说文本实践中,“这些非常态生活本身就具有了传奇文学所需要的‘奇’的美学属性。……选择生僻怪异的题材以增叙事的传奇或神秘的审美趣味,就成为了从魏晋志怪及唐宋传奇延续下来的‘传奇系’文学的一个创作传统”[14]。
三、现代文学实践策略:文本修辞形态的传奇特征
老舍在其传奇文学世界建构中,除了小说主题内容方面的传奇旨趣追求外,常侧重通过文学的修辞形态来增加文本的传奇性特征。“‘修辞’,广义地说,指的是作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与小说内容之间的三角关系。狭义地说,则是特指艺术语言的节制性的运用。”[15]124概言之,广义的“修辞”就是小说家用什么样的讲述语言将故事叙述出来,而我们熟知的中国古典小说典型话语修辞形态就是所谓的“虚拟的说书情境”。在老舍的文学世界建构中,他则通过设定说书情境、语言的民间化、反讽等讲述现代市井传奇故事,赋予作品内在传奇气蕴。
老舍的小说创作深受传奇等中国文学传统讲述方式的深刻影响。正如其自述:“郑西谛说我的短篇小说每每有传奇的气味!无论题材如何,总设法把它写成个故事。”[4]312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一般是一种为现代读者所熟知的典型说书情境,如所谓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话分两头,事归一面”等。这也正是唐传奇所确立的“叙述婉转”“作意好奇”开创性地赋予中国古代小说的典型修辞话语形态。可以说,以传奇为代表的古典小说之所以能让读者欲罢不能,正是在于其讲故事的方式。而由唐宋时期便兴起流行的说书艺术,常常是说书人以全知视角为听众“讲”一个故事。“小说之所以是小说不仅在于它是故事,关键在于它是讲故事。当人们把听故事与讲故事分开,并关注于讲故事这件事的时候,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就诞生了。”[16]从叙事艺术看,传奇的本质其实正在于其是“讲故事”的艺术。老舍曾自述自己十分善于说故事,认为“是小说就得有个故事,但故事本身并不就是小说”[9]234。现代作家虽以启蒙救亡为使命,但老舍深受传统说书艺术熏陶与古典小说影响,其文学世界的展示总是通过类似说书人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也总能在小说家提供的故事情节中感知到一个旁观者的叙事视角存在。
老舍自然深知“说书”讲故事这种传统叙事的魅力,因此常以第一人称视角方式融入创作,使其小说自带说书人风格,始终能够紧紧抓住读者。小说中的说书氛围与传奇故事意蕴,使得老舍的文学世界呈现更显成熟流畅。《我这一辈子》中所展示的生命打击与命途多舛让读者感同身受,《黑白李》中死掉的到底是黑李还是白李始终让读者放心不下,《柳家大院》中来自大杂院的老王在一次次残忍虐待儿媳导致其最终死去后,竟想起来要变卖始终与自己一条战线的女儿,小说的故事走向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内。这些小说所描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勾人心弦正是在于老舍讲故事的方式。限制视角实现了“作者的隐退”,从而赋予中国小说现代品格,如果说五四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是为了抒情,那么老舍作品中采用限制视角多数则是为了讲好故事。老舍小说中的说书情境常在文本开头便开门见山,突显主人公鲜明性格,比如《铁牛与病鸭》中“王明远的乳名叫‘铁柱子’。在学校里他是‘铁牛’。好像他总离不开铁”[17]104;《毛毛虫》的开头:“我们这条街上都管他叫毛毛虫。他穿的也怪漂亮,洋服,大氅,皮鞋,啷当儿的。可是他不顺眼,圆葫芦头上一对大羊眼,老用白眼珠瞧人。”[18]196这些开场极容易让读者想到传统文学唐传奇中诸如《南柯太守传》的开头:“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19]107抑或是《东城老父传》开头的“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19]168等,开篇便把人物形象与性格凸显。交代故事背景、既定主题呈现等也是老舍小说中用来吸引读者的说书情景常用方式,比如《柳家大院》中“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20]68。《断魂枪》中“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13]270类似说书场景的呈现。又如《上任》中“尤老二去上任。看见办公的地方,他放慢了脚步”[21]127,《抱孙》中“难怪老太太盼孙子呀;不为抱孙子,娶儿媳妇干吗?”[22]77老舍作品中鲜明的说书情景,显然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故事性。我们也能够发现,老舍小说中设置的说书情景里,常会有一个自问自答的画外音来推动情节发展,如小说《大悲寺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他为什么作学监呢……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23]27老舍小说中类似说书讲故事的方式与情境,总能给现代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感情触动,进而增强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
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自幼深受《施公案》等古典文学与中国民间通俗艺术熏陶与影响,十分熟悉民间语言传统与习惯。其小说语言俗白质朴、简明通俗、幽默风趣,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又贴近市井生活,因此深受现代读者大众喜爱,其小说文本的传奇特质也藏于通俗化的民间语言形式中。正如老舍自述“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象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24]430。因此,老舍在文学创作中十分擅长借鉴使用民间语言形式,比如《柳家大院》中“她和她爸爸一样讨人嫌,能钻天觅缝地给她嫂子小鞋穿。真要来个吊死鬼,可得更吃不了兜着走。别装孙子啦”[20]72。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民间口头语与表达方式,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传统市井生活的典型场景。老舍也会通过方言使用来增强其小说讲故事的表现力,比如在《柳家大院》小说文本中出现的“死巴”“高招儿”“节骨眼”“狗着”等都是典型的北京民间方言土语,能够让北京普通读者对小说与所讲述的故事感到熟悉而亲切。老舍从小就熟知以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通俗文艺,其鲜明特质就是语言形式的口传、鲜活与质朴、白俗。而老舍的小说语言也常用民间方言、俗语与白话,来实现传奇文本的叙事功能与营造强烈的故事情境,进而形成雅俗共赏的文学风格与传奇性特征。
另外,老舍也常通过反讽增强其文本的故事可读性,引导读者挖掘小说深层意义。“什么才是‘反讽’性的修辞?孙述宇把它译成‘表里不一’,正确地表述了这一转义外来语的实质意义……反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前后印象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这类差异,大做文章。”[15]146我们在以传奇为代表的传统古典文学中经常看到反讽作为一种语言修辞艺术的使用,比如《西游记》中其对各类妖魔鬼怪的寓意影射,《红楼梦》中其对各色人物口是心非的明褒实贬意指,《金瓶梅》中其对市井生活中俗人俗事的挖苦讽刺,《水浒传》中其在对历史英雄人物的肯定中又质疑人性之黑暗等等。老舍熟知中国传统传奇小说中借反讽表达真实主旨与言外之意的套路并将其运用于创作的作品中,比如他的《不说谎的人》《牺牲》《开市大吉》《善人》等,都自带反讽特质。《牺牲》中言必称“美国家家有澡盆”的毛博士,处处看不上脏乱差的中国却还必须生活在这里,他的十二次“牺牲”中的每一次都是作家的调侃与讽刺。标榜高级知识分子与接受过当时西方先进文化的人,实则是彻头彻尾的极具封建顽固思想的利己主义者。而《善人》中叙写的“穆女士一天到晚不用提多么忙了,又搭着长得富泰,简直忙得喘不过气来……她永远心疼着自己,可是更爱别人,她是为救世而来的”[25]200。小说用极致的反讽展示着穆女士言不符实的伪善言行与嘴脸。《不说谎的人》中,作家则借“不说谎”来讽刺周文祥的自我妄信与唯我独尊。反讽能够让小说故事性更强,使得文学空间停留在现实与荒诞之间,赋予文本传奇性特质。“奇书文体的首要修辞原则,在于从反讽的写法中衬托出书中本意和言外的宏旨。”[15]156老舍小说中的反讽并不止于故事本身,而在于通过表里虚实实现小说主旨的特别寄寓。老舍小说语言中说书情境的设置、民间化语言的借鉴与反讽修辞形态等共同建构了其文学世界的传奇品质。
四、结语
富有“中国经验”意味的“传奇”作为古典文学的一种固有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深受传奇等文学传统的熏陶与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老舍,用承袭创新的态度来描摹自己笔下的市井江湖的传奇世界。他的小说实践不仅继承了传奇传统,实现了文学传统在同源关系上的文学历时性接受,而且在借鉴与个人化创新后形成一种独特的传奇风貌。经济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浪潮正深刻改变着中国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文化多元性与混杂性越来越显著。以“传奇”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传统因其重现和表征着“我(们)”的形象,因而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和场域。“传奇”传统所表征的丰富内涵在当代恰恰可以担当起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责任,而这也正是重新探讨现代经典作家老舍与传奇传统关系的当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