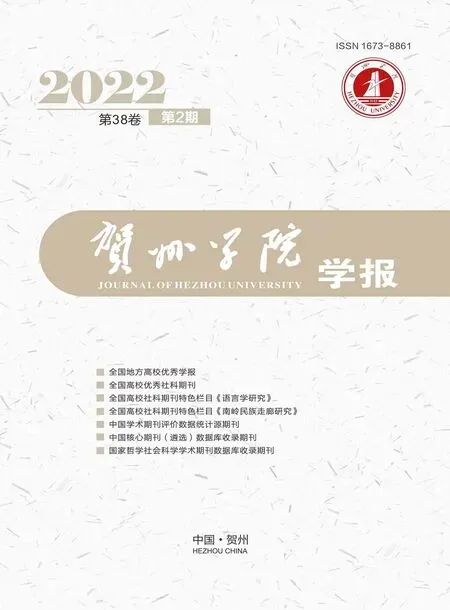聊斋宣讲小说改编特征研究
侯雨含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清初,实行半个月一次的圣谕宣讲制度,随着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的颁布,宣讲制度成为乡村教化的核心。为了吸引民众,避免照本宣科宣讲的枯燥乏味,宣讲活动采用说唱结合的表演形式,并广泛吸纳民间流行故事进行二次改编创作,将其作为宣讲的“案证”来辅助宣讲[1]22,这种具有说唱艺术特色的、用以辅助宣讲活动的道德教化文本就是宣讲小说。聊斋宣讲小说即改编自《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存在着“一再被改编、被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现象”[2]6,其在下层民众间广泛地流传主要依靠改编自聊斋故事的说唱志目。学界对于聊斋说唱志目的研究主要围绕由蒲松龄自己改编创作的《聊斋俚曲集》和关德栋、李万鹏编写的《聊斋志异说唱集》展开,内容涉及聊斋俚曲、子弟书、评书、鼓词、单弦曲子词。目前发现取材自《聊斋志异》的宣讲小说有116 篇,但因宣讲小说的稀见性,聊斋宣讲小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见专文对聊斋宣讲小说文本进行深入研究。《聊斋志异》在被改编为宣讲小说的过程中有何种特征,是聊斋宣讲小说改编创作中必须厘清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宣讲小说的重要切入点。
一、强调人伦关系的题材选择
康熙九年(1670 年)十一月,为表“尚德缓刑、化成民俗”之意,康熙帝正式颁行了《圣谕十六条》,宣讲圣谕开始在各省府州县乡村展开。雍正二年(1724 年)二月,颁行了康熙《圣谕十六条》的衍义《圣谕广训》,此后依托乡约保甲制的宣讲制度正式成为乡村教化的核心。
圣谕之言对于广大的底层民众来说是抽象的理念,“然所宣讲者,圣经贤传,词尚文雅。非愚夫愚妇所能知,且设宣讲者,家塾党庠,地关礼法,非愚夫愚妇所得近,曷若兹之”[3]。为了使圣上之言更好地传达至乡里,需要利用宣讲小说将抽象的理念放置在日常生活语境之中。梁漱溟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并扩散到社会生活,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紧紧围绕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展开。“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4]73,伦理关系的交错构成复杂而又稳定的组织模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聊斋故事的题材选择上呈现出强调人伦关系的面向,特别注重围绕着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展开。
“夫妇人伦之始也”,婚姻关系作为家庭伦理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成为聊斋宣讲小说最主要的表现对象。已知的116 篇聊斋宣讲小说中有40 篇以婚姻关系中的矛盾、冲突作为故事的核心,占已经收集到篇目的35%。这些篇目大多以对女性进行规训为目的,树立理想婚姻生活的模范。如改编自《姐妹易嫁》的《无福受》意在教导在择婿时不嫌贫爱富;改编自《段氏》的《妒妇回心》《义嫂感娣》强调丈夫纳妾时不妒,要以传宗接代为重;改编自《金生色》的《阴魂捉奸》意在宣扬严守贞洁。涉及由婚姻关系延伸出的婆媳、妯娌关系的《珊瑚》被改编为6 篇宣讲小说,改编后的聊斋宣讲小说被十部宣讲小说集收录①。兄弟关系的题材也是改编的重点,聊斋宣讲小说有17%的篇目聚焦在兄弟间利益冲突之上,其目的在于通过故事人物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来传达兄弟间应互帮互助、和睦友善、共兴家业的核心思想。如《二商》被改编为《听信妻言》《重伦获金》《遵兄抚侄》《听妻显报》《莺疏雁影》《悌弟美报》多篇宣讲小说,成为被改编篇目最多的聊斋故事之一。聊斋宣讲小说特别重亲子关系的道德阐释,《细柳》因母亲对两个儿子的教化为训子成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而被改编为《贤母训子》《富贵双全》《双枕帕》。而孝亲之举在聊斋宣讲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孝亲行为往往成为主人公获得福报的根本原因,如改编自《钟生》的《佛禳灾》即因钟生纯孝而获得了官职和美妻;《陈锡九》也因寻父受难而获得了财富。家庭伦理关系是聊斋宣讲小说题材的核心,聊斋宣讲小说通过围绕百姓的家庭关系而展开故事以达到“讲之而如道家常”的效果。
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时也涉及了丰富的社会伦理。《王六郎》以水鬼救人性命而放弃转生机会却最终成神的事迹有力地宣扬广行救济,而被改编为《冤鬼获福》《水鬼为神》《渔仙隐迹》;《董公子》突出刻画了克己复礼的“董公子”,故其作为推广儒家伦理道德的典型被改编为《关帝接头》,意在明礼仪而厚风俗。聊斋宣讲小说的人伦关系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常常交织在一起,改编自《胭脂》的《冤中冤》和改编自《折狱》的《施公奇案》就是因家庭关系的不睦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多重人伦关系交错的情况一方面使情节有波澜,另一方面也把家庭关系放置在更广大的社会关系中,强化乡民的集体责任感,同时这种复杂的伦理情况也符合现实生活,具有真实性。
与其他改编自《聊斋志异》的说唱志目的题材选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聊斋宣讲中的题材选择更具伦理教化性的倾向。根据《聊斋志异说唱集》中收录的说唱志目来看,14 部子弟书选择的题材有12部着眼于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并且在改编过程中重花妖狐鬼与凡间男子的绮丽旖旎的爱情情节,继承了《聊斋志异》书写男女情事缠绵浪漫的风格。聊斋单弦牌子曲同样对男女情爱题材保持着极大关注的同时,还强化了讽刺效果,“发挥了单弦艺术本身的喜剧风格,写起来更加泼辣尖刻”[5]16。而聊斋宣讲小说为了呈现宣讲活动教化风俗人心的效果在题材选择上远离了狐鬼花妖的诙诡奇幻,更倾向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阐释,在改编《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对题材的选择体现了重伦理关系的倾向,同时将抽象的教条融入日常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展开对教条的道德阐释,将“圣经贤传”案例化、生活化,使得原本抽象的教条得以更好地被民众所接受。
二、突出道德说教的艺术形式
将聊斋宣讲小说文本和《聊斋志异》以及其他聊斋说唱文本进行比较后发现,聊斋宣讲小说“以案为证”的文体形式有助于道德说教的表达,同时其多采用第一人称人物讴歌的方式来帮助听众理解其故事蕴含的情感和所表达的道德规范。
“以案为证”是宣讲小说突出的文体形式,主要表现为“诗+议论+故事+议论”“故事+议论”,这样的文体形式重在“将‘案’作为‘理’之证据并运用‘案’论证‘案’之必要”[6]97,主要是通过案证故事来证明其说教之理不诬,所以在改编“聊斋”时,叙述者常将故事阐发的道德规范鲜明地放置在文本开端或结尾,以直接议论的方式阐明道理,如《冤中冤》开头的一段议论:
人生养女须留意,莫待标梅岁过时。妇女往来当禁忌,春风休教出藩篱。
这几句话是劝人养女要教他知三从,晓四德,不可娇养惯惜。至于择配,亦当听天安命,不可过为择选。苟迁延岁月,嫁不及时,淫心一动,丑事败露,其祸有不可测者。试讲一个案证,各位静听。[7]
《冤中冤》改编自《聊斋志异·胭脂》,故事开端以韵文引出要宣讲的核心理念,即嫁女要应时,并加入议论对韵文所引出的理念做出简单阐释,用“试讲一个案证”引出故事主体,说教意味强烈。同样改编自《胭脂》的子弟书《胭脂传》的开头则是以韵文概括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主要起到吸引听众注意和炫才的作用,并未以说理为要。单弦牌子曲《胭脂判》的开头亦是如此。同为聊斋说唱作品,聊斋宣讲小说在“以案为证”的文体形式之下更有助于道德说教的表达。结尾同样在曲折的故事结束之时以议论作结,引导听众思维,避免听众出现理解歧义,强化道德说教的力度。这些议论的内容基本上是对理想的人伦关系的高度概括,诸如“安生理以得富贵”“乡党和睦息事端”“姻缘天定”等等,并通过首尾位置来强化特定的道德理念的记忆。这些议论虽然与《聊斋志异》中结尾的“异史氏曰”都是叙述者的议论,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更多的是个人的慨叹,而宣讲小说的议论更像是“标准答案”,起到给作品定调的作用。将《聊斋志异·姐妹易嫁》结尾的议论和《缓步云梯集》中的《姐妹易嫁》进行比较。
异史氏曰:“张家故墓,毛氏佳城,斯已奇矣。余闻时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为后解元’之戏,此岂慧黠者所能较计耶?呜呼!彼苍者天,久不可问,何至毛公,其应如响?”[8]868(《聊斋志异·姐妹易嫁》)
奉劝世人不可以阴地为主,若无德行,即葬得好地,也不发达。可知阴地不如心地,即张员外葬地一事便知。为女子者,切不可嫌贱丈夫,如以有嫌贱丈夫的,当以长姑为戒。丈夫也嫌不得妻子,若像文简有嫌妻子,都降了一科解元。[9](《缓步云梯集·姐妹易嫁》)
前者主要是个体情感的抒发,表达了对报应神验的叹服,重在抒发对自我时运不济的哀婉,后者则在议论中树立了对世人、为女子者、为男子者的规范,在结尾处结合故事案证强化道德说教的力度。
宣讲小说非案头读物,就目前掌握的116 篇聊斋宣讲小说的情况来看,只有《钟贯山》《莺疏燕影》《舍身取义》《听妻显报》《贤妾化妻》《愈祸愈福》《宣讲明快》《侯氏取针》8 篇②没有在故事中加入说唱。相较于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等由讲唱者“代言”的方式,宣讲小说中的唱词常常是由“宣”“唱”“歌”引出,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这样的艺术形式使得在改编“聊斋”故事进行宣讲小说的创作时常常在人物讴歌中借人物之口传达道德规范。《南山井》冯氏劝其夫戒淫:
冯氏曰:“夫君呀,常言道:‘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遏欲文》说得有:‘绝嗣之墓,无非好色狂徒;妓女之宗,尽是贪花浪子。’近报妻女,远报儿孙,夫君须要谨戒。”何甲曰:“娼妓原是做的生意,有啥罪过?”冯氏曰:“嫖妓之罪有五:一坏品行,二荡家产,三惹祸患,四生恶疾,五伤性命。……”[10]410
二人的对话首先强调了“淫”之恶,又引《遏欲文》为旁证,后详述妓女之恶以断绝浪荡子行淫的重要途径。人物对话中穿插大量劝诫之语,虽破坏了故事整体的叙述进程,但无疑有益于道德教化。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过程中借故事主人公的对话将故事情节中需要强调的道德理念提炼出来,使其成为宣传伦理教化的传声筒,强化道德理念的表达,防止听众因被故事情节吸引,而忽视宣讲活动的劝善意味。
同时宣讲小说作为辅助宣讲的材料,要适应宣讲活动的场景。根据李来章《圣谕宣讲乡保条约》中所收录的“圣谕宣讲跪拜位图”可知,宣讲时围绕着呈放圣谕的条案,东、西、南三面环绕排列着众多宣讲听众。宣讲者通常为两人,在面对广大听众时需要有效传达宣讲内容。为了保证听众有效接受,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聊斋志异》时,会在人物讴歌中大量运用重复的表达技巧。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认为重复的第一种类型是言语成分的重复。这种重复在聊斋宣讲小说中通常出现在语气词和感叹词当中,如在《南山井》中胡成被诬杀人无法摆脱罪责时,胡成以唱词的方式诉说自己的冤屈,反思自己行为的过失,其间“呀!天呀天”重复了三次,“天呀天!”重复了五次。这类包含有强烈感情倾向的短句的不断重复,使得“劝世人,品要端,莫滥酒,莫发癫,若能以我为征鉴,无事无非乐平安”的劝诫主题凸显出来,起到了强烈的以情说理的效果。同时短句与长句唱词的交替呈现也使说唱的结构更加灵活,听众更能直接地感受到人物饱满的情感以及传达的道德规范。重复的第二种类型就是事件和场景的重复。人物的唱词经常会用来诉说经历,在唱词中的经历通常是前文故事情节的概括。《孝子伸冤》中方平之父方正端刚正不阿,好铲强扶弱,遂与鱼肉乡里的羊某有嫌隙。羊某家中失窃,捕盗贼飞毛腿,未获赃物,便贿赂捕役教唆贼诬陷正端为窝户,又贿赂县官臧令使其严刑拷打,后正端死于狱中。以上情节在唱词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方平见到父亲尸骨之时感慨父亲悲惨遭遇的痛声悲唱,第二次出现在方平告县令不成后上告到经理司的诉告唱词中,第三次出现在九王爷銮驾前的诉告唱词中,其核心事件重复了三次,同时每次唱词都附加了之后的经历。同样重复的结构还出现在《双枕帕》《佳偶天成》《雷神报》《一雷双报》③等情节曲折的宣讲小说中。这种诉说经历类型的唱词经常会将过往的经历重新浓缩编写,反复讴歌。“在一部小说中,两次或更多次提到的东西也许并不真实,但读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定它是有意义的”[11]3,这种重复一方面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反复诉说,使得情感的浓度不断加深,同时考虑到听众群体的接受程度,用唱词中复现事件的方式来帮助听众理解复杂的情节并强化其中蕴含的道德规范。
三、强化道德实践的情节设置
聊斋宣讲小说作为宣讲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教化。“教化之感,盖其势之自然,尤影响之从形声也”[12]86,教化方式重在强调因势利导。杨庆堃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进行研究时认为:“普通人精神中有关宇宙的认知——事实上,是人的整个生命模式——受到冥冥中的神明、鬼、灵魂世界的浓重渲染”[13]21。因此宣讲小说的创作者在改编聊斋故事时,特别强调运用报应观作为情节组织的内在逻辑支撑。
百姓在对冥冥之中的力量的敬畏之下,普遍产生了对天、地、冥界的信奉。聊斋宣讲小说中频繁对“天”进行书写,祈求“老天”开眼:“哭一声,老天爷,把我看望”,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天”是作为一个“超自然裁判”出现的。“天”作为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监督者,根据个人行为的善恶降下惩罚或者福报,这种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成为个体进行道德实践的内在驱动力。“此真行孝之美报也”“况淫为万恶首,报应快当”“此即刻薄强娶之报也”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聊斋过程中强调人物的命运和报应的联系,赋予了伦理道德规范先天的合理性,将伦理道德规范用因果报应的故事模式纳入民间话语体系。
宣讲小说改编《聊斋志异》故事的过程中会通过拼接情节的方式加强宣讲小说中的因果联系。这里的“拼接情节”特指一篇聊斋宣讲小说由两篇或者以上的聊斋故事改编而成。在目前收集的材料中,这类小说有《钟贯山》《失新郎》两篇。《钟贯山》改编自《绿衣》《莲花公主》,在《绿衣》这一故事中,主人公救下了绿蜂,却只是经历了一场不合礼法的“邂逅”,后绿蜂离去,善举的福报不强,不足以鼓动人心;《莲花公主》则是主人公偶然受邀至蜂巢世界见到蜂蜜所化精怪,见其美动心后获得美好姻缘,此情节无善举而得福报,只是书生的白日梦。而宣讲小说《钟贯山》将《绿衣》中主人公在现实中解救蜜蜂的情节和《莲花公主》中主人公入蜂巢世界与蜜蜂公主所化的女子成家的情节结合起来构成了新的文本,主人公因为救了被蜘蛛所困的蜜蜂从而入蜂巢、得二美成家,改编将二者情节进行取舍组合,强化了情节间的因果关系,使得积善事必有福报的因果链条更加明晰。《失新郎》是根据《新郎》和《小翠》二者改编的,提取两个故事的核心情节,将新郎洞房前离奇失踪作为好田猎之家的报应,把狐女化人嫁给痴儿使痴儿转慧的情节作为好生之人子孙的福报,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呼应开篇所引入议论的韵文:“一放生,一伤生,两般功过造来深,恩仇报得清。福也临,祸也临,痴儿转慧富转贫,忧喜两惊人”。改编意在突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报应观,并用自身行为影响子孙的福报来引导民众行善。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家族性”[14]68的特点,其行为影响到子孙后代,“后来子孙繁盛,簪缨不绝”“后来子孙鼎盛,富贵双全”“后俱少年登第,世代簪缨不绝”等表达子孙后代福泽绵延的程式化描写成为聊斋宣讲小说改编过程中的固定模式,用来增强对民众践行道德规范的吸引力。
同时聊斋宣讲小说的改编创作常常会对相应的情节进行扩充或者删改,以强化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善业寺》改编自《杜翁》,《杜翁》讲述杜翁误入冥间,阴差阳错之间托生成猪,后在友人张某的指引下返回自身肉体的故事。《善业寺》在保有原有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主人公事父母唯尚虚华,大操大办父母丧礼却不能诚心孝顺父母而使父母在阴间受到惩罚,经历游冥所见后改其行成为真正的纯孝之人的故事情节;改编自《聂小倩》的《易经除鬼》除了保留女鬼夜间勾引书生的核心情节之外,增加了主人公恪守礼法祭奠其父母,诚心哀恸不随流俗,并带领亲族邻友皆依礼行事,使乡风渐归于厚的情节。《善业寺》《易经除鬼》两篇宣讲小说在原有的故事情节之上,通过增添具体的养生丧死的道德实践来教导民众,使“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5]26的思想明白晓畅地传达给民众。此外《义虎祠》增加主人公骑虎杀敌建功立业的情节渲染了忠君报国的道德观;《义犬护尸》则增加主人公曾经是杀猪宰牛的屠户而后向善的情节,与《聊斋志异·义犬》中救犬一命获犬报恩的故事情节相结合,凸显了改恶从善的现实可行性。
与之相应,聊斋宣讲小说还会对不合礼节的情节进行删改,对比《青梅》和由其改编的宣讲小说《节报孝》可以发现,《聊斋志异·青梅》中对青梅的身世有着详细的描述: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为畛畦。一日,自外归,缓其束带,觉带端沉沉,若有物堕。视之,无所见。宛转间,有女子从衣后出,掠发微笑,丽绝。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遂与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谓程:“勿娶,我且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诮姗之。程志夺,聘湖东王氏。狐闻之怒,就女乳之,委于程曰:“此汝家赔钱货,生之杀之,俱由尔。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门径去。[8]742
青梅在《聊斋志异》中是程生和狐女未经嫁娶所生的人狐相恋的女子,而在其改编的宣讲小说《节报孝》中直接略过了青梅的出身,在案证故事开篇即叙述张介受的孝行,着力宣扬张生的纯孝之举,而青梅的出身不合礼法,恐引人非分之想,故有意略去,即使这样会损伤人物塑造的合理性。《宣讲集要》凡例有言:“案证须取确当,其一切荒唐悖谬者概行削去”[16],宣讲活动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有严格规范的教化活动,目的在于熄邪念正人心,需要审慎地选择来源并进行相应的删改,除去可能有碍风化和蛊惑人心的内容以树立行为规范。
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聊斋故事进行宣讲小说创作时,通过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的题材选择凸显了其培植伦常的目的,而宣讲小说独特的艺术形式有利于强化道德说教,更加突出其教化性。在文本内部的情节设计上,以传统报应观作为情节设计的核心,并通过增删情节的方式指导民众的道德实践,在情节设置上增强了聊斋宣讲小说的教化性。聊斋宣讲小说在改编过程中充分利用《聊斋志异》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生动曲折的情节之外,实现了娱乐性和教化性的统一。其在改编《聊斋故事》时的创作倾向鲜明地体现出宣讲小说的“化民成俗”之意,展现了聊斋宣讲小说试图建立百姓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稳定的伦理关系,塑造理想的道德生活的美好愿景。
注释:
①《聊斋志异·珊瑚》被改编为《孝媳化姑》《孝化悍婆》《孝感姑心》《孝逆互报》《紫薇窖》《横柴纹》,其中《孝媳化姑》收录于《宣讲选录》《宣讲大成》《宣讲集要》;《孝化悍婆》收录于《宣讲摘要》《最好听》《宣讲大全》;后四篇依次收录于《绘图福海无边》《自召录》《缓步云梯集》《俗话倾谈》。
②以上篇目中《钟贯山》改自《绿衣女》《莲花公主》,其余依次改自《聊斋志异》中的《二商》《田七郎》《二商》《邵女》《仇大娘》《阎王》。
③《双枕帕》改编自《聊斋志异·细柳》,其余三篇均改自《聊斋志异·纫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