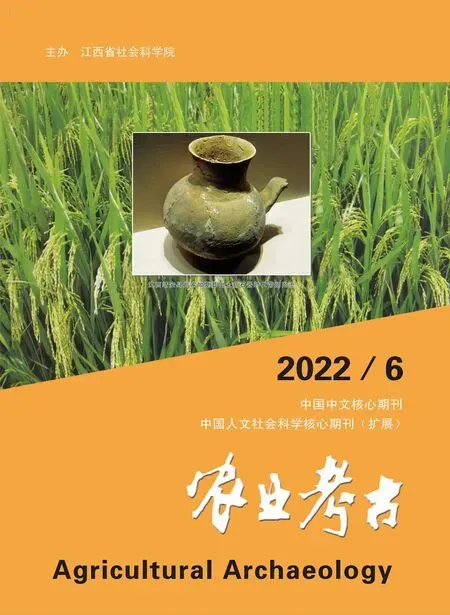海岱地区史前虎遗存简论*
郭荣臻 曹凌子
随着考古学研究重心由古代文化史构建向社会考古、经济考古的转移,环境与生业考古在考古学话语体系中占比日渐提升。作为史前几大文化区之一的海岱文化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相对较为完整,极具多领域、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基础条件。动物种属鉴定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以来,基于动物遗存的海岱地区史前环境与生业问题也愈发受到重视。回顾学者们研究简史,既有长时段全区域的综合研究[1],也有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整合观察[2],还有某类动物遗存的专门探 讨[3](a.p208-219;b.p220-232),另 有 基 于 动 物 遗 存 的 其 他科技分析[4],而为数最多的则还是基于某一遗址的动物考古个案鉴定报告[5](a.p194-215)。得益于这些持续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及考古发现中偶见的动物遗存,海岱地区史前环境与生业相关问题证据频添,为了解海岱地区史前经济形态演变乃至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更新视角。综观多年的动物遗存考古研究,尚未有学者专就出土虎类动物作过专题讨论。2022年恰逢壬寅虎年,对海岱地区史前虎类遗存梳理不但应时应景,而且有利于对人类行为乃至背后文化与社会的考古观察。本文拟从海岱地区史前动物骨骼中虎遗存的考古发现切入,在此基础上对相关考古问题予以简要讨论。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海岱地区史前虎遗存的考古发现
海岱地区史前动物考古研究的历史,可以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国内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即有对田野发掘所获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研究[6](P90-91)。时至现今,几乎所有考古发掘项目进行过程中,发掘者都会系统采集动物骨骼遗存并送交专门人员鉴定分析,从而积累了大量的遗址个案研究。就现有动物考古记录来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沂源扁扁洞遗址未见虎类动物孑遗[7];新时器时代中期的后李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龙山文化皆有遗址出土有虎骨遗存或可能存在虎遗存证据。为便研究,本文拟按文化先后顺序梳理如下。

表1海岱地区史前诸遗址虎遗存共出动物一览表
(一)后李文化
199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潍坊市寒亭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前埠下考古队,对前埠下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动物遗存为数较多。据山东省博物馆孔庆生先生鉴定,此次发掘中所采集的动物遗存至少代表35个种属[8](P103-105)(表1)。需要说明的是,该遗址堆积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期属后李文化,第二期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对于虎骨的出土单位,发掘者及鉴定者皆未作详细说明,不能排除其属于后李文化的可能性。
(二)北辛文化
1975年、1976—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与山东省济宁行署文化局、兖州县文化馆等多家单位在兖州王因遗址做工作,通过调查、试掘、发掘,揭露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时期的大量文化遗迹与遗物。为数众多的动物遗存也是该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经由专门研究者鉴定分析,虎骨是野生动物遗存的组成部分[9](P68-69,P414-451)(表1)。
(三)大汶口文化早期
除北辛文化外,兖州王因遗址还出土有有大量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动物遗存,野生哺乳动物[10](a.p145,414-451;b.p534-542)(表1)①。
(四)大汶口文化中期
1997年前埠下遗址发掘中所见虎骨,属于该遗址第二期亦即大汶口文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11](P103-105)(表1)。
(五)大汶口文化晚期
1989—1995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对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9次,采集到较多动物骨骼,经袁靖先生团队研究,哺乳动物中有虎遗存[12](P424-441);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该遗址发掘4次,动物考古研究显示仍有虎骨出土[13](P306-327)(表1)。
(六)海岱龙山文化
1973年、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等对泗水尹家城遗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发掘,所采集的动物骨骼经专家鉴定后,证实在海岱龙山文化单位中存在虎骨1块[14](a.p79-87、350-352)。199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滕州庄里西遗址发掘中,系统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后经宋艳波鉴定,所出虎遗存为虎头骨[15](P609-626)。在蒙城尉迟寺遗址前9次的发掘工作中,仍有虎遗存出土[16](P424-441);后4次发掘所获动物遗存种类更多,但未见虎遗存[13](P306-327)(表1)。
二、海岱地区史前虎遗存的量化分析
根据惯例,并参考海岱地区史前植物考古研究性质种类划分[17],我们将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系统地采集动物骨骼样品并送交专门研究人员进行种属鉴定甚至开展了量化分析的研究称为“系统动物考古研究”,对未系统采集动物骨骼样品、只是捡获零星动物骨骼、粗略介绍主要动物种类的研究称为“非系统动物考古研究”,并把未采集动物骨骼或零星采集动物骨骼却未公布动物种类的研究称为“非动物考古研究”。本文所涉案例皆系前两类研究,综上简史梳理,不难发现:凡是出土有虎遗存的遗址都开展了系统动物考古研究;凡是未开展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皆未发现虎类骨骼遗存。
据近年相关学者对动物考古及基于动物遗存遗址个案研究的综合统计[18],出土有后李文化动物骨骼遗存的遗址合计6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5处;出土有北辛文化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28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4处;出土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8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6处;出土有大汶口文化早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7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2处;出土有大汶口文化中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7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1处;出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11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5处;出土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23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6处;出土有“大汶口文化”②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6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1处;出土有海岱龙山文化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53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21处;出土有岳石文化动物遗存的遗址合计33处,其中系统动物考古研究5处。
结合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遗址情况来看,后李文化有1处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20%,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17%;北辛文化有1处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25%,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4%;大汶口文化早期有1处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50%,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14%;大汶口文化中期有1处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100%,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14%;大汶口文化晚期有处1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约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17%,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4%;海岱龙山文化有3处遗址出土有虎类骨骼遗存,约占系统动物考古研究遗址数量的14%,约占出土有动物遗存遗址数量的6%;岳石文化遗址尚未见虎遗存。
就虎骨遗存的绝对数量来看,前埠下遗址仅见下颌骨1块、下裂齿1枚、下臼齿1枚,所代表的个体数少;王因遗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虎骨数量为数不多;尉迟寺遗址前9次发掘在大汶口文化堆积中见虎骨1块、在龙山文化堆积中见虎骨2块,后4次发掘仅在大汶口文化堆积中见虎骨2块;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仅见虎骨1块;庄里西遗址所出龙山文化虎头骨仅有1块。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出土有虎遗存的诸遗址中,考古发掘所采集到的虎骨不但绝对数量偏少,而且所代表的最小个体数也少。
量化分析可见,出土有虎骨遗存的遗址在有动物遗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比较低。广域、长程地看,虎遗存的遗址覆盖率不但低于猪、狗、牛、羊等家养动物的遗址覆盖率,也低于野猪、鹿、獐等常见野生动物的遗址覆盖率,甚至与狼、狐等哺乳动物的遗址覆盖率相较也不占数量优势。就绝对数量、最小个体数来看,诸遗址所采集虎骨皆少。虽然海岱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与动物考古研究仍在继续,且已有个案分析存在时代和空间的不一致,但考虑到学界现有考古记录已为数较多,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海岱地区史前虎资源的分布大势。将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或可进一步加深认识。
三、海岱地区史前虎遗存的出土情境
囿于诸遗址材料公布情况,对虎骨骼遗存出土遗迹、出土位置等信息皆乏有效信息,尚难以据之对出土动物遗存的微观环境做更细致讨论。但就各遗址材料观之,以哺乳动物为例,与虎遗存同出的动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家养动物猪、狗,野生哺乳动物鹿、獐等,部分遗址还见有与虎同属猫科动物的猫(表1)。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向这些遗址动物遗存具有相似的生境,另方面,一定的生境中会存在多种类型的动物群。
从时代来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皆出土有虎遗存,甚至后李文化也存在虎遗存的可能性。就空间而言,海岱地区史前时期虎遗存主要分布在鲁北、鲁中南、皖北等3个文化小区,鲁东、鲁西、苏北等地尚未发现虎骨遗存。时空分布特征显示,海岱地区最早的虎可能出现在鲁北地区或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至海岱龙山文化阶段,作为动物资源的虎之分布区域达到史前最广。这种分布格局、传播路径对本区后世先民的虎类动物资源作用产生了影响,如尹家城遗址商周至汉代的考古记录中仍有虎类动物骨骼孑遗(表1)。单就现有考古记录而言,出土有虎骨遗存的遗址所见虎骨皆位数偏少,这种出土状况可能对理解时人社会生活有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已刊材料中,对动物遗存的具体出土背景皆乏有效介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公布及对老材料的不断检视,今后若能有针对性地对虎骨遗存出土单位、出土情境加以详细介绍,或许对剖析虎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有裨益。
四、海岱地区史前虎遗存反映的环境与生业
(一)虎遗存与史前环境的关系
动物遗存对重建古代自然环境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为例,专题研究方面,王青等曾据獐遗存对史前环境进行了研究[19]。综合性动物考古研究中,通过动物遗存判断古代环境的研究为数更多,如宋艳波在对滕州官桥村南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中,也曾综合淡水软体动物、鱼类、鸟类、鹿类等动物遗存组合状况,判断了遗址周边北辛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状况[20](P251-260)。作为典型林栖动物,虎的存在及其指向的特殊生境暗示了出土虎遗存遗址聚落先民生活地点距离丛林、树林不远,或聚落周边有这种环境,这一点与海岱地区史前时期不同文化不同遗址出土有多种类型树木资源相对应。这种情况指向了气候温和、降水适宜的生境,这样的生态环境不但有利于多种动物生存,对人类生活及其发展也有裨益。
就遗址所在地现代地貌来看,潍坊前埠下遗址位于二级台地上的高埠顶端,地势较周边略高,东有潍河。兖州大部属于山麓冲积平原,王因遗址略高于周边地平,地势总体平坦,北有洼沟,东有泗河,西有疑似古河道孑遗。蒙城地处淮北平原,尉迟寺遗址位于崮堆之上。尹家城遗址地处低山丘陵向河谷平地过渡地带的台地上,北有泗河,东、西皆有小河。微地貌反应的聚落选址情况符合人类生存需求,而聚落所在地大环境则与虎等动物所需生境具有一定的吻合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动物遗存推论史前环境虽然具有可行性,但却并非仅据某种动物即可为之。要准确判别遗址周边环境,需要在虎遗存基础上,综合多种证据加以判断,如其他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炭化植物遗存、微体植物遗存证据,利用多种生物证据重建时人生境,所得结论将更具可信度。
(二)虎遗存与史前生业的关系
除自然环境外,动物遗存对复原先民生业行为乃至具体食物结构具有直接作用。一般情况下,发掘者在遗址发掘中所采集的动物遗存系时人利用动物资源的证据,或食其肉,或用其皮、毛,或加工其骨骼,等等。在多重用途中,将其作为时人动物性食物资源的可能性最大、最具普遍性。
虎肉具有可食性,且曾经为古人所捕猎、所豢养、所食用。在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记录中,学者们普遍将考古发掘所获野生动物遗存作为狩猎经济的重要证据。虽然既往研究者未专门强调,但作为野生哺乳动物的组成,对虎的利用也被视作先民生计策略的组成。近期公共考古记录中,2022年1月以来,在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的“虎佑神州”特展中,新石器时代重庆巫山大溪、丰都玉溪的虎牙也被冠以古人“厨余垃圾”的名称,并作为古人狩猎采集生活的重要证据[21]。就此角度观之,虎作为史前先民动物性食物资源的可能性恐怕尚难完全排除,但食用似乎并非史前先民对虎类动物资源的主要利用方式,下文将予详论。
广义的生业经济不唯人们的食物资源获取方式,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方面,出土有动物遗存的海岱地史前遗址中,虎骨遗存的遗址覆盖率偏低;另方面,出土有虎骨遗存的遗址中,虎遗存骨骼绝对数量亦偏少。所以如此,除动物骨骼自身保存状况外,可能也与时人将虎骨骼作为骨料、用于加工生业工具不无关联。在今后的研究中,若能有针对性地对具有辨识种属特征的骨器加以鉴定,或许也有助于此类证据的寻求。
五、海岱地区史前先民的虎文化
动物因其特殊形象,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双重特点。作为大型食肉动物,虎常被视作百兽之王,长期以来与龙并称,对其他动物乃至人类具有震慑力。虎类动物因其象征性特质,也曾作为图腾在不同氏族中扮演过各种角色。虎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引起学界关注良多[22]。学者们对史前时期虎类文化因素的讨论不少,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龙虎墓”为代表的研究中多有文化寓意解读[23]。近年来,以虎文物为主要证据的专题讨论也不乏其例,学者们在梳理商周以降诸历史时期虎文物的基础上对虎的象征意义频有提及[24]。
动物骨骼中虎的发现为类虎文物找到了原型。就史前时期而言,以狩猎为组成部分的攫取性经济行为在时人生业模式乃至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文化象征意义来看,虎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古往今来皆被人们以野兽、猛兽视之,象征着勇猛、威严。如果能将虎捕获且为族群所用,则猎虎的个人甚至社群可能都会被打上勇敢、坚毅乃至强大、权势的标签。
就虎骨的极低出土概率、遗址覆盖率、最小个体数观之,此类动物并非海岱地区史前先民狩猎活动的主要捕猎对象。一方面,可能与虎类动物的活动地域、出没频次相关;另方面,更重要的则与这种动物的捕猎难易程度相关。通常情况下,单人即可捕获为数不少的中、小型哺乳动物,部分攻击性不强的大型哺乳动物也并不难以猎取到。同等条件下,若想捕获虎,则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时间成本。就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史前先民仅是为着食用需求,大可不必冒着生命危险付出更高的代价从事这样的狩猎活动,猎取其他难度不大的诸类动物便可满足聚落先民的肉食资源需求。就此角度推之,史前聚落中的虎遗存,可能扮演着远非食用功能的其他角色。海岱地区史前先民是否也有征服野兽昭示自己勇敢的文化心理,或许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上升到认知考古层面,需要更多的材料、方法、理论支持。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若能积累更多有效证据,或许有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
就笔者目力所及,海岱地区史前时期考古记录中,在动物骨骼以外,人工制品中的虎类或类虎文物尚乏确凿证据。考虑到本区先民自后李文化以降的陶塑或动物类其他人工器物制作传统,不排除先民能够加工多样化动物雕塑或其他制品的可能性。当然,这一推论也需更多考古发现证实。
六、结语
综前所论,仅个别开展过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出土有虎骨骼遗存,非系统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皆未出土虎遗存。海岱地区史前时期先民虽然可能捕猎虎作为自己动物性食物资源、物用资源等组成部分,但更可能将虎作为文化象征的媒介,甚至在仪式性活动中扮演角色。就现有考古记录而言,本区新石器时代最早利用虎资源的先民可能系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人;北辛文化时期,鲁中南地区先民开始对虎资源的利用;大汶口文化至海岱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虎类动物资源利用达到本区史前时期最大范围。虎遗存对海岱地区史前时期先民环境与生业的研究具有助益作用,甚至对了解时人虎文化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海岱地区各时代、诸文化小区田野考古工作、动物考古专题研究的不平衡性,基于现阶段动物遗存证据的相关问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而且只能是阶段性假说,更深、更新的认识仍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解答、阐释。
注释:
①笔者注:各类动物遗存鉴定报告中,对原研究者未作时代区分者统归于“北辛—大汶口早”时期。
②研究者未作细分,不确定动物骨骼出土单位属于大汶口文化哪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