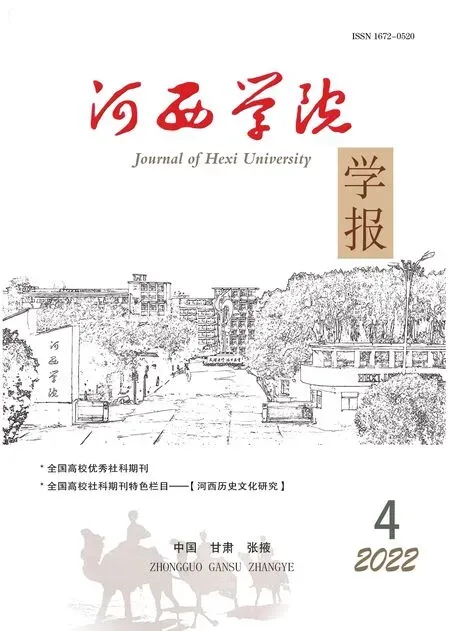甘肃山丹方言中的高程度表达法
葛 媛 媛 梁 吉 平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山丹县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段,隶属于甘肃省张掖市,山丹方言即该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汉语方言。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山丹方言属于兰银官话河西片,作为汉语的地方变体,山丹方言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相区别,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目前,关于山丹方言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且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山丹方言语音及词汇的系统性研究,而对高程度表达法的研究还极为薄弱,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山丹方言中表高程度的重叠形式
程度范畴作为重要的语义范畴,需要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来体现性质与状态的量级差别。重叠是语言单位的一种外在形态变化,[1]汉语中程度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其中重叠形式是重要的程度表示法之一。程度本身暗含“量”的意义,李宇明(2000)指出重叠大多与量的变化有关,并将重叠视为表现量变化的一个重要语法手段。[2]汉语中词语重叠后,基本词汇意义较之重叠前并无很大变化,其改变主要体现在语法意义上。邢芬(2016)认为重叠形式语法意义主要具有两方面特征,其一在于凸显程度量,其二在于描绘状态。[3]山丹方言中重叠是程度表达的重要词法手段,且能够重叠的词仅为单音节词,表现为“AA 式”,且需要在重叠式后加后缀“的”,大多数情况还需要在其后加助词“了”,另外构成AA 式的单音节词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
(一)重叠形式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
山丹方言重叠形式表示程度,在句法成分上主要充当谓语与补语。
1.重叠形式充当谓语成分
无论是形容词重叠或是动词重叠,其主要句法功能在于充当谓语,例如:
(1)水果忘掉往冰箱里搁了,全都坏坏的了。
(2)天爷又下开了,晾的衣服忘掉没收拾,全湿湿的了。
(3)下午没吃上些饭,这会子肚子空空的了。
(4)这些饭就够够的了,再加不上了。(这些饭已经足够了,不能再添饭了。)
2.重叠形式充当补语成分
山丹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也可以充当补语成分,例如:
(5)我刚打扫罢,那就把屋里弄得乱乱的了。(我刚打扫完,他就把家里弄得乱极了。)
(6) 每回外头吃饭都喝得醉醉的了才回家。
(7)天爷太冷了,把人冻得xìxì②的了。(天气太冷了,我都要冻死了。)
(二)重叠形式的组合功能
单个形容词可受否定词修饰,其重叠形式则不能。石毓智(2001)指出否定和重叠的互斥性来自两者语法意义的不相容性,重叠式是一个表定量化的概念,这与否定的条件相悖,因此导致了重叠式与否定之间的互斥性。[4]但山丹方言中个别具有贬义色彩的单音节形容词,在重叠之后,其前可以用“没(有)”否定,表示其糟糕程度还未达到极深的地步,此时“AA 的”后无助词“了”。例如:
(8)这些水果还没坏坏的。(这些水果还没有坏透。)
(9)我就思想的只要是还有插脚处,屋里就没乱乱的。(我认为只要有放脚的地方,屋里就没有到非常乱的程度。)
二、山丹方言中表高程度的准后缀“法(子)”③
加缀式是汉语复合词的构词法之一,现代汉语中“法”被视为类后缀,如“讲法”“手法”“想法”,山丹方言中的“法(子)”也可以附加于形容词性词语或动词性词语之后,其作用并非在于构词,而是用于表示程度极高之意。何茂活(2011)指出,山丹有一首地方民歌《回娘家》,其中最后一节为“回娘家,回娘家,借上穿戴夸一夸。谁知道这个霉什法,穷汉干事乱子大!”[5]并将此处“谁知道这个霉什法”解释为“谁想到这么倒霉!”此处“什”并无实义,也可省略为“霉法”或“霉法子”。我们采用“准词缀”这一说法,将其视为山丹方言中表示程度的一个词法手段。山丹方言中“法(子)”不仅可位于形容词之后,表示性状程度的加深,还可以位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量的加强。就语法功能而言,“X 法(子)”并不能单独使用,其前不能受任何程度副词或否定词修饰,而是总是与指示代词“这个”或“那个”组合,构成“这个/那个X法(子)”。例如:
(10)呦,你没见那个骂法,连八辈子的先人都骂下来了。(何茂活2007:314)
(11)你的这个歪法,谁又不害怕唦?就连我都怯巴巴的。(何茂活2007:314)
在一般认知中,动作动词并不具备[+程度]语义特征,兰宾汉(1993)认为动作动词作为具体的动作行为,总能呈现出某种属性,而不同属性具有程度。[6]如例(10)中“骂法”,“骂”可以是“责骂”,即用严厉的话语责备,也可以是“破口大骂”,指满口恶语骂人。由此可见“骂”有轻重之别,因此“法”作为准后缀位于“骂”之后,一方面在于加强“骂”这一动作量,另一方面在于说明“骂”的严重程度。山丹方言中“歪”为“厉害”义,在例(11)语境中表示脾气大,“法”与“歪”黏合在于说明脾气非常大,且后文出现的“害怕”“怯”,也可加以说明。
另外还可以在指示代词“这个”或“那个”前加山丹方言中最常用的疑问词“咋”,通过反问来传递说话人的主观情感,表现程度之高,例如:
(12)咋这个着气法——跑了三趟子都没盖上个章子。(太令人生气了,去了三趟没有盖上章。)(何茂活2007:314)
(13)咋这个冷法,穿的羽绒服都抗不住。
由以上例句可知,“法(子)”本身并不具有感情色彩,整个话语的感情倾向由谓词决定,它附加在谓词之后,只承担语法意义,增补语句的程度,且适用语境并不受限。
三、山丹方言中的程度补语
补语作为谓语的补充成分,补充说明动作行为变化的结果、状态、趋向、可能、数量、程度等。程度补语是按照语义特征,从补语系统中划分的下位概念,其语法功能在于凸显谓语达到极高的程度量,一般附有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山丹方言中,高程度补语是程度范畴中重要的句法手段,其中包括组合式程度补语“凶”“歹”“砝码”“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提不成/招不住”,以及黏合式程度补语“咂”“美”“零干”。
(一)组合式程度补语
1.凶
“凶”本义为“险恶(之地)”,《说文解字》释“凶”为“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7]《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以下简称《现汉》)对“凶”有如下释义,①不幸的(形容死亡、灾难等现象,跟“吉”相对);②指年成很坏;③形容词,凶恶;④形容词,厉害;⑤指杀害或伤害人的行为;⑥指行凶作恶的人“凶”。[8]由《现汉》释义可知,“凶”在汉语普通话中主要为“凶险、凶恶”之意,该语义对应山丹方言则多用“恶”“坏”来表示,而在山丹方言中“凶”最频繁的用法是表达程度义。沈思莹(2018)认为程度补语是高量级程度表达最典型的句法位置,[9]山丹方言“凶”表示程度义时,只能位于谓词成分之后,构成组合式程度补语“X得凶”。
现代汉语中“凶”也被视为程度补语系统的成员之一,但通过检索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发现,“凶”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用作程度补语的语例极为有限,且适用语境均为非正面语境。莫超(2007)通过考察甘肃临夏方言的程度表示法认为,只有临夏方言常说“……的凶”,而别处只说“凶的很”。[10]事实上“X 得凶”的使用在甘肃山丹方言中极为普遍,且适用语境不受限制。例如:
(14)毛笔字写得好得凶。
(15)今个干了一天的活,费事得凶。(今天干了一整天活,累极了。)
(16)给娃娃买的裤裤大得凶了。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凶”作为补语成分时,其前谓词均为一般动作动词,例如“闹得凶”“骂得凶”“打得凶”“哭得凶”,且补语成分还可进行扩展,如“闹得很凶”,而在山丹方言中,“凶”作为程度补语并不能进行扩展。从组合能力看,山丹方言中程度补语“X 得凶”,“X”一般为形容词或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程度量是形容词的典型特征,因此也可说明形容词本身暗含程度语义,从而可以进入“X 得凶”结构,而心理活动动词能够进入该结构在于,心理动词是人的心理活动在语言上的反映,其不似一般动词需要表现具体的动作行为,因此在动作性方面更弱。
山丹方言中“凶”位于谓词之后,语义指向为前指,用作补语的“凶”所表示的“极了、不得了”程度义得以凸显。例如:
(17)娃子没考上大学,愁豁得凶。
(18)这个娃子干个事去佯干得凶。④(这个男孩儿做事马虎极了。)
以上语例中,“凶”补充说明谓词的程度极高,语义完全虚化,完全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所表示的“凶险、险恶”之意。
另外,山丹方言中少量动词或动词短语可以进入“X得凶”结构,例如:
(19)你个人都是个烂杆,还爱笑话人得凶。(你自己都是一副懒惰、不思进取的样子,还爱嘲笑别人得很。)
(20)老三家的娃子不爱学习,到究爱玩得凶。
由例(19)-(20)可发现,山丹方言中“凶”位于少量动词或动词短语之后,所构成的“X得凶”这一结构从而具有了评价义,即言者就当前语境中的某一事件或事物表达自己的观点。人类对事物或状况所作出的评价是一种主观行为,言语中含有“X 得凶”这一结构,在体现说话人的情感与态度的同时,也使得话语本身富有情绪性。
2.歹
山丹方言中,“歹”同样是一个极为常用的且富有特色的程度补语。“歹”在《现汉》中被释为“坏(人、事)”,如歹人、歹徒、为非作歹,即“歹”本身具有消极色彩义。我们遍检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并未发现“歹”作为补语成分的用法,而在山丹方言中该用法却极为常见。由于“歹”本身所具有的语义色彩,使得其适用语境倾向于负面语境。例如:
(21)年轻人霉气大得歹。
(22)烂杆得歹。
例(21)中,山丹方言所说的“霉气”是一种对别人的脾气和意见的鄙称,[11]“大”为中性形容词,由于其形容的对象为“年轻人的霉气”,因此整个语境为负面语境,“歹”用于说明“霉气”大到极高的地步,例(22)中“烂杆”既可以指生活窘迫却不思进取、懒惰且不努力改变现状的人,同时也可以指这一特性,该例句中“烂杆”即指这一性质,“歹”位于其后,补充说明“烂杆”到达极高的地步。
由于语用类推,“歹”也可以出现在非负面语境中,例如:
(23)学校新修下的楼高得歹。
3.砝码
通过查阅《汉语方言大词典》发现,“砝码”作为形容词在中原官话中也同样使用,如青海西宁,但由于词典中并未给出示例,因而其语法功能不得而知。山丹方言中,“砝码”是一个比较频繁使用的程度表示法,且在句法功能上,既可以充当谓语,也可充当补语,例如:
(24)那家子人砝码的呢。(何茂活2007:282)
(25)这两天的菜贵得砝码,一斤辣子都四块钱呢。(何茂活2007:318)
事实上,“砝码”用作谓语时,具有实在的词汇意义,即表示“厉害”意,如例(24)在于说明那家人能力很强,那家人很厉害,为夸赞义。而作为程度补语时,其词汇意义正处于虚化阶段。
4.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提不成/招不住
“没 办 法”“没 式 样”“没 话 说”“提 不 成”“招不住”在山丹方言中均可以作为组合式程度补语使用,为高程度补语,虽然其外在表现形式相异,但在语义特征以及语法功能等方面大致相同。
在语义特征上,程度补语“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提不成”“招不住”均可以表示达到极限程度,由于程度极高而束手无策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以上程度补语的极性程度语义均是由其虚化后的“否定”义演变而来,其中“提不成”,“提”即“说起、谈及”之意,“招不住”即“招架不住”,“招架”为“抵挡”义,“没”或“不”的出现,使其暗含[+否定]语义特征。沈家煊(2004)在讨论表示“不超过”意义的词组“不过1”向表示程度最高的附着词“不过3”虚化时认为,“程度最高”的意义是根据“不过量准则”和常识推导而来的隐涵义,[12]通常人们在无能为力、迫于无奈等情境下,会作出与“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提不成”“招不住”相类似的具有[+否定]语义的消极评价,当否定评价域通过隐喻这一途径映射至程度域时,则具有高程度语义。例如:
(26)那把人气得没办法。
(27)胳膊碰下了,疼得没式样。
(28)你真是佋⑤得没话说。(你真是傻极了。)
(29)人刚丢了一百块钱,这会子难过得提不成了。
(30)我冷得招不住。
以上语例中的“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招不住”“提不成”均充当程度补语,说明谓词的程度极高。张虹(2016)指出带“不”的结构,语义上具有否定性,容易高度凸显,通过补充说明状态结果,凸显出程度量。[13]另外“没/不”的否定性决定了所发生的事件本身具有很高的负面程度,或者具有异于常态的特征,在认知隐喻的投射作用下,具有“没/不”的否定结构由否定域向程度域映射,从而隐含高程度义。这类表达同样是山丹方言中频繁使用的高程度表达法。
(二)黏合式程度补语
通过比较发现,山丹方言中,黏合式程度补语的数量少于组合式程度补语。其中最具特色且使用最为频繁的黏合式程度补语为“咂”“美”“零干”。
1.咂
“咂”在山丹方言中是极具特色的程度表达形式,其本身并无具体实在的词汇义,只位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充当补语成分,以此说明谓词达到极高的程度。例如:
(31)跑上来的,没坐车,把人挣咂了。(走路来的,没有坐车,把我都累死了。)
(32)刚到门口就闻着饭味了,把人香咂了。
(33)吃个牛肉面,结果等咂了才挨上。(吃牛肉面,结果等了很久很久才轮到。)
由以上语例不难发现,“咂”与其前的中心词结合非常紧密,且语义指向也均指向中心词,由于“咂”本身并不具备实在的词汇意义,因而与之相结合的中心词所受的限制也较小。在表达效果上,“咂”蕴涵夸张的语义,用于补充说明谓语的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再进一步的地步,从而起到凸显语用效果的作用。
2.美
《现代汉语词典》将“美”定性为形容词,根据所示义项,“美”具有褒义感情色彩,其中有“令人满意的”这一义项。山丹方言中“美”位于动词之后用作程度补语,且其后带语气词“了”,构成黏合式程度补语“X美了”,此时“X美了”并非表示“X”达到极高的程度,而是表示因为“X”这一行为,使得主体达到非常满足、愉悦的程度,我们推断该用法来自“令人满意的”这一语义,例如:
(34)今个一天价啥也没干,定定睡的呢,可睡美了。(今天一整天什么也没做,一直在睡觉,真是睡美了。)
(35)中午吃的羊肉颠卷子,又把人吃美了。(中午吃了羊肉面卷,又吃美了。)
(36)刚打大佛寺滑上雪来就又看电影去了,可是玩美了。
以上例句中,“美”用于补充说明在经过“睡”“吃”“玩”这样的享受之后,主体所达到的满足、愉悦的程度。“美”用作程度补语时,其自身语义并未完全虚化,仍具有[+美好][+满足]的语义特征,因此其整个适用语境均为正面语境,而不会出现在负面语境中,如“气美了”则不成立。
3.零干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零干”在中原官话及兰银官话中均有使用,并且具有动词与副词两种词性。其中定性为动词时,分别是“完成、了结”、“离婚”、“省事”三个义项,定性为副词时,表示“很、实在”义,如青海西宁方言“这个娃娃零干不听话”。[14]山丹方言中,“零干”可以表示“干脆”义,如“还是骑上牲口零干些”,[11]另外还主要用作程度补语,大多出现于消极语境中,补充说明谓词的程度极高,如:
(37)可把人疼零干了。(何茂活2007:284)
(38)一周了没洗衣服,脏零干了。
(39)突然喊上声,还把人吓零干了。
以上例句中,谓语与“零干”黏合之后,凸显出谓语的程度之高,传递出说话人不满、消极的情绪。
四、结语
客观世界的事物具有量性特征,将反映客观世界的“量”的范畴投射在语言中,则形成了语言世界的量范畴。程度是量的表现形式之一,且程度量是一个较为活跃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山丹方言高程度表达,其表现手段多样,不仅可以通过重叠或附加准后缀“法(子)”来表达,还可以使用富有特色的程度补语,如组合式程度补语“凶”“歹”“砝码”“没办法/没式样/没话说/提不成/招不住”,以及黏合式程度补语“咂”“美”“零干”。高程度表达是一种主观极量的表现,本身含有言者的情感态度,因而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体现了言者极强的主观性。
注释:
①此处“zà”正字待考,“咂”是借音字,下文不再说明。
②xìxì,正字待考。
③此处“准后缀”这一说法参照何茂活《山丹方言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14页。
④山丹方言中“佯干”为不留心、粗疏、马虎之意,该例句参照何茂活《山丹方言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73页,略作改动。
⑤此处“佋”字形参照何茂活《山丹方言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年12 月,第313 页,“佋娃”,即傻子义,“佋”为同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