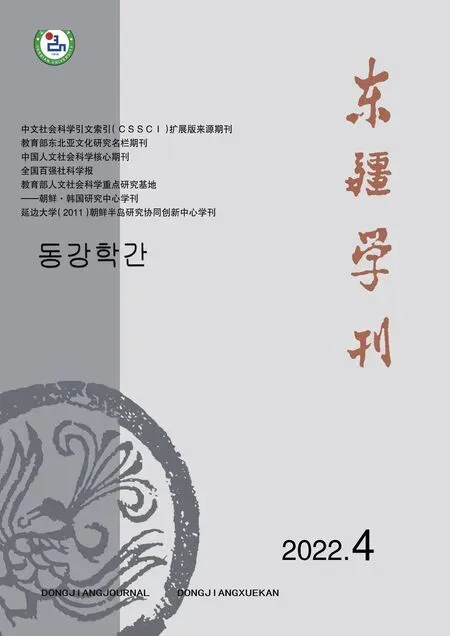由宋时烈传记文学看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
金美兰,曹昊
一、引言
1636年,清朝攻打朝鲜半岛,朝鲜朝军队接连遭遇惨败,最终仁祖国王向清太宗皇太极行三叩九拜之礼,成为清朝的藩国,此后很多朝鲜朝文人引以为奇耻大辱。在此明清交替及新的东北亚政治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宋时烈(1607—1689)撰写了两部传记作品,分别为《三学士传》和《闵龙岩垶传》。这两部传记主要选择对丙子战争结束后重要的事件及人物事迹加以概括性的描述,并着重突出了他们的生死观。
韩国古代文人主要通过轮回来表述他们的生死观。他们认为,死亡不是“生”的隔绝,而是此生的连续。[1](214)人死后即使到了阴间还可以再生,或是人的灵魂永生,思想仍存,可以与生者交感。[2](241-245)所以,韩国古代文人通常不惧怕死亡,生者能够摆脱“死后与此生隔绝”的焦虑,对有限的生命得到安慰。[3](22)《三学士传》与《闵龙岩垶传》的生死观和以往作品不同。区别在于,它们仅对此生的“义”加以强调,而没有对再生的描述。但是,对死亡看得自然,无半点恐惧,甚至以死为荣。
在朝鲜朝以丙子战争为题材的传记文学中,宋时烈的《三学士传》《闵龙岩垶传》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品的主人公分别是丙子战争中因承担斥和责任而献出生命的洪翼汉(1586—1637)、尹集(1606—1637)、吴达济(1609—1637)和丙子战争时期在江华岛率领全家13人以集体自尽方式坚守节操的闵垶(1586—1637)。面对清军的攻打,他们全都以死相抗,非常悲壮。前二者与清展开舌战后惨遭极刑,而后者为免遭清军羞辱率领全家自尽身亡。
宋时烈生活的17世纪正是朝鲜朝经历壬辰、丁卯、丙子战争的混乱时期,他积极奉行“尊明排清”思想和孝宗的北伐论。有人认为,宋时烈主张北伐论的动机有二:其一,“其大哥时熹在仁祖五年丁卯战争中遇害,骨子里产生的报复心成为了他个人的动机,而孝宗要一雪仁祖十四年丙子战争蒙受国耻的坚定意志感动了他,成为他公开的动机。”[4](235)不过,哥哥被杀的个人缘故不会是宋时烈“尊明排清”思想的全部理由。其二,长期以来与明朝形成的主从关系,坚守对明朝不事二君的义理也是重要原因。《三学士传》可以说就是宋时烈从这种思想出发进行创作的。除了宋时烈,李栽和黄景原也创作过《三学士传》,但宋时烈最早。
韩国学界对宋时烈的《三学士传》研究成果主要有金敏赫《肃宗朝政治写作——以崔鸣吉的褒贬为中心》[5],此文认为,作品将清朝和崔鸣吉设定为“三学士”的敌人,为的是联合斥和派以及仕林势力;金日换的《记忆苦难的历史——以三学士传与三学士碑为中心》[6]通过分析宋时烈的写作方式阐明了“三学士”成为忠烈的始末。李承秀的《死亡的修辞学与权力的相关性——以传系叙事为中心》[7]对《三学士传》的死亡修辞样态、修辞内容的真伪与意图进行了分析。关于《闵龙岩垶传》的研究有金贤柱的《“丙子胡乱”时期江都惨祸的文学形象研究》,[8]此文以作家意识为切入点,对作家有无战争体验以及创作动机进行了分析,然后叙述了丙子战争中江都的惨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化问题。迄今为止,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研究的六篇文章,主要对主和派与斥和派的争论以及江都的惨状进行了分析。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三学士”与闵垶的赴死情景,着重探讨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进而探讨出于政治目的写作是如何波及和影响社会的。
生死观是指人们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生与死是一切生命产生、存在和消亡的自然过程。但作为社会化了的人,则有一个如何对待生死的问题。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在中国古代,杨朱提出“贵己”“重生”,主张以保全个人的生命为人生理想,认为死亡是“吾生”价值的丧失。庄子视“悦生而恶死”为人生的一大桎梏,认为要获得人生“自由”,就必须超脱死生之变,提出“以死生为一条”,否定生与死的界限,甚至把死亡视为人生自由、幸福的最终实现。[9](61)儒家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使人们认识到肉体生命的消逝不足为惧,文化、道德意义上的生命延续更值得去追求。[10](48)儒家重视现世人生,追求生命之外更为重要的价值,使得人生更有意义。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1](40),还说:“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11](207),以及曾子说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1](98)等,均对仁义道德精神远胜于肉体生命的道理进行了高度概括。韩国古代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这些观念也体现在了士大夫的生死观之中。
下面将通过宋时烈的两部作品了解朝鲜朝官僚和在野儒生如何采用各自的方式应对与清朝的战争,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
二、《三学士传》与《闵龙岩垶传》内容概述
(一)“三学士”的政治立场与赴死情景
所谓“三学士”指的是丙子战争中的三位斥和大臣,也被称为“斥和三学士”或“丙子三学士”。朝鲜朝降清议和后,清朝将战争责任归咎到斥和论者头上,要求朝鲜朝将他们押送到清朝。洪翼汉作为斥和论代表被从平壤撤军的清军抓获并押送到沈阳,尹集和吴达济则是主动作为斥和论者站出来的。三人没有屈服于清朝的威逼利诱,一直坚持斥和大义,最后全部遇害。朝鲜朝朝廷赐予三人谥号,洪翼汉为“忠正”,吴达济为“忠烈”,尹集为“忠贞”,追封为领议政。从年龄上看,丙子年,洪翼汉为52岁,尹集为32岁,吴达济不过29岁。三人全都通过了科举,都是仁祖反正以后入仕的,官职分别是司宪府掌令、弘文馆校理、修撰等,都是谏官。
洪翼汉与皇太极争辩,理直气壮,直立不跪。因为语言不通,他用文字力主向明的义理:“四海之内皆可为兄弟,而天下无两父之子矣。”其不事二君的儒家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皇太极质问洪翼汉不认自己为皇帝的因由,他怒斥:“明朝反贼,何可成帝?”他说,身体虽然死在异国他乡,魂魄却会飞上天空,飘回故国,因而视死如归的他唯求速死。走到生命尽头时洪翼汉52岁。家人的死也很悲壮,为了免遭羞辱,当敌军挥刀砍向继母何氏时,前妻所生儿子睟元挺身相护,死于刀下;何氏跳水自尽;睟元的夫人自刎而死。小儿子睟寅前日已死,母亲和两个女儿勉强活命。[12](162)
吴达济和尹集与清太宗没有碰面。无论是在清军营地,还是沈阳,都是由龙骨大代替皇帝劝降他们。两人都只有三十岁左右,如此年轻,说他们是朝鲜朝斥和派的代表人物未免牵强,可是二人自告奋勇,以斥和派自诩,是要以死求名。尽管在要求斥和派自首的命令之下,金尚宪、郑蕴等人站了出来,但最终还是尹集和吴达济两人被押往中国。在作品中,崔鸣吉经常出场,解开二人头巾,迎接龙骨大,因为押送两个政敌受到龙骨大夸奖并获赐酒席的人都是崔鸣吉。作品中强调的是,让“三学士”走向死亡的人正是崔鸣吉。和洪翼汉一样,两人也都高举对明朝的义理,斥责清朝称帝之举。在质馆的南以雄、朴鲁、朴潢等撰写书状,劝说尹集、吴达济珍惜生命,允许他们领着妻儿到他们那里生活,但两人均婉言谢绝。理由是活着回去是一种耻辱,不如死。于是,尹集和吴达济最终在刑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二)《闵龙岩垶传》的互文性与死亡模式
丙子战争爆发后,闵垶一家入江华岛避难,江华岛一沦陷,闵垶就领着家人登上天灯寺集体自尽,死亡的壮烈场景构成了作品叙事的主线。
崇祯丙子,朝廷以义斥绝北虏。人知朝夕被兵,载万长姊为赵氏妇,谓载万曰:“脱有兵乱,弟避于何地耶?”曰:“吾贫且病,家累甚多,难以致远,舍江都何往乎?”妹曰:“江都非万全奈何?”曰:“即今国家所恃者江都也。吾家世受国恩,自在胎息中已食君禄,义当与之存亡也。且江都若破,则国事无复可望矣,生亦何为乎?”是冬,贼兵果大至,大驾入南汉。载万挈家属入江都,与子属义旅。[12](162)
从上文与姐姐对话中可知,闵垶预知由于朝廷排斥清朝,战争将会爆发,并且他已经选择江都作为战乱时的避难处。因为,早在高丽朝时期,江都就抵御住了蒙古的入侵,丁卯年后金入侵时,这里也是以国王为首的朝廷避难之地。由此可知,闵垶早已做好了打算,一旦江华岛陷落就选择自尽。而清军真正打进来之后,闵垶就按着原计划,带领家人进入江华岛,与儿子一起成为义兵。作者首先指出闵垶洞察未来的见识,并通过其决心与国家同生共死的高洁品质,展示了闵垶的眼光和人品。
仁祖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作品记录了江华岛沦陷的准确日子。清军终于杀入江都,人们看到江华留守张绅率船前来,自然心生期盼,但从偃旗息鼓的样子,闵垶看出张绅毫无战意。尽管有一只船停在岸边,但他拒绝了一起乘船逃生的提议。对闵垶而言,一人苟且偷生是万万不能的。另外,义兵虽然表现出抗战的决心,但义兵将领逃跑了,义兵们只能各寻出路,纷纷逃亡,义军因此解散。在这种情况下,他担忧国王的安危,想到朝鲜朝的疆土可能已经落入清军的手中,自己已经没有逃亡之所,江都也很难保住,于是,他决心以死殉节。之所以做出这种决定,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在不久以后江都就会落入清军手中,其后面临的将是一场惨祸。
即便闵垶事先决心赴死,但是家人的想法不可能都和他一样。他的妻子已经先行与其他亲戚一起去了摩尼山寻找活路,闵垶对此大为不满。儿女们纷纷说出活命的路子和可能的侥幸,但他全不赞同。有人说,如果有船经过不就有活路了吗?他说人心难测,担心船上有可能发生杀戮和掠夺。有人说,如果退潮不就可以光脚趟水过去吗?他说,如果清军突然杀来,想死都死不成,因而不能心存侥幸。这种推测与江华岛惨状惊人的一致。[12](162-164)
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作为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13](5)郑瀁的《江都被祸记事》展示了这里所说的所有可能性。这是由于宋时烈与郑瀁生活在同一时代,从各种角度接触到了江华岛惨案的详细状况。但是,闵垶的壮举与郑瀁施展浑身解数试图逃亡、想方设法保全性命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是闵垶带着全家自尽而死的行为,就连让三个女儿插上簪子后让其赴死一事还与尹谷给儿子加冠去见先人的行动如出一辙。尹谷是南宋人,元入侵时守卫潭州,城池甫一陷落就带着全家人焚身自尽。[14](10303)可以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对过去的引文的重新组织”。[15](121)可见,宋时烈虽然对实存人物闵垶有意识地罗列了合乎节义的行为,对闵垶一家的高义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彰显,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和自己所读作品的回忆。
三、宋时烈传记的士大夫生死观
(一)在朝官员的名分论与生死观的关联
朝鲜朝士大夫生死观与儒教思想的核心名分论有直接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虽然多少有些差异,但以儒教为国教的朝鲜朝社会是道德本位的德治主义社会。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特别是“三学士”及闵垶的生死观,必须从儒教名分意识的关联性中加以解释。例如,用儒教思想彻底武装起来的“三学士”与闵垶,比起生命更重视道德的名分。那么为什么他们为了道德名分而舍命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就要分析中国儒教乃至朝鲜朝儒教的名分论的变化和发展。
在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传统名分论发展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6](237)的孟子革命论,到了宋朝又以孔子传统名分论进行了转变并得到强化。朝鲜朝的名分论经过高丽朝末期的郑梦周——为名分献出生命的孔子式传统名分论,到追求易姓革命的郑道传、李芳远家族信奉的孟子式革命论,再到世宗以后朝鲜朝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守成期,形成了比“命”更重视“义”的文化。代表性的事例就是杜门洞七十二位士大夫与“死六臣”和“生六臣”为了名分选择死亡。到了宣祖、仁祖时代,这种孔子式的名分论得到了强化,其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三学士”及闵垶之死。“三学士”与闵垶面临的不是内部的王权交替,而是与外部的女真人战斗中的问题,因此更加强调了名分,他们坚持的是事大主义的名分论。
丙子战争时期,朝鲜朝国王向清朝太宗投降的事件引起了重要的争论。君王与臣子在南汉山城抗战时,金尚宪、洪翼汉等人拒绝投降,要求君臣守城、同死。与此相比,崔鸣吉等人却提出了投降,为的是减少百姓的牺牲,保存国家命脉的主和论。当时几经反复,终于投降,主和论被采纳。这时,主张斥和论的“斥和三学士”被带到清朝的沈阳接受审讯,他们始终打着“大义”的旗号,坚守节义。如果说主和派站在实利论的立场,那么,斥和派则是站在义理论的立场。
“斥和义理”基于严格区分中华与野蛮的大义名分论。以中华文化自居的朝鲜朝社会将清朝界定为野蛮的,提出了尊华攘夷论、尊王贱霸论等春秋大义与崇明排清论。丙子战争以后的排清意识是继承春秋大义的大义名分论。孝宗和宋时烈等当时的道学家们甚至还提出了北伐论。道学家的排清论中出现的大义名分论,虽然被朝鲜朝后期的洪大容、朴趾源等北学派实学者彻底批判,但是被确立为这个时代的理念。
《三学士传》中有两股与“三学士”接触的敌对势力:一是,打乱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制的清朝;二是,打算承认清朝的主和派势力。作品通过清太宗与洪翼汉的对立着重描写了僭位皇帝与明朝忠臣之间的对峙,通过崔鸣吉与吴达济、尹集的对立着重描写了主和派和斥和派的对立。洪翼汉与崔鸣吉,吴达济、尹集与龙骨大的交锋不是没有,但宋时烈还是将重点放在了前者上。
另一位撰写《三学士传》的李栽认为,“三学士”之死就是孔子所言的“杀身成仁”,以及孟子所说的“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17](333)他还认为,洪翼汉的家人全部遇难守住气节和尹集一家世代以死效忠非常杰出。丙子战争本有取胜之途,但因为数名宵小苟且偷生的卖国行径而未能如愿。他没有囿于弱小只能防守的逻辑,指出朝鲜朝并非没有反击的可能。他感到非常遗憾,南汉山城口粮充足,可以支撑数月,这时如果国王和大臣痛下决心,表现出决一死战的意志,让京畿兵跟随良将气势如虹地杀入沈阳,形同空城的地方是撑不了多久的。在此基础上,朝鲜朝可以掐断清军的给养,到了春天,土地泥泞,敌人的骑兵一定支持不了多久。
丁卯战争时期,后金军一越过国境,洪翼汉就试图率领县兵对抗,但这已经是朝廷与后金媾和之后了。对此,洪翼汉力主治姜弘立之罪,丙子年则上疏要求处决龙骨大和马夫大。此疏是针对皇太极称帝事件上呈的,疏称生来只知有大明天子,并举丁卯战争为例,强调应将姜弘立枭首示众,彰显朝鲜朝之大义。洪翼汉主张与其听闻僭帝之说,不如像鲁仲连那样死去以免污了耳朵。他还指出,朝鲜朝是礼仪之邦,是小中华,并强调对明的一片丹心。洪翼汉认为,遭受清朝的羞辱是朝廷重臣招致的结果,进而责备朝鲜朝将帅闲坐山梁,国王深居宫中,面对危难束手无策。[18](145)崔鸣吉主管与清朝的和议,他不喜欢别人提出反对意见,在上奏相关事宜时请求屏退承旨和史官。对此,尹集怒指崔鸣吉一伙是蒙蔽天聪,阻断人望之徒,他们主张的和议是亡国之举,断绝社稷之行。他称明为父母之国,清为父母之仇,与清议和卑劣,再三强调明朝的“再造之恩”。同时,他还声称崔鸣吉一伙谋划得再隐秘,又怎能欺瞒得了上苍。朝廷和百姓全都恨不能生啖其肉,唯有国王蒙在鼓里。他还批评李敏求在国王雷霆震怒之下,做出停止使用明朝年号“天启”等举动,表现出含含糊糊的态度,并直言国王没有看穿甚至听从崔鸣吉卖国谋划。[18](145)尹集强调公论之严厉,并指斥崔鸣吉的和议是奸邪、欺瞒之论,可憎之言。他对其间朝廷的公论做了辨别,批评崔鸣吉倚仗国王之意,不顾国家的情势,对上惑乱天聪,对下威胁、压制公议,[19]唯恐无法实现议和,恣意放纵,犯了不可不纠之罪。
可见,朝鲜朝士大夫们普遍视名分论为唯一真理,对时事军政却未正视。他们认为“三学士”之死完全是主和派崔鸣吉的罪过,是因为朝廷没有积极与清对抗。“斥和三学士”对主和派崔鸣吉的抨击,是“三学士”以儒家名分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抗实利论的浴血对决。包括“三学士”在内的名分论者将“尊明排清”奉为首要义理,甚至不惜为此献出生命。他们高举对明朝的义理论,全盘否定、反对与清朝的任何交往。他们将丁卯战争的屈辱到其后朝鲜朝不能自强全部归咎于主和派,对默认主和的国王也提出了批评。斥和论是“三学士”这样的三司谏官提出的,崔鸣吉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崔鸣吉身为实利论的代表对三司言论的不负责任提出了强烈反驳,指责他们不顾国事危机,只是一味高举朱子学的名分论和义理论,道破当时受斥和论影响的官僚、儒生的弊病。如果说,包括“三学士”在内的斥和论将朱子学的名分论和义理论看得高于国家存亡本身的话,实利论则是弱小国家保护民生、将国家存亡放在首位的苟全之策。
主和论和斥和论,经过丁卯战争和丙子战争两场交锋,直接造成朝鲜朝廷内部自乱阵脚,无法齐心协力共同对抗清朝,也成为对清战争的重要部分——精神(思想)战争。《三学士传》就是站在斥和立场上记叙与主和派的对峙情况,是朝鲜朝对清战争中思想战争的历史再现。
(二)隐士与女性的生死观
关于朝鲜朝隐士的生死观可以从丽末鲜初的杜门洞七十二士人说起。李成桂从恭阳王手中继承王位,将都邑迁至汉阳。高丽朝的臣子权门世家和高丽朝王族中,没有向朝鲜朝太祖投降的人留在开城。反对新朝廷的高丽朝遗臣七十二人隐居在杜门洞,一直忠于高丽朝,不仕朝鲜朝。朝鲜王朝就包围杜门洞,七十二名高丽朝忠臣因拒绝投降被活活烧死。他们用非暴力默默地反抗,不事二君,为了忠义慷慨赴死。
式中:Fx方向最大误差为4.55%,Fy方向最大误差为11.49%,Fz方向最大误差为2.65%,Mx方向最大误差为0.45%,My方向最大误差为0.36%,Mz方向最大误差为1.54%。
丙子战争时江华岛一沦陷,闵垶就和家人一起登上摩尼山天灯寺自尽。闵垶的十世祖闵愉知道高丽朝会灭亡便退隐,在朝鲜朝时期至死没有做官。闵垶膝下有四儿四女,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家教。从这里可以看出,闵垶的祖上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坚决不事二君。而闵垶同样不入仕途,尊奉儒家思想,放弃了科举,埋头文史,坚守名誉和气节。
不过,他面对江华岛即将沦陷,选择的不是避难保全性命。女儿提议,敌人追来,一起跳入水中自尽,但闵垶认为在一个地方悄然死去更好。临死前,作为嘉礼,他给未婚的三个女儿插上簪子,还托付大姐保护孩子们,记下祖上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将孩子们送走。他认为年幼的女儿既不会遭到敌人的羞辱,又不用尽士大夫家族的责任。虽然说大姐老迈不堪没有受辱之忧,但身处乱世,一个老弱、无力的女人尚难苟活,何况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指望他们平平安安,并不可能。
尽管如前文所述,闵垶认为别人提出的各种活路全都不可行,却唯独对孩子们的事情非常执着。这是父亲对子女的骨肉之情,是父爱的体现。闵垶说,妾禹氏不是士族,可以不死。闵垶之所以将孩子托付给大姐,也是因为她是庶女算不上士族,即使全家人全都自尽,大姐却可以除外。这又是重男轻女、嫡庶有别的士大夫意识的体现。
大女儿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婢仆时痛哭流涕的场景,多少缓解了作品过于集中于坚守大义而显单调、牵强的氛围,呈现出少许感人的场面。这种撕心裂肺的感人场面,让人感受到了在恐怖的暴力面前,也不会改变的人类骨肉之情。仆人领着孩子们上路逃难,路上却遭到劫掠,崔氏的女儿丧生。闵垶的儿子视目睹父亲自杀为大不孝,自己先行悬梁自尽。余下的儿子、儿媳、女儿和妾共13人全部自杀。在战争这种浩劫中,不论男女老少,所有的生命都像风中残烛,每个人都难逃死亡的宿命。
宋时烈并没有通过闵垶之死谈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他把关注的焦点全都放在舍生取义的姿态上,在叙述上显然是有意为之。作为夫君,作为父亲,闵垶未受其累,自始至终都高举大义;身为隐士,闵垶与在朝官员的对抗方式有所不同,他不是积极的斗争,而是无声的抗议,重名节高于一切。
关于闵垶家女性的自杀事件,《闵龙岩垶传》也有详细的交代。朝鲜朝女性的生死观可以从百济的落花岩事件说起。百济被罗唐联军攻陷后,为免遭侮辱,三千名宫女从白马岗岩石上集体跳崖而亡。朝鲜朝壬辰战役时期,在晋州城被倭军攻陷时,义妓论介引诱敌将,抱着倭将一起跳进晋州南江而牺牲。这种生死观在《闵龙岩垶传》中也体现了出来。
尤其是对妾之死和闵垶对子女所为,作者宋时烈做出了如下评价:
其妾禹姓,贱者也。激于主君之一言,首先取死,以明其志,尤非人之所能及也。当时士夫妇女,甘受污辱,至有贵家大族丑说流播,至使人不欲言者。其平日视禹,不翅壤虫,而顾今所就,反不翅人兽之悬。秉彝之天,其可以贵贱论哉?载万使其处女三人,皆笄而死。昔宋之尹衡州谷城陷,冠其子曰:欲令冠带而见先人于地下,临死而无恇怯错乱,从容于礼法者,其事古今一辙也。[12](164)
闵垶的妾虽然身份低贱,但面对死亡却泰然自若。作者通过禹氏临死之前煮饭吃等行动试图表达闵垶身份低贱的妾尚能如此,更何况其他人呢?
宋时烈提到士大夫家的妇女们甘心受辱,豪门大户也丑闻频传,认为这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这些人其实都是受害者,由于得不到无能的朝廷保护而受伤害,但宋时烈却认为她们连畜生都不如,对此极为愤慨,并给予了抨击。该部分可以说是作者标举的士大夫精神的集中体现。
四、结语
宋时烈是朝鲜朝老论的首领,北伐论的领军人物。李景奭(1595—1671)于1668年(显宗九年)获国王下赐的几杖,宋时烈送去了祝词,表面上是道贺,实际文中加入了“寿而强”字样,暗讽他与宋朝的孙觌没什么两样,后者随钦宗被抓到金国后,阿谀逢迎,左右逢源。宋时烈指斥李景奭也不过是阿谀清朝的人。这针对的是李景奭所著碑文《三田渡碑》即《大清皇帝功德碑》。1669年,宋时烈披露了这一事实,开始了激烈的论争。在《三学士传》中,身为政丞的许积(1610—1680)曾经评价尹集和吴达济“轻浮,喜欢出风头”,由此看来,在立传之前“三学士”并不是口碑爆棚的人物。实际上,“三学士”死亡的准确日期是后来才知道的。1790年,来到北京的朴齐家在琉璃厂发现了《皇清开国方略》,抄录了其中有关“三学士”的内容,朝鲜朝文人这才知道具体情况。由于死亡的时间没有确定,“三学士”的行踪也不是很清楚。《闵龙岩垶传》一以贯之的就是闵垶一家自杀的行迹,对战乱的惨状几乎没有涉及。这种意图明显的叙述带有浓重的理念色彩。尽管传记文学这个体裁特殊性使然,但还是消解了宋时烈立传的目的。《闵龙岩垶传》的创作时间虽然并没有标明,但仅看《三学士传》的创作时期是在两年后的辛亥年(1671年,显宗十二年),也可以看出两部作品的政治目的。
作品《三学士传》《闵龙岩垶传》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当时恪守大义的人物,不仅在那个时代,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也被尊崇为英雄,受到万人景仰。
如果说,金应河是在战场上与后金铁骑军英勇奋战而牺牲的英雄,那么,《三学士传》和《闵龙岩垶传》中的主人公则分别是不屈服于清朝势力舌战敌人而赴死的义士,和为了免遭清军入侵后的羞辱而率领一家13口人自杀,坚守大义的人物,鲜明地体现出了朝鲜朝士大夫阶层的生死观。“三学士”和闵垶登上英雄的神坛,正是宋时烈所著这两篇作品之功。虽然作品表明传记的写作动机是由于遗属的委托,但不能排除这是宋时烈的一种政治手段。因为《三学士传》中主人公除了“三学士”,还让金尚宪、郑蕴等斥和派的代表登场,并描写了舍生取义的金尚容,还有尹宣举和洪翼汉家人的悲壮死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将主和派崔鸣吉描写成拙劣、庸俗的清廷马前卒。同时,《闵龙岩垶传》高度集中地叙述了闵垶一家集体自杀的情景,称此为大义之举,并高度赞美了他们的行为。综上所述,宋时烈的意图在于通过大力宣传“三学士”及闵垶一家的精神,鼓动在朝官员及在野儒生的抗清意识,支持孝宗的北伐论,排斥敌对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管怎样,作品人物的生死观受到当时绝大多数朝鲜朝士大夫的肯定,之后的很长时间仍受到称颂,是体现朝鲜朝士大夫生死观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