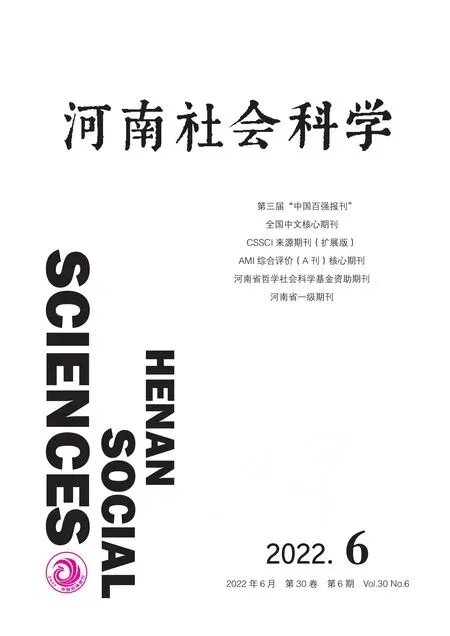论妨害安全驾驶罪
张智辉,杨 崴
(1.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华东政法大学 青年国情研究中心,上海 201620)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一个新罪名。深刻理解该罪的立法精神,准确把握该罪的构成要件,合理解决该罪名与其他相关罪名竞合时的法律适用,对于正确适用《刑法》、维护公共交通安全,更好地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就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立法价值、构成要件、犯罪竞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一、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立法价值
近年,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运营的事件频发,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公共交通安全的担忧,也引起了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惩治妨害安全驾驶的意见》),试图在现有刑法规范的框架内,对已经出现的各种妨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进行规制。为了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 年12 月26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妨害安全驾驶罪。该罪的设立,对于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维护公共交通安全运营
公共交通工具作为当代居民出行最常选择的、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过去几年里,因严重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而酿成惨剧的案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报告》,2016 年至2018年我国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的刑事案件量稳中有升:案件被告人中近七成为乘客,约二成为公交车司机;超五成案件发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而纠纷起因多为车费、上下车地点等小事;超半数案件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近三成乘客出现抢夺车辆操纵装置的情况。在发生实际干扰行为的案件中,超五成出现了公共交通工具撞击其他车辆、行人、路旁物体或剧烈摇晃等危险情况,仅20%的案件没有造成重大不良后果[1]。尽管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惩治妨害安全驾驶的意见》意图改善此类状况,但由于其中涉及的罪名都不是专门针对司乘冲突的,惩罚的力度和效果以及执法的尺度统一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同年相关类型的犯罪仍呈现出上涨趋势,仅2019 年一年就出现了67 例。其中,震惊全国的“重庆公交车坠江案”①,再次诠释了司乘冲突中的互殴行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
这些情况表明,妨害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针对该种行为设置专门罪名,准确惩治该类犯罪,对于维护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十分必要的。该罪名的设立,不仅为准确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还为公共交通工具上司机与乘客理智地对待可能发生的冲突敲响了警钟,有利于遏制这类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安全对于保障社会交往中人民群众正常出行的外部环境与秩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面对近年多发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本罪的立法目的正在于规制此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因司乘冲突引起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刑法既是裁判规范,也是行为规范[3]。以刑法规制社会越轨行为,能够对人们社会交往中的行为约束发挥相较于其他种类处罚更强的警示作用。“国家希望通过刑法干预前置化实现对公众行为的塑造,从而建构规范的认同。”[4]增设新罪名能够强化对于越轨行为的谴责,并起到树立道德模范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5]。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我国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对于具有犯罪前科记录的人员都具有一定限制,如对其参军入党、考取公务员、晋升职务等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影响到其子女。因此,某种行为一旦被刑法规定为犯罪,人们就会尽可能地避免实施这种行为,亦即发挥刑罚一般预防的功能。把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运行、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司乘冲突行为纳入刑法,无疑会警示人们理智对待司乘冲突,遏制因为不能冷静对待矛盾冲突而做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举动。这对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该罪出台以前,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运行的行为通常被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交通肇事罪”来定罪处罚,或者作为一般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来对待。但实际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的重罪,只有在行为的危害性与放火、决水、爆炸等方法相当时才能构成,而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都难以达到该罪的标准,由此便可能出现重罪与非罪之间的空隙。若行为的危害结果并未达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要求的标准就定罪,则可能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被告人罚过其罪,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若严格遵守该罪的构成要件,便没有有效手段惩罚此类行为,难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而交通肇事罪则要求已经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如果没有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就不能按照该罪来定罪处罚。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设立,对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网,促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该罪的设立能够为同类行为的定罪处罚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填补构成重罪与无罪之间的空隙。针对社会危害性不足以构成某种重罪但又确实应予以规制的行为增设新罪名,能够起到收缩刑罚的作用,避免使犯罪人落入与之行为不相符的刑罚中。正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消除司法实践中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当解释适用,是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原因之一[6]。
二、妨害安全驾驶罪共同构成要件的认定问题
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是认定犯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它能够将法条切实融入现实,这对于一个新罪名而言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准确认定妨害安全驾驶罪,必须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刑法在设立该罪时为其规定的构成要件。按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的规定,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地点要件:“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
妨害安全驾驶罪必须是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行为。公共交通工具是指面对不特定多数人营运的从事旅客运输作业的自带动力装置的交通工具。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着不特定多数人的出行安全,关乎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乘客多,行进速度快,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一旦发生司乘冲突,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就很大,因此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安全需要特别加以保护。发生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不仅会使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处于危险状态,从而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而且可能对正常的公共交通运输秩序造成妨害,从而威胁到公共交通秩序的安宁。
1.如何界定“公共交通工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5 号)第二条,将公共交通工具界定为“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6〕2 号)(以下简称《关于抢劫罪的指导意见》)中,将“公共交通工具”重新界定,增加了地铁、轻轨,并规定对于虽不具有商业营运执照,但实际从事旅客运输的大、中型交通工具,以及接送职工的单位班车、接送师生的校车等大、中型交通工具均可以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在实践中,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多发生在从事旅客运输的机动车上。机动车是指由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不特定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关于抢劫罪的指导意见》所列举的机动车,无疑应当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来认定。值得研究的是,其他类型的机动车能否成为该罪的犯罪场所。
一是小型出租车。随着当下“网约车”“顺风车”等行业的发展,一辆小型出租汽车由多名不相识乘客同乘的现象屡见不鲜。笔者认为,有“拼车”性质的出租汽车、“顺风车”等,因其具有与传统公共交通工具相似的行驶特征,也应该被列入此类范畴。理由是,出于对效率的考量,“顺风车”“拼车”等本身在终点的选择上应属“顺路”,若此时某乘客临时修改为不在原计划行驶路线内的终点下车,则实际上已经使这段旅行失去了“拼车”的意义,故可以类比公交车在固定站点停靠的情况。此时,乘客所干扰的对象虽为驾驶人员,但对于与其仅有“路遇”关系而非“同伴”关系的其他乘客而言,却造成了不可预知的安全威胁。因此,在这类出租车上发生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同样是针对不特定人的危害行为。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等行为,与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的同样行为一样,都会对车上其他无关乘客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尽管这种观点突破了《关于抢劫罪的指导意见》所划定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但并没有违背该罪的立法原意。妨害安全驾驶罪以社会治理为目的,法定最高刑不超过一年,属于典型的轻罪;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法定最低刑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属于重罪。故抢劫罪要从严限定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而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则应从宽解释,以满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二是大型三轮摩托车、拖拉机。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型三轮摩托车、拖拉机载客的现象大量存在,它们实际上承担着公共交通工具的功能。发生在这些车辆上的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同样会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因此有必要将特定情况下的承载公共运输功能的大型三轮摩托车、拖拉机等车辆纳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内。
三是私人小轿车。私人小轿车通常情况为个人或家庭所使用,不具有公共运输的功能,因而也不应被列入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着私人小轿车非个人所用的场合。如熟识朋友共同租赁使用的私人汽车以及同行人员共同乘坐的小型出租汽车。笔者认为,在此场合下并不存在“不特定多数人”,车内人员应当视为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群体。因此这类小轿车不能视为该罪所称的公共交通工具。若在该交通工具上实施的行为对道路安全造成威胁,符合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则应构成有关犯罪。
2.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应当以“合法运营”为限
妨害安全驾驶罪所针对的是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的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合法运营的交通工具。如从事旅客运输的城市大巴、公交车、长途公共汽车等,通常都是经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审核批准、车辆和驾驶人员也都是经过审查或检验合格的车辆和人员,具有合法取得的营业执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取得营业执照但实际从事旅客运输的机动车辆。在这类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司乘冲突的概率往往更高。这些车辆及其驾驶人员的合法性问题能否阻却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成立,不无争议。
笔者认为,交通工具及其驾驶人员的合法与否不应成为认定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障碍。只要是客观上实际从事着不特定多数人的交通运输活动,其运输工具都应当视为公共交通工具,该公共交通工具是否合法运营不应妨碍该罪的认定。这是因为,刑法作为公法,其保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即便他人所为不具有合法性,但若对其进行加害可能危及公共的安全和秩序时,同样可能构成犯罪。“黑车”与其他客运汽车同样具有公共服务性和运输乘客的特定功能,具有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在“黑车”营运过程中,上述刑法法益依然存在,不能因交通工具营运合法与否而改变。
3.如何认定“行驶中”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是干扰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行为,因此必须是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危害行为。所谓“行驶中”,通常是指公共交通工具按照既定的路线正在道路上行驶。问题在于,当公共交通工具已经载客但还没有行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认定为“行驶中”。如公共汽车已经驶入站台并停靠在路边等待乘客上下车,或者公共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遇到故障或事故而在道路上暂停等。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车辆没有行驶,也应当认定为“行驶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交通工具上已经或即将有乘客乘坐或上下,驾驶人员仍然对车辆实施着控制行为,驾驶人员仍然有义务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和车上乘客的安全。如果发生司乘冲突,虽然不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但仍然会妨害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行,妨害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公共秩序。如前所述,妨害安全驾驶罪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轻罪,对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作广义的解释,同样地,对“行驶中”也应当作广义的解释。此外,按照《公共航空旅客运输飞行中安全保卫规则》(CCAR-332)(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193号)第四条的规定,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到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都算作飞行中。该规定虽然只适用于公共航空运输中的航空器,但其原理应该能够适用于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即公共交通工具从承载乘客车门关闭直到乘客下车完毕这一期间,无论是快速行驶还是慢速行驶,抑或暂停,都应当视为行驶中,这更有利于保障公共交通的运营安全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行为要件:干扰行驶型与擅离职守型
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或者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据此,笔者把该罪的危害行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干扰行驶型,二是擅离职守型。
1.干扰行驶型妨害安全驾驶罪
干扰行驶型是指“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使用暴力,是指使用自身的体力推搡、抓夺、击打、捆绑、踢踹他人的行为,或者使用武器,强迫他人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首先,使用暴力必须是针对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实施的暴力。乘客对乘客使用暴力,不能构成该罪。其次,使用暴力的程度必须达到影响驾驶人员正常控制交通工具的程度。如果仅仅是通过言语刺激、大声吵闹等方式干扰驾驶人员正常驾驶交通工具,就不属于该罪所要求的“使用暴力”的行为。在实践中,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的行为,通常表现为强力拉扯、拳打脚踢等对驾驶人员躯体造成影响,可能直接使驾驶人员暂时失去安全驾驶能力的行为。例如,薛某某酒后至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某公交站搭乘11路公交车,因上车投币后驾驶员刘某某无法找零,薛某某对刘某某进行辱骂并殴打刘某某头部,致使刘某某短暂失去对公交车的控制,造成该车与前方另一公交车追尾,两车不同程度受损。这种暴力虽然轻微,但对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而言,很容易分散其注意力,危及公共交通安全。
抢控驾驶操作装置,是指抢夺或是控制机动车的方向盘、变速杆等控制装置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妨害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并且由于这种行为是直接针对交通工具进行的,因而不存在程度上的划分。例如,张某某在其乘坐的602路公交车上,当其坐过站并要求停车未果后,便与驾驶员刘某某发生争吵,张某某上前抓推刘某某手中的方向盘,迫使刘某某不得不迅速减速并将车辆停靠在路边。又如,袁某发在其乘坐的15 路公交车上,因公交车没有在其准备下车的站台停车,便与该车驾驶员袁某宝发生争执,双方在争执过程中,袁某发抢夺方向盘,袁某宝没有及时停车,导致在该车右前方行走的被害人吴某英被撞伤,造成吴某英多处受伤。这种抓推、抢夺方向盘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抢控驾驶装置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对于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而言,无疑具有导致交通事故的风险,从而危及公共交通安全。
值得研究的是“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与“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要实施了“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干扰了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还是“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只有在实际干扰了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笔者认为,刑法在规定“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时并没有对其强度加以限制,而作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必须是妨害了安全驾驶的行为,刑法中关于“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规定,正是对“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限制性规定。因此,“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不论表现形式怎样,都应当是在能够足以直接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才能符合该罪对危害行为的要求。
2.擅离职守型妨害安全驾驶罪
擅离职守型是指“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擅离职守”,是指擅自离开其驾驶岗位。擅离职守不应简单解释为空间上的“离开”。因为驾驶人员脱离驾驶岗位,既可以表现为在物理空间上挪动位置,也可以表现为双手脱离方向盘等失去对公共交通工具控制的其他行为。驾驶人员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放弃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本身就违背了驾驶人员的安全驾驶义务,这种行为足以危及公共安全。在前述“重庆公交车坠江案”中,驾驶人员冉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的行为。尽管冉某始终没有离开驾驶座,但在其遭遇刘某的殴打时,其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的行为,使方向盘失去控制,造成了公交车上15人丧失生命的严重后果。
驾驶人员“离开职守”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为了车辆救援、排查故障、帮助他人、处理紧急问题等。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驾驶人员只有在为了“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而擅离职守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实践中,驾驶人员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殴打他人,往往是基于司乘冲突。有时可能是因为乘客的不当行为引起驾驶人员的不满甚至妨碍了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行驶,有时可能是因为乘客对驾驶人员没有满足其要求而不满,从而引起双方的争执,进而上升到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驾驶人员是否有理,都不应当殴打他人,也不应当与他人互殴。因为殴打他人或者与他人互殴,都会失去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从而危及公共安全。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驾驶人员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过程中能否进行正当防卫?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过程中,乘客突然针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驾驶人员可否进行还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法发〔2020〕31号)中规定:“对于正在进行的拉拽方向盘、殴打司机等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实行防卫。”这意味着,驾驶人员可以实行正当防卫。但是,驾驶人员的防卫是否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笔者认为,驾驶人员只有在确保公共交通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防卫,或者是为了保证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行驶而进行防卫。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即使受到攻击,也不能为了防卫就放弃对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因为驾驶人员是特殊领域的控制者,无论是对车辆行驶方向的控制,还是对制动装置的控制,都直接关系到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为了防止乘客发生危险,驾驶人员即使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也应当遵循安全驾驶义务。因为驾驶人员对于交通工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擅离职守,更不允许为了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而擅离职守,放弃对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
(三)结果要件:“危及公共安全”
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规定,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只有在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这就意味着该罪属于危险犯的范畴,不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入罪条件,但必须满足“危及公共安全”的要求。
“危及公共安全”不同于“危害公共安全”。《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一词的表述出现在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五个条文中。“危及公共安全”一词的表述则出现在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之二这几个条文中。从中可以看出,“危害公共安全”所指称的是行为具有造成严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或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结果的情况,其行为对于公共安全的损害程度更高。而“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则是威胁到公共安全而尚未对公众安全造成实际的危害,也没有使公共安全处于现实的危险之中。显然,危及公共安全的危害性要远远小于危害公共安全。因此《刑法》中规定“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都是轻罪,都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的损害或构成严重的威胁。如果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在客观上实际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就超出了该罪所能承载的范围,就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更重的罪处理。
(四)主体要件:“驾驶人员”与“非驾驶人员”
与行为要件相联系,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主体只能是驾驶人员或者非驾驶人员,即干扰行驶型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只能由非驾驶人员构成,而擅离职守型的妨害安全驾驶罪只能由驾驶人员构成。作为该罪的主体,无论是驾驶人员还是非驾驶人员,都必须是年满16 周岁、精神正常、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能构成该罪,单位也不能构成该罪。
值得研究的是驾驶人员的范围问题。一般来说,驾驶人员应当是具有驾驶能力和驾驶资格并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所谓驾驶能力是指具有所驾驶的公共交通工具所要求的驾驶技术,并且身体健康、精神正常,能够保证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能力。驾驶能力的判断依据是是否依法取得所驾驶车辆的驾驶执照。在我国,驾驶大型载客汽车应取得A驾驶证、驾驶城市公共汽车应取得A3驾驶证,驾驶中型载客汽车应取得B1 驾驶证,而驾驶小轿车的应取得C1或C2驾驶证。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就不能认为具有驾驶能力。所谓驾驶资格是指依法取得对所驾驶交通工具控制权的资格。即使是具有驾驶能力,但尚未合法取得对特定交通工具的控制权,就没有资格驾驶该交通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驾驶能力或驾驶资格的人员,实际驾驶着公共交通工具,并且实施了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的行为,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按照该罪定罪处罚。由于这种行为完全符合该罪的其他构成要件,而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合法的驾驶人员实施同样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不具有合法性的驾驶人员实施同样的行为更应当构成犯罪。
(五)主观要件:“故意”
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如“使用暴力”“抢控驾驶操纵装置”以及“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等,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只可能基于当事人的故意而实施,不存在过失的可能。在具体的表现上,既有可能表现为使不特定多数人陷入危险的直接故意,也有可能表现为放任此种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
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应当综合考察其行为时的情势、手段和动机。乘客若因车内人员拥挤、车辆颠簸等原因而不小心栽倒在驾驶人员身上,或以手撑扶、倚靠、撞击驾驶操作装置,一般不应认定为故意使用暴力或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尽管相关行为确实对司机或驾驶操作装置造成了物理上的影响,但属于因情势所迫而作出的下意识动作,不能认定为故意所为。
三、妨害安全驾驶罪与相关犯罪竞合时的法律适用
在实践中,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通常都会伴随着殴打、谩骂侮辱、起哄闹事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条第三款专门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何判断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时哪个罪较重,就成了法律适用的难点。
(一)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通常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但是现在通常都会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论处。例如陈某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为,被告人陈明亮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以拳头击打驾驶人员头部,司机紧急制动导致后车追尾事故,其行为干扰公共交通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撤销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决,以妨害安全驾驶罪论处②。又如黄某妨害安全驾驶案,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为,被告人黄某用右脚踢打正在驾驶客车的司机脸部,导致车辆失控与另一轿车发生剐蹭,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决,以妨害安全驾驶罪论处③。上述判决表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同于妨害安全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这两种罪名严格地加以区分。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区别,除法定刑不同之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特征。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是指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以外的其他方法,因此这些方法在逻辑上就要求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方法具有同质性。就公共交通工具而言,“其他危险方法”也应该是随时都有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等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而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为则是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或者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的行为。这种行为,一般而言,对公共交通安全可能带来的威胁,比“其他危险方法”可能带来的威胁要小得多。如果行为人使用足以使驾驶人员丧失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能力的暴力,就可能超出了“妨害”安全驾驶的程度,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二是危害后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也不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但必须是“危害公共安全”;而妨害安全驾驶罪则是要求“危及公共安全”。如前所述,“危害公共安全”意味着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的结果或者使公共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危及公共安全”只是威胁到公共安全,尚未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尚未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或者驾驶人员擅离职守,实施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的行为,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或者没有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就应当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来定罪处罚,而不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然,在实践中,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可能出现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竞合的情况。如果行为人使用足以使驾驶人员丧失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能力的暴力,就可能超出了“妨害”安全驾驶的程度,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或者在危险路段从驾驶人员手中抢夺驾驶操纵装置等行为,既是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也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对此,就应当以重罪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因司乘冲突而动怒以致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主观上确实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但其所实施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则应当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
(二)与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作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类犯罪,其行为针对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健康权[7]。从行为表现上来看,该罪是针对受害者身体实施的伤害行为,尽管其客观上可以表现为采取多种工具和手段,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伤害他人的身体。而在妨害安全驾驶罪中,无论是非驾驶人员对驾驶人员“使用暴力”,还是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其主观上都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都可能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结果,从而构成故意伤害罪,出现罪名竞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以妨害安全驾驶罪定罪处罚还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就可能引起争议。
笔者认为,在司乘冲突中造成他人身体伤害时,一般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因为与妨害安全驾驶罪相比,故意伤害罪是重罪。但是,如果在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司乘冲突时,一方殴打对方或者双方互殴,实际给对方身体造成的伤害比较轻微,虽然也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竞合,但因故意伤害的情节较轻,而妨害安全驾驶罪更能反映该行为的起因和特点,就应当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来定罪处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具有明显的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但毕竟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结果而从轻处罚,其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与妨害安全驾驶罪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定罪处罚更能体现该行为的起因和性质,也不会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结果。
(三)与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8]。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指国家有关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部门的规定,常见的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铁路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港口法、民用航空安全法等与公共交通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对公共交通运输安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与保障公共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和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旦违反这些法规,就很容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擅离职守,殴打他人或者与他人互殴,其本身就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旦造成重大伤亡,就既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同时也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就应当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因为相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罪而言,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更重。
问题在于,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时,是否能够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从现有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规定的内容看,对非驾驶人员的禁止性规定中尚不包括“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由于乘客或者第三人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因而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的,难以按照交通肇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乘客或者第三人的行为情节严重,足以使驾驶人员丧失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控制,以致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对行为人就应当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四)与侮辱罪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是侮辱罪。侮辱罪作为侵害公民人格权、名誉权的犯罪,属于对特定公民的侵害行为[9]。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发生司乘冲突时,一方往往会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如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辱骂、嘲弄、丑化对方,向对方身上泼洒秽物等,如果这种行为情节严重,就可能在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同时,也构成侮辱罪,出现想象的竞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按照侮辱罪来定罪处罚,因为侮辱罪的法定最高刑比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重。但是如果侮辱他人的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可能判处的刑罚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则应当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定罪处罚。因为妨害安全驾驶罪更能反映该行为的起因和特征,并且不违背“以处罚较重的罪定罪处罚”的原则。
(五)与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故意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10]。寻衅滋事罪通常表现为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小题大做,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或者起哄闹事,破坏公共场所秩序,以满足自己取乐、发泄、寻求刺激或者显示威风等动机[11]。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的人故意寻衅滋事、显示威风,有的人借司乘冲突起哄闹事,故意扩大事态,以致威胁到公共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行和公共场所的秩序。而这些行为都可能既符合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出现想象竞合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按照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因为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远重于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定刑。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寻衅滋事行为的情节不是很严重,若按照寻衅滋事罪,可能判处的刑罚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对这种情况,则应当按照妨害安全驾驶罪来定罪处罚。因为妨害安全驾驶罪更能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特征,也更有利于对公共交通工具运营安全和公共交通秩序的保护。
如果在正在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寻衅滋事的行为给他人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就可能同时也构成故意伤害罪,形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与妨害安全驾驶罪三罪竞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他人身体造成的是轻伤,则仍然应当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因为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五年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但是如果寻衅滋事的行为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的后果,则应按照故意伤害罪来定罪处罚,因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刑重于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
注释:
①2018 年10 月28 日,公交公司驾驶员冉某驾驶22路公交车在起始站万达广场站发车,沿22路公交车路线正常行驶。乘客刘某在龙都广场四季花城站上车,其目的地为壹号家居馆站。由于道路维修改道,22 路公交车不再行经壹号家居馆站。当车行至南滨公园站时,驾驶员冉某提醒到壹号家居馆的乘客在此站下车,刘某未下车。当车继续行驶途中,刘某发现车辆已过自己的目的地站,要求下车,但该处无公交车站,驾驶员冉某未停车。刘某从座位起身走到正在驾驶的冉某右后侧,靠在冉某旁边的扶手立柱上指责冉某,冉某多次转头与刘某解释、争吵,双方争执逐步升级,并相互有攻击性语言。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距南桥头348 米处时,刘某右手持手机击向冉某头部右侧,冉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侧身挥拳击中刘某颈部。刘某再次用手机击打冉某肩部,冉某用右手抵挡并抓住刘某右上臂。随后,冉某收回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急打方向(车辆时速为51 公里),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实线,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车辆时速为58公里)相撞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造成车内15人全部遇难,小型轿车车辆受损、小车驾驶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②陈某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1刑终66号刑事判决书。
③黄某妨害安全驾驶案,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5刑终29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