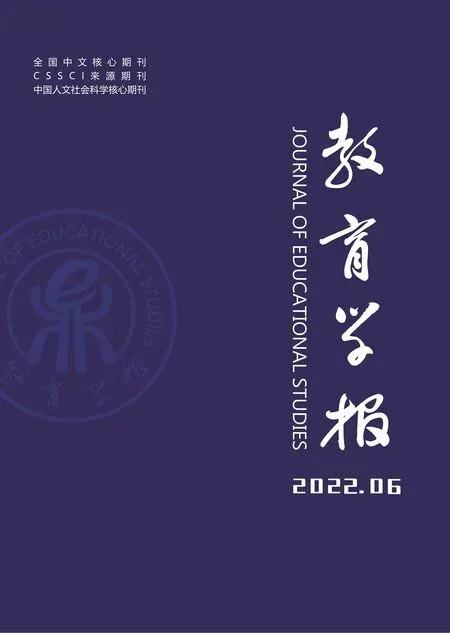《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之教育条款研究
周梦圆 李子江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下文简称“法案”)(1)该法案的正式名称为《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也称346号公法(Public Law 346),《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提交国会讨论时的名称。是1944年美国国会为解决退伍军人复员问题通过的一份综合性援助法案,涵盖医疗、教育、贷款、就业、住房等多方面内容,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法案”[1]。法案中的教育条款开创了联邦政府大规模资助退伍军人教育的先例,奠定了联邦资助学生政策的法律基础,更拉开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序幕。[2]但另一方面,教育条款也遭到许多非议,被指责导致联邦非法干预教育、侵害州权、引起高等教育贬值等问题,可以说美国历史上“很少有法案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受到这样广泛的赞扬和强烈的谴责”[3]Editor’s Note。国外很早就关注到法案对高等教育的影响,(2)参见:OLSON K W. The G.I. Bill and Higher Education:Success and Surprise[J]. American Quarterly,1973,25(5):596-610;OLSON K W. The GI Bill,the Veterans,and the Colleges[M].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4;ALTSCHULER G,STUART B. The GI Bill:The New Deal for Veteran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STANLEYM.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Midcentury GI Bill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2):671-708,等。近年来开始分析法案对不同族裔的差异化影响(3)如,TURNER S,BOUND J. Closing the Gap or Widening the Divide:The Effects of the G.I. Bill and World War II on the Educational Outcomes of Black American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3,63(1):145-177;KATZNELSON I,METTLERS. On Race and Policy History:A Dialogue about the G.I. Bill[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8,6(3):519-537;HUMES E. How the GI Bill Shunted Blacks into Vocational Training[J].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2006(Autumn)53:92-104,等。、对塑造良善公民社会的意义[4],以及法案实施后联邦资助教会大学的合法性[5]等具体问题。国内学者张斌贤等[6]讨论了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中的里程碑式地位,李传利[7]、续润华[8]等也关注到法案的出台过程和对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但囿于主题、史料所限,这些研究并未就法案中的教育条款展开更深入的分析。其他一些从社会流动[9]、军人权利[10]视角分析法案的研究更少涉及对教育的讨论。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都倾向于笼统地就整个法案展开讨论,几无对教育条款的专门研究。只有对教育条款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更具针对性地评析法案的教育意义。
梳理史料后发现,教育条款的制定是联邦政府、州教育管理机构、退伍军人组织、教育人士等各利益团体激烈博弈后的产物,考察教育条款的制定过程能清晰地反映各利益集团的教育立场。因而,本研究基于各版提案、国会听证记录、辩论档案等一手史料,考察立法过程中的相关争论,进而分析教育条款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影响。
一、制定提案:推动教育援助纳入复员计划
在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往往只承认对伤残军人的法律责任,且通常以单一的补偿金形式进行援助。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突破性地将战后援助普及到所有退伍军人,并覆盖医疗、教育、贷款、就业、住房等多个方面,促使这份综合性调适法案出台的直接原因在于前所未有的复员压力。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将出现多达千万的退伍军人,一旦安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引发内战。[11]制定退伍军人复员方案成了时任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面临的巨大难题,为此他任命了数个委员会并向国会提交了多份议案,在一开始罗斯福就考虑到了退伍军人的教育问题。
(一)罗斯福政府提案中的教育条款
早在美国加入二战之前,罗斯福就任命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制定了《战后计划与方案》(Post-War Plan and Program),提出“使教育中断的年轻人继续上学,并为在军队中服役的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平等的培训和教育机会”[12],但该方案未获国会通过。美国参战后,罗斯福总统设立了战后人力资源会(Post-War Manpower Conference)(4)最初建立时称作战后军民人事重新调整协商会(the Conference on Post-War Readjustments of Civilian and Military Personnel)。专门负责退伍军人事务,负责人是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的成员弗洛伊德·里夫斯(Floyd.W.Reeves)。1943年6月,战后人力资源会将制定的报告提交至国会,提出应放慢复员速度同时保障就业,并将退伍军人送入学校视为缓解失业的有效途径。里夫斯建议联邦政府资助所有退伍军人接受为期一年的教育或培训,其中“因服役中断学业的,或取得很大进步的,或表现出特殊天资和才能”的退伍军人可通过竞争性的联邦奖学金获得最多三年的额外教育。[13]这份报告成为此后一系列复员议案的摹本,尤其是分段式的教育资助方案被众多议案效仿,但报告提交时国会已经休会。7月28日,罗斯福根据该报告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明确表态要为退伍军人争取权益,提出要满足军人在退伍补偿金、失业保险金、教育和职业培训、贷款、医疗、残疾抚恤金等方面的要求,[14]这次公开讲话引起了激烈反响。
1943年秋,随着战争的推进,退伍军人数量大增,立法愈加紧迫,但此时联邦政府提交的综合性复员议案仍未被通过,罗斯福只能选择提交单一权益议案。10月27日,他将战后军人教育机会委员会(The Armed Forces Committee on Post-War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Personnel)所作报告提交至国会,请求为退伍军人教育权益立法,这便是S.1295号议案。(5)S.1295号议案全称为A Bill Providing for Loans to War-Service Persons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简称War Service Education and Loan Act。报告提出,“通过贷款和资助混合的方式给予服役6个月以上的退伍军人一年时间的教育或培训,其中成绩优秀者可享受不超过三年的额外教育。”[15]1-211月3号,罗斯福的盟友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主席(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艾尔伯特·托马斯(Elbert Thomas)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综合性援助议案,即S.1509号议案,(6)S.1509号议案全称为A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Merchant Marine after Their Discharge or Conclusion of Service, and for Other Purposes.同样将教育援助视为缓解失业的手段。[15]3-4国会在12月13至15日对两份议案进行了听证,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和联邦教育办公室因争夺教育管理权相持不下,还有一些人对申请教育资助的资格条件意见不合,最后两份议案都未获国会通过。[15]49至此,罗斯福政府的议案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些议案基本确定了战后复员方案框架,奠定了罗斯福作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理念之父”的地位。[3]39
(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提案中的教育条款
除了罗斯福政府以外,各种民间社团也积极参与到制定提案行动中。1944年1月初,退伍军人协会的提案引起了国会注意。退伍军人协会成立于一战期间,是当时美国影响力最大的退伍军人组织之一。1943年11月30日,退伍军人协会会长沃伦·阿瑟顿(Warren H. Atherton)任命约翰·斯特勒(John Stelle)担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制定复员方案。[16]1944年1月6日,特别委员会完成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草案。(7)协会公关部负责人杰克·塞纳尔(Jack Cejnar)详细解释了命名经过,“法案名称应‘引人注目’,不能用‘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这种毫无吸引力的名称。”(见:The American Legion. Proceedings of 26th National Convention of American Legion,Chicago,1944.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197.)在咨询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赠地学院和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Land Gr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中教育专家的意见后,[17]草案提出给予因服役而中断学业且服役年限不低于9个月的退伍军人至少一年的受教育机会,由退伍军人管理局负责向接收学生的机构每人次支付不超过300美元的学杂费,向单身学生每月支付50美元生活津贴(已婚学生为75美元),一年后由退伍军人管理局决定学生是否可以再获得三年额外的教育机会,议案还提出由退伍军人管理局全权负责所有事宜。[3]56
1944年1月10、11日,议案以《联邦政府援助二战退伍军人回归平民生活议案》(An Act to Provide Federal Government Aid for the Readjustment in Civilian Life of Returning World War)为名正式呈交于众参两院。14日,阿瑟顿和斯特勒在白宫向罗斯福阐述议案,罗斯福对协会制定的综合性议案表示支持。随后,阿瑟顿领导协会进行了大规模公关活动,发布了400多份广播录音、125个电影短片以及众多社论、时评、海报记录军人们“在训练场、战场和医院”中的牺牲,通过邮寄信件、刊登请愿书等方式收集了全美200万人签名,[18]198-199[19-20]敦促国会通过这部“军人大宪章”。协会还与当时著名报业巨头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结盟,利用其庞大影响力加大宣传。赫斯特旗下的《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 American)、《波士顿美国人报》(Boston American)和《美国纽约日报》(New York Journal American)都派出记者跟踪报道立法进展。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合众社(the United Press)、国际新闻社(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也对提案进行了大幅持续报道。[17]199通过这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游说活动”,退伍军人协会提交的这份法案成为当时最受关注和欢迎的议案。[3]61
二、国会立法:关于教育条款具体内容的争论
在罗斯福政府和退伍军人组织的努力下,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援助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但教育条款的具体内容还需进一步确定。1944年1月11日,参议院在收到退伍军人协会议案后责成财政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负责,后者成立了退伍军人立法小组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s Subcommittee on Veterans Legislation),并组织听证。3月24日,修正案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50∶0票决通过并交付众议院。与此同时,众议院组建了以约翰·兰金(John Rankin)为负责人的听证委员会,兰金对退伍军人协会的议案和参议院修正案都非常不满,尤其是其中的教育条款。5月3日,兰金向众议院提交了修正案,其中大幅度提高了教育资助的门槛。次日,议员葛莱汉姆·巴登(Graham A.Barden)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教育议案,希望能取代兰金修正案中严苛的教育条款。5月17日,兰金修正案教育条款以88∶77票获得通过,次日,众议院全体会议票决通过兰金修正案全部内容。6月8日,众参两院以兰金和班尼特·克拉克(Bennet Clark)为主席各派代表7人举行了联席协商会讨论分歧,12、13日,新的修正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通过。6月22日,罗斯福签署法案,标志法案正式出台。在近半年的听证辩论中,联邦各部门、各州代表、退伍军人管理局、退伍军人协会、各教育组织等群体激烈辩论,在退伍军人教育援助的管理权、退伍军人申请教育援助的资格条件、资助方式和标准三个问题上尤为胶着。
(一)关于退伍军人教育援助的管理权之争
在众参两院数十轮的听证与辩论中,对退伍军人教育管理权的争论贯穿始终。退伍军人教育是涉及三个权力主体的交叉领域,联邦因出资而享有对退伍军人的管理权,各州历来享有的教育管理权以及学校拥有的自主办学权。在听证和国会辩论中,退伍军人教育“由退伍军人管理局全权负责”“由联邦教育办公室负责”“由州教育管理机构负责”三种观点相持不下。
退伍军人协会的草案认为教育援助属于退伍军人一揽子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应该和其他事务一起由退伍军人管理局集中管理,这样既可以保障退伍军人利益,也可以防止多部门管理造成的推诿、混乱和竞争。[21]16但退伍军人协会也承认教育条款的实施需要其他部门配合协助。在参议院听证中,议案起草者科默里(Harry Colmery)提出建立由其他机构(如战争部、海军部、内阁机构等)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行使建议权。[22]250-251听证会负责人克拉克也支持这个方案,他认为法案以退伍军人利益为最终导向,执行过程可以与其他机构分享,但决策权必须掌握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手中。因而,克拉克提交的修正案写道成立一个教育咨询委员会辅助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但依然维持局长的决策权。[23]5
以退伍军人管理局为主管机构的方案遭到不少教育届人士质疑,他们认为联邦教育办公室能更专业地处理全国教育事务。联邦教育办公室负责人约翰·斯图德贝克(John Studebaker)也曾在听证中公开争取这项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权。全国教育协会尤其支持该方案,协会秘书吉文斯(Willard E.Givens)在听证中说退伍军人入学后便是普通学生,教育事务就该交给教育人士负责,且联邦层面处理不当必然会导致州级出现混乱,因而该由联邦教育办公室担任主管。[22]138-141但由联邦教育办公室主管明显违反了美国的历史惯例,(8)美国宪法并未给予联邦管理教育的权力,因而教育一直是州和地方的职责。联邦教育办公室相当于一个信息部门,主要职责只在于收集、整理、公布教育信息,并无管理教育的实权。即使联邦政府保证“联邦教育办公室只负责提供资金和监督花销,教育过程和录取权由各州和当地教育机构掌管”,[24]该方案依然遭到不少人反对。
无论是由退伍军人管理局还是由联邦教育办公室管理,都让州权主义者感到不安。众议院听证会上,华盛顿大学校长克罗伊德·马文(Cloyd H. Marvin)宣称“在美国,教育是州和地方的职责,任何绕开州去管理教育事务的行为都是对美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威胁。”[21]320马里兰州督学托马斯·普伦(Thomas G.Pullen)认为州掌管教育事务不仅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更是因为州教育机构的专业能力,因为只有州教育机构有能力进行专业的调度,处理学生涌入后给学校系统造成的压力。[22]145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支持州教育机构的巴登议案和支持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兰金议案展开对峙。巴登认为由退伍军人管理局负责教育事务侵犯了州和地方的权力,教育事务的领导权应明确掌控在州教育机构手中。[25]4340兰金一方则争论,退伍军人管理局作为拨付学费的机构理应享有评判学生资格的权力,议案规定由州负责认证学校表明了议案并未对州权造成实质性侵害。此外,各州只能协调州内教育事务,难以解决跨州申请的问题。[25]4321-4325在最终投票中,兰金议案以轻微优势获胜,退伍军人管理局成为退伍军人教育事务的主管机构。
(二)关于退伍军人申请教育援助的资格条件之争
除了管理权,退伍军人申请教育援助的资格条件是另一个争论焦点,这决定了战后教育资助的范围和规模。放宽资格条件意味着大量退伍军人将获得入学机会,这不仅是对联邦财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精英高等教育观的挑战。很多人担忧入学人数剧增将导致“教育膨胀”,大量平庸的学生在资助下进入高校将造成高等教育机会贬值。但若将申请条件设置得过于严苛,把多数退伍军人拒之门外,又会引起退伍军人不满,更无法体现国家对退伍军人的援助精神。
拟定草案时,退伍军人协会内部对此争议不断。草案一开始提出向所有退伍军人提供充足教育,随后有分歧认为只有因服役导致教育中断的人才有资格获得继续教育机会,也有人提出至少服役6个月方能获得教育资助,且应该提供“1+3”式的四年教育。“1+3”式教育资助具体指为合格退伍军人提供一年的普遍教育机会,再为其中表现杰出者继续提供不超过三年的额外教育机会,由高校自主制定获得额外教育的资格,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对退伍军人和高校的双重保护。[22]250在听证中阿瑟顿解释,教育援助是退伍军人的切实需要,更能将原本是国家负担的待失业人口转变为未来的高质量劳动力,但谨防一些人为骗取生活费进入学校,教育资助数量应加以限制,基础资助之外的费用该由学生自己负责。[21]16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全国教育协会秘书吉文斯认为应扩大教育受益面,他提出了一种不限制入学条件但考查入学后学业成绩的方案,“政府应为每位归国退伍军人提供四年教育……但退伍军人在入学后要面临与普通入学者相同的成绩标准与限制”[22]138-139。美国教育委员会成员同时是高校联盟代表的乔治·祖克(George F.Zook)也同意为退伍军人“提供充足教育机会”[22]122,但克拉克坚决反对这种不加限制的入学方案。最终参议院修正案将教育机会扩大到“除有污点退伍军人(dishonorable)外,所有服役期限不低于6个月,或因伤残导致退役的军人”群体。[22]5参议院宽松的教育条款让兰金大为不满,他主持的听证会制定了相对严苛的入学条件,除服役时限要求外,“教育(培训)因服役而延误或中断”也被列为限制条件。巴登议案则将入学条件放宽为“任何服役期限不低于6个月的退伍军人……均有资格获得三年的学校教育”[25]4346。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兰金议案因其严苛被巴登议案的支持者指责为“精英议案”,被迫将服役时限要求调整为3个月,另外还同意入伍年龄不超过24岁的退伍军人都有资格接受教育资助。[25]4646-4349巴登议案则因太过宽松,导致教育耗资过大,未能获得通过。
6月8日,众参两院联席协商会磋商分歧,新修正案再次对申请资格做出修改,将年龄上限从24岁调高至25岁。
(三)关于教育资助方式与标准的争论
立法过程中各方的一致共识是法案以退伍军人利益为导向,“教育条款,旨在为有需要的退伍军人提供教育资助,它不是为了救助大学或建立大学而起草,也绝不是出于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利益。”[21]355但即便前提一致,落实到具体条文上,依然存在讨论空间。退伍军人协会草案中简单的一句“由退伍军人管理局负责向接收学生的机构每人次支付不超过300美元的学杂费”根本无法应对美国复杂多元的高校系统。
美国的高校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高校主要是依靠各州税收支持的高校。公立高校对本州居民提供优惠政策,本州居民进入大学收费低廉甚至根本不收费,但对外州学生收费不亚于昂贵的私立大学,因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进入本州高校就读。由于议案规定联邦会替退伍军人支付学杂费,因此意味着接收本州退伍军人的公立高校只会得到一笔很少的费用。这种资助方式引起了高校一方的质疑,乔治·祖克说,“如果联邦政府要对教育进行补偿,那么,正确做法是按照同一标准向公立高校和私立高校支付学杂费。”听证会负责人克拉克认为,公立高校大部分都受益于《赠地学院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s),它们已经从联邦得到了一大笔钱。参议员汤姆·康奈利(Tom Connally)更是不能理解,身为本州居民的退伍军人却要按外州居民的标准向大学缴纳学杂费。[22]127-128
面对立法小组的反对,祖克态度坚决。他陈述,《赠地学院法案》的收益主要用于学院向社会提供的扩展课程(extension course)和农业、工业的研究,算下来高校从联邦获得的用于普通教学的资金每年仅有5万美元。说到底,公立高校对本州居民收费低,是因为本州的税收支持,与联邦资助关系不大。现在联邦要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福利,那就不能占用州的税收。[22]128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祖克占了上风,听证会同意按私立高校的收费标准向公立高校支付学杂费。另外,身为高校方代表的祖克还提议提高资助额度上限,在他的坚持下,学杂费资助额度上限从300美元提高至500美元。
最终国会听证辩论后达成一致,法案中有关退伍军人教育援助的条款规定:“(1)任何在1940年9月16日后且在战争结束之前服役,其教育(培训)因服役被延误中断但希望继续受教育(培训)者,服役满90天或因战争伤残而退伍,在战争结束后2年(最长不超过7年)内可获得教育资助(有污点退伍者除外)。另规定,25岁以下服役者,其教育(培训)等同于因服役而被延误中断。(2)满足条件者经申请后可获得累计一年以内的教育(培训)。若成绩合格可获得额外教育,但受教育时限不得超过服役期限,且所受教育总时长不得超过4年。(3)满足条件者无论是否为该州居民,都可申请经过认证的教育机构。经教育机构录取后,退伍军人管理局为申请者支付学费、培训费、书籍用品等费用,每学年总额不得超过500美元。另外,申请者本人每月还可获50美元生活津贴(已婚人士75美元)。”[26]
三、法案实施:教育条款的影响
在法案出台之前,很多人都认为教育条款只是法案中“锦上添花”的部分,因为相对于退伍补偿金、失业救济和住房补助这种直接收益来说,教育条款的益处并不明显。也正因如此国会才更容易放宽入学条件,希望以较少的代价博得慷慨的美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法案实施后,远超预估数量的退伍军人申请了教育援助,教育条款成为了法案中最受瞩目的条款。
(一)教育条款带来的人才红利
法案颁发初期,教育条款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截至1945年2月1日,150万退伍军人中只有12844人(少于1%)利用教育条款进入了大学,专家据此预测最终将只有64万名退伍军人会进入大学,[27]这个数字远低于立法前的期待。当时很多报道认为退伍军人无视了联邦的教育援助。[28]美军上将查尔斯·博尔特(Charles G.Bolte)也称教育条款是法案中的“最佳条款”,但遗憾的是由于退伍军人对教育态度冷漠,该条款“对绝大多数退伍军人永远不会有用”[29]。
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退伍军人并非无视教育条款,而是不符合申请条件。法案实施后,退伍军人管理局、退伍军人协会收到了很多对申请教育援助资格条件的投诉。1945年12月国会制定修正案对此进行调整,进一步降低入学门槛,并延长了受教育时间,提高了生活津贴。[30]1946年,退伍军人进入高校的数量出现了拐点,从1945年的8.8万人猛增至101.3万人,在高校入学率占比中从5.2%增至42.7%,1947年继续增至49.2%,1948年开始平稳回落,直到1952年退伍军人在大学招生中始终保持在10%以上。战后十年间共有223.2万退伍军人进入了大学,另有550万人选择了大学以下的教育或短期培训,[31]总计近800万人受益于教育条款,这一数字远远超出预估。
在学业能力方面,退伍军人的表现也让人惊讶。在法案颁布之初,不少教育人士都为大学的未来质量感到担忧,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ames Conant)称法案是“令人沮丧的”,法案将使“战争一代中能力最差的人充斥大学校园”[32]。事实发展却恰恰相反,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调查发现,退伍军人的学业表现普遍比非退伍军人好,成绩最好的往往是那些离开学校时间最长的、已婚的和年龄较大的人,“勤奋”“自律”“认真”“严肃”“稳重”“时间观念强”等词汇成为在校退伍军人的标签。[33]更多的调查表明退伍军人在未来职业、经济上的成就也普遍高于非退伍军人。[34]87-91事实上,法案已经从保护退伍军人基本生存权利的“安全网”变成了推动数百万年轻人实现阶层晋升的引擎,教育、住房、贷款三大条款让良好的学历与体面的住宅成为可能,而这恰恰是跃居中产阶层的典型标志。
对美国社会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后的退伍军人构成了战后社会的中坚力量。数据显示,从1945至1950年,“45万名工程师、18万名医生、牙医和护士、36万名教师、15万名科学家、24.3万名会计、10.7万名律师、3.6万名牧师”中的八成是在法案帮助下获得了学位。[35]109这正如罗斯福所构想的,通过教育将待失业人口转化为战后重建中的高质量人力资源。[36]此外,法案还被认为是五六十年代的非裔群体争取平等权的先导,接受高等教育的非裔退伍军人成为黑人中第一批谋取平等权利的人。[34]141更多调查显示,参与二战的这代人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更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同时具备更优良的政治素养,这也正是这代人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一代”的关键原因。退伍军人颇为一致地认为法案中的教育条款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进入大学并不是服役换来的等价补偿,而是国家给予的一项馈赠。[37]
但另一方面,从种族平等角度看,法案的教育条款可能导致了黑人与白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阶层鸿沟。[38][39]94表面上看法案承诺了退伍军人享有平等的教育资助机会,但实际上在“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确立的种族隔离原则下,看似平等的机会只会拉大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距。在法案实施中,白人可以兑现法案规定的所有权利,但黑人申请房贷遭到拒绝,找工作时被引导从事“卑微、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申请教育资助时,白人可以进入顶尖精英学校,但大部分黑人只能进入“隔离但平等”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一百多所学校中,这些学校长期以来只提供“传道与说教”课程,几乎没有技术或工程类课程。[39]97也就是说,白人依靠法案实现阶层晋升时,黑人依然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甚至要承担起原本属于底层白人的社会工作。
(二)联邦资助下大学的两难困境
法案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争议颇多,上百万计的退伍军人在联邦资助下获得学位远非“伟大的教育实验”这么简单。[40]在法案确立的资助模式下,联邦通过为个人支付学费向大学拨款,作为消费者的退伍军人掌握了择校权,作为出资方的联邦分享对学生的管理权。虽然大部分院校因此度过了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但联邦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也前所未有地加强。
法案实施后,美国高校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发生了扩张。很多大学为了学杂费收入盲目扩招,甚至录取一些没能完成中学学业的人,短时间内学校规模濒临失控。社区学院、专科院校、师范学院、商业学院、飞行学院、理发学校、农场学校等职业学校也统统被纳入认证名单。为了接收更多退伍军人,有的州还临时建立大学,比如纽约州立大学系统(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一时间美国高等院校数量猛增。另一方面,由于法案将选择学校的主动权交给个人,于是大量退伍军人扎堆挤入少数热门的大学和专业中,1946年春季入学的退伍军人中有41%集中在38所院校,其余59%分散在其他712所院校,[41]造成院校规模和专业结构失调。
更现实的问题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接收了大量退伍军人的院校面临严重的设施短缺,即使将仓库、地下室、停车场都改造为宿舍、教室、食堂,依然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高校再次向联邦寻求帮助。联邦将医院、公寓等公共建筑划拨给附近的大学使用,赠与高校土地、图书、设备等资源。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退伍军人教育设施”法案,将战争期间的临时军事建筑分配给各个学校。在联邦教育办公室的统筹下,5 920个临时军事建筑被分配给700多所大学,大学中因此多容纳了约40万名退伍军人,联邦为此提供了总计8 313万美元的拨款。[35]68
作为获得资助的代价,大学的独立性遭到削弱。法案改变了以往直接资助院校的模式,代之以根据学生注册数给学校支付学杂费,并将择校权给予退伍军人,由此构建了一个由消费者主导的市场,学校为了获取学杂费必须迎合学生的需求。[42]另外,为了监察法案实施过程中的低效、贪污、浪费问题,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性修正案,联邦借此进一步渗入到高校教育事务内部。1945至1950年,修正案中陆续制定了农业培训、职业学校和在职培训标准,1948年又设立了退伍军人学费申诉委员会(Veterans Tuition Appeals Board)作为审查机构。另外,联邦在高等院校认证体系中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自19世纪末以来高等院校认证体系一直是高校自发组织的行为,与联邦政府毫无关系。《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打破了这一传统,法案要求对接收退伍军人的教育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名义上由各州政府提供合格名单,但实际上赋予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审核名单的权力。1951年众议院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提出由联邦或者独立于各州的民间认证机构制定认证名单。在1952年为朝鲜战争制定的《退伍军人再调整援助法案》中,国会不再采纳州提供的认证名单,而是选择认证机构(accreditors)来制定合格院校的最低标准和名单。[43]至今,接受质量认证仍然是获得联邦财政资助的必要条件,联邦政府成功地介入了大学评估体系。
四、结 语
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开创性地将教育援助纳入复员计划,以资助个人的方式为教育事业拨款,引发了教育规模空前扩张。法案通常被视作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的里程碑,被认为是美国“巨型大学”时代来临的前奏,更被当作划分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本研究发现教育条款是法案发挥教育效力的核心,围绕教育管理权、申请教育援助的资格条件、资助方式和额度三个问题的争论基本确立了战后教育援助的规模和方式,更反映了联邦、退伍军人群体、高校等相关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在对教育管理权的争夺中,联邦以资助退伍军人之名成功介入教育事务,伴随着资助力度的加强,退伍军人获得大量入学机会,高校则获得足够的重建资金。但另一方面,深入历史细节后发现这看似“伟大的民主教育实验”背后是州的妥协、公平性的不足以及大学自主性的丧失。联邦在教育中的角色不断加强,族裔差距愈加严重,退伍军人身份变成大学通行证更是意味着原本依靠天资与勤奋才能获得的高级学位成为国家对退伍军人的大方馈赠,高级学位含金量大大降低。
法案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对联邦和高等教育关系的重塑上。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行使,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联邦干预教育一向被视为“违宪”。但在这部法案中,由联邦以管理退伍军人之名打破了这层壁垒,巨额资助更使得此后联邦政府的各种教育行动得到更广泛的接受。[44]1958年《国防教育法》、1965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修正案》、2008年《高等教育机会法》以及2014年联邦政府发布的《大学评级体系框架》无不昭示着联邦角色的不断强化,一向依赖于自由市场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接受政府资助后成为联邦宏观调控及制定文化共识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