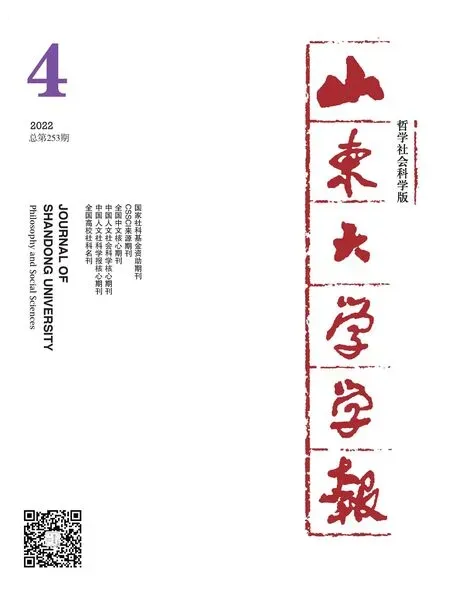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功能与路径
周 凯 张 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凝聚,更是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重建的思想源泉。文化内容包括历史经典、文物和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传统技能、民间活动、民俗民风和活动庆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非遗与旅游融合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模式之一,能够有效保护及传承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完整性,但在传统“传递观”的线性传播中,传播是传授和发送,更看重传者对于受众产生了何种影响,关注的往往是效果。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演进,面对新时代社会变迁和媒介变革的双重逻辑,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随之发生改变,效果导向的文化传播不免带来文化修养迷失、文化传播失灵等问题。从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传播的“仪式观”看,传播是一种意义,非遗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实践,能够有效构建民族共同的文化意义,凝结人们的共识和塑造共享的价值观,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凝聚力、价值力、影响力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产业化发展背景下,非遗与旅游融合是实现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国家、地方政府、社区等不同层面将非遗文化资源与旅游业有机融合,丰富的旅游商品能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旅游收益对当地文化起到进一步滋养和维护作用,有利于推动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非遗与旅游融合作为“活化”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它所蕴含的意义并非仅限于此,Janette Philp把文化遗产的诸多特征看作是重构历史的重要符号,能够昭示一种集体持有的国家观念(1)Philp J., Mercer D., “Commodification of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Burm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26(1), pp.21-54.。Sunny Jeong认为非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续,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助于人们增进民族认同感,维护国家统一,由此其所富含的政治意涵尤为凸显(2)Jeong S., Santos C. A., “Cultural Politics and Contested Place Identity”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 31(3), pp.640-656.;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引发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文化遗产引发争议的案例从深层次说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共享的历史,是区域认同和集体意识形成的基础。
现有研究认为,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得益于与产业经济的融合,在此背景下,众多研究着重分析非遗旅游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传播路径,注重非遗旅游传播的“效果”,却较少触及传播的意义。在对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政治意涵的讨论中,现有文献认为文化传播具有凝聚共识的功用,有助于区域及民族认同,却鲜有研究深入分析这些共识与价值是如何通过传播实践而形成,缺乏对非遗旅游文化传播中意义构建的分析阐释。然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一个群体信仰的重要体现,讨论到人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创造发展就离不开传播,文化生成的本身就是一种传播现象,存在于某种媒介“场所”之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3)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页。。从这个理论视角看,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实践承载着社会维系和共享信仰的重要作用,如何更好地通过文化传承与传播凝聚共识、共享信仰、维系社会稳定和谐,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需厘清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播中承担什么角色,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文化功能有哪些,通过何种路径进行意义建构等问题。以下将重点探讨非遗旅游传播对于文化意义构建的功用,并探索非遗旅游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二、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播中的角色定位

(一)非遗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传播符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4)亚太中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http://www.crihap.cn/2014-07/02/content_17638153.htm, 访问日期:2021年4月4日 。。为了维护共同的社会信念和行为规范,人类祖辈通过口语传播等方式,授予下一代传统的技术技能、思维方式、精神价值等。非遗可以理解为经由人体符号以及物质载体在人类个体或群体间世代相传的遵循相对固定编码和解码方式的文化信息(5)何华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伦理问题初探》,《社科纵横》2013年第1期。。非遗文化符号产生于特定的时空,人们通过将非遗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解码,建立独特的符号体系进行传播,它所蕴含反映特定人群共同生命体验的文化形态得以传承下来,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文资源。种类繁多的非遗文化为传播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这些符号的传播成为文化成员共享信息和知识的基础。
传播是一种将各种现实符号化的过程,通过对于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人们得以表达、传递知识与经验。对非遗旅游的传播活动而言,文化既是来源也是资源,因为“它提供‘可以获得的意义’,这些意义极大地影响文化成员‘能够表达的东西’”(6)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1页。。无论是传统戏剧昆曲还是古琴表演艺术,非遗都需要一套特定的编码向受众系统地传递复杂的信息与情感,引发受众的共鸣。这样看来,文化传播实践就是一种符号被理解、被使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遗得以传承和延续。同时,非遗具有强烈的区域性、民族性、变迁性,因而非遗文化符号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意味着它是一种无法再生的文化符号,这样的独特性使其在文化传播竞争中具有巨大优势。
(二)旅游是提供传播渠道的媒介场所
旅游的动机不仅来源于放松心灵的娱乐和休闲享受,更深层次的是对于文化的憧憬与渴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当下人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和获取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场所”,旅游为受众的文化体验搭建了一个“舞台”,比如传统景观再现、特色旅游活动、大型节日庆典、歌舞表演等,这些渠道的架设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交换构建了文化景观,受众在符号系统中体验各种情景,通过互动完成象征意义的解读和传达。因此,旅游的吸引力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蕴含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媒介场所的丰富性。例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淮灯会,作为历代南京民众辞旧迎新、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传承活动的有机统一,已成为展现南京历史文化景观的重要活动。每年灯会期间,多达数千盏花灯的展览都会引来众多游客观赏,成为国内非遗旅游的代表之一。旅游作为一种传递符号的媒介场所,不同渠道呈现的信息有所区别,景区观光与社区体验不同,影视展演与图片展示有异,现实与虚拟更是效果不一,因而,旅游通过何种方式构建文化景观对于符号意义的交流、互动和共享具有重大影响。
(三)非遗旅游是独特的文化传播实践
“传播是‘最奇妙的’,因为它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它产生社会联结,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7)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第21页。从传播的仪式观看,非遗文化传播是非遗文化符号生产、制造、展示、传播和反馈的实践过程,整个文化传播活动是释放文化生命力和感召力的过程,通过“共同信仰的表征”互动,连接了人们共享的文化。如国家级非遗湖南“江永女书”,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性别文字,是区域女性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传给少女的方式代代沿袭。女书的传承体现了区域内的女性专属的精神空间,当地建立女书风景区、女书生态博物馆等作为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所,女书文化与旅游融合不仅能展示女书的形式形态,还能让人们在观赏浏览时,共享这一区域女性特有的精神内涵。在外来文化冲击严重的当下,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是一种留存民族文化的“动态”记忆,受众能从中感受到本民族的民风民俗、生产传统、技能技艺,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唤醒并强化民族情感、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成为新时代构建共同文化价值导向的重要路径。
三、仪式观视阈下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功能
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地球村”图景,让捕获异域信息和文化变得更加便捷与及时,文化加速流动,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文化是中华民族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富起来”之后的精神需求、价值需要,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认同。非遗旅游作为独特的文化传播实践,体现出仪式性、空间性、参与性的特点,具有承载重要的精神凝聚、认同构建、价值导向的功能。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在“共同的场域”内,受众经由集体参与共同体验情感的历时性模式,非遗旅游在这样集体共同参与的传播中,不断创造可以承载文化精神符号,并在文化变迁中以具体形式留存,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当下,非遗旅游能够构建符号意义、连接民众情感与唤醒民族记忆。
(一)仪式性:凝结文化的价值内涵
仪式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普遍的文化现象,而传播仪式观将传播看作是参加一次神圣的弥撒仪式。在参加这个仪式的过程中,人们并不关注是否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而是注重在规则化的仪式程序中使特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得到描述和强化(8)王晶:《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可以看作是再现和重塑这种“仪式”与“典礼”的过程,通过非遗旅游中仪式化的体验,人们能够感受到古老的生活经验与传承的精神。经过千百年的时间考验,非遗留存和延续下来的是最具生命力和最能唤起民族共同记忆的部分,是民族精神展演具有代表性的典礼。每到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官方或者民间将举办的各种“仪式”“典礼”进行庆祝。清明节各地通过不同的仪式和祭祀风俗,寄托对逝去亲人的哀思,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划龙舟”“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也成为人们庆祝节日的重要方式。这些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通过仪式和庆典凝结精神价值,跨越地域区隔成为人们内在的共同文化信仰。但是反观当下非遗传统节日活动保护不力,传承效果不佳的现象,其重要原因是仪式和庆典的内涵流失和流程简化,非遗旅游需进一步挖掘文化符号,创新再现传统仪式和典礼,才能更好地弘扬文化自信,实现社会和文化价值。
(二)空间性:建构传播的共同场域
“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9)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第18页。凯瑞所言的“共享文化”实际上是构成传播共同场域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或个人创造的,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传承而来,如酿酒技艺、民间医药、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等所富含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都具有空间性,这些特定的文化能够构建一定区域和群体的共同场域。人们以代代流传的技艺提高生产效率、生活质量,通过活动表演、传统艺术,共同纪念过去、歌颂生活,丰富其精神文化世界,在共同的生活体验下从根本上唤起内心的共鸣。在传播的过程中,非遗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加上不同的受众对非遗所蕴含的符号意义存在不同的阐释,非遗文化展现出独特且小众的特性,但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享的精神价值往往是相通的,对于文学、音乐、舞蹈的欣赏是如此,对于民俗、节日、庆典、手工艺的传播也是如此。通过传播搭建的共同场域,能够唤起人们对于过去的共同记忆,表达共同的价值观、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从而增强凝聚力,成为身份有意识重构的过程。“符号互动论”代表人物乔治·米德、库利等人认为,想象是实现传播的重要手段,认同的构建过程是通过想象实现,但想象并不是随意捏造,而是群体达成共识、形成共有认知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非遗旅游为想象搭建了充分的空间场域,在这个空间内,人们的认知受到同一个文化背景的感召,对同一文化源头的不同文化形式产生合理“想象”,从而形成共享信仰的共同体。
(三)参与性:连接受众的情感体验
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是人们情感和价值连接的基础,倡导通过“参与、互动以及创造”,进入共同的“仪式化场域”中。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作为民族或地域的精神象征,它蕴含中华民族的美好品质与内涵。这些象征符号的产生往往依托于个体或者群体的创造,各类民间的典故、风俗、歌谣、技能在生产生活中凝结成文化,传达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取向与智慧。以清明节为例,作为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活动仪式为祭祖和扫墓,是人们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禁火、踏青、放风筝、荡秋千、娱乐游戏等活动也成为清明节的必备的民俗。人们在参与节日的各种仪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继承民族精神核心内涵。因此,非遗旅游文化传播可以看作是一种参与式的行为方式(或是一种互动),在文化和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同一民族的情感被唤醒,参与的仪式和典礼成为贯通古今、连接受众的情感体验方式。共享的情感体验能够产生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正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是通过共同的政治和历史规划,在人们头脑当中和集体记忆中构建起来的文化共同体”(10)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4页。。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呈现多元的转向,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在人的精神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共同的信仰与文化。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除了将非遗的知识与信息传达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受众的互动和参与,将非遗所蕴含的美好追求与价值取向与受众连接,制造良好的情感体验,从而形成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四、非遗旅游文化传播路径

(一)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符号
深入挖掘非遗文化符号,是传播得以达成的前提。文化符号的提取需要反映一定的区域特色,比如成都对于熊猫、川剧变脸、火锅等文化符号的提炼和使用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些具有区域生活特色的形象符号经过提炼和变化,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依托文化符号不仅将成都区域文化传承下来,还打开了区域知名度,形成正向传播循环。该模式也为非遗旅游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挖掘提供了借鉴思路。各地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需要挖掘最能代表当地文化的符号,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融合,巧妙运用和展现文化符号,使之快速融入现代人观念和生活中。传统在不断变迁和发展,甚至也是在变革中被创造的。一方面,在社会变迁中留存下来的非遗传统需要通过排查、建档、保存、研究和保护等手段进行全面梳理,通过纵向的传承传播留存传统。另一方面,要利用媒介技术挖掘和展现非遗文化符号,创造新的传播符号展现方式,利用横向的传播,发扬传统。如杭州的宋城表演、南京秦淮灯会等等,都是借助现代科技媒介技术,通过灯光、舞台、演员、场景等组合,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象,将传统仪式与现代技术完美融合。
(二)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传播场域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创造了一种以产业为连接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场域中,政府、企业、游客、媒体等主体,进行无形的旅游文化氛围的供给和有形的旅游文化商品的生产。非遗与旅游融合不仅提供了一种文化景观展示的文化空间,影响着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同时各类主体参与传播活动实践的过程也是进行文化创造的过程,文化场域得以不断重建。也就是说,在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场域中,各类主体的实践是共享文化和重建文化的重要方式。政府在非遗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中承担主导作用,应当进一步完善具体的政策体系,在制度上保障非遗的存续和完整。企业作为非遗文化市场化、产业化的主体能够为非遗传承引入投资、筹措资金,围绕非遗文化进行旅游开发和舞台演出等产业化运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非遗的多样性。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意味着它将承担“文化传播者”的责任。构建共同的文化传播场域需要媒介营造氛围和创造机会,应积极推动多元化传播平台的建设,利用媒介矩阵增加文化符号的曝光度,大力弘扬以非遗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艺术精神,使公众参与到非遗议题中来,增加对于非遗旅游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非遗旅游的传播应当从政府、企业和媒体等各个主体出发,明确各自的职责,拓展架设非遗文化场域的渠道路径。
(三)注重非遗传播受众参与体验
在线性传播中,由报纸、广播、电视所构成的传播媒介是信息的单向传播者,受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叙事结构由传者单方面完成,用户难以提供反馈,更无法参与信息交流互动过程。在非遗旅游传播中,许多传统文化颇具仪式感,同时可能会带来一种距离感,非遗旅游不仅要注重传播形态,更要注重互动反馈,打造更多有意思、有意义的非遗旅游传播场景,通过增加互动方式,让受众参与到非遗旅游传播当中。在互动反馈上,要设置互动环节和流程,提升传授双方的参与体验感,如面向公众征集以视频、音频等非遗文化的展示作品,吸引观众在互动中获得极高的参与度。积极整合民间UGC,借助智能生产平台,形成各媒介主体共同参与的非遗旅游传播氛围。
此外,还可以借助媒介技术提升受众的互动和在场感。虚拟数字技术支撑的沉浸式传播强调打破信息传播方与受众之间的界限,创造受众的“在场”。通过受众与信息传播媒介的交流互动,调动受众对于非遗旅游的全方位感知,营造受众沉浸于文化“场域”中的感觉。受众在此当中相当于以一个“具身”参与到虚拟仿真构建的“现实”中。非遗旅游可以通过打造各类沉浸式艺术体验会所,使用数字摄像头、遥控器、红外线感应灯,360度全景视屏、沉浸式声音视觉装置等设备,让观众实现对非遗旅游的沉浸式体验。
五、结语
工业文明和全球化进程加速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享有西方先进技术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红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的影响。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其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传统文化的消失将导致文化多样性的消失,使文化生态发展失去平衡,使国家和民族失去凝聚力。因此,文化生态保护已上升为国家任务。近年来以产业融合为手段、以旅游发展为方向成为非遗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非遗旅游文化传播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本利用,还是一种蕴含了凝结民族特有的精神活力和信仰体系的传播实践。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提醒我们,在非遗旅游文化传播中,强调的是于“共同的场域”内,受众经由集体参与共同体验情感的历时性模式,传播是为了更好地对社会进行维系。非遗凝结了人类共同的文化,是本民族文化之精髓。在文化强国背景下,非遗旅游的文化传播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创造“仪式”和“典礼”的重要方式,需通过对非遗文化符号的提炼挖掘,构建非遗文化场域,丰富受众互动体验,全面提升非遗旅游的文化感召力、传播力,探索更多可能的传播路径,在实践和传播中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和认同感,实现社会的稳定维系。
但是,在看到非遗旅游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非遗旅游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商业化开发引发的传统文化流失与缺失值得我们反思和重视,如在旅游的舞台化展演和演出中,传统文化的变迁与重构引发的文化失真现象,迎合大众审美过度商业化,为了提高知名度和经济收入不惜“打造非遗”等问题,导致非遗原本的社会维系作用和深层社会内涵在这种“脱域”状态下很难完整和准确地予以传达。非遗的保护和传播都不应当脱离其所生存和延续的环境,非遗与旅游融合更应注重对其整体性的保护,包括其生长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坚持整体性原则基础之上,非遗旅游的融合应当保持限度。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发展要求,尊重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通过建立“非遗文化保护区”,保留非遗文化所在社区的生活原貌。其次要注重传统文化的还原性创造,提取各类文化符号时,既要在“前台”进行加工和创新,也应当注重“后台”的保护,让游客有机会参与和体验原生态的非遗文化,体会和感受传统本身。再次要因地制宜地提炼文化精髓,形成具有真实性的符号价值,注重创意策划的艺术性,平衡好对于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真实性与观赏性的需求,在利用产业化手段进行文化重塑的同时,也需注意将真实性保留到非遗旅游中,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有限度的非遗旅游融合中,挖掘其文化传播的意义,才能形成新时代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构建以文化为纽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国家发展进步提供可持续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