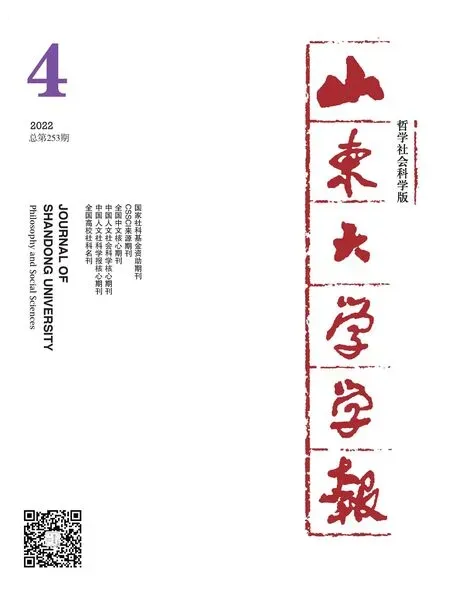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定位下的中国方案
朱 荟
一、国家战略定位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重大转向
人口老龄化是贯穿中国21世纪的新基本国情,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社会新形态(1)杜鹏:《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经济日报》2021年3月26日,第10版。。2021年5月,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明显放缓,以老龄化、少子化为突出特点的人口结构态势凸显。全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持续攀升,60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分别为2.64亿和1.91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8.7%和13.5%。上述两个口径的老年人口比例较2010年分别上升5.44%与4.63%(2)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702.html, 访问日期:2022年3月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再次显示,中国老龄化继续加深: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8.9%和14.2%。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3)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1/t20220117_1826404.html, 访问日期:2022年1月17日。。我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人口格局业已形成且不可逆转,其程度逐渐加深,趋势日益加剧(4)翟振武、陈佳鞠、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中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并将在2035年前后达到重度老龄化;在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将分别以4.87亿和34.9%的数值,达到历史峰位(5)《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我国总人口约三分之一》,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9/content_5307839.htm, 访问日期:2021年7月6日。。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在上述宏观背景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跻身为与乡村振兴、科教兴国和健康中国等并列的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这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重大战略部署,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6)吴玉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尽快形成“六个共识”》,《中国社会工作》2020年第12期。。
毋庸置疑,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老龄化本身并非都是风险或危机。只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在思维观念、资源配置、需求满足以及在制度安排等诸多面向,从个人到家庭、从商业市场到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事务到政府管理,尚未做好足够的前瞻准备与及时应对,因而谈起老龄化更多理解为压力与挑战(7)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河北学刊》2020第3期。。事实上,这种趋势化、稳定化与常态化的老龄社会新形态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增速下降、劳动力供给下行、社会创新下滑等负面效应。以往人们将老化过程片面地与虚弱、残缺与病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刻板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无论是个体的衰老还是社会的老龄化,反而应认定为一种优势或进步的表征。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将出现身体机能与液态智力的弱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人在最后一个生命阶段,确实积累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劳动经验、经济储蓄以及社会支持等有益收获。人类寿命的延长并不会削弱老年人在晚年历程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潜力,相反人口老龄化将产生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学术界称之为“长寿红利”(The Longevity Dividend)(8)Scott A., “Achieving a Three-dimensional Longevity Dividend”, Nature Aging, 2021,1, pp.500-505.。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是国家战略定位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重大转向与理论创新。老龄社会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百年未有之变局,更是全球必须面对的新人口格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在于“积极”(9)《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跻身国家战略,有何深意?》,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19/content_5562488.htm, 访问日期:2021年7月6日。,充分体现了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探索。中国方案的积极意涵,既包括积极的财富储备、积极的人力资源、积极的物质服务、积极的科技支撑、积极的社会环境,又包括以更加积极的老龄态度、社会行动和公共政策来提早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整个国家战略的体系设计中都始终嵌入积极视角(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老龄观的重要指示》,http://www.scio.gov.cn/m/xwfbh/xwbfbh/wqfbh/44687/47548/index.htm, 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0日。。为此,本文尝试从概念路径及其主要特点、理论转向及其解释创新两个维度,更加客观和系统地梳理与阐述中国方案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新视角。从概念再生性与理论自主性构建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从基本理念、理论形态、分析维度、观测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推出一种新的老龄科学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则以国家战略的认识高度、价值共通与机制衔接,展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国家自信与民族自信。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认识:从“危”到“机”的学理增进及争议焦点
作为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议题,既往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将人口老龄化当作自变量,关注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进行理论探讨;二是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因变量,重点讨论社会环境、政策条件及经济水平等对老龄化态势的形塑,由此构建相应的实践路径;三是分析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人口老龄化是机遇抑或是挑战”始终是我国老年科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热议焦点。“危机论”与“时机论”成为两种相互对垒的基本认识。对于中国老龄社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焦虑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担忧舆论是长期存在的主流观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着力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之时,这种“谈老色变”的倾向即随之盛行(11)郝麦收:《谈谈人口“老龄化”》,《人口与经济》1982年第3期。。一些悲观论的思想往往将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老龄化联系起来,顾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的“危”与“机”成了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元问题”。
从研究文献看,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判断从老龄冲击转向长寿红利孕育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战略问题;这项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人口再生产的普遍现象,也是我国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实问题。随着人们对两种生产相互关系规律的深入认识,通过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再生产过程和发展经济及老年社会事业,这个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较好的解决。”(12)陈介荣、李宏国:《云南老龄人口的现状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年第2期。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老年人比例分别超过全市总人口的10%,这些城市已步入老年型城市之列。为此,当年《人口研究》曾刊文讨论天津市人口的老龄问题,该文指出,许多身体不错、有工作能力的天津市离退休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发挥余热,建议组织这些力量为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再做贡献(13)黎宗献:《天津市人口的老龄问题》,《人口研究》1984年第6期。。再如,1988年北京市老龄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包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在内的80多位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集体讨论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14)国家计生委宣传教育司:《加强对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6期。。会议强调,虽然我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先老后富”的情况格外严峻,可能出现“缺乏年轻劳动力、老年负担系数提高、国民经济负担加重以及家庭结构变化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看,“不利影响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利因素是长远的”。会议的基本共识是,“老龄化应当是好事,它使人类的治理释放期延长,有利于社会知识的延续,有利于减轻国家负担,有利于机构改革与调整”,解决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矛盾的关键在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努力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发展,并大力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老年人口再就业问题在1989年中国老年人口调查数据分析科学讨论会上得到更为热烈的讨论。大多学者认为,虽然我国长期存在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劳动适龄人口就业难的状况,但是老年人口再就业不会对此产生冲击,相反将有促进作用。有学者利用微观分析模型模拟了1987年至1992年老年人口再就业状况,结果表明,当时我国老年人口再就业人数仅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的3%左右,鼓励老年人口再就业并不会影响国家就业供求结构。(15)张车伟、刘爱民:《推进老年科学研究 迎接老龄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1期。
综上所述,学界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逐渐从老年负担转向长寿红利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学术增益的背后,仍是时机论无法与危机论相抗衡的现实困境。即便有大量研究围绕人口老龄化的乐观方面,具体从照料负担比、老龄人力资本以及老年人口再就业等多个角度论证长寿红利的可及性与可行性,但是在普通民众、社会舆论甚至不少学者的观念中,人口老龄化仍然被视作一种社会问题,将会给中国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风险与挑战。这种老年负担的危机观点固执存在,始终深入人心。
究其根源在于,“人口老龄化是利好时机”的学术讨论缺乏相对坚实的理论体系与实证支撑,“长寿红利”还仅仅停留在观点上,不仅缺乏可以颠覆老年负担的实践方略与方法体系,还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以及理论支撑。越是有学者强调人口老龄化长寿红利的合理性、充分性与正当性,越是彰显出时机论在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上的薄弱与缺失。一方面,长寿红利的概念并未明确提出,学术讨论中关于长寿红利的提法多是基于逻辑推导,还包括一些预测与猜想。“人口老龄化是时机”仍属于基本论述的阶段,并且时机论的提法中充斥着较多应然性的价值判断,而非实然性的现实例子。这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在中国以及即使是老龄化较早的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也不过两百余年的历史。老龄社会新形态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与发展动力并未充分显现。这种研究路径论证老龄问题是机遇而非挑战,难以对长寿红利的整个话语体系予以有效支撑。另一方面,时机论的解释范畴缺乏完整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迫切需要以长寿红利作为逻辑贯穿。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机遇”的讨论散落在相当广泛的研究内容之中,这些对老龄化肯定的说法多是零散的论点,并未形成关于长寿红利的一套明确且自洽的概念视角与理论体系,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影响长寿红利的概念接受与推广,并影响其理论解释的应用性与影响力。
三、长寿红利的概念旨向、阐述路径及理论意涵
长寿红利这一术语看似生疏,但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长寿红利的概念之所以格外重要,在于它呈现的是人类生存与生命最基本与最重要的本源形态,对于老年学、社会学、生物学、医药学和人力资源科学等相关学科都具有较为基础性的地位。然而,人们对于长寿红利的理解与认识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与统一性。正如老年学重要奠基人斯特雷勒(Strehler Bernard)在定义老年学(Gerontology)这一术语时所强调,其词源ger-“to grow old”(变老)和词根geron-“an old person”(老年人)明确展示出关于人类老化与衰老的研究领域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提出警示,整个社会并未对人们将延迟衰老与寿命增长这项科学意外(the Scientific Windfalls)做好相应的准备(16)Strehler B., “Implications of Aging Research for Society”, Federation Proceedings, 1975,1, pp.3-9.。
长寿红利的基本概念简单而清晰,具有两层含义:一是长寿,指的是人类寿命正在逐渐延长,在克服衰老与疾病的基础上实现有质量的长寿;二是红利,全世界都将以老龄化为契机,创造出社会、经济、文化等新发展成就。虽然长寿红利作为一项明确的概念工具与研究路径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学术界对其既熟悉又陌生。纵贯研究史,长寿红利的学术概念从提出到运用主要遵循两条基本路径。
第一条是以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为主要视角的生产性老龄化(the Productive Aging)路径,概括长寿红利的“积极价值”内涵,以生产性强调人们寿命长且健康是一种社会福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人类的预期寿命延长与健康状况持续改善,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学术共识。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显示,中国2019年整体预期寿命为77.4岁(男性74.7岁、女性80.5岁),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男性67.2岁、女性70.0岁);全球预期寿命为73.3岁,健康预期寿命为63.7岁(17)WHO,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1: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pp.16-35.。虽然从年龄数值上看,人类寿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并非同步延长,在病态压缩抑或扩展理论的争辩下,人们并不笃定寿命延长将迎来一个更为健康且美好的新社会。长寿红利正是在这场激辩中得以诞生与发展。正如有学者对此概念的界定:人类正处于一个从未有过的“活得更久”且“更为健康”的老龄社会新形态,当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都随之改善,从而实现健康、长寿且富有生产力的新生活范式,这种在个人、经济和社会多个层面所获取的收益就是长寿红利,其具体实现机制在于预期寿命、健康与经济三个维度的正向促进(18)Scott A., “A longevity Dividend versus An Ageing Society, in Live Long and Prosper?” The Economics of Ageing Populations,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eds, London: CEPR Press,2019.。英国国际长寿中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UK)运用35个国家在1970年至2015年的预期寿命与每小时国内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论证长寿红利将提高经济生产力,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负担(19)Matt F., “The Longevity Dividend: How Ageing Populations could Boost Economic Productivity”, https://www.globalpolicyjournal.com/blog/29/08/2018/longevity-dividend-how-ageing-populations-could-boost-economic-productivity, 访问日期:2022年3月6日。。
第二条是以生物老年学为学科基础的健康生命延长(the Extension of Healthy Life)路径。如果说上一条社会科学的基础路径更为关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红利面向,那么这一条交叉学科视角下的前沿路径更偏向于探讨如何实现长寿。正如美国老龄研究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for Aging Research,AFAR)对长寿红利的界定:以探索生物衰老的本质及内涵为目标,从根本上预防、治疗、推迟甚至抑制衰老相关的疾病,以此节省医疗开支与延长人类寿命,这种延缓生物体衰老而获取的收益被称为长寿红利(20)American Federation for Aging Research. What is the Longevity Dividend? https://www.afar.org/what-is-the-longevity-dividend, 访问日期:2021年9月23日。。近十几年来,学术界致力于从人口经济学的人口红利到公共健康领域的长寿红利的概念转变与路径实现。《科学》(Science)杂志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人口结构变化下关于老龄化的担忧似乎被夸大。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体可以自然地适应人口老龄化,强调健康预期寿命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预测变量,更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指征(21)Bloom D., “7 Billion and Counting”, Science, 2011,29, pp.562-569.。从2006年长寿红利的概念在《科学家》(TheScientist)杂志上第一次被提到(22)Olshansky J., et al., “In Pursuit of the Longevity Dividend”, The Scientist, 2006,20, pp.28-36.,到2010年和2013年《公共政策与老龄化报告》(PublicPolicy&AgingReport)分别刊发“21世纪的老龄化、健康与长寿”(23)Olshansky J., “Aging,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Public Policy & Aging Report, 2010,4, pp.3-13.与“阐明长寿红利”(24)Olshansky J., “Articulating the Case for the Longevity Dividend”, Public Policy & Aging Report, 2013,4, pp.3-6.的主题讨论,再到2015年冷泉港实验室出版《老龄化:长寿红利》的权威论述(25)Olshansky J., Has the Rate of Human Aging already been Modified?, Aging: The Longevity Dividend, Olshansky J., Martin G., Kirkland J. eds, Longisland: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2015, pp.221-239.,这一概念始终在深化与完善。可以认为,长寿红利的学术概念已经从衰老生物医学的前沿研究走向一种新的公共健康行动(26)Olshansky J., “The Longevity Dividend: A Brief Update”, Public Policy & Aging Report, 2019,4, pp.116-118.。换言之,在老年学家、生物医药学家和多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对长寿红利的探索不仅是确立与寻找人类衰老分子标志物及其阻抗药物,更是以延缓衰老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与预防干预的治理新防线。
综上所述,长寿红利概念描述的是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一种全新理想图景,表现为人类在寿命延长与健康提升的状态下,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和经济增权赋能,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老年歧视所可能取得的经济社会新机会及文化重建构等人类福祉与发展增益。
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发展对于厘清人口老龄化是危机抑或时机的争议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涵。首先,长寿红利的概念具有长远性,避免以直接负担或短期压力看待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效益。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因劳动者年龄增长可能产生的养老与医疗等现实负担,以至于无法全面看待老年人所提供的社会经济贡献。其次,长寿红利的概念具有辩证性,并非一味地从经济产出的标准来框定“红利”的范围。长寿红利之所以没有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并不否认人口老龄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更多地是从广义社会经济效益看待革命之后可能产生的历史性飞跃与革新。在现实性上,长寿红利是老龄社会中一切健康、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效益的总和。再次,长寿红利的概念具有整体性,超越了对社会群体以某种标准进行机械划分的简化论做法。长寿红利有别于以年龄结构为基点的人口红利,也有别于以性别结构为区分的性别红利,这一概念既不是量的划分,也不是一种社会类别的标定,而持有一种以“今天的年轻人亦是明日的老年人”的普遍性立场,这种老龄命运共同体的立场旨在遵循人类生存与寿命延长的根本利益。
四、中国情境下长寿红利的全景式理论转向
长寿红利是由“长寿”与“红利”两个词语复合构成,因此其概念内涵与理论话语应从“如何实现长寿”以及“长寿社会如何释放红利”两个层面共同展开。在中国语境下,学界、政府与实践界对长寿红利的理论探析都处于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之中。从老龄健康研究的蓬勃发展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 “健康中国”战略,充分彰显中国在探索“健康长寿”议题上的积极努力。然而,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理论界对于中国如何释放“长寿红利”仍缺乏较为系统的概括总结。从概念路径的分析可知,长寿红利是一个在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学科中都具有深刻意义的理论术语,内在蕴含着人本思想、经济属性以及生命体延续等内涵要素。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过程中,既需要强调对长寿面向的继续巩固,也需要增强对长寿红利的理论转向,为相关领域实践工作提供新的启示。

第一,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养老压力到银发经济的重大转向,以老龄事业与产业的供给侧改革适应老龄社会经济新常态(27)牟新渝:《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契机释放长寿红利》,《社会福利(理论版)》2015年第10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培育养老新业态。”长寿红利从经济发展新动能视角支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国家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讨论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路径,以转变老年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考察双循环带来的老龄化发展机遇,以此在可持续的养老社会中建构银发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意义(28)杜鹏:《建设可持续的养老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2月19日,第23版。。需要指出的是,长寿红利理论范畴所指的银发经济,不仅包括老年医疗保健产业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等老龄消费市场开发,更是一种全方位、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理念创新。长寿红利的经济效应并不完全刻意打造老年人专用产品,虽其本意是尽可能贴近老年需求,但更应旨向对全生命周期中各年龄段人群都具备吸引力的全龄事业与产业,以此打破养老压力与银发经济之间的现实对立,从更高层次的理论视角上予以弥合,以积极思路开辟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经济“新蓝海”。
第二,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年龄偏见到累积优势的重大转向,以新视角看待既有人口红利理论,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长期以来,学术界以分年龄的人口结构及增长率解释人口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试图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的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奇迹。长寿红利的理论转变突破既有人口红利中暗含的年龄歧视因素,从生命周期的累积优势理解老年人在经济活动与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有研究将这种老龄人口红利定义为老龄人口在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等方面组成的经济贡献率(29)杨燕绥、李学芳:《创造老龄人口红利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载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第七届北大赛瑟(CCISSR)之保险、金融与经济周期论文集》,2010年,第456-463页。,也有研究从老年人力资本红利、老年劳动参与红利和老年消费需求红利分析老年人口红利的构成逻辑(30)李连友、李磊:《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 释放中国老年人口红利》,《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8期。。虽然不同学者对长寿红利的具体界定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共识在于充分肯定老龄人口的经济贡献,将长寿红利视为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为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新的人口机会窗口。
第三,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治疗疾病到延缓衰老的重大转向,以凸显生命意义增强理论分析的跨学科性。长寿红利的理论概括超越了健康预期寿命理论中关于疾病压缩与疾病扩张的固有争议,回应人类生命科技的最前沿问题。放弃以疾病治疗与康复为主线的传统老龄问题应对思路,相反在不改变遗传物质的情况下,以早期预防和衰老干预的全新方向看待人类寿命延长的可能性与可及性。1992年起始的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尝试使用微观仿真数据模型比较延迟癌症、延迟心脏病、延迟生物老化以及延迟社会老化的四种假设方案,分别计算50年间治疗疾病与延缓衰老的社会经济成本差异(31)Goldman D., et al., “Substantial Health And Economic Returns From Delayed Aging May Warrant A New Focus For Medical Research”, Health Affairs, 2013,10, pp.1698-1705.。结果发现,由于相互竞争的风险,分别治疗某一种疾病的收益并不显著;相反,延缓衰老成为预防疾病发生、延长健康寿命、改善公共卫生以及减少社保支出的综合方法。据估计,延缓衰老将预期寿命延长2.2年,并且增大健康余年的占比,将使美国社会产生7.1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1998年启动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发现,若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平均每年改善1%,到21世纪中叶将节约家庭照料成本2.2万亿元(32)曾毅、陈华帅、王正联:《21世纪上半叶老年家庭照料需求成本变动趋势分析》,《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再考虑到可减少的医疗成本,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红利。此外,我国在自然科学界小分子化合物和药品方面取得的重要技术进展也使人类延缓衰老成为可能,清除衰老细胞延长肌体寿命、细胞重新组编等技术取得重大科学突破(33)刘尊鹏、张维琦:《衰老生物学:寻找人生“不老药”》,《光明日报》2017年2月23日,第13版。。
第四,中国情境下的长寿红利强调从社会包袱到生命成就的重大转向,以“老有所为”转变老化态度(34)郭秀云:《如何促进老有所为收获“长寿红利”》,《国家治理》2021年第39期。,探讨人口老龄化视野中不可预期的晚年馈赠。关于衰老过程一系列负面的老化感知与评价,既有来自个体的自身感受(Self-Perceptions of Aging),也有群体的刻板印象(Age Stereotypes),无论来自主观还是客观,这种相对消极的老化态度不一定是真实状况,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一些长寿红利的个人事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老年保守主义的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晚年生命成就的长寿红利已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发展(35)Diehl M., et al., “Awareness of Aging: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an Emerging Concept”, Developmental Review, 2014,2, pp.93-113.。例如,描述老年阶段将更多行动与资源投入到情绪上更有意义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ST),再如论证晚年情境具有补偿效应的选择优化模型(Meta-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SOC),还比如关注晚年实现自我目标的生命发展阶段理论(Models of Life-span Development)。上述理论不仅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长寿红利实现晚年生命成就的可能机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老年学理论视野中的消极判断与负面预设,也为长寿红利时代中国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框架(36)陆杰华、林嘉琪:《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战略视野及其行动框架》,《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五、借鉴与创新:国家战略定位下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
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集中体现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策表述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37)《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3/content_5642301.htm, 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3日。。其中“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既是新时代老龄工作始终贯穿的主线(38)《国新办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7917645.htm, 访问日期:2021年12月9日。,也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的核心纲领,更是中国释放长寿红利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国家战略的定位下,使命提升与内容转型的中国方案需要一个更为宽广的借鉴与创新的视角,既要站在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与宏观驾驭中国发展道路的大使命中去思考,更要置于人类寿命延长的大历史与世界老龄化的大进程中去破题。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与应对策略,始终伴随着与西方老龄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对照与比较、迎合与批判、吸收与升华;当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将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借鉴与创新中影响西方理论界的审题运思与文论探索。
第一,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发展性的逻辑关系下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践创新与发展递进。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社会以来,国家在应对老年负担上推出了系列举措,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重新修订到《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出解决老龄问题的中国力量。国家战略定位下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力量的壮大,在养老服务、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支撑、人才培养与环境氛围等重大工程的协调并举下展开,这种从负担到红利的转变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推进,更是体制的再构与战略的发展(39)朱荟、陆杰华:《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念突破、脉络演进与体制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
第二,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战略性的价值导向下开启了从关爱老年人中国行动到老龄社会中国战略的新征程。老年负担的行动策略具有专业性、类别性与技术性,长寿红利的战略方案具有基础性、广泛性与政治性。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中国老年人来说,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演进过程,是他们从完成本职工作退休到为国家发展奋斗终身的价值升华。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不仅是对老龄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是对老年人作为资源的再次肯定,更是对中国人口实力的进一步阐释。
第三,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基于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在具体议程设置中减少老年人就业障碍,鼓励生产力技术创新和投资终身学习机会等,以开创性展示中国特色。国家战略定位下释放长寿红利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主动构建的争取过程。以往的实践路径大多数以老年负担为框架,因此关于老年人口的膨胀将给养老金制度和医疗卫生系统带来压力的民众隐忧与政策焦虑挥之不去。相反,长寿红利的实践议程在延续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的方针下,支持老年劳动力跨越代际数字鸿沟(40)邱泽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跨越代际数字鸿沟》,《群言》2021年第6期。,在技能与知识上增能赋权,实现老龄社会的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在全体性的内容设计下关涉全体社会成员,是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去构建方案内容。老年负担关注老年群体,尤其是以体弱病残或无劳动能力的视角看待这一群体,长寿红利概念所向是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这决定了两种理论视角在内涵上的本质差异,涵盖概念主体及其社会价值的不同,将引向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意义的基本判断有别。因此,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更具道义感召与责任担当,极具中国话语优势。

总之,“长寿红利”的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龄工作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实践(41)胡鞍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征和意义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更是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中国老年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锚定。当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具有深远影响,其复杂性与应对策略并非通过转换概念术语及理论范式就可以完全解决;长寿红利作为一种新兴概念,其自身成熟度、理念感召力和实证应用性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展望未来,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的研究转向应渐臻佳境,在概念精确、理论完善、指标测量、机制分析和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传播中国声音。构建与国家战略全局地位相配合、与中国老龄化加快加深的新国情相适应、与两个百年征程伟大复兴相匹配的长寿红利中国方案,为全球老龄共同体展现“长寿中的中国”“红利中的中国”和“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