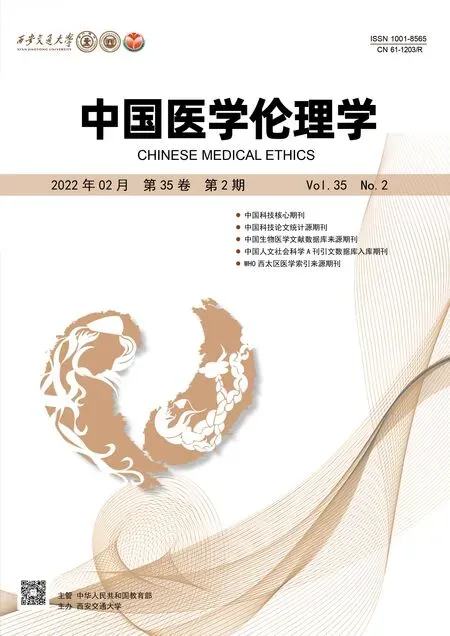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安宁疗护*
王治军,周 宁,路桂军
(1 廊坊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wangzhijun1968@126.com;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疼痛科,南京 210002;3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北京 102218)
在中西方文化中,都会对即将走向终点的生命给予人道的关怀与照护,对生命自始至终充满尊重与敬畏,让每一个生命有尊严有价值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文化背景与信仰上的差异,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对于临终、死亡乃至死后世界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临终之人的心理、社会和精神的需要也有很大不同。所以,这种关怀和照护除了具有一般性外,还具有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对于这一认识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概念上,西方称之为“临终关怀”,中国香港地区称之为“善终服务”,中国台湾地区更愿意用“安宁疗护”。我们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才能对这样一个概念做出全面而精准的诠释,建构出中国特色安宁疗护理论与实践。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建构现代化的安宁疗护,不仅要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本土思想资源,解决中国人的生死困惑,安顿中国人的身、心、精神层面需求。基于此,本文力图在分别梳理中西方临终关怀照护传统的基础上,将两者做一对比,期望能够建构一种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怀照护理论与实践。
1 西方临终关怀的产生及其特征
西方临终关怀最初源于基督教的宗教式关怀,是以人如何克服病痛的苦难、坚定信仰、重返“上帝”的怀抱作为关怀的终极追求(本文中的基督教是广义上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从医学角度来说,临终关怀又属于广义的医学护理,是对处于生命临终阶段患者的特殊护理。
1.1 西方临终关怀的产生
西方有学者指出[1],有组织的护理活动就是源于早期的基督教会,当时的教会团体非常重视患者的身心需要。即便是到了中世纪,护理依然是一个具有神圣使命的行业,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南丁格尔大力推动护理与医院相结合,护理行业才日渐世俗化为大众服务。她本人所接受的护理训练,是来自一位德国新教牧师所设立的宗教护理训练机构,她在1860年所创办的世界第一所专门接受女性的科学化的护理学校,隶属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另有研究表明[2],护理人员对于临终患者的关怀和遗体护理也由来已久。就词源学而言,临终关怀的英文hospice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朝圣。有慈善者在沿途修建了许多为朝圣者休息、充饥和养病的驿站。在这些驿站,病重和濒临死亡的人会得到教士和修女的治疗与照顾,死后的尸体也会得到妥善的处理。hospice与hospital(医院)、hostel(客栈)同源于拉丁文hospitium,意为“小旅馆”“客栈”或提供膳食和住宿的“住所”,同时也代表对客人的热情接待,表示主人与客人之间亲密、善意、友好的关系[3]。
到了十九世纪,朝圣者不再需要这些休息站了,人们便把它们改造成专门照顾无法治愈患者的机构,为他们提供精神照顾。在1879年,都柏林修女玛丽·艾肯亥将其修道院主办的hospice用作专门收容癌症末期患者的处所,以宗教的爱心来关怀照顾他们。1905年,伦敦市的爱尔兰天主教修女院,首先使用hospice来命名照护临终患者的机构,并专门收容癌症末期的患者。此后,这类机构纷纷建立,比如1885年建立的“圣天鸽座收容所”,1892年由妇女慈善团体建立的“上帝招待所”和1893年由巴特勒医生创建的“胜卢克济贫院”及“圣约瑟夫临终关怀院”。在这一时期,此类机构的宗旨,主要是用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来关怀患者,还没有与医学诊疗手段结合起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圣约瑟夫临终关怀院的一名护士西西里·桑德斯发展出对患者进行“全人照顾”的理念和做法。1967年,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化的兼具医疗科技及爱心照顾的“圣克里斯多夫临终关怀院”(St.Christopher’s Hospice)在伦敦郊区建成。桑德斯认为,临终者仍然是一个活人,所以不仅要关怀他的身体,还要关怀他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不仅要关怀他的个体,还要关怀他的家人。事实证明,比病痛更令临终者感到害怕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那种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与此相反,如果他能感受到别人的关注与理解,则会产生一种快慰感。圣克里斯托弗临终关怀院秉承三个基本理念:一是控制病痛和痛苦;二是从生物、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承担起对临终者的责任;三是使死的过程自然化而不至于被夸张。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临终关怀医院的出现,具有悠久的宗教传统[4]。
1.2 西方临终关怀的特征
通过对西方临终关怀产生与发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其典型的特征。临终关怀的宗教背景,是对上帝虔诚信仰的基督教。基督教是一种神爱的宗教,神爱是基督教信仰的灵魂,基督徒坚信上帝是爱人的神,而耶稣基督则是神对人的爱的具体体现[5]。每一个基督徒都坚信,他们效法耶稣服侍主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对上帝给予的无私之神爱的回应,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神的肢体,就是让“圣精神”在自己身体里面做工(即与神同工),藉此必定可以得到神在天国里给予的荣耀。因此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神父和修女,都是以耶稣的奉献精神为榜样和楷模(即效法耶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尽心尽性尽力从身、心、精神层面等各个方面照顾患者。处于终末期的患者也是基督徒,他们最终能够克服困难,坦然面对生死。近代以来,临终关怀医院的建立是源于照顾癌症末期患者的需要,照顾护理患者的手段与方法是源于照顾一般患者的技术和经验。不同点在于,后者以治愈疾病为宗旨,而前者则以提升终末期的生命质量为宗旨,不以延长生命为目的,是一种保守的消极的缓和医疗(palliative medicine),而不是积极的侵入性的医疗。这种医疗护理的着眼点,在于为患者提供疼痛控制和症状管理,提供心理和精神层面支持,陪伴患者有尊严地离世。
2 中国传统的善终理念与关怀照护实践
中华传统儒释道信仰、民间习俗和丧葬礼俗中充满了关怀照护临终患者的理念和经验,我们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概念,但是我们具有养老送终的悠久历史,且是传统孝道的重要内容。下面以传统儒家的善终理念和信仰习俗为例说明。
2.1 传统儒家的善终关怀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生命临近终点的历程,应在温暖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的陪伴下度过,这源于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文化,生老病死以及生命的传承都依靠家庭。善终关怀就是帮助临终者走向安详的死亡,实现死而无憾,帮助家属正确面对亲人离世,化解丧亲悲伤。实现临终者死而无憾是传统社会的终极诉求,这集中表现在中国人的“五福”观念。五福源于《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考终命”就是善终,能够实现心平气和、坦然无惧的死亡。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全社会都关心照顾老人,形成了赡养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为了让老人实现善终,家庭和社会对于老者的关怀,开始于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赡养,延伸到死后的丧葬和定时祭祀。
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诸多关于夏、商、周三代养老的论述。关于养老的地点,《礼记·王制篇》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关于养老的礼制,《礼记·王制篇》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这种礼制在《礼记·文王世子篇》和《礼记·内则篇》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在《礼记·祭义篇》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天子在大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以教育诸侯尊老敬老;天子到各地巡狩,都要去拜谒八九十岁的老人等。
儒家的孝道观念不仅强调对于老者的赡养服侍,而且强调要把感恩回报延伸到生前死后,把丧葬祭祀也看作是孝道的重要内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孟子尤其重视老百姓养老和丧葬问题,他提出“养生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特别强调丧葬的重要性。宋代大儒朱熹注曰:“事生故当爱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于送死,则人道之大变。孝子之事亲,舍是无以用其力矣。故尤以为大事,而必诚必信,不使少有后日之诲也[6]。”在父母有生之年奉养他们,只是为人之道的常行,不能算是人生的重大事情。而死亡是一次性的,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对父母的临终照护乃至丧事料理,必须慎重行事克尽孝道,如果留下了遗憾将无可挽回。孟子还提出“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从政治高度来看待民众的养生送死。也就是说,老百姓死的没有遗憾、身后丧葬事宜有保障,是政治必须首要予以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国家稳定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汚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其实质,就是主张社会财富应当首先用来保障民众的生养死葬,让百姓生死两安。
荀子尤其重视生死安顿问题,强调丧礼的重要功能就是避免人们从功利心出发,对临终之人乃至死者不恭敬不忠厚,乃至厌烦厌恶。隆重庄严的殡葬仪式,就是为了实现生死始终如一,实现人的终始俱善。“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荀子·礼论》)如果没有礼制的保证,人们都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只重视生而轻视死,社会伦理道德将彻底沦丧。《孝经》则详细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不仅把生养死葬按时祭祀作为孝道的内容,而且强调了病痛中的悉心照护。《弟子规》中“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则对悉心照护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要求。
从上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家一直秉承生事爱敬、死事哀戚、视死如生、视亡如存的理念。这种世代相传的理念,保证了老人能够在家庭中得到很好的赡养,在病痛中得到很好的照护。在临终和初死时,还有“随侍在侧,亲视含殓”的习俗规定。这种从生前到死后,照料始终如一的传统美德,让老人可以心安,不用忧虑病痛中的孤独与凄苦,也不用担心身后事宜,从而可以实现了无牵挂的安然离世。对于那些缺少家庭照顾的人,传统文化也充满了关怀。根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在周文王时就有对这些人的特殊照顾。“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礼记·礼运》大同篇中的论述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让这些人在生时无衣食之忧冻馁之虞,在他们年老时实现老有所终,能安度晚年,始终是中华文化的终极追求。《礼记·王制篇》记载,西周时代不仅有了专门的养老机构——庠、序、学、校等,而且明文规定鳏寡孤独“皆有常饩”,也就是有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到唐朝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由佛教寺院管理的养老制度。到北宋时期,政府设立了福田院。与唐朝不同的是,这种福田院已经脱离了与寺院的关系。到元代,则出现了“惠老慈济堂”,通过购买田产、收取地租以供养堂内老人。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首先在北京设立了普济堂,并要求地方政府仿效。普济堂接收老年贫民,视其经济状况而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平。在这些机构里得到照顾的老人,大多在死后能得到宗教仪式的殡葬服务[7]。这种政府性养老结构的存在,是实现善终的一个重要保障。
2.2 民间信仰与习俗中的善终关怀
除了在观念上重视养老与善终以外,在民间信仰和习俗上还有一整套的学说和仪式仪程,来关怀处于生命末期的临终者,帮助他们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感,在温暖的照护与关怀中走向人生的终点。民间信仰认为,活着的人在阳间,死者到阴间冥界,甚至在通向冥府的路上,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比如奈何桥和孟婆汤、恶狗村与打狗棒,就从信仰上为死者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归宿,化解了死后的虚无,克服了死亡的恐惧。这种文化上的建构与宗教的天国、极乐世界的终极关怀作用是一样的。与宗教信仰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还重视身后事宜的安排,比如寿衣和棺木的提前准备,良好风水的坟茔的准备,以及对于后人按时祭祀的期望等。
在各地的民间习俗中,人们都非常重视家中老人去世后的相关准备。有些地区的老人不仅不忌讳自己的百年身后事,甚至还和子女共同策划建坟墓、制作棺材和缝制寿衣等事宜。民间为生者建好的坟墓称之为生坟、生基、寿穴、生圹、寿域、老屋等。家中有年事已高的老人,子女必定给他准备棺材,或称之为寿材,以备不虞。寿材做好后,一般放在宗族的祠堂中,不轻易移动[8]。人到了六十岁就开始准备寿衣,可以由子女为老人准备,也可以老人自己准备。衣物只是备料,一般是年过七十后才做,这是因为年过七十而亡者为喜丧。北方民间,老年人的寿衣多由已经出嫁的女儿在有闰月的年头做好,暗寓哪年哪月也轮不到自己用这套寿衣,间接寓意长寿[9]。
家中老人病重弥留之际,在家的人停止劳作,在远方的直系亲属迅速赶回家,大家聚在老人身边,陪伴老人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送终特别重视儿子、孙子等男性直系后辈的在场,尤其是长子长孙不能缺席。最后是临终搬铺,将临终老人从睡觉的床上或炕上搬移到正堂或客厅。这种习俗在很多地方还保留着。在福建叫“打厅边”或“上厅边”,在中国台湾地区叫“移水铺”[10]。这种在家中厅堂的去世才是“寿终正寝”。因为正寝或正堂是家中供奉历代祖先神灵牌位的地方,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最为神圣庄严,能够与祖先神灵沟通。在这个特定场合,完成对后代子孙的告诫与勉励,安然离世,无愧祖宗和子孙后代,在浓厚的亲情中安然瞑目,这才是真正的“善终”或“寿终”,这是生命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是一种生命自然而然的终止。个人生命虽然丧失,而其血脉亲情在家庭、家族内永存。这种死亡不是毁灭,而是家庭、家族大生命延续的一个环节。这种善终,不仅减轻了死亡带给人的孤独、无助、恐惧和焦虑,而且使死亡充满了家庭的关怀和人情的温暖。
2.3 关怀照护实践中的经验积累
在对临终老人照护过程中,通过细心的服侍与对病情的长期观察,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民间老人中口耳相传,很多还没有通过有逻辑的专业语言的表述,没有通过科学话语的论证,到目前为止仍然得到医疗界和学术界等具有主流话语权的承认。
尉迟凎[11]通过长期的观察,总结了临终之人心理生理的变化。生理上出现包括脸由红转黑、眼睛空洞对外界丧失反应、呼吸不再正常乃至进入若有似无、双腿肿胀以及出现回光返照等现象。心理上出现幻视、幻听、第六感的预知反应以及反复交代遗言等回光返照的征兆。而这些话语,在民间是辈辈流传的,几乎所有照顾过临终老人的都知道。再如,民间有“男怕穿鞋女怕戴帽”的说法,就是说临终之人,一旦到了头部和足部发生大面积水肿,没法穿鞋、戴帽子了,距离生命结束也就不远了。用现代医学的话语表述,就是身体的代谢功能已经衰竭,尤其是肾功能衰竭的一种表现。又如,民间奈何桥和孟婆汤的说法,认为过了奈何桥,喝了孟婆汤,就到了阴间的入口。用现代医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人在身体衰竭到一定程度时,意识就消失了,心智自我就分散了,只是剩下了肉体的生命特征,进入了一种余德慧所说的“存在但是却没有了世界”的状态(医学术语叫作醒觉昏迷),所以人死时是没有苦痛感觉的[12]。我们平时以为的死亡,都是心智自我制造出来的,是活着的人对于死者的一种想象[12]。民间还有关于临终之人味觉改变、味道流失、视觉减退、不认识亲人、听觉变得更加敏锐并最后消失等经验。余德慧对此类现象有深入的临床研究,从心理学和医学等方面证明了民间经验的正确性。
关于临终之人复杂的心理状况,民俗也多有观察,而且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比如不同丧葬用具置办的时间差异,就很能说明问题。基于对老人后事的重视,难以一时具备的应当提前准备好,减缓老人对身后事的牵挂。比如棺木,就应该提前准备好,防止亲人突然去世而措手不及。而那些比较容易置办的,比如敛衣、衾被等,就不能提前都准备好。一方面是没有必要,另一个方面是孝子不忍心亲人很快离去。比如《礼记·王制》和《礼记·内则》都记载:“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紟、衾、冒,死而后制。”意思是年六十的人每年都要准备丧具,年七十每季都要准备丧具,年八十每月都要准备丧具,年九十每天都要准备丧具,只有入殓时用的绞带、衾被和冒,是到人死后才赶制出来的。《礼记·檀弓上》记载:“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因为对亲人依依不舍,加上期盼疾病能够康复,所以容易具备的丧具不提前准备。这充分考虑到了老人的心理感受。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科学的普及和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传统的善终关怀话语渐渐式微。八九十年代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生命末期的质量的追求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于是西方的临终关怀理论被引进和介绍到中国来。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孟宪武教授提出“全人全程全家临终关怀方案”[13]。他主张:对患者的关怀应该是全人关怀:不应当只是局限于身体的痛苦,还要关注心理、精神、情绪上的忧郁、悲伤或绝望;不应当只是关心他疾病的治疗情况或症状的控制情况,还要关心他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方面的困难;不应只是尽量满足他缓解症状的要求,还要满足他们的一些特殊要求;对临终患者要提供全程服务:包括审慎决定是否把病情告诉患者、给临终患者诀别时间、认真实施临终护理操作、做好遗体安置等;对临终患者全家提供服务模式。在临终关怀中,医护人员在关怀好临终患者的同时,也要做好对临终人家属的关怀照顾工作,特别是在患者死亡和死后的一段时间,要使家属能够加强自我护理,承受丧失的打击,以适应新的生活。孟宪武这一提法的独特性就在于对家的重视,他将临终者置身于家庭中,将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了患者家庭,还将关怀延伸到了死后,包括遗体的处理和殡葬服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关怀向度,凸显了中国特色临终关怀的本质特征。
3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异同
正如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说,安详地去世是一项重要人权,可能比选举权或公平还更重要。很多宗教传统告诉我们,临终者的精神未来和福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权利。没有哪一种布施的意义大过帮助一个人好好的死[14]。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与西方基督教一样,都是关怀生死的生命智慧。但是由于信仰上的区别,导致了中西方关怀照护理念上的诸多差异。
3.1 实施关怀的文化基础的差异
人具有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多个层面的需求,因而为了满足患者的精神需求的照顾就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位护理学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与艾滋病末期患者相处,围绕着精神层面与维系生命的希望这个主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5]。是什么力量让绝症患者在生命末期维持希望?维持他们生命存在的又是什么希望?护理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学者[16]进一步研究指出,护理工作为患者所带来的主要是一种宗教的和道德的承诺,这种承诺让患者感到病情有改善的希望,即使是绝症患者,也可以感到痛苦得以缓解,也可以对善终抱有希望。另外有调查显示[17],护理人员把患者精神需求的顺序确定为:信念与信仰、平安与舒适、关爱与宽恕、意义与目的、希望与创意,其中信念与信仰的需求高居首位。这项调查显示,宗教信仰和个人信念可以为受苦受难的患者带来精神解脱,而护理人员必须高度重视患者的精神层面需要,有针对性地予以照顾和满足。以上的几个调查研究,都是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士开展的。对于西方临终关怀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我们看到,西方的临终关怀理念建构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其关怀的思想资源在于基督教,其方法是源于医学和心理学的治疗与护理,其关注患者主要是在生命末期,在临终阶段,所以叫临终关怀。其重点放在技术手段上,因为从精神层面上给予信仰上的关怀是基督教信仰的题中应有之意,根本无需强调。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建构在传统儒释道相结合的孝道文化基础上,在家庭和家族范围之内,通过血缘纽带和传统习俗来维系。中国传统的关怀照护,从时间上讲,不仅仅局限在临终阶段,还包括病重阶段和死后的整个丧葬过程,以实现老人身体安康心灵宁静为宗旨,所有的医疗护理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范围上讲,不是局限在病痛者个体,而是囊括其所有的家庭至亲。所以,从概念上讲,中国特色安宁疗护,既有源自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之根,又有当代国家政策指引支持鼓励,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总结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安宁疗护,而不是西方的临终关怀。
3.2 参与照护的人员的差异
在西方的临终关怀中,所有参与人员和被关怀照护的对象,都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性的承诺与护理息息相关。在古代,参与关怀和照护的人员是基督徒神职人员。在现代社会,给予人精神层面的关怀,除了牧师、修女、神父还有心理咨询师,但是心理咨询师也大多是基督徒,从事专业照护的医生与护士也大多有基督教信仰。他们为人做事秉持的理念,就是“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这样一种奉献精神。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基督宗教信仰正是关怀护理形成的动力,也是生命关怀与心灵慰藉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切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庭和睦、传承、互爱、尊长爱幼为宗旨。在病重、临终时,都是子女至亲陪伴左右,亲朋好友探望关怀。西方人从基督徒身上得到上帝的关怀与博爱,是一种自我想象的爱,而中国人则是从家庭亲友的现实状态中感受到实际的、可触摸感觉到的爱,从而得到温暖和安顿,例如千里奔丧。因此我们的医疗护理,一定要考虑到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能照搬西方。
3.3 关怀的着眼点的差异
护理即将走向人生终点的患者,这个工作是极其复杂的。需要护理者与被照护对象在高度平等、亲密和无私敞开的情景下,才能了解到患者身体、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多重需求,体察他们的精神层面痛苦,进而通过护理过程予以解决。因此,满足患者的精神层面需求,乃是提供整体护理照顾的最基本的部分,而不是额外的可有可无的服务[18]。正是这个精神层面的需求,是我们和西方临终关怀理念的最大差异。基于这种信仰上的差异,中西方关注的着眼点不同。西方人更多的是关注个体。因为在死后上天堂与上帝同在,有上帝对他进行永恒的关怀,所以人的关怀到此为止。与之相比,我们的精神关怀不是局限于临终而是全程的,延伸到生前死后,包括身后事的处理,以及丧葬祭祀等一系列过程。更为重要的,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所以关怀的对象还包括全体家人,尤其是作为至亲的父母和子女。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的家庭和西方人的“上帝”,发挥着同样的功能。
3.4 关怀照护手段的差异
对临终患者的照顾护理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这种专业化的服务应当包括身体上、认知上、道德上和情绪上的种种作为,要求护理者对服务对象身、心各方面需求有所回应。所以,这种关怀和照护,不仅包括情感信仰表达上的关心,医疗保健和工具性的照顾手段也同样必不可少。中西方由于信仰差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关怀照护实践。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通过父慈子孝观念教育民众,传承养生送死丧葬祭祀等一系列程序的善终理念,并且已经落实在实践行动中,形成了家庭文化的代际传承,形塑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注重养生送死的风俗习惯。这一观念在广大民众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与此相对照,西方的临终关怀,主要体现在临终前的护理及宗教关怀。就治疗与护理的具体手段而言,差异还在于我们是以中医为主要医疗手段,以家庭亲情为情感照顾,更多关注丧葬及哀伤过程。比之于西方,临终前的医疗则相对欠缺。所以,在当前必须以西医的口服药物和注射输液等作为补充。1988年崔以泰引进临终关怀概念,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提示我们积极借鉴西方的疗护手段,尽快实现与中国传统善终理念有机结合。
4 小结
在当今老龄化社会,如何安顿照顾严重病症甚至绝症患者,使他们不感到孤独无助,能保持生命的尊严,在死亡来临之时不致感到恐惧不安,乃至能从容自然走到人生的终点,这是当前中国安宁疗护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西方商品化社会导致的过度治疗,避免西方老龄化社会对衰老与死亡的漠视,积极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缓和医疗和护理手段,补充和完善中华文明中的善终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挖掘传统的养老善终文化,继承“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优良民俗民风,建构我们自己的安宁疗护理论与实践话语体系,拒绝简单照搬国外理念和模式,尤其拒绝以西方的视角审视和评价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所秉持的理念和宗旨,是尊重中华传统文化,西方当代先进理念和技术仅仅是对中国特色安宁疗护中医疗技术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中国传统。我们应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安宁疗护,是起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善终,吸收现代中西方医疗技术的进步,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足人民提升美好生活的愿望,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民生大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安”是身体的安泰安康安详,“宁”是内心的宁静宁和宁谧。所有的医疗护理都应当以此为终极追求,实现终末期生命的安宁,实现整个家庭的安宁,实现临终者在温情脉脉的团聚中离世。所以,我们当今的疗护,既要看到临终的个体,也要看到他所在的家庭,把他看作是家庭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看作从祖先到子孙的家族生命链条中的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做好临终阶段的照护关怀服务,更要提前做好生死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辨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安宁疗护才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