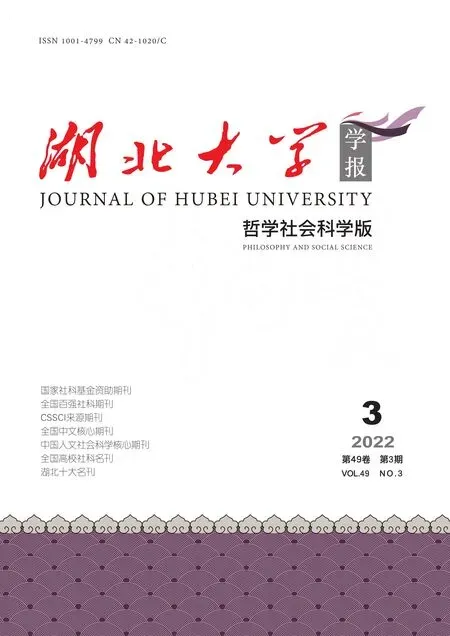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洪迎华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京”者,天子之所居,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四方所向、人所都会,同时也是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1)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11页。作为政治轴心和文化的标征,京城自古是名利追逐之地,也是文人士子施展才华、实现功名理想最好的舞台,故士人眷念京城,于历朝历代并不鲜见。但在唐代,这种情绪在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人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甚至说:“故园梨岭下,归路接天涯。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95页。如此强烈的心声不能不引发我们关注和思考:为何唐人如此眷念长安?这背后的时代动因是什么?它在唐代士人身上如何得以具体体现?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翻检唐代诗歌,我们也发现,这种情绪常成为唐人诗歌创作的诱因,从而使得恋京诗在唐诗中蔚为大观。而且,由于士人具体身份、生平遭遇和时代环境的不同,其恋京诗在情感强度、心理内涵和艺术表现上亦有所不同。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使我们对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相关诗歌创作有真切深入的认识。
一
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首先表现在那些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而不肯归家的普通士子身上。唐代沿习隋代科举制,而日渐完备。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士庶界限,为士子进入仕途广开门径,激发了他们积极求取功名的热情。同时也改变了自汉以来由地方举荐的察举制,各级官吏一并由中央核定和任免,都城长安自然成了唐人追逐功名的目的地,其吸引力比此前任何一个王朝的帝京都要强。每逢春榜,无数士子从各地涌向长安,其场景如张乔《秦原春望》所描绘的:“无穷名利尘,轩盖逐年新。
北阙东堂路,千山万水人。”(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7307页。如果在长安摘得桂冠,则可以春风得意,“金鞍镀了出长安”(4)章孝标:《及第后寄李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861页。。可在麻衣如雪的举子中,落第者毕竟是多数。赵匡《举选议》曾指出:“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5)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20页。这些失意者有的黯然归乡或另觅他途,有的则羁旅长安继续漂泊,动辄十载甚至数十载不肯归家。《全唐诗》卷八六六徐侃《留别安凤》题下记:“寿春人徐侃,与安凤友善,相期同觅举长安。凤先行,侃以母老中止。十年后,侃忽至长安,仍约凤同归。凤辞以久漂泊,耻还故乡。各为诗赠答,然侃死于家已三年矣。”诗云:“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6)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791页。徐侃和安凤两人,一者在长安漂泊十多年,未获功名“耻还故乡”;一者为了高堂不能在长安觅举,留下了九泉之下的遗恨,长安对唐代士人的莫大吸引力可见一斑。唐代像安凤这样因场屋困顿在京师长期漂泊的举子大有人在,即使能荣登科榜,他们还要面临铨选、升迁过程中的干谒和求进,其京城羁旅往往漫长而辛酸。他们常将身在长安的经历诉之于诗,如:
一官何幸得同时,十载无媒独见遗。今日不论腰下组,请君看取鬓边丝。(包何《寄杨侍御》)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钱起《赠阙下裴舍人》)
虚抛南楚滞西秦,白首依前衣白身。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魂离为役诗篇苦,泪竭缘嗟骨相贫。今日鞠躬高旆下,欲倾肝胆杳无因。(许棠《献独孤尚书》)
麻衣穿穴两京尘,十见东堂绿桂春。今日竞飞杨叶箭,魏舒休作画筹人。(唐彦谦《试夜题省廊桂》)(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2173、2674-2675、6985、7686页。钱起“霄汉长怀捧日心”,《全唐诗》原作“捧日新”,据《中兴间气集》、《才调集》改。
尽管有长达十载的献赋不遇和穷途之恨,依然长怀“捧日”之心、声称休作“画筹”之人,甚至苦心冥求“三十载”,仍然“欲倾肝胆”、不改其志,其对京尘的眷恋与执着让人扼腕。这些士人在京城不仅要承受屡次碰壁、失败的精神打击,同时还要遭受饥寒馁冻之苦、饱尝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天宝时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8)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5页。大和年间孙樵《寓居对》云:“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9)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31页。个中的坎坷与凄苦可以想见,而这样的情形在旅食京华的士子身上普遍存在。“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韩愈贞元十六年在《与李翱书》中痛苦地回忆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因有过切肤之痛,次年他在京师调选无成,又有一首《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诗,诉说漂泊长安的辛酸:“君门不可入,势利互相推。借问读书客,胡为在京师?举头未能对,闭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10)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1239、1387、103页。然而,即便京城充满“势利”、“寒饥”,居大不易,但仍有大批士子眷恋京尘,孜孜以求而不肯归去。白居易《长安道》云:“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11)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82页。蔡瓌《夏日闺怨》云:“君恋京师久留滞,妾怨高楼积年岁。非关曾入楚王宫,直为相思腰转细。”(1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764页。久滞长安的客子,不仅自己老了容颜、白了双鬓,同时也给家人带来了长期分离的幽怨与痛苦。
身不在长安的文人士子,其恋京怀阙的心绪集中表现在他们大量梦长安、忆长安、望长安的诗歌中。这些诗人曾经在长安游历、应举或为官,一旦因调迁、奉使、出塞、入幕、漫游等原因离开,长安便成为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和魂牵梦绕的地方。如李白离京后作《送陆判官往琵琶峡》:“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13)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851页。岑参任嘉州刺史时作《郡斋望江山》:“梦魂知忆处,无夜不京华。”(14)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3页。王翰出塞时作《凉州词》:“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戎昱寓居剑南时作《罗江客舍》:“近来乡国梦,夜夜到长安。”温庭筠初离长安在渭川时作《西游书怀》:“高秋辞故国,昨日梦长安。”崔涂羁旅至庐山时作《宿庐山绝顶山舍》:“自嫌心不达,向此梦长安。”(1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605、3008、6742、7779页。在唐代诗歌中,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因思念长安,他们会觉得自身与长安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在表达这种距离感时,唐人常将长安与自然界中的“日”意象进行对举,以书写遥望长安和想往长安的心理感受。如:
行路难,行路难,歧路几千端。无复归云凭短翰,空余望日想长安。(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16)骆宾王著、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浦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去去如何道,长安在日边。(王勃《白下驿饯唐少府》)(1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675-676页。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其一)(18)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第742页。
北海樽留客,西江水救鱼。长安同日远,不敢咏归欤。(张南史《早春书事奉寄中书李舍人》)
故国望不见,愁襟难暂开。……长安远于日,搔首独徘徊。(崔涂《春日登吴门》)(1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359、7774页。
无论望日怀京,还是直言长安比日远,皆传达出长安在诗人心中如同太阳一般高远、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感觉。这不仅诉诸唐代诗人对太阳的实际感受,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太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20)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释:《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60页。,即已将太阳与君王视为一体。之后,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下,“日者人君之象”、君日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太阳是天上的君主,君主是人间的太阳。长安作为天子居宅及权力中心,很自然与太阳发生了联系,故在这些诗歌中,“长安日”隐含着思君恋阙的心理意识,“望日”亦与“望君”、“望京”合而为一。事实上,唐诗中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因不得志而产生的心理距离。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其二云:“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21)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第742页。皎然《送陆侍御士佳赴上京》云:“长安三千里,喜行不言永。清路黄尘飞,大河沧流静。”杜荀鹤《出山》云:“处世曾无过,惟天合是媒。长安不觉远,期遂一名回。”(2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213、7926页。只要有机会回到京城进入修门为君效力,或者只要遂成“一名”,长安即使在三千里外也不觉远,甚至近在马蹄之下。可见,在诗人笔下,长安的远近已超越了时空现实距离,成为唐人衡量功名得失的一个心理标尺。崔涂《灞上》云:“长安名利路,役役古由今。”(2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7777页。白居易《无梦》云:“渐销名利想,无梦到长安。”(24)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1943页。没有了名利之想,也就不再梦及长安。“长安梦”,即功名梦。唐代士人对长安的眷念,也即对功名的眷念。
二
情感心理学认为:“眷念是具有稳定性质的一种情绪态度。它在个性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影响个人的行为;但是人具备的这种情感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表现为鲜明的、突然的体验。这是一种深沉而平和的情感。只有在条件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失去人所眷念的事物)才能因这一情感而出现强烈的体验。”(25)П·М·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王玉琴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页。如果说久寄不归的“长安客”和游离迁转在外的士人们对长安的眷念,是在人生相对平静状态下的一种“深沉而平和的情感”,那么眷念京城最为“强烈的体验”,则出现在因故贬逐、流寓而被迫离开京城的唐代士人身上。
唐代的科举制度尽管使文人士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政局多变、君恩无常,士人们的政治生命也时刻面临着因朝廷变故或个人罪责骤遭贬斥的危机。一旦获罪斥出京城,便意味着他们从自己所依恋的政治圈子和生存空间里被强制性地驱逐出来。个人处境和客观条件的急转而下,自然激化了恋京情绪的急剧增长,使其由“深沉而平和的情感”上升为“强烈情感”。心理学认为,人的情感除了内容有所不同之外,在强度上有明显的等级,“人所体验的情感的强度迅速增长,在一定时间内贯穿着人的意志,并在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中留下鲜明的印迹。……就此而言,在一定时间内控制了意识,并且构成意识主要内容的一切体验都是强烈情感”(26)П·М·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第44页。。对于被移远恶处的流贬士人来说,从离京赴任、踏上贬途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所以他们沿途赋诗,在日行渐远的行程中抒发对京国的不舍和恋阙望归的情绪。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27)沈佺期、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28页。崔湜《至桃林塞作》:“去国未千里,离家已再旬。丹心恒恋阙,白首更辞亲。”(2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666页。这些诗歌“除了感慨、泄怨以外,还有以诗代简,希望经传播以达圣听并获得同情和拯救的意图”(29)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最能说明这一意图的,是唐代文人在贬谪途中所作的题壁望归诗。如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岂意南中岐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30)沈佺期、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第433页。李德裕《盘陀岭驿楼》:“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复一开颜。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3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5416页。这些题壁诗因创作、发布于驿站、寺院等来往行人众多的公共空间,具有广而告之的传播效应,可以通过时人的观览和传诵播扬出去,让世者知其事、了其情。《旧唐书·宋之问传》即载:“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32)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5页。有学人就端州题壁现象解释道:“谪臣行经同地,先后留诗慰解声援。或许借着诗作的发表,共同形成一种声音,以期能够引起执政者的注意,矜怜悃忠,还得清白,获得释罪召回。”(33)严纪华:《试论两组与历史事件相关的谪贬题写诗——“端州驿题壁”与“玄都观题壁”》,《唐代文学研究》第7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这种观点切合贬谪士人眷念京城的主要意识,可以说不无道理。到达贬所后,一方面,因异地陌生、荒恶环境对身体的侵蚀和折磨,他们觉得生命得不到保障,心中自踏上贬途那一刻便如影随行的死亡恐惧感愈发逼近和真实;另一方面,人生的打击挫败,置身异地的文化隔膜和艰难不适,使他们备感精神的孤独苦闷。这双重的刺激和痛苦又会随时触发并加深他们内心对朝廷一罪永弃的忧恐,其恋京归阙之思益发浓郁和强烈。如沈佺期《初达驩州二首》云:“雨露何时及,京华若个边。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34)沈佺期、宋之问撰,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第95页。元和十四年因论佛骨事被贬的韩愈,到了潮州之后觉“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为了争取还朝,主动上表认错:“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35)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2308页。其哀怜望还之心,可谓恳切至极!
心理学认为:“人所体验的情感(暂时很难说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的强度不等。体验的时刻不同,体验的强度往往有一定的‘增’或‘减’。……人在体验最大痛苦时,眼泪会将情感‘转向’新的不甚紧张期,情感上的强烈刺激似乎会减弱。”(36)П·М·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第47页。随着谪居时间的延续和生命体验的加深,唐代士人恋京怀归的情感强度,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对有的士人来说,谪居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生命荒废感和沉沦此生的被弃感,其恋京的情感强度进一步“增长”,诗中思阙望归的声情在时间的累积中愈发哀怨凄厉,甚至转化为一种绝望无助的情绪,读之让人动容。如韦承庆《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戎昱《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梦随行伍朝天去,身寄穷荒报国难。北望南郊消息断,江头唯有泪阑干。”(3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557、3012页。而有的士人,如“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柳宗元(38)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943页。,“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的白居易等(39)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354页。,则在贬地以文史自娱、寄情山水、遁迹佛老的方式,努力将内心的苦闷与期望沉潜、调适或淡化,从而表现出情感强度的“减”和弱化。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燕公中年淹絷江潭,曲江晚亦沦落荆楚,其诗皆多哀伤憔悴。然燕公惟切归阙之思,曲江已安止足之分,恬竞自别。言发于衷,作者亦不自知也。”(40)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4页。认为张说和张九龄二相在被贬后,张说有强烈的“归阙之思”,张九龄则较为安然自适,也正是这两种情况的具体表现。实际上,贬逐士人在谪地的精神状态虽然有别,但恋阙望归的心理期待却是如一的。在他们心底,时刻期望着有朝一日能被召回朝、再展宏图和功业。即使是“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4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29页。的张九龄,其被贬后的诗文中亦溢满“瘴疠之叹”和“拘囚之思”(42)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211页。。而一旦被召还朝或再迁,他们恋阙忠君的衷心、踌躇满志的雄心便在激动的情绪中再度曝光。如张说《四月一日过江赴荆州》:“春色沅湘尽,三年客始回。……比肩羊叔子,千载岂无才。”柳宗元《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4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56、3932页。这种沉潜于贬谪苦闷中的丹心不灭和壮心不已,有力阐释了唐代士人的执着意识和上进精神。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并认为人的需要层次越低,需要的力量越大、潜力越大。对因罪受罚的贬谪士人来说,朝廷的斥逐与弃置,不仅直接削减了他们在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要层面的满足,同时,贬臣的枷锁、谪居环境的荒恶,还造成他们生命自由和安全的缺失,故张说《广州萧都督入朝过岳州宴饯得冬字》云:“京华遥比日,疲老飒如冬。窃羡能言鸟,衔恩向九重。”元稹《江陵三梦》云:“长安远于日,山川云间之。纵我生羽翼,网罗生絷维。”元稹《酬乐天雨后见忆》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4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50、4511、4590页。韩愈《左迁至蓝关示姪孙湘》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4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759页。心理上低层次需要力量的强大,导致他们恋京怀阙的情绪和希望得以拯救的意图最为强烈。
除了贬谪士人,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动乱时期因国之灾难被迫流寓在外的士人,他们对京城的思念也显得情辞悲切。他们并非由于个人的挫败、朝廷的抛置离开长安,在生存环境和生命保障上亦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所以在情感强度上并非如被拘被囚的贬谪士人那样冤屈深重。但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飘转不定,使他们缺乏归属感和逞志报国、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故在其京国之思中,家和国交融在一起,自身的功名诉求与朝阙君王的命运交融在一起。如奉守儒业、生死以之的杜甫,安史之乱后流寓西南,“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46)杜甫:《江上》,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328-1329页。,他的诗作里,家和国、乡与阙相互融通而趋一,思家念亲与忧国怀京两重情感常常相互交织,共同指向对国家时事的关切和忧虑。其夔州所作《秋兴八首》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47)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494页。等,思亲怀乡、忧虑国事、老人迟暮、君恩未报与壮志未酬等诸种情感交融并蓄。对此,有学人论曰:“思乡对于他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家乡意味着亲人,意味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家乡意味着故国,意味着朝廷以及个人的政治生涯;家乡生活意味着一个逝去的、繁荣鼎盛的时代,意味着美好安定的生活。所以,在杜诗中,家乡、故国、兄弟姐妹、故园等等都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诗人晚年复杂的思乡情感。”(48)莫砺锋、童强:《杜甫传:仁者在苦难中的追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5-236页。又如出身关中望族、“平生志业匡尧舜”(49)韦庄:《关河道中》,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7998页。的唐末诗人韦庄,因黄巢农民军攻占京城、僖宗迫走,故于中和二年春离开长安。此后,在其流离飘零的过程中,深慨世乱、有家难归便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情感内容。如《中渡晚眺》:
“魏王堤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妖气欲昏唐社稷,夕阳空照汉山川。千重碧树笼春苑,万缕红霞衬碧天。家寄杜陵归不得,一迴回首一潸然。”《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窜逐同天宝,遭罹异建康。道孤悲海澨,家远隔天潢。……去国时虽久,安邦志不常。良金炉自跃,美玉椟难藏。北望心如旆,西归律变商。迹随江燕去,心逐塞鸿翔。”(5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011、8026-8028页。有国不得报、有家不得归、有志不得逞,皆融会在他对京城的思念里。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们关注的不仅是一己之身,而是朝廷命运、社会安宁、黎民疾苦: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51)苏轼:《王定国诗集叙》,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8页。;韦庄颠沛漂泊,一心梦想“重筑太平基”(52)韦庄:《长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006页。,即使在仕蜀之后,依然摆脱不了对家园故国的思念,时刻企盼与亲人“携手入长安”(53)韦庄:《浣溪沙》,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0074页。。儒学认为家和国不可分,《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4)孟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释:《孟子》,第120页。之后《大学》又明确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观,将个人、家庭与国家三者紧密相联,给予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身经离乱的杜甫、韦庄对长安的思念,除了含有对个人温馨宁静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唐代恋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更高远的思想境界。
三
无论是唐代士子普遍怀有的“长安梦”,还是贬逐、流寓士人的归阙之思,皆缘于唐人执着的事功追求,其背后的精神本质即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唐代道教、佛教得以重视并颇为流行,但儒学仍是一国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根基。加之科举制度的有力推行,使得唐人心怀济世之志,奋进于仕途、汲汲于功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儒释道三教合流,使得士人在坚守儒业、追求功名之外,亦普遍重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即使在意气风发的盛唐时期,亦有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55)刘昫等撰:《旧唐书》,第5052页。般的吏隐情志、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6)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第1103页。式的抽身还林。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继之的却是政治革新的破产和王朝中兴的破灭。宪宗以降,宦官坐大、党争加剧,朝堂政治更是险象环生。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情势下,有的士人出于惧祸远害,选择退隐闲居、独善其身,从而导致对长安一定程度的退避和疏离。如韩愈元和二年因避馋自请离开长安,他在《东都遇春》中说:“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穽。”(57)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第484页。白居易屡次自请分司东都,在分司任上作《赠谈客》云:“上客清谈何亹亹,幽人闲思自寥寥。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清琴正调。”(58)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第2266页。皆道出了远离“长安事”的幸运与满足。还有的士人怀才不遇、欲仕不能,最后心生疲倦,回归自我,走向山林。如顾况《长安道》写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严维《送丘为下第归苏州》亦云:“无媒既不达,余亦思归田。”(5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2941、2923页。然而,这些诗人都怀抱入世之本心,渴望建功立业,“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60)刘禹锡:《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672页。,只是他们远离政治旋涡、调节内心矛盾、保全个体生命的权宜之计;求仕不得、却归沧浪,也只是他们迫于时局、为了安顿一己之身而作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政治和现世总是难以释怀。在中晚唐的场屋之中,我们看到的仍是在长安孜孜以求的士子,如“九试泽宫,九黜有司”(61)孙樵:《骂僮志》,董诰等编:《全唐文》,第8337页。的孙樵,“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的许棠。无论迎难而上,还是无奈退避,唐代士子都不曾真正放弃对京尘和仕宦的眷恋,从而表现出“为儒逢世乱,吾道欲何之”(62)韦庄:《寓言》,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020页。的矛盾与痛苦。
除此之外,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还可从以下几个时代因素中获得解释。
首先,汉唐长安的雄风繁华和政治意义造就了唐代士人心中的长安情结和盛世情结。唐代以前,古都长安在汉武盛世时最为辉煌。作为统一帝国和强大王朝的象征,其繁盛壮丽的形象在汉代京都赋中有浓墨重彩的书写。汉代的两都之争中,长安因其山河地利的优势,被视为帝王育业、霸王衍功之地,在政治上承载着“王气”和“武功”的文化意义。唐朝的都城长安,既在魏晋六朝长期分裂之后恢复了统一王朝的帝京身份,同时又是李唐王室的军事根据地,其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象征意义益发浓重。《大唐新语》卷八载,“太宗常制《帝京篇》”,命李百药“和作,叹其精妙”(63)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3页。。此《帝京篇》描绘长安的壮伟形象和唐太宗安居帝京的宫廷生活,并在篇末表达“虚心”、“诚敬”、“纳善”等为政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篇帝王雄心和皇权威严的政治宣言。据《墨池编》所收《碑刻·唐记》:“唐太宗御制《帝京篇》,贞观十六年岑文本撰,褚遂良书。”(64)朱长文:《墨池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5页。知其问世后即以碑刻的形式得以流传,可以说,皇居长安坐镇全国的帝都姿态和中心意义在李唐江山得以稳定后即被及时强调和昭示。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朝廷面向各阶层广泛取士,“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于投身官僚层;科举入仕者以适合官僚政治为主,地方代表性质较低,士族子弟将以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求取晋身,大帝国由此获得人才以充实其官吏群”(65)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人才的笼络、士族的分化,皆以皇权的巩固和京城的壮大为中心。此时的长安既是拥有历史辉煌和文学记忆的长安,也是继汉之后具有王朝新气象的长安。所以,当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等人来到长安求仕时,皆思接汉武,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帝京篇》、《长安古意》、《临高台》等诗表达他们对长安的感知和体验。他们感叹汉唐长安的繁华和权贵骄奢,在历史世事变迁的思索中,生发风光须臾、富贵无常的感慨;又因个人不遇和贤士沉沦,一抒愤慨寂寥之胸臆。岑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云:“因送故人行,试歌《行路难》。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66)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第65页。即使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长安、思考人事,长安仍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仕途情结和最终理想。当他们离开之后,长安的形象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了忆长安、望长安、梦长安的情思。他们的一切仕途活动,如干谒、远游、从军、入幕、奉使等,也最终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安史之乱后,王朝由盛转衰,中晚唐士人对长安的情感,不仅有个人仕途的寄托,还表现出对开天盛世的怀念。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大历四年左右鲍防、严维、丘丹等人在越州所作《忆长安十二咏》。诸位诗人同题分月,就一年各月长安最具有特征性的城市景象进行了一次集体追忆,再现了大唐社会繁荣和政治清明的盛世图景,其创作背后的心理动因,即文人士子对盛世不再的叹恨与缅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67)王建:《故行宫》,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423页。,“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68)李洞:《绣岭宫词》,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302页。,这种盛世情结不仅成为中晚唐时期社会性的普遍情结,亦是诗人笔下咏及长安的重要情愫。尤其是在晚唐的咏史怀古诗中,唐玄宗、杨贵妃、华清宫、骊山等盛世人物和古迹成为诗人追思逝去王朝的重要媒介。
其次,这一心态与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代士大夫忠君恋阙的人臣之节密切相关。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一方面成功削弱了门阀士族势力对皇权的制约,将大批文人士子输送到官僚阶层,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从而圆了古代学子“学而优则仕”的梦;另一方面,科举制对庶族寒门的吸纳和士族官僚的分化,也使唐代的官员失去了与君主专制相对抗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实力。科举出身的文人士大夫,必须依赖君主的恩典得以保全,其官职成为皇权的附庸,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唐代士人的事功理想,与帝王和事君紧密联系在一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69)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74页。贯休《闻征四处士》云:“一诏群公起,移山四海闻。因知丈夫事,须佐圣明君。”(7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350页。皆体现了唐代文人以在阙佐君为最高理想和政治归宿。忠君弘道,本是儒家所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到了唐代,与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相结合,使得唐代士大夫政治理想中的向君意识和恋阙情绪至为浓厚,杜甫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71)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65页。并非夸饰之辞。出仕的唐人一旦有所授任,即身受朝廷之命、天子之恩,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君主的笼络和控制,即使是贬秩降职,皆要上表叩谢皇恩。唐代的官员无论在朝还是外任,亦普遍恪守臣道,重视忠君爱阙的名节意识。贞元中,席相出刺泉州,“欲因恋主,向北瞻瞩。惟北有楼,半倾半摧”,于是命工重新修筑,以“展北面拱辰之心”,当地文士欧阳詹撰《泉州北楼记》大赞:“夫完城壮邑,有邦之本也;恋阙爱君,为臣之节也。善矣哉!公广兹楼也,远得有邦之本,近贞为臣之节。执邦之本曰公,谨臣之节曰忠,唯公与忠,公斯昭矣。”(72)董诰等编:《全唐文》,第6035-6036页。可见,在唐人看来,事君弘道,为臣义;忠君恋阙,即臣节。
再者,唐人在官职选授上重内轻外的观念直接导致了恋京心态的普遍性。为利于统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和尊卑观念。唐王朝为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在职官制度上亦以京畿为威、重内轻外,故唐代的州依地理位置划为辅、雄、望、紧若干等,县亦依地望轻重分为京、畿、望、紧若干等。虽然唐代历史上有少数帝王如太宗、玄宗重视治人之本和刺史县令的选任,但总体上仍不能改变唐人以京官为荣而轻外职的观念。即使是闲散的东都分司官,在唐人眼中也不失为恩遇荣宠之职。张说不附太平公主被罢相留司东都,他在《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序中说:“太极殿众君子,分司洛城,自春涉秋,日有游讨。……若夫盛时、荣位、华景、胜会,此四者古难一遇,而我辈比实兼之。”(7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70页。明确称分司职为“荣位”。王建《寄分司张郎中》云:“江郡迁移犹远地,仙官荣宠是分司。”(7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3407页。认为与外郡相比,分司之“荣宠”可谓为“仙官”。在官职迁转上,若由外入内,唐人誉之为“登仙”(75)郑处诲撰:《明皇杂录》,郑处诲、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东观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页。;反之,由京出外则被朝廷作为处罚官员的主要手段。除了典型的降罪贬逐,一般的出京外放通常也是对无才不贤者的一种责罚,《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即载,“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京官有犯罪声望下者,方遣牧州”(76)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8、1419页。。这使得唐代官员普遍薄居外任,“纵使超资,尚多怀耻”(77)唐玄宗:《京官都督刺史中外迭用敕》,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08页。。中晚唐时期频繁出现的宰相出镇,其中也有相当不少具有被天子摒弃、左迁贬降的性质,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浓厚的恋阙思京情绪。如李逢吉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在驻所梓州建望京楼,登台赋诗。郑从谠出镇岭南,“以久在番禺,不乐风土,思归恋阙,形于赋咏”(78)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169页。。相应地,时人的送别诗对朝中要员出守也持以“同情”心理,无可《夏日送田中丞赴蔡州》即云:“出守汝南城,应多恋阙情。地遥人久望,风起旆初行。”(7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9155页。而一旦被召还朝,以赴京、归阙为主题的送别作品,则普遍表现出昂扬、畅快或者艳羡的情绪,如李中三《送阎侍御归阙》:“羡君乘紫诏,归路指通津。鼓棹烟波暖,还京雨露新。趋朝丹禁晓,耸辔九衢春。自愧湮沈者,随轩未有因。”(8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8536页。
总之,在唐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多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时期士人普遍浓厚的恋京情绪。这种情绪直接渗透到士人创作中,便衍生出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赴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唐诗中的“长安客”、“长安梦”、“长安日”等并非个别和简单的意象。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分裂动乱,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未形成,京城还不具备像唐代长安那样对士人们的集体向心力。加之社会动荡、政局多变,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使得士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生死、游仙、隐逸等关乎个体生命的主题。唐代之后,各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生活、人生态度、时代风貌均发生变化。而且,封建社会至宋而走下坡路,理学、心学先后得以发展,唐人身上那种高昂的理想、喷涌的激情和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已经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对现实社会、实际人生的关注和反思,宋人傅梦得《许村》即云:“人生要行乐,何苦恋京尘。”(8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90页。故而唐代士人对“京尘”的眷恋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是我们解读唐人精神风貌和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