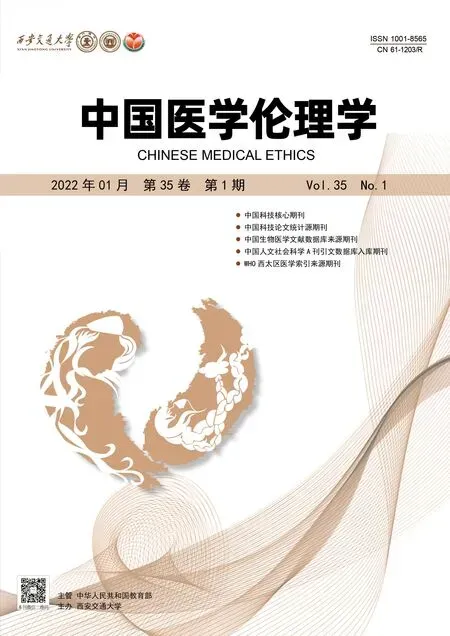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域外电子健康素养研究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牛佳雯,曹竞予,张艳双,冷 滨,尹 梅,张 雪**
(1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940848428@qq.com;2 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3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织科,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4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
近年来电子健康迅速发展,“互联网+医疗”、智慧医疗、精准医疗等在为人们带来健康资讯的同时,医疗信息良莠不齐、专业性术语理解困难、信息难以甄别等弊端也日益凸显。特别是现阶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下,公众响应国家前期居家隔离、后期防疫常态化的要求,如何保障获取有效、可靠、可信的健康信息,也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鉴于此,为提高我国公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电子健康素养培养路径,使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受复杂、专业的医疗信息影响,需要借鉴域外电子健康素养研究经验,提高公众在互联网中甄别、理解、评价和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为今后我国公民应对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
1 电子健康素养的内涵界定
电子健康素养(electronic health literacy)是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领域下的子概念。健康素养的概念最早在1974年由Simonds在国际健康教育大会上提出。2000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NLM)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人获得、理解和处理健康信息或服务,并作出有益于健康的决策能力。世界卫生组织经过发展完善,将健康素养定义为:个体促进与保持健康的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反映,不仅只是个体的识字能力、健康知识、健康态度的表现。此观点将健康素养的内涵再次深化[1]。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面对庞杂繁复的网络健康信息,如何行之有效的搜索、甄别并加以利用已经成为进一步展开研究的方向,电子健康素养的概念应运而生。电子健康素养,由加拿大学者Norman和 Skinner加以定义,是指从电子资源中搜索、查找、理解、评鉴健康信息,并将所获取的信息加以处理、运用,从而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
根据上述概念,电子健康素养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电子健康素养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即电子资源的使用用户,包括根据身体状态划分的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根据医疗角色划分的医方与患方、根据卫生环境划分的常态人群与被隔离人群等,都需要借助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以解决自身问题;其次,培养电子健康素养的目的是通过提升用户的基本素养、健康素养、信息素养、科学素养、媒介素养和计算机素养,利用电子资源深度挖掘真实可靠的健康信息,循序渐进的完成相关健康知识积累,提升用户实践健康行为成效[2];第三,电子健康素养可以被测量,通过量表等研究方法能够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进行评价,有针对性地提高低水平人群电子健康素养,使其在网络资讯中真正获取有效、可信的健康信息,从而改善自身健康行为。
2 域外电子健康素养研究经验
2.1 多维视角扩宽电子健康素养研究体系
域外电子健康素养从测量量表开发、电子健康素养和健康教育、患者服药依从性、患者生活质量关系方面开始展开多维度研究。2006年加拿大学者Norman等以英国为背景研制了eHEALS量表用于电子健康素养测量,通过8个简短条目作为规范电子健康健康素养基本衡量的标准[2]。为了能全面的评估数字素养和健康素养,2015年Furstrand等根据Norman的电子健康素养概念,开发了电子健康素养评估工具包(literacy assessment toolkit,eHLA),从用户使用计算机的动机、信心、熟练程度、具体操作以及功能性健康素养、健康素养自我评估和健康素养实施等7个方向进行综合测量[3]。2018年Kayser等自行界定电子健康素养概念和框架,并以使用技术来处理健康信息、理解健康的概念和语言、能够积极参与数字服务、感到安全和控制、动机与数字服务、访问数字服务工作、适合个人需求的数字服务等7个评测方向为基础研制电子健康素养问卷(e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eHLQ)[4]。除量表研制的多视角探索外,近年来随着“智慧医疗”“远程医疗”等诸多热点话题的兴起,学术界从单一研究差异化群体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向多维视角分析、探索电子健康素养作为中介因素与其他健康领域概念之间的联系及其起到的作用转移。
电子健康素养与普及健康教育、患者服药依从性、患者生活质量等健康概念息息相关。电子健康素养直接影响居民通过网络对健康信息的获取,健康教育是一种有效改善电子健康素养的方法[5]。电子健康素养直接反映了个体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并作出相关健康决策的能力,电子健康素养高的患者能够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从而有效地与医护人员沟通,遵从医嘱进行药物治疗,其服药依从性相应较高[6]。有关于心血管患者电子健康素养的研究发现,通过提高电子健康素养,可以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7]。此类研究对电子健康素养与其他概念进行多维分析,从不同视角对电子健康素养进行区别研究后的结果更具有普适性,为日后建立成体系的、脉络清晰的电子健康素养培养路径奠定基础。
2.2 应用网络健康信息服务工具
由于网络资讯更新频繁,为了及时提供准确、真实、有效的健康信息,网络健康信息服务工具成为公众日常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最早的健康信息服务系统(CHIS)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问世,主要应用于医疗生态圈的健康信息服务工具,包括综合性信息服务系统和健康信息评价系统等。发展到现在,随着电子健康概念的提出与广泛应用,健康信息服务工具的使用不再仅限于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在2017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和维基百科被认为是最具知名度的互联网医学信息源[8],除了图书馆与搜索引擎,大量医学健康网站、健康应用App、健康信息系统等健康信息服务工具接连诞生,旨在为公众搜索、甄别、利用医疗信息扫清障碍,在信息交互中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自身健康。
实践证明,为了有效预防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提高公众防护意识、实施正确的健康行为,灵活应用健康信息服务工具是公众提高电子健康素养的重要手段[9]。有研究表明应用CHESS系统改善了乳腺癌患者的健康状况,有效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处理医疗信息的能力[10]。还有研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应用健康信息服务工具会对身患癌症、糖尿病和心理健康障碍等疾病的患者的诊疗产生积极影响[11]。
2.3 实施电子健康信息应用干预措施
2018年美国和日本两国专家分别实施的电子健康素养干预措施为例。其基本做法是:由医生、护士和营养师等专业的医疗领域工作者作为培训人员,对接受干预的试验者进行为期2~3周的电子健康素养课程培训,课程内容包括评估信息源网站的可靠性、评估网络信息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教授社交网站的健康信息注意事项、处理健康信息时存在的认知偏见和观点以及高质量健康信息应具备的特征,试验者每天需要完成10分钟左右的学习,并通过测验及时了解掌握情况,以此增强电子健康素养获取、理解和评估信息技能;当干预措施的主体是患者时,学习对象是由政府和医院主导的高质量专业健康网站,在开始前医护人员会就如何操作、使用网站进行培训,患者需要持续访问相关网站3个月以获取健康信息,遇到问题时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这种干预方法有效避免其他网站上的不良资讯影响患者对正确信息的吸收运用[12]。上述措施是提高电子健康素养以促进网络健康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健康全球战略的有效途径。
3 对我国的启示
3.1 加强不同视角电子健康素养研究
我国电子健康素养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主要围绕通用量表的本土化应用、新量表的开发以及发展综述展开,研究对象主要是居民。我国居民主要借助百度等搜索引擎获取健康信息,对于互联网信息满意度较低,对其真实性普遍持中立态度,关注较多的健康信息类型是食品安全、养生保健、医疗保险、卫生法规以及药品信息[13]。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迅速发展及智能手机日益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了互联网和科技带来的便利,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然暴发使人们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许多“数字移民”“数字难民”在疫情期间因无法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付款、出示健康码进出公共场所而寸步难行。在“互联网+医疗”时代,首先,应对研究群体进一步细化,对“数字移民”与“数字难民”加强重视,对其电子健康素养培养路径条分缕析、深入探讨[14]。其次,应当在健康领域扩展至其他研究主题,进一步研究电子健康素养在健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间的中介作用,深入剖析电子健康素养培养途径中针对性干预措施以及应用效果,为我国公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常态化防护以及未来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3.2 完善电子健康信息官方交流平台
新冠疫情暴发,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对疫情防护相关知识的需求较高,居民只能通过电视和网络等信息渠道获取疫情信息。其实,在疫情期间,国内接连涌现了大量传递真实、及时、准确健康资讯的网站和社交工具App,向社会大众传递病毒传播途径、预防方法、检测、治疗和医保政策等相关健康信息。但是由于此类健康信息服务工具的社交用户主要为年轻群体,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尤其是老年群体他们使用率最高的即时通信软件是微信,微信上的相关健康信息繁杂,容易传递错误信息使得老年人盲听盲从,危害自身健康。
为了防止居民因虚假健康信息泛滥以及医疗信息商业化造成的互联网健康信息乱象从而影响健康信息的选择和运用,产生误导甚至威胁生命健康,面对这些制约电子健康素养水平的因素,亟须在现有健康信息服务工具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官方发布健康信息、用户交流互动的便捷网络平台。这是疫情发展下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公众电子健康素养理性应对未来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迫切需要。
3.3 应用干预措施开启健康服务模式
在“互联网+医疗”环境下,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影响,对电子健康素养的干预措施可以借鉴域外采取的有效培训方法,将其与线上信息服务工具相结合,灵活适应疫情背景下减少聚集的要求。目前,已有较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线上医疗健康服务,如使用远程血压仪、可穿戴设备等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服务方式,通过此类新信息技术能够打破医疗服务的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保持与医护人员的健康信息交流,减轻在网络搜索中对信息的评估、甄别与处理产生的压力,但很多研究都忽视了线上线下服务的关联,因而难以实际应用于现实情境。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由于国内移动医疗和远程医疗等线上健康服务方式尚不完善,受现实因素制约,患者的大部分问诊、咨询过程依旧需要在线下到医疗机构完成;另一方面,鉴于患者群体的首要问诊对象主要趋向于三甲医院,大医院轻症重症患者扎堆、小医院访问者寥寥的恶性循环使得患者线下咨询健康信息动辄排队数小时乃至数天,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在线上解决健康问题,节约时间与金钱成本,因此仅从“线上”或“线下”的层面提供健康服务已不能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期待。
将线上线下健康服务方式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健康服务新模式,有利于公众评估健康信息质量,便捷高效的获取可靠、准确的健康信息,加强患者教育、自我管理和疾病预防,提升公众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安全系数。
4 结语
“非典”、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不利影响,如何使公众在面对此类事件时能够高效地获取防护、治疗、政策等方面的健康信息并加以处理运用、维护自身健康安全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域外转变电子健康素养研究视角、提供高质量健康信息服务工具以及对公众进行干预培训等措施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我国的电子健康素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国内针对电子健康信息服务板块还存在空白区域,国外在针对健康干预时电子信息服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结合我国国情,首先,国内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数字移民”与“数字难民”电子健康素养的深入研究,并展开对电子健康素养中介因素的探讨,完善电子健康领域理论研究;其次,应当由政府支持或建立高质量医疗健康信息服务网站,为公众提供及时、可靠、准确、真实的健康信息,降低网络医疗资讯甄别利用难度;最后,有效整合线上线下的健康信息服务,为培养公众良好的电子健康素养创造有利条件。